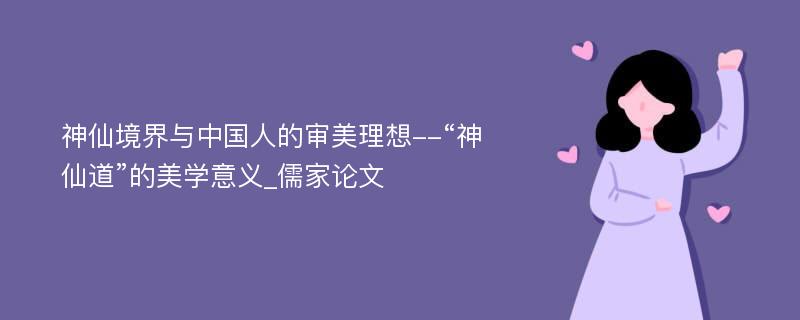
神仙境界与中国人的审美理想——神仙道教的美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神仙论文,美学论文,境界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2-0060-07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鲁迅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话是极为深刻的。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其中主要为儒、道、佛。这三者在其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融入,但也不是没有抵触。相比之下,道教吸收、融入其他文化是最为全面的,道教对于儒家文化基本上是全盘接受,对于佛教文化长期抵制,但元代的全真道一改旧轨,于佛教文化的核心——“空”多有接收并予以改造。在中国历史上,汉以后,唐、宋、元、明均是宗道教的,但明以后,道教的确是难以挽回地衰落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道教,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美学史研究均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显然,这是一个缺陷。本文试图对于道教美学的核心——神仙境界做初步的探讨,求教于方家。
一、本体的衍变:道神之间与神人之间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虽然人们一般将它的理论源头溯到先秦的道家,但实际上它的理论源头不只是道家哲学,而为多元,这其中,肇自先秦而盛于秦汉的神仙学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元。神仙学的内涵也是丰富的,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庄子的寓言为其一,远古巫术、秦汉方术、图谶为其二,黄老之学中的养生之道为其三。老庄哲学作为道教的基础理论最终神学化,与秦汉的神仙学融为一体,使得原为民间巫术系统的道教上升为具有士大夫品格且为统治阶级所青睐的神仙道教。神仙道教产生于魏晋,原只是与民间道教相拮抗的一支,然而后来发展成为道教的主流,民间道教也融入其中。这样,神仙道教也就不只是具有士大夫的品格而具有全民的品格。道在道教中具体化为仙,这样,道教中的仙如同儒家中的圣、佛教中的佛,成为某一思想体系、信仰体系的本体。道教其实并不是不可以称之为仙教。这里涉及三个重要的问题:
其一,“道”的神化。什么是“道”,在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与庄子那里是清楚的,道是宇宙的本体。老子认为,道可以从“无”与“有”两个维度来看。从“无”的维度来看道,道是“天地之始”;从“有”的维度来看道,道是“万物之母”。“始”与“母”其实是一个意思,但隐隐地让人感到“无”才是根本。关于这点,老子没有明说,王弼在阐释《老子》时,则明确指出“以无为本”。“无”的含义很丰富,无形、无色、无味,抽象性、无确定性、自由性、无限性……隐隐地,“无”通向了“神”。“神”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有抽象义,也有具象义。抽象义为神秘、神奇,变化无穷不可把握,《易传》云:“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具象义则是神人、神灵。最高的神灵就是上帝①,它是创物主,也是制物主。在《老子》,道的神化是潜隐的,主要取神的抽象义——神秘、神奇。
《庄子》基本上也如此,但《庄子》论道时喜欢用文学的手法,当它用故事来言道时,不自觉地将道神化为神人了。不过,这在《庄子》是不自觉的,而且,它说“神人”,也说“至人”、“真人”,其实,“至人”、“真人”也是神人,三者没有什么区别。在《庄子》中,神人(包括至人、真人)最突出的地方有四:一是超越生死:“不知说生,不知说死”(《大宗师》),“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二是功夫非凡:“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人火不热”(《大宗师》),“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齐物论》)。三是自由潇洒:“骑日月,乘云气,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四是青春美丽:“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逍遥游》)。神人之所以能如此,原因是得道。庄子如此描绘神人,目的是突出道的伟大,没想到,却是将道化为神人。
其二,神的人化。庄子讲的“至人”、“真人”、“神人”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想象中的神,不具现实性。庄子这样做,无意将至人、真人、神人看做人。他想象出这样的至人、真人、神人来,只是为了说理。在《庄子》中,至人、真人、神人均是某种理论的象征。
真正将神人化的是葛洪。葛洪是晋人,他是实现道家理论到道教理论过渡的第一人,可以讲是道教理论的奠基者。
葛洪著《抱朴子》,首章为《畅玄》。开篇云:“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也,而万殊之大宗也。”这里说的“玄”即道,葛洪表述为“玄道”。“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这里,将“道”归之为“用”,“用”又为“神”。这就等于将“道”看做“神”了。这里的“神”取神奇、神妙义,但这神奇、神妙是“人”用出来的,这用道的人自然就是“神人”了。道为人用,道即在人。那么,道如何才能为人所用?葛洪强调“知足”:“知足者肥遁勿用,颐光山林”。何以见得“知足”?“肥遁勿用”。如何见得“勿用”?就是“颐光山林”。“颐光山林”做什么?“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就是修道。修道达到一定的程度,“恢恢荡荡,与浑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与造化钧其符契”,就成神了。
庄子谈神人是为了释道,绝不是希望人成为神人,庄子不看重人,为了得道,他甚至认为人应“黜聪明”,变得像傻子一样,而且最好是“堕肢体”,身体毁掉了,甚至化为轻烟都不要紧。而葛洪完全是从人的角度谈道的,人得道上升就成为神人。这神人,不是彼岸早就有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修炼成的。它的本体是人。在人成为神人之后,不是傻了,而是更聪明了;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畅玄》结尾一段说得道的人“嘿韶夏而韬藻帨,奋其五羽于五城之墟,而不烦衔芦之卫。翳其鳞角乎勿用之地,而恃曲穴之备。俯无倨鵄之呼,仰无亢极之悔。人莫之识,邈矣远哉”。
其三,人的仙化。神仙两个概念经常并在一起用,其实神与仙是不同的。神字为“示”旁,它重在灵,远古的神大多为自然神,不具人形,当然也有祖宗神,具人形。仙字为“人”旁,说明仙原本是人,人在山里经过修炼之后成为了神,这神就叫做仙。
制造一个神灵的世界是一切宗教共同的特点。但道教与别的宗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道教认为普通人可以成仙。人成仙有三种情况:“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抱朴子·论仙》)这三种仙中,地仙一直生活在红尘之中,然而它不会死。天仙虽然主要生活在天上,但是只要他有兴趣,可以随时下凡来。尸解仙虽然死过,但复活了,复活了人可能是别的模样,但不要紧,重要的是活着。
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活人可以成仙,成仙后仍然活着。人既然可以成仙,那如何成仙呢?葛洪强调学仙有法。整个《抱朴子》谈的就是学仙法。神仙世界就这样出入于神与人之间、此岸与彼岸之间、红尘与世外之间。它将这个之间定位为“仙界”。
道教虽然以道为本体,在它的学仙理论中也有内丹之学,强调清静无为,以道家的道来观察世界,来认识生活,来领悟养生,但是,这一切均是为了成仙。所以,道家的道在道教这里不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降为“体”之“用”、“本”之“末”,真正为本体的不是道,而是仙,道教其实可以称之为仙教。
二、主体的演绎:超越性与世俗性
道教将道本体演化成仙本体,这是道教对道家根本性的改造。道是抽象的,仙是具象的,道是理,仙是“人”。道的演绎充满着哲学的思辨,而仙的故事则充满着审美的情趣。所以,道教对道家的这种改造是美学化了的,径直说,道教就是一种非常美学化的宗教。
道教的核心是神仙,从某种意义上,整个道教就是围绕着成仙而展开的,成仙是修道的最终目的,仙是道修的最高境界。仙是活生生的存在,因为它就是人,长相与人相似,生活与人一般,故而充满着现实亲和性,然而它又是奇异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充满着精神的幻想性。仙可瞬息现身,又可瞬间消失,谁也说不清它在哪里,但谁也可以说他恍惚中见到过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比仙更奇幻也更美妙的了。
仙具有怎样的形象?我们可以用两个维度来说明它的本质:
第一,超越性的维度:这种超越性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1)对自然力束缚的超越。这里最为突出的是对生死的超越。道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关于此,《抱朴子》中的《塞难篇》说得最清楚。葛洪说:“天地虽囊万物,而万物非天地之所为也。譬犹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鱼鳖之托水泽以产育,而水泽非有为焉。”葛洪由此申发:
由兹论之,夭寿之事,果不在天地,决在所值。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犹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适,姿容必妖丽,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远,多致我气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尫弱,或且黑且丑,或聋盲顽嚣,或枝离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况乎天地辽阔者哉?……故受气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余则莫有亲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皆不能损益于我矣。天地亦安得与知之乎?(《抱朴子·基难》)
葛洪的意思很清楚,天道无为,并不管人生死,“圣人之死,非天所杀,圣人之生,非天所挺”,“贤不必寿,愚不必夭”。生死问题与天地即与自然无关,生死操纵在自己手中。如果修道,不仅可以长寿,而且可以不死。既然生死都可以超越,那体能更能超越:
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神仙传·彭祖传》)种种凡人所不致的本领神仙都有。
(2)对社会力束缚的超越。人生活在社会中,行为受到种种社会力的约束,在封建社会,最大的社会约束力是王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只要做了神仙,皇帝管不着了,更不要说各级官吏。《神仙传》中的河上公“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可见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道教的这一思想隐含着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叛逆。
超越性的必然结果是自由。神仙的生活是完全自由的,而且这种自由具有绝对的性质。虽然神仙的自由性是虚幻的、想象的,但是它仍然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美的本质就是自由,自由总是意味着肉体的解放和精神的解放。所以,神仙的故事总是让人津津乐道,这种津津乐道正说明人对自由的向往,虽然神仙的自由并不等于人的自由,但是神仙的自由让人向往,更何况神仙也是人修炼而成的,所以,在相信道教的人看来,这种自由并不虚幻,它是人的一种美丽的理想。神仙自由的本质与审美自由的本质的切合,使得神仙在人类的审美生活中居于最高的精神层面而富有无限的乐趣,以致成为人全身心的信仰。
第二,世俗化的维度:神仙的形象实际上是两个极端的无限延展,一是超越性,向着自由飞升;二是世俗化,向着享乐深入。这里,突出的是对人欲的肯定。中国的几大文化学派:儒家(教)和佛教对于人欲均是限制的,儒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欲看成修身之大害和治国之大害,种种言论教人节制人欲。《周易》有一个节卦,专讲节之道理。佛教有诸多的戒,其中大多数的戒,是对人欲的限制。道教的理论前身道家也反对放纵人欲。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主张“少私寡欲”。但道教中神仙却不是这样,他们对于人欲,极尽奢华之能事,吃的是山珍海味,奇珍异馐,食之不饫。由于道教将房中术视为修炼成仙的重要法门,神仙世界美女如云。李白想象中的仙界:“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②
人欲满足的是人的身体的需要。身体的地位在道教中得到突显,这是耐人寻味的。中国先秦儒家和道家重视的均是人的精神。儒家一直将品德的修养看得至高无上;道家重自然,讲究天放,实际上也只能在精神层面,其“逍遥游”也只能是精神上“上下与天地同游”。两家没有一家将身体看得重要的,孔子讲“舍身成仁,杀身取义”,身体比之精神实在没有什么地位,庄子强调在精神上与万物一体,甚至可以置肢体于不顾,说是“堕肢体”。而道教非常重视身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当与汉代的文化形态有关。经过极端残酷的战争建立起来的大汉朝,自然十分看重肉体生命的重要,以养生为主旨的黄老之学趁时而起。自朝廷到百姓,莫不将保身养生置于重要地位。汉代皇帝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不死之药,为神仙之学的兴盛和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人们突然发现,相比于精神,肉体才是最为实在的。生命虽然可以分为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但肉体生命是基础。“立功”、“立德”、“立名”之三不朽何如身体之不朽。
形而上的精神旁落了,形而下的身体突出了,是是非非一言难尽。仅就美学来说,它的意义不可小觑。众所周知,审美的本源是感性,美学原初即为感性学。不管哪种美,如果不能作用于人的感性器官,首先成为人的感性的享受,它就无法登上审美的殿堂。美的最高层面须达至理性,然而其基础层面却是在感性,而且即使达至理性,其理性也必须与感性相融汇,成为感性的理性,此种审美的形态称之为境界。道教神仙境界融汇了感性与理性两者。它虽然重感性,但并不是仅停留在粗糙的自然性的状态上,而是将感性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体现为自由性的愉快。
这里,理性对感性的调节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只是看到神仙生活肯定人欲的一面,没有看到它还有节制人欲的一面。如何节制?就是积德行善。(《抱朴子·微旨》)葛洪痛斥了诸如“弹射飞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不公不平”、“求欲无己”等等恶行、劣行,认为这些人成仙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道教的神仙虽然重人世间的享乐,但这种享乐却是以德行为灵魂的。
另外,对于房中之术,葛洪认为这是严肃的事,他痛斥巫书妖妄之言“奸伪造作虚妄,以欺诳世人”,说:“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抱朴子·微旨》)即他不认为房中术能致神仙,但是,如果能够“善其术”,能够“令人老有美色,终其天年”。关于房中术,他从理性的高度认识它的价值,他说,古传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不可尽信,且黄帝升天成仙有多种原因,决非御女此单一原因。他郑重地说房中之事“玄素谕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于能用与不能耳。大都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两人足以速死耳。”(《抱朴子·微旨》)这些话说得非常到位。
神仙本质探寻的两个维度,超越性体现神仙非人的本质一面,世俗性体现神仙人性的本质的一面。神仙的本质就是非人与人的统一,概括地说,他们是超人。
神仙生活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浪漫主义,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审美理想。
三、环境的建构:山林之中红尘之外
不仅神仙的生活是美的,神仙居住的地方也是很美的。如果说,神仙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看做人的审美理想,那么,神仙居住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做是环境的审美理想。
神仙是自由的,可以说居无定所,天上人间均可以自由徜徉,自由居住。但是,他们还是有相对比较固定的生活场所,这种场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天宫、龙宫等,二是昆仑山、海上三神山等,三是桃花源之类等。这三种场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世俗性,也就是说,它们基本上都是按照人间的模式来设计的。这三类场所,第一类完全是虚幻的,不管描述如何逼真,天宫在九霄云外,龙宫在水底深处,均是人无法去的,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二、三类,因为这两类场所就在地面,诸多寻仙的人千方百计要寻找的就是这类仙境。
昆仑山的神话由来最早,影响也最大。神话中记载昆仑山是西王母住的地方,这里有异草琼花、珍奇异兽。但实际上的昆仑山却是长年积雪,不是人能生活的地方,所以,没有人去昆仑山寻仙。流传的穆天子去昆仑山访西王母的故事纯粹是神话,不能用来指导实际的寻仙问道,不论是从神仙学的维度,还是从环境美学的维度来看仙境,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三座神山和桃花源之类的仙境。
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齐国的方士在绘声绘色地宣扬了。据说山上有让人不死之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寻找不死之药曾派方士徐福去找过这三座仙岛,但一无所获。汉代,关于三神山之美有着绘声绘色的描绘,激起人们无限的向往。
桃花源是东晋诗人陶渊明散文《桃花源记》中所描绘过的仙境。陶渊明并没有说此为仙境,但是住在桃花源的人历秦汉魏晋数百年而不死应称为仙了,他们居住的地方当然可以称为仙境。历代诸多的遇仙故事也描绘过与桃花源相似的仙境。
仙境尽管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但有人发现,山东渤海有几个与三神山相类的海岛,就认定它们是蓬莱、方丈、瀛洲。陶渊明写的桃花源,人们找到好几处,最有名的当属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虽然后人所找的仙境不是仙境,但仙境的传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仙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环境美学思想,仙境基本性质:在人间又非人间。在人间,指适合人居,具有宜居性;非人间,指它与社会隔绝,因而不受社会,包括官府的种种干扰,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保证了它的绝对安全性。这两性是仙境的本质。环境美学以家园感为环境美的本质,作为家的环境,其生活性与安全性无疑是首位的。仙境的人间性与非人间性正好充分地揭示出理想家园的这一性质。
仙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然风景极为优美。这反映出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审美传统:崇尚自然美,而且这种崇尚达到的程度是自然美至高无上。美好的自然风景总是以生态优良为首位的,而所有的仙境均为动物、鸟类与人杂处,且各不相扰,人与鸟兽相得而生,共处而乐,这种情景正是生态优良的体现。仙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和谐美满,《桃花源记》写桃花源中的人们“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渔人误入桃花源,人们均热情款待,“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两个重要特点,前一个特点体现出环境宜居的性质,后一个特点体现出环境乐居的性质。中华民族对于居住环境,其最高追求就是既宜居又乐居的仙境了。
第二,仙境常被人们用来作为园林建设的理想范式。最早将海上仙山引入园林的是秦始皇,据《元和郡县志》:“兰池陂即秦之兰池也,在县东二十五里。初,始皇引渭水为池。东西二百丈,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汉代神仙术盛行,汉朝的皇帝笃信神仙,在宫殿建设中更是注重将神仙传说中的一液三山引入园林。汉武帝建章宫,在西北部辟一水面,为太液池。在太液池中堆起三座山,象征蓬莱、方丈、瀛洲。唐代建大明宫,又在宫内筑太液池,在池中建三神山,规模较汉代更大。以后的各个朝代,亦情况不一地将各种不同的仙境引入园林,不仅是皇家园林,还有私家园林。“一池三神山”更是成为园林建设的一种范式,沿用至今。著名的园林学家计成在《园冶》中将仙境入园作为一条重要的造园理论,说是“境仿瀛壶,天然图画”。
从种种有关仙境的描绘与介绍中,按今日的环境哲学的要求,道教的仙境体现出这样的重要内涵:第一,环境与人的统一。任何环境都是人的环境,肯定人,肯定人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所有的仙境都体现出来了。《桃花源记》中的仙境几乎就是普通的农村:“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闻。”第二,生态与人的统一。生态重在生命之间的动态平衡,古人没有现在的生态观点,但是,他们懂得人须与万物共荣共生。班固在《西都赋》中说长安的皇城“蓬莱起于中央”,俨然仙境,在这中间“灵草冬荣,神木丛生”,飞禽走兽,潇洒自如,与人共处。
中华民族对于环境一直非常重视,这种重视具体展开为两种理论:一为风水,二为仙境。二者其实可以统一在一起,最为优秀的风水宝地,其实就是仙境。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水学、仙境说,其主要的来源为道教。在中国诸多流派的文化中,道教对于环境理论的建构贡献最大。
四、结语:生命的浪漫
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体,儒家文化将人看做社会的人,注重从社会维度来认识人的本质。既然人是社会的人,人须对社会承担责任,而且这责任非常之多,小而言之是家庭,大而言之是国家。而为了承担起如此多的责任,人需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这修养名目繁多,且要求很高。儒家认为人皆可为尧舜,也就是说,它是按照古代圣王尧舜的标准来要求人的。如此二者,儒家分别称之为“外王”、“内圣”。儒家这样一套人生哲学,让所有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生命之重。换句话,儒家的人生不乏忧国忧民,不乏请命继绝,不乏慷慨悲歌,不乏鞠躬尽瘁,不乏可歌可泣,不乏崇高伟大,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却少了几分自由,少了几分潇洒,少了几分真性,少了几分快乐。
而有了道家、道教,特别是有了道教的神仙之学,儒家知识分子就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他做人的缺陷。不仅能尽做人的责任,而且能尽做人的乐趣。此生就不算白费了。这方面,苏轼算是楷模。苏轼主心骨为儒家哲学,而且他一直沉浮宦海,但是,苏轼也出入了仙、禅之间,领略别一样的人生。禅的洒脱、灵变,对于聪明的苏轼来说,自然是鸟在青天鱼在水,得其性也;但是,羽化登仙的理想一直是灵犀一点,心向往之。
所以道教的神仙之学可以讲从根本上激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意识,让他们明白,原来生活还有这般情趣,这般意义。
如果说用一个核心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本土的三大文化儒家、道家、道教文化,我认为,儒家尚善,道家尚真,而道教尚美。至于外来的佛教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分别吸取了儒家、道家和道教的营养,尤看重心性的灵变。我认为,如果用一词来概括,“灵”差可用之。
说道教尚美,主要在它的神仙之学,之所以以美来概括神仙之学,主要原因在于它对于生命的价值有着新的开发。儒家对于生命价值的开发,主要在生命的外在意义上,即人的社会责任,将人对社会的奉献摆在首要地位。道家与道教对于生命价值的开发,是一种向着人自身的内在的开发。二者相通的地方在对自由的珍重。所不同的是,道家的自由感限于精神上,而道教的自由感则不仅在精神上,还在身体上,其突出的体现就是对自然生死的突破和对自然体能的突破。这样,人生的意义就不在对社会的奉献上,而在自我享受上。而众所周知,对于生命的自我享受正是审美的本质,任何审美,不管是优美还是崇高,亦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究其根本是对生命的品味。
看道教的神仙谱系,有个有趣的发现,最早的神仙是怪异的。神话的制作者似是有意拉开神仙与人的距离。那居位在昆仑山上的西王母,有着老虎牙齿、豹子尾巴,自然是可怕的,然而,后来,这位西王母则美化为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了。在晚起的神仙中,仙风道骨成为神仙的标准形象。吕洞宾在众多的故事中被塑造成这样一位仙人典型。诗人李白也因为拥有这样一副相貌和风度而赢得人们的赞誉。无形中,男性美的标准给树立起来了,那就是仙风道骨。大约从汉代开始,出于史前原始宗教信仰的人与兽共体的神仙形象消失了,男仙形象也一改原初的怪异,即使貌丑,也丑得幽默,如八仙中的张果老。美,成为神仙共同的品格。自东汉,女仙在神仙中多了起来,而且在后来的描绘中,越来越美丽。仙女的美丽,最早见诸文学描绘的是曹植的《洛神赋》,洛神是仙。曹植在赋中描绘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拂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这些描绘后来几乎成为仙女模样的范例。仙女——最美丽的仙!于是,神仙成为美的典范,这样,神仙道教就不仅具有真的品格、善的品格,而且具有了美的品格。这种全方位开拓生命意义的文化,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哲学;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美学。
因为有了道教的神仙之学,中国的文化就多了几分浪漫!而浪漫是生命之灵光,犹如太阳之霞,树木之花,飞鸟之翼,走兽之姿。正是在生命全方位意义上,我们给予道教神仙之学以最高的评价。
道教的神仙之学对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是注重实际的民族,但也是注重理想的民族。儒家的实践理性与道教的审美感性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我将这两者的统一概括为“尚贵羡仙”,作为中华民族的审美的传统之一。③就尚贵来说,中国人认为做官为贵,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贵,从小就有这种出人头地的想法,但一方面总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做官,另一方面做官也有诸多不易,甚至有很大的风险,这就为道教的神仙之学留下一个很大的地盘。神仙多栖隐山林,隐士均为神仙的候选人,即使成不了神仙,做隐士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快乐。欧阳修提出人生有两种快乐:富贵者之乐,山林者之乐。富贵者为官者也,山林者,隐士也,神仙也。富贵者之乐,乐在出人头地,社会地位高,为人尊敬,当然,这乐中实际上含有诸多的忧与苦,它不只是享受,陶醉,也许更多的是责任与奉献。欧阳修当然深懂这一点。山林者之乐则不一样了,它也许不出人头地,甚至不为人知,但是,它在物质生活上一点也不缺,精神上也自有追求,最重要的是无拘无束,无忧无虑,逍遥、潇洒、飘逸、自由。最高境界则羽化登仙,超脱了生死大劫。这种山林者之乐难道不更胜于富贵者之乐吗?欧阳修岂不明白此?尽管如此,欧阳修为什么不弃官去做隐士呢?这就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冲突了,现实毕竟是现实,它活得扎实;理想毕竟是理想,它活得不扎实,二者不能全得,这就难怪欧阳修慨叹“其不能两得,亦其理与势之然与”。虽然不能两得,但又不能两分。做着官的知识分子总是恋着富贵者之乐,又向往着山林者之乐,而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总是在自诩着山林者之乐之时,又向往着富贵者之乐。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就是这样在“富贵”与“神仙”二者之间游动着,内在地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注释:
①中国上古有“上帝”的说法,通常相当于天帝,为中国古代所认定的最高神灵。他不是三皇五帝中的“帝”,当然更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②李白:《游泰山》。
③参见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附录·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8页。
标签:儒家论文; 葛洪论文; 美学论文; 道教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文化论文; 庄子论文; 读书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桃花源记论文; 抱朴子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