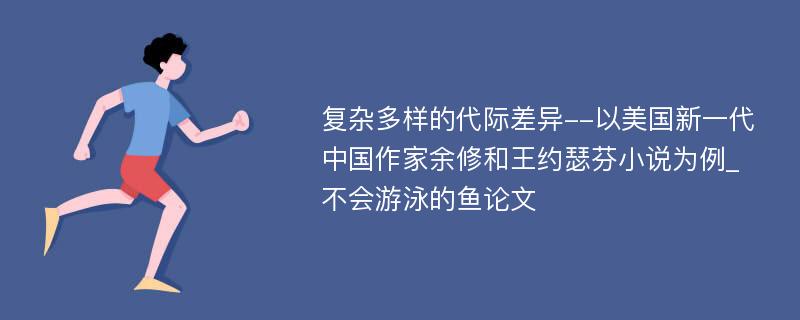
复杂多样的代际差异——以美国新生代华文作家郁秀和王蕤的小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美国论文,新生代论文,差异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5-0108-06 郁秀、王蕤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被称之为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新生代作家。郁秀的代表作品有《太阳鸟——我的留学我的爱情》、《美国旅店》、《不会游泳的鱼》等,王蕤则以《哈佛情人》、《纽约旧事》、《相聚欧罗巴》等作品享誉华文文坛。她们的小说都以美国华人移民或留学为背景,应是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一部分,但在与查建英、严歌苓、张翎等这些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的比较阅读中,可以发现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异特征。对这种代际差异的发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美国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 一、郁秀:展示新生代移民平和、平等的异域体验 郁秀笔下的主人公移民时的年龄都较小,比如《美国旅店》中的宋歌赴美时年仅十二岁,《不会游泳的鱼》中双胞胎兄妹海海、丁丁的年龄是十五岁,《太阳鸟》中天舒赴美留学也就是二十岁(和郁秀赴美时的年龄相近),也就是说,整个美国移民背景参与了主人公们的成长,成为了他们走向成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这一年龄阶段移民群体的关注,目前在新移民作家中并不多见。郁秀选择这个特定的年龄阶段,除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之外,或许与其创作期待视野中的隐含读者大有关联。在《美国旅店》和《不会游泳的鱼》的封面介绍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广告语:“你不一定让你的孩子去美国,但是你应该让你的孩子读读这本书。你如果要让你的孩子去美国,你应该和你的孩子一起读读这本书。”也许这是传媒时代的一种营销策略,利用郁秀在国内的成名作《花季雨季》的青春因素,来迎合出国潮中父母和孩子的阅读期待。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种商业上的模式化操作有可能使作家走进创作瓶颈。如果说《太阳鸟》让我们听到了新移民文学中青春的声音,那么《美国旅店》就是一首新移民文学中的青春之诗,而《不会游泳的鱼》则更像一本背景置换的美国版《花季雨季》,仍然是一本成长类的青春读物。但不管怎样,在当代中国持久不衰的出国潮中,的确存在着小留学生队伍,他们的留学经历、移民感受,必然会带有他们成长时代的烙印,在新移民文学中,这一领域也的确鲜有人发掘,从这个角度而言,郁秀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1.平和的“物质”心态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如火如荼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东西方物质层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独生子女而言,不大可能再次出现上一辈移民作家笔下的“天堂”美国。在查建英的中篇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当“我”发着高烧“36个小时一口饭没吃,饿得眼冒金星,连肠子里的苦水都吐干净了,还在干呕”时,美国所预示的神圣意义,填充了“我”所掏空的一切,“第一眼看见美洲大陆绿悠悠的影子,浑身上下的病倦疲软就一扫而空。第一脚踏上美国土地,就口鼻清爽,行走如飞。”①与新时期的第一代移民以改善物质生活为出国第一目标相比,美国,对于郁秀小说世界中的小移民们而言,已经剥去了神圣的光环,他们在丰裕的物质面前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平和。“天舒来美国几乎谈不上什么深刻的第一印象或第一感觉,甚至没有身处海外之感。当阿晴表姐问她感觉如何,她说:‘没感觉。我不觉得自己出国了。美国不过如此。’”②这种平和可以算作一个明显的代际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新生代移民看来,美国不再是一个物质巨人,也不是自由的天堂,它和中国一样,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来美国就是为了学习,为了成长,为了发展,可以留在美国,也可以再回到中国。对他们而言,所要做的只是选择以及选择之后的行动,这可以称之为物质自由之后的心态从容。这种异域体验在《美国旅店》中也有流露。《美国旅店》中,十二岁的小姑娘宋歌,下飞机时印象最深刻的,并非是美国的物质丰富,而是六年后母亲相遇时的那种生硬和牵扯。虽然宋歌从一进门就两眼大瞪,好好地打量这套母亲拥有的大房子,但最终的评估结果是,“不是妈妈有这么大的房子真好,不是我在美国可以住这么大的房子了,而是妈妈竟然住这么大的房子”③,一个“竟然”消解了大房子所象征的财富光环,凸显出的只是母女亲情的不适和隔阂。由此可见,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小留学生,出国时已经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来到美国后已不再将物质生活的改善当作移徙的主要目标,因而在一种基本没有生活落差的流散状态中,他们的心态十分平和。 2.平等的差异认知 追求在族裔之间建立一种尊重差异的平等关系,应是新生代移民的另一个特征。在上一辈作家的创作中,这种平等的实现更多的意味着艰难、曲折甚至绝望。如严歌苓的中篇小说《栗色头发》中,女主人公为了维护自己的种族尊严,毅然否决掉了美国佬的爱情和殷勤,展现出“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可丢”的气概,尽管它们对她而言,在那种艰难的情景下,有着“必需”的意义;而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作家更是极度渲染了平等得以实现的曲折,甚至不惜牺牲掉一份生命,才换回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平等与理解。而在十几年之后的郁秀和王蕤的小说世界里,平等已经开始意味着实现和享受。《太阳鸟》中,黄、白、黑,三种肤色组合而成的小天地,在天舒眼里就是一个小小联合国(姑且让我们省去“联合国”的象征意义)。在这个世界中,“相处也算融洽”④、“三个室友相处还算不错,彼此包容”⑤,也就意味着彼此之间并没有因为种族不同,肤色相异而感受到歧视和不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毫无差异⑥,有差异也就会有交流的障碍,所以天舒才会“从不觉得自己真正介入过”,“与她们的交往总是隔靴搔痒”⑦。《美国旅店》中,宋歌与继父犹太爸爸之间就是一种由于平等交流而逐渐深入、最终融合的关系,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严歌苓的《红罗裙》和《花儿与少年》,除了题材上的相似性之外,我们也能在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中体会到严歌苓一代和郁秀一代之间鲜明的代际特征。严歌苓笔下继父与子女之间是剑拔弩张的压迫与被压迫,反抗与被反抗的殖民关系,甚至在《花儿与少年》中,少年宁愿以死相挟也要换回平等与自由,但这些在《美国旅店》中已经获得了根本性改变。犹太爸爸温文尔雅,面对无理取闹、无计可施的继女,最激烈的情感反应仅仅是:“麻烦你以后多多提醒我这一点,好让我知道自己多么幸运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儿。他突然声音一粗,却十分慢条斯理地说。这样一来,它的台词味才充分显现出来。这是大卫对我说的最重的话”⑧。这里的“最重”和严歌苓笔下的继父、子女剑拔弩张的关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除此之外,异族夫妻关系在《美国旅店》里也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不管当初的结婚动机如何,在整个婚姻过程中除了有一点异域色彩之外,看不出种族之间的冲突,所有的仍然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包容和尊重。“妈妈”时常提醒“我”要尊重犹太文化传统,犹太爸爸也逐渐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不仅在饮食上征服了黑蛋,而且也养成了晚上洗澡的习惯。与《太阳鸟》一样,这种平等依然是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的,“我”的成长就是由于受到了太多的美国性、犹太性的影响以至于迷失于中国性的寻找之中;妈妈和犹太爸爸婚姻最终的分崩离析,也是由于族裔之间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显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它不仅捍卫着各民族的族裔特征,也促进着各族裔间进一步的交流。《太阳鸟》中的差异性,提醒了天舒的中国性;《美国旅店》中的差异性,对于宋歌而言,是一笔财富,不仅让她发现了继父身上所象征的犹太灵魂——“尽管他不是宗教色彩浓厚的犹太人,甚至已经脱离与犹太神学的任何联系;尽管他是美国第三代的犹太移民,已不会说什么希伯来语或者意第绪语,但他的血管里毕竟流淌着犹太祖先的血液,几千年的犹太精神与世俗生活的紧密结合,不可能不渗入他的初始观念与思维模式。比如说他是犹太人,但并不是犹太作家。他不是写犹太人的生活,但在他的作品里,他的犹太气质与犹太痕迹刻在其中。因为在他看来,犹太人的阐释与人类共同的感情并无二致,并行不悖。他把犹太人作为人类的代表”⑨,这也让宋歌在身份归属的迷惘中坚定了方向——继父的犹太灵魂,多少启发了自己心中的中国灵魂。其实这种差异性所带给宋歌的财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整个移民文学都得益于这种差异性。母国所带来的差异性让移民作家们更清醒准确地认识了居住国,而在居住国所体验的差异性又让他们更积极全面地反思自己的族裔文化。于是,这种差异给了他们一种文化审视的高度,有了高度也就有了新视野和新思考。 二、王蕤:建构多重视界的追寻与自审 与郁秀作品中的青春明快色彩不同,王蕤的小说世界仿若是“后青春期的诗歌”,大都通过一些简单的情节、短小却精致的形式,展现出对人性、文化等问题的深刻反思与遒劲批判,流露出对“人”繁杂而又持久的关注。这一特点或许与王蕤的经历有关。在美国多年,王蕤的身份元素既在不断改变也在不断增加,她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当过报纸记者、做过政府翻译、干过专栏作家,也客串过时事评论员。这些不同的工作带给她观察美国社会的不同视角以及审视自身的不同参照系统,进而使她的创作具备了多重视界。 1.跨越中西的追寻 郁秀笔下的宋歌,一个在中国生活十二年,在美国生活十二年的中国女孩(这也许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两种经验、两种文化的产物。她到底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仅是作者的探寻,也是移民文化的探寻。这种寻找的主题在王蕤的作品中有了更强烈的体现。关于寻找,我们当然想到了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未果的尴尬处境。不仅如此,我们还在查建英和郁秀之间看到了关于此类主题的相似性:两篇小说都涉及到了詹姆斯的《丛林下的猛兽》,虽然郁秀只是涉及到了它的主题,还有那句“寻找是寻找不到的,即使寻找到了也不是你想要的”的箴言。我们无意强调查建英对郁秀的影响,我们看到的是寻找在移民文化中的延续。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是可变的,我们不禁假想,在不断地寻找中,宋歌式的移民们能否发现到“新质”的东西,来适应自己新的文化身份。这在查建英和郁秀那里似乎都没有明确的揭示。查建英式寻找的方向,偏向于西方,《丛林下的冰河》中小D的死以及“我”失望的西部之旅,都预示着东方式理想寻找的失败和终止。而郁秀式的寻找轨迹显然更多地偏向于东方,宋歌在父亲死后再次回归,以及母亲痛定思痛式的反思“我希望我当年能做出相反的决定”⑩,都预示着向东方的再次寻找。有趣的是,同样是寻找,王蕤的作品却提供了不同的结局。 在王蕤的《哈佛情人》中,主人公小叶是一个成功的美国人,“小叶的同事和学校都很器重他。他刚到学校不久,就成为了学校明星,获得了最高荣誉——杰出成就奖”,并且还是一个“英俊、正派,充满活力的年轻单身教授”(11),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显然这“牵动了你的中国和你狂野的乡愁”(12),我们的主人公也就理所当然的受到了魔一般的诱惑。但这一切只是一种表象,潜伏在现象背后的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病态和自私,小叶说,“这个世界让我感兴趣的是病态、变态。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还有疯狂,人类的Insanity和Madness,尤其是中国人的”(13),“他余生的目的就是要学会做一个自私的人”(14),于是,“小叶,是细菌,无法察觉的细菌”(15),毒害着“天真”的主人公。这份天真表现在对远方故乡的思念和依恋,“你是一个迷失异乡的族人,突然间听到了乡音,你不会想到危险或者自我保护,你有的,只是甜蜜地向它传来的方向奔去”(16),可是小叶的表象欺骗了你,包括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尽管他曾高歌“我爱中国的义气。/我爱中国人把气节看得高于生命。/我爱士可杀不可辱。/我爱这个浪漫而骄傲的民族。”但骨子里真正钟爱的是“吞金”、“自残”等文化意象所象征的中国文化中最病态的那一部分。于是,最后毫无防备的、被表象欺骗的主人公,飞蛾扑火般陷入了病态的泥淖中,不能自拔,众叛亲离,“和小叶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你的朋友接二连三地离你远去,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所有的只剩下孤独、疯狂和绝望,也许什么都没有,“反正有很多年,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些什么。这是故事的空白,也许正是故事的中心,你彻底埋葬的那部分”(17)。面对着这样极度的空虚和茫然,“你说你去寻找答案”(18),这种寻找的方向显然不是病态的西方,也没有像查建英那样重新回到同样存在着病态的东方,王蕤的视野开始有了超越。这种超越建立在对两种文化和两种经验的反思之上,已不再纠缠于东西方的差异,而是直指具有共通性的人类灵魂。这种追寻,便被赋予了一层人类普适性的意义。 2.多重视界的审视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哈佛情人》的叙述动机。面对着主人公“你”对往事的回避,“我”作为这段往事唯一的旁观者和见证人,显然不愿意像“你”一样选择沉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朋友,每当我回忆起你所拒绝想起的这个故事时,都会无端掉泪,不知为你,还是为他,抑或是为那逝去的青春年少时的轰轰烈烈、疯狂与绝望”(19),“我”要寻找泪水的原因,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为你、也为他、更为我们逝去的青春。 “你”,是一个盲目的寻找者,离别了自己的母国文化,在遥远的思念中,在强大的西方文化殖民语境中,渴望结束孤立的文化困境,渴望认同与沟通,一旦发现乡音,似乎发现了救命稻草,毫无防备地奔向乡音传来的方向。这里显然是对“盲目寻找”的反思,警告着那些“崇洋”者,小心提防“自由神耸立”的美国表象下潜伏的病态和糟粕。 “他”,即小叶,一个地道的,百分之百犹太血统的犹太人,一个不断地在苦难中磨练的民族基因。在郁秀《美国旅店》中的犹太爸爸身上体现的是一个伟大的犹太灵魂,而在小叶身上体现的却是那样的负面,“我的基因里渗透着危机与不安全感。我很艰难去相信别人,向别人暴露我自己”。从这个角度而言,小叶有一定的代表性。犹太人一直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中国人对这一个不断迁徙,不断经历苦难并最终涅槃的民族是一向尊重和敬佩的。这一点我们在严歌苓的《寄居者》,郁秀的《美国旅店》等作品中都可见到,在整个北美新移民文学中,像这样写一个负面的犹太人例子很罕见,尽管表现这种负面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再优秀的民族基因也抵挡不住病态社会的浸淫,民族基因的优秀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成功的表象,但拯救不了在灵魂深处隐藏的丑陋的人性,这就是小叶的象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小叶也是一个寻找者,却迷失在东西方的病态中,也迷失在非洲式的原始与野蛮中,谁来拯救他?故事的结尾,小叶成为了梦寐以求的知名学者,却仍然是孑然一人。这结尾处的孤独似乎暗示着小叶的寻找失败。但在昏天暗地之中,仍然透露着一缕晨光,因为主人公“你”的寻找,似乎取得了成功,成为了一个“快乐富足得令人忌妒的你”。 一个寻找失败,一个寻找成功,一个是表面成功的男性,一个是内心成功的女性,一个是异族,一个是本族,到底意味着什么?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发现”。我们在前面也说过移民文学是一种寻找的文学,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有得有失的发现和寻找过程。但对我们而言,这种寻找和发现的过程只是一种启发和引导,我们最终关注的仍然是反思。反思造成这种发现和寻找所带来的意味的源泉,那遥远的广袤的非洲。非洲,作为相对于母国和居住国而言的第三方文化,对于新移民文学而言,是一种新视野,它超越了两种经验和两种文化的范畴。 在王蕤的《哈佛情人》中,非洲是一种力量,象征着拯救和重生,而在《纽约旧事》中,则象征着一条鞭挞中国文化的鞭子。如果说,在《哈佛情人》中,小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是诱惑者和欺骗者,主人公“你”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受害者的话,那么在《纽约旧事》中,丽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诱惑者和欺骗者,而法玛尔所代表的非洲文化则是受害者。同样,如果说《哈佛情人》是对西方病态文化的反思、控诉和警示,那么《纽约旧事》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鞭挞和警醒。《纽约旧事》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所隐藏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挥之不去的民族劣根性,同时在与《哈佛情人》精心营造的相对中反衬出我们自身的处境与困境。“面对非洲人的本真和不设防,她却无法丢掉她的顾虑,那种中国人的,知识分子的顾虑,她为此感到羞耻。”但她仍然无法跨越这种顾虑,仍然要找一个中国男子结婚。这种顾虑表面上是出于种族文化,但实际上是一种种族歧视。中国人可以和日裔、韩裔、白人结婚,唯独不可以和黑人结婚。詹妮弗,那个和黑人通婚而不敢露面的表姐,就是一个被人耻笑的对象。但是那个被白人抛弃,带一个混血儿子到处招摇的希拉莉表姐却得到了众人的羡慕和嫉妒。这也就表明了不和黑人通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作为幌子的种族不同,而是实质上的经济力量。故事的最后,一个开着宝马牌摩托车的黑人载着一个穿着时髦的十六七岁的中国女孩揭穿了一切精心设计的面具,“老黑,老黑怎么地了?老黑,也架不住有款爷呀”(20)。中国人就这样在金钱面前一层一层脱光了自己虚伪的外衣。王蕤的反思力度是深刻而猛烈的,不仅仅是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移民的根源以及族裔文化的凝聚等问题。而在《相聚欧罗巴》中,这种反思的张力更为强劲。王蕤在小说中坦言,“有些东西,你们摔不掉的,跟东西方无关”,(21)其视野已站在了人类的顶端,所直视的是人类的普遍性。同样有寻求,对精神寄托的寻求,只不过不在区分东和西,无论是西方的西蒙和东方的亚妮,还是处于之间的J,都在追寻,足迹遍布一切人类的心迹。 从《哈佛情人》到《纽约旧事》,再到《相聚欧罗巴》,从西方、东方到第三方,再到整个人类,王蕤的视野一环扣一环的广阔,思考也愈加高远。王蕤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深刻,也感受到了新移民文学的一种新境界,这能否算是以一种“新质”,我们仍在期待中。 三、结语:模糊却不可替代的代际差异 无论是在郁秀身上还是在王蕤身上,我们都体会到了新生代移民的若干新变。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文学,何况现在的代际转换如此之快,我们关注和强调这种代际特征,也就是关注和强调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新动向。有些可惜的是,郁秀和王蕤所受到的关注显然与自身所代表的意义不相匹配。在2008年出版的《一代飞鸿——北美大陆新移民华文作家短篇小说及述评》的文集里,没有出现她们年轻的身影,如果郁秀因为长篇创作的缘故无法纳入短篇小说集的范围之内,那么王蕤呢,这个曾有严歌苓和于青作序的作家,就这样被大家集体“忘却”了。此外,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我们也鲜见文学研究者们对她们的关注。这不禁让我们联想了当代文坛中“晚生代”的集体突围现象,这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个寻找的主题。 其实,我们在这里特意突出所谓的“代际特征”,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聚焦手段,目的是把当下被忽视的郁秀和王蕤,推向前台,推进华文文学的研究视野之中。但是如果从整个新世纪以来的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发展态势来看,郁秀和王蕤的这种“代际特征”并不特别突兀。虽然我们认同“任何一个个体生命,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都是属于历史中的生命存在,“会不可避免地烙下不同时代的文化印记,带有不同历史境遇中的精神征兆”(22)。比如,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所带来强烈震撼和深刻反思,可以出现在之后的《纽约情人》(施雨)、《遭遇9.11》(严力)等作品中,却永远不会在它之前的作品中。同样,上述我们曾经分析过的查建英与郁秀、王蕤在各自的小说世界中,所表现出的追寻视野的方向和范围的差异,也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色,展现出了这种代际差异。但是,当我们把郁秀和王蕤所体现的那种“新质”拿过来,和张翎、严歌苓等作家在新世纪的创作相比较的时候,便发现他们也拥有类似的“新质”。比如在郁秀和王蕤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世界式的深邃的追寻视野,在张翎和严歌苓等人那里,我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甚至由于二人成熟的创作经验,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深刻反思后的震撼会更强烈,更久远。张翎《金山》中的印第安姑娘桑丹丝,严歌苓《寄居者》中的犹太人杰克布和彼得、《小姨多鹤》中的日本人多鹤,作家们分别对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特有的民族精魂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深刻的剖析。 尤其是严歌苓,更是将族群杂居的背景,从久远的北美大陆转移到亲近的母国土地上来,展现异族者在我们熟悉的环境中的种种挣扎,让族群杂处的微妙感受成为我们经验中的一部分,来印证与反思“我们”在寄居地上所表现的种种悲欢与困顿。这种“陌生化”的探索方式,所带来的效果,无疑是振聋发聩的。隐姓埋名,担惊受怕的多鹤,虽然也像每一个中国人那样经历过种种历史磨难,见证过中华民族每一个足迹的艰辛跋涉,但是在与二孩、小环一点点地由陌生仇视到相知相亲的几十年的生活中,却始终没有消泯掉自己身上的“大和”精魂。那同整个生活、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干净光滑的水泥地,那时时刻刻难以忘怀的温顺的鞠躬,还有那处处提防却又时刻见缝插针的叽里咕噜的日语,都预示着在滴水不漏的中国性的包围中,处处保存着并流露着自己独特的族裔特征。当回国的机会终于来到的那一刻,多鹤的毅然离去,虽然有遗憾,有痛楚,但对于一个海外漂泊的游子而言,不能回归母国的怀抱,便是最大的痛苦。严歌苓等海外华文作家对汉语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其初衷恐怕也正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严歌苓怀揣着世界视野,“细心把握中日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微妙异同并公正客观地加以比较和阐发,表达了彼此引以为鉴、提携进化的美好意向”(23)。这种探寻的意向在《寄居者》中,通过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有关苦难与寄居的比较和阐发,也有着清新的表达。正是对这种“美好意向”的追寻与探索,造就出了张翎、严歌苓等作家们在新世纪中所展现出的“新质”。但这种“新质”并不能完全掩盖住,张翎和严歌苓等人与郁秀以及王蕤之间的代际差异,最明显的一个例证便是,张翎和严歌苓对历史叙事的痴迷,对“文革”痛楚的回顾和反思,这些在郁秀和王蕤那里却几乎从没有表现过。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十年来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中,这种代际差异大体上还是存在的,尽管其表现有些驳杂和隐晦。通过对这种代际差异的追寻与比较,有可能突显出郁秀和王蕤这些新生代移民作家所特有的气质,尤其是展现出她们对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独特的存在意义。 注释: ①查建英:《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②④⑤⑦郁秀:《太阳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第31页;第33页;第34页。 ③⑧⑨⑩郁秀:《美国旅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34页;第57页;第207页;第283页。 ⑥此处差异不是“显然意味着与‘白人标准’之间的不同;白人的标准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参照点”,而是“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角度让我们得以避开政治分析——两种行为准则与对方‘互不’相同,缺乏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是由行为准则的冲突所造成的,而二者任何一边都不占绝对优势”,见[美]黄秀玲著,詹乔等译:《从必需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11)(12)(13)(14)(15)(16)(17)(18)(19)(20)(21)王蕤:《哈佛情人》,山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第5页;第15页;第18页;第5页;第16页;第22页;第23页;第1页;第47页;第55页。 (22)洪治纲:《中国六十年代作家群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3)赵修广:《历史洪流边缘的异类人生———论严歌苓的长篇新作〈小姨多鹤〉兼及其它》,《作家杂志》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