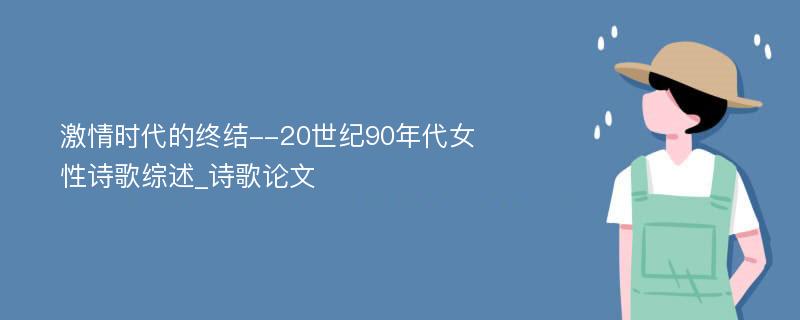
激情时代的终结——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年代论文,激情论文,女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是诗歌在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夹缝中重新寻找出路的时代,接受者的 文化心态与审美取向的转移,其它文学样式和文化样式的挑战以及诗人们自我的重新定 位和新诗艺术探索在路向选择上的迷茫,这种内外夹击、内外交困的情形促使新诗的发 展走向了低谷。然而在整体的冷落、萧条中,女性诗歌却一枝独秀,没有一般“世纪末 ”的颓唐、衰微和没落。相反,经过80年代必要的发育和自觉的奋进,它依然处于生机 勃勃的发展期,在众语喧哗后的灰色大气候中稳步前进,迎来了新的辉煌。
这辉煌有三。一是女诗人队伍的进一步壮大。“常青树”郑敏进入90年代,向晚愈明 ;80年代一批风头正健的诗人——翟永明、唐亚平、伊蕾、张烨、海男、陆忆敏、张真 等,非但没有美人迟暮,反而日趋圆熟;另有一批起点高、视野阔的沃土新蕾——蓝蓝 、虹影、杜涯等的加盟,使得90年代的女性诗歌呈现出花团锦簇、群芳争艳的繁荣景象 。二是诗人心态的练达与平和。较之男诗人们,女诗人们在商品化潮流面前似较为平和 与从容,她们较少那种在金钱面前的“躁动”和在通俗文学面前的“改嫁”,表现出寂 寞中的坚执。翟永明对“鬼诗”的热爱,在寂寞中寻求与心灵、与世界对话的自觉的探 求与自觉的突进正是女性诗人良好创作心态的表征。三是牢固的女性立场的确立。女性 主义精神不再是随意的自觉。张烨面对“真善美是一种巨大的受难/是进行的战争中汩 汩流注的鲜血”(《我很旧,但我存在》)这一“深遭围困”的处境,做出了“我很旧, 但我存在”的倔强回答。王小妮“现在我想飞着走”(《活着·台风》)的对于永恒超越 的企望,庞音“我被男人别在胸襟去参加历史的舞会”(《划地为牢》),马丽芳“你被 省略会思考的头颅/……/只剩下肥大的臀部”(《维纳斯的挽歌》)中对女性历史性命运 的理性追问,张烨“那个男人在怒吼:/我原不想要你死/只想射杀你的灵魂”(《灵魂 杀手》)中对个人灵魂的主动坚守无不昭示了牢固的女性立场的确立。
当然,所有的辉煌都须由创作本身来体现。90年代的女性诗歌既关注人的本质与生存 处境,又尊重诗歌艺术发展的循序渐进的演变规律;诗中既包含较强烈的忧患意识,又 闪现着耀眼的理想光辉。女性诗歌也因此告别了丰富中的贫乏,冲破了“一间小屋”的 狭小空间而步入了火树银花的大格局,诗歌终从奔波流浪的“在路上”回到了休养生息 的“在家中”。
一 向“传统”家园的回归
大格局之一首先体现为女性诗歌向传统、向“东方”精神的一定程度上的回归。面对 一些年轻人一度的数典忘祖现象,郑敏曾郑重提出:“21世纪的文化重建工程必须是清 除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轻视和自卑的偏见。”(注:均出自吴思敬:《九十年代中国新诗 走向摭谈》,见《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与此同时,青年诗人也纷纷对传统进行了 新的思考:“在中国的现时,传统意义是首先的”(注:均出自吴思敬:《九十年代中 国新诗走向摭谈》,见《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在现时的中国最大的创造就是 对传统的继承”(注:均出自吴思敬:《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见《文学评论 》1997年第4期。)。诗界这种普遍的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在女性诗人们的创作中自然也有 所渗透。如何面对传统、如何衔接传统成为此时女性诗歌新的生长点。一些女性诗人开 始借助对一些传统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名胜古迹的吟咏,对一些独具东方特色的传 统意象的描摹,对有节制的抒情方式的恢复与拓展,用日趋澄明的语言表达,来昭示对 传统文化的积极追寻。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诗歌在内容、题材上向传统的“移情”。 二是诗歌在精神向度上对传统道德情操的追随与认定。三是诗歌表达方式上的扬弃,包 括叙述语言对自白话语的取代以及由此产生的日趋明朗、澄明的语言面貌的转变。
先说诗歌内容上向传统的靠拢。以翟永明为例。《道具和场景的述说》、《脸谱生涯 》、《时间美人之歌》、《编织行为之歌》、《三美人之歌》这几首诗,前两首是以中 国传统戏曲为题材的。“一炉沉香焚着一台的宁静/脸谱和脸谱疾走不停/潦倒的我唱一 出《夜奔》。”(《脸谱生涯》)可见,翟永明对传统戏曲是如此的熟谙。后三首也取材 于中国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时间美人之歌》写赵飞燕、虞姬、杨玉环三位美人。 《编织行为之歌》也写了三位古代女性:黄道婆、花木兰、苏蕙。《三美人之歌》写了 三位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孟姜女、白素贞和祝英台。单取材这一点便可以说明 翟永明已将视线投注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某种认同与回归。同样的倾 向还表现在唐亚平的《侠女秋瑾》、《才女薛涛》、《美女西施》中,也流露在张烨的 《长恨歌》、《大雁塔》、《半坡女人》等诗作中。
其次,如果说翟永明式的回归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外在的转向,相当多的女诗人则更深 地将“回归”诠释为对传统美好情操的呼唤与追寻。
诗人李琦在一首题为《一个字》的短诗中写道:“我这一生其实多么简单/从这个字出 发/又向这个字走去/世界你静下来/听我轻轻地吐出这个字。”生命在她那儿是如此明 白纯粹,那点点滴滴只浓缩成一个字——“爱”。而“爱”在张烨笔下则多了份飞蛾扑 火般的悲壮,从而呈现出“复杂的美丽”:“轰轰烈烈地爱过/倒下也是壮烈与凄美”( 《雨夜》)。到了李小雨笔下,“爱”又变得那般细腻、灵动、别出心裁:“逃来逃去 的眼睛/蛛网捕不住的/黑色精灵/它兴奋的羽毛/在最深的红晕背后/闪闪发亮/……/用 子弹追不上它/用歌声追不上它/当猎人无望地转过身来/却发现/它正轻轻地/落在那颗 心上。”(《逃来逃去的眼睛》)多么新鲜活泼的想象!诗人把眼睛从人体上分离出来, 把它羽化为活泼、灵动甚至显得调皮的小鸟,由小鸟又引出猎人——“情人”,故意渲 染“子弹”、“歌声”都“追不上它”,正“山重水复”之际,却忽地“柳暗花明”, “却发现/它正轻轻地/落在那颗心上”。新奇现代的意象中突显着一种传统的具有崇高 感和浪漫情调的爱情美。
对崇高母爱的还原也是此时女性诗歌的一大主题。曾几何时,对于多数新生代的女诗 人而言,“母爱”几乎是一种带有奴性烙印的旧式妇女美德。其实,“母爱”是根深蒂 固的人性的一个方面,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人类文明、伦理及各方面的理想与审美。郑敏 这位世纪诗人就曾满含希望地说:“女性写作如果能在关心解除性禁锢,自由发挥女性 青春魅力之外还能探讨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修女特丽莎那种爱人类的境界和精神,和 生活里一些默默无闻的单身母亲的母爱,就会达到更高的层次。”(注:郑敏·《诗的 交响·历史·人》序言第5页。)她的诗集《诗的交响·历史·人》中整个第五卷《母亲 没有说出来的话》展示的就是一位母亲、祖母心灵深处对青少年和儿童的难以磨灭的挚 爱。还有诗人李琦多年来也一直以爱心经营她和女儿的温馨世界,她的《异乡的雨》写 得分外感人。作者从在异乡淅淅沥沥的雨中想起在家的小孩子开始,很快进入了有关雨 与孩子的细节:“那双17码天蓝的小水靴/那小水靴从不放过每一处水洼/它兴奋地充满 了弹性/我的雨具齐全的小女儿/永远湿淋淋地回家。”想念女儿“就忍不住伸出手臂” 抚在雨中陌生孩子的肩头,“陌生的孩子,惊异地回首/唇角一弯/那是一粒草莓的笑容 ”,于是,雨中的一切都化做了温柔。这是一个由善意和爱共同构筑的世界。
第三是诗歌语言面貌上向明朗化、澄澈化的转变。仍以翟永明为例。她的诗歌语言明 显减少了咬牙切齿、险象环生的阴冷,而多了份步入成熟后的大度与雍容。她在《<咖 啡馆之歌>及以后》一文中曾说“通过写作《咖啡馆之歌》,我完成了久已期待的语言 的转换,它带走了我过去写作中受普拉斯影响而强调的自白语调,而带来一种新的细微 而平淡的叙述风格。”(注:《<咖啡馆之歌>及以后》,见《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翟永 明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而在这新的叙述中,成语的引用是最引 人注目的。比如“穿云裂帛的一声长啸——做尽喜怒哀乐”(《脸谱生涯》)中的“穿云 裂帛”和“喜怒哀乐”,用在表现传统戏曲文化的《脸谱生涯》中,妥贴雅致。类似的 还有“狼烟蔽日,剑气冲天”(《时间美人之歌》);《三美人之歌》中也大量引用:“ 她修炼千年的肉体和/涉世未深的灵魂”等。还有诗中较多引用或化用古诗的诗句,也 给诗歌语言增添了一缕古典澄明的气息。如《编织行为之歌》中反复引用并贯穿全诗的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时间美人之歌》中的“浮动着暗香的热汤”、“动地 的鼙鼓声”等,均显示了从语言角度对传统旨趣的回归。“从《女人》的有些罗嗦唠叨 到后来的结实精准,毫无疑问,翟永明作为一位优秀而重要的诗人日渐趋向练达甚至炉 火纯青。”(注:杨远宏:《灵魂蜗居或者诗歌作坊》,见《诗歌报月刊》1998年第12 期。)
还有,“语言魔女”海男的诗歌语言也日趋澄明,诗的语句之间不再互不关联而有了 连续性。她的爱情诗《花园第八十二首》整首诗都很美雅,很好解读:“等待着你在有 一天的清晨/突然从花园归来/你满身露水和香气/你把芳菲带回故乡/故乡便是花园”。
二 向“现实”家园的回归
大格局之二便是女性诗歌先锋性的淡化以及相应的向现实的一定程度的回归。如何面 对现实、如何呈现现实成为女性诗歌的另一大主题。程光炜给诗歌做了这样的定位:“ 它是个人困境和生存焦虑的强烈的表达”,“诗歌不排斥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相反,它 始终处于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包括世俗生活多种知识交叉性的争辩与对话中。这决定 了它对时代是负有责任的,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在场’。”(注:程光炜:《我以为的 九十年代诗歌》,见《诗歌报月刊》1998年第3期。)邹赴晓也说:“现代诗人应该清醒 地意识到,如果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写作,他必须而且能够自觉、主动地在他的写作中呈 现出当代性因素。”(注:邹赴晓:《一个时代的特征及个性化写作》,见《诗歌报月 刊》1998年第3期。)一些女性诗人也不得不重新思考“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功能, 把视线从女性经验的细处、深处向外辐射,直面更为广阔的现实人生。可见,女性诗歌 的这一“俯就”是顺应整个诗歌大潮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对陈超“深入当代”口号的 积极响应。
在创作中,它首先体现为“使命感”的复归。以舒婷为例。“蒿草爬上塑像的肩膀/感 慨高处不胜寒/挖鱼饵的老头/把鼻涕/擤在花岗岩衣褶/鸽粪如雨。”(《最后的挽歌》) “佛头着粪”一般指亵渎神圣。塑像是为英雄、模范、领袖塑造的,是道德典范的象征 ,体现着某种神圣性。而在利欲熏心者看来,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可以消解,可以买卖, “不如抛向股市/买进卖出/更能体现它的价值”。此外,诗中还充斥许多光怪陆离、荒 诞离奇的诗句,而这正是现实中多种怪现象的集中反映与抽象概括。“都市和农村凭契 约/交换情人”,“列车拉响汽笛人未停靠/接站和送站相互错过/持票人没有座位/座位 空无一人”,“一个吻可以天长地久/爱情瞬息名称”。这些诗句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种 种乖谬、荒诞、错位、悖反等怪现象。尽管诗中运用了反讽、揶揄、嘲弄的手法,表现 出一副玩世不恭的姿态,但读者透过表层看到的仍是一颗赤子之心:“我的诗需要我的 国土,我的祖国是我永远的支撑”(注:舒婷:《当下的诗歌问题》,见《诗歌报月刊 》1998年第12期。)。
从“黑夜”里走进90年代的翟永明则悄悄掀开了咖啡馆、酒吧等当代生活的门帘,给 我们展示了一幅不平静的现代都市生活图景。然而,我们随着诗人进入现代都市生活场 景的同时,感受到的却是它那种表面上的五光十色同实际上的精神贫乏所形成的巨大反 差。她看见了“世界正生活在/买醉的过程”,却又热衷于与那些影子式的当代“他者 ”“压低嗓音交换/呼机号码和黑色名片”(《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她清醒敏锐地 痛感自己的“身体被时间剖开”,却又将自己交给当代不断去扒揭甚至交给“抽签”。 这种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描述,显然包含着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审视。由于现实关怀 的驱使,她的审视是十分严峻的。
当然,此时的向现实回归的诗歌并非等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诗歌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诗歌从总体上呈现出了生活化、日常化、平民化的色彩,一种平常的充满个人焦虑的 人生状态代替了以往充斥诗中的大声疾呼。我们从中体验到通常的、尴尬的甚至有些卑 微的平民的处境。“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们是读者的朋友 。”(注:谢冕:《丰富又贫乏的年代——关于当前诗歌的随想》,见《文学评论》199 8年第1期。)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作为女性诗歌的基本表现对象,越来越多地为女性 诗人所重视。因为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细节,恰恰是人们千百年来未曾变 化的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根基,它们真正地承担起了与时代、与人性对话的重任。因 此,“诗从来就不是日常语言的一种较高形式,恰恰相反,日常语言是遭遗忘因此也是 被用罄了的诗”(注:马丁·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0年版。)。“女人用诗营造世界就像营造自己的家居环境一样,使诗与存在与日常生活 统一于身”(注:唐亚平:《语言》,见《诗探索》1995年第1期。)。这种由日常经验 而生发的真实可靠的声音,自然蕴藏着深奥的哲学、美的光华和生命的智慧。
女性经验日常化是一个有效的明证。90年代,女性的神秘、内在、不可穷尽,对女诗 人来说,依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女性经验的日常化是她们既继承抒写女性身体的传统 也有别于80年代女性写作的重要标志。最典型的一例莫如唐丹鸿《看不见的玫瑰的袖子 拭拂着玻璃窗》:“红窗帘扭腰站定到角落/白窗帘哗的一声敞开胸襟/扁平透明的玻璃 乳房/朝老板和秘书响亮地袒露”,一天就这样充满情味地开始。性在唐丹鸿等一些年 轻的女诗人笔下已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它就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这里 ,唐丹鸿为女性经验的抒写找到了一个不同凡响且能为读者接受的突破口。
在王小妮笔下,对平民卑微处境的揭示中还饱含着诗人对凡俗人事的顿悟以及更可贵 的“纸里包不住”的理想之火。在《活着》一诗中,诗人以一个“心平气和的闲人”的 形象出现:“阳光走在家以外/家里有我/这个心平气和的闲人”。接下来就写日常生活 琐事:“一日三餐/理着温顺的菜心/我的手/飘浮在半透明的白瓷盆里/在我想别的时候 /已经把白色的米/又煮成了白色的饭”。几乎是用纯白描的手法,叙写了日常生活的琐 屑。以下继续写她没有痕迹的日子中的百无聊赖:“不为了什么/只是活着”,得过且 过中不沮丧也不愤激。另一方面,她实不甘心“就这样平凡地活着”,因此她于择菜、 淘米、做饭之际,“试到了/险峻不定的气息/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并“卒章显其志 ”:“我的纸里/永远包藏着我的火”。冷漠、平淡的外表内包裹的还是一团奔突不息 的理想之火。因而,崔卫平称赞王小妮“在陷入日常生活的种种琐事之后还能保持自己 独立的天地”(注:崔卫平:《苹果上的豹》编卷者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王小妮的另一首《晴朗》也表现了同样的意旨:诗人在包围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的形体上的沉溺与精神上的突围。总之,无论是温柔地投入,还是不着痕迹地挣扎,都 透着从容与大气。
在女性诗歌垂下一只臂膀深深插入现实大地的时候,诗歌的表达方式也由此发生了自 然的转变,叙事成了最佳选择。女诗人们开始活用口语,再造叙事,回归日常语言的大 地并激活出生疏的力量,以富有寓言性和戏剧性的细节与经由选择而控制有度的叙述, 直接进入存在,敲击存在的真髓,同时注意对意象与意绪的诗性升华,以“高僧说家常 ”的手法,追求文本内语境透明而文本外有弥散性的张力。
这一转型——由诗性的歌唱转为诗性的言说,由想象界转为真实界,不只是找到了一 种与当代人生命素质更相适应的表层形式,同时更表达了对一种生命形式的寻找——本 色、真实、直面存在,体认普泛生命的脉息和情绪,投射出健康而富有骨感的人格魅力 。这种叙事性口语化的言说所形成的“冷抒情”格调,具有更单纯的力量和更高的内涵 ,它对读者心灵的冲击,甚至远远超过了某些“煽情”的诗句,成为一个真正广阔而坚 实的开放场。另外,这一转型也促使女性诗歌表现域的大跨度拓展,它所生发的语言澄 明、硬朗之美,也是对抒情传统的繁复之美的极为重要的补充。因此,这一转型成为90 年代女性诗歌的又一大突出贡献。
翟永明《我策马扬鞭》可谓成功运用叙事手法的始作俑者。“我策马扬鞭在有劲的黑 夜里/雕花马鞭在我坐骑下/四只滚滚而来的白蹄/踏上羊肠小道落英缤纷/我是走在哪一 个世纪?哪一种生命在斗争?”“我”不是位斗士,只是位真正的梦幻骑士。“我”“在 痉挛的冻原上”“纵横驰骋”,不是要寻找寇仇交锋,而只是在踏勘梦境的疆域。正因 如此,那些无一不与血腥、暴力有关的场景便显得格外触目惊心。它们在诗中如一连串 电影镜头般次第掠过,直到最后隐入“一本过去时代的书”。这本书上“记载着这样的 诗句”:“在静静的河面上/看呵来了他们的长腿蚊。”在诗人透彻目光的逼视下,一 切都将归于“寂静”和“安息”,包括“风波险恶的历史”。这些陈述与叙事,不是简 单地说出一种事实,而是要在这种事实中发掘出生活中某些左右和支配人的潜在的势力 或思维方式,而这种潜在的东西则往往是生活的“无迹可寻”的本质。
最显著地采用这一手法的是翟永明的《咖啡馆之歌》,这首诗叙写了一场域外某咖啡 馆里从下午到凌晨的不成功的朋友聚会。一曲怀旧主题因聚会者始终找不到相关的新鲜 话题和恰当的交流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横亘在“我”和交谈者之间无可逾越的心理距 离而变得支离破碎、软弱无质:“我在追忆/北极圈里的中国餐馆/有人插话:‘我的妻 子在念国际金融’……//我在细数/满手老茧的掌中纹路带来/预先的幸福/‘这是我们 共同的症候’。”“我”的“追忆”与“细数”的动作,与别人的插话无关。“我”在 诗中几乎是个心不在焉的旁观者和旁听者,这场聚会也更像是一幕角色模糊、缺少导演 和必要的情节而各行其是的皮影表演,结果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叙述者——一个不在 场的“我”冷静、克制又细致入微的叙述,包括那些在旁白和独白、铭文和对话之间摇 摆不定、来去无踪的引语。这种可勉强称做“戏剧化”的手法在翟永明的《重逢》、《 莉莉和琼》、《乡村茶馆》等诗中都得到了应用,她以种种矛盾冲突成分的相互错位相 互消解来揭示生活中的种种光怪陆离。诗人没有为了感情而沉醉于感情之中,没有表现 出大于生存状态所应有的感情,节制的诗情反而使诗情无限弥散。这种欲擒故纵的努力 在其他诗人的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整个90年代女性诗歌可谓浩浩荡荡“潮盛水满”。诗歌开始从更高的“人”的意义上 进行了突围,然而却少见雄然崭立的“浪尖”。个中原因我以为有二。一是更为博大的 情怀的缺失。大凡出类拔萃、具有悠久生命力的惊世之作,必然内在地支撑着一颗高迈 拔俗、伟岸刚忍的非凡诗魂,它是一种人溺已溺的同命感和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 ,它赋予诗歌一种杰出的人文高度,放射着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的光辉,并以思想、激 情和美学的独特魅力引领着一个民族以热烈的目光、昂扬的姿态走向新纪元。而90年代 的女性诗歌缺少的正是这样的诗魂。祝福、祈祷、爱和盼望在写作中强化这些中国文学 中久已缺少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应成为女性诗歌创作刻不容缓的任务。二是对生活“淘 洗”能力的缺失。叙事性与口语化被公认为是90年代女性诗歌的一种贡献,它丰富了诗 歌的表现手法,扩大了入诗的范围,但诗歌对现实场景的流连容易导致诗意的流失,有 些诗歌流于平面化、庸俗化、琐碎化。因而,从根本上讲,女性诗人走出“自己的小屋 ”融入更广阔的天空,争取生活的自由度诚然重要,开采自己的精神空间,让它大些大 些再大些,恐怕才是最有效的药方。也许,女性诗人们更应牢记“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 不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才真正有女性自我”(注:郑敏: 《女性诗歌研讨会后想到的问题》,见《诗探索》1995年第3期。)。或者还是唐晓渡说 得好:“那使事物不朽的也必令诗人光荣”(注:唐晓渡:《写作将如何进行下去—— 关于90年代先锋诗》,见《今日先锋》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