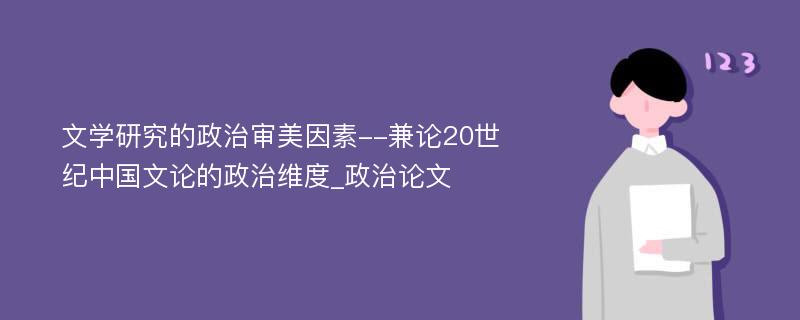
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文学理论论文,维度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7-0181-06
文学与政治以联姻的形式浮出历史地表,既不是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服务论”的回归,也不是对主张文学脱离政治的“审美论”的反驳,而是在新的学术生态语境下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一是思考文学研究所处何种政治语境的问题,二是追问不同政治语境中文学研究何为的问题,三是设想建构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审美因素。换言之,何种政治、谁之文学、如何审美等是文学研究必须解决的三大核心问题。我们可以将20世纪文学理论分为以下五个阶段:清末民初的启蒙与审美,“五四”至20、30年代的革命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政党文艺,80年代的主体论与新启蒙,90年代的后启蒙。当然,就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而言,以上几个阶段还有部分重合的情况,层次之间的界限有时也会被具体语境打破。
一、何种政治——文学研究的政治语境
政治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学研究生态的重要维度,中国自古就有“修、齐、治、平”的文化政治伦理观念,西方也有“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说法。文学研究无法真正脱离政治,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也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分析文学研究与政治之间忽远忽近的原因及其背后的文化权利关系。
传统的政治是指国家政事,即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治理、对人民的统治,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政治主要是指国家政治体制,《周礼》中“掌其政治禁令”的政治是指治理国家的措施,等等。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一般认为政治是与道德、法律、权力之争、公共管理、政府的政策及其执行的多种活动,“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种政治投射到日常生活中的影像是阴暗的,表现在文学中,则多有欲望的趋势、利益的争夺、权力的追逐等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妖魔化、刻板化,悲观地认为政治本身就是非正义的。
现代社会的政治突出了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从文化系统来说,它是物质文化,又是精神文化。从物质文化方面来说,政治是权力设施,社会制度。从精神文化来说,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理想”②。文化学意义上的政治是指“权力结构”,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机构、政治运作等;政治也是“情感结构”,包括情绪、情感、思想、意识和理想等;政治还是“象征符号”,用诗意和隐喻表达审美热情和政治归附力③。政治的文化内涵突出了人的体验和价值,它的美学价值彰显的是现代人的想象、虚构的审美需求,如此一来,政治的冰冷面孔开始消融,走向价值中立和多元。“政治并不值得人们过分地推崇,但也不必认为是可耻的事。人们对政治的美化或诽谤,仰慕或厌恶,便是验证了政治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用来制造一些‘幻想’,并以讨论、沟通来缓和及解决冲突”④。也就是说,政治除了在分配利益和权力等实用功能之外,还具有制造幻想和想象的能力,当然这种功能是通过人类在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创作和研究来完成。如此一来,一种特殊的现象——文学研究的划分以政治语境为标志——出现了,这可以看作文学对政治的想象和审美建构,也可以说是政治对文学的规训与赋魅。
有必要对政治做细致的分层次理解,因为文学是在不同层面和意义上与政治发生关系,文学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厘清两者的关系。第一个是最低层,是具体的政治政策及其落实。文学或者图解政策,或者反对政策,或者保持中立(中立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取向),这在文学上被称之为应景之作。周扬以政治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这样阐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艺术创作活动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当前各种革命实际政策的开始结合,这是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标志之一。文艺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地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⑤。我们不能只用审美标准来衡量这类文学的价值,还要看其对于政治政策的社会功能的影响如何,进行历史、客观的评价。当然,这类作品也会随着政策的变化和消失而丧失其政治价值,并且艺术上也因为功利目的过于明显而具有审美缺陷。第二个是中间层,即政治制度层面,包括政党制度、议会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等。文学在此间也会受到影响而形成自己的一套制度和规则,尤其是体制内的文学与研究受到的影响更大。全国文代会、作协、各类文艺评奖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上承政治意识形态性,下涉文艺审美性,如文代会推进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作协将文艺工作组织化、规范化,评奖把握文艺发展主流导向。第三个是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抽象地以政治观念、精神的形式出现,并且已经融合了社会、民族、世界等其他要素。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文学的政治负担减轻,更加强调文学的个性化、主体性。鲁迅主张的“为人生”看似是捍卫“文学是人学”的宣言,但却与革命文学内在契合,因为当时的政治就是“人的政治”与“非人的政治”的对立。政治文化是对政治政策、政治制度的提升和总结,是政治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学与政治在此得到了相对独立的自由发展空间。第四个是最高层,即政治审美层面。政治政策、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都以高度审美化、形象化的面貌出现,政治如盐入水地与文学融为一体,归于无形。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Q正传》等既可以说指向最大的政治,同时也是最好的文学,但绝不只是政治,也绝不单是审美,恰恰是政治与审美的完美结合。政治审美层面是文学与政治结合的最高境界,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们用“政治审美因素”来形容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文学与政治联姻的四个层面并不能截然分开,几个层面的关系可能同时发生,也可能相互转化。
二、谁之文学——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
文学研究虽然无法脱离政治,但它同样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变革社会的力量逐渐由政治、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领域,文学研究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萨特、伊格尔顿等文学理论家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向政治政策、政治观念、政治文化发起挑战,依靠的是文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显示了文学研究在工人运动、社会文化、政治变动中的重要地位。在文学研究实践中,任何一派都奉行排他原则,都会宣传自己是真理、合法、普遍和有效,同时背后都有不同文化利益集团的支持,“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信念和意识形态标准密不可分”⑥。在无法释怀的政治语境中,文学研究接着要面对的是“文学为谁”或“谁之文学”的问题——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
清末民初,文学及其研究围绕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展开,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是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的核心,启蒙的对象从上层精英转向下层民众,知识分子掌握文学研究的领导权。晚清政治、军事上的失败激起思想界的强烈反应,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成为学界共识,但传统文学及其研究显然无法适应这一要求。对思想界而言,军事上失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化的黑暗、落后造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要从物质技术层面入手,更重要的是改革精神文化。思想文化层面,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科学,二是文学。就科学而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1898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发表,这部解释达尔文进化论的生物学著作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影响和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不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还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从此救亡图存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人为之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的中心主题。就文学而言,大量西方作品被翻译过来,文学成为晚清思想界发泄情感的最佳方式,知识分子通过文学的介绍、创作和批评,表达出鲜明的政治理想、社会责任和精神追求。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发表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者将国民的改造和革新寄希望于小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手者泰半”⑦,文学的政治意义可见一斑。梁启超的主张得到吴沃尧的《说小说》、陶会佑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等支持,形成以文学之名行政治改革之实的社会潮流,开始注意对下层民众的启蒙。
“五四”至二三十年代,由启蒙转向革命是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的主要话语。启蒙的对象开始转化成启蒙的主体,革命话语逐渐超过启蒙话语而具有领导地位,作为革命动力的平民、大众越来越受到重视。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公然提出改革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等主张;紧接着,陈独秀又在2月份的《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更加明确地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号加以呼应和推动;于是,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陈独秀提出“革命家三大主义”,极具号召力: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明确提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⑧。文学革命是知识分子为文学开出的药方,医生(启蒙者)与病人(被启蒙者)关系高下分明;但到了1928年,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将启蒙者的光环打破,主张文学家应该将大众当作自己的导师,投身革命实践,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做贡献。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是政治观念从保守到激进的结果,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政治立场从知识精英转向底层大众的历史选择。文学研究的变革从技术层面深入到精神内部,直至上升到涉及政治立场、道德人格等阶级、阵营的划分,这也引起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失于偏颇。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存在着用左翼革命理论掩盖左翼文化多元性,以及多重鲁迅评价的模糊性,这源于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以及通过鲁迅公共影响建构延安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的叙事策略⑨。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以“政治标准第一”统帅无产阶级文学,明确了文学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政党文艺开始建立。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其中,“为工农兵服务”规定了“文学为谁”的作家立场问题,对于作家而言,最大的影响是知识分子被划入“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想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必须首先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与广大工农兵大众的思想、言行保持一致。这就意味着作家如果顺从改造,不但将丧失思想的独立性,而且还要改变自己个性化的创作风格;而不服从改造或改造不好的作家逐渐沦为嘲讽和攻击的对象,甚至被当作阶级敌人。尽管作家、理论家真诚而积极地进行改造和自我改造,但真正的作家、理论家无法忍受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并在关于典型、形象思维、人道主义等讨论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但这些学术讨论在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的运动中被划入阶级斗争的范畴,政治唯一的标准让文学沦为傀儡,这在“文革”达到极端。
“文革”以后,在“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下反思“极左”政治给文学带来的灾难,重新启蒙成为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有限度地掌握文学话语权。文学界成为思想解放的突破口,知识分子得以具有启蒙者的权威,文学成为社会话语的中心。接续五四传统,重新启蒙肇始于“人”的重新发现和主体价值的弘扬,作家、读者、人物形象等文学活动要素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等精神主体的特点被承认。重新启蒙瓦解了“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基础,文学研究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遵循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解决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国家意志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实施。因此,重新启蒙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在被长久压抑之后的呐喊和反抗,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获得重生而暗合政治的策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受到更大的挑战,反思、忏悔、绝望的思想气质成为重新启蒙的重要特征,近年兴起的“重返八十年代”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90年代以后,受“语言转向”、文化研究等西方思潮影响,语言分析、理论建构、文化模式等后启蒙话语成为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知识分子化身智识分子,文学研究走向职业化、大众化、技术化。语言学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大大提升了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科学水准,文本的分析使得研究真正走向细致和深入,在哲学上更是将“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的观念变为文学常识;另一方面,语言学也被运用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文学曾经独享的语言权威被稀释,也化解了文学的政治因素。如果说结构主义将文学研究变成语言研究,那么解构主义又打开了文学研究重新向社会历史开放的窗户。福柯等人的话语分析理论,又将文本、话语背后的深层权力关系推向前台,文学研究的外部研究重新受宠,并且起点于缜密的语言理论。纯文学的边缘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加速了文学研究的分化,文化研究由此兴起,文学的政治研究转变为文化政治研究,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使得文学的政治诉求显得更加复杂,文学研究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将会同时并存。
三、如何审美——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是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结合的历史产物,是理解和分析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核心和关键。
在晚清启蒙与变革的政治诉求下,文学及其研究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审美层面介于政治政策与政治制度之间。旧文学中的“状元宰相”、“佳人才子”、“江湖盗贼”、“妖巫狐鬼”等文化符号被认为是导致封建思想的根源,新文学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向新的道德、宗教、风俗、人心、人格等,审美价值在“旧民”到“新民”的现代转化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文学研究的政策、制度性因素导致文学他律性逐渐增强,引起了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研究者对文学自律性的张扬。王国维认为文学的自律性主要靠作家的主体意识,要做“专门之文学家”,而非“职业的文学家”;要做“为文学而生活”,而非“以文学为生活”。尽管王国维发挥了康德、席勒、叔本华等西方思想,但追求文学纯粹性的强烈愿望表露无遗。
从五四到30年代,文学的政治审美因素以多元政治文化为中心建构,以国民思想解放为目标,推动了文学观念的更新、白话文的繁荣、新文学作品的兴起和新文学社团的涌现等。维新变法的失败表明,之前文学的政治制度、政策书写难以完成变革社会的政治使命,不如将政治诉求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更加具有文化意义的实际内容。文学的政治审美因素是以文化的形态出现,掌握知识和文化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就成为当然的立法者和启蒙者。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变革、军事成败和社会转型的主力军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大众。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言,他们在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发现,只有通过大众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是军事上的策略,也是党在文化、文学领域的基本立场。大众的地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日益凸显,郭沫若甚至断言: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通俗化,只要不丢开无产大众,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⑩。为了突出文学的大众性,郭沫若不惜贬低文学的艺术性,“‘为艺术而艺术’……事实上只是不通的一个偏见”,“为了大众,为了社会的美化与革新,文艺的内容断然无疑地是以道义美底发扬和维护为其先务”(11)。明显偏颇的论调背后是左翼文学的政治文化要求对文学领导权的夺取和掌控,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受到严峻挑战。
40年代初开始,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退化到政治政策、政治任务层面,政治文化变成了狭义的政党政治,文学家和理论家在有限的政治层面有创作和研究的权利。整风之前要求创作自由的艾青,被改造之后说“我们的文艺,是为政策服务的”,“文艺既然为革命服务,就必须宣传革命的政策”(12)。一直到70年代,政权、政党、政治的无边界介入导致文学创作的合法性首先必须政治正确,文学研究也被纳入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政策、任务的轨道。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家首先是政治理论家,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周扬、茅盾等发表的众多关于文学的讲话和文章既是政治宣言,又是文学理论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政治观点的统一和分歧可以直接导致文学观念的一致和分野,中苏两党在政治上没有分歧的时候,苏俄文论被看成是学习的楷模,几乎所有的文学研究都要引用马、恩、列、斯的经典语录和苏俄文学作品;当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时,对现实主义的不同观点被称之为“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在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想高度一致的情况下,文学研究甚至成为攫取政治资本的捷径。
“文革”以后的80年代,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紧紧围绕“人”、“主体”展开,从感性化的情感发泄到理性化的批判反思,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重回文学本位,更具实践与精神的辩证关系。鉴于文学作品在当时社会的轰动效应,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政治意识、社会思想和文化潮流等外在影响和压力。《伤痕》、《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既是文学观念更新的内在生成,也是政治观念拨乱反正的外在推动。然而文学创造和树立新的研究范式的任务仍然艰巨。第一,文学研究合法性的重新确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语境下,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就是政治的合法性;“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语境下,“正”应该是文学本位,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的文学研究观念、方法和范式,政治家和文学理论家在实践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为文学研究重新找到合法性提供了依据。第二,文学研究主体论的重新确立。“阶级论”、“工具论”的文学及其研究不需要主体的独立性,只需要政治性。主体论的文学及其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政治论,将主体性看作每个文学要素——作为对象的人物形象、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的核心和内容。这样一来,文学研究就必须在尊重文学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甚至成为寻找主体性的活动,文学研究开始由外向内转。第三,文学研究的辩证思维产生。单一化、极端性的思维模式很难在文学研究中立足,辩证的研究思维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选择。虽然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一度引起“方法论热”,但没有哪种方法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唯一选择,在妥协、变通中吸收、综合和创新成为主流。
90年代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围绕“语言”、“文化”展开,文学的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成为政治审美层面的两极。第一,文学的语言研究既是对主体论的超越,又是长久以来文学本体研究过于缺乏的一次“恶补”,符合国际研究范式和思想潮流。结构主义赋予语言符号以本体地位,深刻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算是政治文化、政治观念的一次革命。文学研究对结构主义的推崇实际上是将“文学即语言”替代“文学即政治”,有利于在短期内让文学回归本位,但采取的封闭方式注定不能长久。解构主义瓦解和延伸了结构主义,将文学研究重新开放,政治审美因素开始转向文化研究。第二,文学的文化研究将政治审美因素转化为文化政治,文本与话语、权力的结合使政治趋于中性化、学理化。理想化的新启蒙在市场化、全球化主导下的多元价值和复杂现实面前显得浪漫而无力,相比之下,市场在个性解放方面的作用更加广泛和强劲,丛林法则、拜金主义、市侩哲学等负面因素更是激发起“人文精神”等争论。文化政治既是一种后启蒙话语,又是重新启蒙的基础,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因此趋向开放和多元,有利于文学突破政治的藩篱、学院的界限和边缘化的危机,在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中保持活力。
注释:
①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②钱中文:《文学发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③高永年、何永康:《百年中国文学与政治审美因素》,《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④[法]菲利普·布侯:《政治生活》,张台麟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47页。
⑤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解放日报》1945年6月3日。
⑥[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⑦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⑧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卷6号(1917年2月)。
⑨周维东:《“统一战线”战略与延安时期的鲁迅文化》,《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⑩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
(11)郭沫若:《今天创作的道路》,《创作》第1卷第1期(1942年3月15日)。
(12)艾青:《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载《新文艺论集》,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28-29页。
标签:政治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新青年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