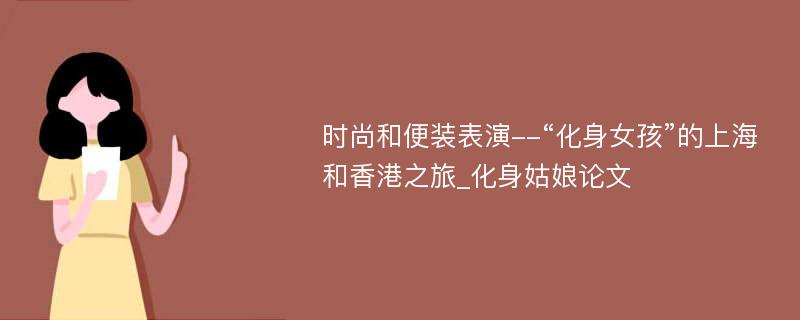
流行时尚与易装扮演——“化身姑娘”的沪港行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身论文,流行时尚论文,姑娘论文,易装论文,港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引:一部影片的“观众”
1936年12月25日,上海《申报·本埠增刊》开始推出艺华影业公司的广告,预告由方沛霖导演、黄嘉谟编剧的《化身姑娘续集》将于西历1937年元旦在派克路卡尔登影戏院隆重上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申报》上关于《化身姑娘续集》的广告每天一变,到正式上映的1月1日,影片的广告又从“本埠增刊”“变身”到了《申报》的头版,占了整整一版的篇幅。接连几天的广告,除了用图片和文字突出“化身姑娘”袁美云“兼饰三角、忽男忽女、千变万化”的“离奇奥妙”,还特别把半年前在北京路贵州路口金城大戏院首映原本《化身姑娘》的盛况搬出来吆喝,称原本《化身姑娘》观众计有八十万之多,是当之无愧的“突破一切记录的喜剧之王”;所以然,片子的续集也必会“场场客满,天天拥挤”。①
原本《化身姑娘》的观众是否真有八十万之多,单凭艺华的广告似难定论。影片1936年6月6日在“国片之宫”金城开映,票价分四档,最低三角,最高一元。设若以平均票价五角计算,那么到6月20日影片被移至上海国片二三轮影院放映为止,《化身姑娘》在金城大戏院放映半月的观众人次大概是二到三万左右。②如果是这样的话,余下的七十七万是不是能被上海的二三轮影院和“埠外”(上海之外)观众补齐呢?考虑到上海为电影之都、金城乃国片重镇的因素,人们有理由对此存疑。不过,话又说回来,围绕八十万观众数的疑问并不能反证《化身姑娘》不是一部颇受当时观众追捧的商业片。影片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从艺华老板严春堂在原本《化身姑娘》上映不到半年就马不停蹄地推出续集上窥见一斑;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严还接着在上海孤岛时期乐此不疲地投拍了影片的第三、四集。此外,从《化身姑娘》下映后的各种即时报道推断,严春堂对影片究竟能否大赚一票估计不足。《化身姑娘》之前,上海娱乐圈内有艺华影业因资金“周转不灵”而致“严春堂售汽车”、“袁美云要加入明星”的传言。③这或许是严春堂在影片正式上映前决定以出售放映权取代拆账分成法的重要原因。原来上海滩电影生意的习惯做法是制片公司与影戏院之间五五对拆,分享票房。但《化身姑娘》却“突破”了这一做法,由艺华“将映权出售,分区倾销”,其中上海映权的价码是五千一百五十元,“买方有联华公司经理及金城十股东”。④唯其如此,《化身姑娘》的放映遂出现了艺华老板因“算盘打错”而只能“看人赚钱”⑤的窘境:
[《化身姑娘》]营业兴隆,实在是一樁利市十倍的好买卖。金城大戏院开映十多天,19日为最后一天。当夜结算,共售得一万余元。拆账结果,净得五千六百元左右。除去六百余元的广告费,有五千元相近之数。……艺华主人严春棠[堂]闻此消息,啼笑皆非。⑥
也就是说,《化身姑娘》在金城一家影戏院的放映“即可出本”,且“盈利信余,稳操左券”,而在上海滩其他影院的放映则会使映权股东们利上加利。如此看来,《化身姑娘》的确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也的确是一部能吸引观众掏钱看的影片。⑦
令人颇觉反讽的是,这些自己花了钱吃“一杯清凉眼目冰激淋”的影迷们在一些评家那里很快成了“落后”观众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电影观众之有“进步”与“落后”之分,正像电影自有“高尚”与“低劣”般天经地义。《化身姑娘》这部比在“水井里投毒药还要可耻,还要狠毒”的影片,靠的是“无聊之极的故事,来迎合一批落后的色情的观众”,也自然会遭到“进步的观众”所抵制。⑧据此逻辑,那些从都市生活的困顿中挤出零花钱看影片的芸芸众生们,只能秘而不宣地消食自己的“低级趣味”,以免公开后被贴上“落后”乃至“色情”的标签。时间再推后几十年,根据吾国一些权威历史的描述,《化身姑娘》在金城的首映不仅没有像艺华广告自吹的那样“开映十二天卖座还是拥挤”,⑨而且还似乎遭到了正义“观众”的坚决抵制:严春堂和“软性电影分子”们在炮制了“大肆渲染资产阶级男男女女的糜烂生活……充满了猥亵淫乱、变态心理的极端腐朽气息”的《化身姑娘》后,“并未在观众的正义的愤怒面前收敛起来,反而接着拍出了《化身姑娘》的续集……孤岛的时期,还继续拍出了第三集、第四集”。⑩
一部影片而有如此多种不同的“观众”描述,还真有点应和了西人约翰·哈特雷(John Hartley)的“后现代”说法,即“观众”不过是被批评家、媒体、政治团体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臆想出来的虚构之物”或“虚构话语”:社会科学家们把“观众”看成独立于其他身份(如父母、子女、学生、职员之类)的社会存在;媒体业者把“观众”看成易于操控的稚童;政治团体把“观众”视为经不起诱惑的脆弱群体,因此而有各种审查制度的建立;而左派知识分子们则把“观众”想象成怒目圆睁的斗士。(11)此情此势,真的颇有点大家都在说“观众”,“观众”却在云雾中的感觉。不过,或许也正因为围绕《化身姑娘》“观众”之跌宕起伏的纷扰话语,才使影片在今天看来仍然饶有兴味。
“化身”的愉悦:流行与时尚
无论艺华的广告词“男人和男人拥抱热吻,女人和女人喂脸温存”、“男人生女病,急煞医生;性机能改变,气煞祖父”把《化身姑娘》吹得有多天花乱坠,(12)实际上影片叙境秩序的暂时紊乱皆因袁美云人物女扮男装所致,也就是西界通常所说的“女性易装”现象(female cross-dressing)。银幕拉开,上海滩归国富商张菊翁苦于膝下无孙承继遗产而气息奄奄,大有不日撒手人寰之势。此时张在新加坡打点生意的儿子儿媳产下一女,知其父盼孙若渴,乃谎称所生系子,电告上海,张菊翁顿时神清气爽,病灶全除。时间前闪到十八年后,长命的张菊翁念孙心切,遂电召他名之为“守本”的孙子来沪省亲。于是,真名为莉英的“守本”只能易装来上海接受老爷子验明正身。易装后的莉英“男人女相”,一副奶油小生样,正合了江南的“审男标准”,惹得周璇扮演的朱小姐为其神魂颠倒,以泪洗面。而莉英却是个规规矩矩的“异性恋”(西人流行语straight是也)姑娘,自然不为之所动,倒是暗恋上了来家做客的翩翩少年林松波,后者则心驰神荡在访客李小姐的娇羞中。好端端的一出性别谨严的男女爱情戏却因莉英的易装被搅得风生水起,阴阳莫辨。待到老爷子无意中发现他的“守本”乃是缠胸束乳的“莉英”时,易装的残局才逐渐被重建的性别秩序收起。影片末尾,从新加坡传来真孙诞生的消息,令又一次病重的老爷子顿释前嫌,高高兴兴地目送“化为原身”的孙女携恋人林少离去。
女性易装并非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的舶来品。吾国历史典籍丰厚,万象似乎都可以在显微镜下找到古已有之的渊源。最著名的例子恐怕是木兰从军和梁祝之间幻飞的爱情故事。花木兰易装为男、替父征战的传说,经由迪斯尼动画的重新包装和倾力推销,似已演变为超越国界的全球文化符号。梁祝故事虽然没有那么“跨国”,不过其名声在吾国文化中却丝毫不输于木兰,只是其爱情的凄婉似乎常常盖过了易装的风头。梁祝之恋发展到与罗密欧朱丽叶难分伯仲的经典,起始于祝英台女扮男装的求学渴望。易装使祝梁相识在一个性别给定的空间,也成就了他们只能在阴间比翼幻飞的缠绵。当然,易装还是中国戏曲的重要程式。京剧的男扮女装不在本文的论列,地方戏特别是越剧把古时的女性易装演绎到了极致,这对孜孜开掘性别扮演和僭越的时下论者来说,不啻是一座富矿。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学者们还注意到,在徐应秋(1616年进士及第)的《玉芝堂谈荟》和赵翼(1727-1814)的《陔余丛考》等随笔辑录以及《列女传》等官修史书中,存有“大量”易装女性的例子,“官书常常把[女扮男装]说成是女子在不得已情境下的自我保护,但坊间传说则包括了出于‘冲破女性限制、追求户外或更刺激生活方式’而易装为男的例子。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案例,[女扮男装]就是为了参与到争官夺权的男性专属领域”。(13)
不过,晚清民初的女性易装,在西风东渐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却似乎显现了与古中国相异的“现代性”品格。革命话语的风行,辅以新技术的使用与传播,令女性易装的向度为之一变。常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感叹的革命狂女秋瑾,透过奇巧照相新术的镜头体验了性别僭越的愉悦。(14)她的易装照,既有配以低檐帽和司迪克(stick)的西式男绅士打扮,也有以伞代拐的长衫马褂型中式儒士扮相,鳅鱼般地滑游在男女中西的拘泥之外。易装秋瑾和革命党秋瑾,一为冲破身体性别的箍限,一为颠覆腐朽政治的羁绊,正应映了性与革命相辅相生的现代交响。彼时领风气之先的不仅局限于秋瑾这样的留日女学生,更有以皮肉为生的青楼女子。因辛亥后发起成立青楼进化团而闻名的沪妓祝如椿,在西人“照相之法”前的易装影态,活泼如生地呈现给看家一个“不必拈粉调脂”却也风流倜傥的叛逆少年形象。设若配上“共和国体,阶级须除,同人发起青楼进化团,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的豪言,祝女简直无异于秋瑾的化身。(15)
革命热退烧后,女性易装的政治涂层逐渐剥落,转而汇流到都市摩登的新浪潮中,成为千面“摩登女郎”(modern girl;日语mo-ga)的时髦扮相之一。(16)远在上海新感觉“圣手”们痴迷拜倒于自己图绘的摩登女郎群像之前,刚与田汉成婚的诗书少女易漱瑜,就在领亚洲转型风气之先的东瀛岛国,轻松愉悦地过了一把易装的瘾头。在青年田汉的眼中,着男装与其游逛日本夜市的易女子,更有一番雌雄难辨的异样妩媚,偶尔逃出男帽的几缕细发和耳际微微泛露的淡红令其目醉神迷。(17)可惜的是,这位与田汉青梅竹马、共创《南国》半月刊的留日奇女子因病过早辞世,否则她也许会在田汉的早期作品中觅得几分自己的影子。归国未久的田汉,持续了他在东瀛初现的文化艺术旨趣,对“凡派亚”(vampire,今人译吸血鬼)、“僵尸思想”、“鬼梦”与“鬼怪的愉悦”、“海贼文学电影”(pirate,今人译海盗)、“森林之人与罗宾汉”、“奇妙的Fantasy”(奇幻文学和电影)这些在当今好莱坞仍长兴不衰的故事原型或类型表现了超乎时代的痴迷。在《凡派亚的世纪》中,田引述东瀛作家坪内逍遥未来“五类女优”的说法,特别将第四类、亦即“能扮强硬,冷酷,或热烈的悍妇,或丈夫,英雄一类的女优”拿出来讨论了一番。(18)在他看来,此类女优实在是现实中近乎“凡派亚”的女人的艺术化,不仅“现代的女性”无不多少带点“凡派亚气质”,而且将来“此种女性更要增多”,因此成就一个“凡派亚的世纪”也未可知:
上海的善良的市民听说汉口有裸体游行,安徽有女军官入男澡堂沐浴,湖南有女军叫男堂差,便相惊于世道日衰人心不古,其实在“凡派亚的世纪”这些都无甚特别,凡派亚者极力主张自我,尊重自己能满足生活刺激的女性而已。(19)
女男混淆、亦阴亦阳的“凡派亚气质”女性在田汉1927年为明星公司创作的影片《湖边春梦》(卜万苍导演)中显形。剧作家孙辟疆在去杭州的火车上,结识妖艳美妇黎绮波,两人很快坠入情网,成双入对。未想绮波正是田汉上文所推崇的“凡派亚”女人,不仅热烈强悍,更有女王式的性虐癖,日以捆缚鞭打辟疆为乐,然后狂吻其鞭痕累累的伤口。有虐必有受虐,黎女在疯狂的鞭打中享受了性虐的快感,而文思枯竭的辟疆也在受虐中幻想着他对“舞台上银幕上比较荡毒的女性”的渴念。(20)从目前仅存的影片剧照看,杨耐梅扮演的黎女手持细鞭,易装为男,衬衫领带搭配西式裤装,而龚稼农出镜的剧作家孙辟疆则上身赤裸,双手紧缚,眉清唇红,活脱脱一幅颠倒性别的现代浮世绘。西界女性主义人士的“凝视”(gaze)说,揭露的是女性在男性“凝视”下的视觉臣服,而剧照中“导向男体的女性凝视(连同她雌雄莫辨的细鞭),却将赤裸裸的男性气质加以展示,启人反思中国现代男性在满足女性欲求和国家诉求间的吊诡”。(21)
田汉的“凡派亚”女性和上海新感觉文人笔下的都会摩登女可谓气脉相承。关于上海新感觉文人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文学、电影和文化研究同仁着力颇多,一时有成为“显学”的态势。(22)究其缘由,或许不啻限于全球“上海热”和近现代中国现代性,更可能涉及1920至1930年代巴黎(la femme moderne)、东京(mo-ga)、纽约(flapper)和上海(摩登女郎或modern girl)的全球性别政治图谱和跨文化行旅。晚近台湾学者彭小妍的新感觉阅释,以“跨文化现代性”为论理轴心,用“浪荡子”(the dandy)、漫游者(the flaneur)和文化传译者(the cultural translator)串联起了西洋、东洋和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姻缘,颇值得细读。在她看来,源自西洋风的“浪荡子”与摩登女郎实在是“一体的两面”,二者彼此依存,互相映射,摩登女郎更是“浪荡子存在的合法理由”。1920、1930年代的上海“摩登女郎”,既是新感觉“浪荡子的凝视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也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摩登女郎与被建构出来的摩登女郎之间”相互影响,彼此重叠。(23)不过,无论是“凝视”创造出来的也好,真实的也好,抑或是二者的彼此“重叠”也好,摩登女郎实在是田汉“凡派亚气质”女性的翻版:“Nonsensical(无内容)的头脑细胞,Grotesque(怪异夺目)的上身,Erotique(肉感)的下身—原动力是金钱与Hormone(生殖原素),It(热)是她的生活武器”。(24)更要命的是,这个摩登“凡派亚”深谙“凝视”与“反凝视”(西人所谓return the gaze也)的性别游戏,她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风华容貌和男性“凝视”下的魅力展示,把浪荡子变成了臣服“荡毒”的性受虐者。尽管刘呐鸥、穆时英等文字“圣手”笔下的新感觉女郎鲜有田汉式的易装“凡派亚”,但同属新感觉一员的漫画师郭建英,在从政从商之余,还是用“充满着现代新鲜的感觉,富于魅力的画线”为都市摩登女郎补绘了易装的面向。(25)《最时髦的男装吓死了公共厕所的姑娘》画的是一个身着西装西裤、条纹衬衫配以粗条杠领带的易装摩登女,她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甩着一根细细的“司迪克”(不妨看成《湖边春梦》中抽打裸男的细鞭?),闲庭信步似的踱入女厕,令面前匆忙整理亵衣的旗袍女子花容失色。郭建英1934年初主持《妇女画报》后,更将“亦阴亦阳”的摩登易装女郎搬到了杂志封面上,为张扬女性的“化身”愉悦推波助澜。1934年10月号《妇人画报》(第22期)的封面女郎,唇红齿白,两腮微醺,短发微卷,丹凤眼柳叶眉,活泼泼一个摩登女性的扮相。只是她的嫩黄西装和西服马甲以及淡蓝衬衫和权充领带的丝巾,在妩媚间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规训。(26)
从梁祝故事拉杂到郭建英主持的《妇女画报》,想说的无非是《化身姑娘》的“忽男忽女,扑朔迷离浑不辨;亦阴亦阳,神迷奥妙难识透”不过是吾国女性易装文化的30年代翻版,与“忘记我们民族之英勇的浴血斗争,要他们来迷醉于男化女、女化男的各种胡调的顽意”本扯不上丝毫关系,倒更与彼时的革命话语、性别政治以及都会时尚牵连纠缠。(27)可资佐证的实例还包括早期中国电影和好莱坞影片之间的风气传承。尽管有“辱华片”这样的不愉快事件和经历,但吾国电影对好莱坞的借镜以及二者的互文性,如《赖婚》(Way Down East,格里菲斯,1920年)与《雪中孤雏》(张惠民,1929年)之间、《史黛拉恨史》(Stella Dallas,金·维多,1925年)与《神女》(吴永刚,1934年)之间、《党人魂》(The Volga Boatman,塞西尔·B.戴米尔,1926年)与《大路》(孙瑜,1934年)之间、《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弗兰克·卡普拉,1934年)与《十字街头》(沈西苓,1937年)之间、《马路天使》(Street Angel,弗兰克·鲍沙其,1928年)与《马路天使》(袁牧之,1937年)之间等等,都透露了这样的讯息,即无论对电影人还是对普通观众来说,好莱坞电影均与流行和时尚脱不了干系。(28)《化身姑娘》也印证了这一点。得力于洋场劲吹的西风,1930年代中期上海滩大银幕和印刷媒体也正蒸腾在一股“化身”(metamorphosized,transfigured)和“化装”(disguised)的热浪中。还在《化身姑娘》公映前,就有人发文看衰方沛霖的处女作,理由是影片只可能是外片的拙劣“摹仿”:
几个没落的人支持着一个空场面,出品的滞销,几乎把人忘记掉还有“艺华”这样一个公司的存在,当方沛霖由布景师而充导演的时候,的确我们都怀着很大的希望,至少和吴永刚一样,给我们一种新的手法看看,《神女》给我是很好的好感,而方沛霖用《化身姑娘》的名词,就觉得不会有什么给我们看……这是一个摹仿的名词(外片有过《化身博士》)……因此失败是毫无疑义的。(29)
作者这里提到的《化身博士》,原名为Dr.Jekyll & Mr.Hyde,1931年12月派拉蒙公司出产,由彼时活跃于美英大银幕和舞台剧的才俊鲁宾·马莫利安(Rouben Mamoulian)执导,1933年初在上海首轮西片影院放映。影片的中文译名承袭了四字组合的惯例,根据内容更改了原片两个对中国人来说没有太大意思的外国人名,也算“入乡随俗”的神来之笔。实际上,“化身”可能不如“变身”来得贴切。《化身博士》玩的是通俗版“双重人格”的游戏,影片一开始,体面儒雅的吉科尔医生在讲坛上雄辩地演说着“人由两面组成,一面是优雅的人性,一面是动物性”的理论;回到豪宅的地下室,他喝下了自己提炼的化学药剂,转瞬“变身”为相貌狰狞、龇牙咧嘴、满手毛发的海德先生,充满了力比多驱动的性本能和破坏欲。《化身博士》之后,又有《化身间谍》(The Great Impersonation)在上海滩火了一把。《娱乐周报》1936年3月关于这部以一战为背景的环球公司影片的专文介绍,无意中为方、黄《化身姑娘》的问世做了广告预热。(30)在《化身姑娘》下映和《化身姑娘续集》上映前,更有范朋克主演的《化装绅士》(The Amateur Gentleman)来上海滩延烧“化身”的热火。(31)三部西人的“化身”片无一例外地在男人的“双重人格”、“双重身份”上做文章,还真没有方、黄《化身姑娘》的“忽男忽女、亦阴亦阳”来得噱头十足,神秘刺激。
“小市民”与日常现代性
围绕《化身姑娘》和“软性电影”观众的左翼评论,经常出现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是所谓的“小市民”。你说像《化身姑娘》这样的影片“场场客满,天天拥挤”吗?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此类片子“具备了吸引落后观众的条件”,“可以博得暂时的声名,可以供给没落的无自觉的小市民以若干的陶然和幻想”;(32)你说《化身姑娘》的营销手段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不仅天天变更广告词、而且在原本未推出前就以“请密切注意开映日期和地点”的单句广告来强化观影期待吗?对不起,那些“天花乱坠”的充满“各种性诱惑的词句”只能“欺骗一部分浅视的观众”、“吸引性欲狂的小市民观客”。(33)在一些论者眼中,“小市民”概念显然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批评杀伤力,于是艺华公司1930年代中期的转型,在数十年后出版的权威电影史里,也被看成“企图实行其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制片路线”云云。(34)
先悬置“小市民”概念的源流,看一看“市民”究竟从何而来。查吾国古籍经典,从东汉至明清,无论是治国谋略还是话本随笔,似乎都不乏“市民”概念的使用。东汉政论家荀悦为献帝讲解治国方略,曾有“皇民敦,秦民弊,时也;山民朴,市民玩,处也”的说法(《申鉴·时事》);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在描写宋徽宗治下上清宝箓宫建成后周围的盛况时,亦有“每岁冬至后即放灯,自东华以北,并不禁夜。滀市民行铺夹道以居,纵博傸饮,至上元后乃罢,谓之‘先赏’”的语句。不过,细究起来,这里的“市民”用词与近现代西风影响下经常出现的“市民”概念意义迥然。研究吾国城市史的学者一般都比较认可韦伯的判断,即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以经济、贸易乃至消费为主形成的市镇,但从总体看,秦以后帝国制度的长盛不衰决定了吾国城市的“政治—行政”特质,城市发展“由政府有计划规划及建设而得,以作为政治中心或行政网点”。(35)帝国制度下无论“市民”还是“乡民”,都是皇上和朝廷的臣民和子民,贵贱尊卑、等级次第来不得半点马虎。而西人所谓的“市民”(citizen)或公民概念,则来自古希腊城邦国家(city-states)制度,其间市民既参与治理也被治理,每个市民在政议中都有发言和选举的权力,以尽自己对社群和城邦发展的公民责任。史家唐振常把这个区别总结得更加清楚:
无近世民主之可言的古老中华帝国绝不可能产生所谓市民意识。与中国所称市民相对应,西方所指,应是城市自由民,那就应是公民(Citizen),是属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当指Publicity,the Public,Public Opinion等。不必牵扯太远,简单地说,从公出发,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句口号本身就包含了义务与权利两个方面。纳税是义务,选举以至被选举为议员,参与市政,便是权利。一是由从一己之私变为关注全市之公,热心公益,关心有关公众之事。(36)
在唐先生看来,吾国近现代意义的市民意识,当源自上海租界这个“体”,辅有上海华界的短暂跟进。以参政议政为例,华人在租界内占绝大多数,但早期租界工部局内却鲜有华人代表。随着“不出代议士不纳捐税”意识的普及,更有五四和五卅风潮的推波助澜和租界华人民间组织的集体抗争,工部局中的华董人数也出现了变化,“从1905年12月发端,到1928年4月正式产生华董3人,再到1930年5月,华董增为五名,前后历时二十五年”。(37)租界市民通过代议士制度伸张诉求的做法也对紧邻的华界是个刺激与启发,清末上海华界的“地方自治运动”(local self-government)即为最直接的体现。该运动从光绪三十一年(1903年)开始到1911年结束,历时几近十年之久,期间的自治架构以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改为城自治公所、市政厅)为中心,下设“户政、警政、工政三科,其所办事务,包括编查户口,测绘地图,推广埠地,开拓马路,整理河渠,清洁街道,添设电灯,推广警察,举员裁判”;(38)总工程局之外,更设议会和参事会(后分别更名为议事会和董事会),前者为代议机关,后者为执行机关,至少在制度上保证了市民通过代议士表达诉求的权利。
回到所谓的“小市民”概念。查西文源流,几无所谓“小市民”的说法。旅美史学家卢汉超在其上海研究经典《霓虹灯之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中,将“小市民”权且翻译为西文的petty urbanite和little urbanite后,干脆以拼音xiaoshimin称之,间接佐证了此概念的中国原初性。根据卢的考察,最接近“小市民”这一中国近现代“普遍流行”、“随意使用”且“覆盖面甚广”的术语的西方概念是近代德语中的Kleinburger,该词专指“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既有别于布尔乔亚资产阶层、又有别于毫无财产的普罗阶层”的一群人,其主要构成是工匠,也包括店员、小生意人、小职员等,英文的对应词是lower middle class,即“下层中产阶级”或“中产下层”。(39)在近现代中国语境里,“小市民”概念从未有过清晰的定义,也鲜有令人信服的细致分析,似乎有点人人皆使用之、人人都知道其涵义、却没多少人能说清楚是什么的味道。大体来说,“小市民”自然不包括财富和地位高高在上的一小撮“精英”,也不包括自认为拥有真理般“文化资本”的所谓知识“精英”,更不可能包括那些身无分文踟蹰街头讨生活的赤贫阶层。去掉两头,剩下的那橄榄形的中段,或因为职业和收入关系,或因为捉摸不定的“观念”(mindset,perspective)问题,都有可能被归入“小市民”的行列。也就是说,“小市民”不仅是个经济和社会阶层概念,更可以是个与“感觉”(perception)相关的评价标准,使用者常带有居高临下的轻蔑感。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小市民”称呼似乎又有点地域化和社群化,从一开始就与上海这座城市捆绑在一起;尽管偶有先例,但总体而言,诸如“北京小市民”、“重庆小市民”这样的说法却颇为鲜见。
姑且悬置其贬蔑意义,单从数量和日常消费着眼,“小市民”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大众”或“芸芸众生”。在吾国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近现代转型中,“小市民”不仅是城市经济的直接推动者和生产者,也是日常文化的主要消费者。他们或痴心陶醉于鸳蝴文人的爱情故事,或目眩神迷在刺激感官的图画杂志,或惊羡迷拜在月份牌女郎画所描绘的完美生活,柴米油盐和闲暇之余更是照相和活动影像等新鲜玩意的忠实看客。坚持“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向不讳言自己就是个“喜欢钱”但也喜欢看电影的“小市民”:
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40)
根据卢汉超的考察,上海“小市民”中较大的一股当属职员群体,他们大多住在典型的石库门弄堂房子里,包含了办公室白领和商铺帮手等形形色色与都市商业发展紧密相关的职业。到1930年代末,上海职员群体大致有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职员与其家庭成员相加不少于一百五十万人,如以1930年代中期为基数,约占[上海]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当时上海共有350万人)”。(41)也许正是以职员为代表的“小市民”群体,才形构了《化身姑娘》观众的中坚,也形构了1930年代国产电影的看客核心。在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观影环境里。他们的口味和喜好,本应是各类媒介咨询机构和制片机构的重点分析对象。颇为遗憾的是,在那些自认为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启蒙”批评者们看来,这些观众却成了“落后”、“没落”、“浅视”乃至“性欲狂”的代名词。甚至连郑正秋“左翼转型”后拍摄的《姊妹花》观众,也被贴上了“落后”、“情感脆弱”、“多愁善感”、“意识落后与歪曲”的标签,实在是早期中国电影充满吊诡的奇观。(42)
在空间局促、节奏快速的现代都市讨生活,“小市民”也好,“薪给仰赖者”也好,日常生活的策略应付和精打细算是城市大众必要且必备的技能。晚近中西学者关于“日常性”的讨论,或许能为我们重新认识“小市民”和“日常生活”以及二者的关系提供新鲜的视角。无论是席美尔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关系论、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德索托的“日常生活实践”、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或者是在此类论说启发下萌生的“白话现代主义”、“日常现代性”(everyday modernity)、“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普通现代性”(ordinary modernity)的提法,说的都是有别于“知识精英”文化生产的大众生活经验和物质空间实践在文化、社会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尽管此文并无全面绍介和评价这些论说和概念的打算,不过约略描述一下已故电影和媒体学者米莲姆·汉森对克拉考尔的重读也许不无裨益。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论说已广为圈内人熟晓,此处不再赘言。这里要说的是,克拉考尔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重新进入电影学术话语、成为早期电影研究的重要理论灵感,与汉森不遗余力的引介和再读有很大关系。在其因病魔戛然终止的学术生涯中,汉森不仅发表了大量专论或涉及克拉考尔理论的文章,还出版了克拉考尔研究专著《电影与经验:克拉考尔、本雅明与阿多诺》(Cinema and Experience:Siegfried Kracauer,Walter Benjamin,and Theodor W.Adorno),并为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物质现实的救赎》(Theory of Film: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撰写了长篇序言。经汉森重读后的克拉考尔,以1925年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克拉考尔承继了德国哲学传统对现代性的悲观看法,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盘理性化预示着历史过程的终结和生命意义的空洞化。不过,“大约在1925年左右,[克拉考尔的]文章日益围绕着变化中的场所和征候展开,包括日常物件(打字机、墨水台、雨伞、拖鞋)、空间(都会街道、广场与建筑、拱廊街、酒吧、百货商店、火车站、地铁站、流浪者避难所、失业办公室)以及日益延展的消闲文化礼仪和机构(旅游、舞蹈、体育、电影、马戏、杂耍、娱乐公园)”。(43)关注点的转移也意味着学术立场的变化。尽管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持批判态度,但克拉考尔关于现代性的悲观论述却逐渐“让位给了一种对文明过程不确定的、犹疑的肯定”。(44)也就是说,克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促其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对大众的“释放”乃至解放意义。(45)这一点可以从克拉考尔对好莱坞打闹喜剧(slapsticks)的溢美之词上窥见一斑。在他看来,打闹喜剧是美国自己为福特-泰勒主义原则所代表的现代工具理性开的一方解药,它以“上佳的即兴式破坏、错乱和反讽的狂欢颠覆了经济上强加的体制”,也救赎了现实本身:
我们不得不把这一切归功于美国人:他们用打闹喜剧创造了一种平衡其现实的形式。如果说那一现实令他们的世界常常服从于无法忍受的戒律的话,那么,电影则反过来强有力地粉碎了这一自我强加的秩序。(46)
更为重要的是,汉森对克拉考尔的重读,发现并彰显了“大众主体性”(mass subjectivity)的革命性意义。根据她的看法,克拉考尔是很早就意识到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是复数而非单数的学者之一。克氏在质疑精英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单数现代主义的同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街头现代主义”(modernism in the streets)和现代社会的“表层”(surface),强调当下生活的表层现象比所谓的高雅艺术更能穿透与理解现代社会。正是这种对“表层”和“日常”现实的认识,使克氏得出了大众消闲娱乐的“美学愉悦”也许比当时饱识诗书人士的所谓“高雅文化价值”更具“合法性”、“大众媒体也许代表了唯一的地平线,其间真正的文化民主化正在上演”的结论:(47)
对克拉考尔来说,电影乃是现代性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吸引与代表大众,更因为电影构成了最先进的文化机制,其间大众作为一个相对异质的、尚未定义的以及未知的群体得以以公众的形式表述自身。(48)
也正是在电影和其他“奇幻作品和新消闲文化的氛围”中,克拉考尔感受到了“正在浮现的大众主体的轮廓”。(49)毋需太多的理论阐释,此地涉及的诸多观念与认识,包括“日常现代性”、大众主体性、“表层”与“日常消闲”的民主化潜质,以及对“低俗”类型打闹喜剧的合法性思考等等,都有助于开启我们对《化身姑娘》类影片观众的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扩而广之,将重审的视野拓展到“小市民”及其都市日常生活和经验的意义方面。
余话:“化身姑娘”的港岛扮相
围绕《化身姑娘》的是非曲直随1949年政权更迭而在大陆尘埃落定。不过,“化身”的戏幕并未全部落下,只是移转了空间,从上海搬到了后1949年的港岛,继续着上海滩金城和卡尔登的残梦。1956年,也就是原本《化身姑娘》问世后的三十周年,南迁的艺华又在香港推出了同名翻拍版,由曾翻拍过港版《火烧红莲寺》(1950年)的多产影人陈焕文执掌导筒。翻拍本和原本之间,尽管故事大同小异,人物设置亦相去不远,但还是有几处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港版《化身姑娘》承继了原本追求流行和时尚的风气,在易装的游戏中加入了欢快的歌舞元素。时在1950年代,太平洋彼岸以《雨中曲》(1952年)为代表的歌舞电影之风刮得正盛,紧追其后的香港电影自然不能免俗。于是,港版《化身姑娘》一开始就让能歌善舞、健康阳光的林翠(1936-1995)高歌一曲,之后才将镜头从尖沙咀外景切到老太爷府邸内景,正式展开叙事。好歌需有舞来伴。原本《化身姑娘》顺滑的剪辑和流畅的叙事在翻拍版中常常被林翠健朗的“猛步舞”(mambo dance)打断,虽然拖曳了叙事,倒也添增了原本乏匮的抒情性。“猛步”后译“曼波”,乃1940年代末兴起于古巴哈瓦那的奔放摇摆舞种,后流行到墨西哥等南美国家,1950年代中期经纽约的“猛步革命”(mambo revolution)而热烧全球。翻拍版《化身姑娘》让林翠扮演的易装小姐躲过老太爷的“凝视”,与姑姑在房间里随歌“猛步”,也算是赶了一把全球化的时髦。林翠的“猛步”,很可能引领了港台流行文化中“曼波女郎”现象的潮头。翻拍版《化身姑娘》上映后仅一年,易文编导的《曼波女郎》(The Mambo Girl,1957年)跟风问世(译为“猛步女郎”也别有风味,应和了粤港文化中的“生猛”崇拜)。了然成形的“曼波女郎”,象征了香港1950年代的青年礼仪和活力,以及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和青春的未来憧憬。时间再前推到新世纪,“曼波”潮更有台湾新电影中坚侯孝贤《千禧曼波》(Millennium Mambo,2001年)的接力,若溯其源头,方、黄的《化身姑娘》应该被提到。
次之,港版《化身姑娘》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参与了香港电影的身份建构。1950年代的香港国语对白影片,因沪港之间的历史联系而诸多呈现傅葆石先生所言的“在香港拍上海”(filming Shanghai in Hong Kong)走向。左翼影人朱石麟的港岛影绩,包括《误佳期》(1951年)、《一板之隔》(1952年)和《中秋月》(1953年),从人物到故事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早前上海电影的味道。港版《化身姑娘》在很多方面也无出其右。艺华公司的沪港双向迁徙,当然是原本和翻拍本之间近密互文性的机构担保。时间回转二十年,上海一些制片公司为规避民国政府对拍摄粤语片的禁令,开始纷纷“转向香港方面去谋发展”,包括成立港岛办事处或分公司,冀望在粤语片票房上捞一把。(50)满眼生意经的艺华老板严春堂亦未能免俗,委派小开严幼详“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办事处”,以谋公司在“华南方面业务的发展”。艺华的华南业绩究竟如何,未挖掘史料不能随意判断,不过办事处成立不久,坊间就开始流传艺华香港分公司将出产的粤语片《糊涂外父》配上国语对白、然后以新片《并蒂莲》送南京审片的丑闻,在“打政策擦边球”之余倒也为沪港电影姻缘增添了一点有色彩的掌故。(51)不过,除歌舞“猛步”之外,港版《化身姑娘》的一些细节改动或许更值得玩味:影片反复出现尖沙咀沿岸的景观,或为外景空镜头,或为男女人物谈情说爱的背景,明显比原本更强调空间的特定性;原本中“化身姑娘”的性别显形,导因于她新加坡女同学的沪上之行,而在翻拍版中,同学的属地从新加坡转到了台湾,令人不得不联想到港片在无法进入大陆市场的情况下日益强烈的台湾市场期许;全本国语对白的翻拍版《化身姑娘》,在“男厕所他不敢去,女厕所不许她去”的关键噱头点,安排了一个粗胖的女龙套,在林翠扮演的男装女刚开门进女厕所时,用粤语把她骂出了女厕所。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有意无意间建构着香港电影的独特身份,哪怕该片不过是二十年前上海原本的国语翻拍。
或许也正因为围绕《化身姑娘》“观众”之跌宕起伏的纷扰话语,才使影片在今天看来仍然饶有兴味
晚清民初的女性易装,在西风东渐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却似乎显现了与古中国相异的“现代性”品格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小市民”称呼似乎又有点地域化和社群化,从一开始就与上海这座城市捆绑在一起
克拉考尔是很早就意识到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是复数而非单数的学者之一
注释:
①《化身姑娘续集》广告,1936年12月25日、26日、28日、29日、30日《申报·本埠增刊》;1937年1月1日《申报》头版。广告未说明八十万观众数是指上海本埠还是也包括中国其他地区。
②据《电声》1936年6月26日(第903期)报道,《化身姑娘》在金城“共售得一万余元”,假设每票平均为五角,那么一万元即意味着二万或更多人次。另据《申报·本埠增刊》1936年6月19日、20日广告,金城6月19日最后一天放映《化身姑娘》;6月20日金城推出了明星公司出产的新侦探片《金刚钻》。
③《娱乐周报》1卷19期(1935年11月9日)。
④《电声》第903、904期(1936年6月19日、6月26日)。
⑤《娱乐周报》2卷23期(1936年6月13日)。
⑥《电声》第904期(1936年6月26日)。
⑦《电声》第903期(1936年6月19日)。
⑧穆维芳《化身姑娘》,原载《民报·影谭》1936年6月7日;高风《〈化身姑娘〉及其他》,原载《大晚报》1936年6月20日。转引自陈播主编《30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页832-836,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⑨《申报·本埠增刊》1936年6月17日《化身姑娘》广告词。
⑩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等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卷,页496-497;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出版。
(11)转引自孙绍谊《通俗文化,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评述》,载台湾《当代》杂志1995年10月号。
(12)《申报·本埠增刊》1936年6月5日《化身姑娘》广告词。
(13)罗兰德·奥登伯格(Roland Altenburger)《服装造就了男人?20世纪前祝英台传说中的易装、性与性别》(Is It Clothes that Make the Man? Cross-Dressing,Gender,and Sex in Pre-Twentieth Century Zhu Yingtai Lore),《亚洲民俗研究》(Asian Folklore Studies)卷64(2005年),p.170。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收入《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赵翼《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秋瑾集》页97,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出版。
(15)贺萧(Gail 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妓业与现代性》(Dangerous Pleasure: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pp.171-172;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16)关于民国时期“新女性”与“摩登女郎”的区别,参见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关于“摩登女郎”自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的跨文化旅行,参见艾丽斯·温鲍姆(Alys Eve Weinbaum)等编《世界范围内的摩登女郎:消费,现代性与全球化》(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Consumption,Modernity,and Globalization),杜克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台湾学者彭小妍称20世纪初叶的全球“摩登女郎”现象为“跨文化现代性”,参见彭小妍《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1930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
(17)田汉《蔷薇之路》7-9页,上海泰东书局1925年出版。
(18)(19)据田汉的绍介,坪内逍遥的“五类女优”包括:“一个活泼愉快而多少有滑稽的天才的喜剧性质的女优”;“扮妖艳而多情的女人的”;“一个寂寞而忧郁的女人”;“一个能扮强硬,冷酷,或热烈的悍妇,或丈夫,英雄一类的女优”;以及“一个扮天真烂灿楚楚可怜的女孩子”的女优。田汉《田汉散文集》页142,页142-143,上海今代书店1936年出版。
(20)同上,页141。关于《湖边春梦》的详细剧情,参见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卷2页1038-1044;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出版。
(21)罗亮(音;Liang Luo)《摩登女郎、现代男性及中国现代雌雄同体的政治》(Modern Girl,Modern Men,and the Politics of Androgyny in Modern China),《密歇根季评》(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2008年春季号。
(22)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下列中西文代表作的相关章节: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盘剑《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The Lure of the Modern: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1917-1937),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李欧梵《上海摩登:中国新都市文化的兴盛,1930-1945》(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23)彭小妍《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1930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页36-37。
(24)郭建英漫画《现代女性的模型》文字说明;转引自郭建英绘、陈子善编《摩登上海:30年代的洋场百景》页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5)1934年2月《妇人画报》第18期,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建英漫画集》出版预告。
(26)彭小妍在《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1930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中,也重点分析了郭建英的女性易装漫画。不过,她提到的第三幅线条画《老黄,让我介绍吧,这位就是陈小姐》中的“易装”“摩登女郎画家”,似乎原本就是男性。虽然画家的头发长了一点,但脸上的棱角线似暴露了他的男性性别。至少,单纯从漫画本身看,画家的原性别难以断定。“吓得全身僵硬、哑口无言”的老黄应该是因眼前的全裸模特陈小姐而震惊,并非导因于画家的“男装”。详见彭书,页114-118。
(27)穆维芳《化身姑娘》,原载《民报·影谭》1936年6月7日;转引自陈播主编《30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页832。
(28)关于《赖婚》与《雪中孤雏》的关系,参见付晓红、王真《〈赖婚〉与中国早期爱情片》,《电影艺术》2012年第1期页138-143;关于《神女》与《史黛拉恨史》之间的关系,参见王亦蛮《〈神女〉及其好莱坞“前作”和香港“后作”:现代性、殖民性与消失的母亲》,载孙绍谊、聂伟主编《历史光谱与文化地形:跨国语境中的好莱坞和华语电影》页300-3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29)罗罗《中国名制片公司之动态》,《电影画报》1936年6月1日(第30期)。
(30)参见《娱乐周报》卷2第9期(1936年3月7日)。
(31)《化装绅士》于1936年12月3日在西藏路外片首轮影院大上海首映,距《化身姑娘续集》1937年1月1日在卡尔登(中片首轮、外片2轮)首映相差不到一个月。
(32)前引自高风《〈化身姑娘〉及其他》,原载《大晚报》1936年6月20日,转引自陈播主编《30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页835。后引自罗浮(即夏衍)《“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原载《大晚报·火炬》1934年6月21日,转引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页156,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
(33)柯灵《论电影宣传》,原载《明星半月刊》1933年5月1卷1期,转引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页211。
(34)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等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卷,页494。
(35)参见韦伯《城市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City),收入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e)编《城市文化经典》(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页23-46。所引文字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页91,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
(36)(37)(38)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载《上海研究论丛》第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
(39)卢汉超《霓虹灯之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页62,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40)张爱玲《童言无忌》,转引自张爱玲《流言》页3,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出版(1944年初版)。
(41)同上,页63。该书页64刊有表格一张,较详细地列举了民国上海“职员”(白领雇员)的各种职业和相应人数,涵盖了百货公司、商铺、银行、学校、媒体、邮政运输、洋行、工厂、政府等传统和现代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政府职员仅占很小比例,总数不过三千五百人。
(42)语见絮絮《关于〈姊妹花〉为什么被狂热的欢迎?》、黑星《从〈人道〉到〈姊妹花〉》、罗韵文《又论〈姊妹花〉及今后电影文化之路》三文,分别原载于《大晚报·火炬》1934年2月28日、3月21日、3月24日,转引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页472-478。
(43)(44)(45)米莲姆·汉森《美国、巴黎与阿尔卑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论电影和现代性》(America,Paris,the Alps:Kracauer[and Benjamin] on Cinema and Modernity);莱奥·沙尔内依(Leo Charney)、瓦妮莎·施瓦茨(Vanessa Schwartz)编《电影与现代生活的建构》(Cinema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p.370,p.370,p.365;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46)克拉考尔“Artistisches und Amerikanisches”;转引自米莲姆·汉森《美国、巴黎与阿尔卑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论电影和现代性》;莱奥·沙尔内依、瓦妮莎·施瓦茨编《电影与现代生活的建构》,p.373。
(47)(48)(49)米莲姆·汉森《美国、巴黎与阿尔卑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论电影和现代性》;莱奥·沙尔内依、瓦妮莎·施瓦茨编《电影与现代生活的建构》,p.374,p.375,p.377,p.378。
(50)参见《娱乐周报》创刊号,1935年7月7日。
(51)《娱乐周报》34期,1936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