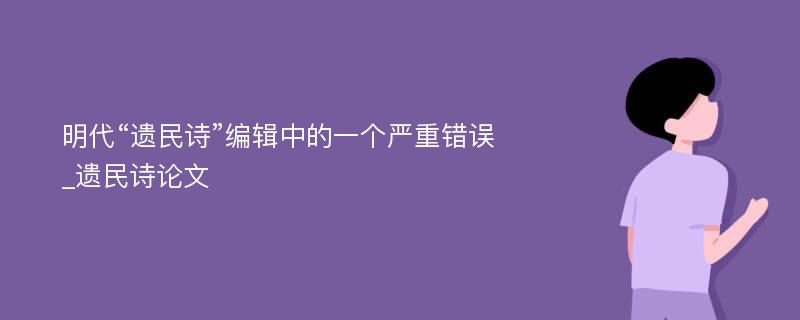
《明遗民诗》编辑中的一个严重失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民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重的失误
《明遗民诗》,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清朝康熙年间初刊时,本名《遗民诗》;清末宣统年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出版,改名《明末四百家遗民诗》。这是一部明末遗民诗作的选辑本,共16卷,收录作者507人,诗2867 首(以中华书局本为据)。
《遗民诗》选辑者卓尔堪(1653-?),字子任,一字子立,号鹿墟,又号宝香山人,清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注:关于卓尔堪的生年,据张潮说,少张氏三岁,则应是顺治十年癸巳(1653)。见《扬州足征录》所收之《近青堂诗集序》。本文取此说,别说从略。卒年待考。)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他参加清军李之芳部平定耿精忠之役,为右军前锋,数立军功。七年后,以母病辞官返里,从此不复出。他回乡以后的情况,据阮元《淮海英灵集》甲集卷一所云:“席门委巷,赋诗学古,与宣城梅定九、曲阜孔东塘、黄冈杜茶村、同郡张山来、吴薗次纳交倡和。”还“壮游四方:辽、江、荆、衡,皆所游历;又曾航海数千里,经普陀、蓬莱,观海市”。他著有《近青堂诗集》四卷;与张潮(山来)共同选辑曹植、陶潜、谢灵运之诗,成《三家诗选》八卷;但以所辑《遗民诗》著称于世。
关于卓尔堪生平,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二七、张维屏的《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二十仅有简略记叙,远不及阮元所编《淮海英灵集》翔实。近人邓之诚《骨董三记》卷一、《清诗纪事初编》卷四,以及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康熙朝卷),对卓氏生平亦有考订,可资参阅。
卓尔堪之所以编选《遗民诗》,自称是为使明遗民“诸君子之诗为之一聚,则诸君子之性情亦为之一聚,其禀诸大造之气,蕴而未尽泄之奇,当亦为之一聚。如闻歌泣太息于一堂,各吐其胸臆而无间,使天下后世,皆得而窥见之”(注:《遗民诗》卓尔堪自序。)。也就是说,其目的在于汇聚、保存明末遗民的诗作,从中了解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思想、情感,而不使“其所蕴之英奇”泯没。从保存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看,此辑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由于该著的刊行,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中,有些人的事迹和他们的一些诗篇被保存了下来,为后世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与文化情况的资料。所以,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曾称赞卓尔堪:“忠贞公后族蝉联,一代遗民借尔传。”(注: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十一;该诗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遗民诗》当已刊行。)邓之诚先生认为:《遗民诗》“取舍可谓谨严,搜罗不遗,一代遗民之作,大约具备。今其本集多半不传,赖此犹得见其梗概。褒集之功,过于标榜风骚,借通声气者远矣。”(注:邓之诚:《骨董三记》卷一。)惟其如此,《遗民诗》虽三易其名,并屡遭禁毁之厄运,仍流传三百年而不衰。民族文化之生命力,可见一斑。
因此,中华书局将《遗民诗》重新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无论康熙本或有正书局本,现在都很难寻觅到。而在60年代初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重版该书,更属不易。
但是,在重版这样一部有重要价值著作的过程中,由于编辑者的疏略,出现了将某人之诗错编入他人名下这种“张冠李戴”现象。依笔者所见,共有三处:
《明遗民诗》卷三,余怀诗24首,误编入杨焯名下,使杨诗从4 首突增至28首。这是余冠杨戴。
卷六,高兆诗4首,误编入韩昌名下,使韩诗由17首变成21首。 这是高冠韩戴。
卷十一,纪映钟诗36首,误编入许承钦名下,使许诗由44首变成80首。这是纪冠许戴。
上述三处失误,至今未得改正,造成讹谬长期流传,实属不当。若能重版,请予订正。
事实的真相
据笔者管见,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所藏之康熙刊本《遗民诗》,相对比较完备。其卷三之首作者小传中,有余怀的传略,文字如下:
“余怀,字澹心,一字广霞,号漫翁。福建莆田人,江宁籍。布衣。读书破万卷,倜傥风流,交多贤豪。隐居吴门,倘佯支硎、灵岩间。著《味外轩稿》。年八十余,吟咏不衰。子宾硕,以诗文淹博称。”
同卷余诗前作者名下,有“余怀,澹心、无怀,福建莆田人,《味外轩稿》”字样。下录余怀诗共24首。
卷六之高兆传略为:
“高兆,字云容(应为云客),号固斋。福建侯官人。广交游,善小楷。著《遗安堂草》。”
高诗前作者名下,有“高兆,云客、固斋,福建侯官人,《遗安堂草》”字样。下录高兆诗4首。
卷十一之纪映钟传略为:
“纪映钟,字伯紫,一字擘子,号戆叟。上元人。贡士。喜交游,足迹遍字内,与傅山友善。晚年侨寓仪征,构草屋数椽,临溪上,题曰‘让风拒雨’。有《真冷堂集》。”
纪诗前作者名下有“纪映钟,伯紫、戆叟,江南江宁人,《真冷堂诗稿》”字样。下录纪映钟诗36首。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还藏有手抄本《卓选遗民诗小传》,乃翁长森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夏日从著名藏书家丁丙(松生)处借得“原本”抄录而成。(注:该书封面标有“己丑夏日叚丁松生原本择抄目录”字样。)该本第三、六、十一各卷之余、高、纪三人传略,与上述所引文字全同。可以证明:南图所藏之康熙刊本《遗民诗》,确为比较完备者;该书关于三人传略文字与诗作,是保持原状而未经涂删的。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著名诗人袁枚在江宁知县任上,主持修订了《江宁新志》。该志卷十九《文苑传》收录余怀小传,全文照录《遗民诗》卷三的文字(仅个别字略有出入),并注明引自“卓子任《遗民集》”(注:《稀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第11册。)(当为《遗民诗》)。这一事实不但可增一旁证,而且说明,直至乾隆前期,《遗民诗》卷三关于余怀传略的文字并无变化。
宣统二年庚戌(1910),有正书局据康熙本《遗民诗》影印,改名《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然而将两本对校,可以发现:有正书局本中,余、高、纪三人的名字与传略文字统统没有了。如卷三,原余怀传略处,两行空白;余诗24首仍存,诗前原作者姓名及其下文字处,一行空白。卷六与卷十一也如此。这种“诗存人废”的空行现象,是明显的挖版、涂版。这是有正书局本与康熙原刊本之最重要区别。它说明,有正书局本所依照的,并非较完备的康熙原刊本,而是经过严重挖、删的本子。顺便提一下,有正书局本中除上述三处之外,还有不少挖、涂之外,如方孔炤、方以智的传略等,在此不一一细述。(注:《遗民诗》康熙刊本被挖、涂情况,各本不尽相同,故完备情况各不相同;又,有正书局本亦有对康熙刊本之增补。不具体叙述,唯请读者留意。)本来,在清末民初的条件下,寻访比较完备的《遗民诗》康熙刊本,并加以考订,尽量恢复原著的面貌,并不是很困难的。很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以至《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出现了诗存人废的现象,造成读者的茫然与研究者的歧见。这是一个不应有的失误。
《明遗民诗》出版之时,清朝已灭亡了半个世纪。该书的编辑者完全有条件去寻访较完备的《遗民诗》康熙刊本,并与有正书局本校核,对其失误加以纠正。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做,反而误以有正书局本所依为“原刻本”,而据以排印。(注:《明遗民诗》之《出版说明》。)一部有重要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著作,两次重印刊行中,一再出现失误;而且,讹谬流传至今,中华书局本已有30余年,有正书局本竟长达80余年,这实在令人惊讶。现在,该是进行廓清与纠正的时候了。
问题的根源
有正书局本诗存人废的空行现象,确实源于其所据以影印的康熙刊本《遗民诗》,只是遭到严重的挖、删罢了。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颇为奇特的挖版、涂版情况为什么会在《遗民诗》中出现?是什么时期、什么条件下出现的?
邓之诚先生在《清诗纪事初编》卷一《纪映钟》条中指出:“映钟负一世盛名。及没,乃无人为之表幽;卓尔堪《遗民诗》选其诗,削其姓名:俱不可解。”这说明,对《遗民诗》中诗存人废的情况,邓氏已注意到,只是认为“不可解”。奇怪的是,他在该书卷四《卓尔堪》条中又说:“晚节不终者,削其名,如纪映钟是也。”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许或是一种疏忽,但确实令人“不可解”。笔者对纪映钟缺少研究,并无定见;只是不明白,邓氏指其“晚节不终”有何根据?且邓氏也未指出卓尔堪何时“削其名”?更未解释何以仅有正书局本出现“削其名”的情况,而较完备的康熙刊本却并无此情况?
笔者以为,《遗民诗》遭挖版、涂版这种奇特现象,在清乾隆中期以后,是颇为普遍的。究其原因,盖与当时日益酷烈的文字狱及与之同时兴起的、持久而大规模的禁毁书籍运动有密切关系。
据《清实录》载,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上谕称:对所查缴的书籍,“其中如有诋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贻惑后世”(注:此下所引之上谕,皆见《清实录》。)。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又下令焚毁“违碍”诸书,并诏谕应毁书籍内有只须删改字句的,“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此后,又多次诏令各地铲毁书籍中“违碍”文字。如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上谕,要求各省“务宜实心查办,俾搜查净尽”。清政府查禁书籍的重点,是明末清初的著作。《遗民诗》名列其中,属“全毁”之书。军机处在上奏乾隆皇帝的报告中称:“诗中词句狂妄处不可胜数,应请销毁。”(注:《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一,“军机处第十次奏”。)《明遗民诗》的《出版说明》说:“清代乾隆年间查禁书籍时,本书曾两度被列入禁毁书目中。”这是乾隆四十四五年的事,有案可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祸,挖、涂已刊著作中的“违碍”文字,就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对此,清政府也相当清楚。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十一月上谕说:所进之《青霞集》,“篇中凡违碍字样,俱行空格”。并指出:“此外各省坊行刻本,如《青霞集》之空格者,谅复不少”,就是证明。当然,挖、删、涂、改已刊著作,并非自乾隆始,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说是古已有之;但那毕竟是个别或较少数人的行为,与这时的情况无法相比。
由此可见,挖、涂已刊著作而造成的空格现象,虽颇奇特,而在当时确实很普遍。这是乾隆中期以后频繁、酷烈的文字狱与持久、大规模的禁毁书籍运动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封建专制制度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疯狂摧残的集中表现。严酷而血腥的高压政策,动辄砍头、抄家甚至灭族的严重威胁,以及望文生义的杜撰、曲解,无耻小人的告密诋诬,好事之徒的反复搅扰,迫使某些藏书者与书贾用挖、涂已刊著作的“自检”行为,或者叫“自行抽毁”来逃避灾祸,保存古籍,保护自己。黄裳先生引用前人诗句“雪夜闭门读禁书”,调侃地说:对那些“禁毁”的著作进行细密的涂改“想来都是在‘雪夜闭门’的情况下进行的吧?”(注:《榆下说书》,55~56页。)对封建专制统治者这种残暴手段及其严重后果缺少认识或认识不足,自然也就无法理解某些康熙刊本《遗民诗》中的挖、删而形成的空格现象,也就不会去进行必要而认真的考辨了。这正是从有正书局本到中华书局本一再出现失误的真正根源。笔者以为,读读《遗民诗》所选高兆、纪映钟的诗篇,如《兵至》三首等,就不难理解,在当时大兴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中,保存这些著作要冒家破人亡的巨大风险。因此,保存诗作而进行挖、删,是不足为怪的。
根据以上分析,大致可以判定,某些康熙刊本《遗民诗》的挖、删行为,发生在乾隆四十年以后至乾隆六十年这段时期,具体地说,当在乾隆四十四五年之后。
花样又翻新
但是,问题并未完全解决。笔者还想就余怀的情况谈点看法。
查阅清朝文字狱与禁毁书籍的有关资料,余怀并不是钱谦益等及各文字大狱中清政府所要明令查禁其著作的人物;细读《遗民诗》所选录的24首余怀诗,也无明显的“违碍”字句。《遗民诗》被禁毁是事实。但是,侥幸保存下来的《遗民诗》,为什么有的(不是全部)会出现余怀的名字与传略被挖、涂的情况呢?
余怀(1616—1696),福建莆田人。由于长期客寓江宁,故又称江宁余怀。顺治二年乙酉(1645)清军占领南京之前,他文名冠南雍,与黄冈杜濬(茶村)、江宁白梦鼐(仲调)齐名,人称“余杜白”(金陵俗称染色“鱼肚白”的谐音)。他曾是壮烈殉节的崇祯名相范景文(质公)的幕宾,为平安书记。清军占领南京以后,他奔走于南京、苏州、松江、嘉兴一带,从事秘密抗清活动。余怀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诗人,他的诗文甚有声于时,所著《板桥杂记》流传十分广泛,有深远的影响。陈寅恪先生指出,余怀并非寻常文士,而是“明末有匡世之志者”;入清,则“为复明运动中之一人”(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五章。)。
但是,《四库提要》卷一四四在评述《板桥杂记》时,指责余怀:“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
《四库提要》卷一三九在评述尤侗的《宫闱小名录》以后,针对余怀续为《宫闱小名后录》,又批评说:“怀亦选妓征歌,以风流自命。考证之学皆非所长。”并指责《后录》“乖谬殊深”。
《四库提要》的作者对余怀的批评、指责是否正确,这里暂不讨论。但是,以官方学术权威的地位,以纲常名教卫道士的面目,以判决式的口吻,连续两次指斥,应该说,给人们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指责余怀对“考证之学”并非所长,实际上从学术文化上彻底否定了他;而给余怀戴上“名教罪人”的帽子,则无异于最严厉的判决。戴震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卫道者“以理杀人”(注:《与某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注:《孟子字义疏证》。)这自然不能不令人深感畏惧。加之“当时官吏,妄揣意旨,额外蒐诛;小民惧祸,私自焚弃”(注:《清代禁毁书目》邓实跋。)。因此,挖、涂余怀名字与传略以保存诗作,躲避祸灾,也是自然而顺理成章的。挖、涂乃不得已而为之,可以理解;民族优秀文化却又遭受一次疯狂的摧折,实在令人扼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