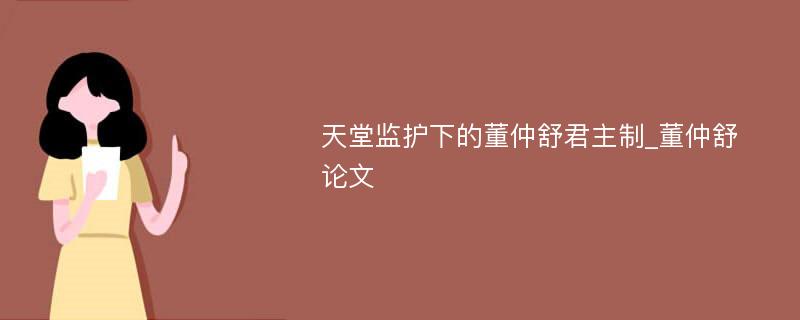
董仲舒的受天监护的君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君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权力是政治学必须研讨的一项内容,君权论是它的一个分支。在君主国里,特别是古代封建国家,国家权力就体现在君主的身上。在我国,君主的统治有着很长的历史,君权这个问题也就为更多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注意。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具有特色的见解,在当时和其后的封建国家里,无论是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是政治思想中必须研讨的一种理论。
“受天监护”的命名,是就董仲舒君权论的特点而酌定的。“监护”本是个法律专词,其意是指没行为能力的人,要受法定代理人的监督与保护。例如未成年的子女,要受其父或母的监督与保护即是。董仲舒的君权论,把君主置于天的监督和保护之下,有些形似,因借取此名,当然实质并不相同,用意只在显示其理论所具有的特色。
权力自天来,事天如事父
君主的权力从哪里来?由于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人世间就不会有它的来源,只有求之于人世之外的超人,那就是神。因有“君权神授”之说。在古代,世界上的君主国家,多采取这样的说法,所以就带有普遍意义。我国古代,对于最高的神,或称帝,或称天。自周代起,渐渐地,天就成了通常的称谓。董仲舒就把天作为最高的神,如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义》,以下引自此书的,只注篇名),“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郊祭》),就是接受了这个传统。
君权源自于天的说法起源很早。孟轲说过:“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师非本文所要谈,且置勿论。君是天为下民而作,天既作君,授之以权乃自然之事。《书》是周代整理出的文献,天作君之说载之于《书》,便可以说君权天授说的出现,不能晚于周代。实际在商代已有这样的意识存在。商王纣拒谏时说:“吾岂不有命在天乎?”(《史记·殷本纪》)以为他负有天命,就可以为所欲为,表明他的权力源自于天。我国古代的君权论所具有的这样的传统,可以名之为“君权天授”。董仲舒又接受了这个传统,把君主说成是天之所立。他这样说:“惟天子受命于天”(《为人者天》),“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三代改制质文》),“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深察名号》)。其所谓受命,就是受天之命。君主受天之命,代天以治人,接受了治人的权力。治人的应该是天,君主则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人是应该从天的,在人间就要从其代表——君主了。所以董仲舒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玉杯》)《春秋》是鲁史,孔子作。董仲舒把它奉为宝典,论事的是非,都以它的义例作为依据,所以提出“春秋之法”。又主张君主为民做出榜样,以换取人民的服从。他以人的身体作比说:“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为人者天》)用以收统治人民之效。统治人民,正是建立君权天授说的一个重要目的。 为了表明天和君主关系的亲密,于是就把君主说成是天之子。他说:“天子号,天之子也。”(《郊祭》)又说:“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是称天子。”(《顺命》)如何落实这种关系?那就是要君主对天尽人子之道,也就是“孝”道。他这样说:“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深察名号》)所谓孝道,人子对父母要养。对于养,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所以,敬还要摆在第一位。敬的具体表现是顺。把这番道理运用于君主对天,那就是养天、顺天。天无形体,就不能像儿子对父母那样的养和顺,只有借助祭祀的形式为之表达。在古代国家里,祭祀是很重要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军事关系国家的强弱兴亡,其为大事,可以理解。而祭祀竟与军事并列,其重视的程度,可以想见。其原因是在以神道设教,视天若父当即在其中了。在养天的方法上,董仲舒提有四时之祭,即春祠、夏礿、秋尝、冬蒸。其说是:“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麦也;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蒸者,以十月初进稻也。”君主按时以新产祭天,取亲先尝之意,故而谓之养。如果君主“过时不祭”,“则失为天子之道”(《四祭》),当然要受到谴责。再说顺,顺天就要像人子对父母那样,事在左右以尽礼,先请示而后行事。他说:“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今为天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是故天子每至岁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为地行子礼也。每将行师,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郊祀》)充分表达了这顺的意思。这样做,只不过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以树立君主的威权,从而起到镇慑人民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君主则被置于天的控制之下。就此他又为君主分配了另一任务,就是“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郊祭》),畜万民也是对天尽为子之道。
行使君权必须奉行天意
君主事天如父,就要像儿子受父母指使那样受天的指使。董仲舒说:“立为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郊祀》)受天使就必须承天意,这也是为子之道。他这样认为:“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楚庄王》)承天意意味着顺从天命,他说:“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也”(《汉书·董仲舒传》),接受了天命当然就不能违反,违反天命也就违背了为子之道。
既然要顺承天意,就必须明确天意是什么。天之为民立君,意在使之治人,这个问题业已明确。但是治人的什么?董仲舒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深察名号》)是要治民未善之性,使成善性。这当归于教化之功。他以为君主应担起这个教化的任务,君主“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竹林》)。所谓“正人”,即使人归正,改未能善为善。只有这样做,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君主。其强调教化之意可以概见,这正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所以要说成天之意,意在加强其必行性。
再一个天意,就是“以子孙畜万民”,这也是治人的一项内容。他以为“天志人(仁),其道也义”(《如天之为》)。天之心志,以仁义为本。君主上奉天施,承天之意,就要依天道行事。“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于是“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王道通三》)。“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诸侯》)这就划定了君主治人,遂行仁义,必以生育养长,利活民无已,爱利天下,兼利天下为事。这是一条“德治”的路线。他正是这样宣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因为“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上天有好生之德,故君主必任德教,这和重视教化是一致的。
如何把这些内容付诸实施?采用什么方法?也就是怎样来治。万变不离其宗,依然是照天行事。他认为“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同上)所以君主要“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如天之为》)明白了这些,就以之为根据,进行政事的具体安排,行使其权力。“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同上)以人事配天行,是“天人合一”的观点,这也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样就为君主制定了行为的准则,从而限制了他行使权力的任意性。
董仲舒认为君主行使权力,处理政事,不必事必躬亲,而要“以无为为道”(《离合根》),“无为致太平”(《天地之行》)。其谓“无为”,也是顺从天道。无为之为天道,在古代,已为多人之共识。后汉王充这样说:“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论衡·自然篇》)更早一些时候,春秋时孔子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王充曾为指出:“夫天无为,故无言。”(《论衡·自然篇》)无言是无为的一种形态,可以为证。君主实行无为的,古亦有例。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舜是传说中的圣人,他的举措是可以垂范后世的。董仲舒进言汉武帝,要像虞舜那样,“垂拱无为而天下治”(《汉书·董仲舒传》),“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保位权》)他提出“执一”这么一个概念,把“一”看做是天的常道。他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天道无二》)执一就是要君主奉行天道。
他在倡无为的过程中,竟把君主神秘化,而提出贵神的主张。他说:“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声之不闻,故莫得其响;不见其形,故莫得其影。”(《立元神》)这样,君主就自我封闭起来,成了神秘人物。但君主是个现实存在,封闭是不可能的,而这样做也不便于君权的行使。于是他解释说:“所谓不见其形者,非不见其进止之形也,言其所以进止不可得而见也;所谓不闻其声者,非不闻其号令之声也,言其所以号令不可得而闻也。”(同上)就是说,不使臣下摸清君主的底数,使之神鬼莫测,君主对之好进行驾驭,以实行集权专制,即所谓“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事情就由这备具之官来做,“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而坐收其成,“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离合根》)。“群臣分职而治,各敬其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君得载其中”,君主就在群臣奋进之中为之左右,结果是“功出于臣,名归于君”(《保位权》)。群臣操劳,君主获利。自然这是为君主谋划的一种如意算盘,但也会产生防止君主滥用权力的效果,不妨说这也是董仲舒不想使君主多做事的一种愿望。他想望君主“引贤自近,以备股肱”(《天地之行》),“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汉书·董仲舒传》),执行一条任贤的路线,以贤能充任百职,这样,君不自虑,便也政通人和了。那正是“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君主无为,任贤则是其必要条件。他说:“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贤,谓之主卑国危”(《精华》),任贤被提到一定的高度,非如此不足以顺天道。
违背天道,天便进行谴告
既然天授君主以命,以子相待,就要保护和支持君主行使权力,这无庸赘言。在君主顺行天意时,国应如此。倘使君主违反了天意又如何呢?又怎样使君主体察到他之所行是顺天,还是违天了呢?董仲舒对此做了解答,认为对君主之行是顺天还是违天,天都有所表示。“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汉书·董仲舒传》),天人是相感应的。君主行使权力顺天,天便示以正常之象。其如“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此圣人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全汉文》卷二四《董仲舒》)“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郊祭》)如果君主违天行使权力,天便示以非常之象,有灾异出现。对灾异,他界定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乃先至而异乃随之。”(《必仁且知》)又说:“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谓阴阳相荡而为寝诊之妖也。”(《全汉文》卷二四《董仲舒》)天现灾害,就是指示君主的施政出了毛病。他说:“今灾害生,见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郊祭》)天现灾异,实是天对君主之违天提出警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而“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必仁且知》)。其本意是,“灾者,天之谴也;异也,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故畏之以威”(同上)。实行“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二端》)在此情况下,君主就该有以自省,正己之政,以副天意。否则,便有更糟的事情发生:“(天)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而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必仁且知》)董仲舒两次三番这么讲,无非是想借天之力使君主知所警惕,不敢滥用权力,以实现“太平之世”,“天下和平”。但其味即苦且辣,君权在握而傲慢的君主,是不容易接受的。有一次,辽东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便殿发生了火灾。借此机会,他建议汉武帝诛杀亲戚贵属在诸侯之远正最甚者和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并说:“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甚罪者重,燔简罪者轻”(《汉书·五行志》),以耸听闻,当即被汉武帝斥为虚妄,下吏当死,险些丧了性命。而其以天监督君权行使的意图,用心却是良苦的。
简短的论评
董仲舒这个受天监护的君权论,把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无疑问这是迷信神学,这是他的理论的一大缺陷,谁也不能否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另外的一面却更是应该注意的,就是在这种迷信神学的掩盖之下,讲了些什么东西。细加玩味,就不难发现,他是在通过天的监护,使君权受到一定的制约,而做些有益于政治,有利于人民的事。这样,其意义还是积极的。
谈到君权,在封建时代,都面向君主专制。诸多理论所探讨的问题则是如何遂行专制,巩固专制。在这个问题上,法家的理论最为突出,也最为典型。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就提出过法、术、势的主张。法是统治人民的规范,势指君主的权位,术是驾驭臣下,使之俯首贴耳为他服务的权术。他认为君主行使权力,必须掌握这三种武器,以防止权力的下移。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君无术则弊于上”(《韩非子·定法》),做到君主集权专制,不容侵犯,是一种君权绝对论。董仲舒的君权论,权源自天,一样维护君权,而且他也这样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威不可分,……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保位权》),主张专制。但君主却被置于天的监督之下,君主要看天的脸色行事,君权就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能是绝对的,这一点与韩非就不同了。有人说,既说董仲舒的君权论也在讲求专制,却又说受到一定限制,其中似有矛盾。其实不然,专制是要君主维护其威权,意在对人,受到限制,顺从天意,则是对天。而这限制,相对来说,也有利于维护其威权,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还有,在董仲舒,极端重视君权的实际运用,非常重视君主的自律,如他讲“天志仁,其道也义”,对仁义的界定则是“仁者爱人”,“义在正我”(《仁义法》),“正我”就是自己约束自己,与受天监督是一致的。在韩非,这是不可有的,韩非所着重的则是君权不能受到损害,其他均非所问。这一点,就显示了董仲舒君权论所具有的特色。
董仲舒要君主奉行天道,遂行仁义,生育养长,利活民无已,爱利天下,兼利天下。具体做些什么事呢?他提过许多,一一列举是不可能的,现只举他就所谓五行之变提出的补救方法中的一些事以为例证。如“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举贤良,赏有功”,“省宫室,去雕文”,“举廉洁,立正直”,“忧囹圄,案奸宄”(《五行变救》)等,都是澄清政治,缓和社会矛盾的一些作法,直接间接都会给人民带来一些好处,因此就不能因为覆盖在迷信神学之下便一概抹杀。当然也不能因为其内容有积极的一面,便忽略他借助迷信神学以贯彻其主张的消极的、落后的一面。其所以要借助作为人格神的天之力,充分暴露了他所处无权者阶级地位的软弱性。他无力毫无掩饰地直向君主陈说他的政治主张,企图在天的掩护下,使君主接受他的意见,当然这是徒劳的。虽然在贤良对策中,他的“天人三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而受天监护的君权论却未受到厚爱,就连他本人也没能够留在中央,而被送到外藩去做骄王之相(事见《汉书·董仲舒传》),命运是悲惨的。但他留下的这套君权论的理论,却给予后世极大的影响。就在后来的封建时代,君主们像是接受了这种理论,特别是灾异谴告。每当灾害发生,君主便来个下诏罪己,说自己罪孽深重,在灾害地区搞些减免租赋等的措施,用以愚弄人民,缓和人民怨怒的情绪,与董仲舒改良政治的企图相差甚远,已非原来的本意了,但也显示了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