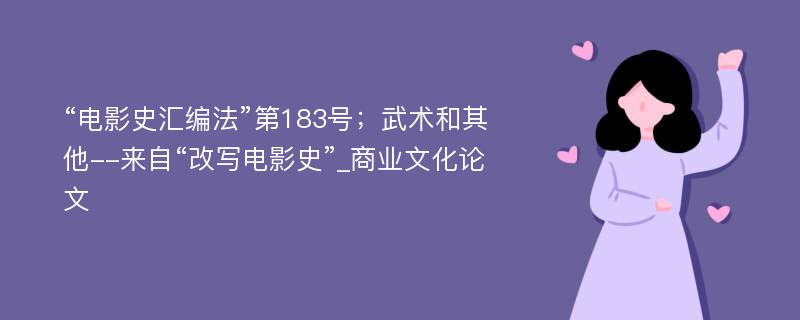
电影历史编纂法#183;武侠及其他——从“重写电影史”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写论文,开去论文,及其他论文,武侠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比上个世纪,今天的电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需要我们的电影研究具有一种新的视野。新世纪电影的发展变化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现在电影是一个多媒体形态,不仅有大银幕,还有从电视到手机到互联网这样的传播媒介,媒介形态的发展肯定反过来会影响到电影的存在形式和我们对电影的认识方式;另一方面,在这种新的媒体格局中,我们对电影的认识和研究也需要放到更广阔的媒体体系中。过去我们说电影是艺术,或者是一个对现实记录再现的媒介,又或者是一个艺术家表现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可能就需要把电影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体系当中,放在现代媒体发展和社会交流的体系当中。把电影看作是一个交流工具,在这个基础上回头再研究电影的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作者想往作品里放什么,或者作者放了什么,又或者作者在作品里面所表现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在艺术发展上面有什么价值等。在更大程度上,电影研究所关注的可能是电影在现代社会交流体系和社会建构当中是如何来运作的。我想从这个基础上来研究电影,特别是研究电影发展的时候,可能就要求我们具有一种更宽的视野。 同样,史学研究也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这个学术视野是什么?怎么来开拓我们的视野?怎么来创新?中国的电影史学研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有了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但是真正的比较系统化、学术化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仍然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它的出现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使中国电影史进入了学术化的领域。从那时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多研究成果,有很多不同的学术表述。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下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和看待这些学术成果,对将来做电影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现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重写电影史”,我想就从“重写”开始说起。所谓“重写”是已经有一个东西,我们再写一个,第一次之后的每一次写作其实都是重写。问题是把“重写”作为一个定义、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它究竟与既有历史描述和历史书写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处在什么样的位置?“重写电影史”的提出是借鉴了以前所谓“重写文学史”的概念。“重写文学史”本身就是对已有的历史表述的批判,是对文学史的重新描述,对于“重写电影史”来说也是这么一个思路。在重写的过程中,改正那些认为以往电影史表述中的问题,重新按照新历史观来建构一个新的电影史。所谓“重写”,重点在“重”的时候可能会更侧重于反思和批判,重点在“写”的时候可能会更侧重于超越和重新梳理。如果“重写”太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重”上,会影响到“写”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史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只是推翻旧的和建构新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延续和深化的过程。这其实是中国几十年来不断革命的思想方法的一种反映。这种“革命”思想能够指导学者把历史上一些错误或偏激的结论纠正过来,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整个电影史学研究来讲,翻案并不一定代表了新的思路,往往只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差异而已。就像我们看到,时代变了之后,对许多事情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判断都会随之变化。以新时代的观点看待对过去时代的评价和判断,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看到其不合理的地方。 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的确是在重新发掘和梳理历史资料的同时做出的,这些重要的新的发现发展了我们对中国电影历史的认识。可是我们也应看到,在“重写”历史的时候,重要的是认识过去的历史判断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建构的,它和其所处的时代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在很多方面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批判、否定就可以用新的结论来代替的,而是需要一种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对以往的思维方式有所超越。重写是一种带来新的历史方法和视野的研究,有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突破,才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历史现象的理解,挖掘出前人没有看到的历史维度,这种重写才更有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就涉及到我们在史学研究上如何运用更广泛领域当中的学术成果,并把它引进到我们的研究领域当中来,帮助我们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每一次历史写作都既是一次新的写作,又是对已有的研究领域的一次历史重写。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希望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认识方法和研究视野,这种“重写”的过程仍难免有许多陈词滥调存在,也有许多从表面上看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仍然在用一种新的历史描述来论证一些既有的历史认识。而我觉得历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走出这种简单化的方法,需要我们有一个新的方法论视野来对电影进行一些新的观照,用新的发现来丰富和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我本科念的是历史系,当时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位大家。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大课时说,学历史不要马上指望成为一个“青年历史学家”,青年历史学家往往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历史研究是需要对历史资料进行广泛、艰苦的收集整理,对历史本身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深入的了解。没有扎实的史料积累,即使是正确的观点,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时也不一定能准确地把握。特别是要切忌只关注支撑自己观点的史料,轻易地否定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以为自己掌握的这部分知识就是真理。不能够轻易地否定前人所做的研究成果,即使对于我们要进行批判和超越的对象,也要持着一种谨慎和尊重的态度。 白先生还说到历史研究需要注意“说‘有’易、说‘无’难”。这就涉及到历史研究中史料和逻辑方法的关系问题。一个史料能证明某事发生过,但是如果要说没有,就是举了99个不存在的例子也不行,第100个可能性它仍然存在。推翻一个既有的否定性表述时,往往有一条直接证明性的史料就能解决问题,但推翻一个既有的肯定性表述时要复杂得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从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和辨析,通过运用理论对充分的历史资料进行逻辑分析,才能够说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东西不可能存在,或那个事件不可能发生。 我们开始学历史的时候,正是“文革”刚刚结束。“文革”对过去的历史研究进行了很多否定和批判,而当时又面临着对“文革”中的学术思想及成果进行清理和反思的任务,大家也都认为这是一个积极创新的时代。白先生跟我们讲这些,就是要求我们在梳理过去、寻求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把理论和历史资料的关系尽量处理好,做扎实的历史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前后,人们在做史学方法研究中的史论关系方面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用当时的说法有两种观点,一种叫做以论带史,另一种叫做论从史出。“以论带史”在从50年代后期到“文革”曾十分流行,即要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历史进行重新阐释。这在“文革”中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表述,叫做“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当时许多严肃的学者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但是在当时的话语环境又很难直接反驳,于是从更加侧重历史研究方法的角度提出了“论从史出”的观点,主张对于历史的任何新的阐释都必须建立在对于史料的完整掌握和细致辨析的基础上。以这样的方法对历史做出新的理论总结,让新的历史观从严谨的历史表述中呈现出来,而不是把历史讲述简化成对新的历史观的论证过程。 “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对于“批林批孔”等“阴谋史学”深恶痛绝,“以论带史”一度销声匿迹。我们在大学里学历史时强调的主要是对史料发掘、整理和辨析的训练,这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能力训练让我们终生受益。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论从史出”胜利了。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许多西方新的理论蜂拥而入,让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学人感到眼界大开,对方法论和史学研究的创新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所以也对方法论方面的学习非常重视。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表述性的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后影响越来越大,给历史研究带来了一片新天地。“以论带史”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重新表现出活力。 在我个人看来,“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是史学研究两个层面的东西。“以论带史”是第一个层面。它是说在历史研究当中,方法论是认识历史的基本出发点。方法论和理论工具的差别,决定你对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和结果。它说明理论方法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就像我们现在说大电影,是把电影放在一个大的体系、一个文化体系当中认识,这样就需要引入关于文化、关于媒体、关于人的认识、关于人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式的认识。所谓现代电影理论就给我们认识电影带来一种新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拥有许多不同的视野和视角,对电影有新的发现的可能性。 但是在有了特定的视野和视角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研究仍然必须在既有的材料上,在已知的艺术现象的基础上来展开研究。“论从史出”就是在历史研究的具体操作的第二个层面上,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追求和还原的基础上。所以对历史的面貌,必须从史料的梳理和描述当中得出结论。真正进入操作层面上来讲我们必须得依靠大量的历史资料才能够让这些方法论落实,能够对于历史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表述和分析。 我们说在方法论层面上是“以论带史”,但是在操作层面上我们更需要“论从史出”。在一个新的方法论的视野下,对于史料的掌握和理解就都会产生变化。以往掌握的史料可能发现其新的意义和价值,以往认为没价值或与议题无关的史料会发现其具有新的认识价值。例如过去对电影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将其看作政治宣传工具上,这使得电影史的研究比较集中于作家作品,集中于社会内涵和艺术表达,所以,对于观众、经济运作等相对来说就不重视。今天当我们更多地把电影看作是文化产业和交流媒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更多地引入更广泛的文化、社会、历史的情境。特别是进入产业研究领域之后,对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角度和认识价值。于是,我们又需要引进许许多多新的资料,比如说商业运作、电影与人们的休闲方式之间的关系等,都可以做许多新的发掘。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用新的方法论就又需要有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历史资料研究,这样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发现。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理论更主要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寻找新的方法来开拓认识电影现象的新方式、新角度和新视野。这种方法论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结论,而是一种观照历史的新思路。一些方法论应用于其他历史领域当中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能够套到电影这样的领域里,这一点是必须切记的。对于方法论来讲,它是一个寻找新的切入方式和新的启示的过程,这并不必然在电影领域中得到与其他领域一样的结果。我们学习或引进新的理论用于电影研究,需要我们结合电影的具体历史现实,对特定电影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看它能否帮助我们对电影现象做出新的发现。这样我们的历史研究的任务也就不再是一个论证的过程,而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有了一个新的切入点之后,能不能够有一种真正具有认识价值的新的发现,这可能是我们在重写电影史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重写的电影史应当是用更广阔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对电影做出的一种更深入的发掘。 在这当中我们并不是完全排斥批判。过去有许多历史表述的确保留了很多时代的、历史的局限,以往的许多结论在今天看来是有问题的。白寿彝先生说对于以前的研究成果要持一种谨慎和尊重的态度,就是想强调对待已有的研究成果,需要放在历史里加以认识。当要推翻一个既有的认识、提出一个新观点时,前提就是除非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前人说的错了,否则后来者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即便对于我们要进行批判和超越的对象,也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前人对历史无知、或有意编造和歪曲历史,要持着一种谨慎和尊重的态度。我要说这些,就是想强调历史研究不仅是一个论证某种既有观念的过程,更主要的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对于既有的历史研究成果,一般应看作是前人对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掌握和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要做出新的认识时,就必须对这些资料进行一种新的整理、补充和辨析。 过去的时代确实有许多政治方面的限制屏蔽了许多东西,或者做出了一些今天看来不正确的评价。但是,在过去的历史表述中,时代的局限和历史学家对历史现象的真知灼见是通过具体的历史表述复杂地呈现出来的。反映时代局限的错误表述和评价往往是今天最容易辨识的,但是在过去的历史表述的文本缝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其他的东西。过去留下的许多错误可能不仅仅是一些可供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时,可能还会发现一些更有趣的东西。其认识价值可能并不一定在于它错还是不错,而是在于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些研究看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观念以及历史研究者与时代主流话语的对话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与那个时代历史观念和表述对话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前人对于历史的表述方式。今天看《中国电影发展史》,可以看到它有许许多多受那个时代局限的结论。对于一些作者和作品的批判性评价,今天看来无疑是有问题的。但是后来的不少研究话题又是基于这本书里面的描述和评价所生发出来的。比如说《小城之春》是近30年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人们怎么知道《小城之春》在艺术上很有特色呢?其实最初的原点恰恰是在《中国电影发展史》里面对《小城之春》做了相当细致的描述,特别是对其艺术特点做了比较正面的描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知道这是一部很有艺术特色的影片,知道费穆是一位很有创新性的艺术家。这部影片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几乎与许多重点介绍的进步影片相当,只是对这部影片做了一种否定性的评价。如果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讲,选择描述对象和描述方法及语言风格,是传递历史评价性信息的重要手段。按照当时的政治观点来描述一段历史的时候,许多不符合这种历史讲述需要的东西,完全可以不放进叙述当中去。就像《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叙述方针是以“党领导的电影事业发展”为主线,按照这一原则,像《小城之春》这样的影片显然是不能纳入这一主线的,完全可以不作具体介绍或不用如此大的篇幅进行比较细致的艺术成就介绍。 从历史编纂写作的角度看,《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写得有一点点杂乱。如果我们对比那个时代其他一些历史著作,如1955年北大版的《中国文学史》会感觉很明显。按照当时历史写作的惯例,以进步电影为主线可以写得更加清晰,并更符合那个时代的历史表述需要,一些不属于主线的东西完全可以仅仅批判几句。但今天读到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更像是一部“历史长编”的体例。它把许多资料放在那里,看来好像有些枝蔓繁多、叙述繁简失当,而这恰恰成了这部书的重要价值所在。从这些看似杂乱的叙述中,后人能找到许多新的意义发现和诠释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这本书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中来看,了解这些前辈学者的写作时,我们可能就会得出另外一种印象:这些历史写作者似乎处在一种难以逃脱的个体感受与历史叙述需要之间的矛盾和困境中。像《小城之春》这样的影片,写作者被其艺术所打动,直觉上认定其在历史上应有重要的价值,不写进去觉得非常可惜。但是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体系下,这样的影片又不能够用一种今天条件下可以做出的理解和评价方式进行讲述,于是有了这种详细的内容描述、正面的艺术评价和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并置的诡异现象。类似的现象在这部书中还有很多,不过具体的呈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重写电影史”仅仅靠政治批判是远远不够的。一些从政治角度做的翻案文章,骨子里还是在政治观念决定论里转圈圈。对一个历史对象的价值评价,基本的思维方式不变,只不过是政治观念的立场变了,但是从方法论角度来讲其实是很接近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能够跳出这种政治化的视点从更多的其他视角上认识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发现。这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走出简单的价值评判,而不仅仅是纠结于过去的结论是对和错。 至于在研究当中所谓“有”和“无”的问题。所谓“说有易,说无难”,是指肯定一个现象的存在是比较容易,只要有材料能证明就可以。但是如果否定一个现象的时候,就比较难,即使有人说没有,也只能说明就他所知没有。所以做出否定性判断时,不仅需要观点和直接材料,还需要对以前说有的人的资料进行分析和辨伪。需要通过逻辑分析,排除“有”的可能性,观点才能成立。比如说前些时间关于《定军山》和《难夫难妻》的一些讨论,就涉及对史料辨析逻辑的问题。 关于《定军山》的质疑的争论中,有一次在一个讨论此事的会上,我和陆红实老师都主张现在不要轻易推翻1905这个表述。《定军山》的认定今天看来确有一定史料缺失和认定及论证规范方面的问题。就今天可见的史料看1905年说和1908年说实际都是间接证据。由于当时认为是重要证据的访谈记录和胶片购置发票等关键史料的散失,对其可靠性的辨析和否认已难直接进行。对此的质疑也是由于现在看不到直接的证明史料,因为当时采访的王樾先生已经去世又未留下文字材料。质疑者又不愿相信关于当时见到购买胶片的记录的说法,认为这是维护已有权威的利益驱动所致。程季华先生曾经撰文把《定军山》拍摄日期说成是1908年,但成书时变成了1905年。可是作者为什么要推翻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一个学者推翻自己已经公开发表的结论而无合理理由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从1908改到1905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因此也很难认定是政治压力或利益驱动所致,而将其解释为有意编造历史。《定军山》一案由于当时没有撰写专门的考据文章,在论证规范方面的确有许多瑕疵存在。但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揣测各种非学术的原因和动机,而是寄希望于更有说服力的史料发现。在“重写”历史时,一般应当看作当时的历史学家进行了严肃的研究才推翻自己以前的结论。我们对此可以存疑,除非能够发现更有力的新史料才能推翻前面的结论。这里也涉及我们说过的对于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所应持的谨慎和尊重态度的问题。 之前有一篇在海外学习的中国学生的文章讨论《难夫难妻》是否是第一部短故事片时,他在列举最初拍摄的一批故事片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郑正秋、张石川等人回忆最初拍片时的几处细节的回忆都举了《难夫难妻》的例子,这些细节回忆恰恰可以作为《难夫难妻》在更大可能上是第一部短故事片的间接旁证。而文章作者却只根据对几部影片内容的简单记载,认为只有《难夫难妻》具有符合共产党宣传所需的“反封建”内容。论文作者继而根据自己的想象做出了推论,断言是《中国电影发展史》出于政治目的编造历史,硬把《难夫难妻》说成了是第一部故事片。这种研究让人哭笑不得,其思维逻辑完全被政治立场所左右。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并不能以此否定大部分“重写”研究的严肃治学态度及巨大成果和价值。但其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却具有一定警示性,如史料选用和阐释上以偏概全、无证据地假设已有成果不是严谨研究的结果、核心观点建立在缺乏严谨证据的假设和推论之上等。质疑《难夫难妻》是第一部短故事片的说法无可厚非,如果作者能够发现新史料证明此前还“有”其他影片拍摄,便很容易推翻前论。但在没有这种新史料的时候做出否定性论证,就要求复杂得多的考察辨析。仅靠《难夫难妻》的内容符合历史写作时代的叙述需要一条,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把写作者的利益诉求引进对历史现象的辨析不是不行,但需要有力的证据支持和严谨的逻辑辨析。我主要想强调的是,即使用新的理论方法和切入点,我们还必须不断发掘新的史料,而不能为某种情绪和立场所左右,依据简单的揣测就做出结论。 当代电影理论在对艺术作品分析研究时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症候阅读”,就是指在艺术家的整体创作或者一部艺术作品的内部都会存在许多矛盾的二元对立。这些“症候”恰恰可以帮助研究者透过表层的外在现象,挖掘隐藏在表层叙述之下的深层结构,这是对于作者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潜意识表达和隐喻性内容进行认识和阐释的切入点。其实在电影史研究中,也需要这种症候阅读的研究方式。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资料和既有的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裂隙和症候当中来发现可能的、新的对于历史的认识方式和结果。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认识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为了能让前面的理论表述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结合的过程中显得更加清晰一些,我想通过自己最近在做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做一点“重写”历史的尝试。这几年中国电影史方面出了不少成果,我也一直在想重新写一本电影史。我觉得其实所谓重写就是每个人要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和角度对于历史做一个再梳理,在这个梳理当中希望发现一些过去的历史表述中没有发现的东西。现在做电影史已经不再满足于只从艺术语言的层面,而希望引进更广泛的经济和文化的因素,放在更大的历史进程中认识中国电影。在设计具体的切入角度时,我想把电影作为一种参与大众文化观念和现代化改造的传播媒介,从电影与中国百年来追求现代化的发展变化间的互动入手,来梳理一下中国电影的历史。 在这里,我拿出一个我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大家沟通一下。在讨论民国初期的商业文化与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关系时,我想把中国电影放在中国从传统封建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大历史环境下,分析电影在上海市民对都市现代化理念接受和适应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我不仅把这时的电影看作创作者的表述,更看成是主流市民观众交流和沟通现代都市生活的理念,以及规则的媒介。 在我们以往的历史表述里一直对商业文化持否定态度。对国产电影市场初建的上世纪20年代电影,过去的结论认为这个时期电影是混乱和投机的。特别是认为其与“五四”以后的现代思想格格不入,在艺术上也觉得因为迎合下层观众的娱乐需求而观念陈旧,到30年代才有真正适应时代需求的电影艺术。我当年写硕士论文时也受这种历史评价很大的制约。现在对于电影娱乐产业的属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商业文化似乎具有了较大的理论合法性,人们不再把商业文化完全看作是负面的东西了。然而,在艺术史研究中,这种承认只是在“有需求就有合理性”的范围内,在认可娱乐需求的客观存在的前提下,主张商业文化存在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不应对其全盘否定和禁止。这最多只是把商业文化看作是无大害的东西,但是理论上的鄙视态度并未根本改观。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艺术评价体系中把压抑欲望、将欲望转化和升华的艺术看作是高雅的,而认同欲望合理性、表现欲望追求的艺术看作是低俗的。这种看法仍然在深深影响着人们对商业文化现象的评价。 我想举武侠文艺的例子,包括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在内。武侠文艺虽然在封建时代后期已经出现,但到民国初年才进入急剧发展的阶段。先是武侠小说的流行,紧接着被大批地改编成电影,成为非常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武侠最初流行的上世纪20年代,正是“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这时新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对于武侠几乎无例外地都持着鄙夷和批判的态度,比较典型的是茅盾先生关于武侠的文章。他们把武侠看作是旧的封建时代的产物,是一种企图把人们拉回封建时代的东西。在几十年里,主流文化圈一直不接受武侠,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无论政治上是左还是右,都对武侠持批判态度,国民政府还数度查禁武侠创作。这种现象直到60年代“邵氏”武侠电影和金庸等新武侠小说出现后才开始有了变化。特别80年代一些海外学者重新评价武侠的文化价值,武侠才不再是被批判的对象,直到今天武侠研究已经成为某种显学。不过,人们论述到武侠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时,看到的仍然是其对商业需求和文化娱乐需求的满足。娱乐消费是人们的一种合理的基本的文化需求,作为电影这么一个媒体产物,满足人们的商业文化需求也是合理的,这就像我们今天对商业电影的评价方式是一致的。 但是当要对武侠文化的内涵进行梳理和评价时,除了认可武侠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积极联系之外,人们更多地还不是从积极的方面切入认识,而是关心武侠这个东西是否有害,或伤害多大。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在商业文化前提下,武侠文艺既然能够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就应当允许这种无害或无大害的东西存在。我个人觉得这种对武侠的评价和考察是远远不够的。娱乐消费需求是合理的,武侠等商业文化满足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所以这些商业文艺的存在也是合理的。这种认识逻辑没有错,但这种认识方式只是被动地承认了满足娱乐消费愿望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解决武侠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建构之中是否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从理性上对武侠仍持鄙夷和排斥态度,或者说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本身无法做出对武侠等商业文艺在文化表达上的正面诠释,故而只能从文化宽容性的角度接受了其客观存在,而不是认识到商业文化用某种积极的方式释放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内涵。就像今天对商业电影的讨论一样,人们看到商业电影满足娱乐消费,由此肯定了商业电影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做文化判断时却认为满足人们娱乐消费一定是以丢掉许多文化品位为前提的。如果说一个社会的商业文化永远是从文化意义上具有负面潜能的结构性存在,它会不会在不断前进的文化和社会当中长久地存留,而且能够不断地受到广泛的欢迎?它难道只是人们那些阴暗欲望的反映,只是满足人们的负面需要吗?我个人觉得如果把一些更广泛的因素引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不同的认识。 当探讨清末民初的武侠兴起时,我注意到武侠在当时的社会中其实面对的主要是一批刚刚进入城市、正在经历从传统乡村向现代都市生活方式转变的都市新移民。进入都市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改变,从而有了看电影这种聚集性娱乐消费的客观需求。从娱乐消费的经验基础和审美倾向而言,他们对于传统戏曲和民间故事比较熟悉。对于这些人,武侠讲述的这些故事是最适合他们接受的。但是,武侠文艺里面是不是仍然在传播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当中那些旧东西呢?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尽然。尽管武侠文艺中仍保留了许多旧的形式和内容,但是这些旧形式中却包裹着新的、现代的东西。比如现代武侠小说对过去封建文化的“忠孝节义”进行了某种改写,武侠里面突出强调了一个“义”字存在,并赋予了某些新的内涵。武侠世界里有一个独立的“江湖”,江湖有着自己的“武林规则”,这里包括不依附权势官场、以武功分高下、尊师重道、有诺必践等。这些“规则”包含着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独立精神、个人能力、竞争伦理和契约意识等诸多精神文化信息。在《三侠五义》等封建时代的旧武侠小说里,白玉堂这样的英雄最终的成功只能是投诚朝廷,得到皇帝的册封。但在民国的现代武侠小说里,“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相对政治权势的独立性。在武侠世界里,勾结官场者几乎一定是坏人。而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一定是蔑视陈腐传统、特立独行,又重情重义、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只有那些尊重武林伦理、不见利忘义的人才能成就为武功卓绝的一代大侠。在武侠的世界里,比武论剑是最常见的评价体系,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种争夺贯穿的是“能力至上”的原则。这一原则其实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价值理念。武侠世界告诉人们,在能力面前出身门第都不算数,谁的本事大谁就有地位。武侠世界注重师门传承,强调了教育和训练对能力培养和提高的重要性。通过教育训练得到的能力,主要不是力量层面的,更多的是见识和技艺层面。见识和技艺的提高是靠学习、传承和训练得来的,并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强者。武侠电影里女性常常是主角,如《红侠》《火烧红莲寺》《荒江女狭》等影片中,女侠原本是一个大家闺秀,手无缚鸡之力,但被一个恶霸所霸占、欺侮,就在自己的身体因被恶霸玷污而要自杀时,机缘巧合被某一个大侠给救了。然后她随大侠隐居深山,经过一段时间练得武功大成之后下山报仇。这时的女侠虽然仍是一个纤纤女子,但是那些比她孔武有力得多的坏人及其帮凶,最后都败在她的手下。观众在不断观看这种故事的时候,在满足情感宣泄和窥视需求的同时,也逐渐接受着女人失身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生存意义,坚持信念抓住机遇、学习掌握技艺和力量就能成为强者,这些都是在现代都市生活需要掌握的经验和理念。 我们从武侠文本的缝隙里还能读到许多现代社会的文化密码,比如权力关系、性别地位与呈现方式,在推崇“武林规则”背后也让人们知道某种契约精神的存在等。武侠故事用一种看似传统故事的方式给那些刚刚进入现代都市的人们提供许多关于现代社会规则的知识,让人们在娱乐欣赏的同时接受现代化改造所需要的知识和思维方法。除了武侠之外,其他商业文化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鸳鸯蝴蝶派文学里关于爱情的描写,也渗透着对于情爱的现代理解。尽管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对于爱情的表现也有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在封建时代爱情的表达总是与婚姻直接联系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是喜剧,反之则是悲剧,即使是婚外情最终也都要指向另外一段婚姻,而不会指向一种纯爱。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不与婚姻相联系的两性关系基本上都是性的吸引而非情爱,都是作为负面价值处理的。到鸳鸯蝴蝶派小说里才开始有不与婚姻直接联系的情爱表现。如《玉梨魂》里写梨娘促成小姑与爱人成婚,其实是在歌颂一份对精神层面的爱情坚守,将爱情表现与婚姻家庭伦理剥离,而将两性关系赋予更加浓重的情感色彩,这在当时无疑是传播一种更具现代性的情爱观。换一种观察和思考角度,这些通俗的商业文艺并不完全像当时精英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样诲淫诲盗,而是在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一种积极的建构性价值。这也是文化研究、性别理论、身体研究等新方法给我们认识历史带来的启示。当然引进新理论不是为了简单地套用,而是必须为我所用,帮助我们对中国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梳理和发掘。 近百年中国的历史的确是一个不断学习西方经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这种主动的学习主要由知识精英层面操作,大众更多地是通过日常生活,包括娱乐消费中逐渐习得的。我们深入流行文化表现的“症候”,选择有效的方法加以读解和阐释,就能了解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今天中国又进入一个商业文化空前活跃的时代,电影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及呈现方式也空前地丰富。在这种条件下,认识中国电影只靠过去从政治社会和艺术语言层面介入已经远远不够了,所以我希望中国电影的历史研究需要从理论方法和资料等不同方面进行开拓,对以往既有的知识资料进行梳理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打开和发现新的历史。标签:商业文化论文; 历史研究法论文; 电影史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定军山论文; 小城之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