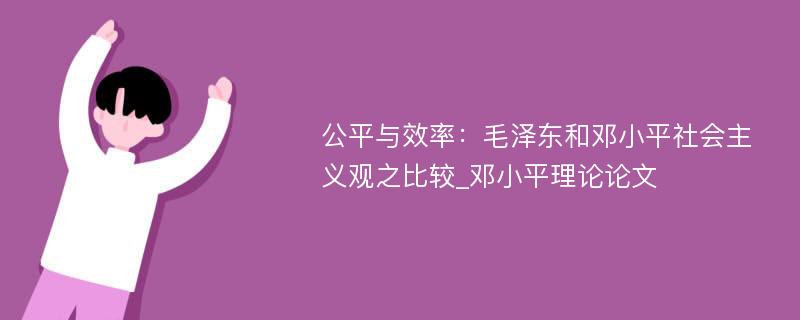
公平与效率: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效率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4年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过一个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政策,是对“文化大革命”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实际上是用婉转的口气,肯定了他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制度,因而,他们都为盟实现这一社会制度而终身奋斗不渝。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它既公平,又有效率。即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既能保证社会生产力更快地发展,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贫富悬殊,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社会物质、精神财富方面,获得最大的公平权利。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这里的“时间长”、“痛苦”,就是指效率低下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这正是毛泽东坚决摒弃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理由。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就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首先表现为它的生产效率“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因此,他坚信农业合作化能使全国大多数农民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并为大规模的轻工业提供发展的基础;同时,农业合作化更能避免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痛苦。同样,只有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发展。
邓小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理由,也是着眼于效率与公平。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按照这种逻辑推断出来的著名结论。
同时,邓小平也始终认为,社会公平或者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另一个体现。他多次指出:“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概括性论断。这个论断与前述毛泽东的论断相比,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结为它的公平与效率,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和邓小平既然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于这个基本点的一致理解,应该说毫不奇怪的。
二
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公平的涵义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观点差异。
一系列事实表明,毛泽东的公平观带有强烈的共产主义色彩,存在着急于追求完全无差别境界的思想倾向。这主要表现为,他不仅认为消灭阶级、剥削及贫富悬殊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而且他也一直相信,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差别及体现在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因均能造成事实上的财富分配不均等,从根本上说,也是有悖于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因而,也必须立即着手予以缩小或限制。
“文革”期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其精神实质,就是试图把全国各行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社会组织,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社会差别(包括三大差别)。在1974年下半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明白表示: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公平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必须开始实行,否则,就是“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可以理解,造成毛泽东这个重大理论失误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毛泽东个人早年的思想历程都可能对此负有相当的责任。但在我看来,相信更大的社会公平必定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因而对社会主义的公平过份看重,恐怕是毛泽东如此执着地追求超越时代公平的直接思想原因。
毛泽东一贯相信,人民群众天然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他就强调:“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穷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只要积极宣传和引导,这种积极性可以在全体人民中占有优势地位。当然,事实的真相却是:“我们曾高度赞扬的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既然人民群众被认定为天然具有追求公平、均等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是:能够满足他们这种天然要求、保证最大限度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为他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与可能。因此,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并不否认,社会公平程度的大小,也就是公有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群众觉悟程度这两个基本因素,但实际上他却相信,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前提。在他看来,公有制水平的提高及人民在物质精神生活方面差别的相应缩小,就是对生产力的直接解放。这样,初级社转为高级社,高级社跃进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均被看成是解放生产力的直接手段。毛泽东在1958年的一份批语中指出,过渡到共产主义,首先必须增加社会产品;可是怎样才能极大地增加社会产品呢?毛泽东又指出,必须搞政治挂帅、群众运动,以及“逐步(进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在当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含义,就是缩小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正是基于这种公平能够保证效率的信念,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立即由衷地相信全国人民的生产建设积极性也急剧高涨,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因而发起了鼓足干劲的大跃进运动。
而当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巨大效率时,毛泽东不仅未能冷静地审视自己原有的信念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反而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认识误区,这就是把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及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尽如意,完全归结为敌对阶级或敌对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因此,不断开展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以净化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以让他们焕发出忘我劳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便成了毛泽东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手段。而当这种完全背离事实的见解和粗暴的斗争方式在党内外遭到越来越普遍的怀疑和抵制时,那些试图坚持按经济规律行事的务实领导干部,以及思想文化理论工作者,就成了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与原则、甚至为敌对阶级思想推波助澜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者”,乃至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尽管在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意识到了超大型的人民公社制度已超越了农民的觉悟程度,同意实行回复到高级社水平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体制,并在“文革”中也坚持了这个方针。但是,他也始终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公平的一贯理解。例如,在农业经营方式上,毛泽东坚持把集体经营看作社会主义的最后防线,再后退一步的“包产到户”,便被他视作完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在1962年断言:“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可以看出,毛泽东坚决否定“包产到户”的根本理由就是它违背了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至于“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完全避而不谈。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解,偏于看重公平一端的思想倾向。
总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理论上确实始终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体现为公平,也体现为效率。因而,他决不是民粹主义者或乌托邦主义者。他过于看重公平,就出发点而言,也是为了促进效率。毛泽东的问题,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时期所可能实现的社会公平作了过高的、脱离实际的估计,并且把公平同效率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劳动还仅是谋生手段的历史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不仅并不是总成正比关系,而且有时还往往成为一种两难选择。过高的公平要求,特别是个人收入方面的过于平均,在许多情况下会窒息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从而造成对效率的严重损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经济建设始终不能真正起飞,当与经济制度中过高的公平要求--“大锅饭”或平均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可惜,毛泽东始终没能认识到这一点。相反,毛泽东总是固执地从经济制度以外,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去寻找影响效率的原因与对策。这正是毛泽东时代纠“左”总不能彻底,而阶级斗争扩大化却愈演愈烈的主要思想根源。
三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看法,与毛泽东相比,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邓小平特别看重效率问题,认为效率才是公平的基础。他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极大地丰富物质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为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公平--按需分配奠定物质基础。换言之,在邓小平看来,公平问题,实质上首先是个效率问题;没有效率,即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却硬要公平,那么得到的只能是共同贫穷。而共同贫穷决不可能是社会主义。
其次,邓小平认定,为了保证效率,必须尊重物质利益原则。这是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明白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既是对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空头政治挂帅加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根本否定,又是随即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可以这么说,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理顺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物质利益关系,让直接体现物质利益原则的经济规律包括分配制度充分发挥作用,以此激励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及各个经济单位的积极性、创造性。
例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就是“抛弃了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今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物质利益更是其激励机制而形成的基础。
第三,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但是,从根本上说,共同富裕只是最终的目标,是要到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公平;在目前阶段,必须承认某种收入差别存在的合理性,而决不能急于缩小差别。这可以说是他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最重要的差别。
根据历史的经验,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而打破平均主义,尊重物质利益原则,鼓励多劳多得,却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尽管这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贫富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损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因此,他坚决主张: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和帮助大部分人、大部分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当然,邓小平还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个逐步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在他看来,现在可以做的仅仅是对一部分先裕富起来的个人征收所得税,鼓励他们自愿出钱办教育、修路,等等。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邓小平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它实际上赋予社会主义公平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涵义。按照这个思想,体现着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将不再是有悖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异物;相反,一定程度的收入差别反而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因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体现着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所以,它一被提出,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邓小平坚信:“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总之,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完全按照唯物史观,把公平看成一个取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范畴。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应该说是对邓小平这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准确概括。
作者注:文中引文均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邓小平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