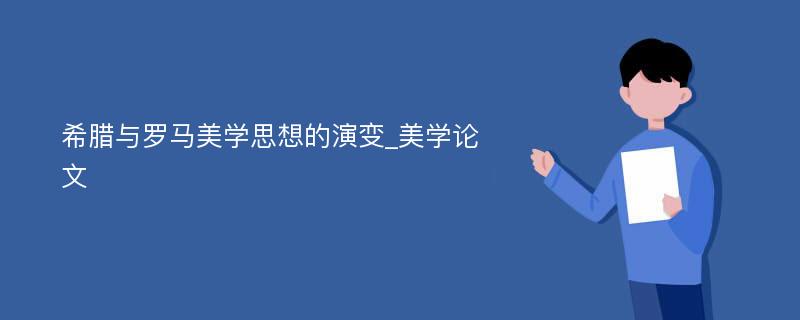
希腊化和罗马美学思想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罗马论文,美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2)03-0149-04
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到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的所有学园,这段时期的西方美学是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历时八百余年的希腊化和罗马美学历来是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勾勒这八百年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把握这段时期美学的全貌。
一
希腊化和罗马美学是希腊美学的自然承续。不过,与希腊美学相比,希腊化和罗马美学早期阶段——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派美学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换。如果说希腊美学的基础是对世界和世界的美的客观理解,人是客观秩序的结果;那么,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派美学则以人的主观感觉为基础,客观对象是人的思维和体验的结果。它们一改希腊美学偏重客体的倾向,把人的主体提到首位,追求人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斯多亚派的美学和伦理学联系紧密。按照他们的伦理学,“有智慧的人”是最高的道德理想。有智慧的人坦然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尽管他们遭遇许多不幸,然而他们在外界的折磨中砥砺德性,他们的内心始终宁静。斯多亚派不追求富有,也不追求日常生活的充裕。他们甚至把犬儒派创始人第欧根尼奉为自己的榜样。第欧根尼住在大木桶里,安于贫困和卑贱,轻视一切外物,追求内心绝对的平静。斯多亚派称颂这种平静的、安宁的有智慧的人,除第欧根尼外,还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因为他们都备受苦难的折磨。这种有智慧的人是斯多亚派的审美理想。
伊壁鸠鲁派也宣扬保持宁静的心境,并把宁静视为快乐和幸福。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自然哲学给他的美学打下了印记。他像早期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一样,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虚空是物的存在的地方和运动的场所,原子则是构成物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此外,伊壁鸠鲁为原子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原子既作垂直运动又作偏斜运动。作偏斜运动的原子和其他作垂直运动的原子相碰撞、缠结和交织,形成了世界。
公元1~2世纪的传记作家拉尔修指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说和人的自由、特别是精神自由的联系。伊壁鸠鲁的头上“没有任何主宰”(10卷113节)[1],他不怕任何折磨、任何艰苦,特别不怕死。“死不足畏的人,在生活中就无所惧。”(10卷125节)[1]伊壁鸠鲁以闲适的心情对待死亡,就像对待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从而达到心灵宁静这一理想境界,并在对这一境界的审美观照中找到慰藉和快乐。在他那里,审美快感是主体内在自由的一种表现。
伊壁鸠鲁自然观中的虚空概念也和他的美的理想有关。在他看来,生活在虚空中、遁入这种不存在中是一种幸福。这时候你已分辨不出周围是梦还是真——一切如雾、如烟、如幻。伊壁鸠鲁的审美意识就是人似醒非醒的一种状态。面对希腊化时期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伊壁鸠鲁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感到失望甚至是绝望,于是遁隐到内心世界。这种闲云野鹤的遗世独立、这种漠视权力名位的大彻大悟、这种于尘世喧嚣中的心如止水,是对社会现实的全面回避和彻底退隐。“不从事社会事务”就是他的一条律令(10卷119节)[1],连他的神都不过问世事。实际上,他的快乐和绝望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的美是遁入虚空,遁入精神的虚静(虚空和宁静)。
怀疑论派的创始人毕洛提出后来广为流行的三个术语。第一个术语是“悬搁”(epochē)。悬搁的意思是避免,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因为事物的本性不可知,对事物的判断也就不可能,应该悬搁判断。第二个术语是无动于衷、漠不关心(adiaphoron)。由于悬搁任何判断,所以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第三个术语是不动心、心平气静(ataraskia)。怀疑论的起因是希望获得安宁。2~3世纪怀疑论者恩披里柯在《毕洛主义概略》中指出:“‘不作判断’是一种宁静的心灵状态,由于我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任何事物。‘不动心’是心灵的不受干扰、安宁平静的状态。”[2](P.648)毕洛把不动心状态理解为幸福。
怀疑论是一种生活方式,怀疑论派美学是一种生活美学。由于不能对事物决定什么,不能对事物说些什么,我们应该完全摒弃自己的判断。采取这种态度的结果只能是沉默。怀疑论派在纷扰人生中对各种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也不是他们对知识秘而不宣。他们感觉丰富,机敏智慧,洞悉精神的奥秘。他们之所以沉默,是因为生活比词语和思想深刻得多,存在比人的意识深刻得多。生活和存在好比汪洋大海,而词语仅仅是大海浪尖上的泡沫。他们的沉默就是对滚滚红尘中各种尖锐问题的回答。只有沉默,才能不受任何烦恼,从而保持内心的宁静,达到一种审美的境界。
二
希腊化和罗马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把人的主体,而且把人的主体的某一个方面、能力和功用提到首位。这种趋势在希腊化早期美学中已露端倪。例如,斯多亚派把理性、伊壁鸠鲁派把快乐提到首位。人的主观心理能力得到更加细腻的划分。这在美学中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对各种艺术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在希腊化和罗马美学中期阶段产生了诗学、建筑学、音乐学的著作,特别是修辞学著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贺拉斯、西塞罗、维特鲁威和朗吉弩斯就是罗马艺术美学的杰出代表。在总体上,罗马艺术美学有两个特点:第一,研究趋于细密,对美的概念进行了仔细辨析;第二,在趣味和思维方式上趋于技术性和功利性,失却了希腊美学深刻的内容和旺盛的原创力。
贺拉斯以诗歌形式写成的诗学著作《诗艺》论述了诗和诗人,即创作客体和创作主体。这种两分法的论述方法常见于当时的修辞学、哲学、音乐学和建筑学著作中。贺拉斯把早期斯多亚派的诗学理论移植到罗马土壤上,从而确立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古典主义。从艺术形式上看,《诗艺》精致、细腻,有鲜明的形象性,富于表现力。贺拉斯作为诗人,受到尼采的激赏。然而在内容上,《诗艺》缺乏激情和思想深度。贺拉斯要求一切都规距合度,一切都简洁整一,他力图把希腊的内容纳入罗马固定的、甚至刻板的规则中。他在颂诗《纪念像》中把诗人的创作比作浇铸铜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马诗人所特有的、对明晰确定的艺术形式的追求。贺拉斯孜孜以求的就是建立宛如浇铸铜像的模式或范型,来规范当时的艺术创作。《诗艺》虽然也受到希腊美学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影响,然而《诗艺》和《诗学》的区别是明显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希腊美学的代表作,而贺拉斯的《诗艺》则是罗马美学的代表作。
作为罗马第一雄辩家,西塞罗的美学思想首先体现在修辞学理论中。修辞学是关于公开演讲的艺术,亦可译为“雄辩术”或“演说术”。西塞罗对词义的辨析具有天生的敏感,对美这个概念作了更加精细的区分。他把美分成威严和秀美,前者是刚强的美,后者是温柔的美,从而赋予它们以明显的伦理色彩。他写道:“因为有两种美,一种是秀美,另一种是威严,我们应该认为秀美是女性美的属性,威严是男性美的属性。”(1卷36章130节)[3]对美的这种区分,不仅适用于男性和女性,而且适用于自然和社会中不同形态的美,以及艺术中不同风格的美。这避免了过去比较宽泛的美的概念,有助于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审美对象,对以后的美学研究和审美欣赏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学者P·蒙泰尔屡次称赞西塞罗对美的概念的仔细辨析:“西塞罗比其他任何人更具有准确语言的感觉和趣味,他的哲学著作和批评著作使他对其他作家不加辨析就使用的那些概念,一一加以确定。”[4](P.100)
威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是全世界保留至今的惟一一部最完备的西方古典建筑典籍。它以系统的、通俗的形式总结了希腊罗马的建筑技术,这种总结带有折衷性。作者列举了许多建筑师的名字和著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了。作者也对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援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伊壁鸠鲁等哲学家的观点,然而作者对艺术作品更多地是技术体验,而缺少审美体验和哲学概括。《建筑十书》的技术性有余,而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维特鲁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技术的观察仔细精确。他的趣味和思维方式符合罗马时代的特点。在这种意义上,《建筑十书》完全是罗马精神的产物。
朗吉弩斯的《论崇高》是一部修辞学著作,然而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修辞学范畴。和贺拉斯一样,朗吉弩斯也是一位古典主义者。然而,他的创新大大多于对传统的恪守。在希腊罗马,“崇高”不是一个新名词。修辞学在阐述风格理论时就用过这个术语。西塞罗在《演说家》第6章、昆体良在《论演说家的培养》第12卷中就论述过修辞学的崇高风格。然而,朗吉弩斯不是在修辞学的涵义上,而是在美学的涵义上使用崇高概念的第一人。尽管他仍然把美和崇高当作类似的概念来使用,没有对它们的区别进行具体的界定,然而他对崇高的生动描述促使近代欧洲美学迅速承认崇高是一种独立的审美范畴。现代美学中的崇高理论是以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为起点逐步走向完善的。不过,对美学问题进行哲学论证并不是《论崇高》的任务。直到3世纪,新柏拉图主义才在希腊之后对美学问题作了深入的哲学思考。
三
以普洛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美学是希腊化和罗马美学最后一个成熟的理论形态。新柏拉图主义的命名本身就表明普洛丁对柏拉图的依赖。确实,普洛丁美学和柏拉图美学,也和亚里士多德美学具有共同性,它们都是本体论美学。和本体论美学大异其趣的希腊化早期美学是怎样过渡到新柏拉图主义美学的呢?只有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才能说明希腊化和罗马美学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不是若干松散的流派的拼凑。
希腊化早期美学向新柏拉图主义美学的过渡和转向,肇始于中期斯多亚派的代表巴内修斯和波西多尼。他们不满意早期斯多亚派的理论,用柏拉图的观点对它加以改造。巴内修斯作为“柏拉图的热烈的爱戴者”(57节)[5],力图恢复被早期斯多亚派中断的同柏拉图的精神联系。波西多尼把斯多亚派哲学和柏拉图哲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斯多亚的柏拉图主义。斯多亚派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原火说,认为万物由火生成。在人身上,原火就是暖的嘘气或“普纽玛”。波西多尼把斯多亚派火的普纽玛同柏拉图的宇宙学结合起来,把火的普纽玛理解为柏拉图的“奴斯”或理智,从而,普纽玛成为柏拉图的宇宙的原则和结构。宇宙由奴斯调节,奴斯渗入宇宙的各个部分,就像灵魂推动躯体的各个部分一样(21节)[6]。具有普纽玛的宇宙是波西多尼美学研究的对象。《斯多亚派流传残篇》中有一则关于宇宙美的引文,虽然没有指明这是谁的言论,然而根据内容来判断,一般认为是波西多尼的观点:“因此,宇宙是美的。这从它的形状、色彩和满天繁星中是显而易见的。宇宙是球形的,它优于各种形状。因为只有这种形状能够同时指向自身的各个部分:作为圆形,它的各个部分也是圆形的。”(2卷1009节)[7]这种观点和柏拉图如出一辙,波西多尼重新回到柏拉图的本体论美学上来。不过,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的,他承认主体的重要性,力图消弭希腊化时期美学造成的主客体之间的分裂。
不仅在审美理论上,而且在审美实践上巴内修斯和波西多尼都一改早期斯多亚派严峻枯冷的形象。作为真正的希腊人,巴内修斯喜欢平易温和的生活态度和自然中的合目的性。在他那里,宇宙、宇宙的逻各斯和人的生活是美的,他欣赏星空、自然、动植物、人体和人的精神的美。波西多尼也像他的师尊巴内修斯一样,喜欢观照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宇宙。
波西多尼注释过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他的注释对后人、包括对新柏拉图主义者产生过影响。波西多尼和随后两个世纪(1、2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的研究工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他们是以普洛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先躯。由于这个缘故,在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派三个学派中,普洛丁与斯多亚派关系最为密切。普洛丁的学生波菲利在《普洛丁生平》中指出:“斯多亚派和逍遥学派的学说以隐匿的形式成为他(普洛丁)的著作的组成部分。”(14节4~5行)[8]
1、2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从与波西多尼不同的方向为新柏拉图主义的诞生打下基础。他们是第五期学园派首领安提奥克的继承者,安提奥克就以在学园内从事斯多亚派哲学研究著称。1、2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精心构筑了存在的等级结构:在最高的神和地面之间有着广阔的空间,各种存在在其中形成完整的系统。处在最高地位的是最高的神、天外的神,它不是理智,是理智的本质和原因,只为紧随其后的理智所知觉。理智有两种,一种较高,一种较低,较低的理智与整个天相等同。理智下面是世界灵魂,世界灵魂栖居在宇宙内部。世界灵魂下面是可以看得见的神、星辰、精灵,它们分别由以太、火、气、水构成,充斥在月亮和地球之间。这里已经出现了三个本体:最高的神,理智和世界灵魂。它们可以被看作为普洛丁的太一、理智和世界灵魂三大本体的雏型。所不同的是,最高的神虽然高于理智,但还不是普洛丁所明确阐述的太一。理智的概念也有两种,不如普洛丁的理智那样清晰。然而无疑,晚期柏拉图主义者的这种理论,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诞生具有直接的意义。普洛丁用流溢说解释太一生成其他本体的过程。“流溢”这个概念是波西多尼首先使用的(1卷120节)[7],虽然普洛丁以柏拉图关于理式世界和感性世界等级结构的观点对它进行了改造。
普洛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关于太一、理智和灵魂三大本体的学说。他提出了美的等级结构:第一等级是理智美,理智美的根源是太一;第二等级是自然的理式美,人的灵魂美,以及德性、学术、艺术的美。最低等级是感性知觉的美,包括物质世界的现实美和艺术作品的美。在普洛丁那里,美不仅是实体的属性,而且是存在的本质。一个实体越美,它就越接近于真正的和永恒的存在。于是,美学成为一种本体论。普洛丁关于太一的学说使他的美学成为绝对的客观主义,一切东西首先要存在,然后才可能是美的。他的美学的这种形而上学基础是新的。另一方面,他的审美经验分析也是新的。美的等级结构按照流溢说自上而下地形成,而审美历程则自下而上,由低级美逐步走向高级美,最后返回太一。要观照和欣赏最高的、本原的美,必须“抑肉伸灵,收心内视”,即把眼睛折回到自身内部、观照自己深层的内心世界。这时候运用的不是观看普通客体的肉眼,而是“内在视觉”,即理智视觉,藉助它我们在自己的理智中观照抽象的、没有视觉形象的表象。普洛丁指出了在自身隐秘的灵魂深处、而不是在外部物质世界中寻求真、寻求美的途径。这对中世纪基督教美学家如奥古斯丁产生了很大的精神震撼。
普洛丁美学不仅是希腊化和罗马美学最后一个成熟的理论形态,而且是对希腊美学的总结。普洛丁吸收了早期希腊美学家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学说在普洛丁那里得到回应。他熟悉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著作,他的《论数》一文(《九章集》第6集第6篇)赋予数以重要的意义。这些数在他的太一和理智之间占据中间的位置。赫拉克利特认为相反的力量造成和谐。普洛丁持同样的看法(3集2篇16节)[9],他还复述了赫拉克利特的见解:“内在的和谐比表面的一致更为强大。”(4集8篇1节)[9]他对赫拉克利特关于美的相对性的观点也感兴趣:最美的猴子与人类相比也是丑(6集3篇11节)[9]。恩培多克勒的六本原说把爱和恨说成是火、气、水、土四种元素聚散运动的本原。恩培多克勒残篇17指出:“万物一时在爱中结合,变成单一,一时又因恨分散,彼此离异。”普洛丁多次援引恩培多克勒的这条基本原理(6集7篇14节)[9]。普洛丁也了解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及感觉和思想的关系的观点。
在希腊美学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普洛丁的影响最大。在柏拉图的所有对话中,普洛丁援引《蒂迈欧篇》的次数最多。在美学方面,普洛丁援引柏拉图对话最多的是《斐德若篇》。《斐德若篇》论证了灵魂的不朽[10](P.119),普洛丁接受了这个观点。他把灵魂分为世界灵魂和个别灵魂两种。产生于世界灵魂的个别灵魂要弱小得多,有时会屈服于欲望。然而,无论世界灵魂还是个别灵魂,它们都是不朽的。《斐德若篇》描绘了著名的灵魂马车,“诸天的上皇,宙斯,驾驶一辆飞车,领队巡行,主宰着万物;随从他的是一群神和仙……”[10](P.121)在普洛丁的《论理智美》中我们可以读到似曾相识的句子:“于是宙斯(在他领导的诸神中他最为年长)首先前来观照这种美,随后是其余的神灵以及凡能观照的精灵和灵魂。”[11](P.256)
普洛丁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137c~142a)和《理想国》(508a~509c)的基础上发展了太一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12卷的基础上发展了理智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比他的《诗学》和《修辞学》包含着更重要的美学思想。普洛丁几乎援引过亚里士多德的每一部著作,特别对《形而上学》作过详细研究。普洛丁美学和亚里士多德美学相类似,在普洛丁那里最美的是理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美的是“第一动者”,也就是奴斯或理智。
普洛丁是站在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之交的美学家,他的美学对上千年的中世纪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方美学史上,普洛丁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2-02-22
标签:美学论文; 柏拉图论文; 新柏拉图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希腊化时期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诗学论文; 伊壁鸠鲁论文; 建筑十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修辞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