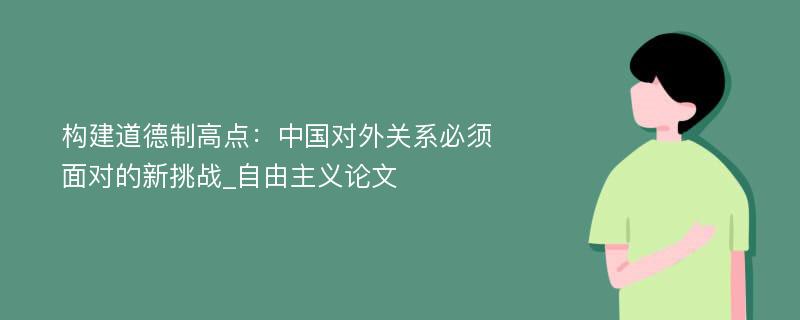
建设道德制高点——中国对外关系必须面对的新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高点论文,中国对外论文,道德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影响世界的物质能力有了显著的增大。然而,作为一个成长的大国,中国面临国际社会的负面评价也在增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主要集中在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而且把世界一些重要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归咎于中国,如失业、金融、货币、贸易、能源以及气候生态变化等。这种负面评价的结果是,对中国道德层面的批判形成了国际上广泛且不断深化的对中国发展的“恐惧”感(一种更为深入的“中国威胁论”),使得一些国家损害中国经济、政治利益的行为披上道德合理性外衣,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空间。出现这种中国的国力发展而又饱受非议的现象,除了外部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在大力发展物质力量同时,相应地建设道德制高点,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状态与中国迅速增长的国力不相称,因此,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道德制高点以应对这种局面。
一、权力作用的局限性和道德的不可或缺性
卡尔曾经说到,国际政治中起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是:权力与道德。“政治行为的基础必须是道德与权力的协调平衡”,“在政治中,忽视权力与忽视道德都是致命的”①。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自不待言,弱国无外交,国际关系中的无数历史事实表明,没有实力将无法获得和平、实现正义、塑造道德。但是,国家的行为都需要有国际道义来辩护或符合相应的社会认可标准,这说明了道义的力量在国际生活中是存在的。因为,道德的话语权是行为的语法结构,它作为一种意识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行为的精神框架,如同物质能力一样,构成人/国家行为的可能性要素或外部环境制约因素②。这种道德话语之所以产生,大致与人类都有把世界化为某种道德秩序的愿望③有联系,不论现实中这种愿望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因此,在国际政治中,权力与道德是共同作用互不还原的(codetermined irreducibility)关系。国家在对外政治的实践中,权力与道德的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注重物质能力(主要包括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建设无疑是重要的,任何时候一个国家忽视物质能力的建设将是“自废武功”,自甘落后。国际关系史中的无数事例表明了“弱国无外交”。比如“9·18”事件后,中国政府由于缺乏实力,且过分相信国际道义,奉行不抵抗政策,结果导致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受尽劫难。目前国际政治尽管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没有摆脱无政府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仍没有完全摆脱霍布斯式的无政府文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与民族利益,统一、独立与主权都必须是以强大的物质能力作为最后的保障。但在承认物质能力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决不能有物质能力决定一切的错误认识。物质力量本身也存在着局限性,而非可以绝对地决定一切。没有道德基础的强制性权力本身就会带来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一条有效的铁律。
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都对权力的局限性有过论述。卡尔曾经精辟地指出,只注重权力的现实主义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局限性:“极终目标、感召力、道德判断的权利和行动的依据”。正是缺乏这四个因素,只注重权力的纯粹现实主义无法阐明和解释政治过程所要实现的政治目的和愿景,因此就无法具有政治动员所应有的精神召唤力;由于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因此,任何时候人们都不会接受极端现实主义否定行为的“应然”价值判断;人的行动与思想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不完全受利益与地位的决定,就权力而权力的追求“无法为有目的、有意义的行动提供基础”。因此,缺乏精神支持的极端现实主义“还是不足以成事”。“纯粹的现实主义关注的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这使任何形式的国际社会都无法实现”④。这里,卡尔这位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先驱对只注重权力的现实主义(这与后来的新现实主义相似)提出了重要批评,批评它忽视了政治的目的与动机,简单地把政治内容归于单一的权力斗争过程,简单地把政治人视为只知道追逐权力的人。没有超越理性的希望与激情,社会就不可能尝试发展与变革;没有理想、信念与精神的人,是一个低俗的、平庸的、贫乏的人。缺乏了这些因素政治就不成为政治,也就不可能有政治目的、动机和领袖。因为,“每一种政治形态都包括了乌托邦和现实、道德和权力这样两种互不相容的成分”,“政治将永远是良知遭遇权力的领域,是人类生活中的伦理和强权相互作用,达成暂时的、不稳固的妥协的地方”⑤。所以,任何只讲权力,不问道德的政治是不存在的;任何只注重权力,忽视道德的政治是行不通的。权力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离开了目的,手段将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手段的使用常常为既存社会道德规范所限制的,不可能做到为了目的无所顾忌地不择手段。纯粹的现实主义只是把手段目的化,这样必然失去了政治的终极目标、感召力、道德判断的权利和行动的依据。
不仅卡尔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批判纯粹追求权力的现实主义局限性,像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也承认权力作用在国际政治中的局限性和道德作用的不可或缺性。摩根索在回顾17、18和19世纪权力平衡作用时承认了道德因素的作用,他指出,文化和道德因素的统一,是权力均衡赖以存在的基础,才使权力均衡的有益作用得以发挥⑥;他还认为,“从长远来看,以权力欲望和权力斗争为基石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制度,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和自我毁灭的”;“强权并不产生凭借这种权力去做物质上能做的一切事件的道德或法律权利。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也为了社会各个成员的利益,权力须受到限制,这些限制不是权力斗争的机制带来的,而是社会成员出于本身的意志以行为规范或法则的形式附加在这种斗争之上的”⑦。在国际政治中,正是道德的限制使得政治家和外交官“或者拒绝、或者在某些条件下拒绝考虑某些目的和使用某些手段,这不是因为从便利的角度看他们显得缺乏经验或愚蠢,而是某些道德规则设置了绝对的障碍”⑧。“当国家被谴责违反协定时,它们总是一无例外地声言它们是清白的、或者是有道德上的理由的。它们的辩白……是对国家有时完全漠视和常常违反的某些道德的间接承认”。“考虑到外交政策与道德之间这种关系,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一种独特的、特别的情势,而是人类一般情况的特殊表现。我们大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生物,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都属于人类。我们或多或少都努力认识到了我们所认同的道德原则”⑨。所以,摩根索在告诉人们,在不要夸大道德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也不要低估了它的影响,否认政治家和外交官在物质权力考虑之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⑩。
全球化时代使得国际社会的特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因此,在国际生活中权力作用的局限性和道德的不可或缺性在今天就愈加彰显。国家和社会的趋同性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的世界传播作用。由于跨国交往的频繁与多元,经济的相互依存、思想的广泛交流与传播,社会之间的融合度大大高于过去,国家间和社会间的共同认识也大大提高。这一方面加强了对权力强制效用的限制,如对待经济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跨国疾病传播问题等,权力强制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的相似性,特别是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的相似性,一些影响人类和各个社会的共同问题困扰着各个社会,如贫富分化、生态与环境问题以及各种社会排斥等问题,技术的进步使得跨国的各种政府和非政府联系与交流愈加便利,相互交流带来了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相似关注,由此形成了各种跨国的联系网络,这些网络促进了人们对一些问题形成某种共同的认识。这样,国际社会性特征得到空前的加强。这种国际社会性特征的加强有助于一个国际规范性结构的(道德作用)出现和增强,否则国际社会就难以为继。这里,不谈强调道德的理性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作家(11),就以注重权力的传统现实主义学者为例,如卡尔认为,“存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国家是它的成员。国家道德义务的概念正是与这种观点密切相关”(12)。摩根索从反面论述了这一问题。他哀叹民主化和民族主义摧毁了国际道德的制约体系和国际道德赖以发挥作用的国际社会,同时赞扬了过去欧洲基督教传统和贵族个人伦理下欧洲社会的道德对权力的制约作用(13)。对像葛兰西主义学派的学者如考克斯来说,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国际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的,建立在跨国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世界霸权必然对国家内外行为进行道德约束(以意识和制度形式表现出来)(14)。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社会趋势加强使得国家受外部道德的压力日益增大。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形成的国际规制都是建立在国际社会的更大的规范性道德框架基础上(15),处于各种国际规制中的国家行为必然受更多的国际规范的约束,进而受到道德的评判。
二、目前的国际道德制约现状
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及在其背后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特征(16),这种体系与秩序尽管自19世纪以来内在的内容发生过一定的变化,从古典自由放任主义一定程度转化到新自由主义,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又向自由放任方面回归,但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没有发生过变化。因此,在这种体系中,自由主义体现出来的伦理是这种国际体系与秩序的道德精髓。尽管存在着一些希望超越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如社会主义以及一些反自由主义的运动,但其道德诉求也是从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这种世界性的道德体制形成的原因在于英国与美国这两个自由主义国家及其社会的塑造,是这两个自由主义国家把自己的国内社会秩序推广到整个世界的产物(17)。“自由、平等、博爱”是其自由主义道德伦理的最重要标识,用来界定公平、正义等道德标准,以及民主、人权和人道主义等概念。尽管这一伦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虚伪性和片面性,存在着三个概念内涵上的模糊与争议,存在着集体与个人道德约束和取向上的矛盾性。但是,由于强权塑造带来的“建构性”,人们普遍把这一自由主义的道德精髓(虽然有着不同的定义)作为把世界化约为某种道德秩序的参照。因为,不论是世界秩序或者是国内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还是造反者/变革者,都大体用这一道德口号作为其行动的道德依据,把自己作为这一道德秩序的化身,把对手作为这一道德标准的违反者和破坏者。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目前整个世界的道德伦理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特点,进而对国家的内外政策施加了某种道德约束。
目前国际政治所具有的存续与变革共存这一过渡性特点意味着国家在世界舞台上面临着自由主义道德约束的压力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的:一是传统的国际政治道德压力,二是自由主义道德伦理在面对新的现实时所发展出来的新的道德压力。
国家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成员,它本身就要承担由此带来的代价,即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传统的国际政治道德约束把这种义务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国际法的原则之中:尊重他国的主权、民族平等和独立/自决、承担国际条约、协议和国际法的义务,承诺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国家的政策手段;遵守国际外交制度,和平与战争时期保护和尊重人类生命,保持“落后”或“少数民族”。这种国家间的传统道德义务大体旨在维护国家间的秩序。它是把国家作为国际法人来进行道德规范的,从格老修斯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家们一直都是这样阐述的。格老修斯把国家的主权称之为“管理国家的道义力量”(18)。这种传统的国际政治道德的核心就是尊重主权,维护和平与秩序。在传统国际政治道义之外,以个人或整个世界为目标的道德也成为国际社会道德的重要内容。这些道德内容在国际秩序大体得以维持时,其重要性就尤为突显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在维护与促进个人权利与国内社会福利上大致获得了共识(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国际社会大体认同国家在不损害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基础上促进本国社会福利或通过进行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各国福利的道德权利(这大致体现出了某种公平与效率的妥协或者是自由与平等的妥协)以及国家在促进个人权利上的道德义务。这些道德权利与义务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规范性框架在联合国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众多的国际组织原则和规范中得到了体现。无论在具体实践中,自由主义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基本的道德要求,但作为一种国际道德,它们已经完全为几乎所有的国家所认同。其实,如果认真地考察国际关系史,还可以发现,这种国际自由主义的传统道德要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过去的国际伦理上进一步发展而来,不论从内容还是在内涵上都是如此。内容上,承认了所有民族,而非西方民族的自由、平等权,内涵上更强调了各个国家的政治平等权、发展权以及对包括个人政治、社会以及发展权利在内的基本权利的保障。特别是个人权利,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与冷战结束,整个世界处于西方主导的态势有关。
然而,在这些自由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实践中,西方国家往往按照自己的经验、或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把其实施的具体模式不加具体分析地,或者有选择地,强加于其他国家,以西方具体的模式作为一种普适的模式,否认实践这些伦理的不同路径,由于西方国家往往处于塑造国际道德话语的地位。这样,往往非西方国家在国际道德上所受到的压力大大地高于西方国家。因为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它们在实现道德秩序上的能力、充分性、具体目标的优先性上,甚至可能是方式上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更因为世界上层建筑的设施(宗教、大学和媒体等)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它们无法塑造国际的道德话语权。尽管西方不时地滥用这种道德诉求,但不能否认这种道德诉求的进步意义,它们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标志。
按照考克斯的理解,国家之所以是有伦理的,是通过市民社会这个媒介来实现的。市民社会既是社会生产结构的产物,也是国家塑造的产物(19)。就是说,市民社会塑造了国家的道德伦理。国际政治大体也是如此。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市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全球化受损阶层和群体感到不平等、被排斥,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以种种议题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个具有跨国联系的市民社会团体,形成各种具有反全球化或反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社会运动。这种组织与运动尽管具有后现代的取向,但是它们的道德诉求的立足点没有离开自由主义核心。他们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所有受益于全球化的阶层和国家。而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国家的作用,引导和资助其国内的反全球化的市民社会团体,借以稳定国内的社会秩序。这样,一些西方国家借助这些组织与运动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在国家形态上与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国家进行批判就不足为奇。在这些跨国运动中,以保护环境与生态为宗旨的组织尤为典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工业化以及市场化带来的污染与生态破坏,使得人类对环境与生态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此产生的生态伦理一定程度上既是人类的“博爱”意识从关注人类自身命运发展到关注整个地球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产物,也是人类对世界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态与环境积弊的反思。这种伦理与反思是超越启蒙时代以来普适理性以及人类是世界普适模式的一种批判意识。因此,生态文明与伦理产生的国际道德制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就像在自由放任自由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过程中,解决公平与自由问题时出现过种种极端与自私一样,人类向新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种种极端与自私。如某些环保主义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环境问题表现出的批判态度有的是对发展中国家复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的不满,认为不发达国家原有的文明方式作为世界多元化文明的一部分不应该发生变化,从而破坏生态与环境。但他们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困、落后导致的包括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或相对脆弱和低下的境遇,以及整个民族由于贫弱和落后在国际舞台上遭受的屈辱和不公正。这大体算得上是一种偏激,即以生态伦理来否认其他道德价值存在的必要性。而西方某些产业集团以极高的市场价格转让环保技术,这大体也算得上是一种自私。
三、中国面临的外部道德挑战
中国有一位学者近来对中国的发展与落后做了一些对比很能说明中国目前的现状:总值大国vs人均小国,制造大国vs创新小国,人口大国vs素质小国,国土大国vs资源小国,经商大国vs威望小国,外贸大国vs外交小国,储蓄大国vs内需小国,消费大国vs生态小国,市场大国vs公益小国,税收大国vs社保小国,制药(医院)大国vs医疗小国,体育大国vs锻炼小国,官僚大国vs社会小国,腐败大国vs法治小国,教育大国vs学术小国,传统大国vs文化小国(20)。尽管这些对比关系有一定的偏颇,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步伐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既是缺乏现代化经验造成的结果,也是所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通病。因此,面对国际自由主义道德体系的诉求,它在促进个人权利方面,在平衡“效率、公平与环境保护”方面不论是能力还是手段都不足,其发展过程本身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是一个“他者”,按照自由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制度本身就不符合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规范”:缺乏政治自由,没有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以及作为社会良心监督者的独立舆论等等。因此,在一个由自由主义国家塑造的世界体系中,像中国这样的政府受到各种道德批判是十分正常的。中国社会出现的任何腐败或其他社会问题不论是否与政治体制有关往往都容易与这一体制挂钩。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按西方国家的标准进行改造,不论中国今后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保护环境上做得怎样出色,西方对中国的道德批判永远不会消失。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对原始的市场经济。市场的不规范是这一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一定程度上既是道德失范的原因,也是道德失范的结果。经济生活中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残酷的血汗工厂、掠夺式地抢夺经济资源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早期资本主义的现象必然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市场无序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把市场的负面作用进一步放大,加大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道德堕落。市场经济本身就有把社会的一切关系都“市场化”、“商品化”和“金钱化”的趋势。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1)。这种社会关系的“市场化”是对社会传统美德、道德和良知的一种否定。推崇和放任这种社会一切关系的“市场化”将对社会的基本和谐、稳定和政治的廉洁起到极其负面的作用。而中国缺乏规范的原始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恰恰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这种道德负面性。这一切为外部世界所有不满中国政治制度的人士、反全球化人士、或担心中国的发展损害其利益的人士提供了批判的依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少数民族相对群居,往往处于相对的落后状态。这种状态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在以族裔为特征的民族主义(这也是自由主义国际道德体系中的一个原则:民族平等与自决)不断输入的条件下,很容易导致由于身份差异而产生的不公平感,疏远感。尽管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断地加大投入,给予相当大的照顾和政策倾斜,但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仍为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煽动的机会,也为外部一些势力批判中国提供了口实。
道德伦理绝非是先验的,它是“利益和环境的产物,是为促进利益而服务的工具”(22)。自由主义道德的各原则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冲突,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或所处的环境作为自己选择道德伦理的依据。中国的发展正在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格局,世界各国依据他们在变动中的利益对中国有不同的期待。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开放,由于内在的优势,如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潜在而巨大的市场,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环境保护相对宽松,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出口了大量廉价的商品。中国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资源的转移与竞争发生的变化,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力量对比格局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影响了世界的政治利益格局。处于利益变动中的各个社会群体或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对中国做出了不同的道德评判。他们结合自己的利益与处境或根据自由、或根据平等,或根据生态(世界的整体利益)的标准对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各种作为提出自己的道德评判。这种评判意味着一个正在逐步影响世界未来的(头等)大国的发展能否符合世界各国以及各个群体理想中的方向,能否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正成为一个世界性关注的大事(23)。中国的现实与世界各国以及各种群体对中国的期待不可能是吻合的,中国的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要考察世界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这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特性决定的。因此,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利益变动,给世界秩序带来变数的背景下,中国面对的种种批评与指责可以说是一种大国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烦恼”,这种“烦恼”在今天资信通达的世界无法回避。但必须指出,来自西方的批评有的是出于对世界文明进步的向往,有的是出于利益的诉求,有的是出于本能的憎恨,因而正确与误解混杂,善意与敌视并存。
四、建立中国道德制高点的必要性
如何建立有利于自己发展的道德制高点是未来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空间。这一课题包括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在内政方面,从根本上说,这一道德制高点必须建立在中国的发展立足于“公平、效率和环保”三者有效统一的基础上,至少是三者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这种统一与平衡是国内与国外兼顾的产物。它既是世界性道德诉求对中国的期待,也是中国能否获取国内与国际和谐的重要保障。因为目前整个世界面临着“效率/自由、平等/公平与生态保护”三个目标的张力,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较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将引领未来世界的潮流。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三者之间的矛盾。这既为中国带来了机遇,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中国目前必须在内部加大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力度,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大力加强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效率、公平与生态保护”三者协调的社会发展之路。在外交方面,作为一个成长的大国要想能为整个世界所接受,它必须在对外关系中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因此,中国应该继续保持近几十年外交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在绝大部分时间和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势’,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这种外交方式的优点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这样的力量是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发生和后果方面相对最可接受的”(24)。此外,中国建立道德制高点在内外两方面也是统一的。要以促进社会内部的“公平、效率和生态保护”三者协调来减少与国外的经济资源竞争,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亲和外交的效力。只有在内政上进一步改革,外交上才能更好地继承传统的优势,中国才可能从根本上占领整个世界的道德制高点。
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要获得世界的接受、认同与理解,除了实力因素之外,超越性的道德感召力也是必需的。葛兰西曾经说过,“现代君主(指新兴的革命政党,本文作者注)应该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宣扬者和组织者,这也就是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今后发展,以全面达到现代文明的高级形态奠定基础。”(25)这里只要把“现代君主”换成有志改革世界秩序中不合理和不公正因素的“新兴大国”,就可以发现道德作用在当代对一个新“崛起大国”的重要性。从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中,只要考察英国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成功崛起史,与德国、日本的失败经历就可以看出,新兴大国所具有的道德感召力对其获得国际发展空间的作用。
历史上英国作为世界新兴大国出现,它的道德进步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市场主体的自由与平等,以及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产生的所谓国内外利益和谐。它在内部与封建专制,与人身依附、重商主义和权力垄断形成了道德的反衬,市场控制与政治专制形成了对照,国际上市场的商业占领和对均势的操纵与领土征伐和军事主宰形成了对比(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较早地利用商业征服、更多地通过均势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美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同样也体现着某种道德的超越性。美国的超越性表现在:以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新政、植入社会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一定程度上注重社会公平的经济自由主义(26))国际经济秩序、反殖民主义和门户开放。这与当时一些新兴大国为解决“公正与效率”矛盾而采取的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掠夺相比,无疑提供了一个更可以接受的方案。尽管德国、日本之类的国家在解决国内“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具有性质上的相同性,但其对内极权专制,对外征服掠夺的方式显然与美国相比缺乏道德的感召力和世界的认同性。
除此之外,中国还必须拓展对外文化交往渠道,增加对外文化流通的方式和技能,增强整个民族的道德修养,以此向外展示中国并不“缺德”。这些方面的大体措施包括:
1.在对外宣传中,要明确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宣示不仅是“中国是和平发展的国家”,而且要宣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大体的轮廓是什么,它体现怎样的道德原则。要有说服力地对外解释,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通过什么来保证的,有什么样的国内外机制来保障这一方向。
2.加强真正的而非官方主导的民间交往,特别是大力发展有一定独立性并且相对忠诚于体制的市民社会组织与人员与国外的交往,通过它们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的成就传播出去,通过它们来消除国际上对中国的种种误解,通过它们来反驳国际上对中国的敌视宣传。“民间对民间沟通”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取得的效果可能要大于官方的宣传。
3.加大中国对外宣传的力度,增强对外宣传的技巧,特别是要用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进行对外宣传,通过事实来宣传中国在促进公民自由,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保护生态方面的成就与努力,包括中国社会如何通过接受批评来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例。制约舆论方面的两个因素包括:事实和人性中固有的乌托邦(27)。事实是消除误解与戳穿谣言最好的武器,宣传中国在“自由、平等和生态保护”上的成就与努力就是要引起目前国际社会中心存美好愿望人们的共鸣。
4.在对外宣传中,应该强调中国社会问题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问题的共性,把中国的努力与它们的作法进行比较,以此说明,中国并非国际道德缺陷的特例,中国出现的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不是源于中国,而是源于世界市场体制或国际秩序,即使是具有中国独特性的问题也在于中国传统的习惯,是中国力图改革的目标。
5.积极加强与国际组织就有关问题的对话,加强政府有关部门与国外和国际组织就一些问题,甚至是中国内部问题的对话与磋商。由此表现出中国愿意以一个合作、真诚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体现中国同样怀有与世界共同的道德愿望。
6.加强全民族的道德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使得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展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赢得世人对中华民族以及中国的社会制度的认同。
注释:
①③④⑤(22)(27)[英]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3页,第96页,第85-89页,第89、96页,第66页,第129页。
②Robert.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ee,Robert.W.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Approached to World Ord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p.97-98.
⑥⑦⑧⑨⑩[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页,第285、286页,第291页,第299、328页,第290页。
(11)像英国学派的学者都是以国际社会作为道德发挥作用的前提。如Martin Wight,Hedley Bull,R.J.Vincent等人都强烈持有这一主张。见H.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R.J.Vincent,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Holmes & Meier,1992).
(12)有关卡尔论及国际社会与国际道德的关系详见《二十年危机》,第136-139,147页。
(13)有关摩根索的这一方面的论述见,《国家间政治》,第313-316,274-283页。这里我必须指出,摩根索生活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争斗以及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使他哀叹国际社会消亡,他忽视了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社会性因素,他由于没有生活在冷战后的时代,因此也不可能看到冷战后,全球化大发展带来的国际关系社会性因素的加强。
(14)Robert.W.Cox,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ee Robert.W.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Approached to World Ord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p.100-101.
(15)Andreas Hansenclever et al,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168.
(16)国际体系的自由主义特点见Louis Henkin,"Influence,Marginality,and Centra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见Marc Genest 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rlando,Fl.,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p.165.
(17)对这一方面的论述可以详见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chapter 5,7.
(18)Hugo Grotius,"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see Marc Genest 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rlando,F1.,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p.147.
(19)Robert W.Cox,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lural World,London,Rouledge,2002,p.97,102.
(20)刘东、徐百柯:“中国是大国还是小国?”,见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9842858.html。
(21)《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23)有学者分析近期内美国的《外交政策》把美国和中国列为世界第一、第二“最危险的国家”就说明,“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国际社会的期待也越大。见吴稼祥:“热烈祝贺中国荣登“最危险国家”排行榜”,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2a780100f4to.html。
(24)时殷弘:“成就与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与对外政策形势”,[北京]《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25)[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26)有关这一内容参见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36,No.2(Spring 1982).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道德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新挑战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