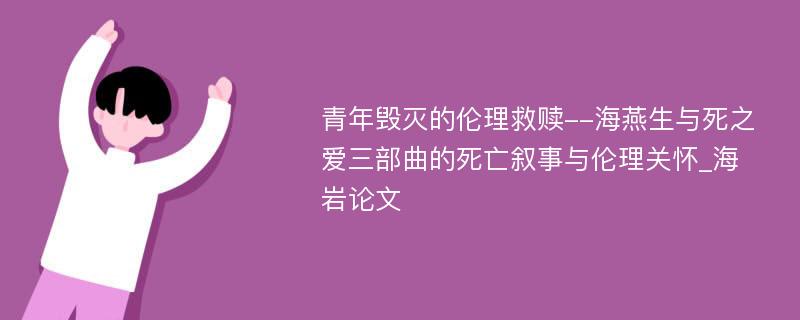
青春殒灭的伦理救赎——海岩“生死之恋三部曲”的死亡叙述与伦理关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之恋论文,生死论文,青春论文,海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5)06-0089-5 一、最后的舞蹈——永恒的死亡 如果说历史长河所裹挟数之不尽的人类生命个体都是在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力对于时间和空间展开抗争的话,那么,人类最后完成的这一动作则可认为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永久超越,亦有可能是对时间空间的永久妥协。《说文解字》中将“死”解释为“澌”,“人所离也”,一般辞书都将“澌”字的意思等同于“尽”,意思是水流到了尽头。“亡”的意思和“死”相去不远,可以理解为“遗落、丢失”,如成语“亡羊补牢”。综合理解的话,“死”“亡”二字连缀起来的意思可以有两种:一是两字做同解,强调生命体征由“有”到“无”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虽在一瞬间完成,但其本体意义却是生命个体的质变。二是两字分解,“死”字强调一个生命体征转变的动作,“亡”字则强调这一过程性动作引发的状态改变——永久性的“遗失、丢失”。 死亡是一个和生命共存的永恒命题,不管情愿与否,死亡都时刻觊觎着生命存在。回溯历史,人类通过各种形式试图超越死亡以达不朽的尝试从未罢休,其中以虚构为本质的艺术符号创作就是超越死亡的诸种形式中最为常见也最为公开的美学化文本,也只有在艺术符号中,生命才能获得审美化的永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生的悲剧性本质也许并不是必然性的死亡,而是知其结局然而又不得不经历、不得不面对。在面对死亡惴惴不安的有限生命中,人类辨别善恶、美丑、好坏,并据此创造了宗教和艺术,希冀神灵和审美能够帮助自身正视死亡,思索死亡甚至超越死亡。加缪曾经说过:“自杀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1]如此来看,死亡问题就是人类艺术创作的必然主题。生命存在的经验使人一次又一次穿越于悲哀、伤痛、无奈,艺术文本也一次又一次的向世人展现病痛、苦楚与死亡。死亡是不可能经历的必然经历,是源起于超越生命的终极生命超越。 二、“生死之恋三部曲”——一场关涉青春的死亡排演 新版的“生死之恋三部曲”是由江苏卫视和知名编剧海岩联手打造的一场视听盛宴,重新打造的三部曲:《玉观音》、《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投资过亿,历时两年,编剧海岩自己也对这三部曲给予了极大期望,“这三部作品是我的心血,如果这次不成功,我就真的要考虑专心回去做生意做设计了。不成功,就彻底退出江湖。”[2]重新编排的三部曲承袭了海岩剧固有的奇情和悲美特质,只是经过海岩大手笔的修改之后,故事结局和人物命运发生了一定转折。在电视剧的展演和制作过程之中,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走势通常是编导人员吸引观众的必要手段,作为标志的奇情故事是当年海岩剧获得收视大观的重要手段,侦查与卧底、缉毒与贩毒、谋杀与自杀,种种离奇故事桥段的巧妙安排迫使观众在认同于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沉溺于电视剧叙述之中,在跌宕动人的故事讲述中来完成叙述接受和价值认同。除此之外,海岩剧的悲美特质同样是其获得标出性涵义的重要特征,不同于其他悲剧品格(如悲壮、悲苦、悲哀),悲美的悲剧品格是将剧中最美好的事物毁掉,让观众沉浸于美好所失的遗憾之中从而获得特殊的美学感受。中国民间传统的很多故事传说就具有着悲美的性质,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和七仙女》,海岩剧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鲜明的悲美特质,结合本文的论述主题,海岩剧的悲美具体体现在剧中人物主动或被动地迎接死亡,欧庆春、毛杰、祝四萍,三部电视剧中每一部都有一个主人公离去,这既可以认为是海岩编剧的固有套路之一,又可认为是深埋于故事讲述者内心深处的审美取向,之于主人公来讲,生命无缘由地被卷入纷争,而后宿命性承受苦难甚至死亡更具有某种无法言说的神秘主义色彩,作者自己也曾经表示过:“可能和我对生活有一定的悲观情绪、对社会有一定的失望情绪有关,觉得这样表达自己会痛快一点,好事在我自己总是成不了,所以确实有一定的思维定势。”[3] 三、“生死之恋三部曲”的死亡伦理研究 死亡或曰艺术作品中虚构的死亡通常分为三种类型:自然之死、被动之死与主动之死。自然之死在儒释道三家学说中有不同的界定,儒家所称的自然之死与道德观念联系最为紧密,德性既是孔子学说的中心也是孔子死亡观的中心,《论语》所载的“知命”“从命”就明显的区别于带有悲观主义倾向的宿命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4]在孔子看来,“人”永远重于“鬼”,“生”永远重于“死”,前两者永远要先于后两者,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伦理的道德主义理想当居于永久性的核心地位。道家的自然之死属于功德圆满,自然化归,如鲁智深坐禅立地成仙,是生命体的魂魄和精气神脱离于物质载体飞升于太虚,是羽化成仙的过程,是精神的无限升华已达脱离肉体束缚的质变过程。佛教的自然之死是脱离苦海归于极乐之境的美好愿景,是以虚构的来世来规约今世行为的体系,是以彼岸引导此岸的涉水方舟。被动之死是生命体的非正常死亡,具体来讲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天灾人祸的突发性事件以极大的偶然性终止生命体的存在;第二种是生命主体不愿就死,但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又不得不就死,如触犯刑律而被剥夺生存权利的人。最后一种死亡是主动之死,主动之死是对死亡这一行为的自我选择,具体来讲则区分为自杀和牺牲两种形式,自杀行为是对现世生活恋无所恋,依无所依,在自我预期中未来生活的负面价值远远高于正面价值,并且超出自身精神肉体的承受能力而主动选取的永久性终止行为。而牺牲则与之完全相反,虽然同属于主动选取的行为,但牺牲行为的发生和牺牲权利的自我选择在于牺牲主体对于未来的正价值充满期望,并且是主体在权衡之下基于理性判断得出自我牺牲所得到的正价值远远高于自己的生命价值。 综观海岩三部曲的故事编排我们不难看出,三位主人公的死亡全部属于主动之死,只是在此统一的主动之死动作之下隐含着不同的美学意味: (一)死于青春的青春献祭 欧庆春、祝四萍和毛杰,三位主人公全部死于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种符号化的艺术虚构之死亡向我们传达了叙述者自身在讲述活动中所选择的伦理取向:即能指的剧中人物之死与所指的青春之死二者相统一,“死于青春”是海岩早期一部中篇小说的名称,来自于革命先烈李大钊《青春》中的一句话:“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在其后来的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时,海岩再次将其命名为《死于青春》,“死于青春”之于海岩电视剧更像是故事编排的常态,除了此三部曲之外,其他海岩剧之中依然能够找到很多“死于青春”的身影。“青春”是充斥着无限美好可能的时代,对于个体而言,生命不可进不可退的线性延展本质使得我们所持有的生命时段只有现在,青春生命既拥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妙和浪漫,也同时承受着个体成长所引发的焦虑、苦闷和失落,青春本质综合了神性和魔性的二元特征,青春个体总是在神魔之间左右摇摆,青春生命在成长之美和成长之痛中享受与承担。从人生经历来讲,青春年代的年少轻狂使得成年个体所拥有的理智情感离之甚远,而现代社会财富积累的客观规律又使得青春个体所掌控的物质财富不多,如此理解,对于青春个体来讲,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此二者都处于赤贫的状态,双重赤贫的生命状态真正给予青春个体能够掌控并且有权利进行任意处置的仅剩下一个美好的身体。乐享生命、憎恶死亡是全人类文化的普世价值,但艺术作品在其虚构的自由中却将死亡意象一次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结束,意味着可能的美好与可能的痛楚恒久的终止,欧庆春之死死于理性克制的失效,祝四萍之死死于托赖终生之人的背叛,毛杰之死死于情理冲突下抉择的示弱,三个年轻人、三次苦难身体的离脱,三份拜献于青春的祭礼。 (二)以死亡超越死亡 超越死亡是人类的美好愿想,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所有试图超越死亡的尝试都源自对生之美好的无限留恋,然而目前的科学知识距离让人类超越死亡已达不朽的愿望还相当遥远,那么所谓的超越只能是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对于不朽的信仰,让人们有勇气以自愿的选择死亡来达到超越死亡的目的,在思想上超越死亡。不朽作为主动就死的评判标准,自身即带有深重的伦理意味,“青史留名式”的超越死亡作为留存在华夏民族血脉之中的价值评判,无论在哲学书写还是在艺术创作中都获得了丰富的存在空间。具体到影视叙述之中,超越死亡的伦理价值即体现在正面人物牺牲的展现和咏叹。 《永不瞑目》的结尾,主人公欧庆春为了保护肖童这个自己长久以来不愿正视也不敢正视的爱人而牺牲在敌人枪口之下,除此之外,她的牺牲更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所深深认可的死亡价值和伦理精神。匡扶正义是欧庆春作为刑侦大队人员的天职,也是社会寄予这个特殊群体的民众期望,社会生产的良性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是警务人员身为“金色盾牌”所要达到的目的,欧庆春的牺牲是为了更广大群体的权益不受侵害,是以自己的牺牲换取民众(包括自己的爱人)更美好的生活能够继续,这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伦理阐释,也是司马迁“重于泰山”之死的精神承继。在视觉符码上,欧庆春之死更是一场“唯美主义”的演绎,视死亡为美并且充分发掘身体死亡所展示的形式美感,以“死亡”来超越死亡,以“美学形式”来完成伦理关照。故事结尾,蓝天白云下矗立的墓碑,全体警队脱帽致哀,黑夜降临,男主人公在两人为数不多的互吐衷肠之处燃起千百只蜡烛,烛火掩映着肖童哀伤的面容,最后一次再为自己的爱人献上一曲挽歌。恰如李金发的诗歌对于死亡的崇圣赞美——“死!如同晴春般美丽,如季候之来般忠诚,若你没法逃脱,呵,无须恐怖痛苦,他终久温暖我们。”[5] (三)自毁的沉重肉身 身体的美好在青春时代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赤贫状态下显得尤其重要,加之青春时代身体的极度躁动和不安,如何处置和安放自己的肉身就显得尤其重要,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和观感本性将身体样态和切肤之感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身体的空间游移和肤感承受成为青春生命的逻辑常态,作为背景的现代都市——广州、重庆和厦门将故事的主人公置于原子状的生存方式中,主人公个体如单细胞的低级生命体,没有存在感、没有痛觉,漂浮于现代社会光怪陆离的视觉景观当中,初入城市带给身体的局促、繁忙和不安明显强过于都市消费带给身体的有限欢愉。肉身之沉重被都市节奏无限放大,继续选择在都市生存需要勇气,而这莫大的勇气来源于心底所留存希望的不破灭,如此看来,“希望”这个无法把握无法言说的虚幻之物就成了个体留存的唯一维系物,一旦希望破灭,一无所有的青春生命只能选择自我毁坏身体这个唯一可以把握之物,借此获得永恒的解脱。 祝四萍生在乡下,初入城市带来的巨大反差在她身上显示的尤其严重。她也没怎么读过书,通过教育达到“启蒙”目的的方式在她的身上也不会显现。因此,对于她来讲,唯一可以让自己继续的理由便是龙小羽投掷在她身上不多的“爱情”,她放弃求学,目的是快点赚钱供龙小羽读书;她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厂长,目的是让龙小羽也能进入这个所谓收益不错的乡镇企业;她办理假学生证混入学校浴室洗澡,目的是省出钱来让龙小羽能够洗上热水澡……如此种种,祝四萍的人生轨迹全部环绕着自己的爱人进行,虚无缥缈的希望二字成为祝四萍生存下来的勇气,她期盼龙小羽能够与她结婚,期盼龙小羽能够回到自己身边,期盼自己和龙小羽能够过上有钱的生活,即使自己身中数刀,依然痴痴的期盼龙小羽回来……一个为希望而生的女人也必然为希望而死,因此,最后的最后,当自己血流满地的面对爱人不肯说出的那句“喜欢你”之时,破灭的希望之火衍化为自我了断刺入胸膛的那把尖刀,抱憾而死,而后,获取永久的超脱。埋葬青春,也埋葬了不复希望的爱情。 (四)生死之间的伦理困顿 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追问:“和死亡一起展开的,到底是虚无,还是陌生?临终死亡是否简单的归结为存在——虚无之本体论的两难境地?”[6]凡人的一生可能遭逢数之不尽的苦难,生和死作为人生在世的起点和终点无时无刻不在管窥着生命时段内部的个人生活,不同于生之不可选择,作为可以主动选择的动作,死亡在某些层面上来讲是个人把控着一定选择权的事情,最起码主动之死的死亡方式和死亡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是把控在主体手中的,然而并非所有的主动死亡都可以泾渭分明的区分为牺牲和自我了断,艺术文本的符号化在很多时候是混淆了崇高、敬畏和超脱,死亡动作发生在生死之间,然而超越于生死之上,生死之间的苦苦挣扎更是将选择的主观能动性交付于动作者手中。而作为青春阶段的生命个体来讲,青春生命本质化的躁动和不安更是时常将个体推入进退两难的处地之中,一旦青春遭遇重大变故,青春期的苦闷和惶恐便会被无限制放大,甚至将主体抛入无法挣扎、无法摆脱的困境当中。 《玉观音》的标题三个字说明的是安心这个人物形象,但纵观整部电视剧,新版的故事编排无疑将毛杰这个人物进行了全方位改写,故事中的毛杰是云南南松地区一位极为普通的年轻人,波澜不惊的和兄嫂安定的生活,直到安心的出现,毛杰的命运轨迹才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从此,为一个女人心甘情愿的付出便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主色调,即使是安心将自己曾经那么温馨可爱的家庭毁于一旦——嫂子被警察击毙,自己的哥哥拒捕逃亡,但他自己对安心的感情却从没有改变过。对于故事编排中毛杰这个人物来讲,也许青春生命本来就不应该理智,又或者毛杰的选择是极大的理智:自己的家庭毁于心中最爱的人之手,而宿命一般的感情汹涌让自己不可救药的喜欢上了这个不一样的女人,自己父母兄嫂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留下自己苦苦挣扎于生死两难的困顿当中,结束和救赎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所以,当故事结尾处自己的哥哥丧心病狂的将枪口对准安心挚爱的男人——杨瑞时,毛杰选择用自己的胸口挡住了那发子弹,用自己的生命永久的成全了安心的幸福,也永久的获得了生死之间煎熬的解脱。 四、乌托邦的此在功能——死亡叙述与影视伦理 作为影视叙述审美乌托邦的重要因素,死亡总是在剧作编排的内外压力合围之下悄然降临,青春生命天然的必须面对多于其他生命时段人物更多的压力,作为一种解决冲突矛盾的方式,死亡是最为有效也是最为直接的解决途径,既是对抗,也是救赎,它终止了青春的苦闷,遏制了成长的痛楚,将生命时段定格在永久的瞬间。然而,对于荒芜的青春来讲,无论是在艺术虚构之中还是在现实生活内部,死亡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并非那么的轻而易举和不值一提,即使虚构的影视艺术有所提及,死亡片段的编排也通常担当着晦涩却丰富的美学意味,作为影视叙述策略和美学体验的青春之死发挥着丰富的功能化意味,它以异态的青春体验来表达青春之死在道义上的合理性,进而完成必要的文化反思和社会批判。 影视文本在制造死亡的同时已经将躲藏于形式死亡背后的伦理意味加载于人物形象背后,生命是先期存在的,是天然的恩赐,是无条件的文化事实,但死亡影像传达给受众的绝非仅仅是生命损毁和消殆的理所应当,牺牲也好,自我了断也好,负载在这些死亡符号身上的是文化的反思和社会的批判,不管是欧阳天的老谋深算、黄建军的欲壑难填(《永不瞑目》),还是张雄的无止境贪婪、七贵的唯利是图(《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又或者毛放的冷酷残忍、钟国庆的以势压人(《玉观音》),所有这些影视符号所标示和传达的都是如今金钱至上和消费主义所导致的人性异化,他们的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才是艺术符号不断书写死亡的根源,也只有借助欧庆春、祝四萍、毛杰这些令人垂怜的生命个体的非正常死亡和毁灭,才能达到呼吁观众正视生命、正视青春的社会疗救和伦理传达之目的。从根本上来讲,这也许才应该是死亡叙述真正所彰显的生命逻辑和生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