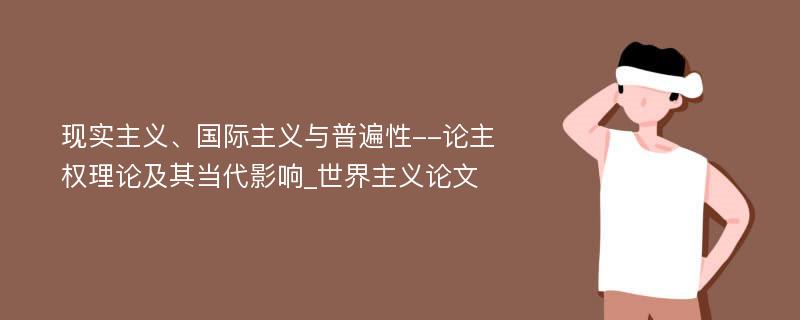
现实主义、国际主义、普世主义——评有关主权的学说及其当代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主义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学说论文,主权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9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国家主权的最基本含义正被重新定义,国际社会应当对人道主义干涉持欢迎态度。安南在第5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又明确提出《联合国宪章》应奉行“超越国界权力”的主张。这立刻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而争议的中心议题显然只有一个,即国家主权是否应当受到限制,如果应受限制则应受到多大程度的限制?
主权是国家的主要标志,是国家身份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和法律基础(注:Prakash Chandra,International Politics,3rd ed.rev.(New Delhi:Educational Books,1979),P.52.)。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反映其基本的法理和政治性质(即在某个特定领土内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的至高无上的中央权威(注:约翰·奥斯汀就是这么认为,见Palph Pettman,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ance of Power,Balance of Production,Balance of Ideologi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Longman Cheshire,1991),pp.31-33.))的主权概念于16世纪后半叶由法国人让·博丹首次提出。此后,主权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并使主权国家成为3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但关于主权的各种学说并不完全一致,它们一直存在着众多分歧,尤其是关于主权是否应当受到限制(特别是外来限制)、以及应受多大程度限制的问题。布尔曾对霍布斯、格老秀斯、康德的国家主权学说分别冠以“现实主义”、“国际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名号(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Macmillan,1977),pp.24-27.),这实际上指出了各种主权学说之间的最本质的分野。
一
根据布尔分类的基本精神,主权学说大致可分为现实主义、国际主义和普世主义3大类。现实主义主权学说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基本前提,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理性、自私的个人都以自身安全为最高行为准则,拥有可用于自保的一切无限制的“自然权利”,但这必然导致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注: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因此,为摆脱这种战争状态、从而相约创建主权很有必要。主权的产生虽然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却导致了国家间自然状态的产生,即出现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间很难产生一个高于主权的权力中心,因为国家拥有比个人更多、更为丰富的自保手段(注:Lynn H.Miller,Global Order:Power and Valu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1985),P.22.),其自保能力远远高于个人,因此国际无政府状态难以通过类似个人契约的国家间契约来消除。现实主义正是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和难以消除出发,认为国家的最高目标是自保,其自然权利——主权——应当是一种国家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完全或基本不受限制。主权的对内方面,体现为它是国内的最高权威,否定了任何其他国内政治实体有独立的或更高的权力;它是国内所有法律的源泉,是暴力的唯一合法垄断者。主权的对外方面,体现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独立体,不承认任何其他实体有更高的权力(注:Theodore A.Couloumbis and James H.Wolf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 and Justice,4th ed.(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90),P.69.)。
现实主义主权学说渊远流长。马基雅维利在博丹之前就已使用了“国家”这一术语(注:当然,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实际上更多地表达了“政府”的含义,见Ebenstein ed.,Political Thinkers,P.344.),“马基雅维利明显承认了主权是绝对的,尽管他并未清楚地表达出来”(注:Bernard P.Dauenhauer,The Politics of Hope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6),P.163.)。在其名著《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主权拥有者——君主——可以不顾道义以实现国家利益(注:Nic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 (Palm Springs:An ETC Publicaton,1988).)。在他那里,主权不仅其对内方面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其对外方面也同样如此,因为君主不仅不承认、也不服从外部任何单位的权威;就连自己与别国达成的契约,也可以违背,国家可以需要为借口运用一切手段——包括侵略战争——来实现国家利益(注:Steven Forde,"Classical Realism,"in Terry Nardir and David R.Mapel ed.,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67;Micheal W.Doyel,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97),pp.99-101;Machiavelli,The Prince,chapter 18.)。
法国哲学家让·博丹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主权概念并赋予其明确涵义,他将国家与主权区别开来,把国家定义为“一个众多家庭及其私人财产的合法政府,它拥有主权”(注:George H.Sabine,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4th ed.rev.(Chicago:Holt,Rinedhart & Winston,1973),P.402.),主权则是国家的一种绝对的、永久的权力,是最大的统治权。主权是永久的,尽管这种权力在一定时段内被委托于一个或少数人实施,但最终这些被委托人仍是主权的臣民。主权是绝对的,因为它是由神权和自然法创设的,事实上神权与自然法不可捉摸或者根本不存在,任何有限制的、有条件的主权都不是真正的主权。在国内,主权通过君主——主权的象征——制定法律,但法律对君主并没有约束力;在国外,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与另一君主达成契约,一俟无利可图,契约也就不再有效(注:Ebenstein ed.,Political Thinkers,pp.349-351.)。让·博丹明确拒绝了中世纪的政府有限权威的观点。对于他来说,主权是绝对的、永久的权力。主权是不可剥夺的、不可转让的(注:Dauenhauer,The Politics of Hope,P.163.)。
另一位现实主义主权学说的倡导者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同博丹一样,霍布斯也认为主权是绝对、至高无上、不可分割和不可转让的,它是国内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源泉。他认为,主权是个人依据理性与自私达成社会契约并进而创立的,但主权一经创立,便要求人们绝对服从,除非其生命受到威胁或主权者丧失了保护他们的能力(注:《大美百科全书》(第14卷),光复书局(台)1990年版,第51页。)。如同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每个国家都平等拥有主权,即拥有无限制的自然权利。为了寻求自身安全和财富及其实现手段——权势,它们可以不受任何道义的约束,甚至连国家间订立的契约也可以不遵守(注:Friedrick Meinecke,Machiavellism:The Doctrine of Raison D' 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London:Routledge and Kagan Paul,1957),P.212.)。“至于一个主权者对另一个主权者的职责,则包含在一般所谓的万民法(Law of Nations)之中……万民法与自然法乃是同一个东西……(它实际上只是)对主权君主和主权议会的良知意识的规定……(注:霍布斯:《利维坦》,第276页。)。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对现实主义主权学说作出了极大贡献。他认为主权具有“个体性”和“排他性”(注: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主权的对内方面,在黑格尔看来,是国家构成了个人的“最终目的”,整体使各个部分实现了其自身的意义,因此个人必须根据主权所制定的法律行事,服从主权(注:列奥·斯特劳斯、约翰·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9页。)。在对外关系上,主权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主体间的关系”,它们要“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6-347页。),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应然关系。
当代,将现实主义主权学说再次推向高潮的是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他从人性本恶性出发,认为主权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国家利益是主权的最高目的,“只要世界在政治上是由众多的国家所组成,国家利益就是国际政治中的最后话语”(注:Hans J.Morgenthau,"Another Great Debate,"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XLVI,1952,pp.9-718.)。因而,不管在国内、国外,主权都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道德不重要,国际法同样不重要,唯有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现实主义主权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悲观的,它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前提,悲观地认为自保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其产生的背景大都与学者们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无论是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黑格尔、摩根索,还是本文尚未论及的联邦党人斯宾诺沙等。他们提倡绝对主权,要么是因为其祖国处于分裂状态、国力赢弱,要么是其祖国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体系中地位不高、常受外来威胁,因此他们都强烈呼吁绝对主权,以期借此避免外来干预和增强本国国力,争取实现自立自强。
二
国际主义主权学说既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又强调与这一状态并存的有序的国际交往。从这一中间立场出发,他们一方面强调主权具有排他性,另一方面强调主权应受一定程度的限制。国际主义认为,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为了确保国家主权不受破坏、保证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必须强调主权有其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一面。但仅强调主权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是不够的,这并不能给国家带来安全感,反而容易导致“安全两难”困境的出现。因此,在强调国家主权独立的同时,如果国家间存在更多的法律、组织、交换和沟通的话,必将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注:Kjell Goldmann,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2.)。也就是说,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必须将主权纳入一定的限制范围,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安全与自保。
国际主义主权学说传统源自与霍布斯同时代的荷兰伟大思想家、现代国际法鼻祖雨果·格老秀斯。他将主权定义为“其行为不受他者控制的权力”(注:Couloumbis and Wolf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69.)。但格老秀斯并不认为主权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每一个政治社会,其最高权力确实是服从于由自然法则和国际法令设置的限制。(注:斯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中),第446页。)”在对内主权方面,他“既拒绝了纯粹的人民主权,也拒绝了博丹的绝对主权,认为应该确定主权的限度”(注: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在对外主权方面,源于自然法的国际法要求各主权自觉遵守。
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与霍布斯一样,从自然状态出发论证了主权的必要。与霍布斯相反,他认为平等、理性、独立的个人生活在一种“和平、好意、互助、保护”的自然状态下,其唯一规范是自然法(注:Kenneth W.Thompson,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Boton Rouge:L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P.82.)。但这种自然状态并不完美,它缺乏明确的法律、能依法公正判决的法官及一个能提供法律的公共权威,因此有必要通过契约建立主权国家(注:Ibid.,P.82;斯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571-572页;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第133页。)。主权国家建立后形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国家之间更多的是和平而非斗争。主权不是绝对的,一个绝对的、不受控制的主权的存在实际上比自然状态更糟(注:斯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573页。)。根据自然状态的唯一规范自然法,国家一方面有义务保护其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尊重他国的权利。也就是说,主权在国内要受人民制约,在国外则应受到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限制(注:Doyel,Ways of War and Peace,pp.217-220;Thompson,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P.82.)。
现代功利主义创始人杰里米·边沁同样提倡国际主义主权观。从功利主义出发,他认为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总和的行为,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唯一目的(注: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年第3期,第8页。)。因此,国内人民的快乐与否成为主权的对内方面的最高标准。在国际上,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缺乏纠正各种不完美的社会、政治机制,因此各国应自动接受国际法的限制,建立国际议会,实现自由贸易、集体安全和裁减军备,进而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注:Doyel,Ways of War and Peace,pp.226-227.)。
当代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家海德利·布尔是国际主义主权学说在当今的杰出代表。他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同时承认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国家间的有序交往,主权国家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共同规则和共同运作机制,从而构成国际社会(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pp.65-74.)。在国内,主权应保护所有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单个国家的对内对外主权的独立既是各主权国家的共同利益,也是其共同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行为规则和共同的国际机制,约束各主权的行为,限制其权力,从而实现所有主权的自保。也就是说,在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的限制下,主权更加容易实现,相反,那种认为主权绝对不受限制或应受严厉限制的主张,都不利于主权的实现。
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国际主义主权学说占据了主流地位。它承认主权的对内对外独立、自主与排他性,同时也提倡主权应受一定的限制,因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外,国家间还存在有序的交往与合作,这于更好地实现主权极为重要。提倡国际主义主权观的思想家们同现实主义主权学说的倡导者们一样,受其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制约。在主权不受限制与严格限制这两个极端之间,他们的祖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方面可以通过主张主权不受限制博得弱小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同霸权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提倡自由主义,在霸权那里赢得支持,借以从弱小国家身上取得优势。如同两极格局下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它们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
三
普世主义主权学说实际上也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也把人性恶作为一个前提,但他们强调整个人类社会,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在于超越国家分野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注: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第9页。)。为了使世界人民摆脱无政府状态,普世主义设计了一幅宏伟蓝图:以宗教等统一世界,或者以革命或法西斯手段建立世界政府,或者建立功能性的国际组织,达到严格限制甚至取消主权,最终实现人类大同。在他们那里,主权是一种恶的、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存在,阻碍了人类正义、公正、和谐的实现,因此必须严加限制,直至最终取消之。
普世主义主权学说传统可归因于宗教。任何一门宗教,都以普渡众生为最根本目的,它不允许异端邪说存在,更别说对其构成挑战。在宗教那里,国际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普天下的好人与阻碍人类共同体实现的坏人之间的斗争关系。即使存在国际关系,它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独特的主体、性质和规律。圣·奥古斯汀是第一位明确表达这种思想的基督教神学家,在其神学名著《上帝之城》中,他将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上帝之城高贵、自由、安全,而世俗之城低下、约束、危险;上帝之城是每一个生活在世俗之城的人的最高目标,但上帝之城是不可能在卑污的世俗之城实现的,众生的使命是竭力使世俗之城更加接近上帝之城(注:Thompson,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pp.44-53;王振槐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约1千年后,意大利诗人但丁提出了类似思想,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他论证了上帝赋予罗马人(意大利人)以统治世界的神圣权力,分析了罗马人充当世界领袖的优秀品质和才能,提出建立大一统的(宗教性质的)世界帝国之必要(注:但丁的有关思想,见但丁:《论世界帝国》(中),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在基督教之外,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也都提倡天下大一统,主权在宗教世界里实际上被遗忘了,如果它存在的话,也必然受到极为严厉的限制,最终主权国家将为宗教帝国所取代。
普世主义主权学说不仅存在于宗教思想中,还存在于革命主义、理想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思想中。革命主义在近代以来主要出现了两大高潮,其一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它主要继承了让·雅克·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和人民革命权观念(注:卢梭的主权学说主要见其著作《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参见斯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中),第645-670页。),并将其付诸实践。革命者们,如罗伯斯庇尔,尖锐地批判了专制制度与专制法律,主张主权应从国王和政府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注:见Couloumbis and Wolf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69.Thompson,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pp.94-98;Doyel,Ways of War and Peace,pp.137-160.)。为此,革命者们不仅在法国国内实现了人民主权,而且大举对外输出革命,试图将人民主权观在整个欧洲大陆普及化,进而消灭主权国家。第二次革命主义高潮发生在本世纪,它起源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时期达到了顶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奴隶社会以来,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关系,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国内、国际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政治、社会、阶级现状,最终实现没有阶级、没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没有主权国家的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将马克思革命主义的主权学说首先应用于俄国并取得了成功,他著名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推向了顶峰。继列宁之后,斯大林、毛泽东又将马克思的革命主权学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一方面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现实,接受主权应首先着重维护本国主权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推进世界革命。苏联甚至在60年代推出了“有限主权论”,其最终目的是要取消主权,实现世界大同。
理想主义的普世主义主权观也同样主张最终消灭主权,只是其方式不同于宗教和革命主义。理想主义试图通过民主和平、商业和平、法制和平或是它们的结合,建立功能性国际组织,实现世界和平,消灭战争,消灭主权。民主和平论起源于康德,1795年他写下“民主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一文,提出永久和平的主要条件:首先是每个国家都实行民主共和制,其次是自由国家的联盟,第三是普遍的友好(注:康德:“民主和平论——部哲学的规划”,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7-144页。)。按照康德的永久和平规划,主权在国内必须确立民主共和制,在国外必须建立联邦,国家虽然可保持一定的独特性和排他性,但活动空间并不大,后人将其思想引伸为今天广泛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商业和平论的起源应追溯到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生,亚当·斯密第一个对重商主义提出挑战,并以自由贸易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此后,自由贸易思想经过科布登、布赖特等人的阐发,逐渐形成今天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商业和平论(注:Doyel,Ways of War and Peace,pp.230-250.)。法制和平论起源于孟德斯鸠、边沁等人,认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必然能带来世界和平。威尔逊总统则是西方探求普遍和平道路的种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综合了民主和平论、商业和平论与法制和平论(注:时殷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伦理传统:西方与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0期,第63页。)。总之,理想主义提倡首先在个别领域实现和平——通过建立功能性的国际组织,最后实现世界和平大统一,主权并无多大意义。
法西斯主义也同样提供了普世主义主权观。在20世纪里,法西斯主义曾一度泛滥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其典型表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普世主义主权观同样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它的解决之道是通过确立个别国家的主权,限制绝大多数甚至是所有其他国家的主权,最后导致世界帝国,而此时主权也就无所谓主权了。二战前及二战中德国、意大利、日本的设想及实践正是这种主权观的体现。
普世主义主权学说与现实主义和国际主义主权学说相比,更加具有道德原则,更加轻理智而重激情,具有极强的使命精神和圣战精神(理想主义的普世主权观或许是个例外)。无论宗教、革命、理想或法西斯,其实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高涨,学者们正是身处这种意识形态狂热之中,才会倡导普世主义主权观。
四
主权学说的三大传统,就其划分而言不是绝对的,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不可能找到可以完全对应的纯粹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或普世主义主权学说或观念。如前所述,这3种主权学说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它们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表现在具体的思想家身上,他完全可能3种思想成分皆有,只是可能更侧重于其中某一或两个方面。如霍布斯,他虽然强调主权绝对不受限制,但推至极点,也就成了普世主义的主权观,即别国主权都受到了限制,主权实际上已失去意义(注:Frank M.Russell,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and London:D.Appleton Century,1936),P.159,footnote 62.)。又如,普世主义的主权学说,不论是宗教的、革命主义的,还是理想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都假定了一国主权是绝对不受限制的。
在现实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的实际取向如同上文分析的一样,都是由其在现存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和实力,以及其所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绝大多数中小国家由于其实力弱小、在现存国际关系体系中地位不高,同时也不为狂热的意识形态所驱使,因而竭力主张主权不受限制。而那些国力处于中等地位、在现存国际关系体系中地位也居中、同样没有意识形态狂热的国家,则比较赞同国际主义主权观。取普世主义主权观的国家在当今现实国际关系中并不多见,它们要么实力非常强大、国际地位非常显赫,因而也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支持,如美国、欧盟等;要以有狂热的意识形态驱使而国力一般,如伊朗,论其国力不过是个中等国家或地区性大国,然而它却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支持下,大力倡导普世主义主权观;而革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当今世界中都很少见。这种不同的主权观取向,实际上也是一幅幅生动的国际关系体系结构图画。
本质上,三大主权学说都是针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解决办法的探索,其前提都肯定主权国家的存在,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人类更好的共存之路。应当看到,我们既生存于现实中,又超越于现实之外,因此我们既要承认现实,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国家主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应承认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外还存在国家间的有序交往,对国际社会给以肯定,对国家主权作出一定的限制——以不破坏国家主权为限。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我们应当取接近现实主义的国际主义主权观,既支持中小国家维护主权的积极要求、反对某些国家欲充当世界“利维坦”的图谋,同时也应遵守合理的国际规则、承认国际社会对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对于某些领域新近高涨的限制主权的呼声,应持一种理性的保守态度,如本届联大上争议颇多的人道主义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