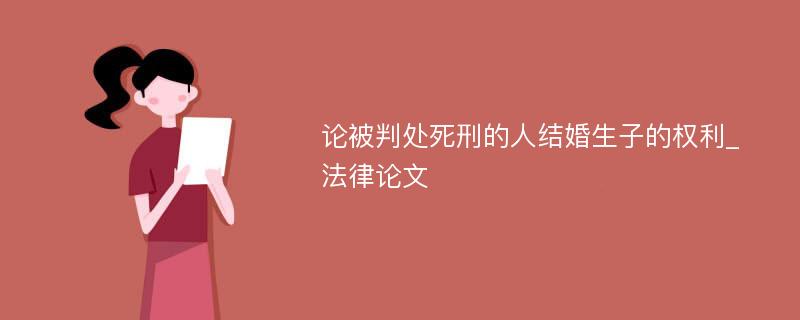
论被判死刑人员结婚和生育的权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被判论文,死刑论文,权利论文,人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被判死刑人员能否结婚与生育
2001年,浙江舟山一名叫郑雪梨的青年妇女,在新婚丈夫犯下命案被判死刑后,给两级法院出了一道难题——“请求借助人工授精怀上丈夫的孩子”,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二审法院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将其拒绝。但是,该案引起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被判死刑人员①生育权、结婚权的关注和探讨。2008年1月23日,《检察日报》一篇《一对有情人判死刑后要结婚,罕见情形难倒司法人员》的报道,②引起轩然大波。随后,《检察日报》开展了“你是否同意这对死刑犯结婚”的“正义调查”,遗憾的是,这对死囚情侣最终是否如愿结婚,因没有后续报道,不得而知。2010年,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一起毒品案件时,让囚车开到了民政局门口,让一名极为可能被判处极刑的毒枭马某和其怀孕的女友在囚车上登记结婚,③该案被称为国内死刑犯行使结婚权的第一例案例。
被判死刑人员不仅失去自由,连基本的生命权都处于随时可能被国家剥夺的状态,是身处社会最底层、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行将赴死之际,被判死刑人员还有多少权利可以保留?司法机关究竟有无义务去成全一个死刑犯临终前想要结婚或者生育的遗愿?国内鲜有先例可循,学者亦是众说纷纭。支持者认为,被判死刑人员既然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亦不属于禁止结婚的人员范畴,加之刑罚明确剥夺的仅仅是其政治权利,因此,被判死刑人员享有婚姻自由权和生育权在法律上并无障碍。反对者则认为,结婚自由是人身自由的一种,被判死刑人员的人身自由已被依法剥夺,结婚自由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生育权的实现以同居权为前提,死刑犯失却自由且行将就死,探讨其生育权没有任何意义。被判死刑人员的婚姻生育权利问题,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以至于我们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保持沉默。但是,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司法,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
二、被判死刑人员享有结婚权和生育权
(一)结婚权和生育权是公民的应然权利
法律和法学文献没有一个词比“权利”更加含糊不清,洛克和霍布斯将权利定义为一种自由,耶林将权利界定为“一种法律保护的利益”,奥斯汀则指出,权利是“强制某人或者其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能力和权力”。④但是,当我们立足于人的尊严谈论使人成其为人应享有的自由权时,强调的是应然权利,它是人基于道德律享有的本性权利和基本人权,它不以实定法为先决条件,甚至“当义务不存在的时候,权利依然存在”。⑤现代人权理论认为,人类的需要、愿望、欲求及与之相关的行为就是基本权利,如自由、政治参与和追求幸福等。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关乎人格、尊严和幸福,体现了自由和权利的统一,是出自于人本性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应然权利。首先,它体现了公民在是否结婚、是否生育、如何生育上的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属于自我决定权的范畴。其次,从社会交互性和祛除妨害的角度看,它们亦是需要保障的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勒鲁提出的深刻论断,“人的整个人生就是一系列的行动;即使人只在思想,他也在行动,那么用什么词来表达人的表现的权利,因而也是他生存的权利呢?……这个抽象的词,就是自由”。⑥
古典自然法强调人的自然权利的神圣性,建立了以“天赋权利”论为核心的关于应有权利的系统学说。自然法学派按照先验主义,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有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免受侵害的本能,有捍卫自身财产的倾向,有异性相吸、生儿育女的天性等。因为与他人结合成社会的缘故,为了获得他人的尊重,这些天性需要成为了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意愿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的自由”。⑦霍布斯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源泉建立在被治者的自然权利上,托马斯·潘恩则进一步论证了,人是为了使自然权利以更好的方式得到保证进入公民社会的,人的自然权利是所有公民权利的基础,而国家权力来源自同意,人们出于建立社会契约的需要才部分地让渡自然权利给国家。⑧当权利让渡于权力之后,人们大部分应然权利就转变为主权之下的臣民自由,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通过律令来保障成员的应然权利,对应然权利的剥夺需要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和个人关系之基本底线。
审视被判死刑人员的应然权利,生命权因死刑的适用被宣告剥夺,人身自由权因刑罚的应然效果被严格限制。但是,其余的应然权利包括财产权、健康权、人格权等均可正当保留。正因为如此,被判死刑人员有权订立遗嘱自由处分合法财产,因为财产权作为重要的应然权利未被法律剥夺;身患疾病的被判死刑人员有权得到国家救治,因为其在被执行死刑前同样享有健康权;被判死刑人员应有尊严地赴死、不受侮辱诽谤、不被游街示众,因为人格权作为未被剥夺的应然权利仍然为其享有。同理,男女结合、繁衍后代是人类的天性和本能,结婚权和生育权并不是国家创设的权利,而是人的应然权利,公民是带着这些自然权利进入国家状态的,既然国家律令并没有剥夺被判死刑人员的上述应然权利,那么,他们在应然层面享有这些权利便具有道德正当性。
(二)结婚权和生育权是法律规定的实然权利
从实定法的角度看,结婚权和生育权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婚姻自由权和生育权均是基本人权。《欧洲人权公约》第12条规定了公民享有结婚的权利,1984年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宣言》和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规定:“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子女数量和间隔以及为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在我国,婚姻自由权和生育权规定于《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宪法》之中,被判死刑人员可以基于民事主体地位和公民身份主张上述权利。首先,按照《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民事权利能力的存续期间是“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事行为能力的要件是成年且心智正常,被判死刑人员在行刑前仍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其民事主体地位不受影响,可以根据民事主体的地位享有婚姻家庭权利。其次,被判死刑人员虽被判处极刑并被附加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其公民权利并未被概括褫夺,仍具有公民之法律地位,“只不过是犯了罪的公民”⑨。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具有婚姻自由,《人口计划生育法》第17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被判死刑人员当然可以依据公民资格主张上述未被剥夺的公民权利。第三,结婚权和生育权是自然人享有的私权利,根据私法领域“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原则,民事主体的自由和权利存在于法律没有禁止的任何空间,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罪犯。
有反对者认为,“法无禁止即自由”中的“法”不仅包括成文法,还包括与此相关的习惯,我国在“被判死刑人员婚姻”问题上的习惯就是其没有结婚自由,⑩因此,其结婚权站不住脚。这种论证逻辑值得商榷。众所周知,习惯向来不是我国正式的法律渊源,“法无禁止即自由”中的“法”只能是有权机关制定并公之于众的法,并不包括“习惯”,因为习惯具有区域性、流变性甚至不合理性,不能随便给“习惯”穿上“法”的“外衣”来否定私法上的一般自由和权利。而且,“被判死刑人员不能结婚和生育”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习惯,大赦国际的时代趋势、司法人道主义的日渐推进以及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完全可能改变这一官方习惯,肆意以习惯来否定公民权利,将会模糊法治社会为国家权力预设的边界。此外,不少学者将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作为反对被判死刑人员享有结婚权的法律依据,该规范第八十五条在肯定犯人离婚自由的同时,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众所周知,婚姻自由权是一体的,包括缔结婚姻和解除婚姻两个方面的自由,既然罪犯的离婚自由不言而喻,又缘何否定其结婚自由?而且,2004年出台的《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肯定服刑人员可以申请登记结婚。因此,在民政部相关《意见》肯定服刑人员拥有结婚权的前提下,以公安部一个试行的《工作细则》来否定一项法律基本权利,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学者激烈争辩的被判死刑人员是否享有结婚权和生育权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法治的精神要求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剥夺要以明文列举为限,刑罚,包括最严酷的死刑,从未否定过罪犯作为人之理性存在,从未剥夺过罪犯的婚姻家庭权利。因此,从应然层面看,这些权利理应为被判死刑人员所正当享有。
三、“判决死刑”对行使结婚权及生育权的影响
长久以来,我们对被判死刑人员诸多权利的根本否定,症结是混淆了权利之享有和权利之行使。任何权利之行使都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因此,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之间必有罅隙,而被判死刑人员的特殊处境,使其权利的应然和实然状态必然呈现比常人更大的分野。但是,无论是监禁刑还是生命刑,并未在法律上冻结、休眠所有的婚姻家庭权利,亦不能导致所有权利的自动丧失。黛博拉·切尼(D.Cheney)等英国学者对此做过形象的评论,“认为人权在每个监狱的大门前就应该暂停,只有在服刑人员重获自由后迈出的第一步才被再次激活,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11)从权利行使的可能性出发,无论是“判决死刑”还是“剥夺自由”,被判死刑人员的婚姻家庭权利仍有从法定权利走向实有权利之可能。
(一)“宣告死刑”与权利之行使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本源,人的生命消逝,依附于上的权利自然随之泯灭。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容易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权利只存在于活体之上,既然被判死刑人员的生命都被国家剥夺,其他任何权利都是空中楼阁,生育权亦是如此,“活的细胞只存在于活的身体之中,生育能力只存在于生命之中,当死刑判决生效的时候,死刑犯的生育权就已经不存在了”。(12)其实,这种论证建立在一个反事实的前提下,即没有看到从指控死罪、判处死刑到实际执行还有一个时间间隔,在此期间,被判死刑人员仍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活生生的人,其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仍在延续。值得一提的是,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实践中,有的案件几个月就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有的案件却长达三五年才被核准,“宣判死刑”到“实际执行”的最长时间间隔是多少,依照现有法律根本没有上限。鉴于“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的不可同步性,以被判死刑人员肉体之必然消亡来论证其现有权利的虚无性,显然难以让人信服。
(二)“剥夺自由”和权利之行使
人身自由是人权的灵魂,是一个人行使各项权利的基础,但是,自由的丧失并不等于权利的概括剥夺。自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以一定的人身自由为条件,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结社、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等政治权利同样以人身自由为前提,如果剥夺人身自由的效力当然及于剥夺一切以自由为实现条件的权利,那么,将得出“所有判决自由刑的罪犯都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荒谬结论,法院将剥夺政治权利作为一项附加刑加以适用也是多此一举了。
在评判监禁对结婚自由、生育自由的影响上,英美等国的判例也往往体现不同的立场。在美国,死刑犯在囹圄中结婚并非稀奇之事,但是,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审理“戈博尔诉希克曼”案时判决生育权与监禁是从根本上相抵触的。(13)英国国内法院在审理“梅勒”(14)案、“迪克逊”(15)案时认为,生育的权利或机会的丧失是“监禁的一个自然后果”,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却推翻了“迪克逊”案的判决,并一直强调“个人在狱中仍然保留公约上的权利”。(16)自由的丧失,的确使许多婚姻家庭权利处于停止行使的状态,但是,自由的剥夺和婚姻家庭权利的实现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譬如,囚犯无法行使对子女的监护权,但子女可以入狱探视服刑的父母;囚犯无法主张与配偶同居的权利,但表现好的囚犯也可在监狱同居房中与配偶团聚。诚然,缔结婚姻是不可代理的民事行为,而被判死刑人员的确无法“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履行登记手续”,但是,这种现实障碍完全可以逾越。实践中,服刑人员结婚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2003年10月,辽宁省康平监狱一名在押犯在狱警的陪同下领取了结婚证;(17)2009年11月,四川嘉陵监狱为7名服刑人员举行了集体婚礼。(18)既然监禁中的普通囚犯可以通过“出所登记”、“上门服务”等变通途径缔结婚约,被判死刑人员更有理由得到国家的特别关照,实现临终前结婚的遗愿。
与结婚自由权不同,生育权是“人权中一个敏感、重要的领域”(19),是一项比较特殊的权利,生育权的实现受制于各种条件:需要个体的人身自由、有赖于男女双方都有生育的真实意愿,且不能违背国家的人口政策,等等。被判死刑人员作为人身受到高度控制的特殊人群,固然无法像常人一样通过性行为来实现生育权,但是,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变革了生育方式,使得生育权的实现不必以男女双方接触为前提,从权利行使可能性的角度看,人身自由的剥夺和生育权的行使可以兼容。
四、结婚权和生育权——从“应然权利”走向“实有权利”的基础
(一)人权意识的觉醒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仅仅是会说话的工具,罪犯则只能是被压迫的对象和客体,任何罪犯权利都无从谈起。封建专制社会中,虽有一些“仁及囹圄”的人道主义关怀,但这只是封建君主偶尔的恩赐,和罪犯权利的内涵相去甚远。12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唤起了人们对理性的崇拜,文艺复兴更使得自然权利学说深入人心,“自然权利理论的兴起导致了将那些不受人们自然能力干涉的被认同的条件设为权利”,(20)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人人平等”、“天赋人权”思想,使得罪犯权利得见曙光。因为,他们同样生而为人,同样被造物主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他们的价值和尊严应当得到体现。贝卡利亚在1764年出版的《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深刻揭露了旧刑事制度的蒙昧主义本质及种种残酷现象,主张废除死刑,为囚犯提供更好的住所,按犯人年龄、性别和犯罪性质分别关押等,拉开了近代囚犯权利保护的序幕。随着上个世纪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有人无时无刻都应享有底线人权的观点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同,“不仅仅是要有社会就要有权利,而且是若要遵从普遍的低度道德标准的要求,就必须让每个人类成员都享有权利”(21),罪犯包括死刑犯亦概莫能外。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该《规则》第61条规定,“应该采取步骤,在法律和判决所容许的最大可能范围之内,保障囚犯关于民事利益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和其他社会利益”。第79条规定,“凡合乎囚犯及其家庭最大利益的双方关系,应特别注意维持和改善”。综上,在保障死刑犯的基本人权、质疑死刑正当性的时代背景下,被判死刑人员的结婚权和生育权,作为关乎家庭最大利益的特殊权利,作为关乎另一自由公民基本人权实现与否的特殊权利,首先具备了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现实基础。
(二)对犯罪认识的深化
传统的犯罪本质论和报应主义的刑罚观,将犯罪视为对氏族、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道德原则的极端背叛,犯罪破坏了共同体的安宁,甚至威胁到共同体的生存,故共同体将罪犯视为敌对力量,甚至需要在肉体上将其消灭。无论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死刑正当性的论证,“他破坏了国家的法律,所以他就不再是国家的一个成员,实际上,他发动了反对国家的战争,如果这个有罪的人被判处死刑,那并不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敌人的身份”(22),还是马克思对犯罪本质的经典描述,“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抗统治关系的斗争”(23),都体现了将罪犯异化和边缘化的否定立场。既然犯罪已使其沦为国家之敌、人民公害,而且罪行恶劣到非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不可程度,死刑犯和国家的关系自然只剩下刀俎和鱼肉的关系,根本无法奢望国家暴力在剥夺其生命前去关注这个“敌人”还剩下什么权利值得保护、需要保护。另一方面,在根深蒂固的同态复仇、报应主义的观念下,人们自然进行这样的逻辑论证:一个死刑犯残忍地杀害了被害人,他便对被害人的人格、生命没有起码的尊重,国家自然可以“以他待人的方式来待他”,即可以剥夺他的生命,甚至可以肆意践踏他做人的尊严。但是,随着对犯罪本质研究的深入,在对罪犯进行集中的道德谴责之余,人们开始试图从政治、经济甚至人类遗传的角度挖掘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如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拉卡萨涅把犯罪比作细菌,把社会比作培养基;恩里科·菲利则提出著名的三原因论,即“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24)20世纪以来,社会对犯罪和罪犯的态度从全盘否定转向理性包容,开始把犯罪看成正常的社会现象,处罚罪犯也基于尊重他是理性的存在。对犯罪本质、犯罪原因认识的深化,部分消解了全社会对罪犯的敌视情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们企图通过肉体上消灭罪犯来实现特殊预防和报复正义的狂热,全社会对犯人包括死刑犯都建立起一种更为客观、理性和公正的评价态度。如此,尊重和保障被判死刑人员的结婚权、生育权才不至于被指为异端邪说,被判死刑人员的结婚权、生育权才具备了从应然权利走向实有权利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传统文化的支撑
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以“家”为基本单位,在对待婚姻问题上,更是重夫妻之“名”胜过夫妻之“实”。对被判死刑人员而言,缺乏人身自由的处境,使其登记结婚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但是,取得这一纸婚契,往往成为被判死刑人员及其恋人、家人的共同心愿。前文所述的毒枭马某结婚的案例中,马某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女友王某强烈要求和马某结婚,以期腹中胎儿出生后有个合法身份,马某、王某的父母也一致表示,二人完婚是四位老人共同的心愿。2008年,新浪网对山东死囚情侣申请结婚一案开展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77.53%的网民赞成批准这对情侣登记结婚。我们已无法忽视、回避和否认罪犯同样享有结婚权,而且这一权利是其临终的心愿,是付诸较小司法成本即可成全的心愿,允许其行刑前了却一桩心愿,符合司法者和社会普通公众最朴素的道德情感。
中国人重视宗族香火的延续,即便在没有人工生殖技术的古代,封建国家也对死囚延续血脉给予恩悯。早在汉代,就规定了“听妻入狱”的悯囚措施,对娶妻无子的死囚,允许其妻入狱,妊身有子再行刑。《太平御览》引《东观政记》载,东汉“鲍昱为泚阳人,县人赵坚杀人系狱,其母诣昱,自言年七十余,唯有一子,适新娶,今系狱当死,长无种类,涕泣哀求。昱怜其言,令其妻入狱廨止宿,遂妊身有子”。清朝则有“留养承嗣”制度,即死刑案件经复核具备“孀妇独子”条件的,经皇帝首肯,可免于一死,留养承嗣。清朝《大清律例》还规定,“凡依刑处死者,新婚未同房,为免无子嗣,特许新妇入狱一夜,下不为例”。社会文明进步的今天,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实质上废除死刑,中国作为一个适用死刑的国家,对罪犯的人性化关怀更应胜于古代社会,更需用司法的温情来消减死刑的严酷。允许被判死刑人员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为实现为人父母的愿望,为家族留下最后的血脉,符合中国人传统家庭观念,对于无任何过错的被判死刑人员的配偶、亲属和家庭,也是一种体恤和关怀。
(四)政府责任的重塑
根据威斯利·N.霍菲尔德的权利概念,“权利”包括“要求”(claim)、“自主”(liberty or privilege)、“权力”(power)、“豁免”(immunity)四个方面的意思,与“要求”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职责(duty),与“自主”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无权利”(no-right),与“权力”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责分”(liability),与“豁免”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无权能”(disability)。(25)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对于自由公民而言,是“自主”的权利,即一个人享有结婚和生育的权利,意味着其他人无权干涉。但对被判死刑人员而言,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却是“要求”的权利,即被判死刑人员的结婚权、生育权能否从应然权利成为实有权利,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愿为这一特殊人群履行一定的义务。被判死刑人员结婚权的行使,依赖民政部门“上门服务”或者监管机构“押送登记”;被判死刑人员以辅助生殖方式行使生育权,更是需要监管机构、医疗机构的通力配合。那么,政府是否有责任这一特殊人群行使权利提供便利呢?
根据德沃金的“平等尊重和关怀”理论,政府统治之下的所有人,包括每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是权利的享有者,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对政府行为道德要求之要义。(26)因此,一个理性的政府,必须关怀、尊重他所治理的人,视每一个人为共同体的真正成员,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人的权利,包括过错的公民、犯罪的公民甚至被国家判处死刑的公民。另一方面,我国死刑罪名多,被执行人等待执行期限长,这一特殊群体的权利状况,往往成为国内和国际社会判断我国人权水平的风向标。因此,从婚姻家庭权利入手,尊重和关怀被判死刑人员的最后愿望,最能体现出政府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如果处于社会底层的罪犯权利都能得到有效保障,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权水平可谓毋庸置疑。
在被判死刑人员的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重塑政府的责任:首先,依法惩处罪犯,这体现的是刑罚的威慑和对犯罪的特殊预防;第二,国家权力善意的动机并非总会实现善意的结果,而生命之剥夺具有不可逆性,因此,政府需要竭力保障被判死刑人员的程序性权利以杜绝非法的指控和错误的执行;第三,保护被判死刑人员的底线人权,因为“罪犯,无论其犯罪轻重,总是作为人而存在,他与普通人一样享有基本人权”,(27)政府需要对每一个公民包括罪犯给予平等的关怀和尊重。目前,触目惊心的冤案已经使中国政府从偏重第一个目标递进到实现第二个目标,但是,追求更高的第三层次目标仍是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以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为己任的理性政府,不仅需要为死刑案件设置繁琐而代价高昂的正当程序,也需要为被判死刑人员合理行使基本权利支付一定的司法成本,因此,这同样张扬着生命至上的理念。现阶段,我们仍无法摒弃死刑这一刑种,但是,当国家在准备发动暴力机器剥脱罪犯的生命时,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行将就死的个体,仍是一国之公民,对其正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应持一种审慎、宽容和悲悯的态度,在不过度耗费司法成本和不危及监管安全的前提下,为保障被判死刑人员的基本权利而有所作为,是一个理性政府的自觉选择。
(五)人道主义的张扬
临终关怀(Hospice Care),原义是指对临终病人的生理心灵提供全面照护,使其舒适安宁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旅程。随着人们对生命尊严和人道主义的反思,临终关怀的价值已超过医学范畴,在国家权力以“报应和威慑”为由准备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出于对生命的敬畏,需要对被判死刑人员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关怀,使其更平静地面临死亡。在古代中国,已经有“仁及囹圄”的人道主义关怀。譬如,晋《狱官令》载,狱中需“去家远无响馈者,悉给廪,狱卒作食,寒者与衣,疾者给药”,而死囚在大限来临前大多享有修整仪容和供给饮馔两项基本待遇,体现了行刑者对将死之人的恻隐之心。当今,随着刑法向人道主义的道路迈进,保留死刑的国家开始尽可能地给予死囚临终关怀。如美国的死刑执行制度便体现诸多人文和宗教关怀,“在行刑现场,为了缓解受刑人的紧张,允许其亲属、朋友、辩护律师到场,心理医生也允许被请到现场进行心理疏导,照顾受刑人的宗教习惯,还允许牧师到场作祷告”,(28)有的国家允许死刑犯行刑前与家人共进最后一顿告别餐,甚至允许死刑犯与配偶临终同居。(29)
现代刑罚讲求人道主义,给予被判死刑人员尽可能多的临终关怀,是平衡刑罚的惩罚性和刑罚的人道主义之必然选择。梁启超曾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让“生命的归生命、权利的归权利”,应该成为解决被判死刑人员权利问题的基本法则。惩罚和关怀可以并行不悖,国家基于严厉刑罚剥夺其生命,并不妨碍我们基于人道主义保障其权利。实践中,在临刑前给予囚犯生活条件上的优待、允许其会见亲属,聆听舒缓音乐等,都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被判死刑人员的临终关怀。笔者认为,既然罪犯同样生而为人,同样享有民事权利包括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在既不妨碍死刑判决的执行,又无损于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其生前最后一个愿望,减少赴死之人的牵挂和遗憾,又何尝不可?
五、被判死刑人员结婚权、生育权之行使限度
在婚姻家庭权利中,结婚权是一项相对容易实现的权利,仅仅需要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变通措施帮助其履行婚姻登记手续即可。但是,被判死刑人员毕竟不同于自由公民,出于羁押安全和社会效果的考虑,其行使结婚权应受到下列限制:(1)被判死刑人员及其结婚对象均需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且不在法律禁止结婚之列,尤其需要保证自由公民一方结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和自愿性;(2)被判死刑人员及其结婚对象具有良好的感情基础;(3)被判死刑人员及其结婚对象依法履行婚姻登记手续成为合法夫妻,但是,无法和普通夫妻一样同居生活。此外,在被判死刑人员的女友已怀有身孕或者二人已养育非婚生子女的情况下,一般应同意二人的结婚申请。从社会效果出发,司法机关一般还应该征询双方父母的意见。
反对被判死刑人员享有生育权一个重要的理由是,生育权行使的结果可能创造一个新生命,而这个生命一出生将被贴上死刑犯子女的标签,也无法在父母的共同关爱下成长,“允许被判死刑人员生育子女,看似保护了罪犯的权利,却同时侵害了他子女的权利”。(30)但是,正如英国学者艾米莉·杰克逊(E.Jackson)所指出的,“将孩子的幸福纳入考虑是一个误导,因为考虑服刑人员可能生育的任何孩子的将来的幸福太具有主观臆断性”。(31)任何孩子都没有选择父母的自由,单亲家庭的小孩也未必不会拥有幸福,我们无法站在“法律父爱主义”的立场来规划一个未出世孩子的最大利益,也无法基于“人口优生优育”的政策来限制无父无母孩子降临人世。英国上诉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迪克逊案”时都正面回应了“未出世孩子的最佳利益”这个哲学争议:这是一个无身份问题(Non-identity problem),被保护的这个人永远无法从他们最佳利益这个假设中获益,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出生。(32)可见,“不利于下一代”只是一种主观揣测,无法以这一假定来剥夺被判死刑人员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鉴于被判死刑人员难以履行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义务,基于社会责任的角度,我们应对其行使生育权给予更为严格的限制:(1)被判死刑人员从未生育过子女(包括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2)坚持申请在先原则和自愿原则,未经被判死刑人员及其配偶的共同申请,不得实施辅助生殖技术;(3)被判死刑人员系三代单传或独生子女;(4)利用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费用由被判死刑人员或其家属承担;(5)被判死刑人员及其配偶的夫妻感情良好,其配偶具备独自抚养子女的能力和条件。为保障被判死刑人员所生子女尽可能具备较好的成长环境,可设置一定的司法审查的基本标准。
我国刑法规定了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如果允许女犯通过怀孕的方式行使生育权,必将与刑法规定发生根本冲突,妨碍死刑判决的执行。从技术层面看,被判死刑的女犯只有通过代孕这一辅助生殖方式行使生育权。值得注意的是,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也就是说,在代孕技术取得法律认可之前,被判死刑的女犯缺乏行使生育权的合法途径。但是,这并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当说,这一规定本身也给我们进一步思考女性死刑人员生育权实现问题提出了新的课题。
注释:
①本文所称的被判死刑人员,是指被一审或二审法院判处死刑(不包括死缓),但尚未交付执行的人,与联合国1984年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中界定的“面对死刑的人”(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范围基本一致。
②该报道称,山东省苍山县一对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的青年男女,在得知双双被判处极刑后,竟然提出了一个罕见的“请求”——在被执行死刑前,批准他们领取婚姻登记证书并举行婚礼。
③文中所述案件中的毒枭马某,在审查起诉阶段向公诉人提出结婚请求时,尚属于“未决犯”,但之后被法院判处了死刑。
④[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四卷),王保民、王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3-54页。
⑤[美]T.M.本迪特:《作为规则和原则的法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68页。转引自公丕祥:《权利现象的逻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⑥[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2页。
⑦[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7页。
⑧参见《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⑨李步云:《论人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8页。
⑩参见周永坤:《死刑犯的结婚自由及其论证方法问题》,http://guyan.fyfz.cn/art/309460.htm,最后访问2012年10月19日。
(11)D.Cheney,R.Dickson,R.Skilbeck,S.Uglow & J.Fitzpatrick,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2nd ed.),Bristol:Jordon Publishing,2001,p.194.
(12)侯国云:《法院应该理直气壮,死刑犯没有生育权》,《法制日报》2002年3月31日。
(13)Gerber v.Hickman,Supra at 622-623.
(14)R(Mellor)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2001] 3WLR 533).
(15)Dickson v.United Kingdom(44362/04)[2008] 1 F.L.R.1315(ECHR(Grand Chamber)).
(16)Dickson v.United Kingdom,Supra at68.
(17)参见:http://news.sina.com.cn/c/2003-11-20/16501157251s.shtml,最后访问2012年3月1日。
(18)罗暄:《四川嘉陵监狱首次为服刑人员举办集体婚礼》,《华西都市报》2009年11月7日。
(19)Skinner v.Oklahoma,316 U.S.535(1942)
(20)[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四卷),王保民、王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21)[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
(22)[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徐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9页。
(24)[意]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25)W.N.Hohfel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6 Yale Law Journal,1917.
(26)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7)邱兴隆主编:《比较刑法》(第1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28)郑延谱:《中美死刑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
(29)杨帆:《关于死刑犯权利保障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0)赵运恒:《罪犯权利保障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31)E.Jackson,"Conception and the irrelevance of the welfare principle",Modern Law Review,vol.65,2002,pp.176-203.
(32)J.Robertson,"ProcreatiVe liberty a harm to offspring in assisted reprodu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Law and Medicine,vol.30,2004,pp.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