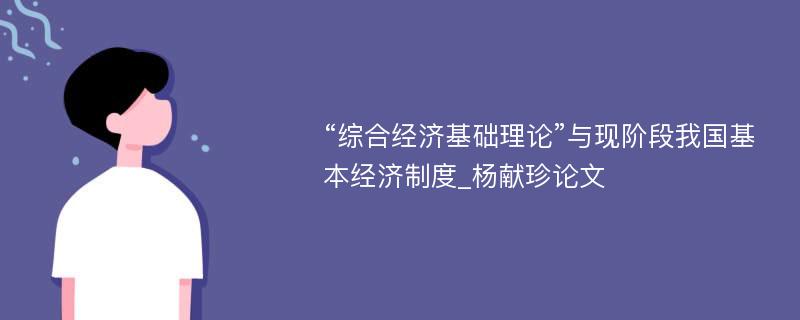
“综合经济基础论”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基础论文,现阶段论文,经济制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3)05—0516—04
一、“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论争的历史考察
“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理论论争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长达近30年之久。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理论讨论时期(1953年~1957年)。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理论界围绕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以杨献珍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我国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以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领导成分的五种经济成分,也就是五种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即所谓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另一方则认为经济基础特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即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分配形式)的总和。因此,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有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国营经济),其他几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不属此列,即所谓的“单一经济基础论”。
第二阶段是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大批判时期(1964年~十年动乱)。在康生等人的策划下对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进行政治大批判,指责其取消了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杨献珍惨遭8年监禁和3年半的流放,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单一经济基础论”成为占主导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观点,此论独尊性地成为“经典”之论,并长期作为制定政策、撰写论著、教育学生的理论根据。
第三阶段是1979年以后,在进行真理标准讨论和拨乱反正过程中重新展开了讨论。杨献珍平反后,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自己从未公开而屡遭批判的1955年的讲稿,以及在狱中所写的从未面世的《关于“综合基础论”问题的申述》,以澄清事实真相,为“综合经济基础论”正名。报刊上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但在理论界未引起大的反响。“单一经济基础论”导致中国国民经济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历史宣告了它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上的失败。改革开放的实践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获得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客观真理性,然而理论上的研究探讨却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以至于是非混淆,谬种流传,相延至今。
二、“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内涵及方法论考察
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基本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他1953年撰写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和1955年撰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以及《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问题的申述》等文章中。他在文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问题进行了论述,从理论上批驳了“单一经济基础论”。
杨献珍十分重视对经济基础问题的研究是基于他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之上。他指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关系着我们党当前及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的问题,是关系我们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若不弄清楚,在实际工作中难免要犯错误。”[1](P5)这一认识有着理论的深度和历史的高度,其理论洞察力和预见性已为历史所证明,哲人的忧虑已成为历史性的悲剧。
杨献珍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视为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强调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来认识我们的经济基础。他指出:“马克思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又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成是自然历史过程,这样他就发现了社会的发展规律。”[2](P99)这就是马克思把社会学变成科学的关键所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经济基础问题,就是要把中国在过渡时期的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处在经常发展过程中的活的“有机体”,客观地分析组成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理清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是由哪些生产关系组成的。[2](P401)他强调中国在过渡时期还是一种多种经济成分的国家,这是一种客观现实,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历史出发点和立足点。在还没有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中国,客观上存在着这样几种生产关系:一是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二是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三是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四是个体农民所有制;五是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幅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轮廓图,完全正确地反映了经济“基础”的实际情况。杨献珍指出:“中国现在明明还是一种多种经济成分的国家,这是一种客观现实,而‘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却硬不承认这种客观现实。这种所谓‘理论’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基础’学说的原理的。”“单一经济基础论”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客观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而是“自命为世界改革家以自己所发明或发现出来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2](P398)根本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杨献珍不仅对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进行了客观分析,而且对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基础进行了普遍性的考察。他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设问:“迄今以前,有没有这样一种社会,即在该社会中只存在着单独一种所有制形式或生产关系?”[1](P8)并对此进行了考察。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占统治地位的,因而就以资本主义来标志这一阶段的社会性质,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也是有几种,而不是只有一种。……除了大工业的生产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还有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者的生产,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企业的生产,还有在贵族地产上做工的农奴式的生产,以后还有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生产。那么在这些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的生产关系,是否只是一种呢?显然不是这样的。”[1](P9)当时的苏联社会开始也是在具有五种经济成分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杨献珍由此得出了合乎历史逻辑的结论:“在剥削阶级没有消灭以前,还没有看到过哪个社会中仅仅只存在着单独一种所有制,单独一种生产关系的”。“在剥削阶级还存在着的社会中,不能说‘基础’就只包括一种生产关系,或者说某一种生产关系就是整个‘社会’。历来的统治阶级就不是这样看法。它们总是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它们的‘基础’”。[2](P423-424)杨献珍坚持唯物辩证法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方法论,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过渡时期的客观经济“基础”的历史考察,得出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包括多种生产关系的、综合性的“基础”的科学结论,即“综合经济基础论”。
杨献珍深入考察分析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论证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科学性。当时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一论断,在理解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将经济基础理解为“一定社会经济形式的诸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是生产关系的诸方面即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分配方式这三者的总和。杨献珍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经典作家对经济基础的科学定义,经济基础是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他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两个名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单数和复数的关系。不能混淆“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与“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区别,将两者等同视之。“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是将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杨献珍阐述了自己对“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理解:在一种有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里,每种经济成分,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其中占领导地位的经济成分是什么性质,就决定那个社会是什么性质。这个社会有几种经济成分,就有几种“生产关系”。这几种“生产关系”的结合,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叫做“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那个社会的“基础”。[2](P51)他认为按照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名词,都是讲的一件事,就是经济“基础”。因此“基础”就是整个“社会”的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2](P403)
杨献珍对“单一经济基础论”的理论误区深为忧虑,他指出:“在阶级还没有消灭的、还有多种经济成分的、亦即还有多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中,若把这两个名词理解成为是同一个概念,那就要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在还有多种经济成分亦即还有多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中,只能说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经济形态,不能说是某一种生产关系组成社会经济形态。说一种生产关系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这无异于说一种生产关系就构成一个社会。这样说就错了。社会经济形态是说的整个社会,所以只能说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经济形态。”[2](P418)遗憾的是当初谬误被崇奉为真理,理论的混乱造成了实践中的灾难。
杨献珍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的基础中既然包括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就应当在上层建筑中也有它的反映,就是说,资产阶级思想观点也应当在新中国的上层建筑中有它的地位”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还是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但在这多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新中国的统治思想。[2](P422-424)
杨献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科学地界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两个概念的内涵,论证了“经济基础”的涵义和在中国过渡时期的“综合性”,而且正确地把握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坚持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从而将“综合经济基础论”奠定在科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三、“综合经济基础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错误地将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斥为异端邪说,把“单一经济基础论”奉为正统思想,造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灾难性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经作了历史性的结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3]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单一经济基础论”作为基础理论起到了破坏性的误导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突破了“单一经济基础论”的禁区,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经济格局,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许多重大改革理论、改革举措和经济政策无不与所有制改革密切相关。经济体制改革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也是对“单一经济基础论”的否定。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初步形成了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私有制、外国资本所有制以及其他形式所有制构成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经济形态,这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综合经济基础”。党的十五大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继承与超越。
从“综合经济基础论”到“单一经济基础论”再到“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运动。我们党对“经济基础”的认识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高度,“综合经济基础论”从我国过渡时期的物质生产力现实发展水平出发,唯物辩证地考察了中国社会一主多元的诸种生产关系,将其视为一个“平衡发展”、动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提出了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范畴的理论内涵,从而得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科学结论,并论证了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由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它决定了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道路。这些有价值的科学思想被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升华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党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深化拓展了“综合经济基础论”,扬弃了它认为过渡时期完成之后就变成纯粹的公有制经济的理想成分,超越了其历史局限性,把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考察和研究在经济基础认识史上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逻辑,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综合经济基础论”,纠正“单一经济基础论”的错误,更正理论界、教育界存在的理论误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是十分有益的。
标签:杨献珍论文; 所有制论文; 上层建筑论文;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论文; 基本经济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过渡时期总路线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过渡时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