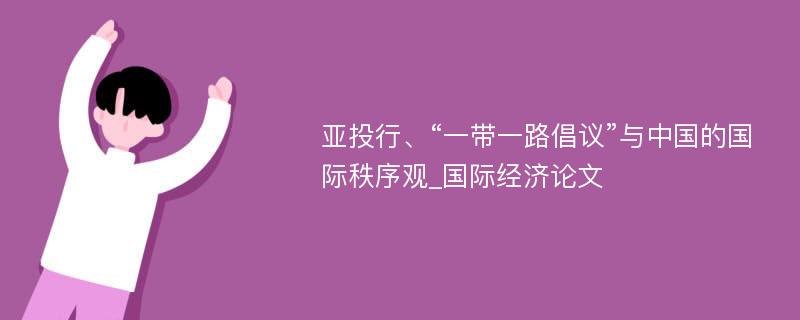
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投行论文,秩序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13年,中国领导人在出访中亚、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等重大倡议。而后,亚投行在域内外获得了众多国家的支持,2015年12月正式成立,2016年1月正式开业。以2015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和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标志,“一带一路”也从最初的设想进入了实施与推进阶段。鉴于亚投行、“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和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①其受到广泛关注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国内外学界就此迅速跟进,展开了热烈的探讨。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亚投行等新机制带来的影响或冲击,以及中国发起一系列新举措的目标或意图。有趣的是,各种观点之间似乎已呈现出明显的“中西之别”。国外多有论者强调亚投行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的冲击甚或威胁,其言辞往往暗示甚至表明了对中国的戒备与忌惮。例如,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罗伯特·魏图认为,亚投行等倡议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的风险。不仅如此,某些由来已久且行之有效的治理标准可能因此遭到削弱。②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帕乌拉·斯帕奇则相信,亚投行或许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但可能危及多边主义及善治的理念和实践。与魏图的看法相似,她也认为亚投行推行的贸易投资标准可能令全球经济陷入碎片化的困境。③至于中国的目标,《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欧美主流媒体多以现实主义色彩浓重的视角加以审视,从而得出大同小异的结论,即中国试图在削弱美国、日本的同时,扩张自身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④亚投行是中国凭以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⑤对此,美国史汀生中心的研究人员甚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亚投行带来的挑战,以“遏制中国过大的战略目标”。⑥ 与上述“怀疑论”、“削弱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论者对这些战略举措普遍予以称许和认同。一些学者认为,亚投行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⑦非但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经济机制,更将创造和带动可观的市场需求,有力维持世界经济的良性运转。⑧ 然而,这些形形色色的褒贬之见看似泾渭分明,实则有着共同的缺陷或盲区。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讨论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更多停留在对事件本身的回顾和阐发阶段。⑨其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在现有条件下,相关视角约束甚至阻碍了讨论的深入。无论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都还只是刚刚起步;与之直接相关的信息、数据、资料还远不够翔实丰富。受此局限,将重心放在事件本身的相关探讨,大多呈现出观点有余而依据不足、判断有余而论证不足的特征;该主题也因此面临着缺乏深度、厚度,甚至泛化、浅化的危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并无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呢?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尽管微观层面的具体信息仍有待充实,但战略性、全局性的宏观探讨完全可以同时展开。后一种分析路径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界忽视以致付诸阙如,然而其蕴含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很可能并不逊色甚至超乎既有讨论之上。 这也正是本文用意之所在:我们希望能够弥补上述空白,提出有新意的问题,作出有价值的探讨。具体而言,我们试图以亚投行、“一带一路”为切入点,通过这些标志性事件来审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变及其根本原因。选择这一视角的理由还在于,任何关于亚投行、“一带一路”之影响,以及中国之目标或意图的讨论,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这一基本背景,就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言之成理的判断。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看法是否发生了转变?如果是,其表现、特征及根本动因何在? 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阐释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二节考察中国此前即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的国际秩序观;以此为观照,第三节讨论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重点是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秩序观延续与变化的根本原因;最后回到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结合本文主旨,就其前景与面临的关键问题略作阐发。 一、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概念辨析与分析框架 国际秩序观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因此在讨论展开之前,对其作出明确界定是必要和有益的。如前所述,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指的是中国如何看待国际经济秩序与本国发展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即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国际秩序观,或者说中国的国际经济秩序观。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三:何谓秩序?何谓观念?为何将考察重点放在经济层面? 首先,根据赫德利·布尔的看法,秩序是包含着特定目标或价值(例如对生命、守信、产权的尊重和保护)的格局。⑩天儿慧在《政治学百科全书》相应条目的基础上,将秩序界定为各行为体的“关系、功能和规范”在静态、动态层面得到稳定的维系。(11)与此相应,国际秩序即追求体系生存、国家主权等基本目标的行为格局。(12)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中“存在着可以指导国家间互动的稳定的规则和安排”。(13)至于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就是“国际经济关系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某种相对稳定的格局、结构或模式”,(14)它涉及一系列“原则、规则与制度”,通过保障安全、减少交易费用而“促成资源的有效配置”。(15) 其次,我们所说的“观念”,包含“原则化信念”与“因果信念”两个层面。这一区分沿用了朱迪斯·戈尔茨坦与罗伯特·基欧汉的做法,他们将观念划分为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三个层次。两位学者认为,观念即“很多人所共有的关于世界本质的特定信念”,其中,那些在最根本意义上“规定着行动可能性”的概念属于世界观;原则化信念是被用于区分孰是孰非、正义与非正义,具有规范意义的准则;因果信念则是“关于原因—结果关系的信念”,为行为体“提供了如何实现其目标的指南”。(16)显而易见,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宿命论”或“命定论”在国家层面早已没有容身之所,用戈尔茨坦等的话说,“认为人类在自身命运的建设中是积极的行动者”这种“现代主义看法”(17)主导着中国的决策与行动。因此,我们集中关注后两个层面的观念。 最后,之所以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仅因为亚投行、“一带一路”首先是经济举措,更因为经济因素历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考虑到冷战结束以来经济互动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日渐提升,我们完全可以说经济秩序观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内容;在国内外局势不出现重大、剧烈变动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首要内容。正如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所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18)许多学者也观察到,利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本国发展被中国视为关键要务;(19)“中国的外交政策历来是通过其发展进程而得以界定的”。(20)罗斯玛丽·富特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塑造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因素,在于其经济发展与国内稳定如何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国际体系内主导国家的影响。(21) 厘清了基本概念之后,随之而来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分析路径。由于我们试图探究的目标——“观念”并非可以直接观察的实体,因此分析的成败就取决于能否找到与之高度相关且相对易于观测的对象。在本文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建立在两个前提假定之上:第一,观念必定体现于言行;(22)第二,国际秩序必然体现为特定的机制。更具体地说,只要中国与外部世界存在互动,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体现在话语和行动两方面:前者包含政策宣示、官方表态、正式文书等等,后者则涵盖中国在不同场合的选择与决定。在纷繁复杂的互动之中,国际经济机制(23)集中反映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关键要素与根本特征。(24)如果我们同意这两点基本假定,那么就有理由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互动,以此来辨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这正是本文将要采用的分析路径。 二、中国国际秩序观之演进:维护自主性 如果以21世纪初为大致意义上的分界线,那么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该时点之间的国际秩序观或可概括为维护自主性。中国在逐渐接受、认同乃至支持多边主义规范主导下、以推进国际经济一体化为己任的国际秩序的同时,始终高度关注并且致力于维护自身在这一秩序中的自主性。(25)从原则化信念层面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既包含着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大致认同,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保留和不满。与此相应,在因果信念层面,中国采取了将推动开放与维护自主性融为一体的主导策略,以实现自身在秩序内的发展。这一特定的秩序观集中体现在中国与国际经济机制的互动之中。 (一)既有秩序观之体现 1978年中国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标志着其身份开始从既有国际经济秩序之外的反对者转向秩序内的参与者。这一转变背后有着观念层面的深刻含义,即中国从1949年之后三十年的实践中得出了如下判断:将自身隔绝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固然可以暂时免于跨国经济活动的冲击和扰动,但就长期而言则意味着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甚至有被“开除球籍”之虞。相形之下,如果应对得当,参与现有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很可能远远超出其代价,从而有助于中国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由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体现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机制之中,因此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于它和该机制之间的互动。 总体而言,中国在这一时期遵守了布雷顿森林机制的基本规范与准则,成为现有秩序的遵守者和支持者。关于中国与布雷顿森林机制的权威分析表明:中国在参与这些代表性机构、遵守其规则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不仅对后者的“正常运转作出了相当贡献”,而且提升了它们的正当性。(26)19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在官方话语中开始使用“相互依赖”这一曾经被排斥和否定的表述形式,隐含地表示了从相互依赖关系中获益的可能,(27)从而赋予其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这一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中国参与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之“核心理念就是对相互依赖、比较优势等概念的认可和接受”。从实践来看,中国既没有试图在理念和组织层面对布雷顿森林机构作出重大改变,也没有为自身要求特殊的、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28)正如阿米泰·埃茨奥尼所指出的,在国际经济活动的众多领域,包括贸易、货币等等,中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表现出长足的进步;如果以横向意义的国别比较来衡量,比中国做得好的国家并不多,而逊色于它的却大有人在。(29) 不过,就本文关注的角度而言,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并未毫无保留地接受布雷顿森林机制的规范和准则,以及相互依赖、比较优势等核心理念。中国固然没有积极谋求改变既有秩序,但是反过来,在既有秩序及其规则可能或试图介入中国重视的关键领域时,后者往往表现出极为坚决、不容控制权旁落的主导姿态。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机制中的保守、被动倾向。例如,江忆恩指出,中国鲜有提出新国际经济规则之举;(30)雅各布森等也认为,中国尽管充分参与了布雷顿森林机制的相关决策,但几乎没有“提出过重大倡议或寻求发挥核心作用”。(31)用王赓武的话说,“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市场经济的贡献仍然有限”。(32)对此,一种颇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关注点集中在理解和认识国际规范与机制,而不是影响、改变之。(33)应该说,这些看法对于考察中国的秩序观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不过,我们想要补充和强调的是,对既有规范及规则的默认,并不等同于在相关经济事务上的“无为”。相反,通过国内层面的调整和干预,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着自由主义理念渗入本国经济领域的途径和节奏。 这一点在中国面对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对相互依赖理念的认同度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使在加入布雷顿森林机制之后,中国仍然重视自力更生的发展理念,并没有因为对相互依赖的逐渐接受而放弃前者。(34)无论“华盛顿共识”还是其开出的政策处方,在中国都没有受到如世界其他地区一般热切的追捧和仿效;(35)中国从未实施过激进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方案,(36)而是在推进经济开放的同时,力求防止新自由主义对本国发展空间构成侵蚀和损害。(37)另外,中国对比较优势理念的接受同样是有保留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之后指出,仅凭比较优势和自由市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做法,很可能是一叶障目;中国实际上并未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来发展本国的生产专业化,其出口结构所对应的技术含量和生产率水平远远高于其要素禀赋所能解释的程度。(38) 弗朗西斯·福山将中国对待国际体系的态度称为“防御性”。(39)这一判断触及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某些重要特征。从本文视角来看,所谓“防御性”姿态,实为“维护自主性”的外在表现。以IMF为例,中国于1980年恢复成员国身份时即已成为该组织内持有份额比例仅次于几个西方大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意味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能够动用更多的IMF资源。(40)尽管如此,中国在向IMF借款方面始终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其中关键的原因应该是:中国不愿因为背负过多债务而在重要的经济决策上不得不受制于外部力量。(41)早在1974年,中国财政部与外交部联合提交的一份报告就着重表达了类似的顾虑,即IMF成员国身份将对中国在财政货币方面的自主权构成约束和限制。(42) 此后的相关进程表明,这种提防与戒备在1980年之后中国与IMF的互动中得以延续。1981年中国向IMF借入4.5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一额度在第一档次信贷区间内、不必面临严格的限制性条件,以及3.09亿美元的信托基金贷款。仅仅两年后,中国就宣布即将偿还第一档次信贷的借款。到1984年,中国如数偿还了所有借款。(43)从数额来看,中国在1980年代从IMF借入的款项总额并不大,(44)偿债压力和风险完全在可控范围内。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再也没有从IMF借入过任何款项,反而成为后者的债权国。(45)中国与IMF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也没有因为双方业务合作的顺利开展而消失,来自中国的一名执行董事在离任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表示,IMF仍然表现出过度市场化的倾向,所推出的政策处方也往往过于教条化和模式化。(46) 中国与世界银行的互动也呈现出相似特征。出于对自主性的高度重视,中国从未寄望于或倚重外部资金作为自身发展的主要动力。邓小平在1980年与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会面时表示:即使没有世行的帮助,中国也能实现现代化建设;但有了世行的帮助,中国的发展就可以更加迅速。(47)中国自1981年开始从世行获得贷款,其额度长期居于世界前列,(48)但即使是1995年世行对中国的贷款支付达到32亿美元的峰值时,该数字仍不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9) 在“维护自主性”这一根本战略的指导下,“以我为主、立足国情、平等互利、相互借鉴”成为中国与世行的合作方针。(50)中国与世行三十多年的合作堪称典范,但双方在价值观、政策倾向等方面的分歧亦是客观事实。1988年中国在与世行就结构调整贷款展开谈判时,明确表达了对限制性条件的拒绝。由于中国的坚持,世行没有对中国提出相应要求。对此,雅各布森等评价道:中国极力避免自身陷入如下境地,即“不得不应外部权威的要求而在国内层面采取行动”。换言之,当外部机构“要求”中国作出改变时,中国通常不会接受;而当外部机构提出改变的“建议”时,中国的应对就显得更加留有余地,也往往更富弹性。(51)其间差异固然与“建议”或“要求”的内容是否合理有关,但一个不容置疑的决定因素则是中国对自主性的珍视与坚持。 中国与GATT/WTO的互动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例证。国外有学者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表现描述为“一贯保持低调”。(52)这种低调姿态既是中国学习WTO规则、作出自我调整的体现,也反映出对既有贸易秩序某种程度的认可。尽管如此,低调并不等于全盘接受,也不等于完全满意。中国于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直至2001年才正式加入WTO。无论是谈判过程,还是入世前后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往来,中国都表现出维护自主性的强烈意愿。奥克森伯格等认为,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在诸多贸易议题上更多地表现出经济利益导向,而不是意识形态导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中国不惮于在贸易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53)前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也指出,中国与发达国家谈判时作出的让步都是在非核心利益领域,且都是相互而非单方面的让步。(54)之所以如此,关键即在于中国从一开始就力图防止本国核心经济产业和部门因受制于自由贸易规则而失去必需的成长空间。这些产业和部门由于蕴含着更多的“市场势力”而成为一国经济竞争力的根基,同时也决定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地位高下、获益多寡。(55)从中国的生产与贸易活动来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这些关键产业发展的措施。罗德里克观察到,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许可证等在内的许多限制性政策,直到1990年代仍得到广泛应用。(56)这些干预主义的做法背后是一种迥然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观念:除非发挥国家的强大力量,否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将无望得以弥合。(57)即使在加入WTO之后,中国也没有放弃对自主性的维护,只是实施方式有所改变。WTO成员国的身份使中国此前运用的许多产业政策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它转而通过汇率政策来实现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和支持。(58) (二)既有秩序观之成因 以“认同与不满并存、开放与自主性兼具”为特征的秩序观之所以会形成,一方面在于国内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另一方面则在于对克服、至少是缓解外部风险及冲击的追求。从内因来看,彼时国内政治进程的深刻变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19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领导层的更迭,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总路线逐渐得以改观,严格、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松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外贸政策开始呈现出更多的外向特征。与之前高度封闭、自给自足的状况相比,打开国门、利用外部市场促进自身发展,已成为这一时期清晰可见的前景。(59)显然,如果没有国内层面的转变,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认同将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对外部世界的警惕与戒备则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考量层面。即便在1950年代中苏关系最为密切之时,加入后者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的提议也被中国断然拒绝。雅各布森等对此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中国力求保持独立自主,不愿成为苏联支配下的国际经济与分工体系的附庸。(60)这种强烈的自主倾向在改革开放后仍然得以维系。在中国领导层看来,世界市场与生俱来的波动性始终是需要谨慎应对的干扰之源。(61)例如,受到1980年代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各国触动,中国对外债风险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态度。(62) 从外因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面临着尤为不利、甚至严苛的外部环境,这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成功者寡、失败者众的现状。首先,主导国际经济治理的基本规范自1980年之后变得愈加偏颇甚至极端。二战后数十年间,国际经济体系曾经以“内嵌的自由主义”为主导理念,(63)后者虽然受到各种因素掣肘而未能完全实现其发展使命,但至少赋予了发展中国家运用适当政策手段、追求本国发展目标以国际层面的合法性。(64)然而到了1980年代,该理念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以“华盛顿共识”为集中体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机制视作“能够激活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行力量”,(65)在“收缩国家”这一核心要旨(66)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与布雷顿森林机构联手以“开放有益于发展”为由,(67)要求发展中国家迅速开放贸易、投资,实施政策调整。(68)受此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失去了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支持,在经济领域又被迫实行利率高企、汇率高估等有害于增长的政策,最终无力缩小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成为必然结果。(69)既然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的”,(70)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必须重视的关键之处就是如何保障国家利益免遭国际资本的侵蚀。(71)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虽然没有完全免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也始终对后者抱以防范姿态,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 其次,发展中国家受到的约束和障碍也反映在国际组织的行为层面。尽管从理论上说,国际组织行事应当以规则为准,对待不同成员国应做到不偏不倚,但现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的多项研究表明,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时,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往往给予更加周到的照顾或特别待遇。(72)换言之,不论合理与否,美国利益在主要国际组织内经常能够得到更多、甚至过多的保护。然而,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这些组织的表现却截然相反。曾经在IMF任职多年且身居高位的一名经济学家批评道,该机构致力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却对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需求漫不经心、冷漠以待。(73) 在“双重标准”的指引下,IMF与世行迫使第三世界放弃了国家主导型政策,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自主性因此遭到严重削弱。(74)而当它们确实陷入困境、需要布雷顿森林机构施以援手时,后者的所作所为却让发展中国家更加失望甚至愤怒。1997年,韩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告罄,不得不向IMF紧急求助;随后,IMF对韩国央行实施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干预,功效却乏善可陈。(75)正如朱云汉所言,IMF给出的解救方案,实质是牺牲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来保障西方债权机构的短期利益。(76)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愿向IMF申请贷款的真正原因:它们相信,与IMF提供贷款的可能益处相比,本国自主权削弱所导致的损失代价要高昂得多。(77)在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境遇也没有实质性改观。虽然GATI/WTO为解决“发展赤字”而规定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区别待遇”原则,(78)但事实却是,近二十年间穷国在贸易谈判中所作出的让步比富国更大、更多。(79) 上述问题由于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支配地位而愈加凸显。长久以来,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机构——IMF、世界银行、GAIT/WTO作为规则制定者、维护者的形象根深蒂固。一些国家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甚至直接受到IMF与世行意见的左右。(80)公共与私人部门对这些组织的认可,使它们掌握了衡量、评判各国政府行为是否“遵纪守法”的权柄;因此,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愿站在它们的对立面。(81)不仅如此,与发展中国家在理念上更为一致的联合国经济机构——如贸发会议(UNCTAD)、开发计划署(UNDP)等,则由于资金等方面的严重约束而难以对布雷顿森林机构形成制衡。这也就意味着,当发展中国家试图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案或求援对象时,它们常常发现自己“别无选择”。(82)因此,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贸发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警告发展中国家:“假如别的国家选择对抗和舌战的途径,我们是可以抵抗的。对于不切实际的建议和先发制人的要求,我们也可以置之不理”。“工业国的力量必须被视为对所有国家取得进步的一种保障;发展中国家如果通过故意造成的匮乏、卡特尔、禁运或者专断地没收财产等行动削弱这种力量,结果只会伤害自己。”(83) 最后,不同时期、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绩效上极为明显的反差,给中国提供了最为直观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使其深切认识到,自主性对于一国发展的成败而言,可谓生死攸关。从纵向来看,战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经历了由迅速到迟缓的转折:1950-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年均增速超过5%,甚至在发达国家之上;此后25年间,其整体表现却陷入持久的低谷。(84)并非巧合的是,1980年正是新自由主义从幕后走向台前的分水岭;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日益成为标准、正统的政策建议,被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推销甚至强行施加于发展中国家。拉詹在回顾近现代经济史之后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是沿着这条看似合理的标准途径而实现迅速发展的,相反,真实世界中的事件次序通常是先有增长、然后才有机制变革。(85)随着各种去规制化措施的推进,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起伏波动骤然加剧。(86)据统计,1970-2007年间共发生了124次系统性的银行危机。(87)而这些危机和波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比在发达国家更为严重。(88)阿姆斯登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内在联系,用她的话说,在美国金融业的兴起、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市场、第三世界经济增长转入颓势之间,存在着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89)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证是,拉美在开放前——亦即1960、1970年代的经济绩效甚至比开放后即1990年代更为出色。(90) 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区、国家之间巨大的绩效差异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增长乏力、成效不彰,而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体在1980年代之前和之后均有不俗表现。(91)埃托姆认为,妨碍非洲各国发展的首要原因是它们“对北方国家的从属地位、以自身利益为代价服从北方利益的行为”。非洲国家此前数十年间提出过许多发展方案,但绝大多数都被布雷顿森林机构否决。于是,1980年代共有34个非洲国家听从IMF与世行的建议,实施了结构调整,结果是其人均收入在1980-1988年间平均每年降低2.6%,就业水平更是下跌了16%。(92)与非洲相似,许多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未能取得预期成效,(93)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升反降:拉美大国的人均收入在1900年约为美国的14%,到21世纪初仅为13%;整个拉美地区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也从7%降至3%。(94)对此,张文木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拉美的发展呈现为“一种有和平但没有崛起的模式”,即“依附于西方资本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自主发展道路被弃置一旁,而国家命运操诸西方之手。(95)反观亚洲各国,它们并未对新自由主义言听计从,而是以切合实际的方式,将国家与市场这两种体系、两股力量结合起来推动发展,缩小了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96)在考察其经验时,罗德里克发现,绝大多数成功的国家都实行了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生产力至上型”举措;尽管产业政策时有失败,但不依靠产业政策就取得成功的例子却百不存一。(97) 二、中国当今的国际秩序观:寻求影响力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呈现为延续中的变化。其中,延续性主要体现在原则化信念层面: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性判断和评价,大致沿袭了此前时期的看法。变化则主要体现在因果信念层面:较之于此前“维护自主性”的主导策略,“寻求影响力”(98)在当今秩序观中的分量明显加重。与前一时期参与及融入世界经济时被动、保守、内向的方式不同,中国在重视自主性的同时,以更为主动、积极、外向的姿态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展开互动,借此实现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长远利益。 随着观念的转向,中国外交实践也出现了新动向与新趋势。中国发起和参与的一系列重大倡议及行动,包括亚投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应急储备安排、新开发银行等等,其实质是希望以这些带有区域公共产品性质的新机制和举措,激发、创造出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与中国共同分享的长期利益,从而培育出以“扩散型互惠”(99)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经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等新举措并不是推翻或试图推翻既有国际经济机制之后取而代之的产物,而是在原机制本来就欠缺存在感、未能发挥作用的地区(如中国周边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领域(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更加符合多边主义原则、更为关注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方式所构筑的新机制。与既有机制相比,这种新机制同样是基于规则的、开放的多边机制,只是它更专注于长久以来既有机制忽视或运转失灵的领域,试图以更具互惠性质的合作来创造共同利益,而不是分割既有利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它挑战甚至威胁到了既有机制,还不如说它填补了全球经济治理中既有机制无力或无意涵盖包容的空白地带。(100) (一)当今秩序观之体现 因应秩序观的转变,中国在国家大政方针、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措辞、表达上出现了某些意味深长的调整。这些变化与调整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首先是总体态度明显趋于积极有为。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101)中国领导人也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中国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102) 其次,较之前一时期的政策宣示和官方表态,中国在如何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方面,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表述。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作为中国未来发展重点依托的地位日益清晰:中国领导人在亚非会议、驻外使节会议等场合多次提出要“为发展中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03)“做实做深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104)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方式不断拓展深化,例如:以产能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其工业化进程;以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等方式,“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105) 与言辞、话语相比,中国在实践层面的积极主动显得更具说服力。亚投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等倡议和举措,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进程;恰恰相反,它们体现出某种内在一致的整体性思维,即通过这些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具有正外部性的机制与安排,或致力于创造、巩固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或致力于防范、化解共同面临的外部风险,将它们与中国的未来发展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某种互为助力、互为强援的良性格局。 在基欧汉看来,机制是一套具有内在关联的规则,而相关行为体往往寻求获得其中的影响力。(106)以此观之,中国的上述举措显然包含着寻求国际影响力的愿望或意图。不过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在以一种正面、积极、共促共享相关利益的方式寻求其影响力。用奥尔森的话说,这属于正向的“选择性激励”;(107)或者按照常璐璐、陈志敏的界定,这属于“吸引性经济权力”。(108)亚投行及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无疑会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109)阿米塔夫·阿查亚等学者曾经批评亚洲诸大国对区域及全球治理的贡献不足,(110)但亚投行的创建表明,中国正在以更具实质性的努力来促成亚洲的区域合作。 2014年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用于亚洲各国互联互通建设。(111)同年生效的清迈协议修订稿将多边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从1200亿美元提升至2400亿美元,显著强化了协议成员国应对国际收支困难或冲击的能力。(112)中国参与创建的应急储备安排则旨在为金砖国家在波动频繁、不确定性较高的国际金融市场中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自身信心。(113)这些安排无一例外,都有着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用意。很自然,它们正在“为中国赢得其他国家的友谊”。(114)与此同时,中国也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得以更好地“降低金融风险和对外经济依赖、保障战略资源储备”。(115)这正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提及的“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以“相互补台”的方式,促成“好戏连台”。(116)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立新”之举并不意味着颠覆性的“破旧”。中国虽然发起、参与了一系列新举措,但对待既有国际经济机制的态度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继续对后者抱有相当程度的认可,同时努力推动其实施必要改革。2009年,中国与IMF达成协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向基金组织购买约500亿美元的债券,以帮助后者拓宽融资来源、扩大融资规模。(117)为支持世行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中国向世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购入15亿美元的债券,以增进贸易融资对发展中国家的效用。(118)为支持拉美、非洲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美洲开发银行设立了20亿美元的联合融资基金,还与IFC共同设立了3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119)2013年10月,在美洲开发银行向牙买加提供的6000万美元贷款中,包含了中拉共同基金贡献的1100万美元贷款。(120)考虑到以上事实,那种认为亚投行等新机制意在削弱甚至取代既有国际金融机构的看法,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 (二)当今秩序观之成因 如前所述,中国当今的国际秩序观既是此前秩序观在原则化信念层面的延续,又表现出在因果信念层面的重要变化。其中,原则化信念的大致延续是相对易于理解的。许多学者在回顾中国此前的发展历程时都指出,这一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开放性的外部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联。(121)事实上,中国已经认识到,只要应对得当,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相当符合自身利益的。正因如此,在国际经济体系面临危机冲击、开放趋势受到保护主义威胁时,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一道,在各种场合维护和支持该体系的继续开放;中国虽然一如既往地呼吁并且要求全球治理机制尽快实施必要改革,但这显然不同于“推倒重来”。用张乃根的话说,中国作为既有秩序之“主要协定及组织的创始缔约国,享有一定的既得合法利益,因而不应全盘否定之”,而“应珍惜和维护既得的合法利益”。(122) 戈尔茨坦与基欧汉指出,原则化信念往往“经久不变”,而因果信念的变化则远为“频繁和迅速”。(123)中国秩序观的演变似乎为此提供了又一个例证:与原则化信念的大致稳定相比,中国秩序观在因果信念上的变化格外引人注目。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之所以发生,根源既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亦在于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治理机制的重大缺陷。有必要指出,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瓶颈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外部世界影响所致。尽管此前维护自主性的策略不可谓不成功,但新时期内外条件的变化,已使其成效逼近极限。这正是近年来中国转向“寻求影响力”策略的根本动因,惟其如此,中国才有可能为自身寻得下一阶段的发展空间。 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当前面临的发展瓶颈是促使其更加注重“寻求影响力”的关键动因。中国之所以提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举措,根本意图是希望以此来化解发展困境、突破发展屏障。进入21世纪后,中国领导层和民众对之前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有了愈发清晰的认知,转变发展模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与旧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相比,较少受到关注但却同样重要的是,旧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外部根源;或者说,国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约束,是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得不实行上述有着严重缺陷的增长模式的重要原因。 这种系统性的外部约束,源自于如下事实:中国自参与国际体系之初,就在和主要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非对称性及脆弱性较高的相互依赖状态。不仅如此,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深化,其脆弱性并未得到实质意义上的缓解,甚至有加剧之势。根据基欧汉的界定,当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产生对彼此都具有成本或代价的影响时,就存在相互依赖;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程度取决于一国在与他国互动中获得替代选择的能力及相应代价,或者说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必须承担的调整成本。(124)由此观之,中国对发达国家之市场、技术的依赖显然属于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范畴;因为一旦双方经济关系中断,身处国际分工体系高端、掌握先进的关键技术、进口市场规模庞大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替代选择明显比中国多,需要付出的调整代价则远比中国少。由于脆弱性相互依赖赋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以更多的权力资源,且后者往往会有意识地运用该资源为自身谋取更多利益,(125)因此中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就不可避免地处于相对弱势,在国际生产合作的利益分配中也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或者说对外依赖已经累积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在市场方面,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目前已超过60%;(126)在技术方面,外资企业掌握着中国高新技术部门90%以上的知识产权;在生产方面,外资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控制着80%以上的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生产”。(127)蓝普顿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面对的相互依赖风险尤其值得注意,具体包括对外贸、外汇收入、能源的高度依赖,以及对外国资本、重要原料和食品的依赖。(128)埃文斯也提醒道,不论贸易带来的收益有多高,过分依赖贸易会让一国在超乎自身管辖权的外部变化面前更易遭到冲击,结果是其在经济领域的行动能力严重受限。(129) 这种具有高度依赖性和脆弱性的增长模式从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显现出种种弊端,其在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引发的沉重代价日益为人们所察觉。王绍光观察到,随着90年代后期市场社会的出现,许多此前不在市场原则支配下的重要领域开始受到冲击和侵蚀,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安全受损等一系列问题。(130)即便是在经济领域,这一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难以弥补的负面效应,即“中国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并未在高速增长中实现应有的提升;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和对自主创新的忽视,导致中国经济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产业结构的低端化以及粗放增长的延续。(131)恰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言,过度依赖外资、外企、技术转让的后果,就是“有市场无安全”、“有产业无技术”。(132) 近期的多项研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种推断性的因果关联,即上述弊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依赖。桑德拉·霍尔珀林指出,以满足外部市场为主要目标的生产往往导致内部不平等加剧。(133)陶施也认为,尽管就短期而言,以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体可能经历快速增长,但这是以牺牲社会公平或平等为代价的。(134)鉴于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随着经济自由化的推进而持续扩大,我们有理由将此视为两位学者之观点的又一例证。另外,科尔迈耶的研究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报酬远低于其生产率所对应的水平,因此其出口产品包含的劳动投入在世界市场上并未得到应有体现,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南北国家的贸易行为提升了后者的国内人均收入水平。(135)这一结论对中国尤其具有启示意义,它意味着:对外部市场的大量出口固然为中国换来了巨额外汇收入和储备,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利贸易条件,以及外汇储备收益率的低下,这种交换实际上隐含着极为高昂的福利损失。 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缺陷同时也是中国在前一阶段发展中,因为受制于系统性约束而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借用一位学者的总结,中国之所以选择压低社会福利水平、资源价格、环境成本、低估币值等手段来追求贸易顺差,目的在于“创造和保持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136)我们想要补充的是,由于初始发展水平的低下和受到脆弱性依赖的制约,中国前一阶段追求的只能是在全球低端或中低端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 既然当前的发展瓶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约束所致,那么突破这一约束、降低脆弱性依赖程度,就成为摆脱瓶颈状态的题中应有之意。换言之,脆弱性依赖与发展瓶颈之间的关联,解释了中国为何要在新时期寻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不过,仍然有待解释的是:中国寻求影响力的具体方式为何是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新机制或举措,而且明显把重心放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而不是其他方式,比如单纯依靠既有机制,或者将重心放在发达国家?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对其他几点因素进行考察,那就是国际经济机制的基本状况,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 首先,既有国际经济机制的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将希望寄托于该机制的自我改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治理规范的进步、国际金融机构的实质性改革一度寄予厚望,然而时过境迁,这一美好愿景已然落空。从规范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缺陷虽然暴露无遗且广受批判,但能够取而代之、更具包容性、更有助于发展的主导观念,尚未在国际社会中形成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在政策方面的体现,华盛顿共识效果不彰基本已成定论,但接替它的究竟是什么,却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37)有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作为政策范式的地位可能比人们寻常所见的更为稳固。(138)危机后数年的情形似乎也表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139)这既反映出美国权力尚未出现实质性衰退,也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复原能力不容低估。(140) 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关于发展理念的分歧仍然一如既往。虽然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机制之间的观点差异自1990年代末以来有所弥合,但双方在对待发展中国家或发展问题上的态度依旧呈现出鲜明对比:联合国机制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制约,布雷顿森林机制则继续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取决于自身。(141)由于布雷顿森林机制的强势地位,主导发展议题的国际规范更多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减贫”,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增长”。(142)在千年发展目标之中,无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均没有得到提及,这无疑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失所望。(143) 从机构层面来看,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在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能力和意愿上都存在欠缺,而旨在解决相关问题的机构改革又因为主导国家的掣肘而难以实现。受此影响,一些较为强大的行为体纷纷自寻出路或相互扶持,以便在主要国际机制无法正常履行相应职能或实施应对方案的情况下,确保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某些议题领域能够继续实现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中国发起的亚投行亦可被视为上述情形的又一表现。 以世行为例,与全球范围内对大规模长期贷款的需求相比——它们主要来自迫切需要发展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但缺乏可用资金的发展中国家,世行的实际贷款发放远远不敷所需。韦德认为,世行及类似组织提供此类贷款的规模“应在当前水准的十倍甚至以上”。(144)曾任世行行长的沃尔芬森也承认,“与主要商业银行集团的资产相比,世界银行2750亿美元资产的确相形见绌。世行的规模淡化了它的重要性。”(145)与此同时,世行的治理结构改革却相当迟缓,(146)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定规则的发达国家没有理由自我约束”,而“受这些规则管束的借款国则几乎无力改变现状”。(147) 再以IMF为例,伍茨指出,基金组织不仅面临着资金不足的现实威胁,还面临着地位边缘化、正当性缺损的双重危机。(148)其采取的改革措施并未取得显著成效,继续改革的空间却极为有限。(149)之所以形成这种僵持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为保持自身在既有机制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支持新兴国家参与非正式机制,另一方面却冷漠对待正式机制的改革。(150) 其次,中国与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及利益关系,决定了后者非但不可能主动采取措施、帮助中国降低脆弱性依赖,反而有相当强的动机坐视甚至推动其进一步加剧。如前所述,中国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国际分工中相对地位的低下。就某种意义来说,降低脆弱性依赖与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其实是一回事。中国近年来之所以愈发重视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其根本原因盖出于此。(151)那么,这一意图和举动对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国家——美国有何影响?或者说,这是美国所乐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我们是否认同依附论视角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之说,(152)一个基本事实应该是无可否认的,即占据分工体系高端甚至顶端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往往会得到份额远高于低端国家的利益分配。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的矛盾(153)就有了深刻的经济内涵。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虽然在近十多年间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若以量值来计算和对比,中国2007年的量值尚不及美国1980年代的水平。(154)如果中国不能从全球价值链条的中低端位置向上跃升、摆脱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之依赖,那么美国等发达国家无疑将从中受益,而中国将被锁定在为主导国家输送利润的地位,无从维护自身利益。(155)如今,中国显然已决心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156)改变此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两头受制”的经贸模式,这势必意味着减少主导国家原先占有的超额利润。(157)对蒙代尔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判断稍加改动,即可很好地用来描述主导国的立场:处于分工体系顶端的国家总是不愿看到低端国家的地位攀升,“因为这会降低它自身的垄断力量”。(158)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态度,以及对华战略的近期调整也证实了上述判断。美国主导下的经济自由化使第三世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能力”遭到严重削弱。(159)产业政策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广为实施、行之有效的工具,如今被国际组织界定为不合规范,无法继续使用。(160)凡此种种的基本意图,与其说是为了维护多边主义,还不如说是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使之不至于威胁到发达国家在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的优势。(161)美国在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之后“刻意冷落多边,移情双边”之举,(162)以及在国际投资领域通过双边谈判以“各个击破”发展中国家的策略,(163)都表明美国在对待多边主义时惯于采用更注重自身短期利益的机会主义做法。就近几年中美关系的走向而言,有学者注意到,美国对华战略中“遏制的分量已有加重之趋势”,“两国战略竞争态势已然形成”。(164)作为其表现,美国“开始有系统地采取防范性的、对抗性的举措”,(165)包括动用经济或非经济手段,试图评判、进而影响中国的行为,使之更合乎美国的利益。(166)从本文的视角来看,这种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对中国试图提升自身国际分工地位的忌惮与提防。 再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潜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决定了中国将这些国家作为相互倚重的合作对象,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意在长远的举措支持其发展,同时实现降低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脆弱性的目标。这一判断包含了两重含义:其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的深化,具备了相对充分的现实条件;其二,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乃至下一阶段最为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合作发力点。 就第一重含义来说,在排除了既有国际经济机制和世界经济主导国作为降低脆弱性之倚重对象的可能性之后,剩余的选择已屈指可数。而赋予该选择以现实性的,则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渐增长的相互需求。中国并不是唯一需要并且试图降低对发达国家过高依赖度的国家,事实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很自然,加强南方国家的彼此合作就成为一条可能的脱困途径。一方面,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由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167)的关键时期,在设法降低对发达国家市场、技术依赖性的同时,迫切需要新的市场、资源与投资场所作为经济发展在地缘意义上的纵深空间和腾挪余地。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亚、西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正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需要支持性的外部环境和市场。(168)用林毅夫的话说,中国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中国通过结构调整让出一些产业的发展空间,以及在投资和技术上提供帮助。(169)较之于发达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更为接近,在发展方式、自主权等方面的观念有更多的共同之处,(170)双方合作中的非对称性及失衡风险也因而相对较小。 正是这种相互需要和相对平衡的依赖关系,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利益基础。实际上,一些重要的变化趋势已经日益清晰。坦顿观察到,发展中国家正在降低对西方市场的依赖。(171)杨霄、张清敏在考察了中国近二十年对外经贸关系的整体格局之后发现,周边国家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在此期间增长了一倍以上,且势头至今不减;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在进入21世纪之后也迅速增长,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自2002年开始出现缓慢下降。(172) 就第二重含义来说,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均将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作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重点,这绝非偶然。一方面,该部门每1美元的投资会带动其他部门3—4美元的新增投资,每10亿美元的投资可以为亚洲创造1.8万个就业机会;(173)也就是说,其“进步的结果会作为外部经济而为其他行业所得到”。(174)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受困于自有资金不足,而发达国家对前者的投资出于风险规避等因素,一直集中在其他领域如能源、制造业等,(175)使得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竞争力的主要瓶颈”。(176)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为缺少增值渠道的国内资本寻求回报率更高的投资场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资本“走出去”已是大势所趋。据世行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投资活动将位居全球之首,占全球总投资的比重将达到30%。(177)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恰恰也是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领域之一。以高铁为例,有研究显示,其单位成本仅相当于、甚至低于其他国家的三分之二。(178)结合相关实际情况来看,基础设施可谓各国之间利益汇聚最为集中的领域。 亚投行、“一带一路”的启动,揭开了21世纪中国对外经济战略调整的序幕。如前文所述,这种调整反映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其实施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能否在本世纪中叶如愿跻身中等发达国家之列,因而与中国之国运息息相关。详细剖析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前景及其决定因素,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我们可以抛砖引玉,就此作出尝试性的简短讨论,为将来的研究探寻可能的方向。 我们认为,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促成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之间持久、稳定、良性的合作关系?用理论术语来说,即如何培育和实现“扩散型互惠”?我们已经阐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互有所需、互有所求,这当然意味着利益交换的潜在空间,各方合作由此具备了可能性。然而,如果旨在实现自我维系的机制化合作,也就是持久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那么这还不够。基欧汉曾经告诫道:“即使在存在互补利益的情况下,要克服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问题也是极为困难的”,“利益的冲突从来没有消失,即使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79)因此,关键在于各国是否会在互动中“遵循那些受到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这正是扩散型互惠的核心要义,(180)它使相关各方对彼此行动的模式、范围有着相对明确和稳定的预期,在发生争执甚至冲突时,也愿意在相关行为准则的指引下协商并解决争端。由于这些预期“使跨部门、跨时期的权衡及利益交换成为可能”,因此其形成和巩固就为机制化合作提供了长久而有效的保障。(181) 对中国而言,上述分析可以给出三点重要的启示。首先,必须有一定的耐心。所谓耐心,既是指机制形成通常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是指在权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时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克制。二战后美国促成欧洲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机制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史实来看,尽管布雷顿森林机构在1940年代中期就已创建,但欧洲直到1958年才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国际货币机制由此得以正常运转。在此之前的十余年间,美国先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欧洲支付同盟为欧洲提供帮助,使其逐渐认同和接受美国主导下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182)美国最终如愿以偿的一个关键,就是它没有在欧洲尚不具备相应能力和决心的时候“坚持在短期内实行平等的交换”;倘若它固守狭隘意义上、严格对等、即期执行的互惠要求,那么后来的双赢局面就不可能出现。(183)应该说,这一经验对亚投行、“一带一路”的运作与推进也有着丰富的参考价值。 其次,应当明确“义”的内涵。关于“义利并举、以义为先”,通常的理解或许是,率先投入资源以提供准公共产品,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短期利益以实现长远合作与共同收益。这种理解虽然言之成理,但没有触及一个尚待明确的关键问题,即“何者为义”。如果“义利并举、以义为先”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指导思想,那么从表述来看,“义”明显地具有规范含义,它隐含地要求获“利”必须具备正当性。然而,这种主导性规范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内容?官方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正面回答。 我们认为,“义”的实质,应该就是扩散型互惠中得到各方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仍以战后美国的做法为例,它在与欧洲互动的过程中遵循的“义”,其实是双方各自根本意愿的折中:美国的目标是让欧洲融入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欧洲的目标则是在融入之前必须恢复自身的生产水平和竞争能力。唯有折中之后的“义”,才能得到各方的共同认可,从而具备正当性。这也就意味着,亚投行、“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主导性规范,必须是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密切协商、相互谅解、彼此折中之后形成的,否则其生命力和影响力就难以得到保障。举例言之,如果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贸易投资自由化,而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加快实现工业化,那么合作中的“义”不能也不应该是简单的、一刀切的“让利”,而应该是努力让自由化与工业化彼此促进、并行不悖的某种折中形式;后者既能为中国提供外部市场与资源,也能为周边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等工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力,使双方都可获得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总之,没有“义”赋予的正当性,寻求影响力就会沦为一厢情愿;同时,没有“利”作为基础,一味让步换取的“影响力”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究难以为继。 最后,应当谨记“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在相对平衡状态下的深化,而不是单方向地加深他国对中国的依赖。其实,这也是前述两点在操作层面的必然结论。长期以来,对世界经济主导国家的脆弱性依赖使中国备感忧虑。同理,如果其他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看到的只是自身对后者依赖度的增加,那么“一带一路”的前景势必因此蒙上阴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曾清楚地表示,安于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料的身份不可能为该国带来期待的发展。(184)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指出,海合会国家希望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中国投资与产品的接受者”。(185)东盟各国也在不同程度上“担心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186)因此,“一带一路”取得进展与成功的可行路径,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中国的“一枝独秀”,而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国际经济地位的集体跃升。这或许才是“命运共同体”(187)的真意所在。 《外交评论》评审专家、黄超博士、何曜博士提出了中肯且有益的建议,笔者在此深表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②Robert Wihtol,"Whither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Finance?" ADBI Working Paper,No.491,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14. ③[英]帕乌拉·斯帕奇:《亚投行威胁全球治理体系》,黄杨荔编译,《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第150、151页。 ④"Why China Is Creating a New ‘World Bank' for Asia",The Economist,November 11,2014. ⑤"Beijing's Challenge to the World of Bretton Woods",Financial Times,October 30,2014. ⑥孙韵:《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挑战》,郭楚编译,《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第151页。 ⑦张运成:《审视亚投行的三个“坐标”》,《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第3页。 ⑧刘军红:《美日旁观亚投行折射其对世界陈腐的认知》,《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第8—9页;贾银华:《亚投行建立项目导向型风险管理体系问题探析》,《理论月刊》,2015年第8期,第116页。 ⑨以亚投行为例,截至2016年1月10日,在“中国知网”以“亚投行”搜索篇名,得到的相关论文数量如下:2014年,19篇;2015年,332篇;2016年,1篇。这350多篇论文中,发表于核心期刊或CSSCI刊物的有53篇。再以“一带一路”为例,根据冯维江的统计,既有研究中“涉及整体战略的研究仅占19%,理论研究只有7%,并且其中相当部分是从空间经济学或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展开,从国内国际互动视角开展的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分析较少”。参见冯维江:《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77页。 ⑩[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1)Satoshi Amako,"China's Diplomatic Philosophy and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Vol.3,No.2,2014,pp.20-21. (12)[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13页。 (13)[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14)An Chen,The Voice from China:An Chen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Springer-Verlag Press,2013,p.168. (15)[德]E.-U.彼德斯曼:《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功能与宪法问题》,何志鹏、孙璐、王彦志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16)[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载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8、10页。 (17)同上书,第9页。 (18)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第7页。 (19)[美]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倪颖、曹槟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20)Xi Chen,"China's Foreign Policy Dynamic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n Yannis A.Stivachtis,ed,International Order in a Globalizing World,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p.46. (21)Rosemary Foot,"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2,Issue 1,2006,p.93. (22)有学者指出,“对任何国家来说,官方文件从来都不是完全可信的分析材料。”参见Stuart Harns,"China and the Pursuit of State Interests in a Globalising World",Pacific Review,Vol.13,No.1,2001,p.16。 (23)莉莎·马丁指出:“当今世界的许多国际经济往来都是通过国际经济机制(IEIs)得以组织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已经高度机制化,而国际经济机构在财富的国际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参见Lisa L.Martin,"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in R.A.W.Rhodes,Sarah A.Binder and Bert A.Rock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654。 (24)斯蒂夫·奥尔森等认为,“国际组织并不是当今盛行的世界经济秩序之创造者,而是该秩序的体现者。”Stephen Olson and Clyde Prestowitz,The Evolving Role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he 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2011,p.14. (25)本文中“自主性”一词,沿用了本杰明·科恩所作的相关界定,即“行动能力”。科恩指出:“如果一国能够自主行使政策——在政策形成与实施方面不受外在压力影响,根据自身意志采取行动”,那么它就“拥有权力”。“在这一意义上,权力并不意味着影响他者,而在于不允许他者影响自身。”他将权力的这一层含义归纳为“自主性”。Benjamin J.Cohen,"The Ma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in David 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32. (26)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0,pp.17,130-131. (27)Stuart Harris,"China and the Pursuit of State Interests in a Globalising World",p.23. (28)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pp.131,127. (29)Amitai Etzioni,"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7,No.3,2011,p.551. (30)[美]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41页。 (31)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p.109. (32)[澳]王赓武:《中国和国际秩序——来自历史视角的观察》,《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28页。 (33)蒲晓宇:《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26页。 (34)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pp.136,132. (35)[德]德克·梅斯纳、[英]约翰·汉弗莱:《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赵景芳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第14页。 (36)Jonathan Glennie and Nora Hassanaien,"Dependency Theory-Is It All Over Now?" The Guardian,March 1.2012. (37)Gerard Strange,"China's Post-Listian Rise:Beyond Radical Globalisation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liberal Hegemony",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6,Issue 5,2011,p.556. (38)Dani Rodrik:《中国的出口有何独到之处?》,田慧芳译,《世界经济》,2006年第3期,第20—30页。 (39)《俞可平对话福山: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 (40)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p.32. (41)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1980年代许多遭受债务困扰的发展中国家都被IMF要求实施一系列政策变革,如减少支出、削减赤字等等,否则就无望得到亟需的贷款。IMF的限制性条件因此在发展中世界引发了极大争议或非议。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p.31. (42)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p.64. (43)Ibid.,pp.121-122. (44)有研究指出,1980年三笔贷款的总和不过16亿美元左右。社科院世经政所课题组:《综合国力的象征——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国际贸易》,2001年第4期,第21页。 (4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7年12月31日,http://www.pbc.gov.cn/goujisi/144449/144490/144541/2871988/index.html。 (46)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p.134. (47)World Bank,China and the World Bank:A Partnership for Innovation,World Bank,2007,p.xiii. (48)社科院世经政所课题组:《综合国力的象征——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第22页。 (49)World Bank,China and the World Bank:A Partnership for Innovation,p.xiii (50)《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成果展:结语》,2010年9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http://gjs.mof.gov.cn/zhuantilanmu/shihang30nian/jieyu/201009/t20100919_339827.html。 (51)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pp.121,18. (52)[德]德克·梅斯纳、[英]约翰·汉弗莱:《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第12页。 (53)[美]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伊丽莎白·埃克诺米:《引论:中国参与世界》,载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闫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54)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回顾与展望》,《百年潮》,2012年第1期,第54页。 (55)谭崇台主编,马颖、叶初升副主编:《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5—476页。 (56)Dani Rodrik:《中国的出口有何独到之处?》,第21—22页。 (57)[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谭力文、张卫东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95页。 (58)Dani Rodrik,"Making Room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0,No.2,2010,p.91. (59)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pp.67-69. (60)Ibid.,p.45. (61)Stuart Harris,"China and the Pursuit of State Interests in a Globalising World",p.27. (62)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00页。 (63)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79-415. (64)参见孙伊然:《发展中国家对抗内嵌的自由主义?——以联合国发展议程为例》,《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102—124页。 (65)Hans Abrahamsson,Understanding World Order and Structural Change:Poverty,Conflict,and the Global Arena,Palgrave Macmillan,2003,p.39. (66)Robert Wade,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468. (67)尽管并无坚实可靠的证据表明开放与增长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参见Francisco Rodríguez,"Openness and Growth:What Have We Learned?" United Nations,DESA Working Paper,No.51,ST/ESA/2007/DWP/51,August 2007。 (68)Alain Noel and Jean-Philippe Thérien,Left and Right in Glob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59-160. (69)Luiz Carlos and Bresser Pereira,Globalization and Competition:Why Some Emergent Countries Succeed while Others Fall Behi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2-3. (70)陈安:《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第10页。 (71)张文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第72页。 (72)Gustav Ranis,James Raymond Vreeland and Stephen Kosack,eds.,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The Impact of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Routledge,2006,"Introduction",pp.1-2. (73)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随后证实,上述批评并未夸大其词。参见Abdullahi Osman EI-Tom,Mugging the Poor: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nd the Pursuit of African Development,Institute for African Alternatives,1994,p.12。 (74)Eric Helleiner,Forgotten Foundations of Bretton Woods: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Postwar Ord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p.276. (75)周艾琳:《亚投行将重塑全球金融治理模式》,《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6月25日。 (76)朱云汉:《中国人与21世纪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23页。 (77)Graham Bird,"The IMF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Policy Op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Issue 3,1996,p.487. (78)Bernard Hoekman,"Doha,Development and Discrimination",Pacific Economic Review,Vol.12,No.3,2007,p.267. (79)Alain Noel and Jean-Philippe Thérien,Left and Right in Global Politics,p.160. (80)William I.Robins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ization: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State",Theory and Society,Vol.30,No.2,2001,p.186. (81)Nicholas Bayne,"What Governments Want fro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How They Get I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2,No.3,1997,p.366. (82)这是撒切尔夫人的名言:There is no alternative。 (83)Henry Kissinger,"UNCTAD IV:Expanding Cooperation for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LXXIV,No.1927,May 31,1976,pp.658,671. (84)Alice H.Amsden,Escape from Empire:The Developing World's Journey through Heaven and Hell,The MIT Press,2007,pp.5,2. (85)[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刘念等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64—65页。 (86)Richard Sandbrook,"Polanyi and Post-neoliber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Dilemmas of Re-embedding the Economy",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4,2011,p.422. (87)Luc Laeven and Fabian Valencis,"Systemic Banking Crises:A New Database",IMF Working Paper,WP/08/224,November 2008,p.5. (88)Richard Sandbrook,"Polanyi and Post-neoliber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Dilemmas of Re-embedding the Economy",p.416. (89)Alice H.Amsden,Escape from Empire:The Developing Worlds Journey through Heaven and Hell,p.13. (90)Ricardo Hausmann and Dani Rodrik,"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72,No.2,2003,p.631. (91)Alice H.Amsden,Escape from Empire:The Developing Worlds Journey through Heaven and Hell,p.14. (92)Abdullahi Osman EI-Tom,Mugging the Poor: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nd the Pursuit of African Development,pp 1,6,11. (93)陈安:《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第11页。 (94)韩琦:《辩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第80页。 (95)张文木:《大国崛起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62页。 (96)Alice H.Amsden,Escape from Empire:The Developing Worlds Journey through Heaven and Hell,p.14. (97)Dani Rodrik,"Making Room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p.90. (98)本文中“影响力”一词,沿用了戴维·安德鲁斯、本杰明·科恩的界定和阐释。安德鲁斯认为,“权力……对应着影响力”,“它指的是某种关系”。参见David M.Andrews,"Monetary Power and Monetary Statecraft",in David 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p.16。科恩进一步指出,如果一国能够有效地对另一行为体“施加影响或迫使其服从”,那么它就拥有“影响力”。影响力可以被理解为权力的外在维度,而自主性则是权力的内在维度。参见Benjamin J.Cohen,"The Ma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p.32。 (99)基欧汉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互惠,即“特定型互惠”(specific reciprocity)与“扩散型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前者涉及不同行为体之间对等的价值交换,而后者并不要求严格的“对等”。参见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Issue 1,1986,p.4。 (100)我们在此表达的观点,与基欧汉提出的“竞争性多边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基欧汉看来,新制度是相关行为体出于对旧制度不满而创建的、对旧制度的“替代性选择”。而我们更希望强调的是,旧制度本来就没有覆盖世界政治经济中相当广阔的领域,或者至少可以说,旧制度在这些领域徒有其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竞争的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20—25页。 (10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02)《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2014年7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74255.shtml。 (103)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 (104)吴绮敏:《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 (105)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 (106)[美]罗伯特·基欧汉:《部分全球化世界的治理》,载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1页。 (107)[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42页。 (108)常璐璐、陈志敏:《吸引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1—16页。 (109)Makmun Syadullah,"Prospects of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Journal of Social and Development Sciences,Vol.5,No.3,2014,pp.155-167; Yu Hong,"China's Eagerness to Export Its High-speed Rail Expertise to ASEAN Members",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2,No.2,2014. (110)Amitav Acharya,"Can Asia Lead? Power Ambi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7,No.4,2011,pp.851-869. (111)张朔:《习近平就“一带一路”提建议,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中国新闻网,2014年11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1-08/6763049.shtml。 (112)《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修订稿生效》,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4年7月18日,http://www.pbc.gov.cn/goujisi/144449/144464/2882251/index.html。 (11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谈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3年8月27日,http://www.fmpre.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69954.shtml。 (114)"Development Finance Helps China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American Allies",The Economist,March 21,2015. (115)俞可平:《全球治理的趋势及我国的战略选择》,《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第10页。 (116)王毅:《共谋和平发展,共守法治正义——在第6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2014年9月27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28/c_1112666664.htm。 (117)《中国同意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的IMF债券》,新华网,2009年9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03/content_11988426.htm。 (118)郑晓松:《探索自主发展道路,创新全球发展理念》,《中国财政》,2010年第18期,第25—26页。 (119)《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3年10月12日,http://www.pbc.gov.cn/hanglingdao/128697/128728/128832/817147/index.html。 (120)《中国投资推动拉美经济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4月1日。 (121)王正毅:《中国崛起:世界体系发展的终结还是延续?》,《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3—20页;Ming Wan,The China Model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Comparison,Impact and Interaction,Routledge,2014; Dani Rodrik,《中国的出口有何独到之处?》。 (122)张乃根:《试论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演变与中国的应对》,《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第186、191页。 (123)[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第10页。 (124)[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3页。 (125)[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第16、11页。 (126)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24页。 (127)[俄]M.Л.季塔连科:《前进中的中国——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及展望21世纪中国发展前景》,李瑞琴译,《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31页。 (128)[美]戴维·蓝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03—205页。 (129)[美]彼得·埃文斯:《跨国联系与国家的经济角色——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家的分析》,载彼得·埃文斯等编著:《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66页。 (130)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31页;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8页。 (131)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第92页。 (132)齐兰:《垄断资本全球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89、92页。 (133)Sandra Halperin,Re-Envisioning Global Development:A Horizontal Perspective,Routledge,2013,p.222. (134)阿诺·陶施:《全球化与发展:经典“依赖”理论与当今世界的关联》,项龙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2年第1期,第78页。 (135)Christopher Kollmeyer,"Consequences of North-South Trade for Affluent Countries:A New Application of Unequal Exchange Theory",Review,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5,2009,pp.803-826. (136)吴澄秋:《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路向何方?——基于全球化时代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第15页。 (137)Dani Rodrik,"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A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4,No.4,2006,pp.973-987. (138)Sarah Babb,"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Transnational Policy Paradigm:Its Origins,Trajectory and Likely Successo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0,No.2,2012,pp.268-297. (139)Gareth Dale,"Double Movements and Pendular Forces:Polanyian Perspectives on the Neoliberal Age",Current Sociology,Vol.60,No.1,2012,pp.3-27;吴澄秋:《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治理理念结构》,《国际论坛》,2013年第1期,第54—59页。 (140)Daniel W.Drezner,"The System Worked: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World Politics,Vol.66,Issue 1,2014,pp.123-164. (141)Alain Noёl and Jean-Philippe Thérien,Left and Right in Global Politics,pp.181-182,193-194. (142)Sakiko Fukuda-Parr and David Hulme,"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the ‘End of Poverty':Understand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Global Governance: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7,No.1,2011,pp.17-36; Daniel E.Esser and Benjamin J.Williams,"Algorithmic and Visual Analysis of Agencies' Annual Reports and Occasional White Papers,1978—2010",Journal of Social Policy,Vol.43,Issue 1,2014,pp.173-200. (143)[美]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世界银行家: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传》,李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144)Robert H.Wade,"Emerging World Order? From Multipolarity to Multilateralism in the G20,the World Bank,and the IMF",Politics & Society,Vol.39,No.3,2011,p.370. (145)[美]詹姆斯·沃尔芬森:《我的世行之路:跨越贫富两界的跌宕人生》,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146)[英]奈瑞·伍茨:《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多边制度》,曲博译,《外交评论》,2008年第6期,第94页。 (147)[美]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世界银行家: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传》,第312页。 (148)[英]奈瑞·伍茨:《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多边制度》,第84页。 (149)Ngaire Woods,"Global Governanc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A New Multilateralism or the Last Gasp of the Great Powers?" Global Policy,Vol.1,Issue 1,2010,pp.51-63. (150)Sevasti-Eleni Vezirgiannidou,"The United States and Rising Powers in a Post-hegemonic Global Order",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9,No.3,2013,pp.646-647. (151)例如,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开篇就提到“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参见《中国制造202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 (152)[巴西]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恩佐·法勒托:《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单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153)蔡拓将其称为“中国走向崛起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参见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24页。 (154)杨高举、黄先海:《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37页。 (155)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第110页。 (156)张幼文:《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新主题与总战略》,《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9期,第55页。 (157)逯兆乾:《美国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第17页。 (158)[美]罗伯特·A·蒙代尔、保罗·J.扎克编:《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张明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159)Ray Kiely,"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Liberalisation? Neoliberalism and the Myth of Global Converge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3,No.3,2007,p.434. (160)Robert Hunter Wade,"What Strategies Are Viab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Shrinking of ‘Development Spa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0,No.4,2003,pp.621-644. (161)Yakub Halabi,"The Expan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o the Third World:Altruism,Realism,or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Issue 1,2004,p.45. (162)陈安:《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91页。 (163)陈安、杨帆:《南南联合自强:年届“知命”,路在何方——国际经济秩序破旧立新的中国之声》,《国际经济法学刊》,2014年第3期,第19页。 (164)门洪华:《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95、200页。 (165)牛新春:《中美关系:意识形态的碰撞与竞争》,《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79页。 (166)顾国平:《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国际论坛》,2013年第1期,第29—35页。 (167)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3页。 (168)[巴西]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恩佐·法勒托:《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第25—26页。 (169)《林毅夫:与中国的合作是世行在全球最成功的合作案例》,新华网,2010年9月13日,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cw30/cfwzc/201009/t20100913_338803.html。 (170)Gideon Rachman,"America Is Losing the Free World",Financial Times,January 4,2010; Ian Clark,""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Succession of Hegemon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7,No.1,2011,p.26. (171)Yash Tandon,Development and Globalisation:Daring to Think Differently,Pambazuka Press,2009,p.29. (172)杨霄、张清敏:《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与外交布局》,《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1期,第29—30页。 (173)Makmun Syadullah,"Prospects of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pp.155-156. (174)[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5页。 (175)陈安、杨帆:《南南联合自强:年届“知命”,路在何方——国际经济秩序破旧立新的中国之声》,第24—25页。 (176)OECD,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3:Industrial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rld,OECD Publishing,2013,p.18. (177)World Bank,Capital for the Future: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2013,p.5. (178)Gerald Ollivier,Jitendra Sondhi and Nanyan Zhou,"High-Speed Railways in China:A Look at Construction Costs",China Transport Topics,No.9,World Bank Office,2014,p.8. (179)[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2、54页。 (180)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4. (181)John Gerard 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 3,1992,p.594. (182)[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75—182页。 (183)同上书,第177—178页。 (184)Yusuf Kanli,"Nazarbayev's Eurasia Union Vision",Hurriyet Daily News,February 27,2005,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default.aspx?pageid=438&n=nazarbayev8217s-eurasia-union-vision-2005-02-27. (185)Abdel Aziz Aluwaisheg,"China,GCC Set to Walk the New ‘Silk Road'",February 3,2014,http://www.arabnews.com/news/518966. (186)陈琪、周舟、唐棠:《东盟对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顾虑》,《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81页。 (1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标签:国际经济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外部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亚投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