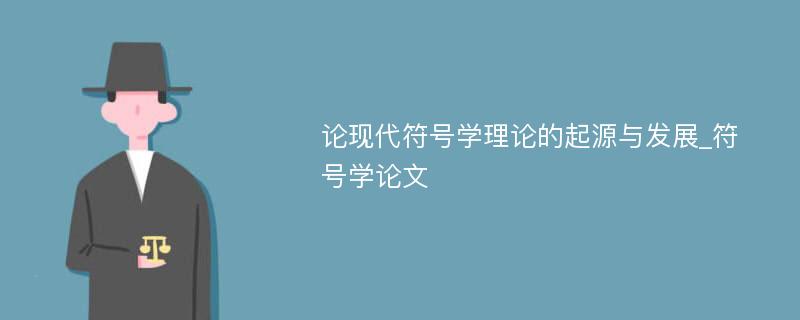
现代符号学理论源流浅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符号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鲍亨斯基、莫里斯:逻辑学家心目中的符号学
皮尔斯传统的符号学,由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进一步阐发,构成了一种基于逻辑学的符号学理论。这种符号学,瑞士的逻辑学家鲍亨斯基是这样描述的:
“符号学的主要观点——它也是符号学分门别类的基础——可以简述如下。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些什么的时候,他所用的每个词都涉及三个不同的对象:
(a)首先,这个词属于某个语言, 这表明它同该语言中其它词处于某种关系之中。例如,它可以处于句中的两个词之间,或处于句首,等等。这些关系叫做句法关系,它们把词与词连接起来。
(b)其次, 这个人所说的话具有某个意义:他的那些词都有所意谓,它们要向别人传递某些内容。这样,除了句法关系之外,我们还得研究另一种关系,即那个词同它所要意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叫做语义关系。
(c)最后,这个词是由一个特定的人向着另一个特定的人说的, 因此,存在着第三种关系,即该词与使用它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叫作语用关系。”(注: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上述引文表明,鲍亨斯基所指的符号学,就是符号学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划分。鲍亨斯基对符号学主要观点的简述,尽管对符号的界定留下相当广阔的空间,但符号学在他那里仅仅只是形式语言的符号学。他对于符号学的分类,正如他所言,主要应归功于另一位学者,美国的逻辑学家,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查尔士·莫里斯。
考察莫里斯的符号学可以发现,莫里斯本世纪30年代的著作《符号理论的基础》,是基于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卡尔纳普的论述。他对符号学的划分几乎等同于卡尔纳普在其《语义学引论》中对符号学的描述。这就使我们看到:具有分析哲学背景的逻辑学家,大都把符号学看作统一逻辑学三大领域: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一种元语言理论。符号学不过是对于人工语言,至多还包括自然语言,进行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综合性理论框架而已。
然而,当我们研究莫里斯的另一本符号学专著《符号、语言和行为》(1946年)时发现,莫里斯的符号学远远超越了30年代那本著作的元逻辑理论的范围,他在该书中认为:
我们需要对上面提到的那个关于符号学领域的区分作出某些改动:必须去掉符号学只研究语言这个限制,符号学应该对科学语言以外的那些符号结构的研究成为可能,在语义学中必须研究不同于指谓的意谓方式的那些其它的意谓方式,这就进而要求在语用学的表述上作出某些修改。
这样,尽管还可以把符号学作上述三分,语用学的研究领域则扩展到符号的起源、应用和效果。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划分只是符号学研究的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罢了。
莫里斯进而从另一个角度来对符号学予以划分,即区分为纯粹的符号学和描述的符号学。一般而言,符号学中讨论数学和逻辑学的部分可以看作纯粹符号学的范围,而讨论这两个领域之外的部分则大体属于描述符号学的范围。
首先,符号学是所有语言学研究的基础。符号学为语言学提供元语言,语言学家可以在符号学术语的基础上定义出语言学的术语。这就使人们能够用一种统一的术语来描述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从而使一种科学的比较语言学的建立成为可能。
其次,符号学在促成科学统一的两个方面都产生作用。他提供一种丰富的语言来讨论人类科学中的每一个领域;又提供一种工具来分析那些表达各种科学的语言之间的关系。符号学是一门几乎沟通人类所有科学的科学。
“因为,我们的讨论已经把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孤立地研究的那些材料统一起来了,从而我们的讨论表明,至少在原则上表明,在关于行为的普遍理论的共同术语下这些材料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注:莫理斯《符号、语言和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9页。)
20世纪的人文科学研究的趋势表明,人文科学研究在19世纪末叶,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开始了其语言论转向的历程。这一转向不仅仅是英美哲学的特点,而且是世界性的人文科学研究的特点。莫里斯雄心勃勃的符号学研究可说是这一语言论转向的产物之一。
以罗素、卡尔纳普等学者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学派所实行的语言论转向,是不断地巩固、加强和扩大语言的逻辑功能,并试图用人工语言的方法来刻划和规范我们的自然语言。因此,分析哲学家的语言分析所要求的是:概念的准确性,表述的明晰性和意义的可证实性。一切科学都以逻辑和数学为范式。分析哲学家意欲构建的符号学自然也就具有这一特征。
在西方学术界英、美的另一端,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学者,也或先或后把目光转向了语言,转向了符号学。但和英美分析哲学家语言论转向不同的是,近代欧陆人文科学对于语言、符号的关注,则是竭力地弱化和消除语言的逻辑功能,阐释和还原语词和符号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力图把语言符号从理性法则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领略欧洲学者如何建构一门研究符号的科学的时候,令人惊奇的是,比莫里斯雄心勃勃的符号学构架还要早20年,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早在20年代就已经出版了蔚为大观的三卷本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莫里斯的符号学方案是显然受到卡西尔影响的,《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的文献索引列出了卡西尔的九部著作,卡西尔的符号理论被誉为符号理论统治时代的开始。
二、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
卡西尔在其《人论》的哲学著作中,一反对于人的亚里士多德定义而主张:“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在卡西尔那里,符号超越了理性的地位成了哲学首先关注的对象。
人首先应该是符号的动物而不是理性的动物,这是因为人类知识的普遍性根源并不全是理性。至少在神话领域,在艺术领域,在人文科学领域,在丰富多采的人类行为领域,理性并不能解释上述所有领域的知识。理性逻各斯在人类的这些非理性领域面前往往束手无策。按照卡西尔的说法,这些领域的研究,“在哲学中仿佛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
在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就有理性的含义。这是自启蒙时代以来激励无数学人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元动力,西方学者所谓“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要我们到逻各斯那里去寻找知识的本原。
卡西尔确实是在逻各斯那里寻找知识的本原,但不是理性的逻各斯,他认为理性不是逻各斯的本原含义。逻各斯这一希腊哲学术语,它的本原含义是语词。
“全部理论认知都是从一个语言在此之前就已赋予了形式的世界出发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以至哲学家无一不是按照语言呈现给他的样子而与客体对象生活在一起的。”(注:卡西尔《语言和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第62页。)
所以,语词逻各斯在起源上居于首,在力量上位于尊。卡西尔借助于语词和人类古老神话与宗教的原初联系来说明语词逻各斯的本原性。
“语言意识和神话——宗教意识之间的原初联系主要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得到体现:所有的言语结构同时也作为赋有神话力量的神话实体而出现; 语词(逻各斯)实际上成为一种首要的力, 全部‘存在’(Being)与‘作为’(doing)皆源出于此。在所有神话的宇宙起源说,无论追根溯源到多远多深,都无一例外地可以发见语词(逻各斯)至高无上的地位。普罗斯在尤多多印地安人那里收集到的文献中,有一篇他认为与《约翰福音》的起首一段颇为相似,他的译文也确实与之完全吻合:‘天之初,语词给予天父以其初’”。(注:卡西尔《语言和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第70页。)
的确,在卡西尔的哲学中,语词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他把语词的这种地位推广到一切具有指谓和表义作用的符号,并进而断言人类:
“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组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体验的交织之网。”(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84页。)
然而,卡西尔对于符号的上述界定,并不是意图建立一门包罗万象的符号学,而是意在为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人文科学或者说文化科学提供一个一般的符号形式哲学。但卡西尔对符号宇宙的自信和乐观,可以说既催发了莫里斯符号学的构想,又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现象学观念和其它哲学观念一起,促成了欧洲大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兴起,形成了欧陆学术界盛极一时的符号学研究热潮。
三、巴尔特、德里达、艾柯:结构主义符号学之一瞥
欧陆的符号学概念,按照一位欧洲学者的说法,是“整个结构主义事业中最负成就的概念之一,而且很难把它和结构主义区别开来”。(注: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本文所要评述的内容也基本上是相关于结构主义这条路线的符号学。实际上,欧洲的符号学学者,至少可以排列出2位数以上的代表人物。 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与欧陆符号学相关的概念。从欧洲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现代符号理论的研究遍布西欧、北欧、中欧、南欧和东欧。就可以称为相关于符号理论的学说来看,我们可以列出以语言学家雅克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理论,以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为代表的丹麦语符学派理论,俄国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话语理论,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符号理论,艾柯诠释本文的符号理论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巴尔特、德里达,以及艾柯的符号学理论予以简略的评述。
巴尔特是本世纪60年代法国文学界崛起的一颗明星,以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所涵蕴的激进、荒诞和独创性享誉国际文坛。尽管他一生活动的精华所在是属于文学领域,但他在文学符号学领域的建树,使他1977年跻身于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的讲座教席。他于1964年撰写的《符号学原理》一书,虽说大部分内容非本人独创,但其论述周详严密、简洁明了,成就了他在符号学学术界的地位。他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以其特有的语言风采展现了他在符号学的基本思想。
巴尔特说:“按照本维尼斯特的一种直观的说法,语言结构就是社会性本身。简言之,或者由于过度节制,或者由于过度饥渴,或者因为过瘦,或者因为过胖,语言学正在解体。对我来说,我把语言学的解体过程就称作符号学”。(注: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第13页。)
巴尔特这里的所谓解体,实际上是指索绪尔对语言结构与言语的划分,语言与言语的划分。正是索绪尔的这一划分,促成了符号学的自立门户。我们就可以把符号学正式地定义为记号的科学或有关一切记号的科学。原先语言学当中不太纯粹的那一部分,语言学弃而不顾的部分以及信息的直接变形部分,“这也就是欲望、恐惧、表情、威吓、温情、抗议、借口、侵犯以及构成现行语言结构的各种谱式”,就成了符号学研究的对象。
现行语言结构的各种谱式都属于符号学研究的对象,这就极大的扩展了符号学所讨论的记号系统,在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中,记号系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自然语言,还包括服装、饮食、汽车、家具、音乐、大众传播媒介等等记号系统的符号学分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而广之,联想到人类之外的其它生物的记号系统的符号学分析。而它对欲望、恐惧等谱式的关心,又使得巴尔特的符号学成为“具有情感性的运动的一部分”。“符号学(至少是我的符号学)是由于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和标志一般道德的良心这二者的混合物而产生的”。符号学要研究由权势影响的语言结构。但权势的难以消除,旧的权势的消除又带来其它的权势,符号学便开始转移其地盘,再次回到专注于文本(text)的符号学中来。符号学家就成了一种艺术家,偏爱于各种想象的文本,小说的、肖像的、方言的、情感的、结构的等等文体。他把这些文本符号当作一种虚构物来加以赏玩。
这就是巴尔特的符号学,空灵飘渺,浮云野鹤,颇有老庄哲学的神韵和魅力。符号学也是一种语言乌托邦?一种虽非现实却又能为我们带来愉悦和欣快的乌托邦憧憬?
在当代欧美哲学界,雅克·德里达这位法国学者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60年代在美国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发表论文《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语惊四座而一举成名。其后又以《书写与差异》、《论书写学》、《言说和现象》等著作开创了符号理论的解构学说。
和巴尔特符号学的风格不一样,德里达是一位四面出击,完全开放性的学者,几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具有封闭型的系统都受到他理论的“颠覆”。
巴尔特把语言学的解体当作符号学的萌生。但这种符号学当中的言语,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的言语,重说话而轻书写:“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注: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5页。)按照德里达的分析,这种反对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代表语言论转向的符号学,如果把文字看作言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派生物,如果仅仅只把语音当作语言学值得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并不否认从来都不存在纯粹的语音文字这一事实,“那么音位学家或逻各斯中心论者的整个逻辑就变得可疑了。它的合法范围就变得狭小和肤浅了”。这种符号学就仍然是用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来反对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对这种语音中心论的符号学进行了解构,作为德里达解构策略的产物,在符号理论中就出现一套互为关联的创新概念:作为一种“非在场的新结构”的“书写物”;作为“延异”的“文字”;“在场”和“不在场”;德里达文字学中代替符号学“说出”概念的“文本”概念等等。
“文字”是德里达符号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狭义的文字领域,也涉及了语言学的领域并且原则上中和了符号的语音学倾向。由于“文字”也是德里达文字学的最一般性的概念,因此德里达的文字学就是符号学。
德里达把他意欲建立的符号学放在一个非常谨慎的位置。一方面,他的符号学必须自由地和严格地在它的文字中使得科学规范发挥作用,因为逻辑和数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立的原则,是不可怀疑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符号学也必须“小心形式主义和数学主义‘素朴’的一面。因为正是逻辑和数学在形而上学中,承担着完善和证实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神学功能,它们和神学的逻各斯及神学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只是伴随着形而上学的消解和数学、逻辑自身体系的深化,数学和逻辑学才成为科学的典范。所以德里达的符号学就必须消解将科学性的概念、规范与本体论神学、逻各斯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相联系的一切东西,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摆脱形而上学链的任何羁绊。
于是,德里达的符号学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一门拥有新内容和新领域的新学科,还不如说它是在文字的“文本”领域内进行探索的“谨小慎微的实践”,同时又是超越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封闭体系的实践。
按照我国符号学家李幼蒸先生的说法,欧洲大陆的符号学研究,第一研究大国当然是法国,而第二研究大国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之所以有此美誉,主要是因为产生了艾柯这样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符号学家。艾柯的符号学理论秉承欧洲文化符号学的传统,同时又兼具英美科学主义的传统,颇值符号学研究者的关注。
艾柯融合了由索绪尔倡导的欧洲式交流论符号学和皮尔斯倡导的美国式意指论符号学。从其思想发展脉络来看,他更偏向于皮尔斯的广义符号概念。与索绪尔强调具有意图性的人工符号概念相比,艾柯倾向于把其符号概念看作为与皮尔斯一样还包括非人工符号和非意图性符号。这样,艾柯的符号学体系就如同莫里斯一样的雄心勃勃。从自然和自发的交流过程出发产生的交际系统,直到更为复杂的文化系统,都可以视作符号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包括:
动物符号学,嗅觉符号学,触觉符号学,味觉符号学,声音符号学,医学符号学,音乐代码,形式化语言,书面语、密码,自然语言,视觉交流,客体系统,情节结构,文化代码,大众交流,修辞学,文本理论等等。
“在今日符号学界中一般符号学在其一切意义上都首先与艾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一学术领域中的成就和缺陷也相当充分地表现在他发表的大量著作中”。(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51页。)艾柯的一般符号学,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整个文化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看作是文化符号学,或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迈向文化逻辑学”。
四、符号学研究的不同范式
我以极其简略的方式描述了艾柯的符号学理论。他的符号学理论,我认为恰好融合了欧洲大陆的人文传统和英美哲学的分析传统。艾柯的文学家身份使他承继了欧洲的人文传统;而其在符号学领域对于逻辑、证据、原因的偏好和他对皮尔斯的偏好,又使他的符号学理论具有英美哲学的分析传统。
这两大传统的符号学演变到今天,虽然符号学的一般理论还未定型,但是,它们分别构成了对符号研究的不同范式。英美传统的符号学研究被看作为逻辑学范式;欧洲大陆传统的哲学,在符号学中最有影响力的范式则是现象学范式,它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考察符号的意义空间,形成当代符号学的新分支,即所谓话语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在考察符号的同时,特别强调“身体”的在场,强调身体所具有的根本作用,(注:高概《话语符号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7页。)这就开创了符号学研究的新领域。因此,尽管符号学的一般理论并未成型,却并不妨碍我们对于符号对象的探索和思考。恰恰相反,这种未成型的学科为我们的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