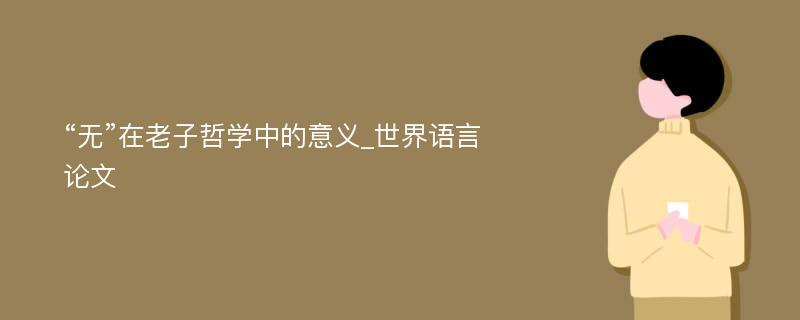
老子哲学的“无”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摆脱盲目被动地适应世界的状况,主体自我需要在认识上把形形色色的个体事物纳入到普遍化的观念系统中,考察不同存在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当精神活动转向对整个世界的存在依据以及人生命运的探寻时,哲学思考承担了反省一切经验现象并对价值判断的标准不断进行质疑的使命。而力求使抽象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知识相对应,以检验那些被人类曾经信赖的普遍存在依据的合理程度,是老子哲学的重要内容。其中,老子关于“无”的论述则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之一。
一、有无相生
各种可以为人类所经验的处于生死交替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事物,包括善恶美丑的判断在内,其中对立的双方无不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老子指出,消除自我存在的个体幻相,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普遍观照,保证认识的普遍性与永恒性,才能化解人类因利益冲突或一己之见产生的各种潜在矛盾。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下引《老子》只注章名)
个体认知不具有完全的有效性,因此以“天下皆知”作为分别美丑善恶的标准与尺度。“难易相成”则把实践纳入到人类的必然能动表现中考虑,突出了认识与实践统一的思想原则。“长短相形”等又从不同的侧面,对“有无相生”命题中一方的存在以对立的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的内涵进行了补充,从而使该命题成为解释运动变化的经验事物的核心原理。“有”指实在之物或表示普遍存在,“无”从消亡的含义中又引申出了潜在的意思。有与无是相生的相互依赖的整体,是对从运动变化的经验事物的归纳演绎中获得的认识的总结。
每一个人直接面对的是无限宇宙的某一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个体事物,而远离感性知觉范围的事物成为本原或决定事物存在的固有依据,我们只能通过理性直观来把握其究竟底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第十四章)“视”、“听”、“搏”的生理活动的极限产生的是“夷”、“希”、“微”的感性知觉,当其出现了“混而为一”的状态时,在自我视域中丧失了生动鲜明的个体特征,转变为“混”的无差别的同一体。“皦”的光明照耀与“昧”的模糊不清,不论是上或下的空间结构,都处于“绳绳”的不可抗拒的时间流逝的变化过程中,这是否认存在着静止不变的绝对个体的认识。“无物”的“不可名”者“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永远处在没有开始与结束的状态。老子以“无状之状”表示“无物”不可言说但是依然存在的情形,而以“无物之象”揭示其与有象之物的差别与联系。仅存在于人类精神活动中的“名”,成为沟通主客体的中介或桥梁。“可”的适度在物的实在或潜在即有无方面,指明了具有“状”与“象”规定性的事物,能够被抽象的概念符号“名”所表达。物向无物的“复”的周期性、规律性的交替循环的变化,是人类能够知晓遥远的“古”的过去,以及存在之物在萌芽阶段的“始”的基础;这种认识杜绝了不可知论的谬误。不确定的“惚恍”是对具有相对稳定性之物的否定,当然也是对无物者“不可名”的理由的分析论证。能够由非“混”的现实存在逆推“古始”的自我,弥合了“古之道”与“今之有”的疏离,见证了道的不朽真理及其“纪”的尺度。“不可致诘”的“一”不是“视”、“听”、“搏”可以感觉的对象,而是终极的知的目标,这间接地区别了感性知觉与理性直观的不同。两者都是心灵活动不同程度地反映,它们统一于主体自我。这表达了借助逻辑的抽象与对经验事物运动变化过程的叩问,都不能寻找到独立于“一”之外的主宰者的思想。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山川河谷等具体事物产生的根源是天地,在宇宙中还存在着先于“天地生”的混成之物。与单一纯粹对立的“混成”,是多样性统一的客观实在。“寂”的沉静、“寥”的幽深,正是独立的无所依傍且不可改变的固有属性的证明。“周行而不殆”表示混成者周遍一切,没有丝毫的生死迁移现象。具备了这些德行则“可以为天下母”,能够造成天下万物的产生成长。“不知其名”意指道不是知识把握的对象,根据其成就万物的德行才“字之曰道”。这种不息的创造能量与慈爱品格,只能以“强字之曰道”的表达形式进行。主体自我固然能够领会其崇高价值,但是无法以精确化的语言符号将道的无穷意蕴传递于世界。“反”的回归是对“远”、“逝”的否定,无限事物“周行”的循环往复始终如一地屹立于我们面前,证明了“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本体之道制约着事物的生死变化的绝对性。
离开了大地,万物就会失去存在的依托。效法大地的自然秩序而能动地变革世界的人类,在认识实践活动中遵循着不可动摇的客观原则。日月星辰的有规律性的运行轨迹,同样是取法于道的结果。道成为万物存在的唯一依据的原因,在于自身的自足圆满即自然。前三个“法”的意思是效法,后一个“法”则是河上公的“道性自然,无所法”的意思。如果以为道法于自然而为大者,域中就是五大而非四大。郭店楚简本无“周行而不殆”一语,当是传抄脱漏。没有“故”的因果关系判断,表明是对经验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有物混成”郭店楚简本作“有状混成”,与“无状之状”在文献上对应,较“物”的语意内涵更为准确。自然概念的提出解释了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是客观存在本来如此,摈弃了宗教神学宣扬的神灵创造世界的观念,否定了世界存在着初始端点的宇宙论思想。自然又具有自生或自发的含义,指明了运动变化来自事物内部的矛盾冲突,澄清了外因论的逻辑谬误。自然还具有自在的规定,因此,它能突破“惚恍”的潜在状态,从无物向物转化,否则世界将是僵死沉寂的状态。自然因此成了统摄各方面概念范畴的枢纽。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自然与无为是同质的概念,分别与人为同有为相对应。
由于德的内在属性的不同出现了多样的万物,但这不会动摇“一”的整体世界的普遍同一。在“字之”的对道的迂回揭示文字中,老子还有直接的论述说明。“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的“物”在此是表示实在的代词,与“那个东西”的意思类似。同惚恍的变化不定的事物始终依存的,是其中存在的象与物等变化的成分。道则是“甚真”之“精”的纯粹无染,是“信”的坚贞诚实决定着“孔德”的伟大德行的呈现,舍此再没有比道更加“真”与“信”的实在者。因此“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的本体之道,在无限世界中发挥着“众甫”即万物的生成之原的存在依据的作用。通过“精”与“甚真”以及“信”的程度之别的确定,划清德与“孔德”的差等结构,凸显了作为万物存在依据的道的绝对地位。“不可名”与“强为之名”,以及不“知其名”与“字之”的逻辑展开序列,隐含了感性知觉与理性直观关系问题的讨论。被意见猜想遮蔽的真理得以显现。是“道法自然”的命题克服了“有无相生”的命题潜存的循环论的局限,使“有”与“无”概念的深意穿过了语言表象的迷宫。至此,老子对“吾不知其名”的内涵在认识形式上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告诫世人必须通过心灵的内省实现同本体之道的默契。
如果物与无物不能在“真”与“信”的尺度检验下彼此区分,“有”、“无”概念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致诘”的认识确定性追求,突出了万与一的两难处境。这一内在矛盾的克服,表现于对德与“孔德”关系问题的论述过程中。而“孔德”的“唯道是从”,无可置疑地说明了“不可名”的无规定性之道,是万物存在的终极支配力量。认识悖论的形成,是由于“可名”的对象具有规定性,面对“不可名”者只能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途径。具有规定性的存在者必然生灭有期,不能成为万物的普遍存在依据的原则。
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在无限宇宙中只有“天长地久”,不会在短时间内流逝消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的理由,“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第七章)“天地”不是某元素的派生物,没有“自生”的个体生命扩张的活动。但是由于天地不能像无物的“惚恍”那样,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的整体,故最终还是要趋于凋零。然而与更加相对有限的经验事物相比,天地以其稳定的依存结构以及表现出来的长久生命力,成为万物依附的对象。“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五章)的认识表明,天地代表的无穷宇宙如同鼓荡不息的空虚风箱,造就了事物的不断生成。“虚而不屈”指天地成为“大”者的根据,彼此的相互作用使潜在的能量“动而愈出”地爆发,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则是其剧烈变化的反映。“先天地生”者没有“动而愈出”的起伏,因此无始无终。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六章)
宇宙的生命活力永恒不息,就是不死的“谷神”的基本含义。创造活动的展开持续不绝,在事物变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万物都从“谷神”中汲取生命的资源,作为“天地根”的“玄牝之门”具有的创造活动,反映了无穷无尽的“谷神”不死的特征。宇宙整体的绵绵生发,与个体事物不断复归于无物同时并存。
作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惚恍”是“先天地生”者,具有实在性而无实体性。追究“混而为一”失去存在合理性的事物的生灭转化条件,是由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阴阳的平衡秩序被打破则“混而为一”,彼此依存的“冲气”达到和的动态平衡而产生,这解释了物与无物的根本差别,回答了潜在转化为实在并重新趋于潜在的根源问题。从经验表象中提炼出来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命题,说明了“惚恍”为阴阳的相互吸引排斥不够活跃,这是逆推万物至天地,进而至“天地根”直到“先天地生”者的过程。“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第三十四章)的论断,已经确立了万物以道为依据的本体论思想;“道法自然”的精深意蕴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有于,有生于无”(第四十章)的阐释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郭店楚简本作“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同传世本在思想内涵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因为“有”在此指具有规定性的阴阳,仅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元素气的功能作用或客观属性,人类可知的依然还是功能作用的存在状态。
是“万物并作”于世界的事实,决定了“吾以观其复”(第十六章)成为可能。而“道之动”的“反”,包含着“成”的成就一切与死的否定的双重内容。把“生”规定为“复”的永恒不息的新陈代谢,“弱”为“道之用”表示“负阴而抱阳”的万物突破潜在成为实在者,是“冲气”的固有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内在依据是“恃之以生”的道,“生于无”的论断因此统一了无规定性之道,与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元素气。在另一方面则强调,纵使万物恃道以生即以道为依据存在于世界,但是道“不名有”,这是警示主体自我在感性经验“不可致诘”的领域面前,需要审慎处理名的适用对象的范围。“观”的默契冥合沟通了主客体的疏离,说明“生于无”之说还包含了无限开放的心灵能够容纳世界的思想。唯一不可分的本体之道,因此决定了无限世界的有机统一。
老子思想中并没有世界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初始的端点的观念,“惚恍”的提法是完全基于区分感性知觉与理性直观界限的说明。因为“万物并作”的整体世界是人类时刻面对的客观现象,故而从纷纭复杂的经验事物追溯其生成的基本物质元素,乃是出于更加全面合理地解释世界的物质同一性问题的认识需要。逆推其初始的同一本原,仅是思维形式的逻辑抽象的表现。由于任何事物的生灭变化必然具有内在的规定性,不能是杂乱且偶然的存在者,因而高下依存的万物以道为依据存在于世界而道性自然,这又在本体论的立场下回答了差别性与同一性的关系问题。关于令后人倍感困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的论述,如果误以为道是生化万物的母体,一二三的先后数字顺序分别指元气与阴阳以及阴阳的冲和,创造出愈来愈丰富的具体之物,就会把战国中期以来的观念甚至是汉代人的意识强加给老子,从而使《老子》中呈现出来的逻辑结构的深意丧失殆尽。在纯粹形式化的认识视域下,我们可以把老子上述论述的含义确定为:宇宙万物的有机整体为一,永恒存在生生不息的依据为道;二为阴阳或主客心物等等对立依存的关系,为一之内在的固有的结构属性;三为突破潜在转化为实在的具体事物必须具备的一切条件要素,是多样性的统一。这一结论的得出是逐步抽象经验素材,使之上升为纯粹的观念的反映。联系老子“有无相生”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命题,这是在强调与“有”的具有规定性相对,“无”的无规定性不是指绝对的空无,而是指作为万物存在依据的本体之道没有任何经验内容。
三、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宇宙万物的内在统一性取决于“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第三十九章)的必然法则,绝非不同个体的无穷累加和简单拼凑。包括天地、谷神以及侯王在内的万物,皆以“得一”成就自身“清”、“宁”、“灵”、“盈”与“生”、“正”的品格属性。丰富复杂的有无关系问题,其微妙内涵无法以语言穷尽。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十一章)
运载货物或代步的车子等,必须存在一定的空间中才能有使用的价值。上述事例都体现了“无”使“有”的实在之物具有“利”的功能的道理。因此“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认识,是对“有无相生”与“有生于无”命题的综合。这一认识的形成是在深入考察语言概念的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借助于列举与类比以及隐喻与分析等手段的运用,最终通过理性化思维确立了概念命题的关系。
在得出“无”具有空间的含义的过程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许受到具体事物会消亡而空间不会改变毁灭的现象的启迪,对于既“惚恍”又无物的“先天地生”者,老子则以“精”与“甚真”以及“信”来规定,杜绝了什么都不存在的虚幻性,肯定了道的实在性。“冲气”之“有”与无规定性之道永远不能分离,其共时性与历时性贯通的依存关系始终不会发生动摇改变。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一章)该章的“无名,天地之始”,在马王堆帛书中作“无名,万物之始”;而且,该章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在马王堆帛书中为“两者同出,异名同谓”。帛书本明确了有与无为同一的整体,其语意也远较通行本严密细腻。运用“异名”把握“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的深远复杂,是认识的需要。
道与可以言说的“可道”者不同,是超验的形上者。概念符号的道作为名,指明了道与人类精神活动的联系。道如果与我们的生命活动完全脱节,就绝不会为自我所感悟。但是此“名”指向的目标并非日常语言概念指称的对象,因为道是“常名”,能够为语言概念指称的是“非常名”。主客体之间产生的对立源自对“天地之始”与“万物之母”的终极存在问题的演绎。通过名之“有”与“无”反映的“天地之始”以及“万物之母”,与主体自我的精神状态密不可分。这是在承认心灵具有容摄万物的能动作用是人类的本质属性的前提下,重申名的概念符号系统承担了沟通“玄之又玄”的媒介的观点。有限个体与无限世界的差距,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巨大挑战。名能够指称世界的“妙”与“徼”,是“常无欲”与“常有欲”的心灵活动的不同层次的表现,反映了个体生命拓展范围的深浅。对立依存的“两者”,皆“同出”于“异名同谓”的同一本原。远离感性经验的“玄”不是世界的究竟状态,只有“玄之又玄”方为“众妙之门”。如果是“常”的牢固凝湛,不论是有欲还是无欲,必将尽观大千世界的真相。虽然“太上,下知有之”(第十七章)的认识已经肯定了每一个人都具有领会本体之道的能力,但是对本体之道的自觉,只能是个人的怡悦欣赏,永远不能与他人分享。意见与真理以及知识与智慧的对峙,终于在觉悟者无限开放的心灵世界中得到化解。
永恒如一之“常”与变动不居之“非常”,被“名”的语言概念指示的时候,出现了确定性与相对性不能兼容的情况。未及于“众妙之门”则认识内容不完整,可是确定之名不能同时容纳肯定与否定的判断在同一的语言概念符号之中,况且“众妙之门”不在经验感受的区域内。具有规定性就是相对有限的东西,导致虚无或有限的事物能够化生万物的错误认识的形成。为此,老子提出了“正言若反”(第七十八章),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或对肯定的对象借助于否定的方式表达的全新认识途径。“有欲”与“无欲”之“常”的确切含义同知与观的区别联系直接同一;“有欲”为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无欲”指凝湛沉静的心灵,是主体自我不可分割的生命活动的不同形式。“观”的理性直观提升整合了所知的“古始”的知性内容,从而消除了其片面性,达到了对有无“同谓”的本体之道冥合的高度。突破概念分析的具体活动成就个体充实饱满的精神活动,与无视语言概念的应有作用截然不同。人生的自由解放就是由于“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的“玄德”的塑造,坚实地安顿在我们的生命中“然后乃至大顺”(第六十五章),达到了普遍和谐,从而实现精神的永恒不朽。
因此,在作为《老子》提纲的首章中提出的“异名同谓”的“同出”的“两者”,其中隐含了认识形式与知性结果的对立依存的区别和联系,是我们把握老子发现的“无”的关键。老子处理普遍的形上学问题以及方法论、社会政治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前提,是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人类对道这个宇宙万物的终极决定力量的追寻,同指向具体事物的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语言存在的矛盾。“天地之始”与“万物之母”的形上学问题,成为区分“名”之有无适应的界限。虽然有无之名存在着功能作用的差别,但是仅为人类认识的同一对象范围大小与程度深浅的不同。相应地,老子在方法论方面揭示了有与无概念内涵中反映出来的逻辑悖论,肯定了“妙”的生动奇妙与“徼”的精密确定能够被自我心灵囊括无遗而容摄整个世界。“徼”的精密确定形成的是系统化的知识,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表现为排除假象与意见而产生真理的过程。“妙”的欣赏认同反映的是主体自我对世界亲密无间的情感态度,瓦解了同万物的疏离对立造成的心灵失衡问题。因为是知情意构成的整体生命的彻底净化获得的充实怡悦实现了自我的超越解放,一尘不染没有丝毫分别意识的无为的主体自我,与本体之道冥合而洞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把自己提升至人生可能达到的极致水平。这一观念既延续了对终极实在的肯定通过否定的方式揭示的态度,又进一步以生命体验的沉默之“无”为主体自我把握世界赋予了空灵蕴藉的韵味,奠定了中国哲学悠久绵长的诗性传统,有力地说明了自由的人生必然是觉悟了宇宙万物真相的智慧明觉,并且圆满自在地落实于生命活动的一切方面。这些包含了众多知识论问题的论述,在彰显了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无”的方法论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无限拓展了概念系统的构造呈现出来的逻辑思考的发展空间。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内容且相互联系的“无”的概念内涵,在前人所断言的已知的即“有”远不及未知的即“无”广阔深邃的主张那里,已经得到了一种知性的支持。既然人类的认识永无止境,有限自我与无限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那么老子发现的“无”的确昭示了把人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的自我解放道路,阐释了理智的实践行为与个人丰富的情感生活彼此和谐的作用决定着人类具有无限发展的潜能。而洋溢着直观感受乃至生命体验的“无”,绝对不会形成同理性的逻辑分析对立的问题。相反,是系统审慎的逻辑建构被哲人的心灵完全领悟,最终洞察超验而实在且普遍而唯一的形上之道,使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无”以其不可究诘的暗示效果或启迪成分,引导生命活动不断成长。这个伟大的哲学开端,固然存在着许多需要系统论证的东西,然而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业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