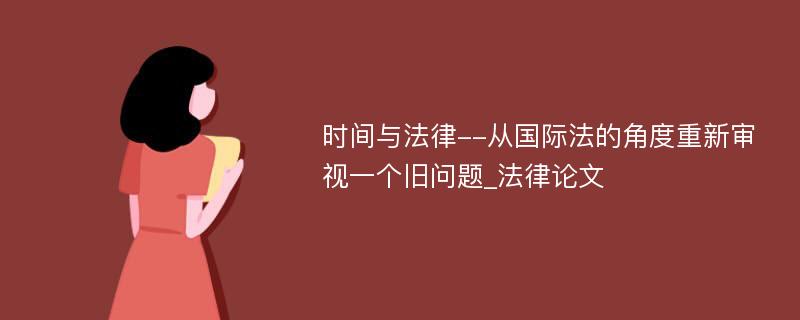
时间与法律——从国际法角度对一个老问题的再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角度论文,时间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 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310(2001)02-0022-04
时间的概念对我而言有着持恒的吸引力。我反复掂量着时间与速度的关系。
当我发现时间观念在国际法领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时,我内心的喜欢是可想而知的。
1 现在和过去
国际法存在于平行状态的法律体系中。因为所有的国际裁判法庭的管辖权都基于国际法成员国的承诺同意。那末,这种承诺是否意味着管辖权可以及于此前发生的事实呢?
一国接受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国际法院第36条第2款,即所谓的选择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一国须声明:当它与其他国家(与自己作出相同承诺的国家)发生争端时,将接受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那么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由于国际法院规约规定:国际法院可以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审理有关案件,因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某一争端的形成与导致争端的事件或事态可能并不同时发生。国际法院以及它的前身——国际常设法庭的明确立场始终是:对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的承认是具有溯及力的,除非声明特别保留。就某个国家而言,避免此等溯及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像比利时在1925年所作的那样,提出一个保留条款。该条款规定,对于“在本声明获得批准后发生的,并且涉及本声明获得批准后发生的事实与情势的任何争端”,比利时政府接受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这种双重时效的排除条款出现在许多接受国际法院司法管辖的声明中。
为了将接受国际法院选择条款之前发生的事件排除在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之外,还可以采取其他的方法。例如以过去某一时间作为起点,或者特别限定某一时间段(通常包括某些敏感的事件),同样可以将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排除在外。到目前为止,已经作出的此类声明大约有20项,涉及的时间包括处在敌对状态期间、军事占领期间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采取何种保留方法,国际法院仍然有必要审查某一争端是否发生在排除条款所规定的时间之前或者时间段之外。争端及引起争端的事件和情势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如果将互惠原则运用于接受选择条款中保留(包括时间保留在内)这一领域的话,则会使每一方当事人都会从对方的排除性规定中受益。这无疑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欧洲人权条约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是具有“选择性加入”规定的人权条约。两个条约均允许其中任何一个条约的缔约一方接受相关条约的司法管辖权。所有这些都无须考虑“纠纷”是否存在以及何时产生。欧洲人权条约第25条和第46条的规定导致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建立。
那么时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司法管辖权的溯及力问题上,欧洲人权法院采取了与国际法院同样的立场: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其对于争端、诉讼请示及相关事件的司法管辖权自有关国家成为欧洲盟约的缔约国时即已存在,尽管各有关国家接受欧盟委员会或者欧洲人权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时间可能要相对滞后一些。当然,上述原则在具体适用时可能会因所谓“6个月原则”而稍打折扣,该原则要求递交到欧盟委员会的申请必须在丧失本土救济权之后的6个月内提出。
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欧洲盟约开展工作的欧洲人权委员会推定缔约国对于司法管辖权选择条款的接受没有溯及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只对接受选择性条款之后提出的申请或者发生的事件行使司法管辖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时并不存在限制司法管辖权溯及力的“6个月规则”。人们不难发现,那些国际法院的法律观念中视为必要的属时理由的,在欧洲人权委员会看来则是不言而喻的。
2 事件的持续性
1938年意大利诉摩洛哥硝酸盐案件中涉及到了事件的持续性问题。在此之前,意大利和法国声明接受国际常设法庭的强制性司法管辖权。法院声明接受该司法管辖权的时间应为1931年9月,而摩洛哥硝酸盐企业的垄断经营许可证是在1920年1月和8月颁发的。但意大利方面指出,这种违法状态是始终持续着的,直到1931年法国宣布接受国际常设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后出台的法律才使其终止。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构成诉讼请求中所指的那种违法的持续状态呢?这种违法状态的逻辑后果又是什么呢?国际常设法庭认为,最关键的是1920年的立法,因为此后发生的事件不可能绝然地与此分开。法院指出,检验的标准就在于,随后发生的事件本身是否足以导致纠纷的产生,而这就目前的案件而言显然是不可能的。
再来看这一问题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有两个案例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案例是古耶案:法国在1984年2月17日批准该条约的选择性条款时并未有保留,而是作了一项声明:“法国对(选择性条款的)第一条理解为:该条赋予人权委员会接受自该条款对法兰西共和国发生效力后发生的、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的、或者因其他事件导致的,对本条约所规定的人权的侵犯活动提出的指控的权力。”
法国的上述解释性宣言与人权委员会自己的解释完全吻合。本案对人权公约的适用涉及从法国军队退伍的塞内加尔人,他们宣称他们受到了与该公约第26条相悖的歧视,事实根据就是他们收到的退休金比法国本国的退休士兵要少。有关退休金的法律是1979年开始实施的,即在人权公约的选择性条款对法国发生效力之前。
塞内加尔人指出,他们一直在与法国的政府谈判,法国政府的经济、财政与预算部长最终作出的是一封落款为1984年11月12日的信,拒绝了塞内加尔人的要求。而这一时间距法国批准人权公约的选择性条款已经6个月了。人权委员会于是决定,原告自1984年5月以来的不间断的法律申请以及与请求的权利相关的决定使得这项请求是可以接受的。从而确立了人权委员会对本案的司法管辖权。
与时效问题密切相关并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另一个最近发生的人权条约方面的案例:斯米尼克诉捷克共和国。原告受到当时政府的安全机关的压力而于1987年被迫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按照当时的法律,他们的财产被充公了。1991年6月,在建立了民主制度后,捷克批准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选择性条款。
就在此前不远的1991年4月,捷克公布实施了一项财产复原法律,该法律规定,对当时因社会制度压力而离开捷克的公民可以就重新取得原有的财产或者就他们的财产损失取得赔偿。但上述法律同时规定:只有那些依然保留有捷克国籍并且永久居住在捷克国内的有关公民,才可以取得原有的财产。原告方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因而声称这是对他们取得救济的非法的歧视性限制。虽然原告所指控的法律是在1991年4月通过的,捷克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选择性条款的时间是在1991年6月,但人权委员会仍然认为,原告所指控的侵权行为在捷克批准选择性条款之后是持续存在的。该委员会进一步指出:“一项持续的侵权行为可以解释为,在选择性条款生效后由缔约国通过主动的行为或者明确的暗示对先前的侵权行为所作的确认。”人权委员会指出,“考虑到缔约国本身对原告方的离境负有责任,如果人权公约要求原告必须回到这个国家并且永久地居留下去,并以此作为返还财产的先决条件的话,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应当说明的一点是,有几个东欧国家对于被扣留的犹太人的财产也作了与此相类似的规定。要求请求人必须回到那个曾经毁灭了他的家庭生活并且犹太人被大量杀害的国家,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持续的行为”的概念并不是那么好理解的。
1995年的雅洛斯和萨尔根诉土耳其一案中,他们指控称,他们被羁押的期限超过了欧洲人权盟约第5条第3项的规定,而且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的期限违背了该盟约第6条第1项的规定。原告因政治活动而于1987年被逮捕,而审判是在1988年举行。从1989年开始,陆续有人被释放,而原告直到1992年才被取消所有指控而获释。土耳其则提醒欧洲人权法院,它承认该法院的强制性司法管辖权的时间是1990年1月22日,且仅承认“基于此时间以后发生的事实”享有管辖权。土耳其反对把发生在其接受人权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日期——1990年1月22日以后发生的事件“简单地视为发生在此之前的事件的自然延续”。土耳其的这一辩护理由被欧洲人权法院否定。该法院指出,某一行为是否是已开始的其他行为的自然延续也许并不重要,因为:“从缔约国接受欧洲人权盟约的选择性条款的那一刻开始,该国所有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不仅都应当符合欧洲人权盟约的约束,而且毫无疑问地应当接受盟约的执行机构的司法审查。”
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也可基于某一条约的规定。在此,国际法院也运用了司法管辖权溯及力原则。1993年3月20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提起了一项针对南斯拉夫的诉讼,指控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西南部地区)违背了禁止种族歧视的公约。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则辩称,即使欧洲人权法院基于禁止种族歧视的公约而拥有司法管辖权,也只能就1992年12月29日之后发生的事件行使其管辖权。欧洲人权法院则认为,禁止种族歧视的公约“根本没有包含旨在以此种方式限制其司法管辖权的任何规定、立法本意或者可能发生此等效果的时间事由,而且任何缔约国本身均不得为达到此种目的而对加入本公约有任何保留”。
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在确立各缔约国接受司法管辖权溯及力方面,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欧洲人权法院都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胆得多。
另一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承认:发生在司法管辖权起始日期前的行为,有时会在该日期之后具有持续性。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比联合国国际法院在观念上要更开放一些,而这已经为他们介入对此类行为的司法审查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3 过去和现在
能够将今天的法律适用于昨天的事情吗?
如果今天的某个法院发现了一条法律规则X,而过去对于所有相关事件都是适用法律规则Y,此时,国家应当对此负责吗?
1974年的马尔克斯诉比利时一案中,马尔克斯针对基于欧洲人权盟约的立法中有关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的歧视性规定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比利时政府辩称:“如果法院试图发现比利时法律中的某些规定与欧洲人权盟约的不一致之处,那将意味着这些规定自从欧洲人权盟约在比利时生效(1955年)以来就始终与盟约相抵触着,这样的判决一旦作出,势必将相应地导致不动产领域的混乱,从而为大量争论涌入法院打开了大门。”
对此,法院判决总结道:“接下来该轮到政府在其本国的法律体系内选择适当的方法以履行自己基于欧洲人权盟约第5条第3款所承担的义务。”
刑法中的溯及力问题具有特别寓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法律的一项普遍原则,对于所有发达的法律系统而言,是普遍运用的原则,从而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因而,这一原则普遍地反映在所有的人权国际公约中,并且在欧洲人权盟约第7条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无疑是公民免受独裁的行政权力的侵犯的重要保障。
1991年R太太诉R先生婚内强奸,该案于1991年提交到英国上议院。上议院的议员认为:那种认为丈夫不构成强奸妻子的罪名的规则,已经不再是英国的法律了。因此该丈夫被判构成强奸罪。被告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如果刑事责任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那么刑法的适用也可以具有溯及力。虽然强奸的婚姻豁免原则仍然有效,但法律委员会已经建议取消这种豁免,并且“对于已经存在的侵害行为适用这一新的规则是凭正常理性完全可以预见到的”。
关于战争罪犯,联合王国1991年战争法草案采用最狭义的概念,该法授权英国法院审判那些居住在英国的在二次大战中实施了谋杀、一般杀人或者其他构成战争罪的杀人行为的战争犯。当时几位著名法官将该法视为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这一点是值得探讨的。在1991年法中所真正看到的,是英国对于国际法的司法管辖权的进一步确认而已。其目的在于审判那些实施犯罪行为时已经知道他们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
[收稿日期]2000-12-15
校对:张越(1970-),男,山东济南人,国务院法制办法学博士。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北京 1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