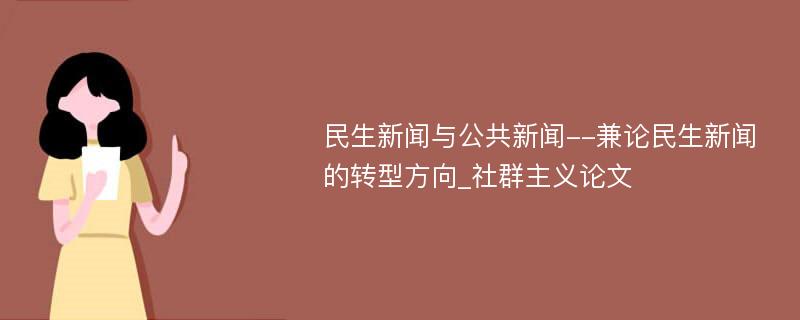
论民生新闻与“公众新闻”——兼议民生新闻的转型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论文,民生论文,公众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视“民生新闻”的勃兴,是中国电视新闻界改革发展的重大成果之一,也是电视业界和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滥觞于2002年元旦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随后迅即波及全国地方电视台的电视民生新闻,正站在转型的关键点上。《南京零距离》的名头已经改换为《零距离》,显示出摆脱地域限制、将“零距离”理念推延至全台资源和全地域报道领域的勃勃雄心,“转型”、“升级”的冲动异常强烈。据笔者所知,全国各地电视民生新闻栏目也早已酝酿自身节目转型之策略。“转型”、“升级”乃是正途,因为它预示着创新的活力,问题是,转型的方向是什么?这事关转型的成败、得失,故而值得人们深思。早在前几年,学界就有一种呼声,认为中国电视民生新闻的转型方向当为曾经在美国风行一时的“公众新闻”。笔者以为,“公众新闻”的部分理念可以植入民生新闻的改版升级,但后者的总体转型方向不可能是在理念、内涵和功能上与民生新闻有显著差别的“公众新闻”。
一、压力与语境的差异:两种不同的“第三次革命”
任何新闻主张的出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某种特定情境的反应方式,换言之,都是对某种特定压力的一种回应。因此,了解任何一种新闻主张所面临的压力或语境,就能够准确把握这种新闻主张是否“因时而生”、“因势而成”,从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公众新闻”的产生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性。
压力之一:商业主义的泛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发展出现了由媒介兼并而催生的媒介垄断和媒介巨头,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主义的泛滥。商业主义以迎合公众趣味为导向,以刺激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的上升为目标,以“消费主义”价值观影响公众思想,加剧了公民的政治冷漠和社会冷漠症。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媒介资本化程度和宣传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垄断资本为代表的“私人利益”和“私人领域”日益取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报刊的公共特性,操纵了公众话语权,从而持续削弱公共媒体的批判功能,最终导致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特征之一的“公共领域”的毁灭。他在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控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统领了公共领域。”①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媒体工业日益依赖资本力量并趋于垄断化发展,以利润为中心的商业法则消解了媒体的“公共性”,尤其是政治报道的公共性。一个最凸显的例证就是,美国公众对媒体关于1988年总统大选的新闻报道非常不满,因为后者基于自身的“专业理念”,越来越关心竞选活动本身和竞选人的言行以及私生活,对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则缺乏深入、持续和通俗易懂的报道。文化观察家迪狄恩(Joan Didion)甚至把这种新闻报道图景中的竞选政治称之为“局中人的棒球赛”②。类似的糟糕的“公共叙事”不仅败坏了新闻业的形象,导致阅读率和收视率的下降,也持续削弱着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
压力之二:媒体的生存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公众新闻”的主要实践者是报纸而非广播电视,更非新兴电子和数字媒体。有学者认为,公认的“公众新闻”较早的实践者是美国佐治亚州的《悬木-探寻者报》(Ledger-Enquirer)和俄亥俄州《阿克伦灯塔报》(Akron Beacon Journal)等,它们分别策划和刊载了关于改进城市生活和改善种族关系的连续报道,这些报道基于报纸和市民的互动③。这些报道的成功波及到其它报纸,并带动了广播电视的创新。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以报业为主体的传统媒体面临着新兴的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的冲击,发行量下降,呈现出自商业报纸以来所没有过的巨大危机,报纸的影响力也江河日下,特别是年轻读者的流失严重。另一方面,主流报纸在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为其摇旗呐喊,实际上沦为政客执政的舆论应声虫,客观上麻痹了公众对严肃政治经济问题的真正关注。在1988年总统大选中,主流报纸不惜冒种族影射、对抗新人权运动“发展权”、“资源共享权”主张的风险,力挺乔治·布什的竞选。应该说,报纸的上述拙劣表现偏离了其应有的公共性立场,也使得公众因厌恶和麻痹而远离了与他们实际利益息息相关的真实的现实政治进程。更严重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被日益壮大的跨国公司的利益所绑架,成为后者开拓市场的政治工具,兼并后的报纸、报团等越来越依附于跨国财团,成为其利益的代言人。显然,媒体同时面临着“为什么还需要媒体?”、“媒体到底为谁服务?”的合法性危机。
“公众新闻”(Public Journalism or Civic Journalism,或译“公共新闻”)恰恰就是此一时期在美国新闻界兴起的一场变革运动,是新闻界针对其在商业化过程中招致的社会批评和种种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作为媒体之本质的“公共性”被商业利益消减之后最直接的反思与挽救。被称为“公众新闻之父”的纽约大学教授杰伊·罗森描述的理想的“公众新闻”具有如下特点:1、视人民为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局限于知晓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听任其遭到破坏;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人们对它感兴趣并投身其中④。概言之,美国公众新闻学运动提倡新闻以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为目标,克服公众政治冷漠症,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改善社会公共生活,通过关注社会问题,并经由公众讨论发现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使媒体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并以媒体最直接的方式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毋庸讳言,“公众新闻”的提出,也是美国报业企图重新恢复“公器”声誉、以期在与新兴电子和数字媒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种努力和自我拯救。如果说从政党报纸到商业报纸是第一次革命,从自由放任的媒体到“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是第二次革命,那么,把相对抽象的媒体“责任”建立在唤起公众政治参与的“公众新闻”范畴则是所谓的第三次革命。
中国的民生新闻最初也源于报纸,脱胎于边缘型的“社会新闻”和“市井新闻”,经电视引入改造后方获得“正名”并名声大噪。但与美国“公众新闻”完全不同的是,民生新闻所面临的现实压力和语境不是商业主义的泛滥和新闻合法性危机,首先是传统新闻叙事观念与新时期观众新闻需求的巨大脱节。在新世纪初期的电视新闻领域,“国家主义叙事话语”是中国电视新闻的主流话语形式,从中央到地方,“大政方针”、“宏观政治经济形势”、“重要会议”、“领导人活动”等以社会精英为主角的宏大叙事主题牢牢占据着中国电视荧屏,民生主题是以上述电视叙事的“派生物”或“证明物”的面目出现的,没有自身的实体性意义。这种状况脱离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实际需求,自然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有作为的电视人开始思考电视新闻的突围之路。就此而言,民生新闻运动必然意味着对上述新闻叙事理念的变革。民生新闻的最初实践者和标杆栏目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创制人景志刚认为,2001年冬天来临的时候,当时的电视人“身陷困局”,他们苦苦摸索出“民生新闻的巨大生命力在于它体现了我们这个平民时代新闻必须具有的精神品质。我把民生新闻的精神品质归结为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⑤。民生新闻取得成功的本质乃在于地方电视台寻找到了寻求自身突破的现实策略,顺应了中央高层对于新闻工作提出的新的政策性要求(“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以及由此派生的新闻工作“三贴近”要求)。这种顺应不仅使民生新闻获得了“正名”和合法性基础,而且争取到了自身生存的最大政治空间。
其二,民生新闻是媒体环境和市场压力的直接后果。新世纪开始之际,央视一枝独秀,占据着中国电视市场的巨大份额,客观上对各地方电视台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各地方电视台尤其是城市电视台在较低的层次上争夺着有限的地方电视市场,“频道中心化”、“制片人制、主持人制”、“栏目化、杂志化”等创新招数之后,电视新闻的改革空间似乎释放殆尽。此外,彼时的电视节目缺乏自身的包装和营销手段,市场诉求方式单一,难以激发观众持久的收视欲望。民生新闻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视呈现方式和营销方式(晚间黄金时间播出的大容量本土新闻信息,最能体现电视媒体独特优势的直播形态,政策话语的新闻化表述,具有亲和力的主持人“说新闻”,多种形式的“有奖收视”营销活动等),使观众眼前一亮,从而成功化解了媒体呈现和观众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当时的电视竞争从“红海”走向“蓝海”。
民生新闻在自身内容上从“宏大叙事”转入“微观社会学”观察,颠覆了观众对电视的原有认知和期待;媒介现实和生活现实的重合,既满足了观众期待已久的新闻收视欲求,同时也使这种欲求定型化和模式化(笔者注意到,民生新闻诞生之后不仅在横向上被各地方电视台“克隆”,从纵向看,各电视台的各类新闻节目也有“泛民生化”的倾向),以致电视观众产生这样的想法:好的新闻就应该是民生新闻这个样子。
李幸认为,自1993年以来,中国电视有过三次革命,第一次以央视《东方时空》为始作俑者(讲述“百姓故事”和记者主持人制、制片人制),第二次以湖南电视台《幸运3721》、《快乐大本营》为标志(娱乐电视的地方经验),第三次则是肇始于《南京零距离》的民生新闻,“第三次革命里出现的平民主播,使得电视的大众性、平民性终于浮出水面,电视回到它应该有的样子上来了”⑥。
很显然,美国媒体的“公众新闻”和中国电视民生新闻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环境,它们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完全不同,应对方式也大异其趣。如果说“公众新闻”面对的中心压力是过度商业化以及新闻公共性的丧失,民生新闻的环境则是“太不商业了”、“太宣传化了”以及新闻本性的丧失。忽视这一点,就不可能超越表象的联系,达到对其差异性本质的正确认知。简言之,中国转型期的民生新闻不可能直接承接美国上世纪末期作为一场新闻反抗运动的“公众新闻”的余绪,因为它们在质上有较大的差异。
二、深层底蕴的不同:社群主义、协商政治与公民意识的萌芽
“公众新闻”和民生新闻除了它们自身所面临的不同媒体压力之外,还植根于更深层次的、超越单纯新闻理念的社会支撑性因素——只有把握住社会思潮的巨大变化,才能精细触摸出两者不同的质地。
从新闻本身的“学统”或“道统”来看,“公众新闻”所标举的“公共性”无疑是早已在新闻界内部存在的“社会责任”的延续。
关于“社会责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密尔的道德功利主义、卢梭强调“众议”应该服膺“公议”(general will)的主张,直至杰弗逊对印刷商“捏造虚假事实”的警告和普利策对报纸坚执最高理想、担负道德责任的呼吁,但是媒体社会责任的要义在1944年由12位著名学者组成的“新闻自由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俗称“哈钦斯委员会”)的调研中才获得了严肃而系统的表述。在1947年该委员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自由与负责任的报刊》中,报刊的社会责任被特别标示为:抵制商业和资本的控制,营造自由而公开的市场,促进社会变革。195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由三位著名传播学者(F.S.西伯特、T.彼得森和W.施拉姆)撰写的《传媒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彼得森执笔写作了其中的第三章“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详尽阐述和解释了哈钦斯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了美国媒体的尴尬现状:“一方面美国人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对传媒的依赖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媒体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因此新闻和评论的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体经营者的任意摆布而无能为力”,据此,彼得森断言,“日益强调新闻界的责任”,并且把传媒的消极责任转化为积极责任,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新兴的世界观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思想”⑦。
但是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招致的批评也是十分激烈的,关键是“社会责任”的概念仍然是比较抽象和含混不清的,而且与传媒人的实际权利和义务、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客观性原则”特别是变化的美国生活现实仍有相当的差距。而在此时势头越来越强劲的“社群主义”思潮与责任理论相结合,正好把相对抽象的责任概念“坐实”了,那就是高扬传媒的“公共性”,促进社会特别是“社群”实质性互动的能力。
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是在批评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和后者构成了美国九十年代的主流社会政治思潮。与传统的自由至上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一样,社群主义不再强调以个人权利为终极标准的价值观和理论出发点,而是以社群(如家庭、邻里、社区、阶层、团体、民族乃至国家)利益为核心,后者不仅是个人权利的保障,而且是人类最高的公共利益。显然,相对于新旧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社群主义的理论代表有M.桑德尔、A.麦金太尔、M.沃尔泽、C.泰勒等人。他们的观点虽然并不完全一致,批评自由主义的着力点和角度也不相同,他们定义的“社群”涵义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张,那就是不再把基于个人主义的“权利”视为先验之物,而是强调把相对抽象和静态的“权利政治”转化为动力学的、当务之急的“公益政治”。“社群主义者从实质上把政治权利界定为个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因而把个人广泛的政治参与当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沃尔泽和米勒都强调指出……没有积极的政治参与,公民资格就不能真正实现,从而个人也就无法享受到充分的权利。”⑧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群主义是“公众新闻”的哲学基础,它对后者的支撑性作用主要体现在:1、媒体担负的社会责任不仅是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而且要满足促进社群互动的广泛性要求;2、媒体担负的社会责任不仅要满足原子化的公民个人的“权利”,更要促进社群的集体“公益”;3、媒体不能满足于静态报道,提供“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更要走进社群,走进邻里,面对面地与“社员”进行交流、征询议题,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从实质上改进社群生活,促进社群公益。
中国新闻人当然也讲究社会责任,《大公报》所主张的媒体“四不”要求,更是把媒体为实践这种责任而呈现出的“独立”、“自由”品质强调到极致。但是不可否认,由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特殊的历史环境,媒体常常被裹挟进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中,或者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或者蜕变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没有可能也没有时间塑造自己连续一贯的“道统”,并使之一以贯之根植于代代新闻人的内心之中——更由于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实质上“外在于”政治选举和权力运作过程,就更难获得政治力量和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难以在平等的社会政治博弈中扮演重要角色,形成积极参与社会互动和政治平衡的牢固“习惯”。在此大背景下,民生新闻与“公众新闻”虽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确立公众的主体地位、强化公众的互动和参与意识、建构社会公共领域等诉求方面,这种相似尤其突出,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民生新闻缺乏可持续的、牢固的新闻“习惯”的有力支撑,也没有各阶层(即各“社群”)政治参与的经验积累和利弊的缜密思考,其产生和勃兴具有因时势而生而盛的巨大偶然性和随机性,其未来命运亦复如此。基于此,在笔者看来,中国电视的民生新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公众新闻”,具体理由如下:
1.制度性差异造就了这两场新闻运动运行的不同层面和方向。中美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媒体制度,媒体的社会角色和功能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自由媒体企业”和“喉舌论”的差异是无法抹煞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两者改革、发展的路径和制度性空间完全不同。如果说决定“公众新闻”发展方向的因素主要有美国的社会现实、新闻文化传统和公众新闻需要的话,那么,民生新闻在上述对等因素之外,还要更多地受到“新闻政策”、“宣传纪律”和“舆论导向”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
2.“公众新闻”和民生新闻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学背景的考量。受西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媒体的功能从来就是被牢牢嵌入在政治运作的机器之中,被视为实现“民主”的重要工具。在代议制民主中,媒体被视为选民表达政治诉求、政治家寻求选民支持的“政治秀场”;在传媒技术高度发达、传媒影响力深达社会各个角落的现代,传媒自身、“科学的”舆论调查、民意代表和利益集团在公共领域的亮相等,实质上构成了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并使后者升级为“远程民主”(tele-democracy)。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协商政治”(delibrative democracy)——应运而生。协商政治,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提出政治议程,讨论这些议程,“直接”、“实质性”地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虽然也指出了协商政治面临的诸多现实困难,但都无法否认协商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和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博曼(J.Bohman)指出:“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公共领域中,今日之问题是从各个角度被探讨的……在重大的创新和变革时期,潜在于制度之下的基本理解和假设就被纳入到了问题视野之中……当把民主共识、平等和参与当作历史经验的结果而实用性地加以理解的时候,它们就不但是今日批判理论的最合适的规范,而且还是在实际的公共协商中可被实现的政治目标。”⑨博曼的意思非常清楚,当代西方的议会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遭遇到多元主义、不平等和社会复杂性的种种挑战,唯有协商政治才能够提供最大限度促成民主的现实动力——在这一进程中,媒体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建构者,理所应当在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媒体、媒体与媒体、公民与政治家、政治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和协商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最终促成政治议程的建构,满足民主的要求。事实上,社群主义和协商政治的主张是生长在一起的,彼此依赖和彼此强化对方,它们共同赋予“公众新闻”组织和促进社会对话、沟通社会各种政治诉求、达成妥协而使各方利益获得实现,最终推动社群政治、国家政治向民主方向发展。显而易见,在“公众新闻”的视野中,媒体已经完成了从信息的报道者到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参与者和组织者的转变。
与带有强烈政治诉求的“公众新闻”不同,民生新闻在当今中国仍主要立足于“信息报道者”这一角色。民生新闻与先前的单一“国家主义新闻”的主要不同,并不是在关于新闻报道的功能理解上,而是在报道对象、报道角度、报道旨趣的差异性理解上。说得更清楚些,相对于其所欲变革的对象而言,民生新闻的使命仅仅在于回到新闻报道的本体,将长期以来失落的时事新闻本应具有的民生话语、民生角度、民生关怀捡拾回来,而非拓展新闻自身服务社会的功能。民生新闻虽然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分量,也有一些观众和主持人的连线互动,但从根本上看,民生新闻作为“信息报道者”的角色没有改变,尚没有进一步成为常态下的“社会讨论的组织者”、“社群政治论坛”。在电视观众既定的新闻素养条件之下,民生新闻不会舍弃报道市民生活的全景图画,特别是市民极为关心的“身边事”、“寻常事”(这些事情当然会经过更精准的选择)。相形之下,只有那些公众强烈关心、政府无法回避、有条件或有可能解决的社会公共事务(尤其是社会冲突事件)才可能纳入公众新闻的议题。
3.美国公民社会资源相对雄厚,社团数量众多,影响力巨大,可以给媒体以强大的组织化力量和议程的支撑。美国的社团组织,作为横亘在政府和公民个人之间的“中间变量”和社会冲突的“缓冲器”,不仅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且对立法机构具有强大的“游说”能力,能够显著“增强”或“减弱”政府对新闻机构的掌控力——其对公众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反观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刚刚起步,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并未根本改观(国家—公民个人通常直接“相遇”),社团组织的数量和功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社会整合程度尚不高,媒体自然无力协调和动员足够的政治资源来完成新闻议程的政治化建构和最终实现,也无力依靠社团组织来完成自身使命的实现以及使之成为民生新闻改革转型的强大社会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民生新闻的功能拓展而言,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改变新闻播报的“前台”形式和面目,而是缺乏强大的“后台”资源的有力支撑。
4.巨大的收视压力不可能使民生新闻在短时期内产生向公众新闻的偏移性转型。即使在美国,理想色彩浓烈的公众新闻仍然难以抵挡资本的利润逻辑。在媒体竞争“刺刀见红”的当下中国,民生新闻不可能实施“曲高和寡”的转型而让收视率掉下来——“收视率末位淘汰制”是中国电视绝大多数节目业绩考核的不二标准,民生新闻必须适应中国观众业已稳定的收视习惯,必须持续供给观众他们感到熟悉和产生兴趣的电视画面。在这种态势下,从具体新闻事实、民生话题、社会矛盾乃至“有奖收视”刺激模式抽身而出,将节目重心挪移到观众尚不太熟悉、甚至还相对陌生的社群政治议程的建构上,将会在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的同时,承担同样巨大的收视率下滑的风险——对电视播出机构来说,这同样是不可承受的。因此,笔者相信,现阶段的民生新闻之转型,将以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激发公众参与社会讨论、推动“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培养公民意识为目标,不可能把自身的主要使命界定为以“议程建构”(agenda building)直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民生新闻现在最需要改变和所能改变的不是政治的实际运行,而是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公民意识。有学者早就指出,民生新闻为地方新闻媒介寻求突破提供了重要借鉴,但若以新闻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以新闻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作为新闻业的理想目标,民生新闻只是一个开端。
尽管当下中国的民生新闻没有“社群主义”、“协商政治”的标签,不可能成长为美国式的“公众新闻”,但后者的新闻理念和实践仍然给民生新闻的提档升级以巨大的启示:从某种意义或更深的层次看,民生新闻的目标观众群应该实现从“市民”到“公民”的提升。公民当然是市民,公民生活当然也是市民生活;但公民不仅仅是市民,公民生活也不仅仅是市民生活,两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公民和公民生活应该比市民和市民生活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社会规定性。在基本的个体生存范畴之外,公民是民主社会的真正主体;在吃喝拉撒、车祸打架、油盐酱醋茶、气象服务之外,公民生活囊括了权利表达、权利实现、社会互动、社会参与、公民自治、文化自觉等无比丰富的内容——转型中的民生新闻应该把镜头更多地给予这些更为本质的生活领域。
注释: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序言,[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②③引自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第139页。
④Jay Rosen,The Action of the Idea:Public Journalism in Built Form,in Gasser,T.L.(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9,p22.
⑤景志刚:《我们改变了什么?》,[南京]《视听界》2001年第4期。
⑥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南京]《视听界》2001年第4期。
⑦F.S.西伯特、T.彼得森、W.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90页。
⑧俞可平:《社群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⑨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2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