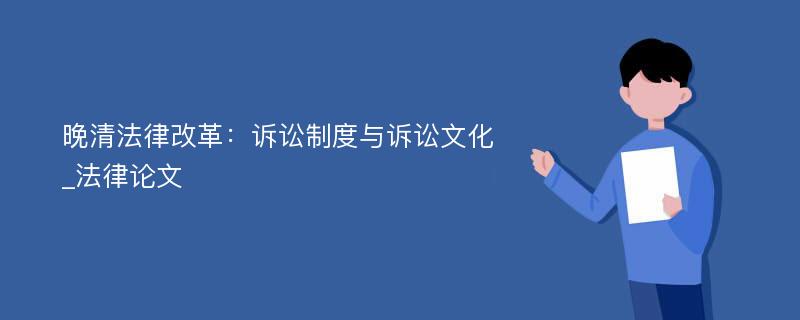
清末法制改革:诉讼制度与诉讼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法制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诉讼立法急功速成
清末时期,传统法制面临转型,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诉讼制度的新构和诉讼文化的转型。在此方面,无论清廷还是法律学者都存共同的意识。当沈家本和伍廷芳被任命为修律大臣主持清末法制改革开始,就把新式诉讼法律的制订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紧锣密鼓地着手清末诉讼立法。
光绪三十年(1904年)修订法律馆正式开馆后仅两年,沈家本上奏《进呈诉讼律拟请先行试办折》和中国第一部诉讼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可见其对诉讼法制订的高度重视。正如其在《进呈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折》[1](卷11) 中所言:一是因为“中国诉讼断狱,附见刑律,沿用唐明旧制,用意重在简括。揆诸今日情形,亟应扩充,以期详备”。以收实施实体法之功用。二是制订诉讼法能够使“断弊(狱)之制秩序井然,平理之功如执符契”。三是鉴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颁行刑事民事诉讼法,迅速收回治外法权的经验,主张中国学习日本,诉讼立法先行试办,“借以挽回法权”。在沈家本的三个基本考虑中,“挽回法权”为最重要者。为此,在诉讼法草案中特意引进“我法所未备”的陪审制度和律师辩护制度。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是清末急功近利的立法急就章,由于草案自身的缺陷,加之其它的因素制约,这部诉讼法始终难以通过便被束之高阁。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虽然被搁置,但是沈家本等人并没有放弃诉讼法的制订,相反,在吸取经验教训基础上,又开始制订《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新律制订,力戒粗疏,谨防漏误,既学习西国之先进思想与制度,又重视中国之情形与传统,讲究立法技术。如开始重视诉讼立法的刑、民诉讼分典制订,又尤其重视民事诉讼法典的立法。沈家本等人在上奏《民事诉讼律草案编纂告竣折》[2](第二卷P4) 中说“中国民刑不分,由来已久”,有必要制订民刑诉讼之专律,特别是制订民事诉讼之专律更是刻不容缓。在中国“刑事诉讼虽无专书,然其规程尚互见于刑律”,但是独至民事诉讼,缺乏“整齐划一之规”。缺乏民事诉讼法规,人民私权难保,而法律保护私权,乃至关重要之事。主张学习西方,以法律保护私权,维护私权秩序,做到“有民律以立其基,更有民事诉讼律以达其用”。如果不制订民事诉讼法律,定会“百弊丛生”。“曲防事制,政平讼理,未必可期,司法前途,不无阻碍。”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沈家本,正是出于对国运艰危下的主权受损的切肤痛感,怀着早日“挽回法权”的殷切期盼,用心用力制订一部完善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尽管颇具几分急功近利的幼稚色彩,但其心可表可敬,其行可钦可佩。其用心之诚、用力之至,恰如奏折中的谦恭之言所征:“所有名词字句,半多创制,改易再三,始克告竣。椎轮之作,固不敢邃信为完善,而比挈损益,亦不敢不力求精详。谨逐条加具案语,诠释译明,免滋疑误。”这两部诉讼法草案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11年1月24日)告竣,并呈报朝廷转饬宪政编查馆核议。这两部诉讼法案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形态的近代诉讼法。不过,未及核议通过颁行,清王朝已退出历史舞台。
当《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被搁置后,《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正在起草中,颁行尚有时日(按预备立宪计划,宣统五年颁布,宣统七年施行),而《法律编制法》即将颁布,为了配合法院编制法的施行,必有一部与其相配套的诉讼法,否则“则良法美制恐亦牵掣难行”,故沈家本提出:“现距诉讼律告成施行之期尚远,而《法院编制法》立待施行,臣等公同商酌,拟请饬下修订法律馆,将诉讼律内万不容缓各条先行提出,作为诉讼暂行章程。”[3] 在此情况下,《刑事民事诉讼暂行章程》得以出笼。但这部诉讼暂行章程也是一部应急的过渡性诉讼法。同样基于种种原因,“未能上奏和颁行,以至时过境迁,蒙尘已久,鲜为人知”[4](第一卷P132)。
清末诉讼审判制度上真正颁布施行的法规是几部法院组织法: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光绪三十三年的(1907年)《各级审判厅试办暂行章程》和宣统元年(1910年)的《法院编制法》。《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是中国近代最早颁行实施的法院组织法,《各级审判厅试办暂行章程》实际上是“清末惟一正式公布的具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法规”,《法院编制法》是“清末制定并公布生效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各级审判机构组织法”。在施行上述三个诉讼法律时,还相应配套地制颁了十余部单行诉讼法规。
由上可知,清末短短几年,制订了一个由多部诉讼法典、法院组织法和单行诉讼法规组成的一个速成的诉讼法体系,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诉讼制度、诉讼文化的转型。
二、诉讼实践轻忽低效
清末法制改革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立法进展异常快速,司法实践非常有限,法制改革中的诉讼立法和诉讼实践亦同样如此。
在清末法制改革中,对于诉讼立法是予以高度重视的,沈家本的一道“先行试办折”颇能说明问题,它奠定了诉讼立法的快步启程的基础。但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少被制定的诉讼法典、法律没有公布施行,使清末复杂的社会关系缺乏诉讼法律的有力规范与调整,诉讼审判实践缺乏适宜合式的法律渊源,因而,严重地影响了诉讼审判的质量。
所幸的是,《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暂行章程》、《法院编制法》制颁,给当时的诉讼审判实践带来了一丝清新之风,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光绪三十二年《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制颁后,一种进步的现代意义的诉讼审判制度开始在京师地区建立,也开始影响全国各地的新型法院制度的形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直隶总督袁世凯率先在天津试行此制,相继设置高等审判分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新型审判机构,诉讼受理、审判进行按新型原则操作。是年6月,袁世凯认为效果不错:“现经试办数月,积牍一空,民间称便。”[2](第一卷P383) “今变通旧章,一切状纸,由厅发卖,每纸制钱五千文,并遵章贴用印纸,方予收理”;起诉之后,搜集证证、逮捕人犯严格按程序进行,书记生负责“写状录供,整理公牍”;承发吏负责“收受诉状,递送文书、传票”;司法巡警负责“搜查、逮捕、执行处刑”。最重要的是拔用“平日研究谳法”和留日法政学校毕业的优等生担任审判员,且设置预审程序。整个诉讼审判过程,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费省而事便”,不仅“民间称便”,而且“外国商民控告华人事件,亦有不先赴该国领事投禀而径赴该厅起诉者”。同时,奉天省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开办各级审判庭以来,也“未及三年,各庭已结案一万七千余起。是结案之多而且速,以视从前之任意积压者,殆不可同日而语”[3](P110)。
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从整个清末社会而言,诉讼审判实践并没有得到普遍根本的改良,先进的司法理念、诉讼审判制度推行效果不佳,旧的诉讼审判机制仍在运转,仍然流弊不绝。各省新型审判机构陆续产生后,由于缺乏新型的审判知识和人才,“或不知法律为何事,或不知审判为何官,或以学部屡试不第之学生,裒然上列;或以从未读律冒名妄充之刑幕,竞获优选。其尤甚者,狂易丧心之辈,犯禁无耻之流,亦毕幸列高科,巍然学者。以此托民生,寄民寄,授以民事、刑事之柄,予以判决、判覆之权,诸事草创,端绪茫然,讼庭初开,毫无历练,诚恐非独不能企各国司独立之盛轨,且较之中国旧司法未独立者,流弊更无穷也”[4](下册P885)。此言,表面上似反对改革的对立不满之辞,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人士的实话实说。孙宝《望山庐日记》就真实记载了一例发生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大理院首先拖拉不办后又草率结案的杀人案。是年正月十七日,春阿氏一案到大理院,由于“牵累人命过多,且有巨公为之斡旋”,故“不敢深鞫,欲办存疑,暂为结案”。二月十一日,光绪帝过问此案,批评“听断逾年,犹未完结”,于是“派员数人,随同推丞商办”。至三月二十一日,大理院对春阿氏一狱以误杀定罪。作者对被皇帝重视的诏狱都如此草率判决深有感慨:“盖人伦之奇变,果摘其伏横尸槁街者,不独阿氏一人也。”“这正是对执法者低劣的审判效率的充分反映。我们由此不难想象,与类此春阿氏的大案、要案相比,无以计数的普通案件,又会遭遇到怎样的命运和结局。”[3](P47—48)
清末诉讼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定罪科刑,讲求证据,禁止刑讯。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指出刑讯之害,主张“省刑责”开始,继而经过沈家本与刘彭年是否禁止刑讯的激烈之争后,沈家本等人禁止刑讯的新章程终于在各地推行,可是实际情况是刑讯依旧,效果甚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有人向皇帝反映:“大理院各级审判厅遇有控诉,彼此推诿不收,及至无可推诿,始行准理,该员等于审判未尽谙习,又复支离讯断,多有传为笑谈者。寻常案件以不能笞责而用跪锁掌责等刑,请托徇情、施用压力,仍不能免。”[1](卷3)即使在会审公廨,也是“仍蹈从前积习,沿用严刑”。对此,光绪帝也只能感慨如是:“颇闻各省州县,或严酷任罚,率用刑求,或一案动辄株连,传到不即审讯,任听丁差蒙蔽,择肥而噬,拖累羁押,凌虐百端,种种情形,实堪痛恨。”[5]
颇具几分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清末司法改革的试验田的直隶省,新型诉讼审判制度的试行已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样板,其诉讼审判的实效也未必如袁世凯所吹嘘的那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直隶隆平县发生一起家庭钱物被劫案,县民吉麦妮为嫌疑人,县衙审讯时“供认不讳”,上解至省后翻供,甚至连事主也认定吉氏只为小偷,不是“案内正贼”。可是法官不按相关规定审判,无罪放人,相反,将吉氏照未定罪名人犯例监候待质三年,结果致告氏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无辜病死监中。
三、诉讼文化缺失茫然
清末诉讼立法的快速发展,却不能形成一个可用的诉讼法律体系;诉讼法律的实施,却难以产生诉讼实践的高效。究为何因?实属诉讼法律文化的缺失茫然所致。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缺失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律文化,法律的强烈的工具性价值,轻程序法的取向,严重地束缚了诉讼法的发达,造成的可见结果是诉讼指导的德与威,立法建制的宽与严,施刑用罚的轻与重的运作不定态。又由于传统社会的家国一体,伦理积重,司法人员的思想儒家化,司法知识的空洞化,因此,在诉讼审判中,情理填充其间,施展其能,“原心定罪”、“狱贵情断”便沉淀为一种稳定的诉讼文化形态,并定型为一种独特的诉讼文化模式。近代肇始,诉讼文化开始转型,严格的诉讼程序意识,紧严的证据定罪制度,先进的诉讼人权保护思想,亟待在立法和司法领域确立。然而在完全相异的诉讼文化土壤上建构新型的诉讼文化,这是一件不谓不艰的工作,特别是在法治建设上,我们处在一个后进型国家地位上,其最典型的表现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拿来其思想、移植其规范、搬用其文化,清末之所为,正是如此,结果倒使问题复杂化了。
诚然,后进型国家向先进型国家学习是一个进步的动力,学其普适性理论、优良的规范、进步的文化,既可取亦可行。故沈家本等人曾果断提出:“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6](卷498) 或有更激进观点者,主张“至于通商交涉之件,则宜全依西例”。“不如改用外国刑律”[7](P418)。这种观点,殊不知不同的法律主张、法律制度是深深植根在不同的法律文化沃土上的,不谙法律文化的异质性,难免善心难善报。实际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编成后,光绪帝态度相当谨慎:“法律关系重要, 该大臣所纂各条,究竟于现在民情风俗能否通行?”[1](卷11) 地方大臣也多有反对: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礼俗不同,暂难更变”。热河都统廷杰反对:“刑事民事诉讼法,边地骤难试办。”山西巡抚恩寿也大不以然:“民间知识未尽开通,新政人才尤须培养,……陪审员、律师两项不免有待踌躇也。奉颁刑事民事诉讼各法,大要准中国之情形。”[8](P50) 更有指出如行新式诉讼法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施至中国,转有滞碍”,“故步尽失,新弦难调,改良之效果未收,自扰之萌芽已播。”[2](第一卷P139—140) 平心而论,此言并非危言耸听,倒是深含反对者的良苦用心。
对于曾创造过优秀的法律文化,并且定型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法律文化模式的后进型国家来说,当她由于相对处于落后阶段,想急功近利地学搬(移植)外域即使先进的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文化时,不同的思想、文化的对立、碰撞、交锋立时而起,实乃自然之事。从理论上说,法律文化实质上是法律人化,其核心作用又是法律化人,法律化人是一个从观念趋同、思想认同到规范束人再到实践效果良美的长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民经过历久的观念磨合、法律运作,普遍认同法律,自觉服从法律,勇敢捍卫法律,此时,一种社会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行为铸造定型,随之,法律人化的实质体现了,法律化人的作用实现了。当此法律文化模式定格后,它的制式(规范行为、思想)力量无比,惯性影响宏巨。因为,这个法律文化模式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甚或还是将来的,它表征着民族法律文化的倾向和特征,呈现着民族法律价值观和思维定式,不管人们对它持何种态度,作为一种定型的文化模式,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孕育、生长、影响,制约着一代又一代后人[9]。正因如此,虽然清末有过在诉讼实践中,当民法缺失时援用法、德等国民法典确立的“契约以为判断之基础”的原则判决一起夫(庞某)妻(张氏)财产相争案[10],也有过在庭审中以“私造外国货币均较本国处刑为轻”的西国条文规定裁判满在田私铸外国银元案的司法实践。但这并不充分有力表明这种诉讼操作具有诉讼文化的普适性真理及普遍性效用。相反,它遇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诉讼文化)的顽强抵抗是异常明显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社会不仅认为类此判决不合中国民情、诉讼文化传统,于事无补,反而担心“若于民情习惯不能相洽,必致滋生事端,求安反扰”。所以当全国相继筹设各级地方审判厅后,而“乡民心目中只知州县衙门为其本管官衙,应行服从。若于州县之外,别设法庭,乡民少见多怪,别生疑虑”[4](上册P32)。其实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当时河南省人们“多仍往县署控案”,尽管县衙依法不受,但是,“执拗之徒,有隐忍息讼,坚不往审判厅呈控”[11]。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被揭示:即使一种良好的制度被学用、被移植,如果没有一种相应的法律文化(诉讼文化)被营造,其制度的运行将会大打折扣,甚至毫无效果。清末诉讼实践并不理想,缺少效能,实与诉讼文化的缺失茫然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