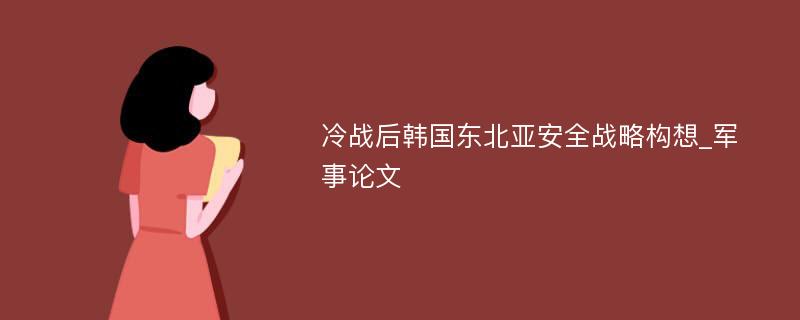
冷战后韩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韩国论文,战后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1.2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11(2006)04-0072-05
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国际关系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中,“不管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power)总是其直接目的”[1]。而“所谓安全困境是指国家在缺少权威(anarchic)和存在敌对国家(有时只是假想敌)的自助国际体系(self-help system)中,无论是增强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力量都处于不确定和不安全的进退两难的情景中。”[2] 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安全困境”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的,只能加以“改良”。而解决因权势竞争造成国际冲突或不稳定局面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政策。从国际体系角度看,均势的功能在于保持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间相互承认主权和独立为根本原则的现代国际体系,即维持这一体系的安全和根本稳定,而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则在于确保体系内各国(主要是各强国)的自主生存[3]。当然,这两项功能还有其“无情的逻辑延伸”即阻止霸权。然而均势只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权宜之计,它可能带来短期的稳定,但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4]。因此,“安全困境”是“均势”产生的根源和结果,“均势”又构成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国家的必然诉求[5]。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传统现实主义因为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国际关系现实而渐趋没落,新现实主义代之而起。基于“公益”论和“免费搭车”理论,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6]。美国是这一模式的积极倡导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二战以来美国逐步建立起了全球范围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制度与规范。“霸权稳定论”一经出现,就遭致了学术界的强烈抨击与批判[7]。批判者认为,就霸权稳定论而言,尽管这种理论有助于超级大国追求权力,占据东亚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将地区安全维持在某种暂时的非战争和非激烈的对抗状态,但霸权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不是平均分配的,“霸权国的行为也不是利他主义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8]。冷战后处于单极地位的美国仍然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国家,其强烈的利己动机不仅不能使所谓的霸主的自我抑制难以兑现,不仅不能增加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消除不稳定因素,相反会引起其他大国的猜测和担忧,促使它们做出某种反应,从而加剧原本存在的安全困境,并使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状态。因此,考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给安全困境祭出的药方,无论是“均势稳定论”,还是“霸权稳定论”都无法有效解决冷战后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这是因为均势只能使地区“朝着更加破败的大灾难发展,因为没有人相信均势能够真正达成”[9],而霸权的嬗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所能控制的”[10]。由于没有任何真正的世界治理能够维护世界的和平与保障国家的安全,国家间的竞争,并由竞争导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所预言的“大国政治的悲剧”[11]。
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正是“大国政治悲剧”频频发生的重灾区。仅从二战后的地区安全议题考量,朝鲜半岛无疑是整个亚太地区的缩影。因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朝鲜半岛南北之间一直剑拔弩张,共同上演了一出安全困境理论的经典实例。整个冷战期间,朝鲜就其不多的人口和不大的财力规模而言,之所以勉力维持世界首屈一指的庞大军队、之所以对先进武器(包括核武器)展开倾力追求,之所以维持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均源于韩美同盟的军事实力、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及其控制全半岛的意图在它那里引起并不时加剧的安全疑惧。在韩国与其美国保护者方面,对朝鲜的疑惧可以说同样强烈,并且同样导致军事安全戒备的不断维持和强化。半岛内的安全两难与半岛外部的安全困境同时并存——即日本和朝鲜、韩国之间的安全困境[12]。作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支轴,朝鲜半岛这一安全困境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冷战时期这一地区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是分别以美苏为中心的两大军事同盟之间的激烈争夺,军事集团间的相互竞争反过来又加剧了半岛原有的安全困境。这样,同盟内部的双边安全协作以及缺乏多边主义意义上的安全合作遂成为这一地区、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主要特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美国霸权稳定的安全目标是保持地区稳定、核不扩散以及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这一地区。为此,近年来美国开发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试图将韩、日、中国台湾地区等纳入该系统,其本意是增强自己在东亚的霸权主导地位,但此举必然会引起东北亚相关国家的疑虑和警觉,促使它们进一步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而这些国家的行动反过来又促使美国进一步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并已成为时下日本增强军事力量的借口。历史和现实均已证明,冷战后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发生与其说是有关双方围绕朝鲜开发核武器的争论与交锋,还不如说是半岛安全困境迟迟无法化解使然。
有鉴于此,冷战后,半岛相关各方开始酝酿化解此一共同的安全困境的途径。目前,虽然双边合作仍然是半岛安全合作的主导模式,但是包括美、日、中、俄在内的大多数亚太国家都开始积极倡导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多边主义逐渐成为半岛地区安全合作的一个新的原则和规范。在这种情形下,三方会谈、四方会谈、六方会谈等各种形式的安全合作模式相继出现,但是动态的谈判并不等同于相对稳定的安全机制。半岛地区应该以及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多边安全机制?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半岛建立什么样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化解半岛安全困境。不少国家的政府和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看法,最后得到普遍认同的是合作安全,即以多边合作求安全。而作为主要当事国之一的韩国为此在政策选择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
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在朝鲜半岛地区这一既缺少绝对权威又存在敌对国家(有时只是假想敌)的自助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增强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力量都处于不确定和不安全的进退两难的情景中。韩国与朝鲜一样,长期陷于安全困境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其安全战略一直以防御朝鲜的进攻为目标,而以停战协定、韩美共同防务条约和驻韩美军为支柱,实行的是典型的依赖型国防。然而在大国政治对峙的年代,韩国对本国的安全战略制定一直没有发言权。躲在美国的卵翼之下,韩国无意也无力去思考与化解自身的安全困境。
随着冷战的结束,前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国际格局中的唯一霸权。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再度发生分野,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泾渭分明的政治分界线日益模糊,地区政治表现出相互依赖的趋势。中、美、俄、日四边关系取代中、美、苏大三角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由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提高,政治对话领域扩大和加深,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和中日影响力的上升,在东北亚地区,中、美、俄、日四国形成了一种“非敌对性的均衡关系”,相互间既竞争又合作,既依存又制约。这一变化给处在大国力量漩涡中心的韩国摆脱安全困境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从1989年10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在联大发言中首次提出建立“东北亚和平结构”起,韩国就开始积极酝酿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想。1993年5月金泳三总统在“新外交”的演说中提及了多边安全合作问题;金大中总统时期对北实施“阳光政策”的同时积极推行四强外交;卢武铉总统时期,提出“和平与繁荣政策”,尤其是面对此次核危机,卢武铉政府坚持主张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和平解决争端。韩国立场的这种变化既是韩国国内因素使然,也是冷战后国际与地区安全形势发展的结果。
韩国认为,周边强国之间的均衡关系是韩国生存与繁荣的保障。从现实情况看,韩国的力量难以同周边大国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抗衡,归根结底,只有在大国间的力量取得平衡并相互制约的前提下,韩国的活动范围才能得以扩大。此外,当前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呈现出动态的均衡,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杠杆两端的平衡,而是表现形式复杂化和多样化的战略交叉互动,中美、中日、中俄、日美、美俄之间任意一组关系的变化都将对整个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均衡关系一旦打破,韩国必将成为巨大冲击波的承受者,这是韩国极不愿意面对的情形。所以,推动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维持当前的地区力量均衡,防止因为周边大国实力的强弱变化导致的地区秩序瓦解,对于韩国意义重大。
1993年8月,韩国外长韩升洲在参加东盟论坛时撰文指出,亚太地区的活力将主导世界潮流,由于东北亚的局势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影响重大,韩国建议并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在多边合作办法中,韩国外交目前最重要的课题是在经济方面建立亚太经济合作体制,在安全方面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体制。在多边安全上必须完善韩美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而不能与之对立,要设法让朝鲜参与。如果日、中、俄、美等亚太国家进行合作,甚至会产生欧洲那样的效果。这是韩国政府第一次具体而明确阐述关于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想。该构想的目的是通过维持周边大国当前的均衡状态,为韩国创造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未来安全机制的结构采取“双轨制”的形式,即同盟安全合作关系(比如美国与韩日的双边同盟)和非同盟性质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协商同时存在;参加安全机制的成员国应该包括地区内的所有国家,使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更具有广泛性和约束性,这一功能最终将在机制实体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该构想还包含一个理想化的结果:在地缘政治上处于核心地位的韩国应该在东北亚扮演大国间关系调停人、仲裁者的角色,“成为四大强国(美、中、日、俄)中间的平衡杠杆”,使韩国从“一种依附的势力变成在东北亚具有支配势力的先进国家”[13]。
该构想在金大中总统时期得以延续,在其《21世纪的亚洲及其和平》中,他说,“我们一定要创造一个我们在东北亚能够发挥主导权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创造只有一个姑娘却有四个小伙子来求婚的条件”,“多少年来一直被几个大国牵着鼻子走的我们,要改变东北亚四国的局面,要以东北亚五大国之一的姿态进入大国的行列,去创造我们民族主导历史的光辉明天,这应该是我们的历史使命”[14]。卢武铉上台后更加清晰地勾勒出了韩国“东北亚均衡者论”的轮廓。2005年3月22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在韩陆军第三士官学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时表示:“现在我们不仅要保护朝鲜半岛,还要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起到平衡作用,东北亚势力格局将根据我国的选择而发生变化。”此后,卢武铉还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到,为了东北亚不再发生矛盾冲突,韩将积极发挥均衡者的作用。
“东北亚均衡者论”是新世纪韩国政府对韩、美、日同盟的新认识。这一外交政策构想认为,在东北亚秩序中,韩国作为韩、美、日“南方三角同盟”的一个轴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韩国不能永远囿于这一框架,不能继续滞留在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南方三角”和中、朝、俄“北方三角”格局之中,否则将会面对新的冷战格局。韩国必须摆脱“冷战阵营外交”,以避免在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上陷入两难境地。因此,今后美日针对中朝施压时,韩国将说“不”,以阻止形成美日和中朝的对立局面。
考虑到在可预见的将来,韩国安全战略的实施依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在预想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中,很难设想让韩国独自充当驯象人的角色在周边大国间维持战略均衡,而让美国扮演这一角色无疑符合韩国的战略利益。针对上述情况,韩国学者提出韩美两国应建立更加现实和成熟的双边关系;将美国拉入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同时保持两国战略同盟关系。这样既能充分利用韩美同盟关系,又能保证在将来美国实力下降实行战略收缩的情况下达到维护地区平衡的目的。为此韩国学者提出了未来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四原则:(1)东北亚的任何多边安全论坛不应削弱本地区现存的双边关系;(2)在推动本地区多边安全论坛时,应强调分步骤行动。由于东北亚地区各国缺乏对话的传统,首先应努力增加信任、培养相互磋商和合作的习惯;(3)除了政府间的联系外还应促进非官方管道的安全对话,它可以比官方论坛更加坦率和自由地讨论安全问题;(4)多边安全论坛应尽可能让所有地区成员加入[15]。
韩国为化解朝鲜半岛安全困境所擘画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架构实质上是“双轨制”的。韩国对“双轨制”式的多边安全机制情有独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可以韩美安全同盟为基轴遏制来自北方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多边安全体制,改善周边环境,解决诸如朝鲜核问题、韩国与朝鲜之间的信赖构筑、军费问题及周边国家间军备竞赛等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多边安全机制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摆脱国家安全中由于过度依赖周边大国而造成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另外,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还意味着多边外交在东北亚的规模扩张,这种扩张将导致东北亚地区内秩序等级的改变。韩国可以借此机会跻身大国集团,摆脱安全的“消费者”的小国形象。从历史上看,韩国属于基欧汉所称的“在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国家”,它们单独或结成小集团采取行动时,决不会对整个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而在相互依存的博弈中,通过多边外交操纵平衡杠杆,掣肘大国力量,往往能够获得超出其实力本身所应得到的效果[16]。这一双轨制安全机制的建立无疑将对维持该地区长期和平发挥关键性作用,韩国也能从中获得可观的和平红利,甚至可能获得意料之外的成果,比如欧安组织在促成德国统一进程中的作用。
不过,韩国所设想的这一“双轨制”安全机制并非无懈可击,它在安全方面存在的漏洞令人不免对它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第一,以均衡作为构筑未来稳定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基石是否可行?第二,韩国能否成为这个多边安全体系内的仲裁人?第三,韩国所倡导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双重架构是否能为地区内各国所接受?从历史经验来看,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并能成功扮演和充当大国竞争的“平衡手”或仲裁人,其先决条件首先是要被其他大国承认为大国俱乐部的一员。目前的韩国显然尚不具备此实力。另外,在均衡下的多边体系内部,由于缺乏一个类似法制市场的最后保证人(the Last guarantor)以维护体系内部力量的平衡,或防止成员破坏游戏规则。因此,以均衡作为构筑稳定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基石也尚存疑问。双重架构问题则涉乎令人敏感的同盟安全合作关系,因为同盟安全完全是冷战思维的产物。这种双重架构同盟关系无视冷战后亚太地区的现状,继续存在必然会导致不必要的地区内部紧张气氛,不利于建立稳定和谐的地区秩序。另外,由于日本也主张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推行“双轨制”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韩国据此指责日本依靠经济和军事实力图谋在亚洲称霸。因此韩国提出以双重架构的形式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似有相互矛盾之嫌。
韩国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构想从总体上来说,是弱国外交策略的表现。其直接目的不仅是企图一劳永逸地化解韩国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安全困局,“不仅是(使韩国)成为一个处于亚太地区活动中心的国家,而且能成为一个处于国际社会活动中心的国家”[17]。不过,就东北亚地区的现状和前景来看,该构想的理想色彩较浓,在实践上也面临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如周边大国关系是否稳定;个别国家的军事扩张步伐;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韩国在何时成为何种程度上的大国等等。
2005年3月以来,因为教科书问题和领土争端,韩日关系高度紧张;美国大力支持日本“争常”,韩认为,美袒护和助长了日本的领土扩张政策,韩、美、日同盟关系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卢武铉的“东北亚均衡者论”和韩欲与中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动向,使人们不禁怀疑韩、美、日同盟是否会因此而解体。日本《产经新闻》就认为,韩国正在明显地“向中国倾斜”,卢武铉可能要摆脱传统的日、美、韩“南方三角同盟”。韩国也有分析人士担心,在美日日益加强同盟关系的情况下,此种论调可能导致韩国更加被美日所孤立。韩国《东亚日报》就声称,国防部增设“东北亚科”,势必将使韩美日同盟关系产生“重大风波”。韩国主要反对党领导人、大国家党主席朴槿惠在议会说:“打破韩美联盟和外交上自我孤立对我国是无益的。只有在我们拥有力量和能力,而且其他国家承认我们能够扮演平衡角色时,这种角色的作用才可能发挥。可是,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俄罗斯,甚至连朝鲜都没有承认我们能够发挥平衡作用。”
事实上,韩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未能统一。卢武铉的“东北亚均衡者论”出笼后,韩国政府高官随即对卢武铉的讲话作了一番解读:“韩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秩序,总统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总是自我封闭在这个秩序里面。”青瓦台也对此发表文告回答说:“有部分人认为我们要否定现存的韩美同盟关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在发挥均衡者作用时,仍将会以韩美同盟为基础。”
据此分析,在未来的东北亚安全秩序中,即使韩国选择“中立”,韩美同盟的基础还是不可动摇的。在半岛南北分裂对峙的状态下,韩美军事同盟关系依然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美国东亚政策的两大支点之一,韩美两国政府都明白,韩美同盟关系对双方都极为重要。但是,在动态的韩、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中,将不断会有此消彼长式的微调,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韩美军事同盟关系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韩日军事合作也将在矛盾和冲突中前行,这些都必然会对韩国以“双轨制”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形式来化解半岛安全困境的努力产生消极影响。
总的来看,尽管韩国所构想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进展因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会步履蹒跚,但它仍不失为目前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并实现永久性和平的有效尝试。尤其是在后冷战时代,和平与稳定内容因符合世界潮流,符合南北双方最根本的利益,符合周边大国的半岛政策,已逐渐成为半岛的主流,今后朝韩两国若能从大局出发,在上述敏感问题上采取妥协或让步,那么此种关于东北亚安全的“韩式”构想最终将会因韩朝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而取得积极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