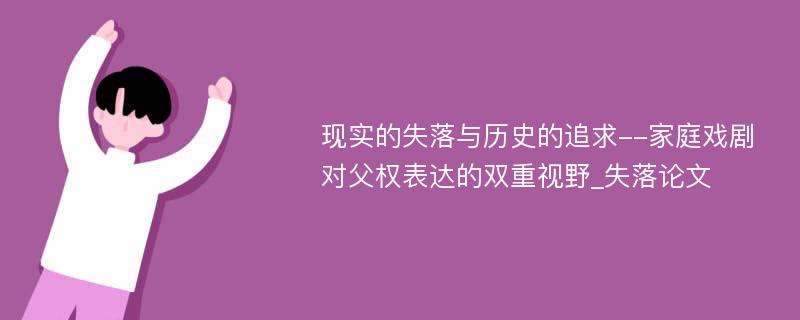
现实的失落与历史的追寻——家庭剧对父性表现的双重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现实论文,家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9)01—0049—06
在传统的文化视域中,父性是权力的象征,是一个家庭赖以生存的物质保证和精神支柱,是一个家族生命力量的重要标志。父性权威高扬的时代,父亲是英雄的代名词,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父亲的权威是绝对的权威;然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父性的权威不断失落,父亲不再是一个英雄,他逐渐弱化或软化,莎士比亚《李尔王》、巴尔扎克《高老头》等作品表现的是父性的高扬到父性的“失落”。和西方国家相比,东方国家现代性的步伐稍慢,父性的失落稍晚。但是,从宏观的角度上考察,父性仍呈现失落的趋势。中韩家庭剧中对父性进行艺术的表现,反映父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失落。父亲形象在现实题材的家庭剧中缺席,父亲成为生活的弱者和沉重的罪身,父亲被剥夺作为父亲的权利,在父子冲突中父性的权威逐渐失落。现实中父性的失落促使人们回眸历史,寻找父性的记忆、关于激情和生命力的故事。
一、父性的意象:“冷漠的拥抱”
意大利著名心理学家鲁伊基·肇嘉在《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用“冷漠的拥抱”形容父性的意象。他阐述道:我们的孩子不仅期望父亲表达安危、关爱和正直,而且希望父亲是强大的,希望父亲具有权力,获得成功。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与父亲相关的角色需要去捕猎养家,需要拼杀护家或不惜以战争来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于是,历史画面中的父亲,比如在荷马史诗中,总是身着盔甲,即使是在拥抱自己孩子的时候。鲁伊基·肇嘉也捕捉到了这典型的意象,称之为“冷漠的拥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视域中父亲的形象是战斗的形象,无论是捕猎、护家还是卫国;其次,父亲是养家、护家的形象,父亲是家庭生存的重要保障,这是父性的本质;再次,父亲的拥抱,给予孩子父爱的具体行为,是父性的表现;最后,穿着盔甲的拥抱,一种随时战斗的紧张感,没有家庭的温馨感。并由此引发了“父亲的悖论”:“我们因此在父亲的内心发现了一种无法袒承的不安全感和一种矛盾的情绪。这是一种外部矛盾的相应反应——他的孩子所怀有的矛盾的期待。”父亲的拥抱是穿着盔甲的拥抱,父性是一种冷漠的拥抱。
父亲带着盔甲对孩子“冷漠的拥抱”,在孩子心中激起不一样的感觉。如果说,不安全感是父亲和孩子共有的话,那么,母亲拥抱的温暖和父亲拥抱的冷漠,还会激起孩子对父亲发自内心的崇拜,并有一种对自己未来和父亲一样英雄的渴望。孩子们的内心深处希望他们的父亲强大也相信他们父亲的胜利。“如果一位父亲是个胜利者,同时也是个好人,公正且满怀慈爱,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对于父亲通常最重要的是要代表一个知道如何取得胜利的男人的意象,他是否善良摆在了次重要的位置。我们的传统屡屡认为,一位行为公正但未能在外界取得成功的父亲,远不及那些不公正但却胜利加顶的父亲更可取。例如莎士比亚就以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而闻名:《李尔王》给了我们一位父亲的原型,这位父亲权力和威望的丧失导致他遭到抛弃。”[1](P3-4)也就是说,评判父亲成功的标准,即胜利男人的意象不来自家庭内部,而是来自外界。换句话说,拥有父性权威,最重要的是在外界的成功。外界的成功意味着在家庭中父性权威的高扬。
“冷漠的拥抱”是父性权威的意象,是胜利男人的意象。然而,父亲在外界并不总是成功,胜利男人的意象只是曾经的辉煌。父性在历史上消失的趋势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从美国到欧洲,再到发展中国家;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然后到农村;最后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社会变迁的确改变了父亲的形象,从威严、不可一世的一家之长,到温和可人得给孩子换尿布的爸爸,这种变迁与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改变是有很大关系的[2]。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穿越历史变迁的社会构建。历史上父亲的角色和母亲的角色不同,雌性作为母亲的角色是确定的,而雄性完全不同,母亲可以不必承担社会责任,不必充任父亲的社会角色。因此父性比母性更脆弱,更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女性走出家庭承担社会角色都会导致父性权威的失落。
父性权威的失落是不是意味着“冷漠的拥抱”变成“温暖的拥抱”、“热情的拥抱”?父性权威的失落意味着从外界到家庭的双重身份的失落,冷漠的拥抱和温暖的拥抱是同时并存的,没有冷漠的拥抱就没有温暖的拥抱。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形象地再现了父性失落后的生活窘境。富有意味的是,李尔王、高老头父性的失落是因为各自的女儿对父亲的掠夺。李尔王被两个女儿的甜言蜜语所欺骗,不喜欢只希望他平安回来的三女儿,然而,他只能在三女儿那里得到仅有的父亲的尊严,前两个女儿彻底抛弃了他,父性的权威荡然无存;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最在意的是父亲的金钱,对父亲漠不关心,女儿对金钱强烈的占有欲望彻底粉碎了父女之情,制造了父性权威失落的人间“喜剧”。曾经给女儿冷漠的拥抱、温暖的拥抱的父亲,现在只剩下女儿对父亲的冷漠,而没有拥抱。
二、权威失落的现实留痕
父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失落有一条清晰的路线,文明程度越高,父性失落越快。但是,就中韩两国来说,父性的失落有些特殊性。中韩两国儒家文化是最具父性权威的文化,悠久的文化传统高扬父性的权威,所以父性权威的失落晚于西方现代文明国家。欧风西雨对儒家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因为儒教作为国教在韩国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韩国虽然现代化进程快于中国,但就父性权威来说高于中国,其相对完整地保存儒家传统,秉承父性文化,把现代和传统相对和谐地统一。中韩家庭剧表现当代生活中父性权威的失落,反思父性的权威。
第一,父亲形象的缺席。
父亲缺席的家庭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是一个残缺的家庭,不幸的家庭。中韩家庭剧对此都有表现。
中国家庭剧表现父母双亡的有《渴望》(大成是个孤儿)、《亲情树》(母亲后来去世)、《大姐》(父亲后来去世)等。
父亲缺席的家庭剧有《渴望》(慧芳父亲)、《浪漫的事》(宋家姐妹的父亲)、《好好过日子》(周博华的父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父亲)、《婆婆》(赵大强的父亲)等。
母亲缺席的家庭剧有《渴望》(王沪生母亲生病去世)、《好好过日子》(安宁母亲)、《大哥》等。
韩国家庭中几乎没有表现父母双亡的。
表现父亲缺席的有《青青草》(泰勇父亲)、《加油!金顺》(金顺父亲、男主人公父亲几乎在最后出现、金顺丈夫去世儿子失去父亲)、《追赶江南妈妈》等。
韩国家庭剧很少表现母亲缺席的。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发现,中国家庭剧中表现的残缺家庭明显多于韩国家庭剧,这说明中国家庭剧更善于家庭苦难的悲情叙事,韩国家庭剧几乎没有父母双亡和母亲缺席,说明其比较注重家庭的温情叙事。《渴望》是最为有力的证明。在《渴望》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这种悲情叙事成为后来家庭剧的模本,中国家庭剧越来越多地表现父母双亡,或父亲缺席,或母亲缺席。
中韩家庭剧表现最多的都是父亲形象的缺席,这种共同的特征同时说明中韩家庭剧女性的角色多于男性的角色,家庭剧中女性往往成为表现的重点。
传统视域的父性是基本生活的重要保证,父性的失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家庭生存方面的困难,家庭剧中父亲的缺席也暗含着父性在这方面的特点。绝大多数父亲缺席的家庭存在经济方面的困难,《渴望》中的刘家、《青青草》中的泰勇家等。家庭剧中父亲的缺席和生活拮据之间的这种联系,说明了父亲在家庭中往往承担着养家的职责。父亲的缺席意味着父亲权威的失落,养家的任务由母亲和孩子承担。相反,母亲的缺席,并没有鲜明地表现出生活方面的窘境,而多是精神和心灵的孤独,如《渴望》中的王沪生等。这充分说明父亲和母亲,或者说,父性和母性,带给孩子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和生活。家庭剧中父性和母性的角色是比较传统的。
中韩家庭剧中父亲形象的缺席,从叙事的角度上说,是为母亲和下一代提供独自面对生活苦难的舞台;从审美的角度上说,着意表现母性的力量和年轻一代的成长。没有父亲的日子,年轻一代克服苦难,顽强地生活。《青青草》中的泰勇,不仅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弟弟、妹妹和母亲。没有丈夫的日子,母亲忍受寂寞和孤独,把儿女抚养成人,依旧可以浪漫地生活着。《浪漫的事》宋大妈和三个女儿对生活充满信心,快乐地生活。
韩国家庭剧中很少表现母亲形象的缺席,和女编剧有关,同时,母亲是孩子们精神退守的最后寄托。母亲的缺席,意味着孩子更多的孤独和痛苦。温情浪漫的韩国家庭剧,没有失去母亲的痛苦。
第二,生活弱者的颤音。
历史上穿着盔甲的父亲,是一个英雄和胜利男人的意象,永远不能被打败。在家庭剧生活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平凡的作为普通人的父亲,他们不再是英雄,生老病死,符合自然的规律;他们不再能养家,或找不到工作或年老体弱,需要得到照顾。父亲这时成了生活的弱者。
生活的弱者,是指在生存能力方面的弱者,它包括两个方面,社会生活方面和家庭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的弱者,逃避现实,中国家庭剧《大姐》中的父亲酗酒,逃避现实,消解了作为父亲的权威,而后父亲死亡,大姐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韩国家庭剧《加油!金顺》中金顺的公公没有了工作,《不良主妇》中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丘秀翰中失业,而崔美娜在丈夫失业之际,她刚好被丈夫的公司录取。父亲在社会生活方面生存能力的弱化是父性权威的最严重的失落。当然,在父性失落中,女性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和关爱。
家庭生活方面的弱者是指需要照顾的对象。生活的强者不仅仅是工作上的成功,面对困难决不妥协,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家庭生活方面的弱者是指不会照顾自己或不能照顾自己。《新结婚时代》中顾晓西的父亲顾教授每天拿着饭盒到食堂打饭回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活的弱者,一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肯定不是一个生活的强者。顾教授在妻子去世后一蹶不振,他更是一个弱者。
权威属于强者,作为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弱者的父亲,当然失去了父性的权威。
第三,父亲权利的剥夺。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鲁迅提出了作为父亲的三项基本要求,然而,在特殊的年代,父亲并没有作父亲的权利,他只是给孩子一个生命,没有机会和权利教育孩子。父亲权利的被剥夺,是父性权威在时代的失落。
传统视域中的父亲是护家的形象,没有了父亲,意味着失去安全感。韩国家庭剧中注重在家庭空间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较少关注时代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所以,在韩国家庭剧中还没有时代剥夺父亲权利的文本;而中国家庭剧不同,比较注重时代背景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对时代剥夺父亲权利、造成父性权威失落有一定的表现。
一是无力保护自己孩子的父亲。《渴望》中具有阳刚之气的知识分子罗冈在“文革”期间因为被追捕,万般无奈,他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人。他被抓捕,女儿下落不明,心理深深内疚。时代对于父性权利的剥夺和扼杀,使保护儿女的“父性”在特殊的岁月中重重失落。
二是儿女因父亲而受牵连。《渴望》中王沪生的父亲是某研究院的院长,因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离开家去“劳动改造”。王沪生因为父亲的问题,先到工厂改造,而毕业分配不能留在北京,必须到大西北。在中国特殊年代中,王沪生的父亲带给子女的不是养家、护家的胜利以及父亲的骄傲,而是批判父亲的风暴拆散了家庭、夺去了母亲的生命、带走了儿女的幸福。
时代剥夺了父亲的权利导致父性权威的失落。坎坷的人生、悲剧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第三,父亲沉重的罪身。
父亲,是孩子心中的骄傲。然而,父亲的行为构成了对孩子和家庭的极大伤害。内疚和忏悔、良心的谴责及道德的审判、不可饶恕的罪恶感,一直伴随着父亲。父亲,沉重的罪身,心灵的十字架、精神的重压,他的生活就是请求被人原谅,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赎罪。
抛弃孩子,无论被动抛弃还是主动抛弃,对于父亲来说,都是一种罪恶。《渴望》和韩国家庭剧《人鱼小姐》表现的是抛弃孩子的两种方式。《人鱼小姐》中的父亲是主动的抛弃,爱上了“新人”,抛弃了“旧人”和孩子。雅俐英对妹妹的一切报复(抢夺其爱人)行为的后果,父亲都认为是自己的罪恶所致。雅俐英对父亲最沉重的报复,粉碎了父性的权威,使父亲对不起两个家庭。二女儿知道真相后父亲的完美和高大的形象顷刻间轰然倒塌。父亲成为两个家庭的罪人,两个女儿不能原谅的人。雅俐英最终原谅了她父亲和继母,而雅俐英因为负罪感最后离开丈夫的选择和二女儿的不能生育预示着父亲的罪恶感还不可能退隐。
被动地放弃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对父亲来说是一种沉重的压抑,无法抹去的悲伤的记忆。父亲通过各种方式赎罪,然而,最终的赎罪还是无望的,这是中国家庭剧和韩国家庭剧的不同。《渴望》中的罗冈,时代让他放弃了孩子,使他背上了心灵的十字架。别人都能够理解罗冈,原谅罗冈,唯独被抛弃的孩子的母亲无法原谅。而罗冈最想得到的原谅就是孩子母亲的原谅。罗冈不断地通过别的方式赎罪,一是写小说,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抛弃孩子的那一段感动了多少青春男女,然而,王亚茹因为罗冈用自己的隐私和伤痛去换得别人的同情,是对自己的极不尊重,她更加不能原谅罗冈,所以罗冈的赎罪无效;二是小芳双腿伤残后,罗冈经常照顾小芳,接她放学、给她讲故事,给小芳这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一些父爱,试图减轻罪恶感。三是照顾慧芳,一个抚养自己女儿的恩人,一个高尚而完美的女人。这样就完成了自己的赎罪。不过就慧芳的性格和电视剧对她的完美塑造来说,慧芳是不可能和罗冈结婚的。罗冈的赎罪注定是无望的。
因为父亲的抛弃,孩子成为没有父亲的孩子。无论是主动抛弃还是被动抛弃,精神的创伤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或消失,而是更加深刻。父亲的罪恶感一直伴随着父亲的生活,韩国的父亲得到了女儿的原谅,而没有得到前妻的原谅(前妻带着对生活的怨恨离开了人世,一场大火夺去了双目失明的她的生命);中国的父亲没有得到爱人的原谅,而得到了别人的理解。
父亲的罪恶感不仅仅来自主动抛弃或被动放弃的孩子和家庭,还源于他行为上和道德上的污点。《加油!金顺》中金顺的叔叔借高利贷,作为父亲,没有养家、护家,却使家人陷入巨债和被逼债的恐慌中。《青青草》中英华的外公利用泰勇外公对他的信任,把钱窃为己有,导致泰勇外公的破产。噩梦的惊吓、恐惧和深深的罪恶感,使英华外公有时不敢面对自己的女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忏悔。道德上的污点使英华外公羞愧难当,泰勇母亲最终原谅了他,他带着自己的罪恶和别人对他的宽恕离开了人世。
中国家庭剧表现忏悔和赎罪的较少,而仅有的表现的忏悔又很难得到原谅。但是,如果是相似的情节在韩剧中可能会忏悔、得到宽恕。韩剧对人物的处理比较宽容,虽然有些人物做了一些让人难以容忍的事,但一般没有绝对的不能原谅的人,这些人物在电视剧的结尾都有一些忏悔的情节,最后他们得到了原谅。韩国家庭剧中的宽容有的已经超出了一般东方式谅解和宽厚的意义,这是受基督教等宗教文化影响的结果。
韩剧价值导向一向符合伦理道德,劝人为善。家庭剧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儒家道德,佛教的因果报应、基督教的赎罪等观念对电视剧的创作影响较大,剧中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是多种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使用“第三期儒教”概念说明现代儒教的国际性。他指出,第一期是儒教的胎动期,第二期是从宋朝开始到元明清朝的儒教复兴期。现在正处于第三期,它以儒教与西方哲学和宗教的和谐为其特征[3](P89)。处于儒教第三期的韩国文化,兼容了基督教文化,所以韩国电视剧中关于忏悔、赎罪和宽容的情节明显多于中国电视剧。
中韩家庭剧在父亲形象的缺席中表现母性的伟大和年轻一代的成长,父性的权威在生活弱者的颤音中和沉重的罪身中失落。中国家庭剧对时代剥夺父亲权利进行艺术上的审美表现,揭示了个人悲剧和时代悲剧的双重性。中韩家庭剧对赎罪中父性的失落表现有所不同,中国父亲赎罪的无望和韩国父亲赎罪的希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三、父性权威的历史追寻
父性权威在历史中高扬,在现实中失落。父性在历史中不断消失,一方面是历史不断进步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类弱化的标志。然而,也许正因为父性在现实中的失落促使人们回望历史、到历史中追寻父性的记忆。在对历史题材的表现中,“父性”“化作一段凝固的历史,沉淀为一种永恒的精神。对父亲的书写实质上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历史性沉入,通过沉思‘父亲’的历史保留在这个世界中逐渐消失的东西,并使之成为一种绝对的要求。”[4]和韩国相比,中国父性在现实中的失落比较明显,所以,对父性的心理渴求更加强烈,历史题材的家庭剧或家族剧中对父性的着力表现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补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与子是生命、价值关系。牟宗三先生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特质时说,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这是因为,父不止是子的自然生命的来源,而且也是子的文化生命乃至价值生命的来源。所以,父对于子来说,具有绝对的权威。
中国父性的失落和文化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抗传统文化,倡导西方民主自由。陈独秀在《东西方人民根本思想之差别》中提倡用个人主义代替家庭主义。他说,西方文明是强调个人奋斗的、民主的和尊重个人权利的。而注重家庭的东方文明要求个人服从于家庭的利益,剥夺了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妨碍了创造性的思维,这样就养成了依赖他人的心理。“父亲”代表着一种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作为传统的落后的和“吃人”文化的代表受到“儿子”们全面、彻底的清算。二是“文革”期间,再批传统文化,只讲“革命”,不讲家庭,父亲有“问题”,和“父亲”划清界限成为很多儿子们“明智”的“选择”。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格局呈现多元化,对家庭题材表现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末表现家庭题材的电视剧初露端倪,90年代不断发展,至今已经比较成熟。从家庭剧的表现中,我们发现,表现现实题材的家庭剧中父性呈现失落的态势,父亲的缺席、生活弱者的颤音、沉重的罪身、权利的剥夺等。在表现父子冲突时对绝对权威性进行了文化反思,试图建构一种理想型的具有平等意识的父慈子孝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和历史上的父性绝对的权威有着一定的不同。父性权威在历史的发展中重重地失落。
父性权威在现实的失落,使得编导把目光投向历史寻找父性高扬的时代,曾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的父性也只有回到历史才能找到当初的那种感觉。日本学者中山认为:“以慈爱坚强的父亲为中心的家庭,是将自己投影于父亲形象的一代男子所追求的一种理想。”[5]父性在现实题材家庭剧中失落,在历史题材家庭剧和家族剧中高扬,如《大宅门》《乔家大院》《大染坊》《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等。
战争年代是男人的年代,生意场和战场是男人的世界,历史题材的时空选择有利于对父性权威的表现。《大宅门》中的白老爷白萌堂在家里具有父性的权威,而且宽容、慈爱,在生意场上具有男人的力量和风度。《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亮剑》中的李云龙等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他们的身上尽显男人的风采。在对父性的历史叙述中,父性具有一种文化象征的意义。电视剧的父性是一种精神,果敢、阳刚而充满激情,现实的重压使人们疲于奔命,男性的阳刚和激情被生活和岁月销蚀,所以父性已经成为历史的梦想。原本充满华彩的生命在现实的压抑和心灵的幽闭中萎缩,对历史的追忆,是一种释放,一种涌动生命潜能的冲动,一种迫不及待的追寻。
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中国历史题材的家庭剧对父性的历史追寻,表明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心理。“父辈与子辈的复杂关系已构成了人类生存最深刻的部分,它往往体现出生命密码的递转和文化基因的重编,这种递转和重编并不就等于后来者和先在者的断裂和决绝,相反,倒有可能为后来者寻获新的生长点和支撑点。……儿子即使反抗一个具体的父亲,但父子等级秩序最终却得以保留。因为这种等级秩序业已成为文明历史的一种重要的象征形式。寻父同时也表明儿辈的一种自恋心理,那就是企图通过对父子等级秩序的重新认定来保护自我,确立自我。毕竟,父亲还标志着儿子生命的未来时态以及他的成熟形式。这是人类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之所以至今还在寻父的动因。”[6]人类总是会在失落中沉思,在沉思中追寻。父性的现实失落和历史追寻构成中国现实题材家庭剧和历史题材家庭剧的双重视野,在彼此对照的艺术表现中,可以看出观众双重的审美心理。父性的权威在现实失落中使其获得了审美的关注,对父性权威历史的追寻试图超越现实和历史发掘其中一种珍贵的精神内质,作为拯救我们这个软骨时代弱化生命的一味良药,达成对自我生命的时代确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