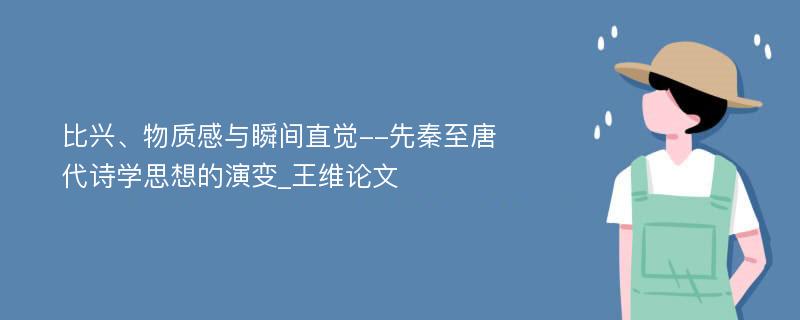
比兴、物感与刹那直观——先秦至唐诗思方式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唐诗论文,直观论文,刹那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中国美称诗国,诗言志、诗缘情是古人关于作诗缘起和目的的两大口号,而比、兴是作诗营构意象的三种基本方法中主要的两种(还有一种是赋)。比兴之说起于先秦,几乎在一开始就给中国人的诗思下了方法论的定义。然而,正如钟嵘所断言,古代诗歌中向来有一些极佳的篇什,读来就如“即目所见”、“皆由直寻”。到了唐代,大量小诗饶于意境,却是不用比兴的。那末,这些非比兴的诗歌其诗思有何特点呢?如果说它们是诗中上品,佳处又何在呢?本文将以先秦至唐若干有代表性的诗歌为个案,结合此一时期诗歌观念以及哲学上时间意识的演变,对这一现象试作深度推究。
一、比兴方法的基本分析
比是比喻,兴是兴起。
《周礼·春官》提出“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比、兴居其中,显然属于诗教传统。汉《毛诗序》以为,无论是“上以风化下”还是“下以风刺上”,都要“主文而谲谏”,即便是“吟情性”,也须“发乎情,止乎礼义”。正如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所云:“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从诗思角度看,比使诗人所拟宣说的理得以附着,兴使诗人所欲发抒的情得以激起。梁钟嵘《诗品序》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也是看重比兴尤其是兴的起情作用。
刘勰还说:“兴之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比兴不同,但是刘勰都用同一个词来定义:取类。这说明,比兴方法其实质是类比。类比的目的在引发联想。作诗者和读诗者的联想由类比所勾起。例如,在先秦被“断章取义”的诗句是作为外交辞令的,这是类比联想中最实用的一种(这可能是最早的兴,不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本文所关注的类比联想主要是指古代诗人将人与自然相联系的传统。可以大别为两种,其一是道德主义,称为“比德”,比较、联想的重心在人的德性。孔子以为道德人格“兴于诗”(《泰伯》),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又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显然,诗歌之联想德性的意义是孔子最为重视的。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联想往往建基于对自然物的观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孔子作过不少类似有名的“比德”,这在古代中国是形成为传统的。屈原作《离骚》,描绘一个众多香花的世界:“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兰花成为他人格的象征(空谷幽兰)。诗人的他“发愤以抒情”(《惜颂》),是与大自然紧密相联的。比喻重复多次,自然物就可能成为德性的象征,如中国诗画中人格化了的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等等。这些,基本属于“比德”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亲和自然的倾向。
类比联想的另一种是自然主义。起初具有泛神论的倾向,如庄子《齐物论》的“天籁”。这种类比并不主张将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明晰区分,恰恰相反,它往往消弭两者间的紧张,使人无条件地与自然为一。亲和自然是这种类比最主要的特点,对德性的关注趋于淡化甚至消亡,人的情感通过诗歌的内在节奏和意象运动得到升华。
就诗歌而论,我们可以见到,虽然同属类比联想,兴较之于比,人与自然的亲和程度要更甚。“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关雎》)用了兴法,男女恋情得到自然之物的隐喻,更为亲切。兴法可以淡化隐喻的作意,淡化愈加成功,自然主义就显得愈加纯粹。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诗经》中最好的兴诗之一,极富意味,且朴质,后人所谓情,所谓景,无从分别。尽管意在求偶,然而男女双方却与自然之芦苇、霜露、河流、小道无间然。诗人眼中的自然,就是情之土壤。
汉代以降,人们普遍以为自然的变迁足以感召人,汉人诗中之兴大量地表现为人对自然节候变迁的感怀。
秋风起兮云飞扬,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刘彻《秋风辞》)
这首诗仍受楚辞的较大影响,但讲人生乐极生悲和由壮至老的转换则明显是与秋风作着联想。这种倾向到古诗十九首就表现为极致。楚辞的影响不见了,诗风趋于朴素,比喻也较少使用,诗中主人公的心境总是与自然界的变迁形影相随。
迥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诗十九首》)
读汉代的古诗,可以更多地体会到诗思被自然所勾起以及与此相联系着的对个体生存境况的忧思。这种倾向十分强大,一直延续到了魏晋以后。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曹植《赠白马王彪》其四)
此诗末尾“感物”一词大可注意。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变迁感召人的观念深入人心,表现在诗学上,就形成了著名的物感说。它以为自然现象对文人创作有触兴、起情的作用。所谓“物感”,极为典型地体现了古代诗人将自己与自然作类比联想的传统。以下我们将看到,物感说作为比兴方法的延伸和深化,构成了古代诗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二、“物感”所引导的倾向:感知优先于抒情
进入南朝,古代诗歌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曰“声色大开”。清沈德潜《说诗语》断言“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提出南朝宋以后诗歌发生了一个转换,“声色大开”是与“性情渐隐”对举而言的。一“开”一“隐”,诗人对声(听觉)与色(视觉)的关注更甚于对性与情的关注。事实上,所谓“声色大开”的局面是由长期的“物感”经验所引发的。
西晋文学家陆机是诗文论上物感说较早的倡导者,他著名的《文赋》中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叹”“思”“悲”“喜”,种种情绪被春夏秋冬四时及自然景观勾起。正所谓“悲情触物感”(陆机《赴洛道中作》)。
东晋玄学家孙绰论诗,也提出了“物感”和“触兴”的观念:“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闲步于林野,则潦落之志兴。……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旦之足,当百年之盛。”(《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很清楚,这里所谓的“物感”和“触兴”,是人的“所遇”(心中因自身境遇而积聚之情感)赖与物相触而兴发为情感,所以人就可以“借山水以化其郁结”。“物感”和“触兴”,两者意思一样。
“物感”现象被诗学家们所严重关注,齐梁间刘勰的名著《文心雕龙》为此专设《物色》一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钟嵘《诗品序》也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个人与自然之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形成一种“联类”的对话关系。“物感”活动则构成双方对话展开的一个场。
“物感”或“触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极为突出的感性经验,它并不表现为繁复的想象,而是十分简捷的联想和感悟,营构意象多用白描手法。它们是感物、悲秋、咏怀,是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情以物迁……由于讲究对自然万象的流连视听,“写气图貌”和“属采附声”,作为诗歌目的的抒情也开始趋向简洁然而不易把捉的感悟。于是出现如下转机:感知优先于抒情。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都以自然为对象,并非偶然。
陶渊明的两首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陶渊明生活在田园之中,与自然为邻,亲自从事劳作,有意思的是,他的诗几乎不用比兴。那么“物感”还有没有呢?当然有,作为自然的“物”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逍遥优游,一切亲切无比,因而亦不必刻意去“感”,只须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既不在诗中抒情,也无须着意表现自我,他与自然全然为一。
如果说陶氏诗歌纯为白描,那么谢灵运的诗歌就正好相反,刻画繁富。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励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谢诗的基本模式,是描述作者在大自然中的游历过程及其感悟。他的诗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变得复杂起来,既要在游览中观物,又欲借观物以悟理,两者水乳交融的境界很难达到,读来自然就难有浑然一体之感。读谢的诗,读者须要准备一份同情的态度,方能与之共鸣。而此共鸣大多赖诗中的“迥句”或“秀句”(钟嵘评语,后者为评谢脁诗语)加以引发。
值得注意的是,谢诗也近于陶诗,极少用比兴,仅用典稍多。他一方面慨叹“表灵物莫赏”(《登江中孤屿》),“妙物莫为赏”(《夜宿石门诗》),以为人们对自然的灵妙之处未能欣赏,另一方面又自称“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悲哉行》),“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邻里相送至方山》),继承了“物感”的传统。他诗中的迥秀之句,如“云日相晖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过始宁墅》),“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等,都是调动自己的视听感官,对自然的声色作第一次、面对面、细致的审美静观之产物,它是独一无二的,新鲜生动的,因此无须调动比喻,而且往往位于诗的中后段,也没有起兴的作用。钟嵘认为谢诗“寓目辄书”,宋叶梦得与钟氏同意: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石林诗话》卷中)
中国的诗歌发展到谢灵运,自然的山水景物开始具有某种现象学的意义,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或陶渊明诗的那种朴素,也决非使人感觉十分地可亲,足以真正地寄托于斯。人如果对它的灵妙之处采取观的态度,那么它可以使人“一悟得所遣”。“寓目辄书”和“猝然相遇”之说若是不错,那么这种得于自然之悟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兴,它建基于对自然变迁的静观。
这里,我们把谢与陶从“物感”的角度作一比较,是颇有意思的。陶氏把自然视作家园,他的生命融于自然的节候节奏,两者浑然一体,而谢氏却把自然作为游观的对象,在游览的过程中为某一灵妙景观所摄住,驻足静观。谢诗中诗思与景物之间存在某种紧张,赖迥秀之句消弥之。陶氏心目中的田园是实的,而谢氏心目中的山水却是虚的。在前者,亲和自然即是悟,在后者,悟在亲和自然之后,亲和是悟的条件,却不是悟本身。前者为纯粹的自然主义,后者则在自然主义之外更添上一重意象主义的意味。这就是陶诗意象中之可亲的田园与谢诗意象中之可观(悟)的山水之区别所在。
中国诗歌史上陶谢并称,二人分别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的传统。发生于田园与山水中的诗歌运动,它的目的不再是简单的抒情,而是在于更直接地感知自然和体认自我。而且,从陶的田园到谢的山水,“物感”经验终于透进一层,不仅感知因素(声色)开始重于抒情因素(性情),而且相应地亲和自然也开始向感悟自然转化。古代诗人的感性经验不期然地走到了质变的前夜。
三、时间意识的根本转变
谢灵运诗中挺出的迥秀之句,把游山玩水提升到审美静观的水平,同时也把传统意义上浑然的诗歌整体给解散了。迥秀之句成为一个清晰、优美的意象,一个相对于诗中游览之动却属静止的景观。它们使诗人逗留于斯,得感悟,也让读者流连于斯,获美感。如果说谢氏骨子里并不与自然亲和,那么迥秀之句就标志着人对自然作审美静观的一种新姿态。审美静观是刹那直观。从此,“观”胜于“游”。“游”的经验基于动的时间意识,“观”的经验则基于静的时间意识。后者是一种新的看世界和看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魏晋以后古人时间意识的变化作一简要描述。
先看魏晋著名玄学家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中表现的时间意识:
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为故;舟日易矣,而视之若旧;山日更矣,而视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庄子·大宗师)注)
《庄子注》讲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认为物体在此一瞬间处于这个位置,在下一个瞬间就转到另一个位置,于是运动就被看作是无数刹那生灭状态的连续。一切事物都没有稳定的质的规定性。在这“日新之流”中,什么都留不住,一切现象即生即灭,交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这种运动观,实际上是对运动变化作了静观的描绘。
这一新的时间意识,将庄子所感叹把握不住的时间之流作了静态的分割,首肯物在时空当中存在之个体性和特殊性(短暂的时空规定),因此众多自然现象就可以被当作审美观照的对象而孤立起来(即所谓“独化”),而同时它们又是无为、无形地在时间之流中“玄合”着的(互相有关联)。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由庄子式大气磅礴的“天籁”(无所不包的交响乐,无限绵延、无限广延)朝向对自然物的个别静观之转化,从此具备了条件,而所谓的诗中迥秀之句,就是这种时间意识影响下的产物。
时间意识更重大的变化是,佛教带进来“空”的哲学。这我们以杰出的中道哲学家僧肇的理论为例来说明。他的非有非无的空观和静止的时间观为玄学美学的佛学化打下了哲学的基础。他的《物不迁论》专门阐发大乘佛教的时间意识,说:“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复何怪哉?”
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仍是先秦辩者“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其实,却是一种很典型的大乘佛教的观物法。认为过去不能延续到今天,今天也不是从过去而来,事物之间不相往来,也没有变迁,世界永恒寂静。“法”本无相常住,一切事相都是“缘起”而有,时空中的自然和生命纽带中断了。
这种时间意识能够从宏观上把运动看破,宣称让庄子(包括儒家)惊叹不置的大化流行(变化中的自然)全然是假象。乾坤倒覆,不能说它不静,洪流滔天,不能说它是动。推论到极点,就会走到以完全静止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以为有相不过是对无相之实相的证明。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把时间和绵延给否定了。这一时间意识,体现了佛教自然观真正的本质。而且此种观照所形成的意象,因为将动静相对的两极统一到了一起,极为鲜明生动,显出一种全然不同于庄子和“世说新语时代”的美。
向郭和僧肇两者的时间意识都以静释动,是一致的。而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肯定世界的第一原理是“有即化”,存在一个刹那生灭的日新之流,主张人们应该“与化为体”即任化,并否认有一个造物主或绝对本体(甚至像王弼所说的那种“无”),而后者以为世界的第一原理是“至虚无生”,空静是绝对永恒的,只不过应该借万物的变化来揭示和体认这一寂灭实相,化不能作为体,却可以“即万物之自虚”,通过万化(用)来观空无的体。因此,向郭的“任化”就转变为僧肇的“观化”,观化是为了把握永恒的不变者(不化即不迁)。
以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为开端,又经过大乘佛教空观的大力熏染,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发生了本质变化。原先在儒道两家俱不争的事实,即自然实存的真实时空,生命的大化流行,开始受到根本的怀疑和冲击,甚而至于将宇宙全然看空。于是,时空脱出浑沌,也不再连贯。动态的时间之流(绵延)被分割为互不相干的连续而细小的静态,相应地,浑然一体的空间(广延)也解散为无数的小块。我们看到,庄子眼中大气磅礴的自然(“大”)在魏晋时渐次分解为园林、山水等视听知觉直接所对的小型景观(此过程从《世说新语》开始,到大小谢则体现于诗中迥秀之句……),中国人的感知方式发生基础之变。空的时间意识,使得感知优先于抒情成为不可逆转的诗学趋势。
四、王维小诗的意义:刹那直观
上述时间意识的变化,导致自然和自我在刹那直观下的完全融合,主客不再分家。可以想象,比喻和起兴所必需的类比联想之过程,可能障蔽刹那直观,从而导致诗歌意义的丢失。我们将看到,在王维的小诗中,比与兴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刹那直观。诗歌意象最终深化为纯粹现象。
王维在自己的诗中,多次提到“安禅”,确实,读王维的许多诗,感觉他就像一位主定喜静的北宗禅师,长于以空的直观来感受这个世界。他的《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云:
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幻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色空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物方酌我于无垠之域,亦已殆矣。……道无不在,物何足忘。
在王维,色与空并非两个东西。迷执(舍)于色空,是幻,脱离(离)开色空,也是幻。最高的境界,是不执着并超越色空的分际,这样,“物方酌我于无垠之域”。“至人”,他执持一种不避尘世之物的空的直观。于是,我们当可以理解王维小诗中山水的崭新意义。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
这首诗描述秋天诗人山居的见闻,是以声色对举和交替的方式进行的。看中间两联,明月照在松林,山中极为静谧,但见清清泉水在石头上流过,这句似乎是写色,其实暗含了声,一个“流”字,发出了声响,给整句诗灌注了生气。下一句相反,似乎是为了与上句“流”字相呼应,先出来一个“喧”字,竹林在闹,浣纱女归来了,水面上碧绿的莲叶粉红的莲花浮动起来,渔舟也返回了,此一“动”字写色,其实也暗含了声,但因“喧”字在先,诗人有意将渔舟划过水面的声像弱化以强化莲动的视象。四句诗,首尾重于写形色,中间偏于写动静,声色相得益彰,内在节奏感极强。诗中没有比喻,也无须起兴(末句虽用了典,但不知出典无碍阅读)。
读王维的山水诗,值得注意的是,山与水的声响、色彩和动静,总之几乎自然界的一切丰蕴和生动,都可以在诗中涌现。王氏尤其长于声色对举,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林下水声喧语笑,岩间树色隐房栊”(《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谷静泉逾响,山深日易斜”(《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细枝风响乱,疏影月光寒”(《沈十四拾遗新竹生读经处同诸公之作》)……这些对句都是极佳的诗句,它们的出现当与禅宗对声色现象的重视有关。可见,空观下的自然决不给人以枯淡之感。
王维诗极喜写“空山”,除了《山居秋暝》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还有: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鹿柴》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以人语反衬山之空静。《鸟鸣涧》则以人之闲、夜之静来托出山之空。山之所以空,正是因为它闲和静。山之空是人对它之动态作静观而得之感悟。比兴亦未在两诗中出现。
王维诗中多有“闲”字,如:“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春日上方即事》)从对自然的审美经验上看,“闲”的意义是把自然看空:
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
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登河北城楼作》)
前一句描写冬雪之夜,飞雪从天空(“空”)洒落,深巷一片寂静,雪花堆积于宽广的庭院,使人感受到“闲”。“闲”与“空”“静”是相通的。后一句描写登城楼远望所见,天地间暮色寂寥,而诗人的心即与苍茫无际的江流化为一体,其感受也是“闲”。空观下的自然所给予人的就是“闲”的感性经验,它使诗人对自然界的静谧(寂灭)具有极度的敏感,缘此,所作诗歌往往臻于极高的审美境界: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王维将佛教典故溶入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几臻天衣无缝的境界。如他的《华子冈》是一首艺术水平极高的小诗:
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
诗中“飞鸟”二字来自许多佛经中均可见的一个譬喻。《涅槃经》云:“如鸟飞空,迹不可寻。”不过,“飞鸟无迹”之空的喻义在诗中已经极其淡化,赫然在目,就是一个鸟飞去的直观意象,然而,挡不住的寂灭感却充盈全诗并弥漫开来。此“情”虽以惆怅名之,却并非世俗的喜怒哀乐爱憎惭惧,而是涅槃之寂灭感。此寂灭感与空的直观刹那生灭,并不需要一个起兴的过程来蓄意地挑起它(恢复忆念)。有意思的是,对空的类比式的联想之消失,反而强化了空观,且有助于读者执持一种当下的、超然的、直接的态度以迎迓诗的美感。柳宗元著名的《江雪》亦应如是读: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中也是以鸟飞之迹和人行之踪的绝灭来直观地表象自己的寂灭之感,这个自我就是诗歌后两句中孤独的钓者。就是诗中的雪,读者虽不妨把它与佛入雪山的典故作一联想,但它依然仅是一个纯粹直观,且意味无穷。
王维的小诗中,比兴已难寻觅,原因何在?我以为,那是因为小诗所描写的,是自然界的声色动静,它们并非纯然客观的物,而是看空之人所观的“色相”。正所谓“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正是因为物或尘世不可忘,自然界具有全部的生动,“道无不在”,诗人才得以透过色以观空。王维的小诗把自然成功地刹那直观作纯粹现象,这,就是最初也是最出色的意境。
五、简短的结论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绝妙、最有深度的诗思不假道于比兴,也不走象征一路。中国古人的诗歌经验,最让人击节叹赏的,是刹那间的感悟。它固然是一种心境,不过,作为纯粹现象,它却建基于针对自然之物声色动静的刹那直观。由于无关于比兴,它已然失去了类比之物和所兴之情。没有联想的诗思,似乎是迷失了方向。然而,它竟然让自然之无穷静动在诗中凝定为刹那之境,既纯粹之至,又丰蕴无比,谜一样魅人,不可思议。这,或许就是意境的妙处及深度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