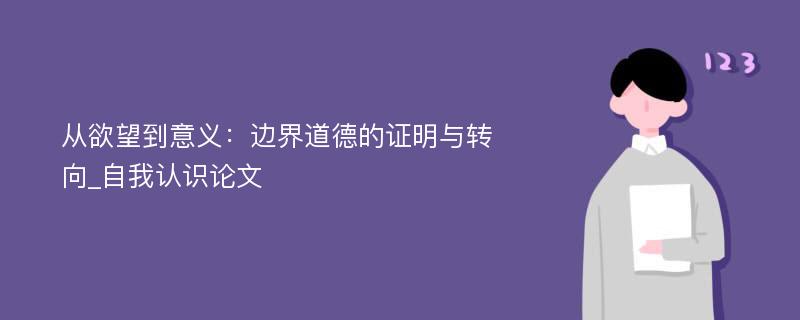
从意欲到意义:边界道德的证明及其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道德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26[2008]03-0076-05
一、概念与问题:边界道德的逻辑定位
边界道德是人们在精神实践中形成的一种道德形态,它被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来探讨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充其量被当作一个和个体的精神生活特别是虚幻道德生活相联系的概念来使用或者在空谈道德、反道德的意义上被误用或滥用。这就涉及到这个概念怎样定义,它在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哪些隐含积极价值的真问题,而厘清这些问题是正确定位边界道德、促使其转向正向价值的逻辑前提。
1.边界道德的概念
道德是人的道德。边界道德也是人的道德,它就像衣、食、住、穿一样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中。边界道德有四个否定性的结构定位:(1)不是虚幻的道德;(2)不是道德的虚幻性;(3)不是非存在的道德;(4)不是“边缘”的道德。分述如次:
所谓“不是虚幻的道德”,是指在它的对立面的道德被经验到、被实在践履,而它却被社会主体遮蔽起来或者被个体主体隐蔽起来,这种被社会主体遮蔽起来的道德存在是受普遍压抑的道德情绪、道德意志,而这种受个体主体隐蔽的道德存在是个体自我的理性强制和非理性释放的特殊表达。前者一般地涵括后者,后者个别地映现前者。
所谓“不是道德的虚幻性”,这种道德形态不是某种神灵的定制,不是某种外来的异物,也不是人们虚拟的谋划,它和实体道德以实存的状态相对立而显现其虚存的状态,或以隐遁的方式奠立其实存的状态。边界道德否定虚幻性是在存在样态、方式上被使用的,它否定那种纯粹以虚存方式存在的道德形态。
所谓“不是非存在的道德”,首先,非存在的道德是指根本不存在的道德,至少在人们可能认识的领域里都被断定为非有、实无,毫不可能、绝对的无;其次,基于这样的认识,这种道德是指并非根本不存在的道德,至少在人们可能认识的领域里可能存在,并以虚有的状态潜存,在从虚有到实有的路途上生息,因而它不是毫不可能、绝对的无,在人的外界环境和内心环境的变化条件下,随时可能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所谓“不是‘边缘’的道德”,实质是前面所述关于边界道德的三个否定性判定的延伸和显见,成为它每个历程中的“此在”。不是“边缘”,意谓边界道德可能从潜在向虚在、实在和从潜存向虚存、实存的方向运动,只是它生存的条件、环境还没有让它齐整、全体露面,它的生存的方式被历史的迷雾所笼罩或者被人为的压制所遮蔽,或者被社会的主流规范所产生的强制驱逐到生活世界的某些角落,以至在人的自我压制中消解到潜意识的深渊罢了。
概括之,边界道德是指现实的人在扭曲、变异道德意识心态、道德理想信念、道德信仰人格基础上以深层化的潜存、表象化的虚存或隐蔽化的实存等方式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并与显在的正常化、规制化的实体道德相依存又相区别的道德虚践形态。正是在现代性进展的生活世界中,产生了种种消解人的生活意义的边界道德问题。
2.边界道德的问题
在明确边界道德的概念基础上,边界道德的问题主要是指:概念存在与事实存在不一致引起的道德现象问题,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不统一凸现的道德界线问题。前者反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扭曲,后者反映为信念与责任、义务与权利的关系的背离。两者都深层地潜存着压抑和侵蚀属人价值的实现的意欲。
首先,边界道德反映了由概念存在与事实存在不一致而引起的道德现象问题。道德离不开行动者本身的道德性。边界道德也离不开行动者本身,但是却偏离了完整的道德性,只不过这种偏离还没有跨越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问题还不在于这种偏离程度多高,倒是在于这种偏离程度并不为与行动者相关联的“他者”所及时了解、体悟和把握到。之所以如此,并非这些“他者”知识不够、觉悟力不足,而是边界道德涉及的意向概念和理智事实、应然的承诺与本然的现实不一致,而且这种不一致并不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域或狭窄的区域内,因此即使这些“他者”体察到了边界道德带来的压抑、无奈、失望,也无济于事。在行动者那边,他并不考虑意向概念和理智事实不一致的必然后果,并不考虑应然的承诺和本然的现实之间逻辑联系产生的生活价值,这样,无论是对行动者个人还是对与他相关联的“他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都被扭曲为意识和意欲的隔离、表达和表征的分离、概念和事实的断裂。费希特就曾指出这样的人:“我周围的人们不应当变得更聪明和更优秀……我不愿变得更文明,我不愿变得更高尚;黑暗与撒谎是我天生的爱好,我愿使尽最后力量,不使自己放弃这个爱好”。[2]毫无疑问,现当代社会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探讨边界道德的问题不成了一个荒谬的假问题吗?姑且不论现代社会有多少这样的人,问题也并不在于有多少这样的人被历史地“观”到或现实地“看”到,而在于问题的这个提法,既揭发了从边界道德产生出来的那种“不协调的非人格力量”[3],又揭示了由概念存在与事实存在的不一致引起的道德问题,由此呈现出边界道德的种种样态及构筑其上的人的生存根基。
其次,边界道德反映了由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不统一而凸现的道德界线问题。从哲学解释学考察,边界道德的存在不仅是一个“概念”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对于与边界道德相联系的人以及这些人的各种关系的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所谓合理性,“便是人之理性”[4],就是“人的思想和信念”的理性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从人的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的。合乎道德理性,是概念关系的理性,即是从概念、理念上把握了来自个人愿意不愿意的意识存在、精神存在的理性;合乎实践理性,是实体关系的理性,则是从实际、行动上把握了来自个人做与不做的事实存在、价值存在的理性。如果仅仅从概念、理念出发去考虑个人的道德理性,或者仅仅从实际、行动出发去考虑个人的实践理性,而不是从概念与实际、理念与行动的统一,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上出发,那么前者因为空谈信念伦理规则、泛化义务条件,其结果必然堕入道德个人主义、道德理想主义,而后者因为放弃责任伦理规范、抬高权利衡重,其结局则可能陷进道德自由主义、价值绝对主义。两者都是对单元价值的独占、对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离。深一层考察,这种分离,实质是道德实践界线的分离。道德不再是实践道德理性的道德,就会形成抽象、虚幻的道德情景,实践也不再是具有道德理性的实践,就会走向非公正、非理性的冒险行动。“一个人不理会,不愿意为自己的思想行为寻找根据,甚至不以任何东西为根据来思想和行动,那便是非理性的思想和行动”。非理性的思想和行动,总的根源在于强调了个人“意识的优先性”、个体“经验的优先性”,这些优先性也“包括特殊社会团体的超个人的经验、观念和愿望”[5]。换言之,具有优先性的个人意识、个体经验,总是反映个人那些主观性、理想性的东西,也就是尼?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一种将自己抛在外面的客观化”[6]现象。这样,只讲人的主观性、个体性,排斥人的客观性、社会性,“无视决定个人行动和心理态势的社会因素”[7]就成为非理性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成为边界道德行动者作出非理性道德选择,滑向虚幻道德实践的深层根据。
迄今为止,边界道德的问题并没有从日常生活世界消除,一定程度上它还渗透到非日常生活世界,从而引起人们深入反思。反思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向度展开:一是怎样消解边界道德所蕴含的压抑人、蒙蔽人的外在意欲;二是怎样把握边界道德所孕生的否定自我、颠覆自我的内在意欲,使之转变为属人价值的存在,即转变为充实人的正向价值。这就涉及到了边界道德的两维意欲的证明问题。
二、意欲的两维:边界道德的复合证明
人的意欲可以区分为外在意欲和内在意欲,这是意欲的一维;而外在意欲和内在意欲各自又可以细分出消极意欲、积极意欲,这是意欲的另一维。边界道德可以看作是人的两维意欲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克服的产物。因此,只有对边界道德的两维意欲作出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复合证明,才能找出其积极意欲实现转向的可能条件。
(一)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从二重性存在到沉淀性存在的存在论证明
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现实中表现为侵蚀真实、欺凌真诚、揶揄真情等消极样态,理论上表现为“耻言理想、蔑视道德、躲避崇高”[8]的存在形态。因此,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体现出两个特征:
1.消极意欲是蕴含恶德的二重性存在
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是蕴涵恶德的意欲。它并不是超验的精神存在,而是可以被人直接经验到的东西,只是被经验到的是消极的、背离人的意欲。
首先,消极意欲是人的经验性的潜存。一方面,消极意欲是可以被人经验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和消极意识有着紧密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9],就是说,意识是可以被人经验到的实在的反映。马尔库塞则指出:“如果真的东西(逻各斯,理念)是实际存在的,那么直接经验的实在就分有了非存在,分有了不现实的东西。然而,这一非存在是存在着的,而且对于直接经验(对于多数人而言它是独一无二的实在),它是惟一存在着的实在。”依照这样的逻辑,消极意欲也表现了人的意识世界的“双向度结构”:其一,消极意欲从人的经验世界中“分有了非存在,分有了不现实的东西”;其二,消极意欲是被直接经验证实的,对个体人而言“它是惟一存在着的实在”。正因为某些人有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实在”,才把它看作是“真的东西”或成为“真的东西”,进而成为他们行动所遵循的道德支撑。另一方面,消极意欲是不完全被人清除的东西。在康德看来,人们不可能“完全清除来自经验的杂质,去掉出自浮夸或利己之心的虚饰”[10],基于这样的理由,“德性的真实面目”就不会自动显示出来,相反地,显示出来的却是与之对立的、背离人的道德意欲即消极意欲。
其次,消极意欲是恶的二重性的颠覆。消极意欲的“恶”是令人压抑的、厌倦的东西,在现实的人那里,它要发生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二重“颠覆”。其一,这种恶的存在是恶的欲念存在,这种欲念在当下并不一定被人们经验到,但是它会在行为主体的思想意识里映现或闪现,随着这种欲念的出现同时,它能够为外在意欲的积极意欲所抑制。这样的意欲过程是人的外在意欲的不自觉的“颠覆”。其二,恶的欲念的闪现往往伴随着积极意欲的出现,而积极意欲的出现必然趋向于抑制恶的欲念。黑格尔指出:“道德的东西必须在广义上来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它就不止是意味着道德上的善……道德的东西在这里具有一种就其在一般意志内部而言的意志规定性,并因而在自身里包含有故意和意图,以及道德上的恶”[11]。就是说,“道德上的恶”只是“包含有故意和意图”的潜在的恶,这种恶,除非它体现为现实行动上的非善即造成恶的结果,否则就还只是“把自己撕裂成为两个对立面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异化,使自己成为既是自己又是他物”[12],就还只是边界道德的内在意欲中的消极意欲和积极意欲之间具有倾向性的正常角力。这样的意欲过程是人的内在意欲的自觉的“颠覆”。
第三,消极意欲是善的消蚀性的存在。人是“感性的人”、“现实的个人”,这样的人就有既相互对立、又自我颠覆的意欲。就像柏拉图把人区分为可见的“外在的人”和不可见的“内在的人”[13]那样,边界道德被人的经验证明为潜在的同时,也就证明有一种东西与潜在相对应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从行动者的思想意识里分有的虚在,也就是消蚀善的意欲的消极意欲。这种意欲由于具有定在的非定性、潜在的隐蔽性、存在的短暂性等特性,往往造成人们把边界道德内在意欲的消极意欲的恶的表现和实体道德的善的取向混淆在一起,从而使作为律令的道德、规范的道德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造成人们把边界道德外在意欲的消极意欲的恶的表现和行为主体的善的意志混淆在一起,从而使作为理念的道德、宽容的道德不时遭遇世俗挑战,甚至为流俗所笑话而孤立。以上情形最后导致边界道德成了消蚀善德的不良存在,一方面这种社会后果被多数人们所忽视,另一方面这种消极意欲被当作非存在的东西而遮蔽。
2.消极意欲是隐入主体的沉淀性存在
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在外观上,它表现为内在意志的外在性,是社会主体遮蔽了的消极道德存在;在内观上,它表现为外在行为的内在性,是个体主体隐蔽了的道德虚践存在,因而它是隐入道德主体的沉淀性存在形态。
首先,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呈现隐蔽的虚在性。边界道德是被人们遮蔽的消极存在,它看到自己的潜在处境,这种处境使它不便于“抛头露面”,因为它“分有了不现实的东西”的缘故。所谓“不现实”,是指在常识的、世俗的看法中,它等同于“不实际”、“不可能”,至少是“难于现实化”或者“可能性很小”的意谓。而在“现实的人”的内在意欲中,积极意欲和消极意欲作为两个对立面开始时总是处于沉静的状态,消极意欲逼于“不现实”的境域而通过自我隐蔽来“实现”存在,这种存在的实现又是被人遮蔽的“现实”。正是在这种境域中,个体人形成了作为“内在的人”的压抑性的道德生活,反映了作为“外在的人”的多面性的生存方式。这种道德生活、生存方式,既是消极性的现实,即虚无现实,又是确切性的现实,即非现实的现实,因而,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是向现实敞开的潜存的虚在。进而言之,人们能够考察、评判既成事实的“伪君子”道德现象从而理解它的存在样态,在此基础上重建矫正性的道德规范,重塑崇高性的道德理想;对未有发现、尚被遮蔽的边界道德现象则不会去主观臆测、作出道德评判,从而不会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律令、道德理念的框架体系。这就说明,沉寂性、遮蔽性、虚在性是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的存在特性。
其次,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呈现沉淀的实在性。未经审查的道德是非理性的道德。边界道德就是这样的未经思想批判和生活审查而存的虚在,但它并不是全体虚无。边界道德的虚在,在于它是不成完形的,因为在它的外在意欲中的消极意欲占有、掩盖了其中的积极意欲就外显了;也在于它是不足理性的,因为在它的内在意欲中的积极意欲还没有占有、改造消极意欲就露面了。对现实的人来说,这种未经文化批判和生活检审就外显、露面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虚无的东西,“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14]沉淀下来;对意欲存在来说,边界道德的内在意欲和外在意欲之两维中的消极意欲暂时压倒了积极意欲,从而导致它以消极的面貌悬浮出来。就像真理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是一个渐进的、发现过程一样,两者是相似的道理。真理是客观的,但它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观性,最初我们并不能捉摸到、感受到它的存在。这是因为真理所蕴含的潜能还没有被挖掘、发挥出来,它的核心元素、价值因子还没有被拯救出来的缘故。真理的这种特殊性和意欲的这种沉淀性有着一定的通约性。就是说,边界道德作为非虚无的实在性内涵及其作为实在的潜在性元素,因其消极面凸现而被再度遮蔽了。这时,在以人的价值域为核心的真理观和道德观的关系视野中进一步考察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就非常必要。
(二)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从道德观场域到真理观场域的认识论证明
从道德观场域到真理观场域探讨人们以什么方式认识边界道德的内涵、状态所作的逻辑证明,就是边界道德的认识论证明。这种证明,一要解决人们认识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的方式问题;二要把握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的内蕴问题。前者是把握边界道德的内蕴存在的认识论前提,后者是怎样从其积极意欲中析出生活价值的问题。
1.从道德观和真理观的相互关系来认识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
随着人的活动的展开,人的内在意欲和外在意欲就会进入紧张的相持关系,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也必然在它的虚无性一面的背后呈现出它的实在性一面,即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虚无性“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所谓“否定的意义”,就是否定它自身的劣根性的自觉性;所谓“肯定的意义”,就是肯定它自身的对象性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要从道德观和真理观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认识。
首先,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渴望真理之光的普照。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包含内在意欲的真实的自善意欲,外在意欲的真诚的善他意欲,及其二者相和谐的圆善意欲,这些意欲有赖于真理观立场中得到澄明。在福柯看来,“真理就是让主体澄明的东西”[15],只有让主体“改变自己”、“转换自己”才能达至真理,反过来说,走向并最终达至真理是主体的意欲的精神性要求。一方面,真理是涵容道德存在的高能形式,在真理成为它自己之前包含着道德的实在和虚在,既包含实体道德的善的德性,也包含边界道德的恶的德性;另一方面,道德存在是发展真理的精神支撑,实体道德尊重真理元素的道德设计,边界道德也为导向真理提供反面素材,包孕真理种子。因此,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作为“主体自身的存在”,作为实体道德的潜在,作为真理成长的中介物,它渴望真理之光之普照以明确自己重生的可能价值。
其次,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期盼真理意义的拯救。道德的可能性就像真理的可能性。边界道德转向的可能性就像皈依真理的可能性。真理就是要促使潜在的真“出场”、“显身”,激发善的虚在向实在的善转变,推动美的潜能向现实的美转换。一方面,在原初意义上,边界道德期盼相对真理的启蒙、指引。这是由于它的积极意欲是暂时未被发现、肯定、确认的实在,这种意欲的充实程度、完善程度尚未达到“显在”和“出脱”的地步。另一方面,在潜存的意义上,边界道德依借一定的边界为中介、作过渡。它的存在首先是虚存、虚在,然后经历潜在、实在,之后被人认识和把握,最后实现为真的现实存在。因此,就像真理并不是即刻生成、轻易获得的那样,把握和拯救边界道德积极意欲的工作,必然是一个求真与求善相统一的过程,是一个从消极价值转向积极价值的复杂的过程。
2.从道德化真理与真理化道德中析出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
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的外化、出场,表现为人的求真意识的外显、求善活动的展开。因此,建立在一定合法前提和合理路径之上,才能析出和实现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
首先,廓清认识论和伦理学之间关系是析出边界道德积极价值的合法前提。人是未完成的类存在,是没有发展终点的文化存在。就像埃德加?莫兰所指出:“在种族、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环路”[16],人的这种存在总是首先在求真与求善两个向度上具体展开。一方面,求真仰望于求善。人的所有认识都包含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这些认识当中也必然包含人对以上所有关系的道德价值判断,形成涵括以上所有关系的伦理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求真是道德化真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求善必需先求真。人们建立一系列的道德规范、道德学说,形成具有核心价值的完整的思想道德体系和认识框架,目的在于为人们处理关于自身生命、生存和生活中所涉及的各种关系提供正确价值指引,在这个意义上,求善是真理化道德的过程。这就是马尔库塞提出的关于伦理学和认识论的关系本质的重要命题,即“认识论本质上就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质上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是析出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的合法前提,或者是认识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的哲学维度。
其次,遵循道德化真理和真理化道德是析出边界道德积极价值的合理路径。就真理化道德而言,它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真理化的道德;二是以真理化道德。前者指吸取了真理精华、获得了真理性认识并内化为实体道德的有机元素而形成的道德规范、道德理想;后者指按照真理的要求和方法去启发、诱导“朦胧”的道德,去解蔽、清理“迷途”道德,去教化、规正“虚幻”道德。就道德化真理而言,也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道德化的真理;二是以道德化真理。前者指道德的规范、理想、信念整个地构筑了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总体,从而它被认为真理的代表、真理的典范;后者指遵循道德的发生机制、道德的发展规律去认识、概括、总结真理。那么,对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关系而言,以真理化道德并建立道德化的真理就说明了“认识论本质上就是伦理学”这个命题;以道德化真理并建立真理化的道德就说明了“伦理学本质上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根据以上认识,对现实的人的意欲来说,其内在意欲的积极意欲和外在意欲的积极意欲相契合,就产生了理性意欲,理性意欲的内在倾向是以真理化道德走向真理化的道德;其内在意欲的消极意欲和外在意欲的消极意欲相谋合,就产生了非理性意欲,非理性意欲的内在倾向是以道德化真理走向真理化的道德。故而,人的理性意欲战胜非理性意欲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在道德化真理与真理化道德的相互作用中析出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的过程。
第三,道德真理化和真理道德化必定是一个偶性的、复杂的、漫长的过程。人们要过上有价值的道德生活,就要批判、远离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要反思、质疑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从而调整现世的道德生活,充实此在的真理价值。但是,就像“真理就是与此在的历史性一起被给出的存在的展开”那样,[17]这种价值的实现是以社会历史环境和道德主体精神的当下条件为转移的。这些条件不成熟、不完备,道德的真理就未能真理化,即理论地为道德主体所掌握;真理的道德也未能道德化,即现实地为道德主体所践履。一方面,人们并不一定刻意追求道德真理化,但是真理化道德依然要孕育、要诞生、要成长,要教化育人,化成天下善德万物,因为这是历史进步的谋划,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世界也不一定全然承认真理道德化,但是道德化真理至今在人文社会世界、自然生态世界牢牢占据着精神灵魂的圣地,它不会屈从于律法的强制和驱逐,也不会屈就于情感的冷漠和误解,因为这是群众生活的谋划,群众创造的文化成果。
三、意义的澄明:边界道德的意欲转向
历史的谋划和选择,群众的生活和创造,文化的整合和复兴,推动了边界道德从恶的、低级的意欲转向善的、高级的意欲,促进了道德主体的行为方式从消极、压抑的样态转向积极、开放的样态,澄明了人的存在从有限性的、不健全的生命存在转向无限性的、道德化的生活存在。这种转向是靠道德主体追求正向价值、维护崇高真理、积淀生活意义逐步实现的。
首先,追求正向价值要介入理解的实践。理解的实践是追求精神价值的感性实践,这种被追求的精神价值,生成于人对人互为主体的理解,一种深切的主体间性的理解之中。这种理解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靠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异化、自我扬弃来达到,而是实现于没有终点的感性实践的“路途中”(on-the-way)[18],这种理解是贯穿现实道德生活的理解,它把道德看成是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并达成统一意志的产物,因而是属人世界的文化的产物。依据伽达默尔的观点,孙正聿教授指出:理解就是“历史文化进入个体意识的方式”[19]。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现象一经出现,边界道德随之出现,确切地说,边界道德也就潜存于个体意识之中,潜存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因此,它并非“万恶不赦”、并非不能转向,它作为与道德并生而存的潜在,最终要以颠覆自我的方式,克服自我的虚伪本质,销弃自我的虚在位置,复归道德的原生形态,体现实体道德的向上性、进步性、理想性的要求,重新取得涵容合理正义和积极自由的高尚本质。
其次,维护崇高真理要深入体验的实践。如果说介入理解的实践只是为边界道德的遮蔽出脱、意欲转向指明了一个正确努力方向的话,那么进展到深入体验的实践,则为生活于边界道德中的个体人“通过体验、理解文化获得人与外部环境的各种意义关系”[20],从而嫁接一座追求道德正义、维护崇高真理的心灵桥梁。因为深入体验的实践是反思已有的实践,批判占有的实践。这种反思,是反思已有的实存、显在,从而去追究潜存、虚在的东西,以及这些东西的背景和根源;这种批判,则是批判确定性中那些消极的东西,汲取不确定性中那些积极的东西。从而“在捉摸不定的东西中去确立合理的恰当的生活形式”[21],并在“合理的恰当的生活形式”中体悟生活真理,在合法的和谐的生活秩序中重建道德生活。因此,否弃、消解边界道德和深入体验实践、追求道德正义、维护崇高真理是高度融合的理性过程。
第三,积淀生活意义要融入升华的实践。人是世界特有的类存在。这种类存在不仅以工具性的劳动、活动同一般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以创造性的生产、生活使每一个体人和每一代人接续发展。这就是作为类存在的人历史地积淀的生活意义。具体来说,一方面,人既要脱离野蛮的动物界、利用博大的自然界、建立文化价值体系,从而成为世界存在的核心;另一方面,人又要对整个世界开放,要“按照现实的实际面目来显示现实,显示这一现实不准存在的东西”,消除那些不利于人的发展的东西,当然包括消除虚幻道德、边界道德带来的一切消极因素。要达成这些目标,个体人只有“一次一次地在较小的程度上,不只是在狭义的伦理学意义上,富于独创性地决定他自己”[22],同时还要勇于智慧地推进文化创造,融入升华生命价值的实践,去努力“显示生命的力量,光彩和尊严”这时,沉沦于虚幻道德、徘徊于边界道德中的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真实、体悟真理的真谛、体验生活的真义,创造和谐的身心。正如费希特所说的那样:“我对我自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世界也对我自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我的一切生存之谜都得到了解答,而在我的心灵里产生出最完满的和谐。”
总之,“边界道德”并不是“虚幻的道德”或“道德的虚幻性”,问题在于人的道德意欲的纷乱化、道德心态的分裂化,才导致人的道德精神的虚幻化、道德理想的边缘化。“边界道德”并不是“非存在的道德”或“边缘的道德”,问题在于人不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在局限、塑造真实的自善的自我;在于人不愿意表里如一地对待他人,展示真诚的善他的本我。在人走向全面发展过程中,边界道德的内在意欲将经批判后实现解蔽,其外在意欲将经审查后获得释放,其积极意欲也将克服、消解消极意欲,从而使人从虚幻的隐蔽存在复归到真实的光明显在,这种显在就是“现实的人”的真实、真诚而和谐的道德生活。正是这种生活,衬映了现代道德实践的理性精神,彰显了当代普世真理的指引价值,澄明了人的高尚存在的生活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叶闯.理解的条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俄]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转[M].雷永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陶德麟.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孙正聿.哲学的目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1][德]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M].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3]柏拉图.菲德罗篇.279c
[1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5][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6][法]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8][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19]孙正聿.哲学观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20]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1]张能为.理解的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2][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阎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