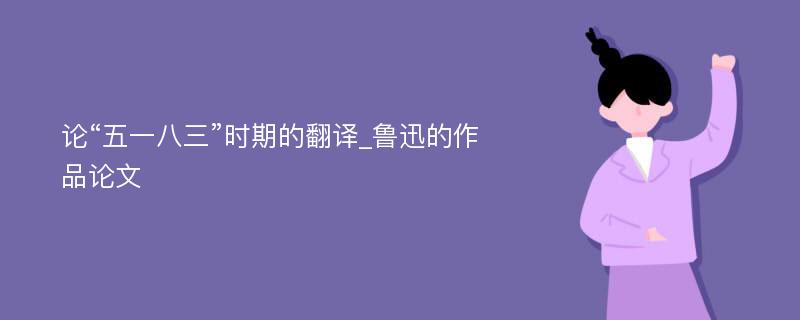
论“五#183;四”时期的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3)05-0120-12
从晚清到“五·四”,文学翻译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晚清文学翻译,最早来自于传教士。1899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来,外国文学翻译开始风行,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等译作大量面世。不过,开始阶段翻译文学中的名著很少,多数都是二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品;在翻译上也不尊重原文,习惯于以中国文体改写外国文学作品,甚至常常不署外国原作者的名字。这种转变的质变,发生在《新青年》时期(1915—1922)。
辛亥以后,袁世凯复辟,共和被打破,文化上回归保守。陈独秀开始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他感到,救国还得从思想启蒙入手,而思想启蒙首先要从青年人入手。1915年9月出版的《青年杂志》,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创办的。
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首先是翻译介绍。在《新青年》上,翻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新青年》对于外文格外重视,开始看起来有点像青年的外文辅导类刊物。刊物上常常有英汉对照,并介绍外文学校,连广告都一直是介绍英汉辞典的。陈独秀很重视西洋文学的翻译介绍,在《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介绍了西洋思想之后,陈独秀接着在《青年杂志》一卷3号和4号连载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介绍西洋文学。陈独秀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几种不同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阶段。①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追逐19世纪科学昌兴之后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的巨大贡献,是为中国文坛确定了文学的阶段和等级。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之所以鱼龙混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坛对于外国文学认识不清,区分不了通俗作品和名家名著。陈独秀对于西洋文学史阶段的分法未必准确,不过他的论述却给国人提供了一个识别西洋文学的标准和方向,对后来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翻译《新青年》最早的翻译家是陈嘏和薛琪瑛。前者系陈独秀的侄子,曾留学日本;后者是薛福成的孙女,吴汝伦的外孙女。他们俩的翻译,全是连载。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春潮》,连载于《青年杂志》一卷1-4号。薛琪瑛翻译的王尔德《意中人》紧随其后,连载于《青年杂志》第一卷2、3、4、6号及第二卷第2号。接着是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初恋》,连载于一卷5、6,二卷1、2号。二卷3号开始,《新青年》又开始刊登陈嘏译王尔德的《弗罗连斯》。这些名家名著构成了《青年杂志》及《新青年》初期译文的主要篇幅。在鸳鸯蝴蝶派和林纾翻译盛行的1915年,《新青年》这种名家名著的文学翻译无疑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了“五·四”文学翻译新时代的开始。不过,如果从翻译的文体层面看,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的翻译仍有较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清的翻译。从语言上看,这一时期的译文主要还是文言。晚清翻译的删节改写,在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仍有遗留。陈独秀事实上并不是文学中人,《青年杂志》对于西洋文学翻译的推出还只是初步的。事实上,《新青年》的宏伟大业还刚刚开始。这个时候,胡适及时地出现了。
1916年上半年,《青年杂志》遭遇了麻烦。上海基督青年会因《青年杂志》与他们主办的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改名。《青年杂志》对抗了几个月,终于无奈妥协。《青年杂志》本为月刊,《青年杂志》一卷6号出版时间为1916年2月,而《新青年》二卷1号的出版时间为1916年9月1日,这中间停了七个月。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陈独秀借杂志改名之际,趁机调整办刊方向,这才有后来暴得大名的新文化刊物《新青年》。《新青年》一卷1号刊登了两条通告:第一条是宣告《青年杂志》更名,同时宣告《新青年》请来了诸多当代名流供稿,该刊将以新的面目示人;第二条是“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新青年》延请的“当代名流”之一,便是胡适。
自二卷1号起,胡适正式为《新青年》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作家泰莱夏甫的小说《决斗》。从二卷4号起,胡适开始在《新青年》登载“藏晖室劄记”。其中颇多介绍西洋文学的内容,如二卷4号“藏晖室劄记”介绍霍甫特曼、易卜生,介绍欧洲的问题剧;二卷5号“藏晖室劄记”介绍了诺贝尔奖(胡适称为“诺倍尔赏金”)的情况,并刊录了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自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以后,国内文坛对于西洋名家名著等级有了大体的概念。不过,陈独秀事实上只侧重于法国文学,对于西洋文学大势的了解未必全面准确。胡适身在美国,对于西洋文学的了解更为直接。他从英语世界发回来的文章,不啻为对于陈独秀的一个有力补充。
自四卷1号起,《新青年》取消外稿,变为同人刊物。《新青年》封面上刊载了十八期的“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眼也消失了。自此以后,《新青年》出现了新的气象。四卷1号,《新青年》发表了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这是周作人在《新青年》的第一次露面。四卷2、3号,钱玄同、刘半农配合演出了一场“双簧戏”,打了一场富于影响的硬仗。四卷4号,《新青年》首篇隆重推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四卷5号,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鲁迅第一次出场,发表《狂人日记》。四卷6号,《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在《新青年》同人中,胡适让人瞩目,似乎有取代陈独秀主导《新青年》的趋势。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改革思想的一次概括,也是他对于翻译思想的一次系统表述。胡适将文学革命的主张概括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认为创造新文学唯一的方法就是翻译西洋文学。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借鉴西洋文学的理由:“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至于如何翻译西洋文学,胡适也进行了规划。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翻译,都不得其法,他拟定了几条翻译西洋文学的具体方法:(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只译名家名著,这是对于陈独秀推崇西洋文豪的一个落实,也是《新青年》翻译与晚清翻译划清界限的一个标志。“五·四”翻译的另一个标志——用白话文翻译——则主要是胡适的功劳。胡适不但进行理论倡导,同时也付诸实际行动。他本人致力于西洋文学各种文体的翻译引进,试图为中国文学现代文类的建立奠定基础。胡适很重视短篇小说。从《最后一课》(1912年译,刊于1915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柏林之围》(1914年11月《甲寅》),到“短篇小说第一名手”莫泊桑的《二渔夫》(《新青年》三卷1号),都旨在提倡短篇小说这一新的文体。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大专门发表了一次有关短篇小说的讲座。演讲稿后经修订,刊于《新青年》四卷5号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开头便说;“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得‘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他以自己翻译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二渔夫》等小说为例,详细介绍西洋短篇小说的定义及特征。短篇小说之外,胡适同时译白话诗。就在刊载《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四卷3号,胡适同时发表了译自苏格兰女诗人Anne Lindsay夫人的诗歌《老洛伯》。“序”中谈到,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诗歌古雅无生气,北方的苏格兰诗人以地方俚语做白话诗,引发整个英格兰的文学革命,Anne Lindsay夫人的诗即是此种白话诗。胡适的意图正在于此,试图以白话诗进行文学革命,翻译西诗是为中国白话诗的创作提供参考。胡适对于译诗很重视,将译诗收进自己的创作《尝试集》中。《关不住了》系胡适1919年2月26日译自美国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甚至将这首译诗称为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胡适也译戏剧,最著名的自然是和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的《娜拉》,发表于《新青年》四卷6号“易卜生专号”上。
鲁迅首次发表译作的《新青年》七卷1号,是后期《新青年》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起,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结果是,胡适逐渐淡出《新青年》,周氏兄弟的时代开始。特别是从翻译的角度看,周氏兄弟——主要是周作人——取代了胡适在《新青年》的主导地位。
就《新青年》的翻译而言,如果说陈独秀首开风气,胡适建立了白话文学翻译的主体,那么,周氏兄弟则较胡适又进了一步,他们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侧重于弱小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在方法上倡导“直译”,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翻译的主流。
从翻译对象来看,胡适开始翻译《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二渔夫》等作品主要限于爱国主义,延续了晚清以来的翻译主题;后来翻译易卜生的《娜娜》等作品,则显示出“五·四”个性主义。周氏兄弟则早已摆脱了从陈独秀到胡适的“名家名著”视野,将翻译的眼光投向了“弱小民族”、俄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等。
周氏兄弟对于“弱小民族”和俄国文学的选择,并非始于《新青年》,而是早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就开始了。据周作人回忆,“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1]1909年,《域外小说集》出版后,销路很差。鲁迅很受刺激,从此罢手。周作人却还在坚持。我们知道,晚清以来的中国外国文学翻译,以英、法为大宗,占据前两位,远超出其他国家。俄国文学的翻译较少。东北欧等弱小民族文学,则更少有人提及。周氏兄弟将视野转向弱小民族及俄国文学,显示出超前的眼光。
粗略统计,自四卷1号(1918年1月15日)至九卷4号(1921年8月1日)三年多时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发表了“弱小民族”文学十六种。鲁迅在《新青年》上翻译了两篇俄国文学作品:阿尔支拔绥的《幸福》和埃罗先珂的《狭的笼》。《新青年》翻译“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作品与《域外小说集》具有明显的承续性。两处有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甚至有一部作品文言与白话两个版本。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周氏兄弟翻译介绍俄国文学,意义格外不同。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后期,俄罗斯研究的篇幅不断增加,八卷2号至八卷6号,居然有连续五期的“俄罗斯研究”专题。此外,还有大量的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唯物史观方面的文章,周氏兄弟的俄苏文学翻译夹杂于其间。
如果说,在谈到翻译《域外小说集》动机的时候,周氏兄弟尚用“排满”、“革命”等术语进行表达,那么,在《新青年》上,他们则开始以“写实”、“为人生”、“血与泪”等术语谈论翻译作品,周作人在翻译托尔斯泰《空大鼓》的“附记”中,称“他的艺术是写实派,是人生的艺术”(《新青年》五卷5号),鲁迅在翻译埃罗先珂的《狭的笼》文后的“译者记”中称这篇文章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新青年》九卷4号)。这些术语后来正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标志。
从翻译方法上看,周氏兄弟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最大贡献是“直译”。周氏兄弟在20世纪初的翻译也受到晚清时风影响。鲁迅后来认为,这种翻译不如说是“改作”,他对此颇后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的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热。”[2]他还说:“青年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3]到了《域外小说集》,周氏兄弟开始转变。《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方法,用鲁迅在“序”中的话来说,是“词致朴讷”、“弗失文情”。当《新青年》时期的译文第一次编集时,周作人在《点滴》“序”中谈到,这本译文有“两件特别的地方”,即“一,直译的文体;二,人道主义的精神”[4]。“直译的文体”居然放在“人道主义的精神”之前,可见对于“直译”的强调。
《新青年》构成了晚清至“五·四”翻译的现代转折,它的传统为《新潮》《小说月报》等新文学报刊所继承和发展。《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也体现在《新潮》之中。大体来说,《新潮》较多承续胡适的思路,茅盾的《小说月报》较多发展周氏兄弟的路径。
《新潮》是《新青年》的学生刊物。《新潮》第一期创办于1919年1月1日,这时候《新青年》尚未结束,正办到六卷1号(1919年1月15日)。《新潮》的创办者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都是北大的学生,《新潮》是在他们的老师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据傅斯年在二卷1号《新潮》发表的《〈新潮〉之回忆与前瞻》一文:《新潮》酝酿之初,他们与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商量,陈独秀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经济上的资助,显然是对于《新潮》的最大支持。《新潮》创办之始,即聘胡适为顾问,“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周作人则亲自担任了《新潮》后期的主编。胡适在《新潮》上发表过《李超传》《非个人主义的生活》及新诗,李大钊在《新潮》上发表过《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周作人在《新潮》上发表过新诗及多种翻译。鲁迅当时虽然不在北大任职,不过也在《新潮》上发表了小说《明天》,翻译了尼采的《察拉图是特拉的序言》,并专门应傅斯年之约发表了《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新潮》与《新青年》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
《新潮》既注重发表新文学作品,也很重视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前一个方面较多为人提及,后一个方面不太为人注意。事实上,在《新潮》中,创作和翻译一向是并重的。在《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化名“志希”)发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一文,表明《新潮》对于国内文坛的态度。这里的“小说界”,既包括创作,也包括翻译,文中的评论也因此分为两个部分。
在翻译评论的部分,罗家伦借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S.Reinsch)的话,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只是翻译介绍了柯南道尔、哈葛特、大仲马等“多半是冒险的故事及‘荒诞主义’的矫揉造作的作品。东方读者能领略Thai keray(萨克雷——引者注)同Enatole France(法郎士,当为Anatole France——引者注)等派的著作却还慢呢。”由此可见,“现在西洋文学在中国虽然很有势力,但是观察中国人所翻译的西洋小说,中国人还没有领略西洋文学的真价值呢。”对于中国的翻译,罗家伦有四点建议:第一:“最要紧的就是选择材料”。选择材料的标准是“改良社会”,翻译外国可资借鉴的作品,由此柯南道尔、司葛特之流不必译,“取材不必限于英美,就是俄、法等国也都可以,如Tolstay,Moupassant同英国H.G.Wells等人的小说尤以多译为是。”第二,翻译须用白话。第三,翻译上须准确,罗家伦在这里批评了晚清翻译的随意删节,如魏易翻译狄更斯《二城记》删除了第三节,马君武将托尔斯泰的《复活》译为《心狱》,后半部全未译出。第四,不可以中国事物改写原文,如“林先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事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
《新潮》的另一位主将傅斯年,在《新潮》一卷3号上专门发表了《译书感言》,强调翻译的重要,并表明自己的翻译观。《译书感言》一文开头一段是:
现在中国学问界的情形,很像西洋中世过去以后的“文艺再生”时代,所以去西洋人现在的地步,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赶上他不必用几百年的功夫;若真能加紧的追,只须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澡了……至于我们赶他的办法——省事的路程——总不外乎学习外国文,因而求得现代有益的知识,再翻译外国文的书籍,因而供给大家现代有益的知识。照这看来翻译一种事业的需要不必多说了。这是典型的“新青年式”的进化论心态,而以翻译作为“追赶”西洋的方法,也显然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译书感言》接着说:
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林译的几种最下流的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对于林纾的翻译,短短几句话居然用了两句“最下流的”,这种咒骂显然也来自《新青年》对于林纾的贬低,只不过学生的口气更加夸张,并且,傅斯年还附带上了对于严复的批评。
傅斯年将自己的翻译思想概括为两句话:“(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前一句话强调的是译文的准确,为此,译者须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后一句强调的是译文的有用,即需要翻译的是对于社会、对于读者有正面影响的文本。就文学而言,傅斯年认为,值得翻译的就是胡适所说“名家著作”,“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在翻译方法上,傅斯年提出三条原则。一是“用直译的笔法”,二是“用白话”,三是“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用‘提要’的方法,不必全译。”很显然,“直译”来自周氏兄弟,“用白话”来自胡适,大概只有不太重要的第三条是傅斯年的自创。
从《新潮》前后两任主编傅斯年、罗家伦的这两篇文章看,他们的翻译观大体是在追随他们的《新青年》导师。在翻译的功能上,傅斯年以翻译作为追赶西方最新思想的说法,不过在重复陈独秀。罗家伦认为,翻译在于“改良社会”,简直回到了梁启超。对白话翻译的强调,对林纾等晚清译文不准确的批评,也是追随《新青年》的思路而来。
《新潮》的文学译作不算太多,不过却颇有名篇。《新潮》第一卷第1号上没有文学作品翻译。一卷2号上只有一篇译作,即宋春舫翻译的德国作家苏特曼(Hermann Sudermann)的剧作《推霞》(Teja)。有趣的是,尽管罗家伦与傅斯年都在文中提出翻译必须使用白话,《新潮》所发表的这第一部文学翻译《推霞》(一卷2号)却是一部文言译作。
苏特曼是与霍甫特曼(Gerhart Hauptmann)齐名的德国近世戏剧家,也是最早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德语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卖国奴》曾由吴梼翻译发表于1904-1905年的《绣像小说》。宋春舫在《推霞》的译文小序中,攻击了剧中的女性人物,认为苏特曼剧中女性人格“皆卑鄙凶淫不足道”,“难免无耻之讥”。译文发表后,鲁迅看到很不满意,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1919年1月30日)说:“昨天看见《新潮》第二册内《推霞》上面的小序,不禁不敬之心,油然而生,勃然而生;倘若跳舞再不高明,便要沛然莫之能御了。”[5]同年4月16日,在发表于《新潮》一卷5号的《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中,鲁迅再一次表示,“《扇误》译得很好,《推霞》实在不敢恭维”[6]。鲁迅的看法并不孤立。1920年3月,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在致郭沫若的信中,也认为宋春舫的序言“非常武断,不类深能了解Modern Spirit之人”[7]。此后,宋春舫的翻译在《新潮》消失了,而被鲁迅表扬的《扇误》的译者潘家洵接连刊载了多部精彩译作。
潘家洵是《新潮》上最有成就的翻译家。鲁迅所说的《扇误》系潘家洵译王尔德的名作,刊登于《新潮》一卷3号(1919年3月1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青年》五卷6号(1918年12月15日)、六卷1号(1919年1月15日)号、六卷3号(1919年3月15日)正在连载沈性仁翻译的王尔德的《遗扇记》。《遗扇记》与《扇误》系王尔德同一剧作(Lady Windermere's Fan,1892)的不同译名。也就是说,《新青年》《新潮》两家兄弟刊物同时刊载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部剧作,堪称奇观,由此也足见《新潮》与《新青年》的思想倾向的一致性。《新潮》编者在潘家洵《扇误》译文的最后有一说明:“潘君译此剧,著笔于两月以前,迨译成四分之三以后,始见《新青年》五卷6号要目预告中沈性仁女士已译成之。潘君亟欲辍译,同社诸君则谓如此名剧不妨有两种本译,功亏一篑,殊为可惜。于是潘君完成此稿。”易卜生这部剧作乃五四时期名剧,1923年洪深再次翻译此剧,更名为《少奶奶的扇子》,刊于《东方杂志》第21卷2-5号上,他还将此剧搬上舞台,引起社会轰动。
接着,在《新潮》一卷5号上,又出现了潘家洵翻译的另一部名剧,易卜生的《群鬼》。《新潮》对于易卜生的兴趣显然也是跟随《新青年》而来。事实上,《新青年》四卷6号的“易卜生专号”(1918年6月15日),《新潮》的几位干将早已参与其中了。“专号”的重头戏易卜生的《娜拉》,即由罗家伦翻译。不过,罗家伦译本不太令人满意,胡适重新翻译了第三幕。《新青年》出版后,前两幕署罗家伦名,第三幕署胡适之名。胡适承诺还会重新翻译前两幕,后来大概太忙,没有做到。不过,这事却由潘家洵代为完成了,潘家重译了《娜拉》的前二幕,再加上胡适译的第三幕,成为一个完整的译本。潘家洵后来成了最为著名的易卜生翻译大家,《新潮》一卷5号的《群鬼》,即是他的早期译作之一。
其后,《新潮》二卷1号(1919年10月30日)刊载了潘家洵翻译的又一部名剧,肖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萧伯纳是五四时期的热门人物,差不多与易卜生齐名。《新青年》“易卜生号”在目录之前醒目位置刊登“本社特别启事”,预告本年十二月号《新青年》将刊登“萧伯纳专号”,翻译发表肖伯纳的《人与超人》《巴勒伯大爵》和《华伦夫人之职业》三剧。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新青年》的“萧伯纳专号”终于并没有如约出版。潘家洵所翻译的《华伦夫人之职业》是否是当时为《新青年》而预备的,不得而知。不过此剧在《新潮》发表,倒是弥补了《新青年》的缺憾。1920年,汪仲贤将此剧搬上剧场,隆重演出,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的一个盛事。
《新潮》二卷2号,潘家洵所翻译是美国Margaret Thomson的小说炉火光里。Margaret Thomson并非名作家,只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名女学生,不过,这是一部反映父母与子女有关跳舞问题冲突的小说,潘家洵认为,在家庭冲突的中国,这类问题有研究的必要。《新潮》二卷4号,潘家洵再次翻译发表肖伯纳的剧作题为《陋巷》。
自二卷5号起,周作人担任主编,他给《新潮》的翻译带来了一些变化。《新潮》二卷5号发表了鲁迅翻译的尼采《察拉图是特拉的序言》,周作人翻译的俄国弥里珍《老乳母》,还有《新潮》同人中与周氏兄弟比较接近的孙伏园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呆子伊凡的故事》。《新潮》三卷1号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作家千家元垫的小说《蔷薇花》、剧作《热狂的小孩们》,孙伏园翻译的犹太作家西尔雪般的剧作《暗中》。周氏兄弟所偏好的俄国小说,日本小说及弱小民族小说,开始在《新潮》上露面。不过,仅此两期而已。此后,《新潮》出了三卷1号出了一个“世界名著介绍特号”就停刊了。此期的“世界名著”并不包括文学名著,而是杜威、罗素等人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新潮》杂志创办的时间并不长,仅有两年零两个月,共十二期刊物。从上述文学翻译的情况看,《新潮》是追随《新青年》的,不过《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也体现在《新潮》之中。我们注意到,作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虽然支持《新潮》的创办,却没有给《新潮》写过文章。对于《新潮》影响较大的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潮》主将多是胡适的弟子。《新青年》后期内部分化,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上海,大谈政治,转向马克思主义。《新潮》却不为所动,仍然走在胡适所支持的“国故与科学”的路径上。从翻译上看,《新潮》也较受胡适影响。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提出“取材不必限于英美,就是俄法等国也都可以”,“也可以”表明并不以法、俄为尚;傅斯年的《译书感言》明确主张胡适的“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在《新青年》上,胡适主张翻译名家名著,翻译易卜生,而后起的周氏兄弟主张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日本文学。潘家洵对于易卜生、萧伯纳等人的翻译,对于问题剧的关注,正是循胡适的思路而来。直到周作人主编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发表俄国文学、日本文学,《新青年》上最为重视的弱小民族文学,则只有一篇孙伏园翻译的犹太作家西尔雪般的剧作《暗中》勉强可以代表。
继承了周氏兄弟文学翻译路径的是茅盾。②
茅盾1916年自北大预科毕业,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翻译最早也是从此开始的。茅盾最早翻译的小说是威尔士的幻想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刊载于《学生杂志》第4卷1、2、4号(1917年1、2、4月)。他翻译的第二篇小说是美国洛赛尔·彭特(Russel Bond)的科学小说《两月中之建筑潭》,刊载于《学生杂志》第5卷1—12号(1918年1月5日—12月5日)。幻想小说、科学小说,看起来仍然是晚清翻译的余绪。茅盾的译文,仍然还是文言的。从翻译方法上看,也是“用华变夷”的改写方法。茅盾居然描写小说主人公的书桌“左定窑壶而右莎翁集”,主编竟认为小说中的那个美国学生有“定窑壶”是合情合理的,他在发排时甚至还加上了“砚”和“香炉”[8]。
1919年后,受《新青年》五四运动的影响,茅盾的翻译开始转向。他翻译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发表于1919年8月20-22日《时事新报》。此后,他又翻译发表了契诃夫、斯特林堡、莫泊桑、萧伯纳、托尔斯泰等的小说及剧作。1920年1月1日,茅盾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一文,列出了他的翻译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再次出现于这个月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宣言”中。这个计划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作家有:比昂松、斯特林堡、易卜生、左拉、莫泊桑、白里欧、霍普特曼、高尔斯华绥、果戈里、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显克维支、席曼斯坦;第二部分的作家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萧伯纳、威尔斯。第一部分的作家偏重写实派、自然派;第二部分的作家偏重问题小说。从这个名单看,茅盾的翻译对象较为接近《新青年》前期的名家名著。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所提到的文豪多数包括在茅盾的名单中。
茅盾对于文学与新思潮的关系的强调与陈独秀接近。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续)里说:“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三大文豪之左喇,自然主义之魁杰也。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也。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益非可以一时代之文章家目之也。”茅盾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他认为:“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所以,18世纪个人主义的新思潮,发源于卢梭的Nouvelle Heloise和Emile,这两部是小说;19世纪家庭个性主义的新思潮,起于易卜生的A Doll's House,这一篇是剧本。尼采的超人哲学,结晶在Thus Spake Zarathustra,这部也是小说。俄国少年党是以赫尔岑做中坚的,赫尔岑便是个文豪,他所做的Whose Crime?便是部小说。其余如人道主义劳动主义他于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便是个大文豪。所谓大勇主义是罗兰先说起的,罗兰也是个文豪。萧伯纳、哈德曼等都拿文豪的资格提倡社会主义。自来新思潮的宣传,没有不靠文学家做先锋呀!”③茅盾对于写实派、自然派文学的强调也自陈独秀而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3号和4号连载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介绍西洋文学。陈独秀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几种不同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阶段。④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追逐19世纪科学昌兴之后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茅盾对于西洋文学的分法更为切近,他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在自然主义之后又加上了更新的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不过,尽管如此,茅盾认为,中国文学尚停留于写实主义之前,不过“因为艺术都是根据旧张本而美化的。不探到了旧张本按次做去,冒冒失失‘唯新是摹’,是立不住脚的。所以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⑤
自加入《新青年》以后,茅盾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开始将翻译对象逐渐集中于俄苏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茅盾只赶上了《新青年》的尾声,不过恰恰是《新青年》的激进左倾时期。我们知道,陈独秀到上海后,《新青年》同人分裂,在北京只有周氏兄弟继续写稿。陈独秀于是在上海发展了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左”倾青年作为《新青年》的中坚,茅盾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新青年》的。据茅盾回忆:“大概是一九二零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9]他还提到:“那时候,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不给《新青年》写稿,所以写稿的责任便落在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身上,他们也拉我写稿。当时我们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10]在1920年12月10日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信中,也有“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11]的说法。
在陈独秀南下上海以后的《新青年》上,翻译主要由周氏兄弟承担,茅盾进入《新青年》后也主要从事译介工作,壮大了周氏兄弟的阵营。茅盾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在译介上与他们思路一致,相互配合。茅盾的文章常常与周氏兄弟的文章并列登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八卷2号上,周作人翻译发表了柯罗连珂《玛加尔的梦》,茅盾翻译发表了《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新青年》九卷3号上,鲁迅翻译发表了日本菊池宽的《三浦右衙门的最后》,茅盾翻译发表了《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新青年》九卷4号上,鲁迅翻译了埃罗先珂的《狭的笼》,茅盾翻译发表了挪威包以尔的《一队骑马的人》。《新青年》九卷5号上,周作人翻译发表了西班牙伊巴涅支的《颠狗病》,茅盾翻译发表了爱尔兰葛雷古夫人戏剧《海青赫佛》。在此我们看到,茅盾关注匈牙利、挪威、爱尔兰等弱小民族“为人生”的文学,关注苏俄,与周氏兄弟路径一致。
茅盾的更大贡献,是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延续和光大了周氏兄弟的翻译传统。从1921年1月开始,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该刊从此成为以“为人生”为主旨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刊。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沿袭了《新青年》后期的风格,以大量篇幅翻译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俄国文学及日本文学等。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第一期(12卷1号)的“译丛”翻译发表了(俄国郭克里)《疯人日记》、(日本加藤武雄)《乡愁》、(俄国托尔斯泰)《熊猎》、(波兰高米里克基)《农夫》、(爱尔兰夏芝)《忍心》、(挪威般生)《新结构的一对》、(俄国安得列夫)《邻人之爱》及“杂译泰戈尔诗”。弱小民族四篇,俄国三篇,日本一篇,这个翻译构成基本上是《新青年》翻译的延续。据笔者粗略统计,茅盾主持革新后的《小说月报》1920-1921两年时间(其后由郑振铎接任),翻译总量仍然与此相符,其中弱小民族文学85篇,俄罗斯文学75篇,其他国家文学明显较少,其中,法国文学19篇,英国文学9篇,日本文学8篇,美国文学4篇。对于俄国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是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的突出特点。茅盾在主编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时候,一共只编辑过两个专号,正是“被损害民族的文学”(12卷10号)和“俄国文学研究”专号(12卷号外)。
《小说月报》所翻译的弱小民族文学,涉及多种不同的国度,包括瑞典、匈牙利、印度、波兰、比利时、挪威、新犹太、捷克、芬兰、新希腊、智利、阿富汗、爱尔兰、塞尔维亚、乌克兰、阿美尼亚、波希米亚等国。因为对于弱小民族文学术有专攻者不多,其中很多作品都由茅盾本人转译。以《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为例,茅盾翻译了这个专号中的大量作品,如“小说”中的(新犹太)拉比诺维奇的《贝诺思亥尔思来的人》,(克罗西亚)森陀卡尔斯基的《茄具客》,(捷克)波西米亚贝克的《旅程》,(乌克兰)L.Vkraink的《巴比伦的俘虏》,“杂译小民族诗”中阿美尼亚、乔具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捷克、波兰诗人的十首诗,全系茅盾所译。茅盾还写了《芬兰的文学》、《新犹太文学概观》等文,另外茅盾还请他的弟弟沈译民译了(塞尔维亚)Lazarevic的《强盗》和Chedo Mijatovich所著的论文《塞尔维亚文学概观》。除此之外,其余的译作都来自周氏兄弟的笔下,其中周作人翻译了(波兰)科诺布涅支加的《我的姑母》,(新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思的《伊伯拉亭》,(英)劳斯《在希腊诸岛》,(芬兰)哀禾《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还翻译了(波兰)诃勒温斯奇的论文《近代波兰文学概观》,鲁迅翻译了(芬兰)明那·亢德的《疯姑娘》、(勃拉格利亚)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还翻译了(捷克)微拉绥克的论文《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可以说,这个“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大致上是沈氏兄弟和周氏兄弟合作的结果。
由此也可见周氏兄弟对于茅盾的支持,可见《小说月报》与后期《新青年》的渊源。的确,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与周氏兄弟,特别是周作人,联系紧密。周作人当时是“五·四”的理论家与翻译家,地位颇高,无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小说月报》,都在竭力寻求周作人的支持。茅盾对于周作人相当恭敬,不但一再请求周作人予以稿件支持,而且就《小说月报》的编辑安排诸方面问题进行请教。只要看一看当时茅盾致周作人的信,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在茅盾主持《小说月报》这段时间,他与周作人的通信,多是在请示翻译稿件等方面的问题。在1921年7月20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茅盾向周作人详细询问有关于这一年十月《小说月报》拟出“被压迫民族文学号”的事情,部分引录如下:
《小说月报》在十月号拟出一个“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名儿不妥,请改一个好的),里头除登小说外,也登介绍这些小民族文学的论文。现在拟的论文题目是:
1.波兰文学概观(如此类名而已)
2.波兰文学之特质(早稻田文学上日原文。已请人译出)
3.捷克文学概观
4.犹太新兴文学概观
5.芬兰文学概观
6.塞尔维亚文学概观
其中除(2)是译,余并拟做。(1)(3)两篇定请先生做,(4)(5)(6)三篇中拟请先生择一为之,关于(4)的,大概德文中很多,鲁迅先生肯提任一篇否?(5)我只见《十九世纪及其后》一九○四年十一月份上一篇的《芬兰文学》(Kermione Ramsden著),似乎译出也还可用,但这是万一无人做的说法,如先生能做更好了。(6)也只见Chode Mijatovich著的《塞尔维亚论》中《文学》一章,略长些,如无人做,也只好把这个节译出来了。但不知先生精神适于作长文否?十月出版,离今尚有一月。此外译的小说拟
1.芬兰 哀禾 先生已译
2.塞尔维亚 即用巴尔干短篇小说集中之一,如无好的
3.波兰 先生已译
4.犹太 阿布诺维支剧(在《六犹太剧》中)
5.捷克
6.罗马尼亚等
上次鲁迅先生来信允为《小说月报》译巴尔干小国之短篇,那么罗马尼亚等国的东西,他一定可以赐一二篇了。如今不另写信给鲁迅先生,即请先生转达为感。茅盾对于周作人依赖之深,请教之详,由此可见一斑。在1921年1月7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茅盾得知周作人有病在身,很着急,因为三号《小说月报》“俄国文学专号里若没有先生的文,那真是不得了的事。”为此,茅盾甚至决定把“俄国文学专号”后移,变成了十二卷的年终号外。在“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周氏兄弟果然都有贡献,周作人发表了《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鲁迅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医生》,撰写了《阿尔志跋绥夫》一文,甚至于周氏兄弟的另一兄弟周建人也加入其中,周建人翻译了梭罗古勃的小说《白母亲》,翻译了英国人约翰·科尔诺的论文《菲陀尔·梭罗古勃》。茅盾照例有大量翻译,沈泽民也在其中。不过,中国当时翻译俄国文学的较多,不必只仰仗沈氏兄弟和周氏兄弟。《小说月报》上的重要的俄国文学翻译家,还有耿济之、王统照、孙伏园、郑振铎、瞿秋白等人。
《小说月报》首篇连载的俄国小说是耿济之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这篇小说从12卷1号一直刊载到第15卷,时间长达四年,其间主编已经由茅盾换成郑振铎,小说却连续不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首先连载的小说也是屠格涅夫,是陈嘏翻译的《春潮》和《阿霞》。在这一点上,《小说月报》也与《新青年》的相类。其后,《小说月报》又连载了鲁迅翻译的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耿式之(耿济之的弟弟)翻译的安特列夫《海洋》等。据笔者的统计,《小说月报》翻译较多的俄国作家为:屠格涅夫、安德列夫、阿尔志跋夫、契诃夫、梭罗古勃、高尔基、路卜询、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库普林、普希金等,关注点大体与《新青年》有继承关系,只是翻译介绍的作家更多,作品量更大。
茅盾所主编的《小说月报》对于翻译极为重视,不但以大量篇幅登载翻译作品,还进行翻译理论的讨论。在《小说月报》12卷第3期上,郑振铎首篇发表了长篇论文《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这篇文章迅速引起了回应,茅盾在《小说月报》12卷4期上发表了《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沈泽民在《小说月报》第5期上发表了《译文学书三个问题的讨论》,对郑振铎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郑振铎的文章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文学书能译吗?”谈论的是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即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能否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完整传达?郑振铎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与他的“世界文学”的思想有关。二是“译文学书的方法如何?”,郑振铎在文中借鉴A.F.Tytler《翻译原理》一书提出了翻译方法的三个法则:一是“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思”;二是“著作的风格与态度中所有的流利”;三是“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沈泽民的观点与郑振铎相反,他认为译文不可能传达出文学作品的情绪、灵感、乡土等,因此不可译。在翻译方法上,沈泽民主张“传神”胜于“传字”。
茅盾的看法值得注意。他首先肯定了“直译”的方法,他说:“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但他又认为,“直译”的最大困难,就是“形貌”和“神韵”不能同时保留。注意了形貌,则容易减少神韵,而注意了神韵,则又不能在形貌上保持一致。那么,在“形貌”和“神韵”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取舍呢?茅盾认为:“就我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12]如此看,茅盾虽然肯定了周氏兄弟的“直译”,但对于“形貌”和“神韵”上的取舍,显然与周氏兄弟不完全相同,而与其弟沈泽民有接近之处。笔者对茅盾发表于《新青年》九卷1号上的莫泊桑的小说《西门的爸爸》进行了译校,发现茅盾的翻译的确很忠实,而且句子也不扭曲。这种相对来说既准确又流畅的译文,显然是茅盾试图调和“形貌”与“神韵”的结果。茅盾提出的问题,恰恰延续了对于周氏兄弟翻译方法的讨论,即肯定“忠实”,肯定“直译”对于晚清译风的扭转,不过,他仍在技术上继续讨论。百分之百的“逐字译”、“逐句译”是不可能的,那样就不成为汉语了,文字上的对应只是程度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茅盾所说的偏重文字对应,还是偏重意义传达的问题。这就是“直译”虽然取得了公认的地位,却一直有争议的原因。
收稿日期:2013-07-28
注释:
①《青年杂志》一卷六号(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在“通信”答张永言:“我国文艺尚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
②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的笔名是1927年以后写作《蚀》三部曲才用的,方便起见,文中统称茅盾。
③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1920年1月10日《东方杂志》17卷1号。署名佩韦。
④《青年杂志》一卷六号(1916,2,15),陈独秀在“通信”答张永言:“我国文艺尚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
⑤《小说新潮栏宣言》,1920年1月15日《小说月报》第11卷1号。不过,茅盾到底耐不住按部就班,时隔不久,他很快就发表文章转而提倡表象主义以至于新浪漫主义了。这一点后来曾受到胡适、鲁迅的批评。
标签:鲁迅的作品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胡适论文; 鲁迅论文; 傅斯年论文; 读书论文; 罗家伦论文; 最后一课论文; 周作人论文; 陈独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