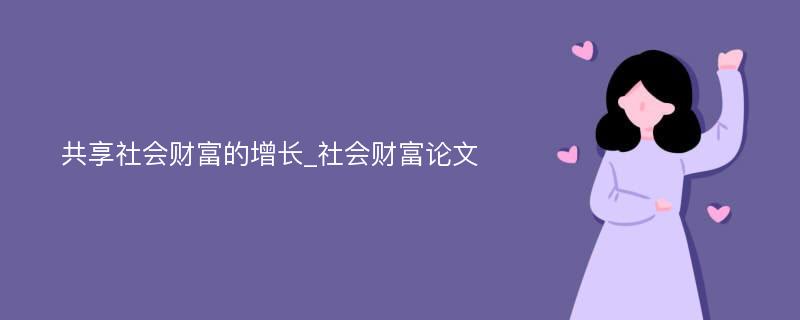
共享社会财富的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富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一阵子从报纸上看到两条对比强烈的报道,一条是广东《新闻人物报》登载的一篇报道:四川某县一个下岗工人家里因生活困难,1997年妻子自杀,1998年17岁的儿子自杀;另一条消息则罗列了广西合浦以原县太爷何建林为首的腐败官僚群体榨取民脂民膏、挥金如土、腐化奢侈的事实。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从这两条对比强烈的消息里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体制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而这两极分化是因为权力与市场相结合而形成。
权力与市场结合作用下的两极分化
我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个人收入分配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1981—1984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社会所有阶层普遍享受到福利水平的提高,收入不均只是略有加重。1984—1989年,个人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不均,这意味着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下降了。1990—1995年,收入的重新增长惠及社会较贫困阶层(但不是最贫困阶层),但也带来了收入不均程度的大幅度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测算收入不均的一个常用指标)从1981年的28.8升高到1995年的38.8,这么大的变化标志着财产及收益的分配发生了深层的结构性变革。从结果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非常类似于美国,接近东亚的平均数,大大高于东欧国家数字,但比拉丁美洲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数字要低。
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均过程,产生了基于教育、财产及性别的形形色色的得益者与失落者,常被谈到的问题有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根据官方1995年的数据,城乡收入比超过2(大多数国家低于1.5);这种巨大的城乡差距显示出生产要素市场的流动性有障碍,尤其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而沿海与内陆差距的扩大则有两个因素:一是靠近世界市场,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二是得益于中央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刺激了外国投资。但这两种差距还并不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公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大多数社会也都得容忍这种因为地理条件不一样而形成的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获得机会的权力越来越不均等,尤其是通过权力市场化而形成的收入差距更是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但上述有关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是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本身有许多缺陷:调查未包括流入城市地区无户口的外来打工人员;城市与农村调查是根据不配套的收入定义进行的分析;城镇住户调查不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福利等实物收入。此外,调查似乎主要记录劳动者的收入,因而遗漏了许多新富者的收入,更兼《1989—1995年国家统计年鉴》所载城市数据摘要由于存在汇总的问题,低估了城市收入不均的状况。
事实上,我国收入不均加重在很大程度上要联系我国的体制转型加以评估。在改革启动之初,我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让权力整体崩溃,重新建立权力体系,如苏联的“休克疗法”;二是让权力进入市场,进行渐进改革。这两种道路各有利弊,我国选择了社会震荡相对要小得多的渐进改革模式,而这种改革的两大特点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与精英转换的连续性,如果没有相对的调校机制,将使权力的掌握者在财富的分配上处于绝对有利地位。事实证明,中国现有部分新富是依靠自身长期勤劳与冒着巨大风险,得益于新的市场机制,但还有更大的群体则是利用转型期的体制弊端,敛取不义之财。在宪法上要确定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人的财产而言;而对后一部分人的财产,我国政府必须着重注意,加大打击腐败现象和制止权力寻租行为。这就要求减少官员的随意处置权,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增大透明度和准确性,通过监管金融市场杜绝获得内幕信息的机会。政府行为改革的主要重点该放在上述几方面。
贫富分化成因的考察
前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都是要对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由于前苏联选择了让权力整体崩溃的“休克疗法”,我们选择了让权力进入市场的“渐进改革”,所以改革进行到现在,面临的局面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区别。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与我国现在都有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但是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却不一样:前苏联改革后,普通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公平”:每个人不分年龄、性别,都得到一张价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用于购买国有资产。但是在自由化、加速私有化的背景下,老百姓和官员得到的“效率”却大相径庭,许多精明的官员廉价攫取了大量国有资产,形成以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大资本群体;而老百姓在高达数百倍的通货膨胀中,一辈子的收入化为零。由于生产严重衰退,许许多多普通工人、教师、医生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只能站在摆满进口商品的货架前兴叹。而我国则由于权力市场化,国家资源掌握在少数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部门官员手中,这些人就成了“先富起来”这一群体中的主体部分。这样一个结果使大家对两国改革有着殊途同归之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雷同,有一位名为Gornia的外国研究者研究比较了东欧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转型经验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验,指出一个问题:东欧国家的贫困与不平等是骤然出现的,而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相对比较稳定,程度较低。但东欧出现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实施宏观经济改革(贸易自由化、价格改革等),因此社会制度使穷人失望,使富人受益这一普遍概念并不准确。Gornia找出了证据:东欧的社会制度具有显著的平等和缓和倾向。 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总体贫困减轻了,这主要是因为内部政策措施,如逐步降低社会开支、财政权力下放和解散公社制度等,但却由于未能触动更深层的制度结构,引起了收入差异的加剧。另3 位外国研究者曾比较了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和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提供的两组数据,发现在官方数据中中国不平等的变化被严重低估,1978年以来的真正不平等的范围要大得多。
社会不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目前我国政府用以解决不正当财富问题的措施是适宜的,因为必须通过反腐败消除权力寻租的机会,监管金融市场——因为在金融市场上非法财富的敛取主要依靠官员的随意处置权和内幕消息,这对经济健康和社会和谐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这种事后惩治型的反腐败还只是较浅层面上的改革,中国的改革要向纵深推进,还需要从更深层面上着眼。从对社会的影响来说,某一社会面临的危机分为第一级危机与第二级危机。第一级危机一部分源于制度层面,其影响是隐性的,如政治腐败、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等等;另一部分则由人口和资源比例失调生发出来。第二级危机由第一级危机派生,是显性的,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失业率升高、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第二级危机的解决必须以第一级危机的解决为前提,因为只要现在的制度结构不发生变化,中国社会的各级权力的拥有者就会继续凭借其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谋求利益,决不会将谋利的途径从金融领域转换到生产领域,从国库转换到市场。
这里还需要指出学术界对不平等问题认识的不足之处。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在极端贫困的不发达国家根本没有条件根据社会正义原则来考虑问题,也无力为进行公平的改革而付出代价。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时,容忍一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是必须支付的代价。其实这一“经典理论”的发明权还不属于中国学者,因为国外学者早在40年代就有如下表述:“在发展和均等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收入不均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经典理论”近30年来受到的各种挑战相当严重,因为几乎从70年代起,在南美国家巴西、墨西哥,亚洲国家巴基斯坦、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等,无一不是由于政府容忍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放任权力进入市场,使中下层人民边缘化,社会陷入动荡不安,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垮台。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屡有对抗和冲突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敌视是一件谁也不能轻视的事件,我国现在的状况验证了这一点:流动人口成了犯罪渊薮,社会摩擦急剧增加,治安状况急剧恶化。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如印尼、泰国等)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较弱,社会紧张程度增加,成了“高风险社会”。
社会管理者的责任伦理
中国改革的初始绩效优于东欧和前苏联,但这是因为我们的初始条件比较优越,如海外庞大的华人资本集团及低成本劳动力等。但越到后来,改革的难度越大,这难度源于原有的政治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载体。这就需要认真考虑一点:是承认制度变迁的断裂性,强调政治制度的变革、意识形态的创新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还是从传统制度的连续性出发,坚持改革只须局限于经济层面。这是一个已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城市贫困人数的急剧增加,为了缓解利益分配造成的剧烈社会摩擦,在改革风险日益增大的90年代,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又被推上前台。从目前看来,这项改革正在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强弱者的生存能力,真真实实成为“社会的安全网”,实在让研究者不敢妄下断语。
作为社会管理者,必须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一是社会管理能力,二是较高的道德素质。前者的含义比较明确,而后者却包括两点:首先是要能为本阶层的利益考虑,这种利益考虑不仅要包括眼前利益,还要包括长远利益;其次是要为其他阶层的利益考虑。因为本阶层的长远利益奠基于其他阶层的安定之上。不可能设想一个国家存在太多边缘化的人,而社会管理者阶层却可以安享财富增长带来的繁荣与快乐。现在被揭发出来的大批贪官污吏,正好说明这些腐化堕落者不仅不为其他阶层考虑,甚至也不为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及长远利益考虑。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在挖社会主义的基础。从经济上来说,这些由贪污受贿积累的财产有不少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流往国外、不可能促进国内的公共积累。个人尊严建立在尊重他人的尊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剥夺他人的尊严之上。与此同理,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仅只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财富的增长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