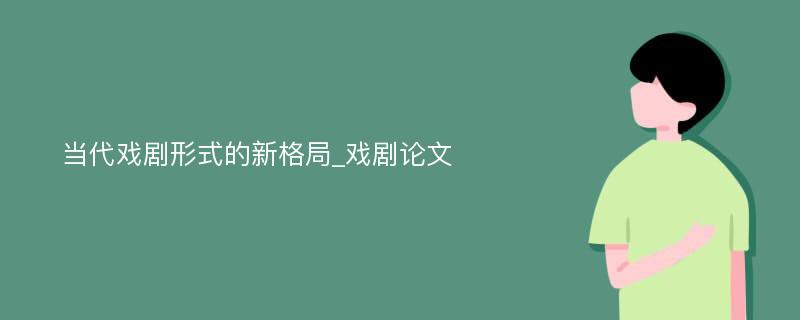
当代戏剧形态新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形态论文,新格局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十年,戏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于众多戏剧家的共同努力,从全方位、多层面上突破了传统戏剧观念的束缚,使得新时期戏剧在经历了观众更为严格的审美要求的考验和电影、电视及其他娱乐形式的冲击后,证明自己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最终形成了多元戏剧美学形态并存、竞荣的新格局。
一《小井胡同》、《狗儿爷涅》、《天下第一楼》等再现型戏剧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由我国优秀戏剧家曹禹、老舍奠定的具有写实倾向的再现主义戏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以成功的艺术实践呈示着再现型戏剧发展的活力。经过1979年前后以《丹心谱》(苏叔阳)、《报春花》(崔德志)等剧作为代表的短暂的复归期,1981年,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标志着再现主义戏剧进入了新的拓展阶段,此后,郝国忱的《榆树屯风情》、《昨天、今天和明天》、魏敏等人的《红白喜事》以及李杰的《田野又是青纱帐》,以相应的艺术追求表现了再现型戏剧的扩展;1985年前后,在剧坛风靡“探索”的风潮中,刘锦云的《狗儿爷涅》表明了再现主义戏剧的深化,李杰的《古塔街》、马中骏的《老风流镇》、杨利民的《黑色的石头》、刘锦云的《背碑人》,同时显示了再现主义深化的强大实力;1988年,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的问世,则代表着再现戏剧的新成就,证实了再现主义戏剧虽不再独尊剧坛,但依然涌动着不息的生命活力。
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是以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评说现实人生、从小井胡同的变迁纵览当代中国历史的成功典范。剧作以评书式的叙述方式,通过北京一条胡同中一个大杂院里五户人家从解放前夕到1980年夏三十来年的命运变迁,形象地评说了当代中国三十来年的历史。剧作以刘、许、石、周、陈五户人家为轴心的十三条线索、四五十个人物有个性的活动构成了北京下层市民的风俗图象,以解放前夕、大跃进年代、“文革”初期、“四人帮”跨台之际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五个渐次发展的历史关头,构成戏剧纵向过程的五个层次,把五幕话剧展开的历史内涵进行评书式评点。剧作没有剑拔弩张式的紧张的戏剧冲突,但是,在自然流动的生活图象隐层,善与恶、美与丑的对峙构成了剧作的结构内核,在历史、民族、人生的三相交叉上透露出深刻的主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剧作采用“人物绣像”展览的方法,使剧中四五十个人物,须眉毕露,各得其趣。老工人刘家祥的幽默性充满着韧性,他与小媳妇的冲突,既饱含愤懑情绪,又不乏其独特的性格情趣。当小媳妇借口“五七”建仓库要扒刘家的防震棚又自称是“一片好心”时,刘家祥说:“那是,那是!没你这片好心,小井这些年不会这么热闹。您等等再去!我记得我那咸菜缸底下好像压着个当年红卫兵的箍儿。我给您找找,找找,您戴上!戴上威风……”使小媳妇恼羞成怒,无地自容。水三儿是祖祖辈辈世袭引车卖水的穷苦汉子,他的义胆侠骨中渗透着刚正之气,使邪恶势力凛然生畏。第一幕他一出面便整治了欺凌滕奶奶的人贩子毕五,瘳廖数笔,既点明身份,又有动作感,使人物形神俱备,个性毕肖。其他如吴七的胆小怕事,许六的憨厚窝囊,马德清的慈眉善目,滕奶奶的见多识广,小曹的善良耿直,还有心软嘴硬的刘嫂、心善嘴拙的九嫂子、自作聪明的石嫂、精于权术的小媳妇、死皮赖脸的小环子,都各具鲜明个性,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总之,在具有喜剧性意味的场面中挖掘深沉的悲剧性意蕴,是《小井胡同》刻划人物、设置场面的鲜明特点。因而形成了素朴中蕴含深沉、幽默凝聚在悲剧感中的独特的审美品性。
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揭示出中国一代农民的悲剧性命运。作者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生活、解释生活。他不将人物的阶级属性作为唯一的人性内容,而是透过人物外显与内隐的行为模式,去探询积淀在社会心理中的文化历史内涵,挖掘狗儿爷身上的深潜的滋生于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的传统文化性格,使狗儿爷这一艺术形象具有更大的历史跨度和更宽泛的文化涵盖性。这部戏提供的新东西,正是狗儿爷这一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容量的形象。如果把他放到话剧文学的发展史里,可以说他是最成功的一个农民的悲剧形象。狗儿爷大号陈贺祥,只因他爹为赢二亩地,跟人家打赌,愣是活吃了一条小狗儿,还搭上了自个儿的一条小命,剧中主人公才落得这么个不雅的浑号。狗儿爷正是伴随这个父辈迷恋土地的记忆跋涉着自己七十余载的人生旅途的。他把“土里刨食儿”看成“正道儿”,是个痴迷土地、“舍命不舍财”的庄稼汉。土地是他的灵魂,“庄稼人地是根本,有地就有根,有地就有指望,庄稼人没了地就变成了讨饭和尚,处处挨挤打。”他曾经历过占有土地又失去土地的年代。在隆隆的炮声中,狗儿爷却抄起家伙进了庄稼地,拥有了土地。但是,“这把土儿还没攥热乎儿,就奶妈子抱孩子——人家的啦”,丧失了刚刚获得的土地,狗儿爷的心理倾斜了,犯了病,在奇诡的幻觉里,他梦萦魂绕的仍旧是土地。二十多年后,还是老村长李万江,提着一把小酒壶,将土地和牲口交还给狗儿爷。显然,狗儿爷因袭着父辈对土地感情的专一和挚爱。但是,这块土地及其构成特殊氛围的环境是虚化的。他承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阶段中社会历史变迁投向普通农民心灵深处的创伤,社会政治事件则被推向幕后。于是,狗儿爷沉甸甸的灵魂便直接撩拨着人们的心弦。他兼有几千年来农民勤劳、俭朴、淳厚、刻苦的品质及保守、自私、顺从、短视的弱点。他的视野极其狭窄,只感觉到像祁永年那样拥有土地是极有诱惑力的,这是狗儿爷一生追求的理想。因而,当他重新获取土地以后,依然藏有这个梦寐以求的愿望。当儿子和儿媳要把狗儿爷、祁永年生息过的破门楼推倒铲平、开辟一条新大道时,狗儿爷点起大火烧毁了门楼,火光显示出他迷恋土地的最后固执。显然,狗儿爷与土地的关系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涵意。
在艺术形式上,《狗儿爷涅》的叙述方式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交叠出现,第一人称展示了剧中主人公的情感历程,第三人称的叙述式插入,旨在使观众从幻觉中“间离”出来,从理性的高度重新审视狗儿爷的心态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以及狗儿爷灵魂波动的历程。全剧共有十六节,但采用无场次格局,以人物的意识流动为中心结构带动全剧,并且现实与回忆两部分穿插交织起来,构成了以倒叙、插叙等人物心理结构为中心的多层面的戏剧世界。因此,该剧没有显著的连贯统一的情节,也没有按时间顺序而展开的戏剧行为,剧作以狗儿爷的心理视觉在更高次上统率剧情并达到诗化现实主义的高度。显然,这种艺术手法的创新与运用,不仅以深刻的概括力和丰富的涵盖面揭示了剧作的题旨,也使狗儿爷这位悲剧性的农民形象获得了多层面的意义。
1988年的剧坛,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女编剧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最为引人注目。这部三幕四场话剧,以其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启合有度的情节构置、有声有色的氛围渲染以及主题清晰的创作题旨,形成了鲜明的具有世俗写实的再现主义风格。
《天下第一楼》以名噪京师的老字号“烧鸭子铺”“福聚德”的盛衰历史为戏剧结构情节的中心。第一幕,在北京城遗老遗少们庆贺“张勋复辟”的欢饮中,吃食业也“回光返照般地闹腾起来了”。但是,“福聚德”的两位少掌柜,大少爷唐茂昌流连梨园,二少爷唐茂盛迷恋秦服,“都不是做买卖的样儿”。靠唐家祖宗“两条板凳支一块案板”起的家业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老掌柜唐德源只得请爱出“妖讹子”的卢孟实当了二掌柜。第二幕即三年后,卢孟实心高气盛,惨淡经营,终于救活了垂死的“福聚德”。第三幕,经过十来年的努力,“福聚德”已是名噪京城的“天下第一楼”,与之“对过儿”的“全赢德”,非但没有赢“福聚德”反而被它吞并了。但东伙之间的矛盾也随着福聚德的“日进百金”的盛况而激化了。二掌柜卢孟实终于被两个不思经营的少东家挤走了。卢孟实满腔悲愤,留下一幅耐世人仔细品味的对联,拂袖而去。“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正是剧作从世事兴衰、人生沉浮中面对世态炎凉的真切感悟。一部“福聚德”的“兴衰史”,犹如一场丰盛的宴席,正是酒菜畅酣之时,也是席散人走之际。剧作者在戏剧情势的高潮使之急遽激变,把自己对人生的哲理感受醒目地展示给人们。
卢孟实是《天下第一楼》性格关系构成的焦点。他出身于“五子行”,深谙个中人物的内心困苦和辛酸,他有老父被辱身死的惨痛记忆,也有难以施展抱负的满腔苦闷。在挽救气息奄奄的“福聚德”的经营过程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该剧以他为中心构成了三个层面的人物性格关系。首先,卢孟实与两位少东家的关系决定了戏剧情势发展的方向。卢孟实是励精图治的实业家,与一位是票友、一位是侠客的少东家不是一路子人。正当“福聚德”红火万分,“日进百金”时,两位少爷却釜底抽薪,奏响了“福聚德”的“尾声儿”;其次,卢孟实与出入“烧鸭子铺”的三教九流、社会各色人等的关系,如落魄的贵族食客、沦为“辑私队”密探的克五、见风使舵的中心钱师爷、总统府的侍卫副官、胭脂巷的女人等,暗示了“福聚德”盛衰的社会内涵。而最重要的一层是作品着意铺展的卢孟实与堂、柜、厨、伙计们的关系,尤其是堂头常贵、八大胡同的青楼名妓玉儿的关系,它揭示了潜隐在“福聚德”盛衰史这一浅显故事面背后的内在意蕴。在这层关系中,二掌柜卢孟实按“高儿”修鼎彰新的比喻也是个“掌勺”的,他是苦的,李小辫是咸的,罗大头是辣的,常贵则是酸的,“大到一国,小到一室,都要有人执掌,古诗云‘盐拔金鼎美调合’,就是比喻宰相用朝廷这个大炒勺做菜。”剧作家由此揭示了被杯光碟影掩饰了的酸甜苦辣,从盘中五味表现了人生五味,透视了在中国美食文化背后的泪痕和血迹,丰富了剧作的创作题旨。
二《屋外有热流》、《魔方》等表现型戏剧的勃兴
从1979年初露端倪的戏剧艺术探索潮流起,表现型戏剧就呼之而出。其最大的特点是把目光投向人的“内宇宙”,表现人的灵魂、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我为什么死了》(谢民)、《屋外有热流》(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以死者的现身说法来展开戏剧性行为;《路》(贾鸿源)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第一次把人的内心世界作为第二自我以舞台形象表现出来;《街上流行红裙子》(贾鸿源、马中骏)在寻找刻画当代青年形象的多维视角,传达一个包裹着浓郁诗意气氛的主题;《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马中骏、秦培春)则把红、白、黑三个色块的象征意蕴由客观空间延伸到心理空间;《WM》(王培公)、《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魔方》(陶骏、陈亮等)、《挂在墙上的老B》(孙惠柱、张马力)、 《寻找男子汉》(沙叶新)、《街头小夜曲》(赵耀民)等,为开拓人的主体精神新的表现天地作了努力;《中国梦》(孙惠柱、费春放)以“梦”为轴心演绎故事,可谓是具有现代品格的“写意剧”的成功范例。显然,以表现主义倾向为主体的“探索性戏剧”,在开掘新的表现领域,探求精神世界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
《屋外有热流》(贾鸿源、马中骏、瞿新华)是一出独幕短剧,它选择了一个习以为常的题材然而写得极有新意:一方面是生动、意蕴深沉的舞台图景赋予“人最宝贵的是灵魂”这一哲理性主题的全新意味,另一方面是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语汇而形成的独特风貌,使戏剧界感到了强烈的震动,成为新时期戏剧艺术拓展新路的第一次躁动。“剧本在剧场上改变了话剧舞台上长期形成的传统格局——完整的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的戏剧冲突、凝固呆滞的时间空间。剧本别开生面地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平常的道理放在不合常理、近乎怪诞的环境和冲突中展示、使之产生出一种令人震惊的效果。”〔1〕它跨越了写实性生活表层的描写而指向生活的纵深处,完成了对生活的哲理概括。“可以把整个戏全部归结为实现生活中弟妹的一场噩梦;也可以理解为是作者一种虚幻的想象,巴不得有个灵魂出来对兄妹猛喝一声”。这个灵魂就是已经死去的哥哥赵长康,剧作者借此表达对“丢失了灵魂”的青年“强烈的义愤、强烈的爱憎、强烈的焦心”。〔2〕赵长康身处冰天雪地的北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有乐观的信念和健康的理想,终于在平凡的岗位上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性命——冻僵在雪窝里,但他的“灵魂”依然充满热情和活力。剧作者以“灵魂”的游动为戏剧行为展开的主要动力,创造了自由舒展的结构格式——时间顺序的错位和空间的灵活转换。赵长康的幽灵穿堂入室,在屋内屋外、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幻景中来去自由,使冷与热、屋内屋外的对峙成为贯串始终的象征性意象。冷与热这一自然特征,在剧中实已转化为生命的象征。弟弟、妹妹住在屋内,有取暖炉、音乐、咖啡和面包,但是,“炉火通红没有热气”、“妹妹披上毯子,弟弟披着大衣,兄妹俩仍冷得上下打战”。因为他们心里结了冰,他们丢失了一样最可宝贵的东西。兄妹俩见利忘义,浑浑噩噩,一味在“铜钱眼里跳伦巴”,信奉“有钱不捞猪头三”的市侩哲学,在狭小自私的小天地里过着没有“灵魂”的生活。因此,“在这间屋子里,火不再是热的”。但是,他们也曾是真诚的少年,有过纯真的笑声,作者因此而借赵长康的口呼唤他们:“趁大雪还没有把最后一房屋窗子封住,你们快去,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没有它,你们要冷的”。屋外,“西伯利亚寒流南下”,“气温达零下50度”,可以冻死人,但是,屋外有创造生活的热流,“马路上的嘈杂的人声;车间里汽锤的撞击声;汽笛高鸣;火车的疾驶声……”,构成了沸腾的生活,“连雪花都变得温暖极了”。“屋外有热流”,那里有“发光发热的生命的灵魂”。于是,屋内、屋外这种建筑空间的性质,被赋予象征的意蕴而获得了一种哲理性的升腾。近乎荒诞的冷热倒置与不合常规的戏剧冲突,揭示了一个平凡而严肃的主题:一个人只有投身到社会的创造性生活中,才会发出有价值的光和热,生活的热流是由无数平凡的光和热凝聚而成的。
欧洲最富权威的《格雷高世界戏剧大全》,把我国实验话剧《魔方》收入该书第十四卷,同时收入的还有《天才与疯子》(赵耀民)和《挂在墙上的老B》(孙惠柱、 张马力), 该书把这些作品列为1984 ——1986年间出现在全世界话剧舞台上最重要的剧作。的确,1985年由陶骏、陈亮等人创作的《魔方》充满了对戏剧传统观念的挑战意味,它没有统一的语汇,没有情节间的联系,自由“组合”而成的九个戏剧段落,表明对戏剧创作既定规范的悖逆。“黑洞”、“流行色”、“女大学生圆舞曲”、“广告”、“绕道而行、”“雨中曲、”“无声的幸福”、“和解”、“宇宙对话”九个片段各有其主旨和独立的品格,如关系松散的无主题变奏曲,构成了一个新颖的艺术“魔方”。它没有贯串全剧的焦点,每一段戏的含义都是多向发散的。但是,《魔方》作为一个复合的整体又透出一个共同的神韵:“舞台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大魔方,世界也是如此。”〔3〕寻找自己对世界的解法, 便是《魔方》的哲理性思考的品格,从而使缺乏因果关联的戏剧片断获得了内在的凝聚力。当代青年试图从多角度、多层次去探索社会、究竟人生。《魔方》就是以这种贴近现实人生的关切感,传达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人应该怎样生活?人应该成为怎样一个人?”这种贴近现实人生又具有哲理意味的思考品格有利于构成剧场中轻松活跃、自由探讨的气氛。因此,《魔方》的戏剧性因素包括两个层面:每个戏剧片断并不一定具有现实的直接现实性,但具有生活楔入剧场原有的特质;同时,剧作的整体性意蕴具有维系演观关系的思考品格,事实上,《魔方》斑驳陆离的戏剧景观正是人生丰富复杂图景的象征。剧中,来去自由、无所不在的“主持人”,沟通了两个戏剧性层面,成为连接舞台和观演厅的活跃因素。在时空观念上和情绪气氛上使剧场成为有利于感情挥发、心灵往返交流、感应的有效磁场,这是“马戏晚会式”戏剧《魔方》的独特艺术魅力。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易卜生式写实戏剧的模式,使戏剧艺术形式从凝固、封闭的格局中解放出来,呈现出多元、开放的发展总态势。
高行健作有《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彼岸》等表现型剧作,其中《车站》影响较大。话剧《车站》运用超现实的荒诞手法,假借一个荒诞无稽的戏剧故事,表达了作者的哲理思考与思想意蕴,即在生活中不要消极等待,不要怨天尤人,而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不断积极进取。剧本较成功地借鉴和运用了荒诞派戏剧的艺术手法;不仅剧本的整个情节框架是虚拟的、荒诞不经的,剧中的一些具体人物、情节和细节,也大都舍弃了生活原样的具体状态,而运用了反逻辑的怪异、极度的夸张以及扭曲、变形的艺术手段。如,剧中写人们在车站久等汽车不到,竟眼睁睁地看着时光流逝,说话间就过去了“整整十个年头”。那准备报考大学的“戴眼睛青年”,等过了入学的年龄;身体健壮的“大爷”,成了老态龙钟的老人;年青的“姑娘”,也满头白发成了老太婆。然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极度夸张、变异的荒诞的艺术形象,对于“时间就是生命”这一思想内涵,作了十分形象的象征和直喻。这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变形形态或突破了正常生活逻辑的荒诞逻辑的荒诞形象,不仅具有强化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的效果,同时,由于剧中所构成的现实与超现实的鲜明反差,也可进一步激发起观众丰富的联想,把观众的思绪引向生活的纵深处。《车站》与被西方视为荒诞派代表的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都共同地写有“等待”的情节,但却鲜明地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对立的思想;前者否定消极对待,要人们像剧中“沉默的人”那样,不断前进,积极进取;而后者则始终处于一种毫无意义也毫无结果的无望的等待之中,反映了一种希望幻灭后的精神危机。因而,前者表现的乃是一种本质的乐观,而后者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由此也说明,《车站》的作者在借鉴西方荒诞派戏剧上,乃是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作了有批判的和创造性的转化与改造。
1988年,沙叶新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问世,将沙叶新的喜剧性的世俗趣味和宏观的思考协调在一起,成为沙叶新十分重要的剧作。主题性的象征意蕴展开在不同文化、哲学背景的比较上而使该剧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显然,耶稣、孔子和列侬已经超越了形象本身的意义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哲学文化色彩。承载文化思考和叙事性层面的是一个熙熙攘攘如市井的天堂,若有若无幻景般的月球以及金人国和紫人国,剧作以绚丽的想象和哲理意识完成了一种寓言式的构造。天堂里,上帝已经忘记了他的誓约,而人类事实上在抛弃上帝以前已经被上帝遗忘。自古以来,人为了摆脱灾难,都借助神力。神已经疲劳不堪了。人,早就长大了呀,他还要依靠神吗?但是,人却在“渎神”的歧途上迈向邪恶。作者通过人类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对立,通过对拜金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的讽喻,揭示“人如何完善自己的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的命题,呼唤超越时空的理想存在。不过,剧作由于主题性象征的意蕴过多地流失于浅显层面,因而缺乏一种维系全剧的戏剧张力。神子耶稣、圣哲孔子和披头士列侬因为承载了不同的文化、哲学背景而较多地具有理性色彩,但是,他们又经常被淹没在具有世俗色彩的喜剧性机趣中,于是,主题性的整体象征意蕴散失在局部的、充满机趣的喜剧性场面中。
三《桑树坪纪事》、《洒满月光的荒原》等再现与表现兼容的话剧
社会的发展,变革的时代,要求戏剧艺术有新的发展与新的突破。写实倾向的再现主义戏剧仍具生命力便不再独尊剧坛,以表现主义为主体的“探索性戏剧”虽有魅力但也有其发展的障碍,于是一种再现与表现相兼容的话剧就适时而生,从苏叔阳的《太平湖》起,到陈子度、杨建、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和李龙云的《洒满月光的荒原》,标示着戏剧创作的兼容倾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审美拓展。
北京青年剧作家苏叔阳曾以《丹心谱》崭露头角,此后,他的剧作如《左邻右舍》等,以自然、真实、朴拙和幽默等特征倾向于风俗写实的再现主义风格。而他以沉着醇厚的笔法展示的《太平湖》却是一个新型的戏剧世界。该剧的副题是“无泪的长歌”,作者以此奉献给二十年前含冤而死的老舍先生的英灵。剧作再现了老舍先生的谦恭、热诚和幽默,但又不同于传统再现型戏剧在一定性格关系中塑造性格的表现方法,其传统的悲剧情绪也不再是单一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情绪,而是在历史、人生和命运的交叉点上展开老舍之死恢宏的悲剧性背景,从而使剧作深厚的情绪内涵得以整体提升。从叙事层面上看,《太平湖》是以老舍之死作为情节主线,叙述主体舒乙的回忆和倒叙中楔入老舍的回忆,老舍的灵魂活动于明幽之间,时而在与舒乙对话,时而在与老舍自己和作品中的灵魂对话,时而又与“那个人”对话,或幽幽地自审,或深深地叩问历史。作者选择了1986年8月24日和1966年8月24日这两个特殊的日子作为表现的中心。但是,在历史的长链中,昨天和今天,现实世界和幽冥地府之间已不再有隔阂,于是,过去与现在在无尽的、永不停歇的人类精神的流运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整体,历史和现实在舞台生活中平列,生命的意义也超越了物理时空而得以无限延伸。因此,《太平湖》写老舍先生之死实质上写的是老舍先生不死的灵魂,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老舍先生的灵魂之永恒存在。同时,《太平湖》中老舍先生之叩问历史,他与现实的对话,他的深沉的自我剖析,传达了超越于生命而实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自审意识,使个人的、命运的悲剧提升为民族的、历史的悲剧。《太平湖》以多层面的意识潜流为核心的戏剧世界,既与传统的具有写实风格塑造角色的趋势吻合,又超越了对人物性格的再现的深度,再将笔触深入到意识的深层次,使人物形象具有感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表明了当代戏剧创作正以现代意识推动再现戏剧兼容表现风格向现代审美品格的迈进。
陈子度、杨建、朱晓平的无场次话剧《桑树坪纪事》,是由青年小说家朱晓平的中篇小说《桑树坪纪事》、《桑塬》和《福林和他的婆姨》改编而成的一部“中国现代西部戏剧”。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片特殊年代特殊的生活。全剧没有贯串始终的中心事件,而是通过主题性整体象征意蕴使之获得内在的凝聚力。幕启,在一阵沉重、古老而缓慢的钟声中,桑树坪人邻村的陈家塬人敲着家什定着点子有板有眼地对骂着,桑树坪大队队长李金斗和生产队李主任死拉活拽。“知青娃”朱晓平与生产队大动干戈,这绝不是仅仅为了雨水在哪埠地上落和一亩地二百还是一百七的问题,而是贫瘠土地上生命的呐喊。于是,随后展开的彩芳和榆娃的爱情悲剧、月娃被卖为哥哥“阳疯子”福林换亲、青女受辱变疯、桑树坪人对异姓人王志科的围攻和村民们追杀老牛“豁子”等没有因果关联、平列的戏剧性行为就有了一个悲剧性的背景,他们的生命激情都消失在与群体力量产生对峙的精神围攻中,许彩芳是李金斗的儿媳,一个十二岁入门当“干女儿”、十八岁便守了寡的青年女子,她把青春的热情献给了麦客榆娃。许彩芳和榆娃精神和肉体的结合是极其美好而合乎人性的行为,但他们却遭到了乡亲的围殴,最后,许彩芳因不愿和“柳拐子”结“转房亲”,把生命的最后一点火花熄灭在村口的那眼磨井里。因生活窘迫娶不上婆姨的“阳疯子”福林,在桑树坪这块精神荒漠里“哭闹”但在他心底里却藏有一方明净的天地——为了妹妹月娃不哭,他可以“一辈子不娶婆姨”。但是,正是为了他能成个家,费尽心机的父母却要十二岁的月娃“女大当嫁”,远送到甘肃做人家的童养媳。青女也是因兄弟的亲事被父母草率地聘给福林的,为了唤醒福林久被压抑的生命冲动,她甘愿丢弃少女的羞涩,但是,她的忍气吞声、委屈求全,换来的却是全村闲后生们的凌辱,终被逼疯。外姓人王志科,在李金洪、李福绵父女的庇护中寻到了人生的暖意。他不愿离开这块埋着爱人的土地,于是,桑树坪人便诬告他为“图谋杀人报复”的凶犯,原因就是队里正等着用王志科的窑安石磨。在这种瘠薄而愚昧的土地上,为了生存的竞争竟能演化为一场活生生的厮杀。桑树坪人追杀老牛“豁子”的场景,使生存选择的悲剧内涵得到了哲理性的超越。祝贺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富队出了猪啊、草啊,还有鸡、蛋和干果等啥的”,桑树坪则得到指令,公社要用四十元钱买大队的耕牛“豁子”。“我们打都舍不得,可他们要杀了吃哩。”桑树坪人终于愤怒了:“那咱就不让它活着去!”最爱牛的人变成杀牛的人了,演出了一场远古初民似的围猎。这“围猎”,是《桑树坪纪事》的中心意象,它不仅使散布在局部的象征性意义获得了整体的凝聚力,同时也开掘了剧作的悲剧性主题;争取生存权利的人之自我害。于是,它便超越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获得了新的意义。悲剧性的主题因其赋予了命运的凝重感和历史的厚实感,而得到了具有哲理意味的擢升。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桑树坪纪事》择用了“电影化”的叙事格局,使剧作构成了流畅、自然的节奏形态。全剧三幕二十七节戏剧性行为没有按起承转合的程式及生活循序渐进的外在逻辑组接,而是在主题的控制下展开。巨大的转台通过人物、场景的渐次“淡入”、“淡出”,突破了舞台时空的局限性,把体现生活无序性和诗意性特征的场景有机地融入时空交错、虚实相间的戏剧世界中。借助电影艺术语汇使剧作形成了新的舞台形象。无论是李金斗按手印的动作特写,还是村民们围猎耕牛的“高速摄影”式和慢动作展开,都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它使人们从生活表象的幻觉中挣扎出来,在震惊之余对戏剧场景所蕴涵的哲理意味进行清醒的思索。理性的评判构成了这一剧作戏剧结构的另一层面。歌队代表当代人和编剧的冷峻评判,为剧作引进叙述性因素,引发人们对戏剧场景的思考,赋予场面更多的历史反思的内涵与震撼力。剧作把对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和歌队的理性判断有机融合,构成叙述体戏剧特有的审美效应。它所追求的“陌生化”效果并不排斥各章各节内部的传统戏剧性戏剧的特征,有时在具体场景处理中采用某些有象征意蕴的艺术语汇,使叙述体戏剧与传统写实的戏剧性戏剧结合在一起,既能使观众沉浸在剧作家营造的悲剧气氛中,又增强了戏剧的思索品格。《桑树坪纪事》发挥了综合性艺术的艺术兼容性,结合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表明叙述戏剧与戏剧性戏剧有机融合后所具有的巨大艺术潜力和充分的艺术表现力。
李龙云的《洒满月光的荒原》(又名《荒原与人》)则在历史、社会、自然和人生的多相交叉上开掘人的生命意识。它的总体背景氛围是价值的失落、现实与理想的对峙和人的自我分裂。剧作在对生活在北大荒的拓荒队的知青的表现中,包含着一种对人类的思考,把哲理思索化为艺术表现,使《洒满月光的荒原》获得了哲理的凝重感和真情的感染力的有机融合,完成了他艺术创作的新飞跃。
《洒满月光的荒原》是人类生命意识的多声部交响。这部生命的交响奏响在“人的两次信仰之间的空间”。“当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就是一场大风刮过,殿堂上的一切,连同所有的粉末统通被刮走了。人感到失去了归宿,人性失去了平衡,人在茫然不知所措中开始了疯狂的寻找自我……为理想而奔突的人最终没有找到归宿,人的永恒的失落感便成了它的悲剧性背景。荒原,既有地理概念上的指代意义,又被赋予心理概念上的特定内涵,它是人生存的客观存在,也是精神家园的荒漠。”这部交响曲的主题是马兆新带有生命原质的冲动,它表明人在宗教中寻求心灵平衡的失败。马兆新需要宗教的慰藉,也有现世的需求。人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马兆新的情感世界也始终存在着两极对立的倾向。他对细草的感情,一方面是理智支配下的温柔、爱抚、理解;同时又有狭隘、嫉妒、占有欲所带来的暴躁与残忍。他采用“世界上只有男人对女人才作得出来的报复”,发了疯似地轰赶着辕马,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送给了一位愚蠢的马车夫。在爱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远走他乡。剧作家由此深刻地昭示:“有人说,世界上最残酷的斗争总是发生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其实这是一种偏狭。最残酷的斗争是人与自身的搏斗。”该剧中的马兆新分裂为两个自我:一个是当年的马兆新,一个是十五年后带着淡淡的忏悔和自审意识的马兆新。十五年后,重新回到落马湖的马兆新,展示了以青春为代价换来的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但是它无法掩饰精神家园失落而带来的惆怅和苍茫。生活从来不给人第二次机会,马车与爬犁的反复错身而过,那永远平行着而不会再有交叉点的深深辙沟,使剧作对个人命运的象征提炼擢升为对人类生命的沉吟浩叹。苏家琪和宁珊珊、李天甜的爱情生活构成了该剧的副部主题。人类需要通过爱情获得心灵的平衡,但是,爱情却充满战争和死亡的阴影。在人人都希望去打仗的年代里,胆层的苏家琪孤零零地留了下来,宁珊珊走出落马湖荒原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为逃避孤独而死去的人带来的是双倍的孤独,而死者孤寂的灵魂需要活者的抚慰。苏家琪和李天甜的爱情使荒原充满诗情,但是,为追求美的完善,李天甜不惜投身落马湖沼泽,把美投向黑暗和寂冷。这就是该剧思考的人类生存的两大支柱:宗教和爱情。
在艺术形式上,剧作在过去和现在的支点上观照人生,以人物内心独白为叙述主体的戏剧格局形成了多层次的“对话”形式。剧作的主体部分是由无数浸透着人生体验和饱含诗情的内心独白组接而成的,剧作家创造性地把人物与自己的独白作对白式的处理,使人物的心路历程带有浓厚的自审色彩。十五年前的马兆新、六岁的毛毛和十五年后的毛毛,甚至十五年后的马兆新楔入回忆中的人物对白中,并引进叙述因素来调动读者的哲理性思考。剧作家还常常把人物独白作对白式处理,使传统再现主义戏剧中相对独立、静止的独白呈动态特征,使人物深层意识的潜流化为心灵的有声交流。与对人物的心灵剖白过程对应,剧作还建立一套音画交响系统,教堂钟声和丘比特塑像、落马湖钟声、板胡、小号、长笛和大鼓等听觉因素;荒原、月光、火苗、大火和太阳等视觉因素,把落马湖荒原人的精神探索历程以强烈的音响和视觉画面诉诸于人们的感官,强化了心灵探索的历程和人类生命流动的历程。
注释:
〔1〕苏乐慈:《〈屋外有热流〉导演阐述》。
〔2〕贾鸿源、马中骏:《写〈屋外有热流〉的探索和思考》。
〔3〕陶骏、 陈亮:《我们的解法——〈魔方〉编导原则的几点诠解》。
标签:戏剧论文; 魔方论文; 艺术论文; 天下第一楼论文; 文化论文; 老舍论文; 车站论文; 小井胡同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剧情电视剧论文; 喜剧电视剧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