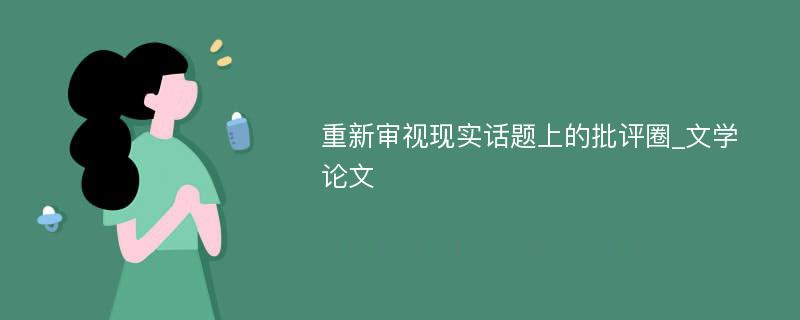
现实主义话题再热评论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话题论文,评论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位评论家说过,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坛上,也许没有什么“主义”能够像“现实主义”这样与文学的进程始终“纠缠不清”也“纠缠不休”。当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现实主义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现实主义重新成为热门话题的起因是,近一两年来文坛上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界出现了一批深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密切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其中许多还直接切进了当前改革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基层农村这两大正面战场,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侧面的真实状况。如有评论者指出:这些作品面对正在运行的现实生活,毫不掩饰地、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以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并力图写出艰难竭蹶中的突围。它们注重当下人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贯注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其时代感之强烈、题材之重要、问题之复杂,以及给人的冲击力之大和触发的联想之广,都为近年来所少见。
至于这种现象之所以形成,其实个中原因并不难理解。现在人们所处的正是一个历史在发生前所未有深刻变化的时刻,旧有的传统社会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人们之间新型的社会关系正在逐渐形成,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也正在萌发。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人们自然会呼唤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式的“时代书记官”,在其作品中将这一社会面貌忠实地记录下来。然而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某些方面却并不能令人满意。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严峻问题被有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人们在生存中感受到的艰难也常被局限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圈子中。而这些切入现实生活的小说的出现,则较大地拓宽了生活表现领域,其立意也得到了深化。它们并不回避世俗性,但已不再专注于一个小人物或一个小家庭的日常生存戏剧,而是带着更强的经邦济世的色彩,着眼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和整体的生活走向,这就使作品比以前更凭添了一些参与意识与使命感,使社会转型中的状况得到更深广因而也更真实的表现。虽然在人们看起来,这些作品较多地停留在现实的形而下表层而稍显肤浅,但多数人还是为这些作品的出现表示出惊喜和欢呼。因为这些作品以其不回避的勇气揭示了大量新鲜矛盾,提供了鲜活的新形象和新图景,并以其对时代生活的崭新思考和密集的信息给人们带来新的审美冲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学总格局上的某种缺憾,满足了读者的某种需要。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能够引起广泛关注,这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现实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对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作深入腠理的真切表现,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现实的逃避和扭曲。的确,中国社会的复杂变化给作家们把握现实带来了一定难度,但这丝毫不能构成作家逃避现实矛盾、放弃对社会历史深层关注的价值追求的理由,否则其作品只能因营养贫瘠而丧失其魅力。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写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是对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最起码的要求。一个真正具备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不仅要能够拥抱生活,更应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把握社会历史的脉搏,同时将自己深刻的体验通过冷静的沉淀,作出审美的锤炼,以熔铸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精品。
二
在对于当今现实主义创作的看法中,有一些评论者不同意“现实主义回归”的看法,他们认为现实主义创作从来也没有走失,即使前一阶段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声嚣日甚时,现实主义创作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质量看依然未处于绝对劣势。若说现实主义的确有时在与其它流派的竞争中显得过于羞涩,那其中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些现实主义创作抱残守缺,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新近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上的收获正是经历了“主义”林立的洗礼之后,对自身模式既有继承又有突破的结果。它们更真切地把握变化了的现实状况,更深入地刻画了人生。也有些同志不赞同这样看法。他们认为,前一阵子,现实主义在舆论上受到一些同志的贬斥,在实践中遭到一些同志的冷漠,这是不争的事实。主义的林立、旗帜的翻新,固然使人开阔了眼界,但文艺与人民、与时代、与生活的疏远,确也给文艺本身带来了窘迫与尴尬。正是窘迫与尴尬教育了人们,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现实主义的不可抛弃。现实主义要不断发展,要不断地吸收各种养料,它植根于生活,而生活之树本来就是常青常新的。所以,真正的现实主义与抱残守缺是绝缘的。把现实主义的一度被冷落说成现实主义本身的过错,是不公允的;把现实主义的新收获归功于“主义林立”,也是欠准确的。这两种观点的争鸣,无疑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当前创作的认识。
当今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表现出新的特点,为我们深化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人们注意到,它们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对社会现实和对人的认识上。
谈到这些作品对于当下社会现实关系揭示的独特性,用刘醒龙一篇小说的题目就可以概括,这就是“分享艰难”。有评论者指出,在这些作品中,现实关系有了与以往作品中常见的“斗争”形态与“同一”形态都不相同的“磨合”形态,从中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听到一些美好的东西被磨损时的呻吟;同时更能看到人性党性在“入世”而非“出世”的多种磨合中闪闪发光,它留给人们的是分享一份艰难的气度和力量。应该承认,这些作品以更全面、更冷静、也更求实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某些现实问题的尖锐性,把文学的真实领域发掘到一个新的层面。但如何来“分享”这种艰难,有些作家和评论家显得有些惶惑。因此,有评论者在里面嗅到了一些“温和的”气息,也就是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将原来激烈的矛盾冲突逐一化解的文本结构。而且,作家还对于人物身上的利己性、唯利性和实用观也给予“温和”的关照和宽容,这些都是与分享艰难的立意相一致的。认为只要人为地“分享”一下“艰难”,达到一种“谁活着也不容易”的共识,就可使社会结构转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解决大半,这不能不说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这说明有些作家还未站在更高的历史制高点上去看待时代的发展。对此,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文学凝视现实时,不能滞留于现实某一横断面或角隅之中,它需要的是历史眼光与纵深的把握。要把现实横断面与深远的历史相衔接,从当代中国(甚至更为古老的)历史的曲折道路中考察,才会深深认识到这场改革有其历史必然性,是改变贫困落后的必由之路。这艰难是新旧体制转型的“阵痛”,它不仅需要“分享”与心理承受,更需要深化改革。
三
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来说,人物的塑造是创作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缺少了对人物的成功塑造,现实主义创作就会大减其成色。
针对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不同,有评论者指出,近来一些小说的人物的价值中心在于“身份”而不在于性格。人物对他人身份和自身身份的疑问、调整和确认,恰恰体现出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各种利益的摩擦。而在“身份”中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形象。他们身为官员,同时又最为近切地联系着广大民间,常常作为官与民的混合体。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样的人物是作为融摄社会关系的首当其冲的枢纽式人物出现的,这样便使外在的社会性矛盾转化为人物自身中的一个焦点。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的步伐如何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一步步向前迈进,或许其中融合着许多艰难困苦。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注重人物“身份”的同时,切不可将“性格”忽略掉。人们常说,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故事情节的枝干上并没有结出多少人物之果,即是指作品重在把握围绕“事件”所交织起来的复杂的社会现实,但缺少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这恐怕就与缺少有深度的、富于个性魅力的性格刻画有关。因此只有在深刻把握现实关系的同时,深刻地把握人物内在灵魂,使“身份”与“性格”有机结合而不能偏废其一,才能达到现实主义创作所要求的典型化高度。
人们还注意到,近年小说创作中的许多人物身上都弥散着一种“中性色彩”,即人物多是亦善亦恶的交织,呈现出不黑不白、不冷不热的“温和色”。这些人物在总的方面保持正直善良的同时,也有不少芜杂色彩甚至是某些“恶”的方面。这个中的缘由恐怕是因为单纯的“善”无法适应这一日趋复杂的社会。虽然我们不可否认在现实中金钱与道德、物质与精神、恶的手段与善的目的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但在如何去写“恶”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警醒。作家可以不在作品中明确地加以谴责,但无论如何不应该表示宽容与认可,哪怕是以什么历史进步的名义。这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最起码的道德出发点。人们心中隐藏的忧虑是,一批“中性人物”的出现虽比以前较有突破,为人物形象画廊增添了新的内容,但如果将这条路一味走下去,写人物一定要写得不黑不白、不冷不热、善恶交织,难免不会成为一种新的“模式化”,从而也会违背作家创造人性深度的初衷。
四
如果我们把视界放到世纪之交的文化背景上,就会发现,这场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并不限于这一创作方法本身;从某种角度上说,它因袭的是前些年风起的人文精神论题,是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借现实主义话题的继续。
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当前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最大的缺陷是只写出了社会生活的一些表面现象,缺乏更深层次的超越性的东西,缺乏对人的灵魂的关注,缺乏更高的人生信念,因而表现出迷惘和犹疑,甚至对一些现实流弊也显露出迎合和迁就。这种评判的潜在含义是要求作家必须承担“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崇高而神圣的责任,以一种更富“理想主义”的话语去做前进的导引。因为,缺少了理想价值便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这种启蒙色彩浓厚的论点实质上契合了人文精神倡导的某些特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将“现实主义精神”当作为“人文精神”的替代语。更有一些人尤其强调了现实主义的所谓“批判性”,在精神态度上摆出了一种启蒙大众的精英心态。他们认为,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中,更多的人在有意为之的理念上尚缺乏批判现实主义的主体意识,缺乏抵抗平庸和流俗的批判性勇气,这实在是文学莫大的悲哀。
而一向是以“后”学昭显的人物,却似乎也在那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为支持自己解构启蒙理性的论点找到了依据。在他们看来,这批关注现实的文学正是“中国‘后新时期’的‘社群文学’”,即对于“社群”的当下形态的关注与表现,力图分享共同文化、凝聚社会“共识”的文学。它们所试图建构的“社群意识”乃是基于对一个共同的社群生活的认同与归属感而产生的对话、沟通与交流的意识,它导向一个情感空间的生成。这位评论者对“启蒙者”的角色不抱太大兴趣,因为那正是他希望被消解的对象,他倒是宁愿作家们降格为一般民众的水平,对社会尤其是当下的现实生存多做些世俗的关怀。因此,以这种“凡人”的眼光来看社会,常会发现道德的善恶不象是“小葱拌豆腐”式的一清二白,“发展”也不是正义取代邪恶的简单过程,而是在冲突中求沟通和妥协,用哪怕是不够崇高的世俗的方法为这个社会贡献责任。否则一味强调“清洁世界”,则无疑是“对于‘当下’的无尽的恐惧与仇恨,对于‘发展’的敌意与反抗”,是“一种破坏性的、充满敌意的、造‘墙’的、与普通人彻底隔绝的文学”。这也就难怪一些作品对社会转型期矛盾少加评判的“中性”描写,让这位评论者不亦乐乎。
然而也有一些评论者尽管也对人文主义色彩浓厚的“启蒙”话语不以为然,但也有别于解构“启蒙”理性的“后”学者。他们倒是十分注重创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较少抽象层次的清谈。有评论者认为,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一度成为滥觞,这种倾向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束缚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今天一些作家实实在在地描写现实本身,把笔触深入到人民的生活深处,写出现实的严峻艰险,写出生活的生机与创造,这种积极的态势也许会成为文学主题开拓的新发展点。
有的评论者也站在相似的立场上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提出质疑,认为对现实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对现实真切把握、反映时代的本质真实,而不一定非要批判。作家对现实的“批判”必须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及可行性,不能为批判而批判。因为无论怎样深刻、尖刻乃至骂娘式的批判,都不能象现实的社会实践那样解决现实中的生存难题。而那些一味强调“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批评家们将那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视为向“权力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或献媚,实在是在“现实主义崇拜”情结的纠缠下自寻烦恼地预设假想敌人。那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不以批判的视角和方式来反映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正是体现着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体现着当代中国特定社会历史状况及人文状态的新兴文学形态。
不论对新近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人文精神态度如何,评论者中的多数的出发点都是在关注人民大众的生存境遇,都是为世纪之交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作着殊途回归的思考。任何优秀的现实主义之作都必然包含对人的关怀,正如有人所说,文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人性的描述和评判。正是对人的新的生命活力和人生观念的呼唤,才是现实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理由、价值和真正吸引中国读者的魅力之所在。
现在,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势头依然强劲,而与此相应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也在深入进行,但愿这场世纪之交的讨论不会仅仅成为关于“现实主义”概念的清淡,而真正能对我们的创作实绩有所助益,使我们的现实主义创作得以用崭新的面貌步入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