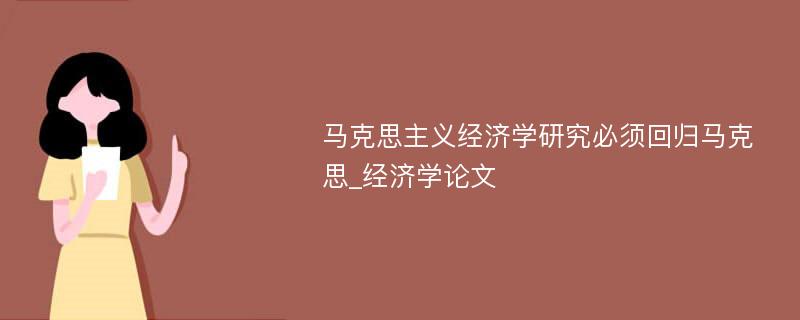
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必须回到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继承,二是发展。所谓继承,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范畴、方法、结构、理论及至体系的形成有一个完整、准确的把握,这样才是真正的继承。我国学者早就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80年代末期,理论界还是传出了要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完整意义的呼声(注:参见刘英:《应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完整意义》,《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0期。)。这说明,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存在着非科学的东西,需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否则,就只能是“非马克思的马克思”或者是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发展,就是在准确、全面继承的基础上,适应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主题变化,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这种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就是赋予马克思经济学新的时代特征的过程,就是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剖析的过程,就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前,继承和发展同样的重要。只有正确地把握了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才能摈弃一切非科学的东西,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科学的继承和科学的发展。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一点思考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发展为我们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指导。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因为,对象问题的解决是一门科学得以确立的前提。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是涉及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关键。在马克思之后,恩格斯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建立,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成为争论的焦点。列宁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早在19世纪末,列宁就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观点。《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列宁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注:《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166页。)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 列宁阐明了同样的思想:“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注:《列宁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42页。)。 列宁的这些认识虽然并没有特殊地强调研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还是从政治经济学一般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进行阐述,但是表明了列宁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原理的捍卫。
马克思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曾明确指出:“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8月第1版,第487页。)所以, 马克思经济学不是生产本身的科学,因为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就是因为其对象的特殊性。马克思所建立的经济体系虽然对广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一些指示性的论断,但是更多地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还是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这是恩格斯早就说明了的。
但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中,我们必须注意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既不能将其限定过死,也不能将其无限泛化。所谓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般性,就是指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6月第2版,第492页。);所谓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就是指适应于不同时代或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制度特殊生产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对象。
问题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或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其一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限定在生产关系上,或者说仅仅研究生产关系本身;其二是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泛化理解,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一切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任何事情。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对社会经济制度深入分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的分析,认为在物的关系外表下的生产关系才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也就是说,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整个生产环节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将这一研究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则必然地使得研究对象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限定在生产关系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限定在“生产关系”本身,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了在一个设定前提下进行理论推导的空洞、乏味的科学——这个前提就是:生产关系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而这恰恰是错误的。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最初,马克思是将私有制作为研究对象的,而这一“研究对象”虽然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但是却无法揭示私有制以及私有制的基础——私有制财产的内部联系,或者说无法揭示私有制得以产生、发展的规律。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从“私有制——私有财产——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演变过程,并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起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大厦。这一过程表明,马克思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一个层层剥笋、逐步深化的过程,是一个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过程,因此,才使得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这里成为科学。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并不是纯粹逻辑上的推导,这是马克思本人所痛恨的。恰恰相反,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与时代发展的脉搏相一致,并且是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统一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
因为,历史的顺序和逻辑并不是一致的,对历史现实的揭示是在逻辑上进行解释,这不能取代历史发展本身。但是,如何科学地对历史现实进行解释,则是研究者运用逻辑工具能力的体现。马克思正是由于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革命,从而可以在唯物史观之下运用科学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进行解说,并揭示其发展趋向。所以,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确定既不是单纯的历史的复述,也不是单纯的逻辑推导或演绎,而是在对客观事物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得出的,是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统一中作出的。也因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进行分析的时候,并不是局限在生产关系本身,而是首先对大量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貌。这一点,无论是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大量手稿中、还是在马克思生前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都可以得到说明。
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并不是先刻意地规定一个研究对象来进行研究,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对研究对象进行丰富和说明,并最终揭示对象本身。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实现的,而不是预先设定,再反过来为了这一对象进行证明。在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说明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现实的生产为起点,就必然要联系生产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进行。所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对象决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或者进行生产关系的单纯演绎的。
可是,是不是说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一切经济活动中问题的呢?这种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泛化的观点也很普遍,尽管这种认识是在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旗号下的,是为了赋予马克思经济学以现代意义或与现代的经济学接轨。但是,这种趋势不仅造成了对马克思经济学本身的误解,而且有可能损害到马克思经济学的未来发展。
无论是直接的生产本身,还是生产的流通过程、劳动及其劳动力、最终的产出物……都是在说明生产关系的时候才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作出了许多说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首先是从商品这一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为切入点的。商品首先表现为使用价值,商品主体本身的使用价值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商品入手并不是由于商品的直接使用价值,而是作为这样一种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的,而“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2版、第10页。)。同样,对于财富本身的研究,也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马克思指出:“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页。)。所以,马克思将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限定在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上,所有要研究的事物也只是由于其体现了生产关系才纳入分析的范围的。
因此,在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的争论的解决方案,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回到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上来。无论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还是由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而忽视了对生产关系的揭示都是错误的。同时,在马克思那里,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始终是与现实经济问题揭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抽象、空洞的批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显然,正确认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对于我们在今天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重要意义的。许多研究者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种种方案,有认为是研究生产方式、有认为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注:参见张熏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等等。关于研究的起点也是众说纷纭。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在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借鉴过程中,由于社会发展重点的转变,关于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就更加模糊和混乱。
列宁于1920年写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中,就已经对布哈林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的论点进行了批驳:“(1)定义比恩格斯的倒退了一步;(2)商品生产也是‘有组织的’经济!”同时,对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的断语(注:参见【前苏联】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1—2页。),列宁指出:“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ⅠV+m和ⅡC的关系吗? 还有积累呢?”(注: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版,第2—3页。 )这里列宁不仅说明了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整个经济运行,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不是仅仅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科学——尽管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同时也揭示经济运行的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仍然是揭示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变化的规律。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仍然是商品,而不能是其他的东西。在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作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作为人们劳动的生产物,仍然包含着不同生产者之间(这些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现实的发展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股份制的施行、外资的引进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等等)的关系。即使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仍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的物品也仍然体现着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那个时候,这种关系不体现对抗性质。
所以,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发展及其理论结论表明,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要在对经济现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仍然要以商品为起点,揭示社会生产关系。当然,这种研究的侧重点会随着社会历史发展重点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改变。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一个说明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发展表明,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中所涉及到的事物的研究和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是不同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政治经济学和纯粹经济学——单纯研究经济活动本身的经济学进行区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它要揭示的是在物的表面之下的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结成的关系,揭示这种关系当然要对经济现实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只是为了“揭示”的手段而非目的。所谓的“纯粹经济学”则只是描述经济活动本身,并且只是说明收益本身,而不深入探讨这种收益的来源,或者说,并不探究财富增长的终极原因,而只是说明收益增长的情况。所以,纯粹的经济学可以解释在一定投入基础上会产生多大的收益,而不能解释这种收益是真实的财富的增进,还是仅仅是流通中产生的“贱买贵卖”。所以,马克思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在这样的总体生产背景之下,在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四个环节统一的框架内对财富生产的根源进行研究。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使得这一研究就必然解释二者对立的经济根源。这就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在这一过程中揭示了财富或价值本身的产生基础。所以,为了第一个方面,即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就必须用“抽象力”来进行。这种“抽象力”所运用的场所,当然地是现实经济生活本身。对于第二个方面,即揭示财富增进的原因,也必须用抽象力来进行,其所运用的场所自然是对生产关系揭示的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讲,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同于纯粹经济学的方法,而更多地体现出政治经济学特有对象所特有的方法。
一般地解说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在掌握这一方法后如何运用它去分析问题。简单地说,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无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体系构建的方法,都是围绕着研究对象而变化的。对象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是研究方法,结构的方法是体系构建的方法。当然不能截然分开。在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时,我们往往犯一些错误,这最明显地表现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中。
作为研究方法可以有许多种,现代科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分析工具,如数量分析、边际分析、归纳法、演绎法、抽样调查……等等。但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由于其研究材料和对象的特殊性,使得这些方法仅仅是基础性的。重要的是马克思所建立的科学的辩证法。所以,在研究和体系构建中就需要处处以辩证法为圭臬。
马克思穷其一生的经历,揭示了现代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建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为了科学地阐述剩余价值的产生、实现和分配,就必须在纯粹状态下进行研究和说明。这一论证的前提就是对各种现象进行考察,并且“对各种现象要在他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212页。)。因此, 就必须通过特殊来研究一般。在对特殊进行了研究之后,就需要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书评中,曾经对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说明,即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首先要解决“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1页。)这当然是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也只有采用这一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5页。)。因此, 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既不是抽象的演绎法,也不是对现实简单的归纳法,而是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统一中的科学辩证法。
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也只有在具备了科学的知识形态的共同特征和内在条件之后才能再现出自身的规律。但是,由于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没有从本质入手,导致的是为了说明已经“假设”了的结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24页。), 从而违背逻辑论证和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29页。)。这样,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也就不是科学的体系了。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所谓的“体系热”,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蜂拥出现,带有强烈的“制造体系的外表”。因此,马克思关于方法的启示,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经济学的指导。
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及其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结构,马克思给我们也留下了许多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应该成为在未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过程中需要时时警醒的。
首先,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这是在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时候要把握的重要一点。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过程看,马克思不仅研究了当时西欧——主要是资本主义最为发展的英国,而且对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也都进行了尽可能的研究。同时,广泛研究和涉猎包括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和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有益结论。广泛关注包括工艺学、科技史、农业技术等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学科。这样,就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建立在全面的、扎实的基础之上。或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776— 777页。)这些研究不仅使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并且使马克思能够用最新的成果去充实自己的理论、用最新的方法去进行研究,使得马克思经济学博大精深。
从马克思经济学本身来看,它从商品出发,循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断由最包含着最丰富规定性的简单范畴,上升到规定性不断丰富的范畴,从而将整个经济关系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纳新的范畴和规定性的过程。所以,必须充分认识马克思经济学的开放性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使其得到发展。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是一个动态体系,而不是僵化的教条。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 版,第406页。)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 都有其特殊的国情,任何一种理论不加以改造,就不可能发挥理论的威力。马克思自己也说过,如果把他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的话,这是对他的历史理论的误解,这样做,会给他带来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带来过多的侮辱。1886年恩格斯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重要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在实践中,仍然在僵化、教条从而也就是错误地理解和运用着马克思经济学的若干原理,在从事大量的把马克思经济学“经典化”的工作,人为地把马克思经济学与实践越拉越远。在世纪之交的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恩格斯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95页。)
再次,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马克思经济学过时论,一种是研究中的贵族化倾向。马克思经济学是革命的理论还是建设的理论之争,是过时论在我国存在的主要根源。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社会科学家和革命家,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只是分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只是革命的科学,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下降。这种观点在中央高层最早是1965年林彪提出,多年来虽然对此错误观点不断批判,却其仍不时地显示出来,繁衍出形形色色的马克思经济学“过时论”,以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中央确立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许多人叫嚣搞“私有化”,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不可能提供中国改革的良方,甚至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改革的障碍,等等。这都说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准确、全面、科学地理解,将马克思经济学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体系的重要性。
同时,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贵族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当成一个小学术圈子里进行讨论的东西,而不进行通俗化的解释,使得一些观点以讹传讹。马克思生前曾经一再表示,如果有时间,要写一本“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的”的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9 月第1版,第250页。),而将马克思经济学通俗化、人人能够理解,是当代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如果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成了“阁楼人语”,那么就扼杀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
第四,就要把马克思经济学当作一个科学的经济学体系,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说教。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实际的深刻考察,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所以,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一部“发达商品经济论”,这是不无道理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分析了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分析了各个社会阶级的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分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问题,分析了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运行及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等等。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认为马克思在现代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以,用现代经济学的眼光看,马克思经济学有它内在的科学价值。我们理当坚持、继承、丰富、完善和发展它,而不是象以前那样盲目地尊崇它,现在又盲目地抛弃它。
最后,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科学理解和发展的时候,必须深刻把握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的内涵,防止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等等现象。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博大精深,需要扎扎实实地钻研,所以浮躁是无法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一定要善于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第815页。)邓小平也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运用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所以,必须花费扎扎实实的苦功。
收稿日期:2000—06—15
标签: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