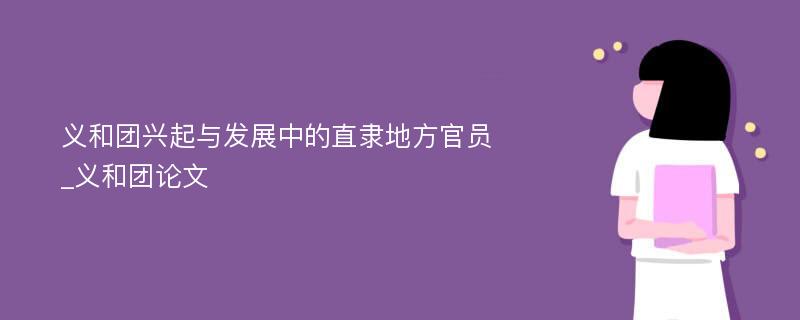
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的直隶地方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运动论文,地方官论文,直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也是这一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的兴起和发展、其迅猛性和狂热性,以及导引人们心理的无序互动,除受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诸因素影响外,清廷和直隶地方官的态度和决策也是影响义和团运动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往对此尚缺乏研究。本文拟就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直隶地方官对义和团的态度、政策及心态进行探讨,希望有助于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深入研究。一
直隶地处京畿,对拱卫京师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直隶的控制,在地方官的设置上,只设总督不设巡抚,避免了督、抚同城相互牵制之弊。直隶总督是直隶地方政权的最高首脑,并以其为核心,形成了包括布政使、按察使、督学御使、道、府、州、县官在内的一个地方统治系统,成为清王朝统治直隶人民的直接工具。
1898年春,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渐激化,直隶大名府出现了大刀会团体,“其秘密宗旨,颇似一种谋乱,天主教士,时与之发生争端。”据称,外国教士亨利和来因士两神父被害,便是大刀会会员所为(注:吴宣易《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7页。)。 他们在民间散发反洋教揭帖,并与山东曹州的大刀会开展联合斗争。接着,直隶与山东交界地区,如广平府之威县,冀州之枣强、南宫,河间府之景州、吴桥、阜城等地,陆续发生民教冲突。他们以武装反抗教会势力的压迫为中心内容,烧教堂、杀教士,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直隶东南部的教会势力,鼓舞和促进了其它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面对刚刚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以直隶总督裕禄为首的地方官仍把其看作一般的民教冲突,把威县、枣强义和团攻打教堂之事称为“拳教之案”。对于这一系列教案起因,裕禄认为,“入教之人往往欺压平民,教士不问事理曲直,多方袒护,”最后导致了“民间积忿已深,铤而走险”(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第216页。)。但是, 为了一省的安定,为了阻止列强的横索刁难,裕禄饬令地方官迅速办结教案,修复被烧教堂,抚恤被扰教民。大名府在解决开州等地的教案时,就由开州库存及开州等三县调拨1000两白银作为赔偿教堂、教民损失之资。(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二辑,第49—50页。)此外,直隶地方政府还调拨一些军队驰往重要地区驻防,对义和团采取了查禁政策。1898年秋,大名镇总兵吴殿元、大顺广备道万培因选派得力营弁,酌带马队,驰往威县、曲周等地驻扎,保护教堂,弹压解散义和团。1899年11月底,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部3营, 赶赴景州、阜城;12月,当景州等地义和团合攻朱家河教堂时,梅军将领范天贵率队前往劝阻,与义和团发生冲突,义和团死伤五六十人,武修等80余人被捕。武修和尚被捕后,押往朱家河,遭受了严刑拷打、断其手足等酷刑,最后壮列牺牲。鉴于当时山东、直隶两省义和团此来彼往的情况,1900年初,裕禄还致电山东巡抚袁世凯,建议专派营弁,与直隶所派军队,“不分畛域”对义和团进行“合力捕缉。”(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二辑,第73页。)他们对义和团采取的联合镇压政策,基本上是原山东巡抚张汝梅给直督裕禄电中所说的“饬县会同东省营印,并力弹压解散”(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二辑,第29页。)政策的继续。
在裕禄调解、弹压解散政策的影响下,直隶东南各州县的地方官采取了相应措施。1899年冬,梅东益及景州、阜城、故城、东光及吴桥五州县令同赴景州,共商查办义和团之办法。他们认为义和团是犯上作乱之徒,而非爱国忠君之辈,“其人数众多,蔓延广远,声势浩大,骄悍难驯,非厚集兵力,不能镇服”(注:资料丛刊《义和团》(四 ) 第474页。)。为了找到对义和团进行镇压的依据, 吴桥知县劳乃宣写下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把义和团定性为白莲教之余孽,并向直隶总督提出了“正名以解众惑”、“宥过以安民心”、“诛首恶以绝根株”、“厚兵威以资镇慑”、“明辨是非以息浮言”、“分别内外以免牵制”(注: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467—472页。)六项具体建议。阜城知县王柏峨也遵承上宪旨意,对义和团首领及其团众进行了残酷杀戮,临阵村的义和团首领赵斌,八里屯村的耿振楚、米家小营的米书秀等相继被捕入狱。许多团民被迫逃亡他乡,有的甚至隐姓埋名,终生未归。
直隶地方官在查禁义和团的同时也设法保护教会势力。直隶总督裕禄在给其属员下达的指令中,不厌其烦地要求各地切实保护教堂及教民,“毋稍懈忽,致酿巨案,同干严谴”(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二辑,第33页。)。除抚恤教民外,被派往各地的清军,还担负起保护教堂的职责。1899年底,当范天贵得知张家庄教堂有遭拳民围攻的危险时,立即亲率军队到教堂内驻扎。每天如有余暇,即带一、二个护兵在寨墙内巡防,一面鼓励教友,一面指示方略,“教士教民莫不依为保障”(注:献县教区《义勇列传》(一),1935年版,第480页。)。为了协调地方官与教会的关系, 裕禄还调离了与传教士关系不融洽的威县知县戚朝卿,而由熟悉洋务的后补州牧胡良驹署理,以期更快、更好地解决民教冲突。
总起来看,义和团兴起之初,直隶地方官所采取的政策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多数直隶地方官对义和团采取调解、劝谕解散的政策。一方面,直隶省府向有关州县调派军队进行镇慑,以兵威来劝谕义和团解散;另一方面,裕禄令按察使廷雍将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印制百余本,在有义和团运动的州县广为散发,用以瓦解义和团。各县也纷纷张贴告示,“出示谕禁”,许多知州、知县还指派地方士绅到各村落进行游说,劝阻百姓习拳练武。直隶定兴知县罗正钧就曾嘱托城关绅士,函至本县牛家庄、老李村、仓巨村,“劝谕解散”。(注:《义和团》(一)第443页。)这充分说明, 多数直隶地方官是以解散义和团为最终目的。裕禄再三饬令各地“以遏乱萌”,便是害怕引发中外争端,以保一方平安。
其二,直隶地方官对义和团的弹压审慎而有限。裕禄并没有完全采纳劳乃宣的镇压政策,他经过“一再筹度”之后,认为对义和团“非稍用兵力,不能震慑解散”(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59页。)才下达弹压命令。其实施弹压是以义和团抗官拒捕为前提,使用“稍用”两字,也限制了对义和团弹压的规模和程度。在具体的弹压过程中,虽有梅东益对义和团的剿杀,但总的来说,对义和团没有采取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方式。重点捕杀了义和团的首领,对于普通的团众并没有尽数追杀,只要求拳民按教民所受损失酌量赔偿,其它作乱之罪一笔勾销。(注:《义勇列传》(二),第12页。)
其三,在大部分直隶地方官对义和团进行调解、弹压解散的同时,也有少数地方官暗中对义和团采取了庇护态度。枣强知县凌道增,在本地义和团团首王庆一率众闹教之时,不仅没有认真缉拿,还任其自由出入衙署。当军队前去捉拿时,王庆一却事先逃脱。1899年8月, 故城义和团将大列庄等教堂先砸后烧,故城知县、河间知府等“无论大官小员,皆敷衍从事,一连数月之久,毫无结果”。(注:《义勇列传》(二)第2—3页。)
总之,在义和团兴起之初,多数直隶地方官的敷衍姑息政策,为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
1900年春,伴随着直隶持续奇旱、饥民充斥和瘟疫流行,义和团运动在全省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以直隶省府所在地保定为中心的直隶中南部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任邱、雄县、霸县、静海、清苑、安肃、定兴、涞水、易州、涿州、新城、固安、安次等地,均纷纷设坛练拳、开展仇教灭洋活动。甚至北京、天津也出现了义和团的坛口,并迅速蔓延开来。同年夏天,芦汉、京津铁路沿线的京、津、保三角地带的义和团运动逐渐走向高潮。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完全出乎帝国主义者、清政府及直隶各级地方官的意料。面对日益壮大的义和团队伍,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剿、主抚两大派,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则表现为态度暧昧、剿抚不定。这种情况直接影响着处于天子脚下的直隶地方官,使他们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对策和态度。
1、总督剿抚两难
义和团运动在直隶腹地进一步发展后,直隶总督裕禄继续主张对义和团采取弹压解散政策。当得知任邱县梁召村义和团持械抗官拒捕时,他提出了三项具体解决方法:“自以访明首要,严密缉拿,解散胁从为上策。如该匪势甚猖獗,即须胁以兵力,务令交出要犯。倘竟抗拒不服,亦惟有用兵捕击,以免蔓延。”(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85—86页。)仍把解散团民作为动用兵力进行剿办的前提。对怎样才能尽快平息义和团运动,他本人没有具体的措施及设想,处于“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 102页。)的剿抚两难之中。
1900年4、5月间,涞水义和团发展迅速,在知县祝芾的要求下,裕禄派出候补道张莲芬、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率马队120人前往查办。 杨福同一到涞水,就包围了高洛村拳厂,逮捕团众十余名,激化了义和团与清军之间的矛盾。5月22日,当杨福同率马队再度到石亭镇缉捕时,遭到了预先埋伏在两狼沟内二三千义和团民的伏击,杨福同被刺死于马下,义和团取得了涞水之役的胜利。
杨福同的被杀,使裕禄十分怒恼和震惊。他认为义和团“日聚日众,断非语言文告所能劝解,若不厚集兵力,稍加惩创,恐成燎原”。(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3页。)从此, 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弹压解散政策转变为以剿杀为主的镇压政策。为了达到剿杀义和团的目的,裕禄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即抽调劲旅两支,一支由东安(即今廊坊市安次区)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支由天津取文、霸、雄一道至省城保定,自南而北;并联合已驻扎涞水、定兴之营队,三路兜拿义和团。与此同时,裕禄也没有完全放弃劝解政策,饬令“多贴告示,声明其罪,晓谕良民,勿为所惑,解散胁从,庶查拿首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3页。)
在裕禄的督促下,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领武卫前军30营,赶赴铁路沿线剿杀义和团,并作出军事部属:武卫前军马队统领邢长春率队驻扎保定西关车站,逐日派兵到定兴、安肃(今徐水)一带巡逻;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率步队驻扎于高碑店,保护高碑店以南铁路之安全,“兼防涿匪南扰”。(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40页。 )不久,在杨村,聂士成率军攻击义和团,当场击毙团民六、七百名。(注:《义和团》(二)第165页。)在涿州, 杨慕时部公然向烧毁铁路的义和团及夹道两旁观看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团民十余人并伤及无辜百姓多人。(注: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338页。)6月5日, 杨慕时又在高碑店打死打伤义和团百数十人。(注: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346页。 )邢长春也在保定及其周围地区屠杀义和团。在这一过程中,驻扎在沧州的梅东益、范天贵清军,于1900年5 月血洗了沧州,屠杀义和团三千余人。
聂士成等人的镇压政策,激起了广大义和团战士的极大愤慨,他们积极行动起来,给清军以有力的回击,聂军在芦保铁路沿线节节败退。面对这种结局,清政府不得不重新估计和认识义和团的实力。特别是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清朝统治者制定了“欲纵拳匪以与洋人为敌”的以民制夷政策。1900年6月,清廷派出赵舒翘、何乃莹、 刚毅等前往良乡、涿州一带探听虚实,对义和团进行“劝谕”、“招抚”,并把涿州的义和团“道(导)之入京师”(注:《义和团》(一)第12页。)。驻守芦保铁路的聂士成因剿杀义和团遭到朝廷的申斥,其所亲率的武卫前军五营也被迫撤离,前往天津去抵御八国联军。
清廷对义和团的“招抚”政策,使裕禄的剿杀计划无法继续执行下去,只好命令杨慕时部暂时驻扎涞水,看看刚毅等人如何对待义和团,然后再作定夺。此时的裕禄陷入对义和团欲剿不能,欲抚不愿的矛盾之中。
2、藩、臬两司从抵牾到对立
在直隶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直隶布致使廷杰与直隶按察使廷雍还能相互合作,执行了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实行调解、弹压解散的政策。他们一方面颁贴告示,“不许轻信邪说,再行学习,亦不得聚众生事,致干重咎。……但敢有为匪肇衅者,定当严行拿办,不稍宽贷。”(注:《义和团》(四)第480页。) 严厉禁止百姓习拳练武与攻打教堂。另一方面,他们还秉承裕禄的指令,大量印发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甚至共同参奏了对义和团有庇护倾向的枣强知县凌道增及其他类似官员。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的迅速发展,清廷内部主剿派与主抚派之争走向白热化,廷杰与廷雍原先在感情、性格及处事方式上的差异,表现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廷杰倾向主剿,廷雍倾向主抚,二人发生抵牾。1900年6月,臬司廷雍致电裕禄,郑重声明:“近月余以来, 凡论拳教一事,或电或禀,皆由藩司主稿”(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89页。),否定了他在这个时期决策过程中的参与, 表明他对剿杀义和团政策的不赞成态度,把他与廷杰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杨福同被杀后,廷杰与廷雍的态度迥然不同。廷杰认为,义和团与天主教为仇,姑可勿论,如今戕杀国家大员,焚毁铁路,乃是叛君逆父,“若不严密搜拿,痛加惩讨,使匪党知所警惧,所患何堪设想”,主张剿杀义和团。廷雍则认为,拳民乃乌合之众,如果“纵兵剿捕”,必会伤及无辜百姓,造成玉石俱焚之结局,因而坚决反对出兵征讨。他们为此常常争论不休,甚至互相“喧哄诟詈”(注:《义和团史料》(上)第309页。)。杨福同的灵柩运回保定时, 廷杰“抚棺痛哭”,而廷雍则独谢不往。(注:《义和团史料》(上)第337页。) 对于两司的矛盾分歧,当时退职官僚吴慰祖在家信中写道:“省内藩臬不和,见面抬杠,臬惟迎合内廷之意,一味主抚;藩一力主剿。”(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61页。)可见两司的对立分歧乃众人皆知。
形势的发展和朝廷主抚派的日益得势,使按察使廷雍对义和团纵容的态度更加明朗。他把义和团视为义民,认为“杀义民不祥”,反对用武力阻止义和团进入保定省城。同时一改对教会势力的保护态度。当在保定的比利时、法国各类人员数十人准备去天津避乱,请求省府派兵保护时,廷杰与之协商,廷雍则愤然以“我未曾降附外夷,奈何以华兵而反为之用耶?”作答,(注:《义和团史料》(上)第309页。) 拒绝派兵保护。当张登教案发生后,廷雍又声言“持平办理”,实则袒护拳民,从而引起了传教士的极大不满。
直隶布政使廷杰和按察使廷雍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对立,是清政府主抚派与主剿派相互斗争的一个缩影。这场分歧最后以1900年7月廷杰遭到朝廷斥责并调回京师候用, 廷雍被晋升为直隶布政使而暂告收场。但藩、臬两司唱对台戏,却对下属产生了很大影响。
3、府、州、县官表现各异
直隶的府、州、县官与义和团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对各自管辖区内义和团的态度的差异就更明显。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对义和团采取一定程度的庇护及纵容态度。清苑知县陈鸿宝、庆云知县夏声乔、晋州知州刘藩、深州知州曹景郕、完县知县王开运等属于这一类。当布政使廷杰要求查禁清苑境内的义和团时,知县陈鸿宝多方讳饰,上报说不是义和团,乃是少林会,后又冠以保甲之名,千方百计为义和团遮掩。廷杰派军队前去搜捕,陈知县又密告义和团,使他们得以逃避。(注:《义和团史料》(上)第308页。) 庆云知县夏声乔“不禁拳,且唤入署中观演之,并赏以食物”。(注:《庆云县志》1941年本,《新政志》第99页。)晋县刘藩“仇教颇甚,乃练游勇,招拳师,驻于文庙内演习神拳、红灯照”。(注:《晋县志料》1935年本,卷下,《故事志》第4页。)深州知州还出示四言告示: “有教村庄,挨户清查,禀报到官,一律抄封”,对他们一体拿问、格杀勿论。(注:《义勇列传》(二),第257页。) 他们对义和团的庇护与纵容态度,对其辖区内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庆云县就由于知县的纵容,“城乡纷纷效尤”,境内各祠宇以及文庙书院都被义和团安炉设坛,并进一步带动了周围各县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其二,为保辖区内安静,对义和团采取敌视态度,视其为“匪”,主张进行弹压。这部分人除吴桥知县劳乃宣、景州知州王兆骐、阜城知县王柏峨等人外,还包括涞水知县祝芾、宣化知府李肇南、河间知府王守堃、固安知县王继武、广宗知县张祖咏、蠡县知县章焘等。其中涞水知县祝芾不仅亲自率队,拘捕了高洛村义和团首领阎洛福,还不断请求直督裕禄派兵驻扎涞水,以资镇慑。河间知府王守堃在听说任鄚镇有义和团设坛聚众之时,便前往弹压。宣化知府李肇南认为义和拳乃八卦教之余孽,主张“力禁之”(注:《宣化县新志》1922年本,卷11,《宦缚志》第37页。)。他们的所做所为,在很大程度上阻遏了当地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其三,对义和团采取鼠首两端的态度,或是无所适从,或是心中有自己的小算盘。具体表现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地方官,本意上并不赞同义和团,但迫于形势,他们对义和团采取表面迎合而实际监视的做法。临榆知县俞良臣就假意派兵保护义和团,实质上“隐寓监视之意”。(注:《临榆县志》1928年本,卷8,《舆地编》第24页。) 宁津知县祝嘉镛见义和团声势浩大,不敢阻禁,乃假意欢迎潘大师兄进城设坛,并声言叫他儿子也参加义和团,以此骗取了义和团的信任。(注:《宁津志稿》转引《义和团史料》(下)第973页。) 万全知县吴沂对义和团也“阳为尊奉,阴实监视”。第二种地方官,虽然不断地向上司请求派兵镇压义和团,但他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又却了恻隐之心。如安平知县何子宽,一面派兵拘捕了义和团首领陈锅元等人,一面又慑于义和团的声势,不久便把陈锅元等人保释。(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52页。)武邑县的地方官也一面请兵镇压义和团, 一面称病乞休,并将监禁的义和团民朱胖子等三人提禁外押,拨医调治,后来竟提案开释。(注:《义勇列传》(二),第511—512页。)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矛盾心态。第三种地方官,面对复杂局面一筹莫展,或冀求明哲保身,或辞职解任。或坐以待毙。保定容城知县俞明府,以“不能进言于上,复不能施禁于下,……幡然南归”。(注:《义和团》(一)第482页。) 景州知州洪复,也见时局日非,托病辞职不准,后经亲友多方运动,幸得如愿以偿,立即“挂帆南下”,(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41 页。)以避风波。涿州知州龚荫培在义和团占领涿州城,官府瘫痪的情况下,自行绝食,以待自毙。
以上情况表明,在直隶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时期,社会秩序已被打乱,与义和团的自发、分散相适应,地方官也表现为各行其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无政府状态。
三
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直至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直隶各级地方官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和态度各不相同,并呈现为一定的无政府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从社会矛盾和社会环境来看。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走向激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各阶级以不同方式进行了救亡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了武装暴力的反抗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农民阶级则以自发的方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以反洋教为主要内容的义和团运动。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强烈的排外情绪兼具造反精神,打乱了原先的社会秩序,被统治阶级视为非法而列入镇压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义和团又旗帜鲜明地喊出了“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等口号,并渲染其“神术”,矛头对准外国侵略者,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保朝护官倾向。这又使清政府感到“忠义可佳”,镇压理由很不充分。面对相互交错的两种倾向。清廷及地方官陷入了剿抚两难的抉择。正如劳乃宣在《拳案杂存》中所说,“若曲徇教士之请,横加之罪,则彼实无辜,既不足以服众人之心。若秉公裁断,不徇其意,而彼党实有烧杀之言,又不足以释教民之惧,而折服其口,势处两难。”(注:《义和团》(四)第454页。)如何对待义和团, 如何尽快平息教案,直隶地方官没有统一的规则可循,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去办理,从而造成了他们具体做法上的各不相同。
第二、直隶地处天子脚下,清廷统治集团的政策对直隶地方官有很大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在畿辅地区迅猛发展,他们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其“刀枪不入”等“神术”,以及讹言四起等情况,使清政府陷入了更加矛盾和困惑之中,是抚团抗洋,还是和洋剿团,清廷内部的主抚和主剿两大派争论不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以及刚毅、徐桐、毓贤、李秉衡等人构成的抚团排外派,由于他们自身的顽固、愚昧,并且为了报列强阻止废立之仇,主张对义和团“抚而用之”。“阴实欲纵拳匪以与洋人为敌”,(注:《义和团》(四)第171页。) 以达到借义和团杀洋人的目的。而许景澄、袁昶、联元、徐用仪等京官,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构成的剿团和洋派,主张对义和团坚决镇压,以换取中外相安无事。西太后则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行无定见,其发布的上谕中存在明显的前后不一致。1900年4月16日, 总理衙门电令直隶总督,对义和团“务须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9页。)第二天发布上谕,语气大变,提出“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谊”;进而命令地方官“随时剀切晓谕,务使各循本业,永久相安”。(注:《义和团档案史料 》(上),第80页。)4月21日又发布上谕,认为“民教皆朝廷赤子”,在形式上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甚至于1900年5月1日,发布了拟将义和团改为团练的上谕。但到5月9日,清廷就又转而命令步军统领衙门对义和团要“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87页。)清廷决策的瞬息万变,已使地方官无所适从,再加上清政府“饬地方官吏准情酌理,因应得宜,非朝廷所能遥制”(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82页。)的谕令,给了地方官很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因而地方官对义和团态度及决策的五花八门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直隶一省而言,作为封疆大吏的直隶总督及其藩臬两司的态度,又影响着基层地方官的一举一动。裕禄的剿抚两难,两司的公开对立,使其僚属不知所措;“司道如黄方伯不敢发一言,惟杨年伯尚敢进言,而不敢力争,幕中娄冯街道等亦无一词。”(注:《义和团史料》(下)第650页。)这加剧了知府、知州、知县决策的难度。从而, 有的地方官仰上宪鼻息而行止,有的甚至不惜改变自己原有的态度,去迎合上司的意图。直隶景州候补知州吴立达,“仰承廷雍意旨,遂转而助匪”。(注:《义和团》(一)第262—263页。)任邱知县王蕙兰,先前同传教士杜汝梅司铎“常通往来,感情不恶,自从往保定去了一趟,见了臬台,回来以后合(和)先前大不一样了”,对传教士不再保护了(注:献县教区《义勇列传》(一),1935年版,第413页。), 随后便发生了任邱境内教堂被义和团捣毁事件。可见,省级官员的意见不统一,是造成下属官员各行其是的重要原因。
第三、从直隶地方官认识程度及感情倾向来看。直隶总督、藩臬两司及府、州、县官虽然同属于直隶地方统治集团,但由于各自的社会角色和经历的不同,他们的对义和团的认识程度和感情趋向也各不相同。廷雍、陈鸿宝、夏声乔、刘藩等人,对义和团所采取的纵容及庇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抚派的主张相似,但他们与载漪等人的愚昧落后及泄愤心理有着很大差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往往有感于对列强侵略中国行为的强烈不满,由于对传教士干预中国内政的逆反心理所引发。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地方官的挟持、欺凌,并坐公堂,使地方官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但清政府软弱的外交政策,紧紧捆住了他们反抗的手脚,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当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抚拳灭洋就成为地方官发泄心中愤懑、实现其摆脱洋人压迫愿望的有效途径。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吞,无论出于维护中国主权,还是出于保护大清江山,大部分直隶地方官都能尽最大努力,抵制列强的勒索,甚至不惜冒一定风险,在一定时期内,把义和团看作为“精忠报国”的义民,并依靠义和团来对抗侵略者。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认识与态度。
以廷杰、祝芾等为代表的主剿派直隶地方官,把义和团与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军、捻军等量齐观、把他们看作是祸国殃民的“乱匪”、“乱党”,把义和拳看作为“白莲教之余孽”的邪门左道。因此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义和团会变为流寇,“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注:《义和团》(四)第165页。)言外之意,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必会危及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将会动摇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从而告诫人们: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实际上是引诱愚民而蛊惑朝廷,是“以符咒惑人,传教煽动,实不能避枪炮”。(注:《义和团》(三)第327页。)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更为了一府一县的安宁,他们对义和团采取了敌视及抵制态度,主张对义和团进行镇压。这又是另一部分官员的认识与态度。
面对义和团运动,一些地方官之所以采取明哲保身态度,知难而退,则出于避就心理。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义和团的认知程度及感情倾向难于把握。特别是他们对义和团与对列强各国的认知平衡被打破后,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和无奈,逃避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涞水知县祝芾在“日坐愁城,奈何从唤”的情况下,要求好友李鞠生在廷杰面前“设法速为量移,或即径行撤省,俾免于患。”(注:《义和团》(四)第384—385页。)胡千里受命管理天津府,曾向裕禄要求授以兵权剿杀义和团,遭到拒绝后,也“力辞缴檄,奉母南归。”(注:《义和团》(一)第473页。)武邑县令则以病为由, 再三恳请上宪派员来县接署。总之,在庚子多事之秋,一些地方官以往对仕途的渴望已被避就心理所代替。如北京一新任官吏亲属,听说其四叔补缺后反颇为伤感,说:“逢此乱世,入署如入虎穴,虽则可喜,然颇可忧”(注:《义和团史料》(下),第564页。), 就充分证实了当时一些官员的避就心理。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清廷政策摇摆不定的影响,直隶地方官大多表现为各行其是。但就总趋势而言,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清廷态度的更加暧昧以及中外关系的进一步吃紧,越来越多的直隶地方官或出自民族情感,或由于从众心理,转向了对义和团的同情、纵容和支持。一位传教士说:“当拳匪乱党恣意横行时,各地方官长,能烛其奸邪,排斥捕拿,不遗余力者,惟吴桥知县劳乃宣一人而已。其余皆推波助澜,纵容拳匪,仇教害民。”(注:《义勇列传》(二),第257页。)这话虽说得过于绝对, 但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直隶地方官对义和团态度的主流。正是这一情况的存在,直隶义和团运动才得以迅速走向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