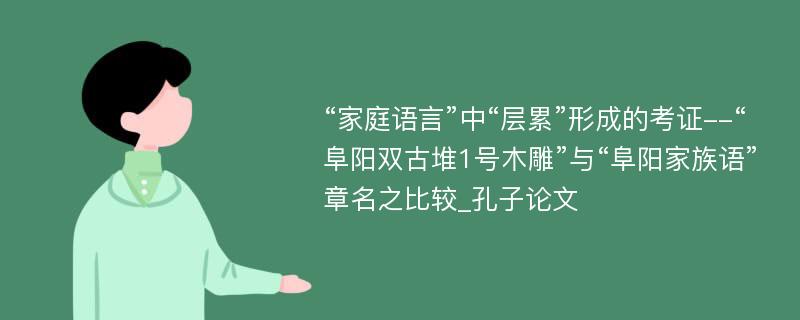
《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阜阳论文,所见论文,家语论文,双古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3-0009-09
晚近以来,由于若干出土文献(如信阳长台关楚简、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所出《儒家者言》、阜阳双古堆汉墓简牍、上海博物馆所藏竹书《民之父母》等)与《孔子家语》多所印证,使得传统有关此书的“伪书”说面临很大的挑战。但实际上,尽管今本《家语》有些内容与出土文献能够对应,说明其书确实来源有自,但与出土文献细加比较就可看出,今本《家语》还是存在诸多改动、重组的痕迹,不独与出土文献比较高下立现,即便是与某些传世文献(如《说苑》)相比也逊色很多①。本文主要关注阜阳双古堆汉墓所出一号木牍上与《家语》对应之相关章题。2000年胡平生在《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一文中首次披露了相关简牍的释文②,稍后,同样参与简牍整理的韩自强也在其《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一书中③,公布了相关简牍的释文,并有考证。他们的工作为学者研究这批简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现综合两书所见,就其中与《家语》对应之有关章题加以比较考证,试图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是《说苑》而非《家语》才与这些章题最为接近,《家语》相关篇章虽与木牍章题大致对应,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大量改动、重组的证据,而《说苑》则绝少改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在出土材料、《说苑》、《家语》三类文献中,往往存在着出土文献——《说苑》——《家语》这样章句结构梯次演进的序列,而《家语》明显是最末的一级,是经由前面环节的积累而“层累”形成的。以下即按木牍章题序号,依次与《家语》、《说苑》相关章题进行比较分析。
4④ 孔子之匡
此事当系《论语·子罕》等篇所言“子畏于匡”之事。《家语·困誓》⑤ 作:“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比较大的不同是“之匡”与“之宋”。此事又见今《说苑·杂言》:“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但《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卷三百九十六引《说苑》都作“孔子之匡,简子将杀阳虎”,这说明当初《说苑》亦与木牍同,作“之匡”。《韩诗外传》卷六说:“孔子行,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以围孔子舍。”没有“之匡”的环节,无从判断。但河北定州八角廊所出汉简《儒家者言》⑥ 之12章第666号简云:“之匡间(简)子欲杀阳虎孔子似之。”其明云“之匡”,与木牍章题正合,当为原貌。而且,《庄子·秋水》也提到“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游于匡”与“之匡”,大致与木牍及《儒家者言》接近。看来此处“之匡”当系原貌,今本《说苑》、《家语》的“之宋”当系后人妄改,《家语》“匡人简子”尤缪——匡地何曾有过简子?另外,还要提到的是,孔子之遭厄于匡,《史记》、《韩诗外传》、《说苑》均认为是孔子长得像阳虎⑦,而阳虎曾暴虐于匡。但是,《家语》对于阳虎却并未提及,何所为证?我们看上引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666号简明云“欲杀阳虎孔子似之”,从属该章的905号简亦云:“阳虎如为阳虎则是非丘□⑧。”据此,笔者曾经指出,《家语》的不提阳虎,当是故意隐去,因为“杀阳虎就要引出杀孔子”,特别是“孔子似之”,凡此均于尊不讳⑨。更突出的证据是,《家语》中孔子自己解释遭厄的原因,也是绝口不提阳虎。因此,我认为:“《家语》前后‘一致性’地不提‘阳虎’,这已不是脱简所能解释的:不可能前后都这么巧地都脱去了有关‘阳虎’的内容。这只能反映《家语》进行了重组,这种‘重组’既大胆——彻底地将有关‘阳虎’的内容清除出去;而且还有相当的‘系统性’——前后‘一致性’地清除。这都是其‘后起’的证据。”⑩ 不过,个人以为,这种基于回护孔子而对原有材料进行的剪裁,孔安国等孔氏后人显然有比王肃更为强烈的“作案”动机。
15孔子曰丘死商益
此章对应《家语·六本》,其文为:“孔子曰:‘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此章还见于《说苑·杂言》32章(11):“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孔子之自称,《说苑》与木牍同,俱作“丘”,但《家语》却作“吾”,显然也是出于为尊者讳而作的改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木牍和《说苑》所见看,该章本来应该是独立的一章,而《家语》则又有合并。《家语》该章之外尚有:“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以及“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等讨论交友之道的内容。《家语》多出部分内容又见于《说苑·杂言》之46(12),就是说,《家语》把本来两个独立的章进行了合并。清代孙志祖也说《家语》此章是“撮《说苑·杂言》篇二段为一”(13)。不过,《家语》的合并也有一定道理,原因就在于前面的“商也日益,赐也日损”与后面的部分同是讲的交友之道,把这样具有相关性的两章合并确实显示了整理者举一反三的功夫。但也要指出的是,细加分析,《家语》捏合这样两章还是让人感觉到有点牵强:前面是谈卜商、端木赐或“与贤己者”处,或说(悦)“不若己者”,因此产生对本人或益或损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所关注的是在交友上到底是要交比自己强的还是比自己弱的问题。但是,后面“不知其子视其父”等等却只是就“一般的”交友之道发表评论,最后的“善人”、“不善人”则完全沦为对立的善、恶两极,这和开头讲的交友对象上的强弱其实并不是同类概念。正有鉴于此,清代范家相才说“不知其子一章,与上论商赐难以合并”(14),是非常正确的。这就说明,此处《家语》的强加捏合,是只关注了表面现象,并没有深求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家语》这种工作是否具有普遍性,值得我们重视。另外,《家语》为很好地捏合这两章,还增加了“曾子问”这样的情节,这是非常大胆的,当然目的也无非是让这样重组而成的一章更像“一”章。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曾子而不是其他人?是顺手拈来?还是曾子确有关于交友之道的论述?《大戴礼记》的记载,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后者。《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与君子交,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这说明《家语》的整理者对曾子的言论是非常熟悉的。不过,他此处也不是全盘接受《大戴礼记》的说法,因为从后面的“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来看,他似乎主要根据的还是类似《说苑》这样的材料。当然,从今本《家语》所附孔安国的后序看,“家语”材料曾经一度“散在人间”,当有不同的传本,《家语》整理者所接触到的材料可能恰好兼具《大戴礼记》与《说苑》两方面的特点。有意思的是,本为曾子的话,但捏合成一章后,就成了孔子的话。既利用了曾子,又把著作权归之孔子——但这却又符合《说苑》中是孔子的话的面貌。我们因此应该承认,曾子的出现以及将最后的著作权归之孔子,是《家语》整理者很巧妙的做法。这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当某些言论在孔子师徒之间出现“著作权”纠纷的时候,《家语》整理者是否出于尊孔的原因都归之孔子?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家语》中孔子的言论恐怕也是“层累”地造成的。
还要提到的是,《说苑·杂言》中“丘死商益”章、“将行无盖”章、“新交取亲”章、“赠汝以车”章是章序相连的连续四章,但木牍中只有“将行无盖”章、“新交取亲”章章序相连,我们认为这反映了《说苑》章序组织的渐趋有机化,而且,这种“有机”可能有早期木牍这样的前期积累作为铺垫。在今本《家语》中,“丘死商益”章见《六本》篇,“将行无盖”章见《致思》篇,“新交取亲”章、“赠汝以车”章同见于《子路初见》,但却被合并成了一章(论证见下文)。从两章到一章,说明在“有机性”上《家语》又较《说苑》往前推进了一步。虽然《家语》就“有机性”上讲是提高了,但这却是以损害材料的原貌为代价的(15)。从古书成书的梯次上讲,《家语》此处所见显然是要晚一个梯次的,是经多次“层累”而形成的。这种“层累”性,不要说与出土文献比较,就是与《说苑》等传世文献相比也看得很清楚。
19子路行辞中尼敢问新交取亲
此章见于《家语·子路初见》,其文为:“……子路曰:‘由请终身奉之。敢问亲交取亲若何?’”此内容又见于《说苑·杂言》之34章及定州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之14章(16)。《说苑》34章其文为:“子路行,辞于仲尼曰:‘敢问新交取亲若何……’”比较来看,还是《说苑》与木牍接近,而今本《家语》则又有明显的重组和改动。《说苑》不但文字与木牍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该章也是如木牍般独立成章的。但在今本《家语》中,该部分却并非独立成章。上引《家语》之文前面省略的部分,尚有“子路将行,辞于孔子,子曰:‘赠汝以车乎?……’”一段。有意思的是,《家语》前面的这部分,在《说苑》中也是独立成章的,而且就是《说苑·杂言》中相邻的35章。更巧的是,阜阳木牍后面的第44个章题正对应《说苑·杂言》的35章,这样看来,情况就非常明显了:无论是“新交取亲”章还是“赠汝以车”章,看来当初都是如木牍和《说苑》般独立成章的。《家语》则明显是两章捏合之后的面貌,而之所以会有捏合,这两章形式上的相关性是重要的原因(17)。进一步支持我们这个判断的还有定州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该组简14章为“新交取亲”章,而15章即为“赠汝以车”章。虽然定州汉简缺乏分章的直接证据,但整理者认为“新交取亲”部分对孔子径称“仲尼”,而“赠汝以车”部分则屡称“孔子”,故而将它们作两章处理,是可信的(18)。由阜阳木牍的两章不相连,到《说苑》中前后相次之两章,最后到《家语》中是将两章合并——这再一次说明《家语》一书在章句整合上的“层累”性质。
21子曰里君子不可不学
此章见于《家语·致思》,其文为:“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惟学焉。……故君子不可以不学……’”木牍章题之“里”,当为“鲤”,即孔子之子伯鱼之借字,《大戴礼记·劝学》之“野哉”之“野”亦当为“鲤”之误写。此处显然是孔子在教导伯鱼要重视学习。同样的内容还见于《说苑·建本》。有意思的是,在《家语》中本为一章之内容,在《说苑》中却是两章。兹不惮繁琐,具列于下。《说苑·建本》之14章: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僭不亡,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说苑·建本》之15章:
孔子曰:“鲤,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则无根,无根则失理;失理则不忠,不忠则失礼,失礼则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从上观之,知其非源也。”
《家语》为一章,《说苑》则为两章,何所为正?在阜阳木牍发现之前,这个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为无论哪一种都有合理性。但结合阜阳木牍所见,我们认为《说苑》两章的处理仍当是原始面貌。木牍既是章题,看来当初“君子不可不学”章确实是单独成章,这就与《说苑》所见一致。另外,《大戴礼记·劝学》作:“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也是单独成章的,尤可证。《韩诗外传》卷六之15章相当《说苑·建本》之14章,也是单独成章的。再回过头来看《家语》的合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重组的工作很有眼光。因为原来的两章都是讲“学”,在内容上有联系(19)。尤其是在两部分之间加上关联词“故”,使两部分形成逻辑上的因果联系,更可见其重组之用心,也说明其合并是刻意的。阜阳木牍中只见“君子不可不学”章,《说苑》中则出现两章并列的同为讲“学”的章,到《家语》中则干脆将两章合并成一章。这一系列事实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一,就像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那样,从单章到多章,再到多章的合并,从文献的创生梯次上讲,《家语》确实是最末一个等级,反映在版本特性上就是比较晚的,是“层累”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戴、韩诗作单独一章的处理,而且不让两章序上相连,甚至比《说苑》还要原初。或者说,阜阳木牍这样“零散”的章序特征还有更多的“别本”作为支撑。二,由单章到多章相连再到多章的合并,确实反映了和孔子言论有关的材料在汉代不断“集约化”的倾向,这恐怕也是《家语》最终能成书的深刻原因。三,我们认为《家语》的整理者很有可能是见过类似《说苑》这样的材料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巧地把本不相连的两章合并,也就是说,类似《说苑》材料的先将两章拉近——次序上前后相接——可能是个前提性的关键步骤,这也是我们“层累”立说的主要依据。今本《家语》所附孔序曾说其书曾一度“散在人间”,因此“好事者各以己意增损其言”,这其中可能即有将类似《说苑》的材料进一步向“集约化”推进的工作。不过,孔氏后人对别人工作的评价太低,而对孔安国的工作则不乏溢美的成分,所谓“与世所传者不同日而论”(见《家语》后序所载孔衍奏文)。我们下文还会提到,孔安国的整理恐怕也不能避免“以己意增损其言”的情况,而就保存文献的原貌来讲,他们显然都远逊刘向整理的《说苑》,这一点我们从木牍章题往往与《说苑》而非《家语》接近可以说就看得很清楚了。
22子曰不观高岸
此章见于《家语·困誓》,其文作:“孔子曰:‘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木牍“岸”,《家语》作“崖”。另外,《说苑·杂言》之20章即对应此章,其文为:“孔子曰:‘不观于高岸,何以知颠坠之患……’”“岸”字同木牍。从木牍和《说苑》来看,该章本为独立一章,但现今丛刊本《家语》却又存在合并:将其与前面的“孔子之宋”合并成一章。不过,丛刊本的合并应该系后来刻书者妄合,因为全书本、同文书局本以及孙志祖、范家相、陈士珂本都没有合并(20)。这说明《家语》章句结构上的“层累”整合,甚至到后世还是一直存在的。不过,这两章确实在内容上有相通之处:“孔子之宋”部分是讲孔子遭困于匡,而本章所谓的“不观高岸”、“不临深泉”、“不观巨海”显然也是强调“曾经沧海”,才能“难为水”。有意思的是,《说苑·杂言》之17章是“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18章是“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居环堵之内,席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读诗书治礼不休……”、19章讲匡简子围孔子、20章“不临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可以说都是围绕“厄难”来组织的,其“组织”的有机性是明显的。《说苑》的这种有机的章序组织板块在《家语》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家语》“孔子之宋”章之前正是《说苑·杂言》的第17章,这再次说明它们之间在材料来源上的相关性。与《说苑》不同的是,《家语》这样的有机板块唯独没有《说苑·杂言》的18章——而该章《家语》是把它放在《在厄》篇中。其实,从篇名来看,“困誓”、“在厄”其主旨是具有一致性的。《说苑》把有机的四章放在一起,而《家语》偏偏把内容上同样相关的一章,异置于另一题旨近似的篇目下,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家语》整理者所见材料虽与《说苑》接近,但仍存在一定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木牍章题之4章对应《说苑·杂言》之19章,木牍章题之22章对应《说苑·杂言》之20章,也就是说,有机章次在木牍的时代章序上并不相连,或者说他们还比较零散,但到了《说苑》、《家语》中则有了较为有机的组织。
41(21) 孔=见季康子
此章对应于《家语·子路初见》,其文为:“孔子为鲁司寇,见季康子,康子不悦……”另外,该章还见于《说苑·政理》之46章:“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两相对比,还是《说苑》此章与木牍章题最为接近,而《家语》则增加了“孔子为鲁司寇”的环节,这显然是“解释性”的安排(22)。王肃于“康子”下注云:“当为桓子非康子也”,盖因孔子为司寇事在定公十一年,其时康子尚未主政。所以,宋胡仔《孔子编年》卷二于此即云“孔子见季桓子,桓子不说”。我们相信,《孔子编年》所载当系考证之后的结果,并非胡氏所见宋本《家语》即如此。因为宋杨简《杨氏易传》卷十三仍然说孔子“见季康子,康子不悦”。既然历史事实是孔子为司寇时尚是桓子当政,但为何从《家语》到《说苑》,甚至阜阳木牍都云“康子”呢?笔者曾撰文指出,《家语》、《说苑》书中内容很多都是“诸子百家语”式的“说”类材料,这类材料不太重视历史细节,而主要措意于人物的谈说内容(23),因此其文很多都具有鲜明的“演义”色彩。这就提醒我们,对待这样一类材料,不能过于以历史考证的眼光看问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五有条“传记不考世代”,即专门讲此类“关公战秦琼”现象,举证之丰富,可谓触目惊心。自西汉以来,学者有意识地将《家语》与以《论语》为代表的记载了较为可信的孔门师生言论的文献适当区分,正反映了在这些学者看来,《家语》作为孔门师生言论记录在可信性上是有问题的,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充分注意。今天由于多宗出土文献与《家语》可以对应,因此王肃“作伪”之说自然很难成立,但“书”之真(何况它还是“层累”的)并不简单对应“内容”之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把“书”的“历史”与“内容”的“历史性”分开来看。
42中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
此章见于《家语·六本》,其文曰:(孔子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现今丛刊本《家语》“君子”作“男子”,“男”当是“君”之讹。除此之外,该章还见于《说苑·杂言》之31章,其文为:“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值得注意的是,对孔子的称呼,木牍和《说苑》都是直呼其名“仲尼”,而《家语》又是用了尊称“孔子”,可见这是整理者重组《家语》过程中一项重要而系统的工作,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24)。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说苑》在此章之前和之后的两章都是用“孔子”,唯独此章用“仲尼”,这说明刘向在整理《说苑》之类的材料时,并没有像《家语》整理者那样做这种系统的修饰工作,而比较能够忠实于类似木牍章题这样的原始面貌。进一步支持《说苑》比《家语》更近原貌的证据是,在木牍和《说苑》中,该章都是独立的一章,而《家语》则又将其与别章进行了合并。《家语·六本》中实际上是将该章与其他两章进行了合并。一则为“回有君子之道四”章,再则为曾子闻孔子“三言”而“未之能行”章。有趣的是,《家语》合并的这三章同见于《说苑·杂言》,而且章序相连,依次为29(曾子闻孔子“三言”)、30(“回有君子之道四”章)、31章(“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章)。从木牍及《说苑》看,《家语》这种合并“晚出”的性质是没有问题的。在《说苑》为相连三章,在《家语》中又是将这三章进行了合并,就此而言,《说苑》与《家语》在材料来源上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重组《家语》是王肃做的,那么王氏显然利用了《说苑》这样的材料;如果是孔安国完成的,那也说明孔安国利用的材料与《说苑》的很接近。然而我们从今本《家语》中很多王肃注文纠正原文之缪看,说王氏重组是很难想象的(25)。不过,这种合并也同样有生硬、勉强之嫌。在《家语》中,整理者是刻意要将孔子对颜回、史鰌的评价组织成情景性的孔子对曾子教诲、曾子略述感受的样子。《家语》该章最后说:“(曾子曰)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终不及二子者也”,此“二子”显然意指颜、史二人,后来王肃作注也受了这种误导:“二子,颜回、史鰌也。”但这最后一句话《说苑》中并没有。所以,不是《说苑》为把章次拆开而故意删去,而是《家语》为把章次合并而“无中生有”。但恰恰是曾子相关内容的存在使得合并顿显生硬。从下文内容看,所谓的“三言”是孔子的话,更具体地说是讲孔子自己的,这和“君子之道四”、“君子之道三”分别是讲颜回、史鰌,就存在矛盾。实际上,曾子所说孔子之“三言”:“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见人之有善若己有之”、“闻善必躬行之,然后导之”与上面对颜回、史鰌的评价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前人已看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像范家相即云:“其曰‘不及二子’云云,于夫子之‘三言’似不相蒙”[2] (卷四)。这再一次说明《家语》整理者的工作是初步、生硬的。不过,孙志祖把合并三章归之王肃,则未必,因为王氏又为“二子”作注,这种自为其文,又自为其注的行为,也未免太有故事性了。从王肃多处纠原文之缪看,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不大可能的。退一步说,即便王肃真的是这样处心积虑地作伪,但这对于支持他自己的学说,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此处所涉及的事情实际是无关紧要的。鉴于《说苑》该章与上一章章序组织上的有机性(26),说明尽管《说苑》无暇进行文字体例上(将孔子、仲尼整齐)的统一,但在章序的有机处理方面还是做了些工作的(27),尽管这不很完备。《说苑》中相邻的三章只有“史鰌”章见于木牍,应当说木牍时代章的“集约化”和“有机性”还很低,但到《说苑》中则被组织成章序相连的三章(这三章是有明显关联的,如29章的“三言”、30章“君子之道四”、31章的“君子之道三”),最后到《家语》中它们干脆被合并成了一章。这种“集约化”的不断推进,再次说明《家语》在古书成书的梯次上是较晚的一级,是“层累”形成的。
44子路行辞中=尼=(28) 曰曾汝以车
此章见于《家语·子路初见》,另外还见于《说苑·杂言》之35章、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之15章。我们上面在讨论木牍第19个章题的时候曾经提到,该章及19章在《说苑》中是分为两章的,这也为阜阳木牍19、44两个独立的章题所证实,但在《家语》中两章却是被合并成了一章,显然缘于后人的重组。还应提到的是,从两章的次序关系上看,阜阳木牍19和44这样的章题次序说明它们相隔甚远,并不相连,但到了《说苑》中它们却是两个次序相连的章(34、35),到了今本《家语》中则干脆合并成一章。我曾经另文指出:“这样一种演变线索是文献梯次演进的生动范例,也再一次揭示了《家语》在文献创生过程中较次一级的地位。”(29) 而且,从两部分的次序看,无论是阜阳木牍还是《说苑》都是“新交取亲”章在前,“赠汝以车”章在后,《家语》中两部分的次序却进行了颠倒,这也是有特殊用意的(30)。再者,为了把这两章捏合得更像“一章”,《家语》还增加了一些起到“链条”作用的语句(31),这些同样表明其在文献创生梯次上是处于较末一个等级的,也是“层累”形成的。
据笔者统计,木牍明确对应今本《家语》的共有22个章题,而这些章题我们发现它们几乎也同时对应《说苑》的相关章次。《家语》与《说苑》这样的“如影随形”,说明它们的材料来源是很接近的,学者谓它们都是取材于早期诸子百家语的“说”类材料,可谓不易之论(32)。这也说明,今本《家语》所附孔安国序中曾评价《家语》材料间有“属文下辞往往颇有浮说,烦而不要”、“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这样的特点,还是符合事实的。不过,《家语》、《说苑》虽同时与木牍章题可以对应,但比较可知,与木牍章题最接近的其实是《说苑》而非《家语》。《说苑》虽在章序组织上较木牍章题有了一定的“有机性”,但章内之内容则很少变化,基本与木牍章题可以对应,而《家语》则章内改动、重组之处则比比皆是。这种情况应该启发我们思考《家语》与《说苑》两种文献不同的整理方式。从古到今,《说苑》多题“刘向撰”,现在看来这并不准确:一则刘向是面对“中书”、“臣向书”、“民间书”这样的既有材料;再则从其与木牍章题基本一致看,刘氏整理绝少涉及章之内容的改动和重组,还是比较好地保存了材料的原貌,“编”比“撰”显然更为确当(33)。这提醒我们,较之《家语》而言,《说苑》材料的原初性及价值更应该得到重视。
《家语》对应木牍的22个章题,有多达18个都表明《家语》存在改动、重组的痕迹,这一点只要与《说苑》比较就一望可知(34)。这些改动、重组为我们考察《家语》一书的形成及性质,特别是孔安国、王肃二人与此书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材料。总体而言,今本《家语》这些改动、重组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系统性”非常强,把一项要求贯彻始终,拥有明显的“全局”意识。这说明它的改动绝不是由于文本自然流传,出之于“无意识”的点滴“修补”,而毋宁是一项非常用心的工作。通过上文我们对其中8个章题的考证,这种“用心”尤其体现在它重组章句,以及捏合多章成一章的努力上。这就使得今本《家语》在古书形成的梯次上处于较晚一个梯次,体现出明显的“层累性”。通过上面阜阳木牍章题与《家语》、《说苑》的比较,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在木牍或《说苑》中是单个或零散的章,《家语》往往都将它们与其它章进行了合并,而我们在做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家语》的比较研究中,也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35)。也就是在章次的整合与组织上,《家语》显然要较木牍及《说苑》更为“有机”化,这也是其“晚出”的又一证据。而且,在木牍、《说苑》及《家语》之间,我们还经常看到这种“有机”化梯次推进的轨迹:在木牍中是比较零散的章,到《说苑》中就把有关联的两章或多章组织成章序相连,最后到《家语》中又把若干章序相连的章合并成一章。笔者在做《老子》“早期传本”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这种“有机”化的梯次推进,是某一类古书章句结构整合及成书的基本方式,具有很大的普遍性(36)。现在看来,今本《家语》的形成也同样走的是这条路线。另外,从上述梯次推进的轨迹中,我们也明显看到在“有机”化的推进上,《家语》显然比《说苑》走得更远,这同样意味着较之《说苑》等书它的多“层累性”。不过,这种“晚出”的“层累”推进可能完成得也很“早”,并非后来的王肃所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推进无关什么持论立说之宏旨;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力挺《家语》的王肃本人,其实对于《家语》也不是全信的,甚至不乏批评之处,因此说其作伪或重组就是难以想像的。今全书本《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颜回“三十一早死”,王肃注谓:“此书久远,年数错误,未可详。校其年,则颜回死时孔子年六十一岁。然伯鱼五十先孔子卒,卒时孔子且七十。此谓颜回先伯鱼死,而《论语》云:‘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槨。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槨。”’或为设事之辞。”(37) 此段注文今丛刊本无有,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王肃之说与此正同,故此为王肃之说无疑。王氏明云“此书久远,年数错误”,显然是在批评(38)。虽则批评,但并没有以己意妄改和调整,因此可以说是相当谨慎的(后世怀疑其作伪者,正是失却对此细节的注意,流于简单粗暴)。这就说明上述章次合并这样大的动作,也不大可能是王氏所为,而毋宁就是与《家语》一书有极大干系的孔安国。
我们上文已提到就“回护”孔子而言,孔氏显然比王肃更为可能,而重组章句这样大的动作我们也能找到孔氏所为的蛛丝马迹。今本《家语》后附孔安国的序文称,孔安国对世间流传的《家语》材料现状是很不满的:“好事者亦各以己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所以才起而整理,方法就是:“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其中,“撰集”一词最值得玩味:它意味着孔氏不是对旧材料只是“集”或者“编”,还有自己“撰”的内容在里面,其孙孔衍在奏文中也称其祖所撰“与世所传者不同日而论也”,这无异于说孔安国已经以自己整理的工作,使得新成之《家语》较之材料来源面目全非了(39)。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今本《家语》基本内容确系经孔安国之手整理定型的,通过《家语》与阜阳木牍章题、《说苑》的比较可以发现,这种“整理”的痕迹可以说都昭昭具在。这样看来,孔氏的这种“整理”可以说既“早”又“晚”:“早”主要侧重于绝对的时间线索,它是早在西汉就由孔安国完成的,并非后来的王肃所为;“晚”则主要强调横向的空间概念,侧重于不同版本的横向比较,即它与同时期存在的其他《家语》材料相比改动很大,尤其存在章句重组这样梯次推进的事实,这表明它又是“晚起”的。这种既“早”又“晚”的特征,可以说很好地诠释了当前《家语》一书的尴尬现状:由于其绝对年代的“早”,说明它也保存了大量比较原初的材料,因此与出土文献多所印证,故而“伪书”之说渐渐然归于沉寂;但由于其版本学上的“晚”,因此妄加改动甚多,且不说与出土文献相比,即便与某些传世文献相比也大为逊色。这不只赋“伪书”说者以口实,也令“翻案”者气短。就此而言,孔安国的重组和整理简直是帮了倒忙。
不过,我们认为,《家语》一书的出现应该是汉世儒家经学兴盛的必然产物。孔安国对《家语》的整理原则和重组的标准,都代表了经学特别是孔子地位隆升时代的价值取向。比如这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孔子本人的“回护”处理。这方面既包括将“仲尼”改成“孔子”,也包括将一些章类似“杀孔子”这样的内容删去。这项处理都是非常具有“系统性”的,尤其是上文提到的“孔子之匡”章前后“一致性”地隐去“阳虎”,更可见是刻意为之。如前所述,这种“回护”的处理,孔安国显然比王肃有更为强烈的要求和动机。但也要提到,从上文我们所做的考证可以看出,孔安国对《家语》的重组和整理其实水平并不高:未能深求章句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只关注章句表面的相关性。与此相关,我们发现孔氏重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增加了很多“解释性”内容(40)(这恐怕也和汉世章句训释之学流行有关)。这些“解释性”内容既包括相关背景的交代、细节的补充,也包括把原本呆板、枯燥的行文变成生动形象的叙述。经此处理,《家语》之文就较原来更加完善、丰满,也更生动,诚如孔衍奏文所称“典雅正实,与世所传者不同日而论”。但其实这只是“文章学”上的优势,而从版本学上说,无疑意味着“层累性”的“晚出”。在近年来的古书年代学研究上,我们往往把古书“文章学”上的优势(诸如语意丰满、文从字顺、逻辑严密之类)简单等同于版本学上的“早出”,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既然上述“解释性”环节仅涉及行文表述上的润色,而无关什么持论立说之宏旨,那么,传统说法谓《家语》系王肃伪造或“增加”借以驳难郑玄,显然勉强。虽然今天我们还无法就王肃与《家语》的关系做一准确判断,但我们认为他对《家语》的工作肯定不会是上述“解释性”内容,因为这些纯粹是“技术性”工作,在驳难郑玄上显然是帮不上忙的。
上面提到,《家语》最初是脱胎于诸子百家语这样的“说”类材料。因此,其中内容很多并非实录,甚至连孔安国都说它们“颇有浮说,烦而不要”、“其材或有优劣”(见《家语》所附孔氏后序),这恐怕主要就其材料来源立论。面对这样的材料,孔氏可能也是很为难的:一方面它们很多都打上“孔子”的标签,但另一方面又“颇有浮说”。何所去从?我们认为孔氏最终的态度仍然是“信”超过了“疑”,这从其序中说“实自夫子本旨”就可略窥端倪。而孔氏所能做的,恐怕就是类似上面“解释性”工作的补苴和弥缝。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西汉尊孔隆儒的经学大背景才导致《家语》最终从“说”类材料中独立出来,而这个背景也显然制约着《家语》一书选材的标准:“宽”要超过“严”。这其实也是经学史上经常存在的现象,那就是儒生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重建,以及由此导致的儒家经典系统的更新和扩张。由于这些林林总总、来源多途的材料的“层累”,实际上孔子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再塑造的过程——由“文献”的“层累”到“历史”(包括人物形象)的“层累”。事实再一次证明,上个世纪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提出的通过考辨古书进而探究古史的主张,仍不失为我们今天从事古史研究的不二法门。不过,可能正是由于脱胎于属“诸子百家语”式的“说”类材料,以及在选材上“宽”胜于“严”的标准,《家语》在内容及价值取向上就体现出一定的“多元化”色彩,这也恰是反郑学的王肃以之为应援而较多回旋的原因。但他恐怕没有想到,《家语》书中与其“重规叠矩”(见今《家语》前所附王肃序文)的很多内容,可能本来就是“他山之石”,并非夫子本人的东西。而王氏对此类内容心有戚戚,是不是也注定了他将被正统经学家视为经学诠释史上对抗郑玄的“异数”?
注释:
①拙文《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
②《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凡引胡氏释文及论说均见是文。
③该书“附录”,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④此为木牍章题序号,下同。
⑤本文所引《家语》之文,均以四库全书所收明毛氏汲古阁刊本为据。
⑥本文凡引八角廊简《儒家者言》之释文均见《〈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
⑦《庄子·秋水》也说:“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
⑧末一字模糊不可识。
⑨参见前引拙文《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⑩同上。
(11)本文所据《说苑》之文及其章序均依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另外,《说苑·奉使》、《荀子·性恶》尚有与“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大致对应之内容。
(13)孙志祖《家语疏证》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4)范家相《家语证伪》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5)比较而言,《说苑》的将相关章放到一起的“有机”处理,其实无涉材料内容的损害,而像《家语》这样合并多章就难免对原有内容分化整合。
(16)其文为“何中(仲)尼曰亲交取亲”。
(17)两章开头都有“子路(将)行,辞于仲尼”字样。另外,《家语》捏合两章所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在“新交取亲”章中增入“汝所问,苞在五者中矣”(《说苑》无此句),以照应“赠汝以车”章的“慎此五者”。元王广谋本《新编孔子家语句解》“赠汝以车”章单独成章,且未见“新交取亲”章,莫非王氏所见与今本有异?或者说今本两章合并的面貌是晚至明清以降才完成?但王本属节略本,未足为据,且宋杨简《先圣大训》中所引已有“汝所问,包在五者中矣”,这说明两章合并是很早就完成的,并非后人所为。
(18)拙作《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19)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本为独立的两章,在意思上还是有所扞格的,像范家相即云“按下章以饰容为说,另是一意思,不当联合。”(《家语证伪》,卷二)这再次说明《家语》对有些章次的合并工作只能是初步的,有简单、生硬之嫌。
(20)不过,丛刊本的合并来源也很早。我们看元王广谋本即是合并的,这是否反映了丛刊本与王广谋本的亲缘关系,值得深究。另外,明何孟春《孔子家语注》于此处的处理也是合并的。
(21)此为“孔子”二字的合文符号。
(22)此种“解释性”安排也是今本《家语》形成过程中,整理者所做的一项系统性工作。对此,拙文《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与〈孔子家语〉相关之章题考证》(待刊)有详细分析。
(23)《由出土文献再说〈孔子家语〉的性质及成书过程》,《孔孟学报》(台湾)第82期,2004年。
(24)据笔者统计,今本《家语》只有一处提到“仲尼”,其他则一概为“孔子”。而这一例用“仲尼”也是势属必然:那就是《家语·本姓解》中介绍孔子的家世、生平时提到:“……生孔子,名丘,字仲尼。”
(25)如今本《家语·五刑解》“下官不识”,王注“识,宜为职,言其下官不称务其职”。在这里,王氏显然是在纠原文之谬。据笔者统计,王氏像这样只是在注中纠缪,而非径改原文,达十余处之多,这说明王氏还是相当谨慎的。其一字之慎尚且如此,又如何能说他重组甚至伪造全书?我们今天在探讨王氏与《家语》的关系时,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考虑。
(26)都说到了“君子之道”。
(27)章序有机化的处理,可能也并非由刘向来完成,也许他所面对的材料已经是初步有机化的本子。但鉴于阜阳木牍此处的章序组织还相对零散,所以我们推测《说苑》的这种章序处理应该晚于阜阳简牍。
(28)此处依上下文,应为重文符号。
(29)《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见过《说苑》一类材料,并不意味着《家语》就是王肃利用今本《说苑》来伪造《家语》,应该看到,从上面木牍章题多与《说苑》相合看,我们认为刘向在整理《说苑》这些材料时,改动是很小的。所以,很可能孔安国在整理《家语》时所利用的材料即古本《说苑》就已经是这样的模样了。
(30)《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31)比如“汝所问,苞在五者中矣”,但孙志祖认为是王肃作这样的合并,其实仍然是从王氏伪造《家语》的传统观点出发。孙说见《家语疏证》卷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王广谋本及何孟春本似乎并未合并,但既然二书有“节取”之嫌,故此处亦未可遽定。此处若是孔安国完成,则正印证了我们上文一再提到的孔氏对《家语》材料的重组和整理。
(32)见前揭胡平生文。
(33)关于《说苑》一书的性质,以前沈钦韩《汉书疏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均认为刘向只是据旧材料编订,并非手著。但徐复观不同意此说,力主《说苑》系刘向“撰著”(参见徐复观《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今从《说苑》与木牍章题的比较看,徐氏之新解实妄,而沈、余二氏旧说确不可易。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今本《说苑》就没有刘向本人的“撰著”成分,像该书的一些篇开篇介绍本篇大义与主旨(纯粹论说的形式,而不是像其他章那样多以短小精悍的故事为依托),倒是很可能出自刘向之手,但这类内容为数很少。
(34)拙文《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与〈孔子家语〉相关之章题考证》。
(35)拙文《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36)拙著《〈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第266-27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37)王氏此处于颜渊卒年之致疑不无道理,晚近学者对此都是基本认同的,详参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第7页。
(38)传统上对《家语》持“伪书”说者,一般说王肃是“自为其书,又自为其注”。那么对此处王氏的批评《家语》本文,恐又可说成:自为其误,又自为揭批?成见若此,直不知其可也。
(39)汉志所载二十七卷即为民间本,拙文《由出土文献再说〈孔子家语〉的性质及成书过程》已有申说。
(40)见拙文《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与〈孔子家语〉相关之章题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