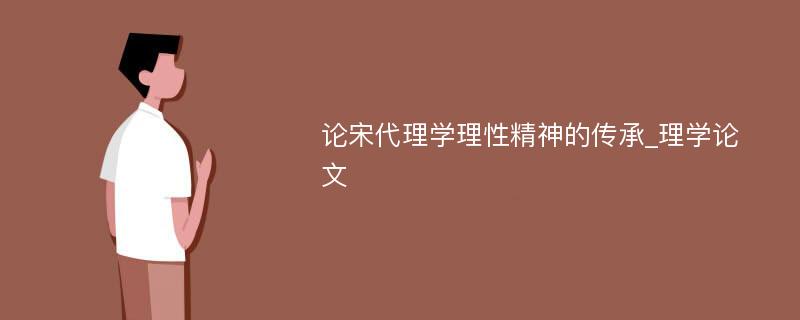
论宋代理学理性精神的承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宋代论文,理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联系思想史和文化史发展的背景,从哲学的层面上剖析宋代理学,就能发现,在理学体系中确有一个富于理性主义色彩的思路和框架,体现着宋儒人文思想的“真精神”(梁漱溟语)。那么,宋代理学理性精神的源头究竟在何处?其理性精神的内涵及实质又是什么?本文拟作分析。
一、《周易》与理学理性观念的确立
从源流上看,宋代理学理性精神的思想理论来源当然是多方面的。善于吸收道家的有机宇宙论思想、积极回应佛教文化的理论挑战、对经学传统的继承和转化,都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不过,一般来说,宋代的理学家大都承续了王弼开创的义理派易学的传统,普遍注重《易》之意蕴的挖掘,比较自觉地吸收《周易》的理性思维因素,并把它纳入理学的轨道加以阐发。这种阐发,主要是在遵循先秦儒家“道统”的基础上,通过对《易》理的诠释、理解、发挥,以提炼和形成宋儒自己的理性观念;又多方面拓展理学理性观念的内涵,进而转衍和发展出理学的整个思想体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宋代理学理性精神的思想源头,主要是《周易》的理性观念。
《宋史·张载传》曾称,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宗者,思想指导也。“以《易》为宗”,颇为精当地揭示了张载虽以崇儒、循礼、敬德为标帜,然其构制体系的思想指导和思维方式却主要来自《周易》,并力图与《中庸》、孔孟的思想互相渗透、溶合。这与周敦颐、程颐俩人也是一致的。正因为有这种理论上的自觉,北宋的周、程、张三大儒在重续“道统”、倡导儒学复兴的过程中,就特别注重发挥《周易》理性思维的意蕴,使之和先秦儒家的“道统”意识相契合,又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活动,从中提炼并形成一种兼有哲学本体论、伦理学和认识论特征的理性观念,奠定了理学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也制约和规定了理学理性精神的基本特征。
确立理学的理性观念,理学开山周敦颐是始作俑者。史称周敦颐“善谈名理,尤深于易学”(参见潘兴嗣作《墓志铭》),朱熹认为其学说之奥“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见《周敦颐集》卷二)。不过,周敦颐擅长以“说”解《图》,所撰《太极图说》、《通书》就是他“著书立图”、“发明其蕴”的成果,尤其是《通书》的“城”、“理性命”、“动静”、“礼乐”、“圣学”等章,更集中反映出他力图把《周易》义理和儒家的“道统”意识相沟通。就通过这种沟通来阐发理学的理性观念而言,周敦颐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周敦颐热衷于解《易》、说《易》,目的是在彰明《易》理之意蕴,以此透视、发挥《六经》、《语》、《孟》的精义,揭示儒门“性学之统宗, 圣功之要领”,由太极阴阳之道来阐述理学理性观念的本体论根据。周敦颐在解释“大哉《易》也,性命之源”的意思时,就顺着《易》理思路,着重发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四象八卦之说,从中发展出以阴阳、四时、五行观念立论的宇宙有机论和万物生成模式。尽管周敦颐的《太极图》传自道士陈抟,与道教的《太极先天图》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比较来看,周敦颐作了自己的解释和发挥,特别是他在《太极图说》中清除了《太极先天图》以“反者道之初”、“可以为天下母”等观念为内容的道家道论传统,突出了《易传》关于“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三才之道”学说,强调了“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易学(参见《太极图说》)主题,以此论证儒家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来“立人极”的主张。显然,周敦颐是抓住了《周易》思维的理性意蕴,进而证明伦理规范和道德行为对天地自然秩序和阴阳变化之道的遵循与因顺,在社会人事问题上确立起合“理”性原则。
另一方面,周敦颐又引进思孟学派的“诚”概念,以儒家性理之学的因素充实理学的理性观念,强化和发展了理学理性观念的道德学和价值论的内容。周敦颐断言:“诚者,圣人之本”,指出:诚之源就在“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又认为:“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通书·诚上》)。进而肯定:“诚者,五行之源”(同上书《诚下》)。从道德本体论与宇宙本体论相统一的角度确定“诚”的基本内涵,显然是把《中庸》“以诚为本”的观念纳入《周易》“三才之道”的思维框架,又作理论上的概括、提升,论述了宋儒的“实理”、“实性”学说。
在“实理”、“实性”学说的意义上阐述理学的理性观念,是周敦颐对《周易》和儒家传统的理性观念的一个发展,后为程颐直接继承和进一步发挥。
我们知道,程颐是北宋义理派易学的代表,其“语及性命之际”大都因循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思路(见朱熹《太极通书》后序)。但程颐曾批评孔孟以来的“前儒”、“后学”虽有《周易》之“传言”、“诵言”,却概皆“失意”、“忘味”,未得《易》之真蕴,申明他之所以作《易传》,目的是求《易》之“意、”体《易》之“味”(《二程集·易传序》)。这无疑又是在易学研究中倡导变革和开新,因而为理学的理性观念增添了新的内容。
首先,程颐以“天者,理也”的命题立论,“自家体贴出”天理概念,并在大易之道的基础上,解释他所谓“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中”“理”(“道”)的含意:既指“《易》者阴阳之道”一类的天地自然规律,又包括有“随时变化以从道”,因顺阴阳之道来规范人事行为的原则,力图揭示“圣学之本”、“道德性命之始”,为孔门弟子“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之学提供理论论证,这就进一步补充了周敦颐对理学理性观念的本体论根据的论证。
其次,程颐也对理学理性观念的内容作了新的阐述。他特别注意吸收孟子的心性论和性善说来发挥《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命题,称:“天所付为命,人所受为性”,又提出:“性只是理”,认为“理”是“天”所赋于者,为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本只是善而无恶,故人所受以为性者,亦本善而无恶。(大意参阅《性理大全》性理篇)这样,程颐就从“理、性、命三者异名而同实”的思想出发,用孟子的性善说充实理学的“实理”、“实性”观念,对《周易》的理性观念也作了积极的引伸。在这点上,程颐和他的弟弟程颢(明道先生)是一致的。诚如后来朱熹的弟子陈淳所说:“明道又谓孟子所谓性善者,只是说继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语移就人分上说,是指四端之发见处言之,而非《易》之本指也”(参见《北溪字义·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程氏兄弟并非一味因袭《易》理而是借《周易》发挥己意,进一步把《周易》思维观念和儒家“道统”意识相沟通、结合,以一种经过重新解释的理性意识和理性化态度从事儒学复兴和理学建构工作,发展了理学的理性精神。
不过,程颐主要从孟子的“性善”论和《周易》的“继善成性”说角度讲理性,偏重于共相性、普遍性的意义上解释理性观念的内容。其实,理性观念(包括理性思维和道德理性的境界)还有高下之分、 优劣短长之别、善恶程度的不同,即理性观念亦有特殊性和差异性问题。尽管程颐已经意识到对这一问题论述的不足,故提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也”(《遗书》卷第十八)。提出气禀说以弥补性本论的不足,但他没有具体展开论述。这个问题,是通过张载围绕着性气、性情关系的分析进一步完善了理学的“实理”、“实性”学说后才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的。
张载曾明确提出“《易》乃是性与天道”的命题,直接把《周易》的理念和孔孟儒家的“道统”意识合为一体。他又称:“《易》即天道,独入于爻位系之以辞者,此则归于人事”(《横渠易说·系辞上》)。主张“天人不须强分”,“天道人事一滚论之”,以此为指导来阐发《易》理,富于自己思想的特色。尤其是张载引进元气论思想,说:“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现、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须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以来,则深于《易》者也”(《正学·太和》),在《易》理阐发中渗入了唯物论因素和辩证思维内容,这更是周敦颐、程颐所缺乏的。不过,张载虽用元气论思想发挥《易》理和儒家性理学说,但后来并没有引向气一元论而导致与周、程思想的对峙和分裂。恰恰相反,他正是为了弥补程颐指出的“论性不论气”的理论弊端,故在肯定性本论的前提下,强调:“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以为“虚”者,即“理”也,理与气合才有人之“性”,在逻辑上确立起性气关系结构,以此说明人“性”虽纯善无瑕,但因气禀有清浊、昏明之别,故性之具体落实就有差异。禀气清正,则得“性”之全体;禀气昏浊,则“性”被遮弊而导致恶行,此即是“形而后有气质之性”的意思。但张载强调:“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又从人“性”的共相与殊相统一的角度,肯定了理性问题上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联系。
张载还提出“心统性情”的论断。统者,犹兼也。“心统性情”,就肯定了人之本性为善,同时兼具情感、情谊的因素。在张载看来,“情”是对应于“性”而言的,情为性之动,亦是性之用。情非单纯由物欲而引发,它是出于内在本性的,故亦归之于心。心有体用之分,心从“体”上讲,寂然不动,本然为善,是为性。心以“用”上讲,则“感而遂通”,使“性”有所发而有“用”,是为“情”。所以,情是出于人“性”、发乎善端而成,视“情”为合理而正当的心理情谊。
值得注意的是,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同时也对性与情的关系次序作了严格规定。据朱熹的概括和介绍,张载是以“好善而恶恶”为情,申称:“其所以好善而恶恶,性之节也”(见《张载集·后录下》)。强调了人之情感又受心“性”的节制和约束,其情之发动皆自然中“节”,从而产生好善而恶恶的思想行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张载把“情”概念引进理性观念,就和近代西方哲学纯粹以“理智”的尺度、局限于知识论的范围来解释理性有着明显的区别。显然,张载力图证明理性不仅是一种干巴巴的、冷峻的思辩,不仅只强调行为要有合“理”的根据,理性还应包括正当的心理情感,以此批判佛家所谓“情是恶底物”的说法,并直接否定了佛家的“灭情复性论”。应该说,张载不仅视理性观念为认识论与伦理学结合的产物,而且把理性扩大到心理学、情感论的领域,足以表明理学家常讲的“存天理”、明“实性”,并非绝对地排斥人的情感欲望,而是在严辩公私、义利之分的前提下,要求人的情感欲望能出于本性、发于善端,既循必然之理,又合于当然之则。这一思想,后来特别为朱熹所继承和发挥,对丰富和完善理学理性精神的内涵有很大的影响。
二、朱熹:理学理性精神的展开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同时也对理学的理性精神作了理论概括和系统表述。朱熹能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定程度上具有吐纳诸家的学术开放心态、兼容并包精神和朴素辩证的综合思维,在周敦颐、程颐、张载诸大儒的基础上,更为细微、具体地论述了理学的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思维而且在实际应用的层面加以展开了。
综观朱熹的一生,泛滥诸家学说、溶摄释道,是其治学的一大特色。他自称:“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语类》卷一百零四)。又称:“出入於释老者十余年”(《答江元适书》)。朱熹虽博闻广识,但他主张:“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语类》卷一百二十),又强调以自己的体验和理会,对诸家学说作综合的选择吸收,故他的治学亦有明确的主旨和重点。最能体现这个主旨和重点的,还是朱熹通过对《大学》、《易学启蒙》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钻研、体会,创造性地阐发先秦儒家的“道统”意识和《周易》的理性思维传统。据《语类》卷十四记载:朱熹“说《大学》、《启蒙》(指《易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朱熹自信“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表明他确能以超越前人的眼光和兼溶并蓄的态度,契入《易》理的意蕴,提升儒学的传统精神,完善和进一步展开了理学的理性观念。
首先,朱熹分别从程颐、张载的思想中拈出“性即理”、“心统性情”两个命题,并加以综合贯通,全面展开了理学理性观念的具体内容。
朱熹在应用《易》理观念解释《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一句时,曾断言:“性与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参见陈淳《北溪字义》)。他又说:“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虚莫非是理而已”(《伊洛渊源录》),继承和发展了程颐推出的性、命、理三者“异名而同实”的观念,并揉进张载的“心统性情”说,从中引伸出心、命、性、理四者“合一”的思想,揭示了理学之“理”须落实于“性”,“理”与“性”并用、联通,既是“得天地之理”,又“具于心之理”而成性,肯定了心即性、理,理性即心体的属性;又肯定了心兼具“出于本性、发于善端”的心理情感因素,这就确认了理学的理性观念实包括有本体论、价值观、伦理学、情感说等多方面涵意,体现着天人合一、情性合一、仁知合一的思想特征。像朱熹那样理解“理性”,也对以后儒家理性观念的演变发生过很大影响。近代学者梁漱溟在比较了中西哲学及其文化,肯定“人类的特征在理性”的同时,特别用理性与理智的区分来揭示中国与西方理性观念的差别,指出:“心思作用”常有二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据此断定:理性为道德之事,系对伦理情谊的体认和践履,理性“要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均见《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可以看出,梁漱溟实际上是顺着朱熹确认的理学思路来剖析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的,他偏重于理学的理性与西方理性的同中之异,旨在揭示中国理性精神的特征所在。
其次,朱熹又提出体用、理事关系范畴来阐发《易》理意蕴,弘扬儒学精义,在本体和事用的结合上,把理学的理性观念转衍为一种理性的思维态度和行事践履工夫。
我们知道,朱熹曾十分欣赏程颐“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句话,说:“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太极图说》附辩,载《周敦颐集》)。这里,朱熹把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理数(象)统一之说发展到理事关系范畴上展开论述,视“理”为幽微之体,明“理”则可举体而用之;“事”则是显于象之“理”,即“事”也可见“理”之体,进而提出了“先体而后用”(由微而显)或“先显而后微”(即用而见体)两条把握本体之“理”的途径,着重发挥“依理立象”、“见象明理”的《易》理思维原则。
朱熹用体用、理事关系范畴来讲《易》理,也溶铸了他对《易》理意蕴的新见解。在朱熹看来,“理”为体,“事”为理之“用”,既认为“理”之体“该”(主宰、贯穿)万事万物,然因其“初无形迹之可见,故无”;又认为“理”能以“象”示,则实有其事,由此断定:“理之用实,故有”。他还批评圣人作《易》“只是说一个理,都未曾有许多事”,主张“稽考实理,以待事物之来;存此理之体,以应无穷之用”(《语类·易纲领》)。这就强调了《易》之理不光是一种无形迹的本体,而且是可显于象、事的“实有”,不仅要靠抽象思维加以理解、领会,还应该通过认知、观察、稽考的手段展开应用。这样,朱熹一方面把周、程依恃“意”、“味”才能体察的《易》理,转化为在喻象、考卦、衍数的操作层面上也可直接把握的功夫、方法。另一方面,朱熹以“执古御今”的态度,推演古《易》之理,处置“今日之事”,主张治《易》、解《易》要在明“理”、体“道”的基础上,还应推广于社会人事,使人人皆能应用、受益,变“圣人之道”为人伦日用之学,这就深化了“理”作为“事理”、“实理”的具体内涵,发展了理学的理性精神。难怪朱熹曾不无得意的声称:“某之说《易》所以异于前辈者,正谓其理人人皆用之”(《语类·易纲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经周、程、张等重新发现并加阐发的《易》理意蕴,到了朱熹那里,更由一般的理性意识、理性观念,发展成一种切近社会人事、注重日常人伦,以理性的态度处事待人的精神和方法,从而使《周易》、孔孟到宋儒一直贯穿、流衍的理性观念有了具体的形态化表述。
第三,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讲的“理性”,虽重在德性,也兼有认知论的因素,但他把德性和认知都看成是源自内心、“据理而发”,是排除了经验和感性的一种“悟解”、“体认”工夫,又使理学的理性精神涂上了直觉主义的色彩。
朱熹和其他理学家一样,也肯定“心者,一身之主宰”。他顺着张载的思路,说明心之所以为身之主宰处,原因就在心“有人虚灵知觉”。当然,朱熹讲的“心”,也兼有心性、情感、意志等多重涵意,很难作明确界定,但相对于“物”、“事”而有心知,又和性、理范畴联系,则朱熹主要在“知觉”的意义上规定了“心”的内涵。问题在於,朱熹把“心”夸大成具有“包万理”、“应万事”的能力,认为知觉若“以理而发者”便是性,亦即是道心;知觉若以形气上发来,“便是人心,便易与理相违”,明确排斥了知觉中经验感知的作用,这势必导致以“悟解”、“体认”作为认识的全部途径和方法,那就片面发展了张载的“德性之知”、“天德良知”的先验主义认识论,把人的理性知觉看成是“至虚至灵”、“神明不测”、“圣不可知”的,则和神秘主义的直觉论难划界线了。
三、结语
以上的分析,旨在揭示先秦以来的中国理性观念在宋代经历了提炼、阐发及演变的过程,从一个重要侧面说明:宋代理学通过其特有的理性精神的发扬,确实把儒学传统的哲学思维和伦理探索提高到新的阶段。这是宋代理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塑造上所做出的贡献。但同时,宋代理学也把先秦理性传统中的内在矛盾和负面价值大大发展并定势化了,尤其是理学家常以理“即礼”的命题并论,强调理为“不可易之则”,又不断发展出以道心人心、性善利恶、天理人欲对峙并列为特征的两极思维和价值判断,容易把理性精神引为宗法等级观念和封建道德伦理的附属;再加上宋代理学家善于运用“天理”的权威和理论的说服,又强化了对宗法等级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的论证,用一系列教条式的普遍准则,去规范和框照社会人事行为,势必导向反理性主义的宿命论。可见,理学的理性精神确实有内在矛盾和两重价值,所以,以“理性精神”为观察角度来把握宋代理学的历史定位,要有辩证思维和分析态度,切忌简单化的单一模式,避免陷入“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两极对立思维的巢臼。
事实表明,自宋代理学兴起以后,先秦以来的中国理性精神传统,在其发展的顶点处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惟有以改铸和重建为前提,才能有新发展的转机。这一转机,终於在明清之际出现了端倪。随着功利主义思潮的再度崛起、人文启蒙思潮的潜动、在科学推动下的重知识、讲实践效应思想的盛行,都促成了对理学理性精神的重释、批判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使其有了健康发展的可能。
标签:理学论文; 周敦颐论文; 朱熹论文; 儒家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宋代理学论文; 读书论文; 太极图说论文; 易经论文; 国学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