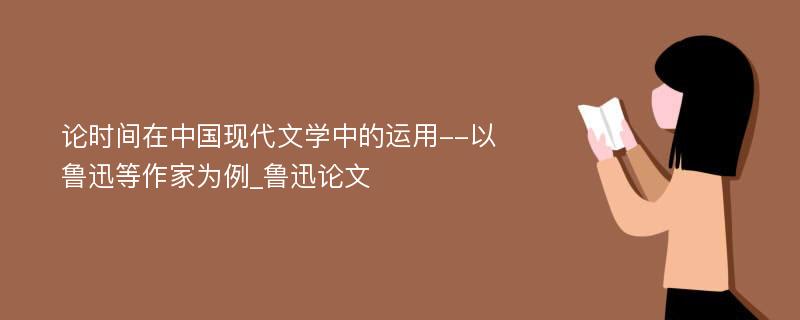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时间运用——以鲁迅等作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作家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日期的象征性运用历史上任何节日都有。毕竟,节日本身取决于历法的存在。而且日期在中国又特别引人注目(注:谢海华编《纪念节日手册》,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年版。)。中国传统上每每用一个日期代表一个阶段。本世纪汉语中“五四”这个词就是颇具活力的一个。当我们谈论本世纪中国文学时,就无法回避“五四”运动——尽管这个缩略语表达的时间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注:周策纵《五四运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这个涵盖十年时间的词具有象征意义,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这个“新文学”的运动特别富于乌托邦式的期待,我们可以找出十几个带有“新”字的词汇来说明这一点,其中包括“新历”。“新历”这个词具有末世学意义。西历的公共纪年法,即纪元,据《圣经·马可福音》,是以耶稣基督的诞辰开始计算的,其中使用了“准确时间”(Kairos)这个概念。但另一方面,古典修辞学上把准确时间这个词的意义解释为“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中,瑞士和德国的宗教社会主义运动则把“准确时间”解释为“完成的时刻”,即得到最后拯救的“富有意义的时刻”。它不同于单纯的对时间长度的衡量——即对时间的客观记录。
毫无疑问,具有鲜明前卫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把一种文学叫做“新文学”的时候,对上述末世学和修辞学方面的外延是都相信的。他们最现成的背景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天即1912年1月2日发布的一个法令,该法令确定用哥利高力太阳历代替旧的农历。如所周知,对时间的确定不单单包括对现在的确定,而且也包括对过去的确定。
本文的目的是描述民国时期的时间记录法,首先我将引述某些其中包含有时间运用的文本,然后举出若干日期记录方式,对其特点加以讨论,最后则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虚构文学上,探讨虚构的日期在作品中的作用。
一.某些讨论日期记录问题的文本
陈衡哲最早发表的作品中,有一篇通常被人忽略的新文学的先驱作品,就是有关历法的专论《改历法议》,它实际上是191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历法简化会上一份文件的节译(注:《改历法议》,见《新历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它首先介绍了现行历法的情况,将基督诞生日定为“无日”——还引用了英文原文noday ——然后对向几种古代历法做了简短的回顾,从古埃及、希腊、犹太和伊斯兰到哥伦布以前的美国历法。在讨论时间计算法时,把金字塔和格林尼治时间做了平行比较。这些都是在涉及究竟采用公历还是采用农历时举出的——这显然是陈衡哲最关心的所在,她的所有“译者注”都指向这个问题。她在原文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最近,中华民国也采用了公历纪年。”她把这个改变看作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证据,就像日本国此前做的那样。
同样的对比也出现在胡适的几首即兴诗中。胡适所关心的是他那一代人共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包办婚姻。《我们的双生日》一诗的内容是,公历1920年12月17日(胡适生日)正好是他的妻子江冬秀农历生日,八月十日。胡适写道: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约定,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的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
要不是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他撕了。(注:胡适《尝试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从传记材料来看,此前胡适刚同他的情人曹沛生在西湖度过了几周他称之为“蜜月”的时间,这首本来听起来是和解的诗,读来却有相当的不快。他不但将妻子同“旧”联系起来——农历也叫旧历,而且妻子也是他的一切与文学有关的活动的障碍。还有,胡适笔下的妻子简直是个文盲,威胁着要消灭他的文学作品——作者在注释中还特意强调“诗”和“撕”的谐音押韵。
同样,对农历的“旧”和公历的“新”进行对比联想的还有鲁迅,他的多篇作品中都有此类对比,最明显的是写于1924年的短篇即兴作品《奇怪的日历》,其中他简洁地叙述了他购买一本印刷质量很差的日历的经过,但对他来说真正“奇怪”的是它竟是新旧历法的混合物:按照公历排出了13年的日期,却还列出了很多所谓黄道吉日,诸如哪天宜于沐浴、理发等等。(注:《奇怪的日历》,《鲁迅全集》第8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另一篇作品《头发的故事》中,墙上的挂历扮演了主角。它构成了故事的主框架,鲁迅让N 讲述了几世纪以来中国关于头发的寓言故事,作品的开头叙述者说: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啊,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注:《头发的故事》,见《鲁迅全集》第1卷。)
在这里,公历的地位无可置疑,但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记录系统,其中有着“记住”和“忘却”的分界线。这里引发的问题更复杂,不能单纯归结为使用这种或那种历法的态度,而勿宁是一个系统内部的问题。记住双十日很有意味地表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N 的相当悲惨的个人与集体的经历和他与叙述者的谈话得出的结论却是:“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使用“新”历,而且意识到纪念日来自这个历法,又通过双十节,指向“新”历法的来源,这个纪念日可以同代表“正常”时间的记时概念进行比较。该“正常”概念是梯利奇创造的,是上述“富有意义的时刻”(Kairos)的反意词。
毕竟, 鲁迅本人是绝对不会忘记这些的。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1925到1935年——当他按照惯例在年底编纂他的杂文成书时,每书的前言和后记都给他充分的篇幅,或以快乐、或以悲伤的心情署上日期。他死后出版的最后一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就准确地指明一个富于文学意味的新年,即从12月31日深夜到他去世那一年的1月1日早晨。(注:见《鲁迅全集》第6卷。)
鲁迅公开发表的信件——它们可以称为教谕式的——即所谓公开信,也包含着一些例证。我们在《语丝》杂志上发现了一封给一位青年读者的回信。根据介绍,读者提出如下哲学意义上的问题,而且是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无论是什么历法上的年)提出的:
我生二十五岁了。从民国元年改用西历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个新年了,——不,三十四年新年了。因为过了阳历新年,还照例要过旧历新年的,若按过一个新年算添一岁的话,我现在应是三十九岁了。那么“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民国却并不“稀”了。今日又是阴历除夕,……(注:季廉《通信》,见《鲁迅全集》第8卷。)
在给未婚妻宋若瑜的信中,充满活力的左翼作家,在中国北方不停地旅行的蒋光慈,承认他自己在感情与理智上存在矛盾,后者拥护“新”的,前者却依恋“旧”的:“我仍然无法摆脱旧习惯。当别的人都在庆祝新年的时候,我禁不住加入进去。”(注:致宋若瑜信,见《蒋光慈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然而,“新”历已经渗透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至少对那些生于世纪之交的人来说。但“旧”历依然有它的市场。对章衣萍来说就是如此,他在三十年代初期作了一系列有关白话书信的讲座。当时语言的规范化建设正飞速发展,已经达到建立文学样式和讲究风格的阶段。章氏没有受谦让传统的影响,径自选了自己一封信。这封信主要探讨的是“旧”的修辞手法的消失问题,开头是这样:
今天是一九二七年的第七天。如果是阴历一月的第七天,我想我会更高兴的,因为那才是春天。(注:章衣萍《书信讲话》,上海沪江书店1932年版。)
很久以后,谢冰莹将“新”与“旧”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变成一种经验的积累和丰富。她为其余不同的历法打开了新的天地,并且起草了在今天看来是“多元文化”的东西,而又不失本文化的特点——至少从与历法有关的习俗上来说:
记得在马来西亚教书的三年中,每年我们要过四个新年:印度年、马来年、洋年(当地侨胞有的叫红毛年),最后,也是最隆重的,是我们的农历年。
也许因为农历年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太深刻的缘故,我一直感觉阳历年是外国人的年,也是应付公式的年。真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年;至少一年要过两次年:一次属于自己的国家民族的,一次属于世界性的;这两种年,都有存在的价值,用不着我们提倡或反对,它会自然地永远保存下去的。(注:《可爱的农历年》,见《谢冰莹散文》上卷,中国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
二.日期的形式
很明显,日期的形式应该分为两组,一组是公历纪,另一组是农历纪。而且,考虑到以上零散的议论所提供的情况,应该说不用这一个而用那一个历法来记录日期反映了对待“新”与“旧”的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便这种用法很快就变成一种稳定的个人习惯,即个人习语——它因此可以被用来反对习俗,无论其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也因此会变成一个战略意义上的工具或美学的工具。最终,即使在公历内部也变得同样明显,有了民国纪年和公历纪年的双重纪年法。后者是容易被忽视的一方面,在三十年代,它甚至成了书报检查机关的一项工作:1937年6月6日,内务部出版署禁止《呐喊》发行,声称“其内容无涉反动”,但命令其将“年月日依国历改正”(注:见《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另参阅《且介亭杂文·后记》,其中有被禁书书目。)。
从技术上说,六到九个数字(或三个数字)和三个汉字,或者三个数字、四个汉字(或者五个,如果民国简称“民”的话)足够明白无误地按照公历说明一个日期,五个汉字和两个数字在六十年循环中足够说明一个农历日期。那么,在这种模式下,有些有趣的图表(在一个方框中写两个数字汉字代替一个两位数字)和读音法(廿读作二十,而不读作nian)被采用了。全部写出汉字,不写一个数码(注:《〈壁下译丛〉小引》,见《鲁迅全集》第10卷,写作“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或者干脆采用时兴的办法写成英文,如,March,12,1925 (注:刘梦苇《竹林深处》,载1925年7月17日《莽原》第13期。), 只是少有的例外。
在随后的一封信中,蒋光慈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的心的归属。那封信里附有一首诗,关于日期是这样注明的:中历闰四月十五夜诗意,二十一夜写出(注:见《蒋光慈文集》第3卷。)。 这种注法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说中历闰四月,与通常的假设相反,很明显地说明不但这封署了5月21日的信,并非写于5月21日(注:另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1990年修订版。);其次,它有一种对文学创作的理想化概念,这种观念来自传统诗歌,这里体现在所谓“诗意”和“写出”上,其间相隔六天;再次,数字后的“天”字的省略,尽管用“新”的阿拉伯数字写出,可以成为对阴历纪年法的一种暗示,阴历同样用两位数字计算天数;第四,对更具体的时间的指明(夜),这里出现了两次,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很多问题,下面将予以讨论。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这个很简单平常的格式,在李霁野的《病》中却是很罕见的(注:李霁野《病》,见1937年4月15日《文丛》。)。为了标准的稳定性,也因为日期的表意和修辞功能的共同丧失,日期记录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程序,特别是以简略形式出现的时候,即用逗号将数字隔开,就像葛琴在《药》中那样,只将数字写出,并将十位数的表示法省略(一九三七,三,一八)(注:葛琴《药》,见1937年5月15日《文丛》。)。
即便在公历纪年中,无论是民国还是公历,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当一个数字省略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的要素都省略,例如十一月廿二日(注:鲁迅致陶元庆信(1927年11月22日),见《鲁迅全集》第11卷。)。但更常见的省略出现在“日”被“夜”代替的时候(注:鲁迅致李霁野信(1929年10月20日),见《鲁迅全集》第11卷。)。用单音节和双音节表达十位数时(廿、卅)是例外,其特点是把两个数字融在一起(二十日,但廿一日)。如果按西文顺序纪年月日,则不一定使用此法,如七,十四,一九二九(注:章衣萍致吴曙天信(1929年7月14日),见《衣萍书信》,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当天数用一个数字写出来,或者数字写法不同时,有些用简单的数字,有些却用填写支票时的大写(注:章衣萍《秋冬的信》(1930年11月9日),写作“一九三0,拾一,九”。另有“一九三拾,十一,二十”。)。
无疑,一个事件不会只以一个形式来记录,它可以有特别指明的时段,或者小时直至分钟。的确,中国现代文学是从一个大学校园里的一声钟声开始的(!!)——陈衡哲的小说《一日》(1917年,这个标题很好地反映了语言的转型,后来变化成标准的“第一天”,但她之后有不少作家的叙事作品都袭用了这个题目《一天》在描写一天时,按照一个白天的时间来构建作品。而且,小说每一部分开始时都很明显地在写报时的钟声响起的同时,也写时钟的指针怎样指向那个小时。这篇小说在计数方面的意象是相当丰富的。 (注:《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6月。)
但通常,在书信中,越是随便(且不说更亲密),对标注日期甚至小时的方式就越是具体准确,例如在许广平和鲁迅的通信中,开始用的是十一,三,十四年(许广平把“民国”和年月日省略了),三月十一日(鲁迅省掉了年份)(注:1925年3月11日和14日, 见《鲁迅全集》第11卷。),结尾时用“下午五时”(鲁迅),“上午十时十分”(许广平)(注:1929年5月27日和30日,见《鲁迅全集》第11卷。 另鲁迅致许广平信(1932年11月20日)中还用过“夜八点”,“点”比“时”更口语化一些,见《鲁迅全集》第12卷。)。这种情况下通常逐步省略掉大的单位如年份甚至月份,为的是保持数字的平衡,当然也有的为了玩笑。例如在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出现三个“11”,组成n-x-n-y-n-z 模式,这是为了指明时间过得很快,有双关的意思(“快速”和“快乐”)(注:(1926年)十一月十一晚十一时,见《鲁迅全集》第11卷。)。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把这种方法推向极致,并且在汉英两种语言间转换:
十二点了。你还没有消息,我再上床去躺着想吧。
十二点三刻了。还是没有消息。……
一点二十分!
一点半——Marvellous!
一点三十五分——Life is too charming,too charming indeed,Haha!
一点五十五分——天呀!……
两点十八分——疯了!
两点三十分——
三点七分——
三点二十五分——火都没有了!……
六点三十分
七点二十七分(注:徐志摩《爱眉小札》(1925年8月18日条),见陆小曼编《志摩日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很明显地,在日记和书信(这里指的是没有虚构成份的)里时间被视作最适合表达个人和主观性的一个因素,因此被广泛使用,这就为日期表示方式提供了大量材料。我们发现郁达夫的《九篇日记》(1926年和1927年,1927年出版)使用了一套很有力的纪时系统,有时候一个日期用三种方法来记录:第一种是官方使用的公历,第二种是农历,通常被称为“旧历”,一般能提供一些关于气候的信息,以上两种都作为题头,标明要记录的一天,最后,第三种,在结束的时候说明被描述的这一天,常常给出相应的白天的时间。这种情况有时甚至被提到多次,如7月30日:“七月只剩下明天一天了”,还有1927年7月31日:“七月的日记到此结束。”(注:《郁达夫文集》第8卷第184—185页, 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胡适的日记从二十年代开始使用民国纪年并不奇怪。日期用最简省的方式表示,即年、月、日中间用逗号隔开,尽管用拉丁书写规则记录一星期各天增加了非中国化的味道。(注:见《胡适的日记》1921 年7月,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0—167页。)
鲁迅的日记,很明显最初无意于出版,我们从中发现了最简单的记录方法,即一般用公历来记录月日。但是,其中也有零星几处采用“旧历”的:在1920年前后他放弃了用干支纪年的方法。但在1918年前,他保持用这种方法记录,如“正月”。后来变成简单地用序数字来标示,如1920年的“日记第九”。于是我们发现两种历法在1912年日记结束时碰到一起,这一年最后一天的日记记有:“华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之”。但翻开“癸丑日记”,发现2月6日条下,特意记着“旧历”的新年(注: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38—39页,又43页。)。他的弟弟周作人的日记,在这种技术性的记录上与他的日记差不多。但在1919年,周作人的日记向现代化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年他开始使用印刷发行的日记本,上面辟有专栏,让记事者记下天气、气温和书信往来的情况(注:《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 卷第574—755页和第3卷全部。)。
三.与日期有联系的传记和非传记材料
很多日期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联带着某种东西,我试图用最简略的方式称之为“外延”,尽管从句法意义上说,只指明一天时间或者给出具体的小时只是一种标志。这种外延有两种基本形态,那些标明作者个人处境(真实的或者虚构的)的我称之为“内在的”,那些指明的事件与作者传记材料没有直接关系的,我试称之为“外在的”。后者更多地用来指明对于外在世界的一般意识,只是附属于日期的一个东西,而不提供对于思想的启示。
最普遍的是标明“夜”(注:郭沫若《献诗》,见《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第259—2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和“晚”(注:《“题未定”草》,见《鲁迅全集》第6卷。另1933年5月4日同一天写给黎烈文的两封信中用了“夜”和“晚”两个字, 见《鲁迅全集》第12卷。)。这本身具有含糊性,可以用来开启浪漫主义者创造和感情的天地,还有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蕴含的诸如思乡等情绪。它可能含有多种特性,诸如“深夜”、“半夜”,或者“夜中”。在鲁迅笔下,这些词的同义词“灯下”经常被使用。
典型的内在的材料见于艾青的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作于1933年6月16日,作者注明“在病中”(注:见《艾青全集》第1卷第6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诗的主题似乎是与基督重生相关的经验,不是他自己的病。但我们发现章衣萍也有这种写法,他给汪静之写了一封信, 注明“写在她(指吴曙天)的病榻前”(注: 《衣萍书信》1926年5月17日。)。疾病甚至可以作为月、日的替代,在1926年有 “秋天,于伤风头痛之日”这样的记录(注:《衣萍书信》1926年5月21日。)。这种纪时法变成一种普遍使用的题目,如鲁迅作于1936年的《写于深夜里》,用常见的结尾注“后半夜”来强调和特别标明(注:见《鲁迅全集》第6卷。章衣萍写过《在灯下》(1925年5月11日致伏园信),见《衣萍书信》。)。
同样的转换也出现在茅盾的短篇小说《夏夜一点钟》里,小说的开始是一个无名的女主角在难眠的夜里叫道:“一点钟了呵!”像陈衡哲的小说一样,作品里充满了对钟表指针运动状态的详细描写,但时间主题却被用另一种方式表现;陈衡哲的女大学生们被校园那座钟强有力地控制着,而茅盾小说中的女主角的时间经验则完全是个人的,就像她看的是她自己的表一样。给她带来烦恼的钟表,本是一个男子所赠,号称“走时最准”,实际上快五分钟。当她把表与给予大上海最准确时间的海关大钟对时时,她终于忍不住迁怒于那个给她写过二百多封情书的赠送者身上。其中一封情书是“上月20号写的,正好是他赠她表的前两天”。她的思绪,在公共时间早晨两点和个人时间两点零五分这样结束了:“现在的男子,真是——真是太不尊重女性!”(注:见叶子铭等编《茅盾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我们这里不但看到不同时间观念的一个寓言,而且还看到一个错过准确时间的寓言,这个寓言在不能提供准确时间的手表上鲜明地体现出来。
日记中常见的还有关于天气和气候的记载(在周作人的印刷格式的日记中, 这种信息没有多少意义), 如“大风时”(注:《两地书》1926年12月5日,见《鲁迅全集》第11卷。)、 “暴风雨过去的晚上”等等。但后一个句子中的“暴风雨”不是真实的暴风雨,而起到贯穿整个信的主题的作用,这封信是写给一个隐去姓名的“湖上漂泊的C ”的(注:章衣萍《东城旧侣——寄湖上漂泊的C》,见《衣萍书信》。 )。
很明显,关于季节的说明,就像前面说过的“秋日”那样,也指明某种特殊的气候,但另一方面,它们设定了更长的时间间隔,或者被用作更一般性的日期。汪静之的许多首诗就是好的例证,其中善用季节,如“二五年初冬”(注:汪静之《悲愁仙子》,见《寂寞的国》,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我是天空的晚霞,二五年春”(注:《我是天空的晚霞》,见《寂寞的国》。),有时候对某个季节的本质进行描绘,如“红叶的秋天”(注:《无题曲》,见《寂寞的国》。)。
另一些日期记录法直接指明写作过程,如最常见的“记”或“写”,或简单的“作”,往往在文后注明。另一种涵盖相当长时段写作过程的记录办法是特别指明两个不同的日期,即“初稿”和“改削”的时间(注:郭沫若《凤凰更生歌》,见《郭沫若全集》第1卷。); 有时只有一个日期,写上“改作旧稿”(注:汪静之《伊心里有一座花园》,见《寂寞的国》。)。在学术文字中,署上多个日期的情况是常见的(注:这方面的例证可参看方铭和吕美生《论桐城派》,见《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写作:1962年2月初稿,同年11 月修改,1963年5月定稿)。)。
这种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其写作过程意味着不断提高。还有一些与现代方便的交通相联系,如汪静之的诗《窗外》,其内容即是“速写于沪杭路车中”的直接结果(注:汪静之《窗外》,见《寂寞的国》。)。另一个例子是在铁路上写的一封信,以作者的思绪而不是以旅行作为主题,为了记录时间的进行,加上了时刻的说明:“十一点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车了”(注:茅盾《一封信》,见《故乡杂记》, 曾被章衣萍《书信讲话》引用。)。
如果我们将胡适写在信后面的附言作为一种时间记录的话,将它看作直接指明过去的时间和可能是作者本人看到后加上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尽管胡适很严格地使用公历,而且为使用它感到自豪,就像上面引的一首诗中表现的那样,但他仍然按照农历来过生日,尽管他不说出来。“我刚刚在这里过了四十岁生日。当我做大寿时……明年我们会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注:胡适《致梁实秋》,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卷第954—955页。 )这是他在1930年12月23日写的,那时他刚过了三十九岁生日。他明显地把这一年作为他的“四十大寿”,就像他在三年后出版的自传《四十自述》中写的那样。
外在的日期明显地以两种方式表现,一种是指明一件与日历相关的经常发生的事,另一种是指明一个单独的事件。第一种差不多都既与基督教节目相关,但又用国历,是一种混合物。在完成了具有首创性的女作家作品选集的编纂工作后,张若谷在序言的末尾这样写道:“十七年写于真美善编辑室,耶稣诞生后五天”。这个记录出现在附记中,前面的正文后已经有了日期记录,是“十七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两点。”这同时也说明了作品的生产过程(注:张若谷《编者讲话》,见《真美善杂志一周年纪念号外:女作家号》,上海真美善书店1928年版。)。
在中国国庆日,许广平在她寄出的信后署上“双十节”(注:见《鲁迅全集》第11卷。)。此外,一个国立的机构在署了“五七国耻纪念日”的一篇文章中被提及,北方各省普遍举行了活动,这一天是发布有关二十一条要求最后通牒的日子,但实际上官方记录的时间应该是五月九日(注:常燕生《胡景翼先生的遗念(二)》,1925年5月15 日《莽原》第4卷。)。
纪念日不一定都是官方的。正相反,对徐志摩来说是个人的,他的一条日记上这样记着“回国周年纪念”,这样就把它转化成内在的记录了(注:《志摩日记》1918年10月15日。)。
广义上说,“正月”这个说法可以被看作明显记录以外的一种记录。但是,我们也看到别的一些节日诸如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章衣萍在《秋冬的信》中使用过——“一九三○年重阳后二日”(注:《秋冬的信》,见《衣萍书信》。)。
一个单独的事件的例证,可以举出1927年12月1 日宋美龄和蒋介石的金钱和军权的联姻。章衣萍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注:《海上通信》,见1927年12月17日《语丝》。)信中说他“在病中”是否与这个婚事有逻辑上的联系,则不得而知。
四.象征和有意的安排
民国时期以日记形式出现的两种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是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都为象征性地使用日期记录法提供了许多机会。对《狂人日记》来说,日期记录简直找不到踪迹,时间的进行是模糊的和不规则的(注:尽管研究《狂人日记》的文章很多,但似乎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丁玲的作品则完全相反,首先,日期造成了节奏感,时间持续了三个多月,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事件是在夏至后的一周内发生的;其次,对一些主要的日子,叙述时用了日期来加以强调:日记开始于12月24日(注:这里似乎应该提一提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当时郭沫若的译本在城市青年中影响很大,丁玲显然是熟悉的。该书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恰是12月24日。关于歌德作品中的日期的象征意义,参见G.布尔《歌德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日期的运用》。),这一天不仅仅是“对肺结核病患者很危险的严酷的冬日”而已(注:G.布尔吉《〈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言》,见《淡江评论》1974年第5期; 顾彬《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性与文学——〈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反映的49年前后中国的妇女问题》,顾彬与瓦格纳编《中国文学与批评论文集》,布罗克梅耶1982年版。)。同时,住在西方化的都市上海的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日子是圣诞前夜。特别对丁玲来说,她的女主人公莎菲在三月八日对什么是“爱”表达意见不是偶然的。在不到两天前(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而且在这一天以后,她远离那些“老喜欢研究这一个‘爱’字的青年人”。莎菲继续说:“虽说有时我似乎懂得点(爱),不过终究还是不很说得清。……怀疑到世人所谓的‘爱’,以及我所接受的‘爱’……”(注:《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文集》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考虑到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三八节有感》(1942),莎菲日记中的日期问题尚未引起特别的注意是相当奇怪的事。
至少,表现在莎菲日记中日期记录上的时间进程是十分明显的。在后面的日记中甚至具体到小时。后三天的日记记录的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已经上午九点了”(3月27日晚上),以“天哪!九点三十分! ”和“九点四十分!”结束的三月二十八日早上三点以前的内容:“十二点半了,他还没有走。”的确,时间进程(甚至结束前那个条目中落笔前的十分钟迟疑时间)指向莎菲的“准确时间”,是她自我探寻所能达到的完满结果,她最后决定到南方去以获得解脱。但当丁玲让莎菲到达南方后重新拿起笔来时,很明显她没有找到她追求的东西。这两条写于1931年的日记的第一条,注明日期是“五月四日”,可能意味着丁玲表达的是整个一代人希望的破灭,这个日期正是这一代人的身份标志。
在另一份日记中——小说集《自杀日记》中的同名小说,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同一年——丁玲用了很复杂的日期记录系统,构筑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框架。在八个部分里,伊萨的日记和她的逐渐恶化的健康状况被叙述者报道着,有许多有关写作进程的细节描写,如笔划的力度、草稿上日记的位置等等。第一条引文揭示了伊萨复杂的精神状态:“今天大约是十八吧。”这些暗示随着叙述者后来引用伊萨的“另一天的日记”似乎逐渐消失了。然而在最后一条日记中,伊萨写下日期时,意识变得十分明确(这是第三层叙述),指向全文的中心关系:“(我)请父亲到母亲坟上去,向母亲说一句:‘今天是十月二十六。母亲为我最吃苦的一天’。”这个时候正是伊萨一生中所谓“大限来临”的时刻。日期在此处明显地表达了伊萨的精神错乱,同叙述者的精神状态形成对照,因为在结尾部分,叙述者宣布道:“这天是二十七日。”(注:见《丁玲文集》第2卷。)
这种时间的错乱,在张天翼的讽刺性作品《鬼土日记》(1931)中达到极致。其中一个死去的朋友对记日记的人扮演了心理时间的角色,他描绘了在鬼土的经历,那里两个社会阶层的人,住在上边和住在地下的,组成两个强有力的政党,一派主张使用蹲式厕所,另一派主张坐式。四十四条日记都署上“末日”这样一个日期(注:见《张天翼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92年版。)。 这表明这个地下国家的国务活动是超时间的,即没有日期。这是不是意味着,没有衡量时间的工具就没有获得具体时间的希望这种说法有些过于迂远了呢?或者,这个记日记的人的朋友在“适当时间”到来时传达给他这样的信息:这个世界(在作品中很明显就是中国)正处于疯狂状态中?
当鲁迅在为《华盖集》写题记的时候,不但提到他的文字产量的增多,也提到已出版的文集的题目,这也表明他有策略上的考虑:“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注:见《鲁迅全集》第3卷。)
很明显,时间的单位变得越来越小具有象征的意味,它会走向对时间的超越,当鲁迅写下“七月二十九,或三十,随便”时,(注:见《鲁迅全集》第11卷。),有意义的时间变得没有了意义。或者说对时间相当在意的鲁迅,突然宣布对时间漠不关心了。一次他建议许广平发表文章时,没有忘记提醒对方将《五分钟以后》和《半年以后》两部分合在一起,成为《五分钟与半年》。该文发表在《莽原》上时题为《过时的话》(注:景宋《过时的话》,载1925年7月31日《莽原》第15期。),上述两个小标题均予保留。无疑,它们都与时间有关,内容关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那场风波,他们两个的关系也正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1929年5月4日,茅盾写作长篇评论《论〈倪焕之〉》,指出小说的主人公对十年前那天发生的运动所标举的理想感到失望时,竟没有想到日期上的巧合,这总有些不可理解(注:见《茅盾全集》第19卷。)。那么,我们还可以问,1931年10月10日,鲁迅校改了曹靖华译的《铁流》并为之写后记,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注:《〈铁流〉编校后记》,见《鲁迅全集》第7卷。)
最近几十年,文字产品所署日期有时也显得极为重要。这方面我所发现的最好的例子是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1973年9 月出版的一本研究著作《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该书扉页上写着:“一九六九年十月初稿,一九七三年五月增改”(注:赵纪彬《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标签:鲁迅论文; 胡适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中国历法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章衣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