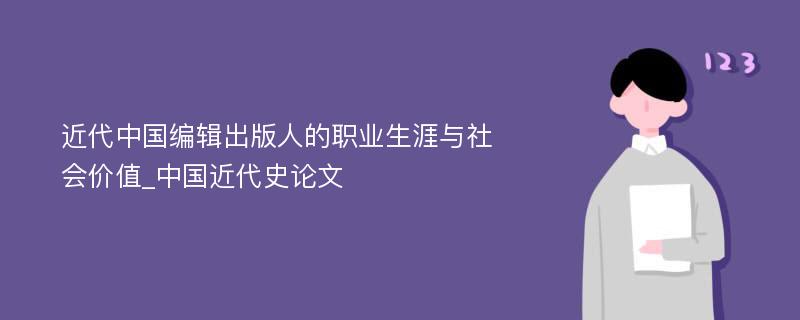
我国近代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生涯与社会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生涯论文,近代论文,编辑出版论文,价值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史学界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史学界对近代史的分期存有争议,有的学者主张1840年—1919年为近代史阶段、1919年—1949年为现代史。本文从近代出版业发展的特征和连续性考虑,选取史学界的第一种分期结果)。中国近代出版史与近代史的分期基本对应。在近代百年历史中,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近代编辑出版人群体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这个特定的群体具有特殊的时代特质、职业特点和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其产生的时代条件、文化氛围、社会背景以及自身的经济基础、政治倾向、文化追求和社会活动等均值得研究。
一 近代出版机构的兴起与编辑出版人的出现
我国近代出版机构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首先是西方传教士为传教需要在中国设立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不面向市场、不具备企业的性质,它们采用先进的技术,为近代出版企业的出现准备了技术和物质条件。其次是,洋务派和维新派设立了一批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机构,其崭新的出版方式对近代出版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1.教会出版机构
19世纪末,外国教会以及传教士大量从事西学书籍的编译和传播事业,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不少在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据统计,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就有17家基督教出版机构先后成立。[1]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墨海书馆、益智书会、上海同文书会、广学会及美华书馆等。除了图书出版机构,外国传教士还在中国设立了诸多报刊出版机构。在19世纪的40年代到90年代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0%。这些报刊的主编都是中国当时有名的传教士,如麦都恩、林乐知、傅兰雅、李提摩太、艾约瑟等。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出版机构并致力于译书办报,其直接目的是传教,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西学的作用。这些出版机构为近代中国的出版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培养了一些掌握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出版人才,为日后民营出版企业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官书局和译书官局的兴起
官书局是晚清地方官刻的重要代表。1863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金陵书局。随后,浙江书局、崇文书局、广雅书局、湖南书局等先后设立,在光绪年间形成了官书局刻书的繁荣局面。官书局虽然采用的是当时先进的机器印刷设备,但所刻书籍大部分是经史子集以及部分低廉的普及读物,其重心并没有转移到西学书籍的出版。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政府设立新式翻译馆(译书官局)翻译西书。进入20世纪后,译书官局主要从事新式教科书的翻译出版,以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
3.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兴起
随着西方先进技术的输入和新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中国相继产生了一批新式出版企业。1872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馆,并于1879年设立点石斋石印书局,这是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出版企业。1882年,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这是中国人集资创办的第一家民营出版企业。此后出现的中西五彩书局、积石书局、鸿宝斋书局等都是初具企业性质的民营书局。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标志着近代民营出版企业的诞生。随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新式出版企业纷纷创办。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在后来的教育变革和文化创新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以上近代出版机构聚集了当时中国大批出版业精英,形成了近代出版史上特殊的编辑出版人群体。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处于大变革时代的近代中国出版业迈开了近代化转型的步伐。翻阅历史,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编辑出版人群体和个体所遭遇的时代风暴和创造历史的空前机遇,可以体会他们在拼搏与奋斗过程中跳动的脉搏。然而,学术界对于编辑出版人进行研究的专著和文章均不多。现有的出版通史对近代编辑出版人也只是一笔带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试图将近代编辑出版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近代新兴职业视角下,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学交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全面分析。
二 我国近代编辑出版人的类型分析与社会文化源流追溯
我国近代编辑出版人的类型非常复杂,这是由近代社会大变革、大变动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古代出版的主体基本限定在政府机构、有学问且有经济实力的读书人、追求利润的商人、寺庙中的出家人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出版业中官刻、坊刻、私刻和寺庙刻书的出版格局被打破,新的出版机构迅速兴起,新的出版主体突破了古代出版的小圈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和丰富性。
1.传教机构的学徒成为出版人
近代传教士兴办的出版机构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出版技术,也为我国的民营出版业输送了许多人才。王韬早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协助英国传教士麦都恩翻译西方经典,并在香港英华书院翻译中国经典书籍。后来,王韬相继创办了香港中华商务总局和韬园书局,成为近代出版史上的重要人物。商务印书馆的四位创办人夏瑞芳、高凤池、鲍威恩和鲍威昌均有基督教背景,都曾经到美华书馆学习印刷技术。夏瑞芳和鲍威恩后来还在上海的《捷报》做过排版工人,因不愿忍受西人歧视,便自立门户创立了商务印书馆。
2.旧式文人投身编辑出版行业
在近代,旧式文人通过互相招揽和引介广泛投身出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张元济经夏瑞芳推荐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之后,又招揽了蒋维乔、邝福灼、恽铁樵等进入编译所。大量的旧式文人进入出版行业,或办报办刊,或既为作者亦是出版人。这种趋势与清末废除科举制关系甚大。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制度。这就逼迫旧式文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求新出路。当时,旧式文人或弃文从商,或求诸新学,或进入新政权,或投身军界。令人欣慰的是,新学的发展催生出许多新的职业,例如翻译、大学教师、记者、编辑、出版人等。这为旧式文人提供了新的舞台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其中有很多人都投身出版业,壮大了近代编辑出版人队伍。
3.教师加入编辑群体
在近代,大学教师成为出版机构的编辑非常普遍,商务印书馆在改良编译所时就曾招揽到许多知名学者。这些学者大多都是当时著名大学的教师:朱经农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段育华曾留美专攻政算学,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胡明复、杨杏佛、秉志则是上海、南京两地著名大学的教授。
4.大学生和归国留学生加入编辑队伍
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与学生结盟,吸收了不少精英分子。至王云五主持商务工作时,更是刻意与大学生建立关系。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年轻人中成长起来新一代编辑出版人。据研究资料显示,五四之后全国产生了新型图书报刊编辑几千人,这些人在编辑出版实践中完成了由旧式书贾雇佣者向主体性编辑家的代际过渡。[2]
另一支不可忽视的群体是归国留学生。近代国人海外留学始于1873年,随着清政府的提倡和支持,至清末科举被废除时,自费或官费留学已成一种热潮。当时国人主要的留学国家有日本、英国、美国等。留学生回国以后若要以学术或文化谋生,加入出版行业是不错的选择。当时比较大的书局都吸收了大量归国留学生。其中商务印书馆是吸纳留学生最多的出版机构。据周越然统计,“从1897年到1930年,商务编译所一共进用了海外留学生75人,其中留法者2人,留英者3人,留美者18人,留日者49人。若以编译所的人数为300人计算,留学生的比例约为25%”,[3]“外国留学生加入商务,其工资及条件,小如书桌与书架的尺寸大小,都比国内大学的毕业生有较佳的待遇”[4]。
三 近代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生涯
1.职业认同感
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使编辑出版日益成为一种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职业。知识分子选择并投身出版本身就是对近代出版业的职业认同,其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就是——出版业即是知识分子谋生的归宿,也是实现其理想的平台。知识分子凭借职业化形成了出版业的近代知识群体,成为近代出版的主角。他们有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他们与同样职业化的商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从事营利的出版业,而在于能不能依循文化理想和学术传统对于社会人生尽一种道义”[5]。正是这种共同的理想和职业的认同,使近代的知识分子聚合成为庞大的编辑出版人群体。
2.职业理念
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理念关系到出版业的发展方向。近代中国出版人的职业理念受到西方“出版自由”等思想的影响,他们或出版图书或创办报刊发表主张,利用新文化、新思潮启蒙民众。梁启超强调办报是为了“立言”,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新民”。他主张报纸应多刊载那些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探求救亡图强之道、唤醒民众、教育民众的文章。[6]张元济的编辑宗旨为“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应我国国情的教科书。此外,章士钊、章太炎等通过革命报刊都确立了“反清和民权”的编辑理念。邵飘萍、戈公振等人以“公益事业和商业”为编辑理念,认为报业是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的社会服务性行业,以“公益”为目的,报业是“社会的耳目”、“国家的口舌”。在这些编辑理念的指引下,近代报业向企业化、现代化迈进,出现了一大批民营大报,如《商报》、《申报》、《时报》、《大公报》等。
3.职业生活
中国古代的出版,无论是官刻、私刻、坊刻还是寺庙刻书,都不存在后来称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内涵,[7]这与近代和当代的出版有很大差别。近代编辑出版人的职能是中介性的,不管是埋头于书案还是忙于日常事物,都是为图书的出版提供服务。在近代有名的书局中,出版人和编辑的工作也有区别,出版人的角色类似于书局的公关角色,不但要与社会各界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还要负责馆内的日常事物,如人才引进、日常管理等,而审稿读书的时间和普通编辑人员相比可能会少一些。张元济的日记记录了他所做的事情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确定选题计划;对编译的图书进行甄选;约请有专长的学者编书或译书;与专家学者商讨编译方法,订立编译合约;与有关编译人员研究确定出版物体例。张元济除了做大量的书稿加工校对工作外,还为所编的书籍做附件和索引。作为编译所的负责人,他还得考虑纸张的选择和订购,确定稿酬标准以及成本核算等。
当时普通编辑的日常工作也非常繁忙。一位当年在《大众生活》周刊工作的编辑记录了他每天的工作:在韬奋的领导下,每天至少和韬奋联系编辑业务;列席编辑委员会并做记录;向有关作者约稿和取稿;在韬奋审定后集中稿件,制订版样;把全部稿件送印刷厂进行初校,二校以至签字付印;每星期五下午到印刷厂取出样本,送请韬奋审阅。此外,还有拆阅和处理读者来信……[8]
四 近代编辑出版人的社会价值
1.政治运动的参与者
近代出版是时代政治的感应器。在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都可以从出版活动中找到踪迹。林则徐和魏源率先出版《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使国人第一次了解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此后,自强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翻译出版成为一种图强的政治活动。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论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立言”的新形势。严复等人的译介活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一大批具有先进意识的编辑出版人,以《新青年》等书报刊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实现“救国救民”的政治愿望。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中,出版界实际上是新思想的直接策源地,出版者和作者密切结合,成为思想启蒙和思想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先锋。近代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先进的编辑出版工作者对社会政治的发展的确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出版行业发展的推动者
从历史视角考量,我们不能否认近代出版业的发展速度的确很快。这其中有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的刺激因素,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近代编辑出版人的艰苦付出和不懈奋斗。首先,近代出版业对纸张的需求量猛增,带动了国内的造纸行业。其次,在近代编辑出版人的不断学习和努力下,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全面推进,使民营出版企业的资本急剧扩张。商务印书馆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后很快成为亚洲最大的出版企业。中华书局1912年以2.5万元开张,因出版发行教科书获得丰厚利润,仅仅几年就成为经营八大杂志、兼备多种实业、拥有数千员工的大型企业。稍后成立的大东书局和世界书局也各有2000人的规模。当时的出版企业多数为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还可以上市买卖。[9]
3.国民阅读习惯的引导者
由于近代编辑出版人的努力,阅读书报刊成为中国人一种新的生活习惯,报刊书籍的需求量激增,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近代都市文化现象的普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报刊在青年学生中的流行大大促进了国民阅读习惯的形成。出版机构为了进一步发展自然要顺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引导和创造新的阅读方向和潮流,此时的编辑出版人又充当了国民阅读习惯的引导者。
4.教育改革的倡导者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改变。当时的有识之士已深刻意识到改革传统教育的必要性。王韬、薛福成等编辑出版人都是呼吁教育改革的先行者。至维新变法时,振兴教育已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和近代编辑出版人的普遍呼声。张元济等近代编辑出版人通过主办教育类杂志、开办教育机构、出版平民教育用书、大量编写近代教科书等,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对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儿童启蒙教育的推动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