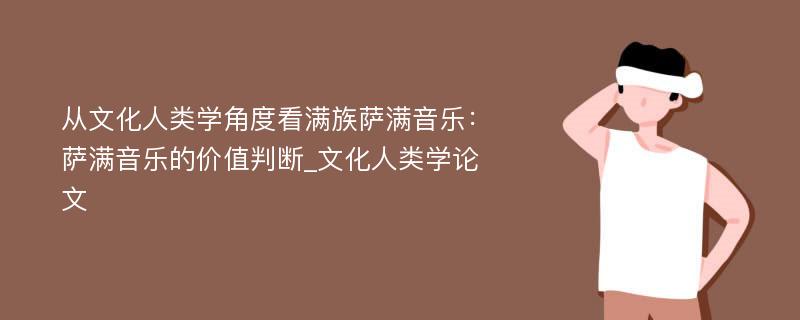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满族萨满音乐——对萨满音乐的价值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萨满论文,人类学论文,音乐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种种原因所致,长期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及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探究远远落后于对周围生存环境的认识。直至19世纪中叶,当人类学在欧洲逐渐发展形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这种令人尴尬的状况才得以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这一学科领域的扩展,人类学被划分为四大分支,即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三个分支: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①a]其中,文化人类学的形成,通常是以美国考古学家W·H·霍姆斯于1901年创立的“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专称为标志,其基本指向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过程,分析比较各民族、各部落、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区文化的异同,探讨和发现人类文化之一般和特殊规律”。[②a]可以看出,文化人类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对人类整个历史时期遍及全球的各种不同社会文化形态都有所触及。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它的侧重点一直在原始民族(包括史前)社会文化方面,并由此形成了诸如进化论、播化论、功能论、结构论、历史学派、心理学派和生态学等理论流派。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正愈来愈广泛地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领域。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将对中国满族萨满音乐的探讨置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之内,以期能使这种研究建构在一种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使萨满音乐恒久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更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得以显现。
一、萨满音乐的源流
在中国北方民族音乐奔涌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汇聚着一股来自远古时期的音乐支流——满族萨满音乐,即便在现代音乐文化广泛传播、覆盖的今天,它仍然带着古朴、神秘的色彩,默默地流淌在广袤的北方田野之中,成为人类原始音乐文化的“活化石”。
借助史料和民间传说,以及对满族现存的祭祀活动的考察,不难寻觅到萨满音乐的原始踪迹。萨满音乐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人类早期音乐形态,在满族的创世神话中就已显露,至今流传在嫩江、黑龙江两岸满族村屯的最古老的神话《尼珊萨满传》中,即可窥探一斑,故事中的尼珊萨满为求助神灵助她渡河,唱起“埃库勒叶库勒”神歌,然后将手鼓投入河中,站在鼓上过了河[③a]。另外,在满族民间故事《手鼓的传说》中,也详细地叙述了手鼓的来历。这表明,“神歌”和“神鼓”作为满族萨满原始文化的载体,很早就已确立了它们的地位。
在有满族萨满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神本子中,记载有关“神鼓”、“神歌”诞生的传说,对于探讨萨满音乐的源流也有着十分重要的考证意义,以下,是吉林珲春地区满族瓜尔佳氏的神本子中的一段描绘:
“本姓瓜尔佳哈拉,敬祝赫赫瞒尼,她是由阿布卡赫赫身上搓下来的泥所变的。赫赫瞒尼摘下一片青天作鼓,拿起一座高山作鼓鞭,当青天和岩石撞击的时候,从那震天动地的咚咚的鼓声中,生出了男人,女人和宇宙万物,从此,世上留下了吉祥幸福,驱走了邪恶”[①b]其中提到的阿布卡赫赫,就是生育出整个宇宙的满族创世女神,她“不仅是伟大的创始神,人类的始母神,而且是建立巨勋的文化英雄神,她用柳枝把人类和其他生灵从洪水中拯救出来,并教会人类唱乌春(神歌)和各种技艺。她派尼珊做世上第一个女萨满,斗邪恶,救苦难,传下了神鼓和萨满教,是人类的守护神”[②b]以上的传说,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判断:其一,在满族创世的同时,音乐艺术也由此而生了;其二,神鼓和神歌是满族祖先最初创造的乐器和音乐形式,这种创造直接反映出人类艺术创造思维的某些原始特征。
作为旁证,根据前苏联的考古发掘,在西伯利亚地区保留下来的属于公元前四千年到两千年的原始岩画中,分离出许多表现萨满艺术活动的图案,其中,有的人物手中握着成空心圆状的物体而被认为是萨满神鼓,[③b],这些岩画的内容与形式均与满族文化处于同一体系。它展示了满——通古斯部族的遥远的古代就已进入实践的艺术思维形式。
此外,本世纪60年代在黑龙江流域考古发掘中确认的辽代五国部女真人的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一些女真人用以娱神的“腰铃”,这一发现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萨满神器之一。[④b]
随着满族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生产生活内容逐渐趋向稳定,原来那些带有偶发性、多发性特点的祭祀活动,在民间已形成“特有的自上而下的典范化了的传说”。[⑤b]到了金代,女真社会萨满中盛行的祈祀、巫术等通神行为甚至被规范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的一部分。有关萨满的准确记载这时也已正式见诸文献之中。
明代后期,当氏族社会逐步向封建专制社会过渡,女真社会开始出现急剧的震荡和变化,与此同时,藏传喇嘛教在民族统治者的强制推行下,大举传播,对萨满的生存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时,也改变了萨满文化的传播途径和环境。清之后,除了在偏远的山野林莽间还保留着那种古老原始的野祭外,在民间盛行的则大多是经过改头换面,被简化了的家祭,这种变化,无疑也使萨满音乐的风格发生一些变化。关于清代东北地区满族民间的萨满跳神活动,清人何秋涛曾作过生动的记述:
“降神之巫日萨麻,帽如兜鍪,缘檐垂五色缯条,长蔽面,缯外悬二小镜,如两目状,著绛布裙,鼓声阗然,应节而舞,其法之最异者,能舞马于室,飞镜驱崇,又能以镜治疾,遍体摩之,遇病则陷肉不可拨,一振荡之,骨节皆鸣,而病去矣。”[⑥b]
类似的描述在《奉天通志》、《吉林通志》、《黑龙江志稿》等一些东北地方志中,多处可见。在这些有关跳神场面的详细记录中,仍保留一些原始宗教色彩较浓厚的野祭样式,其中,神歌和神鼓仍作为重要的音乐载体。值得注意的是,神歌的演唱在家祭中已出现“一领众合”的形式,这也是萨满跳神时,为了吸引观众参与,共同营造表演氛围而采取的一种作法。
在东北古代曾兴盛过的几种音乐,如高句丽乐、渤海乐、女真乐等,有的随着地方政权的更叠已不复存在了,随着民族经济、文化的融合已发生很大的变异,与本来面目相去甚远,而唯有满族萨满音乐,至今仍以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和古朴的韵味,顽强地传播在北方的山乡僻壤之间。
二、萨满音乐的构成要素
满族萨满音乐在文化传承上保持着的这种相对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一方面是与满族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文化根本密切相关,另方面是由萨满音乐的独特存在方式、表现功能、传播途径以及音乐结构形态所决定的。
满族萨满音乐的构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音乐表现工具
在萨满的观念中,对于在跳神活动中应用最广泛的神鼓和腰铃,并不具有乐器的含义,而只是人们所说的神器、法器或礼器。按照现代乐器分类方法,神鼓和腰铃则分别归属于膜鸣乐器和体鸣乐器。此外萨满经常使用的神器还有抬鼓、晃铃、扎板、神镜、哈马刀等,其中,有的神器按照发声机制、形制、以及使用功能严格地划分,很难划入乐器类。
从一些乐器的形制和制作材料上看,以及通过一些满族民间传说中的记载,可以判断,神鼓的历史最为久远,而腰铃、晃铃等一些金属制乐器,最早也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掌握冶炼技术之后。能够看出,萨满使用的乐器基本是以体鸣乐器和膜鸣乐器为主。这些乐器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又一代萨满文化交流传入北方的一些弦鸣乐器、气鸣乐器,尽管音色多变、技巧丰富,但已很难再进入萨满的祭祀仪式以至观念当中了。有些弦鸣乐器后来尽管在清宫萨满祭祀活动中出现,但已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
2、音乐表现形态
如果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剖析现存的满族萨满音乐,它所具有的人类早期音乐特征是极其明显的。神歌的音域一般较窄,旋律平直,多以同度、二度、三度、四度音程构成。有的神歌甚至只用了两三个音,如被认为是满族民间“原生腔”的神歌《念杆子调》,只用了宫、商、徵三个音,全曲通篇几乎完全是在调式主音宫音上进行的。[①c]从满语研究的角度,这种近乎于念白的旋律特征,被认为是“受满语语音谐合规律”所制约(满语无四声)。按照旋律生成、演化的规律,这种缺少小二度、大小六七度及增减变化音程的旋律形态,正是音乐欠发达的标志。此外,萨满神歌中大量的类似数板式的说唱体和“一曲多词”的形式,也足以表明,萨满神歌尚未完全脱离语言的胚基而进入独立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求得曲调方面的变化,萨满们在演唱神歌时,往往采取运用各种装饰音的手段来润色和喧染旋律,以此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
笔者认为,造成神歌旋律缺少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神鼓在萨满祭祀活动中的意象作用,而使节奏(鼓点)占居主导地位,这也是人类原始音乐构成特征之一,由此,对于萨满音乐的研究,尤应重视节奏的形态和作用。从目前探知的一些具有规律的节奏原型,如老三点、老五点、快五点、正七点、花七点等节奏型来看,其组合运动形式完全是以满族语言的“音节规律”和人体的律动周期规律作为发展基础的,其中也蕴含着满族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形成的独特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趋向。这里,有一点需要特殊强调的是,即对于尚不十分发达的音乐形态进行分析时,应拓展节奏的概念内涵。萨满音乐中的节奏的含义绝不仅仅是“将长短相同或不同的音,按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这样一种概念,[①d]至少还应包括重音的变化以及各音之间的疏密关系,人们常说的“轻重缓急”,即为是也。
3、音乐表演形式
与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原始音乐存在方式,表演形式相类似,满族萨满音乐的表演形式也带有一种综合性艺术表演的特点。所不同的是,由于萨满的艺术表演一直贯穿于整个祭祀活动当中,大量神辞溶于其中,从而形成“歌、舞、乐、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形式。匈牙利学者迪欧塞吉曾作过形象的概括:“萨满是一个演员、一个舞蹈家、一个歌手和一个整体管弦乐队”。[②d]其中就包括了词、舞、歌、乐四个方面的表演技能。
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演进,作为萨满文化框架的祭典程式逐渐定型,无论是野祭(俗称“放大神”),还是家祭(俗称“跳家神”),都已形成严密规范的表演程序,在这其中,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并不具备独立的存在意义,而只是一种物化了的祭祀内容。所以脱离这种艺术模式,对其中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进行单独的分析的研究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进行必要的比较和说明,在这里以与北方萨满文化处于同一历史层面上的我国南方盛行的傩文化为例,作以类比。作为傩文化的主要外化形式傩乐,其表演内容和形式都是在傩事活动的固定框架请神——酬神——送神过程中体现的,“跳、唱、念、做”是傩乐的主要表现形式,与萨满表演中的“歌、舞、乐、词”是对应一致的。这种“多职能的混融性文化现象”,构成了原始时期的“仪礼之俗、礼乐之风”[③d]。
如对萨满音乐的构成作进一步的探讨,必然要涉及萨满的音乐观,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微妙的问题,尽管在萨满的头脑中没有形成明确独立的音乐观念,但不能由此而否认音乐在萨满世界中的存在,只不过是在萨满的语言中没有“音乐”这个词汇而已。通常,人们将神歌、神鼓仅看作是体现萨满个人意志、个人信仰、个人情感的行为和表现工具,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在欧洲有一本很有影响,很有价值的音乐著作《音乐的四万年》,当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对原始人来说,音乐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力量。通过音乐,世界才被创造出来。……在原始人看来,音乐是人所能获得的唯一的一点神赐的本质,使他们能通过音乐去规定礼仪的方式而把自己和神联在一起,并通过音乐去控制各种神灵。”[④d]在萨满祭祀活动中,“神器的介入,使虚幻的精神信仰有了实实在在的寄托对象,制造了人神杂处,相互交往的一个宗教环境,身置其中,神入其境”。[⑤d]
在萨满看来,神器有一定的暗示作用,从各种器具奏出的音响中,可判断是什么神降临。此外,神器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一些萨满的神鼓鼓面上常绘有云、鸟、虎、蛇、海涛、树、日、月等自然景象和动物图案,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宇宙世界。在萨满观念中,“鼓代表云涛,灵魂坐神鼓飞天入地,所以萨满神鼓一敲,即台翔天飞舞。”[⑥d]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曾传流一部满族先世女真时期的著名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其中有一段描述乌布西奔因神授而成为盛名再世的大萨满的内容:
“轰勿(晃铃)响了,腰铃响了,神鼓响了,众萨满焚香,叩拜东海,只见从江心水上走来了一鸣惊人的哑女。她用海豚皮做了一面椭圆鸭蛋鼓,敲起疾点象万马奔驰……神鼓轻轻飘起,像鹅毛飞上天际。在众族人头上盘旋一周,忽悠悠落在乌林毕拉河面之上……‘我为乌布逊部落安宁而来人世,你们就叫我乌布西奔萨满吧!’从此,东海响彻新的征号,——乌布西奔萨满大名历世传流”。[①e]
乌布西奔相传是当时女真部落中一位“神威无敌、盛名盖世”的大萨满。
这段描述,形象地揭示出神鼓在萨满世界中的意象作用,从中也可窥测出早期萨满使用的乐器的种类和形制。在满族萨满经常使用的其他几种乐器中,“通肯”(抬鼓)声音宏大、粗犷,它象征着宏伟壮阔的山峦、江河、大浪波涛。而“西沙”(腰铃)的撞击声,意味着萨满进入宇宙世界,身边风雷交鸣,行途遥远广阔,有时它又代表神行走时震动的声音。还有“轰勿”(晃铃)则代表魂魄精灵,它那清脆迷离的声响,烘托出自然界中的各种神秘气氛,也象征着神灵的踪迹。[②e]
萨满的神器在充当各种角色的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娱乐作用,一些萨满在挥弄神器时的出色技能表演和着意创造出的娱乐氛围,也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在人类学家看来,“音乐往往与故事一样地表达出该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所关心的事物”,而且,“无论是从技艺还是从完全为表演娱乐的意义上看,音乐都是可以培养而且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一种个人创造技艺;它也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通过音乐,人们可以互相交流或分享情感和生活经验”。[③e]以上对于满族萨满原始音乐形态特征的客观分析,以及对于萨满音乐观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从萨满本体文化上去判断其价值,否则,容易造成音乐价值观方面的错位,尤其是当研究主体与客体在音乐概念方面,表现出巨大的理论认识差距时。
三、萨满音乐的发生机制
对萨满音乐发生机制的探讨,自然会触及艺术起源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艺术的起源提出过许多理论设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也包括艺术起源于巫术说,艺术起源于图腾说,以及艺术起源于萨满信仰说,等等。尽管它们单独都无法科学地阐释艺术的发生机制,但至少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细节材料和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分析。
按照通常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途径,一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史前的艺术遗迹的研究;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现代残存的原始部族的艺术模式进行研究;三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在儿童艺术心理学方面进行研究。对萨满音乐研究而言,从第二条途径切入最容易接近实质。19世纪上半叶,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问世后,进化论的理论对艺术起源的探讨产生巨大的影响,从19世纪的最后30年出现的大量论述有关艺术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论文和专著看,当时许多人类学家都非常重视人类文化的初始阶段与原始艺术的联系,“人们希望从那些简单而又难解的神秘符号中去追寻出人类审美意识的最早起源以及隐藏在符号后面的艺术推动力。”[④e]
在我国北方满族、达斡尔族中广泛流传的著名长篇叙事诗《尼珊萨满》中,就有描绘萨满显灵时,隐含在其中的音乐发生过程。
“为了帮助英勇的猎手包尔古迪·费扬古复生,女萨满尼珊与一名助手男萨满穿起8种法器装饰的神衣,头戴神帽,围上神裙,拿起神鼓、鼓槌,开始祷告,唱起祝词。随着鼓点,一一从天上请下她的护法神灵。然后她对助手说要到黑暗处追回死者的灵魂;到恶魔处去索回死者的生命;到阴间去讨回死者。说完尼珊便敲起鼓,跳起来。跳到最激烈的时候,她昏迷过去。这时,她的真魂便带领她招来的神灵,直奔阴间,经过许多周折,最后要到了死者的灵魂和生命,当她带领死者的灵魂与生命回到家中,躺在地上的尼珊萨满立刻摇动了神衣上的铜铃,全身抖动,并跃身而起,敲起神鼓,跳起舞,唱起神歌,宣告死者复活”[①f]。
这个传说与现实中的萨满附身、显灵的过程完全一致。在这个过程中,击鼓声、歌唱声对萨满进入忘我恍惚的昏迷状态,显然起了一定的刺激和诱导作用,而苏醒后的萨满又获得了新的音乐创造能力。按照“萨满”的母语,鄂温克语的本意,它指“激奋者”、“癫狂者”,这正是萨满最突出的外部特征。萨满在与神灵沟通时,口诵咒语、吟唱神歌、手击神鼓、跃跃起舞,在宏亮的歌声和激越的鼓声诱发下,进入一种如痴如狂的状态,各种臆想,也包括艺术创作的冲动和灵感由此而产生出来。一位前苏联的学者曾说过:“可以充任萨满者,往往是那些神经质的。易于激奋的人”[②f]。无庸讳言,萨满的这种神经类型与一些从事音乐表演和艺术创作的人所具备的潜在性格有许多相近之处。
实际上,萨满的艺术创造能力作为一种个体行为,是在外部的某种因素激发下产生的,但这并不能排除,萨满本人先天具备的艺术素质及萨满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根基对萨满的艺术塑造。对于这种文化方面的依存关系,文化人类学家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其中,以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和L·罗伯特提出的“文化模式”的观点最有影响,对我们全面认识萨满音乐的产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文化模式”(Culture Pattern)通行的界定是:文化内部特征的协调一致的组合状态,是文化诸要素组合的内在形式结构。它更“注重地域、民族、部落文化的内部整合状态,尤其着力捕捉其集体无意识的东西,更能抓住各个文化或文明的本质”。[③f]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特别提出要把不同行为领域中的习俗联系起来看,反对分离的个别研究。在她看来,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对于个体行为来说,塑造着不同的行为类型。[④f]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本尼迪克特选择了印第安人中的萨满术士作为人类文化形态的“反常”的例子,她注意到,“在原始部落中间,阴魂附体和僵直症都极享美誉”。并由此认为,在任何形态的社会当中,“社会和个体二者并不是对抗的东西。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人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文明的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最丰富的音乐感受力也只有这种感受力所生于其间的传统的资质和水准中才能表现出来。也许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只有传统,而不是传统所成就的东西,才和文化所提供的乐器和乐理保持着一种相称。”[⑤f]
对于这一观点的认同,至少不致于使我们将满族萨满音乐视为超越满族传统文化之外的一种令人捉摸不定、非稳定的文化形态。在满族社会中,萨满现象确属少数人的一种个体行为,但萨满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变形延伸,它所包容的一切又都来自于滋润它的生活和文化。
四、萨满音乐的本质
根据目前各国人类学家对人类原始文化的生成、进化规律的全方位研究,以及满族萨满文化自身所包含的人类原始文化的某些特征,对于寓于萨满文化中的音乐艺术,是否可视为,它是满族先民在认识自然、开拓自然、征服自然的漫长艰辛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原始艺术思维产物,它的外化形式为歌、舞、乐、词,其本质“名为娱神,实则娱人”[①g]对于这一结论的内涵,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也有过相近的阐释:“在考察不发达民族中间那些包含了对于自然界中无处不有的神灵的信仰的集体表象时,在考察那些作为与神灵联系着的风俗之基础的表象时,不能产生这样的印象,即这些风俗是理性求知欲在其对原因的探索中的产物。神话、葬礼仪式、土地崇拜仪式、感应巫术不象是为了合理解释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是原始人对集体需要、对集体情感的回答,在他们那里、这些需要和情感要比上述的合理解释的需要威严得多、强大得多、深刻得多”。[②g]当我们把满族萨满音乐放在满族原始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放到当时的社会关系及社会互动形式中去考察,可以看到,萨满音乐的存在,完全是满族先民为满足个人或集体的情感需要,所创造的一种特殊风格的艺术形式。其中,凝聚了满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心理素质、审美观念、文化价值取向及生生不灭的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通过对满族萨满音乐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取它的价值:1、在寻找人类艺术起源途径方面;2、在认识人类原始艺术思维形式方面;3、在建立人类原始音乐模式方面;4、在发现人类音乐演化规律方面;5、在探讨满族民族审美观念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无限拓展,一方面萨满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不断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濒临消失,另一方面,萨满文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它所反映出的“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又使它充满了无穷的魅力。我们深信,满族萨满音乐作为人类“原始文化的遗存”,它的自身价值交替地伴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而不断地升值。
注释:
①a [美]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铭铭等译,第9页。
②a 林嘉煌:《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载陈国强等著《建设中国人类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7页。
③a 见《东北艺术史·音乐》。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①b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②b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③b [俄]E·A·奥克拉德尼科娃:《西伯利亚的萨满岩画》。载《萨满教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④b⑤b 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第47页。
⑥b 参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5,清朝咸丰刻本。
①c 参见李玉珍:《浅谈满族萨满音乐》。戴《乐府新声》1994年增刊。
①d 指目前通行的乐理书中对“节奏”所下的定义。
②d 石光伟、刘厚生:《满族萨满跳神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③d 柯琳:《傩文化刍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71页。
④d 柴勒:《音乐的四万年》。伦敦1964年版,第54页。
⑤⑥d 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151页。
①e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②e 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e 同上,第545页。
④e 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①f 乌丙安《审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8页。
②f 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③f 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④f L·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页。
⑤f 同上,第231页。
①g 石光伟:《满族烧香萨满跳神音乐》。载《中国音乐》1989年第3期。
②g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5版,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