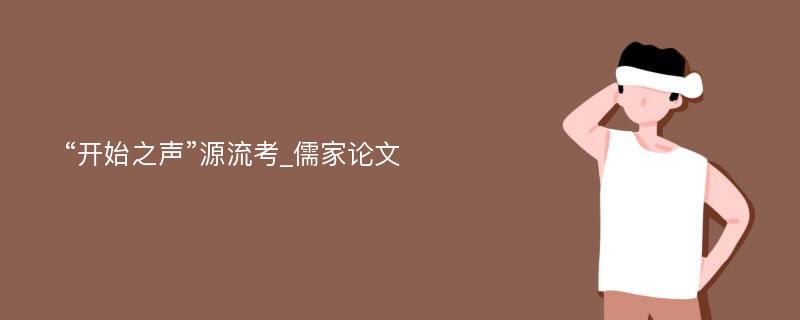
“正始之音”渊源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始之音论文,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始”指三国时期魏国齐王曹芳在位时使用的第一个年号(240—249年),共十年①,这个时期是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明争暗斗之期,思想文化呈现波诡云谲之状况,出现了王弼、何晏、夏侯玄等玄学人物与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等人物,与相隔一代的建安文学相邻。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素以清幽玄远、风采独具构成中国文化史的独特风景,后人往往用“正始之音”来称呼。②而围绕着“正始之音”的评价之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主要集中在能否用它来指称文学,抑或专指正始玄学。 本文认为,“正始之音”是诞生于三国时魏国中期至后期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以远大遥深、兴寄幽缈、思致与抒情相结合为特点,涵盖玄学思辨与诗文创作,彰显出正始士人的精神追求与心灵境界。因此,要揭示这种精神文化特质,除了从概念上进行辨析外,还须进行综合的研究,要找到正确的途径,即要从士人主体入手,结合时代来分析其成因。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缺乏对“正始之音”进行历史溯源与总体把握,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正始之音”与先秦思想 “正始之音”作为魏晋时代出现的特定思想文化思潮,融文学与哲学为一体,其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始于先秦思想文化。先秦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年代,中国文化的早熟在先秦时代表现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深刻思考。“正始之音”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是人生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这一点在以先秦诸子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中可以找到源头。其中最主要的有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以及战国时代的屈骚精神,这诸种思想文化的有机融合,构成了“正始之音”的基本来源。 (一)“正始之音”以儒家思想为底蕴 以往研究“正始之音”的论著,大都强调老庄与玄学对于“正始之音”的泽溉,这其实是表面的看法。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段话大体上指出了儒家的出身与后来的变故,儒家思想以人格建设为底蕴,延及社会人生。两汉儒学过分强调政教功能,知识分子将其作为博取功名的器物,原始儒学逐渐失去灵魂。 汉魏以来,随着政治的变故与社会动荡,原始儒学的一些精髓反倒彰显出来,正如孔子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在动荡的年月中,人格精神的坚贞是支撑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在“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的人生经历与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儒家人格精神的底蕴。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深刻地分析道,阮籍这样的名士“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1](P513)。阮籍曾作《孔子诔》,称颂孔子:“养徒三千,升堂七十。潜神演思,因史作书。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2](P195)阮籍受父辈影响,早年饱读六艺经书,追求建功立业,《咏怀诗》中自叙:“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3](P265—266)这明显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转变经历。问题在于,阮籍服膺老庄之后,是否与儒家思想诀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阮籍一直与司马氏集团虚与周旋,他内心的痛苦始终没有泯灭。理想与现实的纠结,构成了他一生的矛盾与思想的特点。如果没有儒家思想的支持,那么他可能会变成郭象那样油滑混世的人物。南朝颜之推在《五君咏》中曾叹:“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可谓道出了阮籍始终无法摆脱的内心痛苦。 嵇康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本家世儒学。《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引其兄嵇喜的《嵇康传》:“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臧荣绪《晋书》亦称嵇康“幼有奇才,博览无所不见”。对于嵇喜所言“家世儒学”这一背景有必要加以强调,嵇康早期的家庭教育中应该有儒学教育的基础。其父嵇昭曾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晋书·职官志》记载,汉魏以来治书侍御史之职“掌律令”,即掌管文牍律令者,嵇康之父应受过儒学教育。另外,从后来嵇康早期论说文中,如《释私论》、《明胆论》、《声无哀乐论》等引儒学经典来看,足以说明其“家世儒学”的可能性。嵇绍在《叙赵至》一文中曾记载嵇康在年轻时曾在洛阳太学中抄写古经。嵇康在因吕安事蒙冤下狱时,给儿子嵇绍所写的《家诫》中告诫儿子:“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4](P544)家诫中的这些高士与苏武,都是儒家气节的楷模,而不是老庄的信徒。嵇康最后视死如归,也是受儒家人格主义影响的结果。他的儿子嵇绍在西晋时成为忠臣烈士,在“八王之乱”的荡阴之战中,为保护晋惠帝而被乱兵杀死。西晋士人裴希声在《侍中嵇侯碑》中称颂他:“夫君亲之重,非名教之谓也。爱敬出于自然,而忠孝之道毕矣。朴散真离,背生徇利,礼法之兴,于斯为薄。悲夫!晋弋阳子嵇绍,字延祖,资干刚之纯粹,体中和之淑虚。少有清劭之风,长怀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掩济,靡才不经;学为儒宗,庶绩光被。”[5](P1649)称嵇绍是真正将儒学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忠孝君子。嵇康性格的刚肠嫉恶与尚奇任侠,既来自于老庄的任真自得,同时受到儒家思想的泽溉,这是不争的事实。嵇康的刚直峻切的性格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方式有关。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但这是他的自叙,并不代表事实的真相。 嵇康的另一位兄长是嵇喜。他与嵇康志向不同,留意仕途,以秀才身份从军,嵇康曾为他作《五言赠秀才诗》、《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劝其与自己一起过隐居的生活。嵇喜作《答嵇康诗四首》,其中出现了鼓吹老庄思想的诗句:“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时至忽蝉蜕,变化无常端。君子体变通,否泰非常理。”“达人与物化,无俗不可安。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原。”[6](P550)这些诗充满着放任情欲,及时用世的思想,与孔孟的人格主义绝不相通,也与弟弟嵇康的刚烈与执著迥异,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说:“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三国志·魏志·王粲传》中云:“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钟嵘《诗品》中云:“晋中散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钟嵘点明了嵇康诗文表现出“峻切”和“清远”这两个特点,其实从思想渊源来说,正是老庄与孔孟思想的互补,“峻切”来自于儒家,而“清远”则受道家影响。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评论:“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7](P53),也认识到了嵇康与阮籍思想的趣尚有所不同。 “正始之音”的另外一派玄学人物王弼、何晏与夏侯玄等,任职当权,以调和儒道为主要思维方式。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在他们看来,是可以互相调和的。《世说新语·文学》载:“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从王弼答裴徽语中,可见其融会儒道之用心。王弼将儒道融为一体,既维护了圣人的地位,又提高了道家经典,为玄学思想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比如《论语·泰伯》中记载:“子曰:大哉,尧之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孔子认为尧的品德展现了天的荡荡无私,宽怀为大的品德。这里用的是先秦时代常用的比德品评的方式,与老庄所说的天道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王弼从沟通与调和儒道的角度出发,解释曰:“荡荡,无形无名之称也。夫名所名者,生于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恶相须,而名分形焉。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安在?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8](P626)王弼正是巧妙地利用汉语的这一特点,将“荡荡”解说成没有具体规定、“无形无名之称”的精神人格,这正是儒道合一的人格境界。 儒学对于“正始之音”的浸润,集中体现在《周易》这本经书上。魏晋玄学以《老子》、《庄子》与《周易》三本书号称“三玄”。其中《周易》为兼综儒道的儒家六经之首。王弼的《周易注》是其玄学思想的重要文本,其兼综儒道的思维方式十分明显。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特别注意到了王弼《周易注》的范式成就:“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9](P328)指出王弼解《易》具有“要约明畅”之特点。在文辞风格上也简明扼要,自然清拔。为了建构解读经典的新型方式,王弼还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言之筌也。”[10](P609)王弼引用了庄子用鱼和筌、兔和蹄的关系,说明言与象、象与意的关系犹如捕捉鱼、兔时用的工具一般。只有忘象才能得意,忘卦才能得情,从而为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方法论。阮籍大约于正始年间作《通易论》,《通易论》旨在调和儒道玄,成为魏晋文学理论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哲学基础。魏晋南北朝的易学,从王弼到阮籍,主要会通儒道,重在哲理的建构上,在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构建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正始玄学的灵魂人物何晏的著述有《论语集解》、《老子道德论》以及《无为论》、《无名论》,其中《老子道德论》亡佚,《无为论》、《无名论》仅存残篇。正始六年(245年),何晏三十八岁,召集其他人物注释《论语》。《晋书》卷三三《郑冲传》记载:“初,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经典释文》曰:“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论语集解》体现出正始玄学以儒道为一体,兼容并包的思想特点,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华平在《论语集解校释》的前言中指出:“从政治上来看,何晏主持的《论语集解》,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儒道兼综,名教与自然统一的特点,这也是当时社会司马氏与曹魏两种政治势力的妥协所致。”[11](P4)从何晏的《论语集解》的形成中可以看出,正始玄学,调和儒道,对于传统的情性观进行了重释,当时的嵇康与阮籍的文艺理论观念的构建,无不体现出儒道合流的特点,从而推动了正始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创新。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批评:“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七五中评论:“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这显然是偏见。从何晏召集多人编注《论语集解》来看,他并没有“谓《六经》为圣人糟粕”。而是致力于兼综儒道。何晏虽然在《论语集解》中表现出援道入儒、以道释儒的思想,但《论语集解》的思想根本是崇儒的,因而《论语集解》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流传不废。清人钱大昕在《何晏论》中评论说:“予尝读其疏,以为有大儒之风。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长守位而无迁废之祸。此岂徒尚清谈者能知之而能乎……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宁既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顾诬以罪深桀纣,吾见其蔑儒,未见其崇儒也。论者又以王何好老庄,非儒者之学。二家之书具在,初未尝援儒以入庄老,于儒何损。且平叔之言曰: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于时变,若是其不足乎庄也,亦毋庸以罪平叔矣。”[12](P13)这可以说是中允的观点。 (二)“正始之音”深受老庄思想泽溉 老庄思想启发了“正始之音”中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对于两汉的官方思想进行大胆的怀疑与批判,冲破礼教中过于禁锢的地方,对于人的自然情性进行释放,可以说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纠正与补充。老庄思想对于“正始之音”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史上的启迪,另一个是诗文创作中的渗透。 这一点在嵇康身上尤其明显。鲁迅先生指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13](P511)嵇康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他在《幽愤诗》中感叹:“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晋书·嵇康传》记载:“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晋书·阮籍传》记载:“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可见,“正始之音”的重要人物将老庄作为心目中的偶像并非偶然。 关于专制与名教的批判,成为嵇康、阮籍继承老庄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他们采用老庄思想主要用于反对当时司马氏集团所操弄的名教之治与历代的专制政治,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并不代表对于传统儒学的摒弃。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评价:“嵇康的文化论,一句话说完,就是反礼乐,反名教,反教育,主观上要修正两汉博士的意识形态。而他所否定的,却是司马氏偷盗着以欺蒙天下人耳目的法宝,因此,客观上也具有政治的意味。”[14](P189)嵇康作有《太师箴》,其中抨击“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专制暴君。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反对小人的匿情作伪:“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衿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15](P402)《释私论》是嵇康探讨人生的代表作之一,《晋书·嵇康传》论曰:“盖其胸怀所寄”。此文致力于个体精神的超越,时至今日仍给我们以深省与启迪。《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指出了嵇康思想从前人那里汲取了老庄思想,用以强烈地反对专制与名教。 阮籍则创作有《达庄论》,提出崇尚自然的思想。阮籍还在《大人先生传》中批判:“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也。”阮籍约在此年作《通老论》,融合儒道:“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洽,保性命之和。”[16](P159)阮籍又作有《老子赞》:“阴阳不测,变化无伦。飘遥太素,归虚反真。”阮籍的融合儒道,表现出魏晋玄学与名士的思想旨趣,亦对于文艺理论批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他的《乐论》、《清思赋》等。 正始玄学受道家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王弼的《老子注》,它奠定了正始玄学的地位。在涉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时,王弼往往强调自然之道的根本作用。在《老子指略》中他提出:“夫素朴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隐,虽极圣明以察之,竭智虑以攻之,巧愈思精,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则乃智愚相欺,六亲相疑,朴散真离,事有其奸。盖舍本而攻末,虽极圣智,愈至斯灾,况术之下此者乎!”[17](P198)王弼将素朴之道与无为无造结合起来,强调背离了素朴之道,一味地运用巧思,只会适得其反,从而对于名教的作用进行了批评与否定。王弼在《老子指略》上文中还提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18](P198)王弼通过对于《老子》一书言简意赅的赞美,批评了两汉一些学者治学繁琐不得要领,从而倡导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客观上为人们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方法论。 何晏也擅长会通儒道。《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文章叙录》曰:“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又注引《魏氏春秋》曰:“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何晏不仅着有《论语集解》,而且着有《道》、《德》二论。今据《列子·天瑞》张湛注,保留有何晏《道论》曰:“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向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员。员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19](P10—11)这一理论旨在申论“无”是宗率有形之物的精神性概念,正是魏晋玄学贵无论的代表作,它奠定了魏晋文学理论批评以无为贵,追求精神之美的理念,以何晏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它显然比诸王弼更起到引领时流的作用,何晏也因这一学说而引起当时人的广泛争议。 “正始之音”受老庄影响的另一个方面,便是诗文创作领域的表现。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指出:“阮籍、嵇康的自然论的玄学思想是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发展而来的,典型地反映了正始之后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只有着眼于这种演变进行动态的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的特征。”[20](P149)“玄学宇宙论的提出,极大地提高了哲学的抽象思辨性,它影响各种精神领域,自然也有助于提高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思维水平,正始以后,笃信玄学的诗人著名者有阮籍和嵇康,他们受王弼何晏‘贵无’思想影响,以玄学眼光观察生活,指导创作。”[21](P299)当然,正始诗歌中的哲理还不是如玄言诗那样单纯地以玄理的阐发为中心,而是借鉴了玄学中的思辨精神。罗宗强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认为:“嵇康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22](P85) 不仅如此,玄学领袖人物何晏的名作《景福殿赋》也彰显出道家思想。此赋是魏明帝曹叡于太和六年景福殿修造完成后所作,《文选》李善注引《典略》记载:“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景福殿赋》是一篇京都大赋,主要内容是描写都城之壮丽宫殿之华美,何晏在《景福殿赋》中引入了道家思想的成分,如开篇论“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上则崇稽古之弘道,下则阐长世之善经。”[23](P172)《景福殿赋》以虞舜无为之治作为帝王的榜样,“故淡泊而无所思,历列辟而论功”,含有隐喻与讽谏的意味在内。当时明帝连年修建豪华宫殿,劳民伤财,引起大臣的上书劝谏,何晏此赋表面歌颂宫殿,实际在谲谏帝王,而其中的思想来源则是儒家与道家的思想。 (三)“正始之音”彰显屈骚精神火花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最后赞道:“屈平行正,以事怀王。瑾瑜比洁,日月争光。忠而见放,谗者益章。赋骚见志,怀沙自伤。百年之后,空悲吊湘。”屈骚精神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黑暗年代中的精神意志与审美理想的结合,彰显了个体人格,它与庄子思想是相通的,都代表了在特定年代中士人的理想人格与审美境界的融合。嵇康诗文中,这种屈骚精神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卜疑》便是代表作品。《卜疑》是模拟屈原《卜居》的一篇辞赋。嵇康的《卜疑》从结构上模拟《卜居》,开篇虚拟了宏达先生,是嵇康自身的写照:“有宏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24](P235—236)这位宏达先生显然是一位得道之士。然而时代黑暗,“大道既隐,智巧滋繁。世俗胶加,人情万端。利之所在,若鸟之追鸾。富为积蠹,贵为聚怨。动者多累,静者鲜患。”这个时代让嵇康产生了困惑,他以一个道德极其高尚的“宏达先生”,在“大道既隐,智巧滋繁”的时代,感到无比的失望、怀疑,他不知如何前进,乃求见“太史贞父”求卜疑问,全文只一问一答,他所问的就是嵇康面临如何抉择自己扮演的角色问题,也是当时社会士人如何去选择道路的问题。 关于阮籍《咏怀诗》的渊源,钟嵘指出:“其源出于《小雅》。”但是五言《咏怀诗》四十五中的屈骚情结是很明显的。“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葛藟延幽谷,绵绵瓜瓞生。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25](P335)这首诗将屈骚的香草美人与道家的逍遥思想相融合,创造出另一种境界。在阮籍四言体的《咏怀诗》其二中,这种咏叹更是明显:“月明星稀,天高气寒。桂旗翠旌,佩玉鸣鸾。濯缨醴泉,被服蕙兰。思从二女,适彼湘沅。灵幽听微,谁观玉颜。灼灼春华,绿叶含丹。日月逝矣,惜尔华繁!”[26](P202)这首四言诗写出了那种美人迟暮、时不我待的惆怅,隐含着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而欲隐遁的心态。东汉王逸在《离骚经序》中赞扬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沈而死”,首先肯定屈原的人格,然后指出《离骚》“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人们在欣赏《离骚》时,深深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悯惜其高尚志向。宗白华先生曾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提出:“所以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27](P65)正是先秦多元而丰富的思想文化构成“正始之音”的人文蕴涵,形成清峻幽雅、远大遥深的风格特点。从回溯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正始之音”的形成既有哲学因素,也有文学精神,“正始之音”不仅提出了新的哲学与文学观念,而且其贡献在于兼容并包的智慧与方法。因此,片面强调“正始之音”只能指称玄学是并不确切的。 二、“正始之音”与两汉士人精神历程 “正始之音”作为在正始年代形成的特定的思想文化与时代精神,传导着先秦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总是与人格相结合,成为士人的主体人格精神。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道的范畴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格精神,没有人格精神的承载,思想观念便成了空中楼阁。“正始之音”是从汉代转变而来的思想文化现象,考论“正始之音”的渊源,当然也必须从两汉士人精神加以追溯。我们在嵇康、阮籍的著作中,经常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历史意识,在何晏与王弼的论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两汉思想文化的评论。 因此,对于“正始之音”的源流,可以从西汉与东汉的大致阶段来考论,通过“时代——士人——心灵”这样的互动关系来分析。 先秦时代,士人明显地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自由。当时各国纷争,得士则兴,失士则亡,士可以自由游走于诸侯国之间,因此,百家争鸣与自由思考成为先秦士人的特点。两汉大一统帝国结束了春秋战国年代的百家争鸣,代之以森严的封建专制统治。两汉时期,王与士的关系在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格局下变得日趋紧张,甚至有人把人主之威比喻成雷霆万钧不可一世。西汉知识分子的压力感多来自专制政治自身,是全面性的感受。而东汉的知识分子则多来自专制政治中最黑暗的某些现象,如外戚、宦官之类,是政治上的局部压力。他们的依违两难的心境,与“正始之音”中的士人心境颇为相似。 东汉晚期士人觉醒和心灵世界分成两个方面:首先,汉末士人社会批判思潮的涌动,出现了一批勇于批判现实,思考理想之治的论著与人物。例如张衡、王充与稍后的仲长统、王符、崔寔、荀悦等人,特别是王充,他将对社会批判与天道思考、文学批评集于一体,成为魏晋思想文化解放与转变的先驱。王充一生反神学的斗争精神不倦,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论衡》这一巨著,其宗旨:“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桓谭与王充等,虽因坚持理性反对神学而受到压抑与迫害,但王充在历史上被正直者誉为“千古知音”,桓谭亦被后来的思想家当做先驱。他们坚持理性的思想与斗争精神,被载入史册而永不磨灭,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反神学斗争的优良传统。“正始之音”作为魏晋思想解放与人生觉悟的精神文化概念,与王充的思想是直接相关的。而后汉晚期诸家社会批判思想,也对于“正始之音”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产生了直接的启蒙。其次,这些士人在进行思想批评的同时,内心世界也产生了退隐与独善其身的想法,从张衡《归田赋》、仲长统《述志诗》中已见端倪。 东汉桓帝与灵帝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更是粉碎了士人仅有的一丝政治希望,使正直的士大夫与朝廷相分离,他们的精神信仰受到空前的摧残,转而投向归隐。范滂临刑前的悲呼就是这种心声。同时,许多原先并不参与党事的著名人士,如郭泰也对朝政彻底失望。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则将阮籍作为魏晋清谈的代表人物,用来取代王弼、何晏。他指出:“清谈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28](P44)陈寅恪从史学的角度认为,阮籍不独是诗文作家,而且首先是玄学清谈的代表,这种看法是较为全面而辩证的。 党人性格的刚烈与性格的狷介、怪诞在党人代表范滂身上有深刻的体现,“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不止之,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郭林宗闻而让蕃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无自取不优之议邪?’蕃乃谢焉。”(《后汉书·范滂传》)范滂狷介、不拘常礼的刚烈性格在汉末士大夫群体中十分突出。另外,党人亦与独行精神为邻,《后汉书·独行列传》指出,“独行”之人是“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在于“操行俱绝”,其个性和坚持所在,可归入孔子所云“狂狷”一类。传序中有“或志刚金石,而克扜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一段文字,由此可见,“义”是范晔评价本传人物“操行俱绝”的关键所在。并且,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也指出:“初,滂等系狱,尚书霍谞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谞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竟无所言。”这种“幽明共心,蹈义陵险”的士人精神无不影响着后代士风的形成与发展,例如嵇康在狱中写给儿子嵇绍的《家诫》中提出:“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29](P546),赞美孔融的党人精神。我们在嵇康身上,时时看到这种党人刚烈精神的存在,他的视死如归,与东汉晚年的党人精神是相通的。然而,随之而来的党锢之祸使党人群体受到禁锢与严重摧残。党人精神从原先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积极用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转向明哲保身,逍遥游放。“正始之音”的逍遥游放与遗落世事,其内在焦虑与坚持正义理想的矛盾心态,透过历史,清晰可见。 东汉末期士人命运多舛,蔡邕的命运即是例证。先受宦官迫害,后被董卓拉拢,最后为王允所诛,未竟之志终成世之遗憾。蔡中郎影响到整整一个时代的各色人物,例如曹操、孔融、王粲和阮籍父亲阮瑀,是承接汉末与魏初的重要思想人物与文学家。正始之音的人物,例如嵇康与琴赋音乐思想,阮籍的文学创作思想,都直接受到蔡邕的影响。另觅新路的士人开始重新选择人生道路,心志也发生变化,他们的诗文创作即是这种心志的抒发,建安文学开始形成。“建安文学”与“正始之音”整整隔了一代而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相距整整一代人,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建安七子的阮瑀与“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是父子关系。而阮瑀所代表的建安时代与其子阮籍所代表的正始时代,鲜明地传达出时代精神的变化轨迹,这便是从追求建功立业到希冀逍遥游放。从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的异同来说,有这样几个不同之处:第一,建安风骨以慷慨仗气,抒写现实为特征,而“正始之音”则远大遥深、清峻超迈;第二,建安文士追求的是建功立业,犹有两汉时代士人修齐治平之理想,而“正始之音”诸人,则以逍遥游放,以静制动为旨趣,其中何晏、王弼与阮籍、嵇康的人生旨趣有所不同;第三,建安文学批评倡导“文以气为主”,而“正始之音”的批评观念是以无为贵、体道悟玄。“正始之音”从两汉士人心灵世界中汲取滋养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另外,正始士人的悲剧在建安年代也已出现了。例如,曹操因为政见不合与气质个性的相忤而杀害了孔融、杨修、边让等。鲁迅指出:“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30](P511)这与司马氏杀害何晏、夏侯玄、嵇康的性质并无不同。因此,正始士人的命运我们在建安文士身上也找到了清晰的印迹。正始之音超轶于建安风骨之上,其特征便是从感时伤乱,吟咏情志,上升到一种理想人格的人生自觉与文化自觉境地,无论是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还是嵇康、阮籍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追求理想的人生与理想的人格这一母题,从而使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三、“正始之音”的现实情境与蕴含 当然,“正始之音”在传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受到现实情境的感染。 自文帝曹丕死后,魏明帝统治之后期,统治者骄奢淫逸,心态趋于保守与玄虚。明帝临终前托孤不当,让曹爽与司马懿互相牵制,埋下了正始年代最大的政治隐患,而这两派的内斗愈演愈烈,也将当时的各派士人牵连其中,形成正始年代特有的思想文化风景线。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去世,死前他委托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从此开始了魏国的多事之秋,二人初期尚能合作,但后来越来越交恶。曹爽援引何晏等人,开始形成政治集团。双方各自的文人也开始浮华交游,而思想学说与文风开始转变。魏齐王芳嘉平元年(249年)正月甲午,曹爽车驾谒高平陵。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马懿发动兵变,关闭城门,逼迫曹爽回城,解除其武装,并乘机奏免大将军曹爽等人。司马氏集团随即强诬曹爽等人图谋不轨,“皆为大逆不道,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三国志·魏志·曹爽传》)腥风血雨弥漫一时,给士人心灵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经过高平陵事变,司马懿杀死了曹爽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掌控了曹魏政权。开始了向西晋政权的过渡。士人在这种现实情境下,心态也变生了变化。《文心雕龙·论说》中指出:“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简要地分析了正始玄学诞生的原因。《文心雕龙·明诗》中还指出:“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大体上也指出了正始文学形成的现实情境。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嵇康被杀,景元五年(264年),阮籍逝世。同年,“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入洛,作《思旧赋》。《晋书》卷四九《向秀传》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云。”陈寅恪先生评论向秀此举:“则完全改图失节,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矣。”[31](P184)实则向秀内心是很痛苦的,从他作《思旧赋》中可以看出这种心情,嵇康被杀,确实说明士人阶层内部发生了思想与人格上的分裂转向,从嵇康与向秀先前就“养生”问题发生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正始之音”逐渐消逝了,但遗响却绵绵无尽。 从思想蕴含来说,“正始之音”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它不仅可以指代哲学、文学,也可以指代音乐等艺术,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思想的高峰。古代典籍中的“正始之音”或为玄学概念,或为音乐概念,或为文学概念。作为玄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魏晋清谈风尚;作为音乐概念的“正始之音”,指具有中和之美的纯正音乐;作为文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作品寓意深邃,内容纯正,风格古雅,音节谐美。“正始之音”作为典故用时又常指魏晋时期的文化精神及社会总体风貌。因此,由于它广泛的包容性与涵盖意义,将“正始之音”运用时需加必要说明。 在历史上,用“正始之音”来指称正始文学在北朝时代就开始了。《全北齐文》卷三载有邢邵《广平王碑文》:“侍讲金华,参游铜雀。出陪芝盖,入奉桂室。充会友之选,当拾遗之举。发言为论,受诏成文。碧鸡自口,灵蛇在握。方见建安之体,复闻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僚右。”[32](P3842)这是一篇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写成的碑文,其中“建安之体”与“正始之音”对举,都是指当时的文章创作风范,而非指正始玄风。这可以视为最早移用《世说新语》中正始之音概念来形容文章写作的事例。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正式沿用了“正始之音”的说法:“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此,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33](P70)唐初李善《上文选注表》中提出:“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鞶帨于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同时,“正始之音”的魅力在于无法克服的思想矛盾与人生悲剧性。《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弼在台既浅,事功亦雅非所长,益不留意焉……然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与融亦不终。”这位在著作中论宏观宇宙变化、体悟自然无为真理的大哲学家,却无法“自然无为”地超越现实的卑微利益,与执政者相谈不能投其所好,与朋友相处不能善始善终。同样,阮籍与嵇康亦是“正始之音”中的两个悲剧人物。 正始名士及竹林诸名士所提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所谓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由此所激发出的对生命伦理天道自然的质疑与探索、其中或痛苦或惨烈的悲剧美具有无法阻挡的艺术魅力,都吸引着后代知识分子对正始之音的特殊魅力表现出无限怀念与倾慕。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指出:“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的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因此,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34](P7)“正始之音”因为与“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相联系,人们往往为其中的人物风采与玄学、文学所叹服,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种人物与思想的背后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与内在渊源在起作用。因此,对于“正始之音”作必要的思想渊源的考论,将是探讨其本质特点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文学史上所讲的‘正始’,实际指从正始元年到嵇康、阮籍之逝(263、264年)的二十余年时间。上距建安之末(220年)二十年,距建安诗坛的最后一位诗人曹植之卒(232年)仅七八年;下距太康之初(280年)十六七年。”参见杨合林:《玄言诗研究》,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②“正始之音”的称谓,最早出现于南朝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文学》中:“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唐初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慨叹:“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此,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这可以说是正始之音引入文学领域的例子。标签:儒家论文; 嵇康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竹林七贤论文; 玄学论文; 咏怀诗论文; 景福殿赋论文; 孔子论文; 儒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