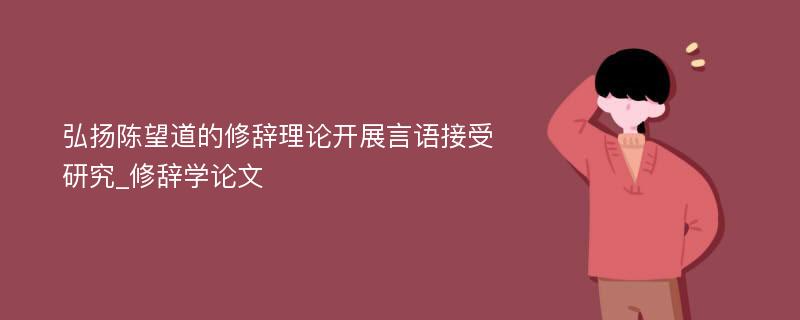
弘扬陈望道修辞理论,开展言语接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言语论文,理论论文,弘扬论文,陈望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0月29日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今天当我们缅怀望老光辉业绩、重温先生道德文章的时候,更加感觉到陈望道先生思想上的博大精深,学问上的深思熟虑。就修辞学来说,自《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出版至今,六十余年间的汉语修辞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凡》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我们认为这不应仅仅归结为汉语修辞学本身的进展缓慢;相反,以《发凡》为代表的陈望道修辞理论的成熟、严密,体大思精,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面对这样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仅仅是消极地乃至片面地接受显然是不够的。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过多的是照搬这一理论,总是在全盘接受这一理论之后再去认识这一理论,总是置身于这一理论框架之中观照这一理论框架,这种态度显然不能使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去审视陈望道修辞理论,这不仅不利于汉语修辞学的进步,也不利于陈望道修辞理论自身的发展。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不断地站在新的高度,采取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理解和诠释这一理论。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随着人们对修辞现象的认识不断地走向全面和深入,对于陈望道修辞理论也应作出新的解读,并从中获得新的启示。陈望道先生指出:“怎样继承?要革新地继承。专讲继承,要变成复古。”(《陈望道修辞论集》267页, 以下简称《论集》)这种态度同样适合于对待陈望道修辞理论。本文将以我们对于修辞学的理解,来重新认识和评析陈望道修辞理论中有关“听读者”的思想,同时希望对这一思想能有所发展。
一
应当指出,陈望道先生对于听读者及其接受过程是极为重视的。据我们粗略统计,《发凡》一书有关听读者的论述近30处;《论集》一书,除去与《发凡》重复的部分,论述听读者的也近20处。与其他所有的汉语修辞学著作相比,论及这个角度的份量都是空前的。
从内容上看,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直接开展对于听读者及其言语接受的分析研究,或总论修辞理论对于听读者接受活动的重要性,或分述听读者如何利用修辞知识理解修辞作品;另一类则是强调听读者对于表达者的影响和制约,论述说写者当如何针对听读者调整自己的语辞,这方面的内容有总体概述,也有针对某些辞格的分别论述。在这两个大类中间,如果我们按照国外有些学者的提法,把第二大类称为修辞活动中的“听读者中心论”的话,则第一大类不妨称为修辞研究中的“听读者中心论”。
下面让我们看看陈望道先生在这些方面的具体论述。
陈望道先生十分重视修辞研究对于听读者接受活动的重要性。在《发凡》中曾经指出:
(修辞学)最大的功用是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这同读和听的关系最大。大概可以分做三层来说:(一)确定意义 以前往往把修辞现象当作“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境域,其实修辞现象大半是可以言传的。我们既知道它的构成,又知道它的功能,大半就可确定它的意义所在,扩大了所谓言传的境域。……(二)解决疑难 偶然有修辞上的疑难,也比较容易解决。……(三)消灭歧视。(《发凡》17—18页)
此后陈望道先生又曾多次表述过类似观点:
我认为修辞对阅读和欣赏的帮助,比对写作的帮助更大一些。因为随机应变的技巧,不能告诉,而原则却是可以告诉的。(《论集》278页)
陈望道先生不仅一般地强调修辞理论对于听读者接受活动的帮助,而且还论及如何借助修辞知识去接受和理解一些具体的修辞作品:
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如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句句子里的一个“秋”字,便当如本书借代章所说的“年”字解,不能望文生义,直把“秋”字解作夏后冬前的“秋”。(《发凡》9页)
知道夸张辞的作用,在乎抒描深切的感动;我们赏鉴抒描感动的小说诗歌等类文辞时,遇有此种辞格,就当原情逆意,还它本来面目,实事求是,不为言过其实的字句所拘泥。好象孟轲说的,“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篇上),这才可算真能领略夸张辞的真意。(《发凡》128页)
除了这些对于听读者及其言语接受活动的正面论述和剖析之外,陈望道修辞理论还从另一角度关注听读者,那就是从实际的言语表达活动出发,论述听读者与说写者之间关系,着重探讨说写者应当如何针对听读者进行言语表达活动,强调听读者在修辞活动中的制约作用。这一类的内容也有“总论”和“分论”之别。总论如:
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对于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到。(《发凡》6页)
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或则对应写说者的心情和写说者同读听者的亲疏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发凡》10页)
分论如:
(运用夸张)客观方面须不致误为事实,如“白发三千丈”,决不致误为事实,倘不说“三千丈”而说“三尺”,那便容易使人误认为事实。如果被误为事实,那便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只是事实上的浮夸。(《发凡》132页)
避讳的作用大都在顾念对话者乃至关涉者的情感,竭力避免犯忌触讳的话头,省得别人听了不快。(《发凡》138页)
综上所述,可见陈望道先生对于听读者及其接受活动不仅十分重视,而且有着较为全面细致地探讨,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可以说他已经注意到了存在于修辞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的言语接受方面的问题,指出了它们在修辞活动和修辞研究中的地位,对一些具体现象的论述已经比较深刻。
陈望道先生对于听读者的关注和论述,使其修辞理论对于言语交际全过程的考察、对于修辞现象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入,也使其理论体系本身,较之此前乃至以后的修辞学说更为完善、更为严谨。这正是其体大思精之所在。他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最早并不止一次地从理论上阐述听读者在修辞中的重要性的学者。同时这也是陈望道先生对修辞学的杰出贡献之一,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并未认识到这一贡献的重要意义。
不过就有关听读者及其接受活动研究的系统性来看,陈望道修辞理论又有其不足之处。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能说是非常自觉的和有系统的。例如他谈到了对借代、夸张等辞格的理解应如何进行,但对更多的辞格却未涉及这个问题;他指出写说者“对于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到”,但他并未就此找出写说者可以依循的规律。因此,总的来看,陈望道先生对于听读者的研究构成了其修辞理论的重要一环,但同时却又是相对薄弱的一环。显然,这正是需要我们“革新地继承”的地方。
二
然而,陈望道修辞理论中的听读者研究这一环,在以后长期的汉语修辞学史中失落了。这方面的研究一直被忽视。尤其是对于听读者及其接受活动的直接的、正面的考察。如果说在修辞活动中给听读者留下一席之地,联系言语接受来讨论和评价言语表达的做法,在以后的汉语修辞学史上还有人在有意无意地继承的话;那么,在修辞研究中给听读者一定地位,直接分析其接受活动的做法,则被遗漏或抛弃了。对于陈望道先生这方面的理论连继承也谈不上了,遑论“革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陈望道修辞理论在这一环节上的相对薄弱,已经使这一研究有些先天不足。如上所述,陈望道先生对听读者及其接受活动的研究还只是分散的,而非系统的,在实际研究中,并未贯串始终。这种状况不仅使人们容易忽略这方面内容,而且被引用成了排斥接受研究的口实。学科理论上的不足反被当作“学术传统”,这便有些故步自封了。
其次,陈望道先生认为修辞在如何适应包括听读者在内的“题旨情境”上没有规律可循,这种观点也给后人造成一定的误解。的确,他曾多次谈到:“怎样适应题旨情境的规律不容易找,如要找这种规律,就容易生搬硬套。”(《论集》279 页)但是他显然又意识到了这方面研究的价值,所以他又指出:“如果能防止生搬硬套,研究修辞规律的运用是可以肯定的。”(《论集》280页)可见, 陈望道先生对于开展包括听读者在内的题旨情境的研究,以及如何适应题旨情境的研究,并不持完全排斥的态度。相反,这正是需要“后出转精”的地方,却一再的从后人手中滑过去了。
此外,我们认为在现代汉语修辞学史上,学术研究越来越彻底地“以语言为本位”也是个中原因之一。这一转换在《发凡》时代已现端倪,但应当说还未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然而随着这种观点被后人不适当地“发扬光大”,尤其当它事实上变成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本位之后,其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具体表现为修辞学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方法越来越单调;拘泥于静态的形式研究,而排斥存在于交际过程中的主体意识等活性因素。
这种以语言为本位的具体做法,按照陈望道先生的说法,“用的就是语言学的工具,把语言学的原理用到研究写作上来。”他并且说:“当时我接触比较多的就是索绪尔的语言学说。”(《论集》308—309页)我们知道,索绪尔语言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认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323页,以下简称《教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陈望道先生认为:“我们应当注意一些更重要的现象,就是各个辞格的组织和功能。这等于文法以前单讲所谓反正虚实,而今要说各个词类的组织和功能一样。”而其他的一切都是所谓“末梢现象”(《发凡》250页)。因此我们看到,陈望道先生研究比喻,以其本体、喻体、喻词的异同和隐现为标准,将其区分为不同的结构类型,并为之列了一个整整齐齐的表格,这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布拉格学派研究音位的方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确,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汉语修辞学对于修辞方式的描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比起古代诗话文论中较为随意的评点议论,这一变化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强调修辞学的作用在于使人们的达意传情更加适切的话,则《发凡》关于比喻类型的研究,在指导人们如何具体运用比喻方面,其收效并不很显著。
可见,“以语言为本位”的代价是巨大的,它在使修辞学对修辞作品的描写有了长足进展的同时,逐渐放弃了对修辞作品的意义生成和效果实现等方面的研究,在修辞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交际双方的主体意识以及题旨情境等,都被当作“末梢现象”加以摒弃了,这与长期以来语言学界盛行的结构主义方法有关。
结构主义方法用来研究修辞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不完全合适的一面。结构主义的初衷是为了使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向自然科学靠拢,它的途径之一是排斥单个人在行为过程中的主体意识,索绪尔把他的研究对象描述为:“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教程》41页)然而修辞现象却更象是他所描述的言语,即“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组合”(《教程》42页)。索绪尔认为:“要用同一个观点把语言和言语联合起来,简直是幻想。”(《教程》42页)但是我们的修辞学却正在企图实践这一幻想,许多修辞学者向语法学、音位学看齐,也同样地排斥主体意识,乃至意义、内容等,热衷于形式、格式、公式、模式等。这种方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既成修辞作品的描写畸形发展和“辞格中心论”。而结合语境,尤其是交际双方的主体意识来探讨和解释从修辞现象的生成直到其效果实现的全过程则远远不够,这一缺陷越来越成为阻碍修辞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然而,结构主义方法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的影响却异乎寻常的巨大。尤其是解放以来,修辞学彻底归属语言学,修辞学者也多是从语言学科出身,而这期间在语言学领域结构主义方法占统治地位。因此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些修辞学者总会把结构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带入修辞学研究中来,并且按照语法学和音位学的标准来要求修辞学。直到90年代,一方面人们拿结构主义的标准来律修辞学的成果,认为其“科学品位不高”;另一方面,为了让自己的“品位”高起来,更加地向结构主义靠拢,以为科学化便是公式化、模式化。这种做法对于修辞学来说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有害的。拿结构主义理论来套修辞学无异于削足适履,而企图借结构主义方法来提高品位更是南辕北辙。其结果导致修辞学长期依附于语言学的门下,却又备受冷落、进展乏力。
三
修辞活动明显是一种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的行为,而绝不象索绪尔所描写的语言那样“对任何人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同时,修辞学研究也绝不应当是“就语言和为语言”的研究。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修辞活动在从说写者到听读者之间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修辞学必须以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把存在于这一过程中的语码部分切割下来,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描写,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正如陈望道先生再三指出:“语言文字的美丑是由题旨情境决定的。并非语言文字的本身有什么美丑在。语言文字的美丑全在用得切当不切当:用得切当便是美,用得不切当便是丑。”(《发凡》19页)因此,对于语言文字及其组合作形式化的静态描写,其价值虽应充分认识,但毕竟是有限的。我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修辞学研究必须把修辞活动的参与者一并纳入自己的视野。当然语码仍然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但绝不是全部,它只是我们可以见到的冰山的一角,我们要做的是让隐藏在它下面的更多的东西浮出海面。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认为应当把修辞学的对象重新定义为着眼于交际效果的言语交际的全过程。具体操作中,应当透过以语篇为主要形态的语码,联系语境,全面考察其意义生成直到效果实现的动态过程。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以至于陈望道先生认为“没有规律可循”。然而若能摆脱结构主义的羁绊,广泛采纳语用学、功能语法学等所谓“外部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哲学、心理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营养,同时继承我国古往今来修辞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就这一动态过程找出一些规律乃至建立一些规则不是不可能的。
在对这一过程的考察中,要均衡地研究表达和接受,而不是停留在长期以来畸形发展的表达一方。相反,由于长期以来修辞学忽视言语接受方面的研究,致使这一环节相对薄弱。因此在言语交际的全过程中,接受一端的研究是现阶段修辞学亟待加强的工作。言语接受研究的主要课题则仍然不出陈望道先生所曾涉及的两个方面:一是站在接受者一边直接观察接受者,研究他是如何接受、理解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的;一是站在表达者的立场上观察接受者,研究他对言语表达所产生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后来均未真正有效地展开过。不过相对说来,后一个方面,仍有人不断地涉及,许多修辞学者和修辞论著在评价表达效果时,往往是从接受的角度着手的;而前一个方面,则几乎无人提及了。因此,两者之中又以前者更为紧迫,这不单是因为它特别薄弱,还因为如果对它没有充分的研究,后一个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也无法有效地进行。此外,言语接受本身也是一项言语技能,又是修辞效果实现的关键,修辞学有责任为人们的言语接受能力的提高作出贡献。
对于修辞过程中的接受者及其接受活动的分析,在这里我们还只能简单地勾划出一个轮廓,深入细致和卓有成效的研究,还有待作出艰苦的努力。
在修辞学范畴内进行接受研究,可以继承的东西不多,可资借鉴的却有。解释学哲学肇始于神学解释学,经过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尤其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努力,已成为较具普遍性的阐释学说,它的一些观点可以作为言语接受研究的指导思想。例如它的“前理解”的观念,它的“视野融合”说对于日常交际中的言语接受研究均不无参考价值。
而在较为具体的层次上,接受美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内的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对于修辞学领域的言语接受研究也都有其借鉴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接受美学属于美学范畴,从美感的实际出发,它特别强调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再创造,即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而它认为,在接受者那里,文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定的,作者是无关紧要的。这一点与日常交际中的言语接受有着本质区别,取消作者及其话语在意义上的规定性,片面夸大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这在修辞研究中是难以接受的。
另一方面,修辞学中的言语接受研究又不同于人工智能领域内的自然语言理解研究,后者对于自然语言的认识只是对人工语言的延伸,其中的接受者自身是一片空白,它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还原语码的本来意义。目前,这种还原还不能很好地考虑语境,甚至也不能顾及表达者的意图,当然更谈不上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了。这种状况也不能合乎修辞学中的言语接受研究的要求。
如果能够注意到既不夸大,也不忽视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野”与“视野的改变”,以及“空白”、“空缺”、“否定”等概念,和自然语言理解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加工模式与策略等,都对日常交际中的言语接受的研究有借鉴作用。
由此可见,修辞活动中的言语接受就其性质来说,当是介于审美和自然语言理解之间的东西,积极修辞中的有些现象可能接近接受美学,但不可抹杀作者意图和文本意义方面的规定性;消极修辞一端接近自然语言理解,但也不仅是语码意义的简单复原,不能完全否定接受者的再创造。表达者的主观意图与接受者的能动作用,正是这处于交际过程两端的主体意识决定了修辞活动中言语接受的特点,也决定了修辞学范畴内言语接受研究的性质,使之与邻近学科区别开来。
无庸讳言,在修辞学范畴内开展言语接受研究绝非易事,这不仅是由于这方面的理论成果极少,可以继承的东西微乎其微。还由于言语接受主要是一个心理过程,而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心理机制的认识还很不够,人的大脑至今仍是一个“黑箱”,现有的心理学理论许多是作为假说出现的,而这些假说立足于日常言语交际的不多,这也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
然而这种研究无疑是有巨大价值的,除了能够丰富、完善修辞学理论,全面揭示修辞现象的奥秘,提高人们的言语交际能力之外。它还是接受美学的起点,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只有正确地把握文本话语的意义,才能领略其美感。在人工智能方面,它又是自然语言理解研究的归宿,人机对话最终不可能停留在语码阶段,而必然要进入到对切情切境的话语的理解。对心理学来说,言语接受研究尤为重要,新兴的认知心理学把人的心理过程看作是信息加工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显然是言语加工过程。由此可见,展开对日常交际过程中的言语接受研究,无论是对修辞学还是对相关学科来说,都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