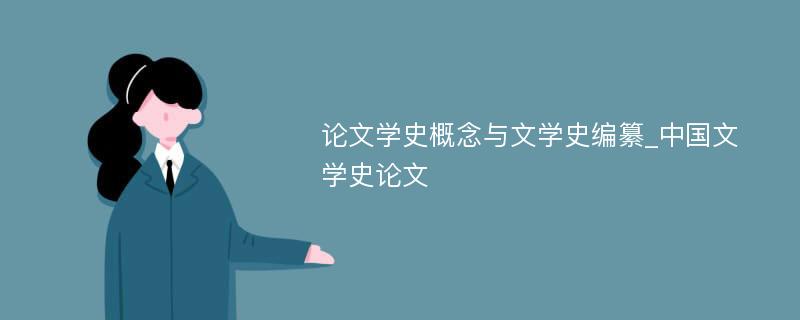
论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编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观念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219(2006)02-0033-06
20世纪是中国文学史学科诞生并获得充分发展的一个世纪,不仅文学史著作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学科结构和文学史编写方法,产生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经典性文学史学术精品。然而毋庸讳言,在千余部各类文学史著作中,滥竽充数和抄袭拼凑者也不算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受到质疑。如何吸收前人编写文学史的经验教训,开创21世纪文学史编写的新途径,推动文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文学史编写谈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文学的观念
文学史顾名思义就是文学的历史,它以文学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然而,编写者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首先必须确定什么是文学,以保证他所描述的历史确实是文学的历史。换句话说,编写文学史,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一定会有关于文学的观念,不然,文学史是无法编写的。文学观念是文学史编写的逻辑前提。文学的观念不同,所关注的文学现象和描述的文学事实也就不同,文学史的面貌也会两样。因此,中国早期出版的文学史,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等,都无不要花一定的篇幅来讨论文学的观念,以便使自己的文学史建立在相对稳固的基础之上,至少保证他们所编写的文学史自身体例能够统一。
不过,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基本定型之后,文学史的编写者们一般都不再讨论文学观念问题。现行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同样也不讨论文学观念问题,似乎这一问题早已解决,不必再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行的中国文学史不讨论文学观念,不是这一问题已经解决,而是大家习焉不察、见怪不怪罢了。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作为上古官方诰令的《尚书》写进了文学史,而后代皇帝的大诰、训令不写进文学史?为什么先秦诸子著作如《论语》、《孟子》、《庄子》写进了文学史,而宋代理学家的著作如《张子正蒙》、《二程遗书》、《朱子语类》不写进文学史?为什么记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左传》、《史记》等写进了文学史,而同样记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唐书》、《宋史》等不写进文学史?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然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而回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所谓文学观念,也就是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认识,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一般说来,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一定会有对于文学的基本认识。不过,要他明确说出这种认识,却并不那么容易。即使能够说出这种认识,要想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同样十分困难。从理论上说,文学是什么应该是能够回答的,因为文学一定有它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产品的本质属性,不然它就不必存在也不会存在。然而,文学并没有一种固定的形态,它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不是它的所谓本质决定了它的存在,而是它的存在决定了它的本质。不同时期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同一时期的人们由于视角不同对文学的认识也会两样。就中国而言,古人和今人的文学观念不同;古人与古人之间,今人与今人之间,对文学的认识也存在差异。例如,孔子说他的学生子游、子夏长于文学,所谓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包括典籍文献和礼乐制度;①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为文学,而更多的汉人以为文学主要是经学,他们的文学观念就颇不一致。今人对文学的认识也各有不同,有的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有的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有的说“文学是精神的灯塔”,有的说“文学是现实的镜子”,有的说“文学就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西方,文学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含义也不一样。19世纪之前,文学一般指著作或书本知识。写于1800年的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被认为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其所谓文学“包括诗歌、雄辩术、历史及哲学(即对人的精神的研究)”,[1] 与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仍有距离。而当代西方的文学研究已经转向语言学和文化学。种种情况说明,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本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且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某一种认识,常常只是突出或强调了文学自身的某一特点,并不能反映文学的全部内涵,更无法规定文学自身的历史发展。企图寻找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观念来指导文学史写作,无疑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甚至只是一种幻想。如果我们硬要用一种固定的僵化的文学观念来编写文学史,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了。
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来编写文学史呢?我们认为,编写文学史所采用的文学观念应该是符合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实际的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学观念。也就是说,文学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而文学史的编写者应该尊重历史,运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探讨文学观念的历史演进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追寻造成文学观念变化和文学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这样才能编写出既符合历史实际又具有逻辑联系的中国文学史。
就中国文学而言,早期的文学观念是与社会对鬼神的崇拜转变为对世俗的关注相伴生的,是礼乐文化取代祭祀文化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产物。因此,这种文学观念就包含了与文治教化相关联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举凡礼乐制度、文献典籍、政策法令、道德伦理、宗教艺术、行为规范,无不可以视为文学。[2] 这是一种大文学观念,或者说是一种泛文学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社会意识形态和人的精神生活逐渐细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宗教、艺术向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形成自身的体系和形态,于是文学开始剥离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而独立发展。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玄、史、文、儒四学,标志着文学观念出现重要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文学外延的收敛和文学内涵的加深。历史、哲学与文学的分别,虽然缩小了文学的地盘,却也促进了文学的生长,刺激了人们对文学文体特征的关注和文学创作规律的探讨。不过,对于应用文体和审美文体的明确区分,则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才为人们所重视,人们将西方文学观念引入中国,中国文学观念才具有了现代意识。[3] 中国文学观念的这一历史发展进程,无疑是文学史编写者需要认真对待,并在文学史著作中加以注意的。
二、文学史的观念
自从20世纪初年经由日本传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以后,不仅文学在中国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文学史在中国也成为了一门显学。据不完全统计,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迄今已经出版了一千余种,包括文学通史、断代史、分体史、专题史、区域史等等。②
编写文学史,不仅要有文学的观念,而且还要有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这种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史的观念。没有文学史的观念,编写者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就会束手无策,即使勉强成书,整部文学史著作也会是一盘散沙。有了文学史的观念,就有了贯串文学史实的一根主轴,一条红线;文学史著作章节的设置,材料的取舍,文字的详略,叙述的方式,都围绕着这一观念。这样,文学的发展才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的逻辑线索,读者才能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印象。
与文学观念一样,不同时期不同人们对于文学史的观念也是不一样的。在20世纪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编写者们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史观念就很不相同。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认定:“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4] 由于建立了这样的文学史的观念,他的文学史架构便围绕着白话文学的发展来设置,他的全部叙述都是为了论证古文文学的没落和白话文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文学史家大都相信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赞成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所编写的文学史便十分重视文学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一部文学史就像是一部形象化的社会政治史。到了90年代,社会更关注人的人格、人的心灵,所以又出现了以反映人格的发展和人的心灵成长为主线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既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也是一个重视文学的国度。从《汉书》开创《艺文志》著录文学作品以来,历代正史无不仿效编撰《艺文志》或《经籍志》,使我们有了清理文学发展的文献线索。从《史记》设立《儒林传》特别是《后汉书》设立《文苑传》以来,文学人物史不绝书,使我们有了对于文学创造者们创作活动的了解。古人之所以没有撰写出独立的文学史著作,是与他们的文学史观念密切相关的。在古人看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龙·时序》)。在他们心目中,文学并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文学的发展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而且这种社会历史主要是社会政治史。因此,文学的发展只能在社会政治历史的整体面貌中寻求解释,而不必要有独立的文学史。即使是像刘勰《文心雕龙》那样专门讨论文学问题的专著,在其文学史观念中也是以“原道”、“宗经”、“征圣”作为论述的基础,以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文心雕龙·征圣》)。这样,文学就只是圣王治理社会的副产品,自然没有独立成为历史对象的必要。这种文学史观念尽管不被现代文学史家们所认可,但它的潜在影响却不可低估,我们在20世纪出版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都能够或隐或显地感受到这种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人缺少独立的文学历史意识,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时也缺少对于具体作家作品和文体发展的深入研究。事实上,古人们对于作家创作和文体发展的研究,其细致和深入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例如,陆机《文赋》对文章创作的理解和文体风格的说明,钟嵘《诗品》对诗歌发展的描述和对历代诗人的品评,刘勰《文心雕龙》“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都不仅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学修养,而且反映出他们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尤其是对文体变迁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夫设文之体有常,而变文之数无方”,“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文心雕龙·通变》)。这种文学通变观与《易传》所主张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相一致,构成了中国古人对于文学发展特别是文体发展的最基本的观念之一,影响巨大而深远。我们可以从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所明确主张的“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以及他对魏晋以来的文学发展变化的描述中看出这种影响。也可以从胡应麟《诗薮》所论证的“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为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为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亡矣”的结论中看出这种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家们一般并不采用这种文学发展观念,然而,他们所描述的文学文体发展往往呈现出由俗到雅然后鼎盛、僵化、衰落从而被另外一种文体所代替的历史轨迹,又不能说完全没有传统通变观的影子。
文学通变观虽然可以说明一部分文学现象,但由于它强调源流正变,倾向复古,不能解释各种文体递嬗的直接原因,容易滑入历史循环论的窠臼,因此,人们尝试从文学体裁与社会风气的联系入手来认识文学的发展。例如,元人虞集便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至正直记》卷3引)明人王思任则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王季重十种·唐诗纪事序》)清人焦循在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后说:“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易余龠录》卷15)他认为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五言、唐之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之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近人冯桂芬则提出:“自来一代之文章,恒与一代之气运相表里。扬子云有言:虞夏之书浑浑耳,商书灏灏耳,周书噩噩耳。尚已。降至秦汉,迄乎元明,盛衰升降,代有不齐,要各成为一代之文章。”(《显志堂稿》卷2)这种文学文体代胜观不仅注意到文学主流文体与朝代气运的联系,而且强调文体风格与时代精神的联系,为人们考察文学发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不过,这种文体代胜观却是以“名理相因,通变则久”为其理论基础的,这就为复古主义留下了地盘;并且,究竟应以何种文体作为一个时代精神气运的代表,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而“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本质退化论更容易使人们对文学的发展丧失信心,人们自然有理由对这种文学史观持保留态度。
由于受西方生物进化论的影响,20世纪最主要的文学史观念是文学进化的观念,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1903年梁启超就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迹。”[5] 他竭力提倡“小说界革命”,企图通过新小说而新民,达到改良社会政治的目的。他的这一思想对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发展富有启发意义。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表面看来,王国维的文学史观与虞集、焦循等人并无多少差别,其实,王国维是从现代文学观念来确定文学文体,又从文学进化论来认识文学的发展和文体代胜的。[6]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提倡“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进一步深化了王国维的文学进化史观。他指出:“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理,故不能工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7] 他以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8] 这样,文学文体的代胜就变成了文学由古语向俗语的进化,或者说由文言向白话的进化。这种文学进化观显然是有别于古人的。
无论是由古语进化为俗语,还是由文言进化为白话,中国早期的文学进化史观最初都是从文学形式上着眼的。后来,人们又把它推广到文学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和审美心理等各个层面,使得文学进化观念渗透到整个文学史学科体系之中。
文学进化的观念为人们理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工具,它确实能够较好地解释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使得人们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认识更有条理和统绪,也跳出了古人所主张的通变说和循环论的怪圈,自然为大家所青睐。然而,文学进化史观也有自身的问题,它并不能说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现象和全部事实。例如,历史学家可以根据人类使用生产工具质地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彰显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化,也可以根据人类从茹毛饮血的生食到火炙火烤的熟食再到精工细作的烹饪,来描述人类生活方式的进化,如果文学史家因为文学描写了这些内容而认为文学也在进化,那显然是把文学当作了社会历史的附庸,文学史也就难以自立,只得退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这是现代的文学史家们所不愿看到的。文学史家当然也可以描述文学如何从声口相传到刻于金石、载于竹帛、雕版刊印、活字印刷,来反映文学生产能力和消费方式的进化,但那显然只涉及文学的形式与技术。然而,说文学的进化只涉及它的形式、技术而不涉及它的内容,不涉及作家的思想情感,恐怕许多文学史家都不会接受。而具体到文学的哪些内容在进化,大家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些看法又容易引起争论。就拿文学史是人类心灵进化史这一命题来说,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有很多。首先,人类的心灵是否在进化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心灵应该包括智(智慧)、情(情感)、意(意志)各个方面。就心智而言,科学技术史能够很好地说明人的心智在进化,因为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的确在不断增强,然而,文学所涉及的人的心智主要应该是认识自我和把握自我的能力,而在这一点上很难说今人超过了古人。庄子的逍遥,陶潜的恬淡,李白的飘逸,苏轼的旷达,都是他们把握自我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他们应对生活的一种智慧,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心智后来如何在进化,现在又进化到了何种程度。至于情感问题,更难以用进化的观念来说明。谁能够证明今人比古人有更淳朴的亲情,有更坚贞的爱情,有更纯洁的友情?谁能够证明诗歌后来的政治抒情意味超过了《离骚》,人物传记后来的情感贯注超过了《史记》,小说作品后来的爱情表达超过了《红楼梦》?如果不能证明这些,又凭什么说人类的情感在进化,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在进化?!章太炎就曾指出:“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此亦可为反比例也。”[9]
毫无疑问,文学史的观念只是文学史家们对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认识,不同的文学史编写者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是不一样的,各种文学史观念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同时也都有其认识的局限。我们不能要求一部文学史著作能够说明文学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而只能要求它说明了它所想要说明的问题。当然,这种说明应该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的,也应该是符合文学史自身的逻辑的。这就是数以千计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所以能够存在的理由。我们这样说并不表示文学史观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或深刻与肤浅之别。事实上,不同的文学史观解释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的有效性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种解释的有效性正是判别文学史观优劣的重要标准,也是判别文学史著作优劣的重要标准。至于那些没有自己的文学史观,仅靠东拼西凑而形成的所谓文学史著作,在这个标准面前就会原形毕露,因为没有文学史观的所谓文学史著作是说明不了文学发展中的问题的,只会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因此,我们编写的文学史虽然不能保证其中的文学史观念是最先进的,但我们力图使自己的文学史观念尽量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能够尽可能多地解释中国文学历史的客观事实,给读者以知识和启发。
三、文学史的写法
文学史并没有规定的写法。如何编写文学史,是与编写者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相一致的,所有的编写者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表达需要的文学史写法。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一般都采用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编写方法,也就是说,它的基本线索是社会政治历史线索。这种写法的文学史大都持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发展相表里的文学史观念。它的优势是借用了历史编撰者们以朝代更替为历史发展的时间段落的传统方法,人们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同时也适合学校分段教学的需要。将一个时段的作家作品放在一起叙述,方便介绍一个时段的社会背景,也比较容易描绘出这个时段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便于读者从总体上加以把握。而将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放在一起叙述,也容易反映这个作家的创作全貌,便于对这个作家的了解,当然,这种写法的不足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因为,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它常常积极地干预生活;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并不同步,它有自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作家作品的风格并非必然与社会风气相吻合,有个性和有创造性的作家反而会体现出与时代不一致的精神风貌。
例如,现行文学史著作一般都把刘辰翁、周密、张炎等作为南宋词人放在宋末叙述,把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杂剧作家作为元曲大家放在元代叙述。而实际上,刘辰翁、周密、张炎均出生于13世纪中叶,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的杂剧创作活动可能已经开始。元朝建元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统一中国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那时的杂剧体制已经成熟,杂剧创作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的杂剧代表作都诞生在元朝建国之前,入元以后并无多少创作。倒是刘辰翁、周密、张炎等人入元后有大量创作,但由于他们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所以历代文人将他们视为南宋遗民作家,这样就出现了时间和空间的颠倒,使人误以为刘辰翁、周密、张炎要早于关汉卿、王实甫、白朴,又以为关汉卿、王实甫、白朴是元代早期杂剧作家,并且用元初的社会状况作为论述他们作品的时代背景。同样的情况在元明之际、明清之际也存在。如宋濂、刘基在元代生活了近60年,入明以后的生活时间都不长,刘基不过8年,宋濂也才14年,与他们同时或稍晚的作家如萨都剌、脱脱、戴良等,都被作为元代作家,而由于宋濂、刘基二人是明代开国大臣,故被列入明代作家,这样就人为地把同一时期的作家分在两个不同时代来叙述。宋濂、刘基的文学成就与他们的政治作为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而以朝代为线索,就用政治观念代替了文学观念,用政治历史判断代替了文学历史判断,对我们认识文学自身的发展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编写方法,常常使人们过多关注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和经典作家的文学成就,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虽然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和经典作家的文学成就是文学史应该关注的,但是,文学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典作家的出现,往往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其所处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并且这种文体正处在发展的成熟阶段,不然,他们就不可能取得那样高的成就。才情四溢的大诗人李白写不出《红楼梦》,关心民生疾苦的诗圣杜甫也写不出《窦娥冤》,不是他们没有那种胸怀和能力,而是戏曲、小说在唐代还没有发展成熟。而一种文学体裁,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一般都要经过漫长的孕育和发展才能成熟,在其幼小阶段往往不被重视,也难以出现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如果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编写文学史,当然会重视当时最有成绩的文体和作家作品,而忽视那些新兴文体和具有探索性的作家作品。因此,对宋以后通俗文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唐代俗讲,在以展示诗文成就为主体的唐代文学部分就得不到充分重视,以致我们描述宋代话本、元代杂剧和明清小说的辉煌时,并不能讲清楚这些文体的来龙去脉,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被朝代特有的时空所隔断,读者并没有真正从中获得文学发展的观念和清晰的历史线索,这显然与文学史的编写目标背道而驰。
文学就其文本而言,包括内容和形式。文学内容的发展是一个有争议且至今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而文学形式特别是文体的发展则是得到学术界公认且有清晰历史轨迹可循的事实。正如刘师培所说:“凡论文学之变迁,当观其体势如何,然后文派异同,可得而说。”[10] 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编写文学史,比较有利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分析,却不大利于文学文体发展线索的清理。而文学作品的内容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双重品格,并不是建立历史架构的理想材料。所谓历时性,是说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当时社会生活有一定联系,可以提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某些信息。所谓共时性,是说文学作品的内容依赖于读者的解读,它不是僵死的材料,而是活着的精灵,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的解读是不一样的,这种解读必然会渗入读者的主观意识和当下的社会思潮,因而它并不完全是历史的而主要是现实的,这也是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之所以为今天读者所喜爱的原因。因此,作家作品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的研究而不是文学史的研究。如果以文学文体的发展为线索来编写文学史,就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使我们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描述建立在比较客观的基础上。当然,这种描述并不是要抛弃作家作品,而是将作家作品置于文学文体的发展史上去理解,去认识,而对于作品的内容只做一般论述,把深入讨论和理解的权力交还给读者。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同样也应该受到关注,不然,我们就无法说明某种文学样式何以在这个时期诞生,又何以在那个时期成熟并取得杰出成就。
这里其实涉及到文学史编写的基本方法问题,即是采用文学的方法,还是采用史学的方法。文学的方法主要是审美,史学的方法主要是实证。采用文学的方法,文学史的编写就可以细致分析作品,不回避编写者的情感介入。采用史学的方法,文学史的编写就应该多做史实的清理,少做主观的判断,让事实说话。当然,在历史学界,传统史学家们往往追求历史真实,甚至主张还原历史,而新历史主义则认为,历史的本来面貌已经逝去不可能恢复,而留下来的历史材料(包括文物、史料、遗迹等)只是历史的一些片段,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原貌,至于那些历史著作更渗透了著作者的主观意识,离真实的历史更远。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相对论自有其合理性,然而,对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并不表明人们可以任意编造历史,更不意味着追求历史真实毫无价值。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持何种观点,他们都尽可能多地搜集史料,辨析真伪,使自己的结论与基本史实相一致,说明大家并不否认有一种接近历史真实的东西存在。历史相对论倒是提醒我们不要盲目自信,以为只有自己的认识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应该关注其他的历史认识,因为它们同样也可能提供了某些历史真实。由于文学史的对象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不仅不应该排斥历史的方法,而且应该主动地采用历史的方法,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真正成为文学的历史。当然,文学史毕竟是以文学的发展过程为对象,后代作家常常吸收前代作家的创作经验以丰富自己的文学修养,除了借鉴前人所创造的文学形式之外,他们还会借鉴前人所创造的文学题材、形象、意境、风格等等,来提高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而要清理这些历史线索,只能运用文学的方法。因此,文学史的编写也应该允许采用文学的方法。我们的意见是,在文学形式和文体发展的描述中,应该尽量采用历史的方法,而在文学内容和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应该注意采用文学的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能否有机结合,是文学史编写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参见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和孔子四教》(《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和《游夏文学发微》(《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②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统计,1949年前有各类文学史著作346种;据吉平平、黄晓静《中国文学史版本概览》统计,1949~1991年出版各类文学史著作578种(其中重版55种);据黄文吉《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统计,1949~1994年海内外有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1606种(含台湾地区部分硕士、博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