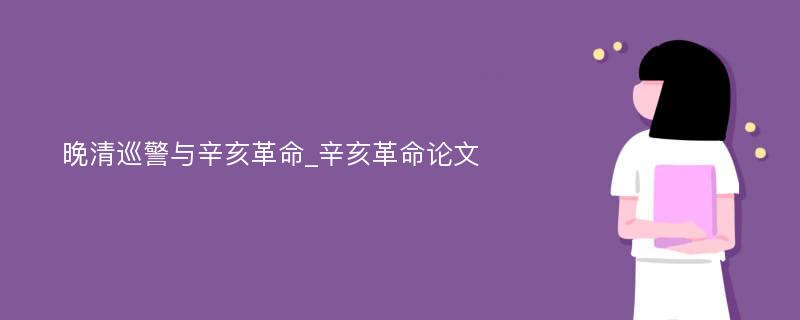
清末巡警与辛亥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巡警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1—1911年,清王朝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新政”。如果说,清末“新政”中废科举,兴学堂,发展近代教育产生了新兴的学生群体的话,那么,作为新政之一端的警政改革,则在统治阶级队伍中形成了庞大的警察武装。过去,论者对资产阶级、学生群体、新军、会党等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研究的多,而对巡警与这场革命的关系则未问津,本文在此作一探讨。
从最高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一场殊死决战,而革命派展开斗争的舞台则主要是在统治阶级的中心区域城市。这就决定了巡警必然要与这场革命直接交锋。
辛亥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学说的滔滔横流,引起了统治者的惶恐不安。革命党人着重发动武装起义外,还重视对国内人们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以扩大反清斗争阵营,进一步孤立专制政府。《革命军》、《警世钟》、《黄帝魂》等革命书籍的发行,引起了官方的恐惧,各地官府下令巡警道出示严禁,并“派侦探多名扮作购书之人分途查防”(注:《饬查违禁书籍》,《大公报》1909年7月24日。)。特别是报纸, 既是社会舆论的喉舌,又是导致民情激愤的催化剂。1908年清政府正式在全国颁行《大清报律》,对于开设报馆者,必须预先呈报备案,发行前须经巡警官署查核,不得刊载“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之语,如违反则永远禁止发行,把管理权归于警界。报界人士为伸张正义,往往登载言辞激烈文字抨击政府,当时《可报》、《天明报》、《中华新报》等报馆就遭封闭的厄运,报人也被巡警逮捕。但无论如何,仍无法阻遏反清新闻传播的扩散。
本来学生与巡警都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是近代化过程的新生群体。但前者拥有自身群体的独立人格,后者与生俱来只能是统治者使唤的工具。于是,每当风潮来临时,历史的命运则安排他们成为兵刃相见的对象。随着清末学潮由地方而全国发展的逐步升级,学生与巡警针锋相对斗争的频率、规模也随之扩大。这在清亡之前两年间尤为明显。立宪党人被清政府的“开明”姿态迷住后,发起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仍未放弃自身的竭力追求,至1910年又形成以奉天、直隶的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及立宪派再次发动的请愿运动,声势浩大,使统治阶级进退失据。12月初,奉天五千多名学生聚集督署静坐请愿,要求速派请愿代表进京,全国其他团体纷纷响应,激起了请愿狂潮的重新高涨。特别是他们自行进入请愿的举动,给京师震动不小,使统治者大有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感。步军统领衙门连日添派岗警梭巡,还出动禁卫军分路巡卫。其它部门如资政院,“各自保卫,每出必加派护兵、警兵沿途拥护,无论何人求见,非日常见其姓氏者,即行拒绝”(注:《民立报》,1910年12月27日。)。北京的学生也坐不住了,一些学校学生手持传单上街宣传,被巡警拘入警局,激起学界无比愤怒。为防止京师学堂学生卷入学潮,当局还派警兵驻守各校门,严防学生无证出门,企图削弱学潮的社会冲击力。无论请愿代表如何哀求,董之威等代表还是被军警押回奉天。群龙失首,一时震动京城的民主浪潮只好退潮了。
同时,天津的学生也随之响应,引起了当局的不安。直督陈夔龙派警兵围困学堂,阻挠学生请愿,学生更为愤怒。奉天学生路过天津时,发表演说,无日无会。他们慷慨激昂,誓争国会,轰动全津学界。还散发传单,通电全国各省同志会和青年学生等联合行动,声势浩浩荡荡。直督闻后,十分震惊,决定派出兵警联合镇压,“即时传见警道畿镇统制全为防备”随即“发兵围攻”(注:《天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12月19日,天津学界罢课,集合三千多人,逼直督代奏,但受到清廷的反对。学生们不顾反对,21日晚各堂学生300余人集中于自治研究所,召开会议,陈督“闻之盛怒, 立饬警道解散”。不久,由天津镇派兵200名,巡警道派巡警百名外, 加卫队多名赴三条石开会地点,设法和平解散。但由于该道对此事预防不足,未能解散,受到直督“严斥”,这位巡警道“因两面不能落好,已决意辞职不干”(注:《天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22日,学生再度汇集开会,陈夔龙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立派 400名军警前往镇压。总兵张怀芝回去调兵时,巡警道员恐酿祸变,飞令 5人驰往劝谕和平解散。学生代表敌不过军警,在各界人士的劝导下,只好作出解散的决定。接着,陈督接连下令解散同志会,禁止报馆“危言耸听”,传知商人不准附和,将严加查办的告示张贴于众,命令军警持枪巡逻,随时驱散聚集的群众(注:转引自候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面对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清廷决定采取极端措施,下令各省督抚随时弹压,出动大批军警侦探镇压罢课风潮。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是这次运动的倡导者,直督亲自下令巡警道“拿办,并电请惩敬。奉旨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注:《东方杂志》第8年,第1号。)。还严令军警监视各学堂,要求学堂停止罢课斗争。在国家机器强制镇压下,这次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终于悲剧性地结束了。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广州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地方官吏下令巡警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张鸣歧亲自出动,会同提督李准率营队、巡警分头搜捕,一些尚未撤走的革命党人还与巡警发生冲突,进行枪战。他下令关闭城门,饬区协同弁按户稽查搜捕党人,企图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搜捕中,“凡见有剪辫西装之人,稍有可疑即被拿去”,并派水上巡警搜检港澳轮船,企图从水道上堵截革命党人外逃(注:《粤督报告乱事电》,《民立报》1911年5月1日。)。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党人不屈不挠,至5月30日还在顺德乐从墟竖旗起义,当地巡警“众寡不敌, 纷纷避匿”(注:《革命党再闹广东记》,《民立报》1911年5月8日。)。起义时,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对于巡警亦无嫉视”。后来还将“起义时所夺该墟巡警枪枝一一点还清楚,乃各散去”,人们感到“颇异”(注:《革命党再闹广东记》,《民立报》1911年5月8日。)。在其他省份,地方官吏也是坐卧不安,加紧采取防范措施。苏州汪巡道下令“各区巡警严缉逃犯,并在城内外各客栈大肆搜查”(注:《吴中戒严记》,《民立报》1911年5月16日。)。 福建省城制台命令孙统制各营加强戒严,又令“吕警道夜派巡士查夜,数十人一队持枪装弹,彻夜梭巡”(注:《闽省戒严记》(二),《民立报》1911年6月10日。)。 同时还派暗探百余名四处密查,到各学堂调查寄宿学生人数及姓名、籍贯,然后造册呈缴以备稽查。在武昌,鄂督“特派特别警察守卫东西辕门,不准行人通过,以防意外。凡往来行人有不知闯入辕门者,该警察举手即打,如多言以刺刀背乱砍,行人苦之”(注:《鄂中戒严记》,《民立报》1911年5月7日。)。还派探警分途密查,所有武汉地面,夜间均派双岗巡士巡逻,不准擅离岗位。京师更是不敢松懈,下令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严搜京畿一带匪党线迹,故日来警察防查甚严”,一些革命党人不时被捕(注:《民立报》,1911年5月1日。)。粤省巡警道为了一网打尽革命党人,还与香港英警察署立约协拿起义人士,企图杜绝后患。统治者以为布下天罗地网革命党人插翅难飞,但是,仍挡不了黄兴等领导人物安全逃走。这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仍毫不气馁,准备潜入长江一带企图风云再起。清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密电地方官吏严加防范。这时,湖南争路风起云涌,统治者犹如惊弓之鸟,“甚为惶恐”,只得传知警道桂龄暨中路巡防队统领侯补道员跃金饬令,转饬各段认真严密稽查,令“添派军队、警队不分划夜轮流梭巡,革靴、号令之声彻夜不绝”(注:《民立报》,1911年6月19日。)。 同时下令禁止集会,取缔印刷店;信行邮局检查军学界往来函电,刊登广告须经巡警道派人核阅;并出示悬赏举发缉拿私刻传单的学生;派遣密探暗中查访,凡有煽动风潮者,按名访拿等。整个长沙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强大的反动势力压制之下,省城斗争风潮渐趋平息。起义后几个月的广州城风声鹤唳,阴霾难散,不时还传出革命党人将攻城的消息,人们纷纷出城逃避。警道不敢怠慢,特密派侦探队分段暗查,并于晚间会同各区警员赴各旅舍、栈房查察有无新到住者,并记明其来历情况,以防意外。张鸣歧还亲自拨派北较场第一队警察兵十余人,并派姓刘排长一人前赴观音山脚;第二队警察营驻扎,“以资侦缉而保治安”。又派警兵搜查炸药,以防不测(注:《草木皆兵之广州》(三),《民立报》1911年8月4日。)。可见,革命形势的咄咄逼人,弄得统治者惊魂不定,只好借助国家强有力的工具警察进行弹压,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清王朝的末日为时不远了。在保路同志会的倡导下,掀起大规模的罢市、罢课风潮,尤其成都积压着大量外地涌来的群众,社会秩序呈难以控制之势。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赵尔丰利用巡警道劝解商人开市,并派巡警、巡防军、新军进行戒严巡逻。警道采取与地方绅商联合维持秩序的办法,发起官绅商学界联合维持保安会,研究开市之前以及奉旨后社会秩序的维持问题。警道发出通知:“由各街公举三、四公正明白的人,朝夕与区官接洽。街中有暴动者,街众见之,则一面劝阻,立即报知举出人,与巡警劝阻之,不听,则处理与法。”(注:《川路股东之风云风》,《民立报》1911年9 月13日。)各协会对巡警也进行争取,认为“争路破约,吾辈爱国之天职;保守秩序,吾人本分之义务。惟权力有限,今得贤长官筹以吾辈同巡警共保之法,必能达我文明争路之目的矣”(注:《川路股东之风云风》,《民立报》1911年9月13日。)。 这种由警绅配合共保社会秩序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失控局面。随着运动的发展日益深入,统治者深切感到只有诉诸武力镇压才能维护统治局面。于是,立宪派和广大群众的叩头请愿最后换来的是赵尔丰的血腥大屠杀,许多群众纷纷倒入血泊之中,“督署院址,陈尸累累”就是真实写照(注: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83页。)。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 横冲直撞,践踏群众,死伤者难以数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封锁交通邮电,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各地群众在成都发出的“水电报”的警报下,纷纷揭竿而起。值得注意的是,清王朝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民愤,连巡警也甚为不满,部分巡警开始觉醒。保路运动特点之一在于重视群众的宣传工作,金堂县一次演讲会讲到川路岌岌可危时,“在场之巡警莫不痛哭”,赵镇警务长易静安亦“泪湿官衣”(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4、35号。)。这些“巡警和陆军大都是受过教育的四川人,对保路同志会抱同情态度;他们曾经宣布,打算拒绝对本省同胞开枪射击”(注:《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9页。),“不过限于军令不能不服从其长官之命令耳”(注:《成都特别通信》(一),《民立报》1911年9月15日。)。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 为此后的光复中倒戈转向革命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正当四川保路运动轰轰烈烈高涨之时,鄂督瑞澄以“川事危迫,关系甚大,未可忽略”,特饬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警道王履康等军警头领人物商讨对付办法。为全力加强警戒,他们采取兵警合力分配地段布控整个城市网,二十九标巡警中区管督辕至司门口长街一带,三十标与巡警前区管阅马厂、大朝街、望山门一带;四十一标与巡警前区第三分区管大东门、大东岳庙、洪山一带;马队八标、炮队八标与巡警上区管十字街、保安门、新桥、王惠桥一带;辎重八营与巡警后区管平湖门、黄鹤楼、汉阳门一带;混成协炮工辎三营与巡警下区管武胜门、筷子街、小东门一带。规定下午七点钟起,上午5点钟止,巡警每班4人,陆军每班16人为率。沿江一带,上自白沙洲,下至新河,均归巡查队稽查(注:《时报》,1911年8月3日。)。还传谕各城门守城巡警:闭城后,除督院关于紧急公文外, 其余均不准开放。 并通饬各警区巡警在夜12点时,遇有未点灯笼行人,细为盘查。并派探警四处刺探消息,学社、客栈成为严密稽查的重要对象。当时武昌已有一些革命党人准备起义,有时还与巡警发生正面冲突,革命形势如弦上之箭有一触即发之势。不管清政府防范多严,仍未能遏制辛亥首义在武昌的爆发。
首义冲击波极大地震撼了全国各地。统治者企图在各大中城市进行全面戒严阻止革命浪潮的层层涌进。在上海,第一路巡警分局巡官、巡长督带巡警每日进行军事操演,“以期有备无患”(注:《鄂乱中上海巡警》,《民立报》1911年10月15日。)。南市加紧梭逻,保护治安。安庆遇有形迹可疑者,立即将其行李衣箱打开检查,轮船码头水巡逻对下水上岸之人皆“盘诘尤严”(注:《鄂乱中之安庆》, 《民立报》1911年10月20日。)。京师更加手慌脚乱,外城巡警总厅指示:“在京各报馆,于此次鄂省匪徒倡乱情事暂缓登载。”(注:《北京政府方寸乱》,《民立报》1911年10月20日。)因形势吃紧,原有巡警不敷分布,只好将高等巡警学堂学警110人先行调回,分拨各区队加强警力。 灰厂至西长安门一带右一区,原有三岗警卫队,原有六岗准备增到十岗。摄政王五府前,除每日值班及赴府有事者外,其余车马一律禁止通行。还抄封了一些报馆,企图遏制社会反应,阻延革命浪潮的蔓延。天津警道也令南段各分区,每区挑精壮巡警20名,共挑出250 名以便革命蜂起时可以进行弹压。
在革命浪潮的巨大冲击之下,统治阶级土崩瓦解,许多巡警看到腐朽的封建王朝末日已到,不愿为其卖命,他们对于清廷的反动行径“均极反对而又不敢明言,恐遭区官重责。现已秘密结盟,俟有乱起即行解散”(注:《革命声中之天津》,《民立报》1911年10月26日。)。有的在革命党人的开导下,开始倒戈转向革命,成为革命势力的一部分,并在部分地区光复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上海为例,起义前,驻守吴淞、上海一带军警共10000余人,在革命党人陈其美、李燮和的策动下,“淞沪两地军警皆静待后命以应起义”(注:《辛亥革命》(七),第42页。)。为后来起义排除了主要的军事障碍。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战役中,在上海商团、敢死队、起义了的上海军警三者当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军警。南汇县城起义中,城内巡警当即在局内树起白旗打开城门。宝山起义中,吴淞巡警与盐捕营兵组成一支队伍径入县署,拘捕了知县。有人评价道:“上海起义是在中部同盟会、光复会上海支部共同领导下,革命党人领导的敢死队、上海商团、起义后的上海军警等武装共同努力下取得胜利的。”(注: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4页。)他们还加入民军,补充军队不足, 有的甚至参加光复南京的革命军的战斗,成为冲击末代王朝的重要力量之一。
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较早重视对巡警的争取工作,如武昌发布了《通告各省城乡地方巡警文》,上海有《军政府告巡警文》。广东军政府的文告指出:“本军政府担任光复之重任,指日即率大举,深恐饥寒无告之民,乘间窃发,施其抢劫之手段。而本军政府军事旁午之际,势难兼谋并顾。所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持地方之安宁秩序,皆唯我同胞巡警是赖。理应通告各省巡警父老兄弟,共谋同胞之幸福,方不负本政府吊民伐罪之本意。凡我义师所到之处,为地方巡警者,上至官长,下至巡警,左手均袖以白布,局中高悬白旗,晓谕安民,以示诚意。其守望巡逻之规则,官弁长警之薪饷,概照向章办理。至义旗将到,切勿自相惊恐,畏缩不前,是为切要。倘临事之时,官警弃局先逃,置人民于不顾,致使同胞受掳掠之害,本政府惟有派探拿获,以重治罪。此深望亲爱同胞巡警所鉴谅也。”(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1—132页。)这基本上代表了军政府对待巡警的基本政策,这有利于革命党人团结旧营垒中的阵营由反革命向革命方向转化。为了稳定社会治安,一些军政府还下令地方绅商续办巡警,有的将地方民团改编巡警等加强警力,保证已被打乱了的社会秩序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减弱社会振荡的幅度,为各地光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见,巡警作为清王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受到革命威胁时,他们充当抵御的工具,帮助扑灭革命烈火的蔓延。但是,武昌起义前后,他们当中不少倾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同情革命到支持、参加革命。
综上所述,巡警的出现,给清王朝增加了一支准军事力量,并在对付革命浪潮中发挥过强化作用。在学界风潮中,统治者利用巡警镇压青年学生的请愿示威,平息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资产阶级革命派每次发动反清起义后,他们又充当清政府的鹰犬,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加强警戒,成为维护专制政权统治的得力工具。巡警与新军都是清政府编练出来的新式武装力量,但他们在武昌起义前后的表现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革命中纷纷作鸟兽散,转向革命比较少,后者则相反,他们成为摧垮清政府的主力之一。主要原因有:其一,巡警大多是旧式营兵制勇改造而来,文化素质较为低劣,革命派基本上对他们没有象对新军那样进行宣传、组织、争取。其二,新军的俸禄直接由政府财政拨给,而巡警的薪饷主要通过士绅筹集,士绅拥有控制巡警的相当部分权力。在革命爆发后,一些地方的士绅继续发给巡警薪饷,让他们维持社会秩序,有的甚至参加革命队伍。另外,巡警比新军腐败、缺乏集中性等方面也不应忽视。总之,革命后,巡警的纷纷解散,表明专制政府对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运作不灵,部分巡警倒戈转向革命,有助于加速皇权政治的彻底崩溃。一句话,清廷设巡警、练新军是为加强其统治,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培植了自己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