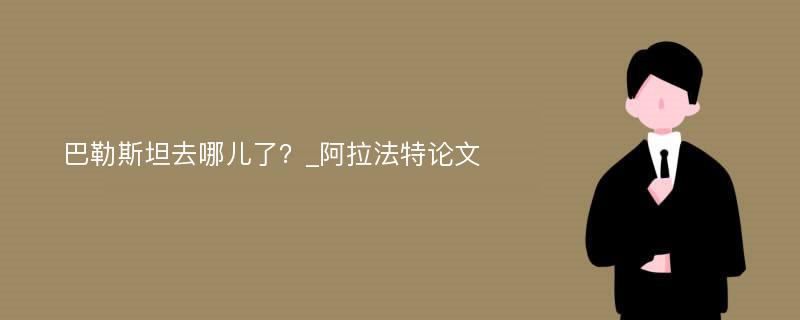
巴勒斯坦向何处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勒斯坦论文,何处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媒体中的热点,今年以来更是如此,今后一段时间恐怕也将成为 决定巴勒斯坦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半个多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为了恢复民族权力 、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进行了一次次的抗争,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挫折,遭受了各种各 样的痛苦,一些处于绝望中的巴勒斯坦人甚至不惜以死相拼;其对手以色列在大国的支 持下,自恃拥有强大的战争机器,动用最先进的坦克、飞机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了一次 次的打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留下了满目疮痍和累累废墟。尽管巴勒斯坦人民得到世 界大多数国家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下,迄今为止道义并没有战胜 强权,巴勒斯坦民族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危机。
阿富汗化的可能性
9·11事件之后,以色列当局利用国际上形成的“反恐势头”,利用媒体丑化巴勒斯坦 自治机构,同时加紧对巴勒斯坦的打击和镇压,企图使巴勒斯坦问题“阿富汗化”或“ 塔利班化”,即试图通过媒体将所有反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行为指称为“恐怖主义行为 ”,并将其同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系起来,进而企图将巴勒斯坦民 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机构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尔后“名正言顺”地像美国打击塔利 班那样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机构彻底铲除。
然而,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图谋并没有实现。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并没有认同以色 列的作法。沙龙执政以来,不断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残酷镇压,先后实施“百日安全计划 ”、“定点清除政策”等黩武主义政策,出动先进的坦克、战斗机随意轰炸、摧毁巴勒 斯坦民族权力自治机构控制区内的标志性建筑物和各种重要设施、目标。9·11事件之 后,沙龙政府利用美国组织国际反恐联盟、打击恐怖主义的时机,指责巴解组织和巴勒 斯坦自治机构涉嫌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行动,加紧对巴勒斯坦方面进行军事打击,刺杀巴 勒斯坦高级领导人。今年3月,当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自治机构驻地进行野蛮轰炸、 对阿拉法特进行围困并断电、断水10多日的时候,世界各国纷纷谴责以色列的非人道做 法,许多国家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以色列军队野蛮行径的示威游行,欧洲一些人权组 织和媒体将以色列当局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做法称为“种族清洗”。在声援阿拉法特的 队伍中甚至也不乏犹太人。虽然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控制区的7个主要城镇,但 是并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更没能征服巴勒斯坦人民。
以色列企图把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机构和巴解组织丑化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做法没有 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最终没能将巴勒斯坦问题“阿富汗化”。这是因为,巴勒斯坦人 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恢复民族权力的斗争是20世纪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是 尚未实现其斗争目标的一部分。所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有其正义性、合法性。尽管 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对此均无异议,但是媒体在谈及巴勒斯坦问题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个十 分关键的性质问题。实际上,尽管美国一直采取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但是联合国大会、 安理会还是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主要有:1948年联大通过关于 成立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决议(该决议还涉及耶路撒冷国际化、难民回归与赔偿等问 题);1949年联大通过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决议;1950年专门成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 难民救济工作署;1967年安理会通过了关于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战争中占领土地的24 2号决议;1969年安理会通过了进一步明确关于耶路撒冷地位(不承认以色列改变圣城地 位的做法)的决议;1971年联大通过了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重申不允许通过武力来占领 他方领土的原则);1974年联大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 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难民回归并获得赔偿的权利, 有权采取一切手段恢复他们的权利);1975年联大通过关于邀请巴解组织参加谋求中东 和平的决议和成立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决议;1976年联大通 过关于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成立巴勒斯坦国的计划;1977年第32届联大会 议决定把每年的11月29日定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1980年联大通过要求以色 列撤出全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决议;1982年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 杀,紧接着联大特别紧急会议也通过了决议谴责以色列的暴行;1988~1989年联大、安 理会先后4次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驱逐、镇压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1990年安理会通过 决议谴责以色列在圣殿山事件中的暴行;1992年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驱逐大批巴 勒斯坦人;1994年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以右翼极端分子制造希伯伦惨案;1995年联大通 过决议认定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为非法;1997年联大、联大特别紧急会议先后通过3项 决议反复重申在被占领土上特别是耶路撒冷建立移民定居点是非法的,等等。今年3月1 3日至4月19日不到40天时间,安理会就巴以两国和平共处、支持沙特和平方案、要求以 色列撤军并解除对阿拉法特的围困、派调查组了解以军在杰宁的屠杀真相等问题通过了 3项决议。联大和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表明,50多年来联合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认定巴勒斯坦难民拥有返回家园和获得赔偿的 权利,谴责以色列驱赶、镇压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暴行。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国际 组织的一贯立场和它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从国际法的角度赋予了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 族权利而进行的抵抗和斗争所拥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尽管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尚 未取得最终胜利,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动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所具有的正义性与合法 性。这也是以色列无法将巴勒斯坦问题“阿富汗化”的最根本原因。
能否架空阿拉法特
沙龙政府对巴勒斯坦进行一系列残酷打击的另一个目的是,拖垮、架空目前以阿拉法 特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权力机构,扶持一个以色列认为“负责任”的(傀儡)政府, 最终“取消”巴勒斯坦问题,至少也要推翻奥斯陆协议达成的和平框架,为以色列牟取 更多的利益。今年6月布什提出的“中东和平新倡议”也迎合了以色列的这种政治需要 ,要求巴勒斯坦进行改革,选举新的领导人。(注:美国社华盛顿2002年6月24日讯。) 此外,巴勒斯坦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出于对长期未能实现和平的现实不满或渴望摆脱长 期贫困的生活,要求进行改革。
以色列和美国要架空阿拉法特、要求更换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做法,无疑是不明智、也 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力的正义斗争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共同事 业,并非阿拉法特的“家事”。因此,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能否继续推向前进 并不完全取决于阿拉法特的去留,而最终取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深谙中东事务的 美国政界人士和资深学者也纷纷指出了布什中东和平新倡议的种种弊端。例如,负责中 东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墨菲(曾多次出任过美驻中东国家大使)认为,“一切都 是强加于人的,并且有着苛刻的条件。”“如果巴勒斯坦人全然不顾美国要求他们抛弃 民族运动偶像的压力,让阿拉法特连任,那么布什将会面临两难的境地。”(注:《纽 约时报》,2002年6月25日。)负责主持制定《米切尔报告》的美国前参议员米切尔认为 ,“布什要求更换阿拉法特有可能引火烧身,如果伊斯兰抵抗运动或伊斯兰激进组织的 代表当选巴领导人,中东局势将比现在糟糕得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知名学者奥汉龙 也认为,“布什对阿拉法特进行封杀,是作出了一个很糟的选择”。(注:新华社华盛 顿2002年6月26日讯。)
今年7月中旬在纽约举行的有关中东问题的美、俄、欧盟、联合国四方会议上,布什想 架空阿拉法特的做法也没能得到支持。会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 和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都表示,将继续承认阿拉法特为巴勒斯坦 合法领导人的地位。
毫无疑问,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机构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拥有最广泛 的群众基础,代表着最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将巴 解组织认定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注:参见王京烈:《阿拉法特》,长春 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1974年巴解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员,1976年巴解成为阿拉 伯国家联盟和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员。阿拉法特领导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力斗争的 历史也经历了从早期武装斗争、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到以 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主(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重大转变与战略调整。这种转变与调整 充分说明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领袖,是举世公认的。阿拉法特领导巴 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当然不符合、也不可能符合以色列强硬势力企图扩大并 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战略目标,同时也不符合美国目前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这是以 色列和美国极力想架空阿拉法特的主要原因。
阿拉法特本人在面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强大压力时,也做出了明确的选择。阿拉法特在 接受埃及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如果巴解执委会再次决定推选我作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候 选人的话,那我将参加竞选。”(注:《环球时报》,2002年7月18日。)当然,巴勒斯 坦方面为了趋利避害,对布什的中东和平新建议也做出了适当的回应,诸如宣布成立临 时内阁、批准基本法、撤换安全部队的领导人以及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等。
由于阿拉法特本人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不尽人意,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或阿拉法特之 后的巴勒斯坦,早就是众说纷纭的话题。其实,这也是自然规律。
目前在巴勒斯坦政坛上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9个人(国外媒体称之为“潜在的阿拉法特 的接班人”):阿布·马赞,巴解执委会总书记,也是奥斯陆协议巴方设计师,阿拉法 特的密友;阿布·阿拉,巴立法委员会主席,根据立法,在阿拉法特无法履行职责时, 他可执掌大权60天直至选举出新的领导人;埃雷卡特,地方政府部长,负责同以谈判的 巴方首席代表;沙阿斯,计划和国际合作部长;拉布,新闻和文化部长;贾巴利,民事 警察司令,主要负责巴勒斯坦内部安全事务;巴尔古提,法塔赫在西岸地区的领导人, 曾领导被占领土的起义;拉琼布,西岸负责预警安全部队的领导人,参与了有关安全问 题的谈判;达赫兰,加沙地区负责预警安全部队的领导人,参与了2000年在戴维营举行 的巴以谈判。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是充满传奇色彩并拥有人格魅 力的老一代领导人。而在上述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中,虽然既有“元老派”,也有“务实 派”和“新生代强硬派”领导人,但尚无任何人可以同阿拉法特的威望相比拟。因此在 阿拉法特之后,巴勒斯坦政府将更多地依赖“体制”动作。这也是民族独立国家政治发 展的一般规律。
当然,即使在阿拉法特之后,以色列也不可能扶植起一个让以色列认为满意的政府。 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曾经在黎巴嫩南部扶植建立了亲以的“南黎巴嫩军”,这些 人被黎巴嫩人视为出卖民族利益的“黎奸”;2000年当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出时,这些人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那些试图出卖巴勒斯坦民族利益的人。其二, 即便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扶植起一个傀儡政府,巴勒斯坦人民也不会任其摆布,巴勒斯 坦人民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正义斗争不会就此终结。如果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冲 突、流血将依然如故。
就目前情况来看,由于以色列不断加紧对巴控区的军事打击,进一步激发了巴勒斯坦 人民的抗以、反以情绪,导致激进势力上升。如果在这种条件下民主选举领导人,无疑 激进势力将得到更多的拥护,新政府可能将更趋强硬。
巴勒斯坦的前途
“阿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将几十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肯定 将在那里引起根本变化,致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陷入痛苦境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世界版图上已不再有无人居住的空地。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 悲剧。犹太人无论选择在哪里定居,迟早都会和当地人发生冲突。民族国家的成立意味 着非正义行动,本地人或者被吸收或同化,或者被大批屠杀和驱逐。”(注:沃尔特· 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阎瑞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26、727页 。)这是犹太史学家沃尔特·拉克30多年前对阿以冲突历史根源的论述。不幸的是,最 近两年巴以之间的暴力冲突再一次印证了沃尔特·拉克的论述。阿以之间因矛盾引发了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血冲突和战争,但是冲突和战争并没有解决阿以之间的矛盾。
今年以来,以色列军队持续对巴勒斯坦控制地区进行更为残酷的军事打击,镇压巴勒 斯坦人民的反抗,任意摧毁包括广播电视台、机场、自治机构办公楼等巴方标志性建筑 物和平民住宅等。4月在攻占西岸城镇盖勒吉利耶时,以色列对没有军队的巴控区甚至 一次出动了100多辆坦克。(注:参见中国新闻网,2002年4月1日。)7月22日,为了刺杀 哈马斯军事领导人谢哈德,沙龙命令以色列空军派出F—16战斗机,对谢哈德在加沙的 寓所发射了1吨重的激光制导导弹,当场炸死16人,其中包括一名只有两个月大的婴儿 。以色列的做法遭到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甚至一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谴责了其暴力 行径。以色列炸死了一个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两天后加沙却有25万人参加了谢哈德的 葬礼。(注:《环球时报》,2002年7月25日。)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不仅没有征服巴勒斯 坦,相反,激起愈来愈多的反以抗以活动。为了争取民族权力和生存权,巴勒斯坦人不 惜以死相拼。他们中间不仅有成年男女,甚至还有十几岁的男女学生。“无自由,毋宁 死!无尊严,毋宁死!”或许这也是巴勒斯坦人面对以色列强大战争机器时无奈的选择。
今年3月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以沙特方案为基础的《贝鲁特宣言》。《宣言》提 出:阿拉伯国家将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保证其安全、实现关系正常化为条件,换取以 色列撤出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领土,承认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公正解决难民问题。《宣言》的内容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的有关解决中东问题的 决议保持一致,并且得到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欧盟、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普遍支 持。鉴于《贝鲁特宣言》是阿拉伯国家集体作出的决定,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终将成为解决阿以冲突的基本框架。
《贝鲁特宣言》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将做出重大妥协,为实现和平承担巨大的牺牲。根 据联合国1947年181号分治决议,巴勒斯坦将建立两个国家:犹太国、阿拉伯国。犹太 国面积为1.45万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面积的55%;阿拉伯国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 ,约占巴勒斯坦面积的44%;占地187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地区为国际共管。第一次巴勒 斯坦战争后在1949年7月实现了停火,当时的停火线被称为“绿线”,以色列在绿线内 占领控制的地区约为20697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面积的78%。1967年战争前,巴以( 阿以)双方的控制区基本上以绿线为界。据此,《贝鲁特宣言》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将做 出重大的妥协,将让出约22%的土地。与分治决议相比,以色列将多得到约23%的土地。
有鉴于此,在阿拉伯国家再次发起“和平主动行动”的情况下,如果以色列政府能够 审时度势,改变其扩张主义的强硬立场,实现和平就不是不可能的。
曾是西亚一隅小国的以色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甚至拥有了 核武器)。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以色列就已经成为阿以冲突这一矛盾中的主要 方面,决定着矛盾冲突的发展态势,掌握着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注:参见王京烈: 《论阿以冲突矛盾中的角色转换》,载《以色列动态》,1994年第5期。)目前,以色列 掌握着开启和平之门的钥匙。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政府采取相对灵活的政策时, 中东和平进程就能取得某种进展;反之,和平进程就陷入僵局、甚至出现倒退。例如沙 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不仅使和平进程发生重大倒退,还使中东局势急剧 动荡。尽管阿拉伯国家早已向对手摇起了橄榄枝(1982年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发表的《 非斯宣言》表明了阿拉伯国家对以战略的整体调整),但是,自恃拥有强大军事力量、 并有美国全力支持的以色列并不为之所动。沙特方案是阿拉伯国家再一次向以色列摇动 橄榄枝。尽管以色列掌握着开启和平之门的钥匙,但它并没有改变其强硬立场。为了夺 取更多的利益,以色列不愿归还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不愿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力 。这是解决阿以冲突的主要障碍。然而,以色列不可能靠暴力长期统治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因为这与以色列立国基本原则(犹太属性与民主原则)是相悖的。
对和平的认识是影响未来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经过半个世纪的生死搏斗与血腥 冲突,巴以双方都对对方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认识到和平是共同的需要和利益所在。但 是对实现和平的方法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影响和平进程极为重要的原因。
果尔达·梅厄在谈到暴力冲突时曾说,“当他们爱孩子的情感胜过对我们的仇恨时, 和平就实现了。”这种观点代表了目前以色列右翼势力的思想。他们想和平,但是不愿 放弃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和军事打击,不愿放弃已经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他们不想让 别人对他们心怀仇恨,但是在被占领土上的暴力镇压和军事打击除了播下仇恨的种子, 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你想要别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待人。”这是源自古老《圣经》的一句训言,虽 然经过近两千年的风风雨雨,却依然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它反映了人类淳朴的思想 情感和人际关系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试想,如果种下了仇恨,怎么可能收获友好。所以 ,为了和平,请不要播种仇恨!
巴勒斯坦将向何处去?我想实现和平是最佳的也是惟一的选择。巴勒斯坦人民要求在公 正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并能够尊严地生活。以色列方面则取向于按现有实力来解决 冲突、实现和平。利库德集团的主张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它提出“以和平换和平”的主 张来取代“以土地换和平”的方针,其实质是在保持现状、不归还已侵占的阿拉伯领土 、在获取更多实惠的基础上实现和平。(注: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以色列,对如何 实现和平都是众说纷纭,有许多观点和想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占主导地位的则是 文中所述。)
人类文明已经进入21世纪,无论当今世界还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和冲突,和平与发展仍 是时代的主题。巴以双方当然不会永远停留在血腥与暴力中。那么,是巴勒斯坦人民为 此承受更多的牺牲、蒙受更多的屈辱而实现和平,还是以色列政府审时度势放弃占领的 巴勒斯坦领土而实现和平呢?回答这一问题的只能是巴以双方。或许他们还需要更长时 间来认识对手,认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孰轻孰重,或许他们还需要等待人类理性之光 驱散战争阴霾,重新照亮古老的加南地。不过,时代发展的步伐将促使双方及早做出历 史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