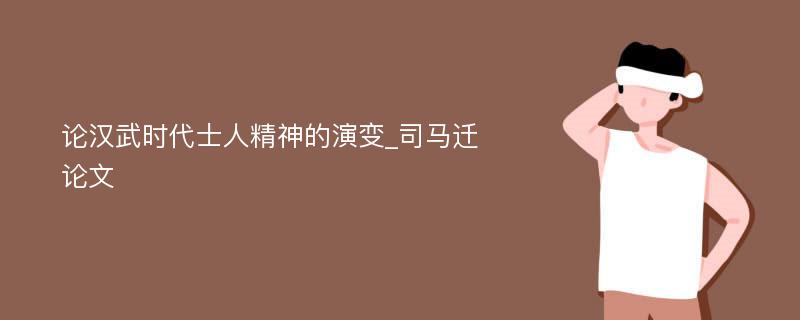
论汉武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汉武论文,精神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士人精神在秦汉之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士人由王师君友沦为弄臣家奴,失去了人格的平等与自尊;由天下游士变为一主之臣,失去了自由意识;由布衣之士变为仰禄之士,失去了自主性;由四民之士变为儒臣之士,失去了主体意识。士人精神的嬗变至汉武时代趋于定型。
宋人张耒云:“司马迁尚气任侠,有战国豪士之余风。”〔1〕由《史记》看,司马迁的个性气质与思想精神都深深植根于战国士人文化土壤中,他一生的心事都在追踪古代的国士风范。可是,汉代士人的生活环境与春秋战国时代已完全不同,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士人已有了新的要求。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这就使他的心态交织着种种矛盾。究其根源,就在于从战国到秦汉这一历史过程中,士人的身份、地位、作用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士人文化精神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下笔者试从四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一具体论述。
由王师君友沦为弄臣家奴,地位下降,失去了人格的平等与自尊
得士者得天下,失士者失天下,这是春秋后时代的共识,士的多少与优劣已成为各国国力的标志,各国都大兴求士之风,士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史记》记载:“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2〕各国君主对士人不仅要待之以礼,而且还要以士人为师。士人虽为君王之臣,但在君王面前仍有自己的自尊,士人与君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魏文侯说:“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3〕对于无权无势的士人来说,唯有保持自尊才能为世人所重,并提高自己的生存价值。孟子说:“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4〕在士人的“去就”之道中, “礼貌未衰”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谓不食“嗟来之食”也是这一心理的反映,这是在西周宗法等级礼制解散之后,新兴士人阶层所追求的新的平等之礼,也是时代赐给他们的殊荣。
但是,到了司马迁时代,士人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奠定中国封建统治模式的汉武王朝,是以帝王专制为核心的。它需要以严格的等级制度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它要使所有的人都成为这个等级秩序中的臣民,至高无上的皇帝是绝对不允许其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已向士人开刀,如制定《游士律》搞焚书坑儒等,他主要是从肉体上除掉自己不喜欢的角色,汉武帝采取的手法虽与秦始皇不同,但本质上仍是一致的。到汉武帝时汉家大一统局面已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王权的力量,而不再是人才的力量。士人的社会地位则由先前的王师君友下降为家臣私吏,由人才沦为奴才。在司马迁笔下汉武时代的高官显贵都是奴性十足,如象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虽才华出众,又颇有政治谋略,可是也只能以介优滑稽的方式才能够在朝庭立足。又如《史记》记到:“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丞相弘燕见上或不冠。”〔5〕(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6〕汉武帝已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求得士人为己所用,士人在君王面前也无自尊可言,唯以顺上为务。
汉武帝也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曾“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为数”,但是,他首先需要的是绝对服从自己的奴才,在才与忠两者中,忠是第一位的,士人一旦与此相迕则变得毫无价值以至被视若草芥。汉武帝身边一批儒士重臣往往只是因一言不合则失了性命,如窦婴,灌夫,主父偃等都是这类悲剧人物。《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武安者,貌侵,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7〕这说明王权统治者就是要以剥夺天下的自尊来强化王权的尊严。司马迁与同时代士人一样,一方面为汉武盛世气象而振奋,积极投身于汉武王朝政治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自尊心而自卑,他这一矛盾心态正是他那个矛盾时代的反映。
由天下游士变为一主之臣,身份改变,失去了自由意识
春秋战国时,天下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如此的历史背景则为士人活动提供一个宽大的舞台,那个时代游士之风大盛,士人可以自由地从一国到另一国活动,不必受一国之主的控制,也不必只仰靠某一个人。臣与君并没有固定的依附关系,士人对君王只有为知己者死的道德义务,并没有绝对服从的君臣“大义”。在思想上,他们也没有定于一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一切都是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他们可以取己所需,宣传任何一种观点。如苏秦先持连横之术游说秦惠王,不成之后,又主合纵之说,支持山东六国。当时他就被人称为“左右买国反复之臣也。”可是他在燕“益厚遇之”,在齐“齐宣王以为客卿”。〔8〕《史记》又云:“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9〕可见,多国并立的政局, 使士人们获得了择善而“游”的人生自由,也使他们在思想上取得了百家争鸣的言论自由。
秦汉之后,士人的这种自由却完全丧失了。封建专制的本能就是要使所有的士人都必须服从帝王这一唯一的中心,在这一点上它是不可能给士人一丝选择自由的。汉初诸侯王尚有养士之风,到武帝时私家养士已与叛逆同罪,如桑弘羊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或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及叛逆,诛及亲族。”〔10〕卫青也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客宾,天子常切齿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11〕这样,天下游士在汉武时代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只能成为汉武帝的一主之臣。对那些游离于专制关系之外的士人,汉武帝则用严酷的法网对附他们。如诛杀游侠郭解、淮南王谋士伍举就是如此,这就在政治上剥夺了士人的人生选择权。在思想言论上,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剥夺了士人思想言论自由,翦除与专制相违背的声音。如颜异对汉武帝与张汤“造白鹿皮弊”这类欺民之举有异议,竟以“腹诽”之罪论死。士人已不能自由的“各著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而只能引经据典替皇上旨意作注。司马迁指出:“是上方向文学,(张)汤决大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廷尉絜令,扬主之明。”汉武帝并不需独抒己见的思想家,只需要借古颂今的御用儒生或润色鸿业的宫廷文人。司马迁追慕游士之风,向往游士的自由境界,力建一家之言,可结果只招致更大的不自由,从肉体到精神都背上了沉重的压抑感,他的心态总是在求取功名的热情与失去自由的痛苦矛盾中起伏。
由布衣之士变为仰禄之士,生存方式改变,失去了对命运的自主性
在春秋战国之际“士农工商”中的士是既无世袭之位,又无恒定资产的布衣,他们所能凭借的只是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这种处境促使士人劳心苦志刻意求道,对环境、对命运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如孔子就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作为士人的人生信条。又如苏秦早年落魄,受兄弟嫂妹妻妾讥笑,后游说天下,成功后叹道:“且使我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他们一无所有,无所依托,唯有靠个人奋斗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存在价值,获取尊荣。可以说布衣处境的外在压力与知识的内在动力使士人阶层生来就有一种改变自身地位的进取意识与把握命运的自立精神,同时,各国求士的目的在于解除国家危机或争霸天下,严峻的现实要求统治者必须按才录用,论功行赏。如“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14〕士人的才德不同,享受到的尊荣也就不同。因此,不安于现状,主动向命运挑战也就成了那个时代士人特有的生存方式。
汉武时代,由于天下之士都要归附到汉天子一人脚下,他们的命运只能系于汉武帝一人之身。正如司马迁所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15〕士人全凭遇合天子这一条路才能展现出来,他们被纳入封建等级秩序之中,只能沿着精致的仕途台阶一步一步地爬行,那种由布衣到卿相的传奇再不可能出现了,那种主宰命运的自主精神已丧失了。作为仰禄之士,他们依托封建吏制而生存,已获得超出农工商的社会特权,他们已失去了改变命运的外在压力。
东方朔《答客难》曰:“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16〕扬雄在《解嘲》中说:“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无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无所患……向使上世士处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17〕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需要的是超稳定的思想与个性,它要求士人必须安分守已,听天由命,力斥不安现状反抗命运的思想与举动。士人只有以老庄知足无为的思想来安慰灵魂。如《史记·日者列传》中司马季主感叹到:“故君子处卑隐以群众,自匿以群伦,微见德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18〕先秦士人那种蹈厉奋发的意气至此已化解为无可奈何的虚静之心,安身之道。
不过,汉武帝广招贤良文学之士,又促使更多的士人挤身宦途,盛世气象又不断激发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建功立业的渴望。但是,这种守成求稳的生活环境,这种一切都靠皇上恩典的生存方式,使得个体的生命张力总是受到君主意志的压抑。面对深不可测的宦途与倏忽即变的命运,他们总是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尤其象司马迁这些抱负至大的有志之士,遭遇更为悲惨,对命运之神尤为困惑。他在《悲士不遇赋》中叹到:“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因此,对现实功名的积极追求与对不公正命运的无能为力则成了他矛盾心态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由四民之士变为儒臣之士,文化精神嬗变,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
先秦士人与农工商人一样都是有职之民。《谷梁传》成公元年条曰:“上古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孟子亦云:“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是以自己的知识思想作为生存手段。《孟子》记曰:“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20〕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士人阶层也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与职业道德,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它包括士人权力和士人义务两方面。所谓义务就是指积极为他人谋利解难的社会责任和坚守信仰、知恩图报的道德责任。孟子所说的“居仁由义”就是其中的突出表现。所谓权力主要包括享受人格的尊严与平等,具有不受权势约束的自由,以及应得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地位。即如司马迁所言:“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21〕对这两者各家的解释与要求不尽相同。如道家更重个性的自由,杨朱之说更重自身的权利,墨家多重个体的社会义务,而法家则完全否定个人的权力,儒家在偏重社会责任基础上也不排斥个人的权力。先秦时期的士人文化精神在总体上都体现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他们在极力张扬人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责任感的同时,并不晦言个人的权力与价值,作为四民之中的一个成员,他们还不断地向不公正的社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如李斯言:“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22〕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也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士人的主体价值观。孔子既说:“事君能致其身。”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3〕在君臣关系上,他也没有放弃士人的自身权力与人的主体意识。孟子笔下的士人形象则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4〕这更是将士人的主体精神推崇到极点。
从汉初到汉武,法、儒、道三家几经较量,儒家思想最终取得了正统地位,成了专制王朝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所谓的“礼”。为适应大一统专制王权的需要,汉儒将这种伦理文化更加狭义化了,并以此对士人文化传统加以改造。董仲舒云:“《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25〕他是以君神合一的观念在极力张扬君权的神圣性同时,抹杀了士人自身的主体价值。他还说:“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下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凶其天,臣乱则凶其君。故为天者务刚其气,为君者务坚其政,刚坚然后阳道制命,……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供设饮食,候视灾疾,所以致养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伏节死难,不惜其命,所以救穷也。推进光荣,袤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是故地明其理为万物母,臣明其职为一国宰,母不可不信,宰不可不忠。”〔26〕在他这套君刚臣柔,君坚臣顺,君尊臣卑的人格规范中,士人的主体意识就被这种君臣大义过渡掉了。至此,先秦时的士民文化精神已嬗变成以王权为轴心的儒家士大夫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的士民意识与西汉后的封建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士人文化的两种历史形态,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武时代的士人阶层正处于这两种士人文化的交替时期。在司马迁笔下,这两种文化演变的痕迹及冲突也被反映出来了。如灌夫、汲黯就属于春秋战国士民文化的继续,“(灌)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交通,无非豪杰大猾。”〔27〕“(汲黯)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结,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28〕在他们的人格形象中具有明显的游侠之气,最终只有被汉武王朝所抛弃。又如公孙弘,张汤之流则属汉儒士大夫文化的定型人物。“(公孙弘)其行敦厚,辨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文缘饰以儒求。”〔29〕“(张汤)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30〕他们已完全脱去了春秋战国的士民之气,因而成为汉武帝的心腹重臣。司马迁、郑边等人又可以说是这两种文化精神的过渡者,“郑边以任侠自喜。”〔31〕“然郑边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32〕他们是要以游士文化精神来完成儒家士大夫的使命,其结果必然是忠心不被察,有才不能施,而且由于士民的主体意识触犯了皇权的威严,反而会陷入更大的自卑中。“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人。”〔33〕专制的社会对士人的人格形象已作出了唯一的选择,双重文化的角色必然使司马迁心态交织着进取与失望的矛盾。
黑格尔说:“对中国人来说,他们的道德律正和自然律一样,乃是外来的实证命令,乃是强制权利和强制义务,或彼此之间的礼节。实体性的强性规定必须通过自由才会成为伦理的信念——而这样的自由在中国人那里是缺乏的。”〔34〕其实,以忠君济世为核心的封建士大夫精神是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对多数士大夫来说并不意味着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一种自觉的精神追求,历代士大夫就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以社稷之臣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尤其象司马迁这样的思想家更为自觉地将自身价值与王朝政治联系在一起,为王朝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乃至力呼疾号,强颜犯上。然而,由于这种人生思想的中心指向是王朝而非主体自身,士大夫的人生希望也就只能托于君王一身。因此,他们的忠心与良策就免不了与王权的专制独断发生冲突。为了完成士大夫的历史使命,他们只有以扭曲的人格形象来体现自身的生存价值。对他们来说“事君能致其身”,“致君尧舜”是一种神圣的选择,是人生真正价值之所在,而屈己事君,牺牲主体人格又是痛苦的。这就是历代士大夫矛盾心态的核心内容,它的产生固然有其渊远的文化源头,但秦汉后士人文化精神的转变,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汉武时代又可算是它的定型时期,太史公更是以其不幸的遭遇和饱含骚人之情的史家绝唱,将这种矛盾心态最强烈、最集中地表现出来,充分体现了士人文化的转变过程。因此,研究司马迁的矛盾心态及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特色是极有意义的。
注释:
〔1〕《张右史文集》卷五六《司马迁论》。
〔2〕《史记》第2345页中华书局82版, 以下所引《史记》原文皆据此本。
〔3〕《淮南子·修务》。
〔4〕〔14〕〔23〕〔24〕《孟子》告子下,万章下,尽心上, 滕文公下。
〔5〕〔6〕〔7〕〔8〕〔9〕〔11〕〔12〕〔13〕〔15〕〔16〕〔21〕〔22〕〔27〕〔28〕〔29〕〔30〕〔31〕〔32〕《史记》第3107页、2950页、2844页、2242页、2346页、2946页、3129页、2262页、 3191页、3206页、2429页、2539页、2847页、2951页、3110页、3112页、 3115页。
〔10〕《盐铁论·晁错》。
〔17〕《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第69页,中华书局62版。
〔18〕《史记》第3220页,吾从现代学者之说,认为《日者列传》非后人所补。
〔19〕《全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文》。
〔23〕《论语译注》中华书局80版第5页、30页。
〔25〕〔26〕《春秋繁露》第12页,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89版。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34〕转引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06页, 人民出版社5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