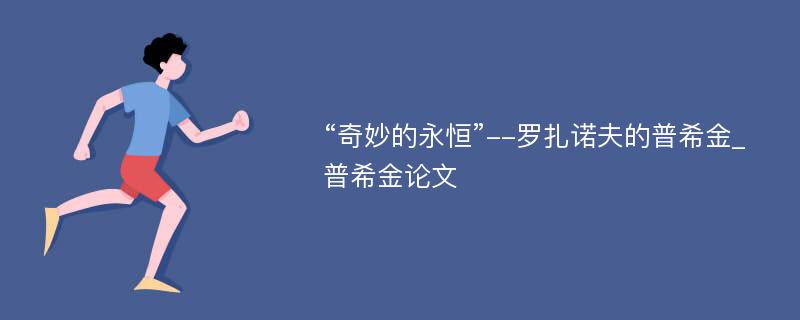
“奇妙的永恒”——罗赞诺夫的普希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诺夫论文,奇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5)06-0032-09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6.007 罗赞诺夫不仅是当时俄国新基督教哲学运动的风云人物,独具一格的文化狂人,他还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留下了丰硕的文学批评遗产,他曾论及罗蒙诺索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费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契诃夫、弗·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安德烈耶夫、阿尔志巴绥夫、勃洛克、库普林、高尔基、阿勃拉莫维奇等,以及歌德、卢梭、狄更斯等国外作家、各种文学流派和现象。不仅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开启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时代,他关于普希金、果戈理的论述颠覆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根基,而且他关于俄罗斯众多重要作家的论述,从自己新基督教哲学的角度全新揭示了俄罗斯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他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一批俄国宗教哲学家一起,开创了俄国文学的宗教哲学批评路径。 在这些俄国古典作家中,罗赞诺夫钟爱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是很矛盾?在他那里,普希金是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分裂。可是,他都爱,他都要,既要圣母理想,也要所多玛理想。是不是很像斯塔夫罗金?“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在两极中找到了同样的美,找到了同样的快乐’,感觉到圣母理想和所多玛理想同样具有吸引力。”[1]34但许多评论者都说他像老卡拉马佐夫。洛斯基说:“他的人格在许多方面是病态的,最明显的证明是他对性问题有不健康的兴趣。他可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2]437而别尔嘉耶夫则直接说,他“就是一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诞生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他身上有某种类似费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东西”[3]394。梅列日科夫斯基则批判罗赞诺夫性观念的疯狂和无耻:“在罗赞诺夫那里……是费多尔·巴甫洛维奇的‘戏谑’,无耻的戏谑。”[4]55他们对他有偏见?不理解?或只理解其一,不理解其二?他的同时代人对他有各种态度,赞同者有之:吉皮乌斯、霍列尔巴赫、杜雷林、列米佐夫;反对者有之:梅列日可夫斯基、普里什文、司徒卢威;批评者有之:别尔嘉耶夫、沃伦斯基、维·索洛维约夫。然而,他就是他,他爱普希金,他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他的两极。 不过,不止于此。这是他的“两极”,不是他的“两点”。两点是断裂,是不连接;两极中间有多少“点”?这就是他的全部?一根有两极的线?不,他不是线性的,他是一团,正如他自己说的混沌的一团,“我简直没有形式(亚里斯多德的‘形式’),‘一团’什么,或说‘乱麻’。……我是‘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仿佛‘还躺在母体中(一团)’”[5]20。可是,我们还是硬要找出他的两极,我们多么可怜,有什么办法?不然,我们只能对他缄默不语,一切文学标准于他都无效。我们只能姑且为之。 在我们的研究中,已经触及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有《罗赞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①,谈论得比较集中深入。而他关于普希金的论述,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目前只有四篇文章②谈到他的普希金,但所有这些只言片语加起来不超过2000字,并且一半集中在《俄罗斯白银时代普希金研究概观》(2000年)一文的两段文字中。同时,我们也仅译介他的一篇《重返普希金》③。这也难怪,就是在俄罗斯,也是到了2010年才出齐了他的全集30卷,对其个性的全面认识才有了可能。根据已发现的文献,他对普希金的论述多达二十多篇,如果仅从着笔的频率上看,甚至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还要多。 从1886年的第一部著作《论理解》开始,普希金就成为了罗赞诺夫写作的一个特殊对象,并伴随了他一生,其最后关于普希金的笔记写于1918年,几近他离世。根据普希金在罗赞诺夫著述中出现的情况,我们可以将罗赞诺夫的普希金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86到1899年。他有《普希金与果戈理》(1891),《“政府”的两种形式》《基督教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1897),《永远悲伤的决斗》(1898)。这一时期是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讲后逐渐意识到了“普希金主题”。第二个时期从1899纪念普希金诞辰百年开始到1900年代。他开始写普希金专论,有《阿·谢·普希金》《关于普希金的笔记》《论普希金科学院》(1899)、《普希金新论》《再论普希金之死》(1900)、《评伊万·谢格罗夫的书〈普希金新论〉》(1902)、《易卜生和普希金—布朗德和安哲鲁》(1907)。这一时期罗赞诺夫对普希金展开了自己独特的论述。第三个时期是1910年代,罗赞诺夫开始了普希金思考的新阶段。他有《普希金中学一百周年纪念》(1911)、《重返普希金》《莫斯科的普希金小屋》(1912)、《普希金和莱蒙托夫》(1914)、《论普希金的去世》《论莱蒙托夫》(1916)等。在这些论述中,罗赞诺夫对诗人的思考更为深入和全面,视诗人的悲剧不是某种性格的悲剧,而是整个个性的悲剧。 除了对普希金的专门论述,诗人的名字还经常出现在罗赞诺夫的其他写作中,如《论大法官的传说》(1891),《当首领不在的时候》(1910),《隐居》(1912),《文学流亡者》(1913),《落叶》(1913第一部,1915第二部),《逝水流年》(1915),《俄罗斯文学启示录》(1918)等等。在这些著述中,普希金的名字,普希金作品的援引,总是与罗赞诺夫试图揭示俄国社会生活及艺术的本质问题联系在一起。普希金的名字还经常出现在罗赞诺夫与斯特拉霍夫、列昂季耶夫、霍列尔巴赫、拉钦斯基、弗洛连斯基的通信中。书信这种体裁,使罗赞诺夫发现了最接近自己的那个普希金。他或是在别人的审视中理解自己的普希金,或是试图借助普希金说服对手相信自己论断的正确性。无论如何,普希金都不再仅是位诗人,而是携带了某种语义,使诗人超出了自己固有个性的界限,而成为艺术创作问题本身。 罗赞诺夫爱普希金。有人说,罗赞诺夫爱普希金爱得如痴如狂,说他简直不是朗读,而是吟唱,像人们吟唱祈祷文一样吟唱普希金。他对待诗人的态度在《落叶》中也表露无遗:“普希金……我是在‘吃’他。已经熟知他作品的每一页。每一个场景,还是要反复阅读,而且百读不厌。这是‘食物’。它已进入我的体内,在我的血液中流淌,使大脑变得清新,使灵魂变得纯净。”[6]195 这是作为读者的罗赞诺夫对作为作者的普希金的态度。这时他对普希金的爱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爱。罗赞诺夫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893)中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惶惑、犹豫、苦恼的天性中,不仅没有任何与安静、明亮的普希金相类似的地方,而且仿佛是普希金的对立面,与果戈理接近,也许走得更远,与莱蒙托夫接近”[7]31。按照罗赞诺夫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爱普希金,把他当作自己的安慰”,“当作自己的守护者,免于各种愚蠢的想法和诱惑的最好的保护人”;而他自己,与“普希金灵魂异乎寻常地充实”相比,罗赞诺夫觉得自己的灵魂“完全不是充实的”,而是“凌乱的”,“痉挛的”和“可怜的”。因此,他们同样缺乏普希金的和谐与安静,都把普希金作为自己不可企及的理想,也作为自己的守护者来爱他。在性情上,罗赞诺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接近。 但是,作为批评家的罗赞诺夫开始评价作为诗人的普希金时,情形就不同了。“普希金迷”的罗赞诺夫对待普希金的态度,在保留某些总的不变的底色的同时,普希金的形象随着罗赞诺夫将之放置的语境而变化,因而罗赞诺夫遭遇了定义诗人及其创作本质的困境,其中我们发现怀疑和摇摆,有时“赞同”的证据会成为“反对”的证据。因此他笔下出现的是多面的普希金。这里我们就来谈谈罗赞诺夫的多面普希金。 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普希金的演讲。毫无疑问,这一讲话是罗赞诺夫思考普希金的指标性事件。他说,在1880年莫斯科诗人纪念碑揭幕仪式上“所有金子般的思想和话语”都讲完了,只剩下小心翼翼地“对那些已经说出的进行谦虚的总结,不要奢望有什么新奇和创新”[8]37。因此在罗赞诺夫的早期研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普希金的个性阐释对于他来说相当清晰,不需要额外地思考。在罗赞诺夫的首部著作《论理解》中,他把普希金视为一位永远完整的人,毫无内在的分裂,而且正因此而热爱生活,热爱人,没有感到作为一个人活着是痛苦的。这一定位奠定了未来批评家罗赞诺夫对待诗人态度的底色。 一、和谐性 在罗赞诺夫那里,“普希金是安宁、光明和和谐”;“他下意识地绕过了所有的偏差和偏颇”;“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没有一点刻薄的东西!这简直是奇迹”。“他没有在任何一页文字里洒上毒汁”。“他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一页表现出对人的鄙视”。他“什么‘致命的罪孽’也没有;一种极为纯净的血液——这几乎就是普希金的本质”[9]249-250。这一切构成了普希金的完满,也构成了罗赞诺夫“美的理想”。他身上“没有任何紧张的东西,没有任何病态的想象或不正确的情感”[10]。 罗赞诺夫把普希金的生活比作自然现象,一切在其中如此自然地流动,如此异于“先定”。罗赞诺夫对照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认为普希金的经历令人惊奇地完整和统一,“在发展中没有任何异常的巨变”[8]38,“其精神形象中没有任何的裂缝和缝合”[8]44。而与果戈理相比,普希金是正常的、没有秘密的艺术家,他唯一的谜就是他“如何可以没有斗争,没有努力,甚至没有可以看得见的沉思就站到了那个最高点,那个中心,从那里向四周辐射出这规范之光,人类的宁静、美丽之光”[8]333。无论是在世界文学中还是在世界精神中罗赞诺夫都没有找到与普希金类似的现象,他把普希金的遗产置于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之上。他认为,普希金的心灵是自由的,甚至面对像基督教、古希腊文明那样强大的东西也没有屈从,而在这些力量面前没有谁能自持。这点让罗赞诺夫想起了拉斐尔——在自身中包含了“天使的成分”。在普希金身上,尽管单纯、安静,但依然是超自然之光。但与果戈理不同,普希金身上的这些品质很难察觉,因为“他身上的一切只是‘透亮’,而不是引人注目”[8]334。 二、包罗万象性 普希金让罗赞诺夫迷恋的另一面是其多元性,甚至不是多元,而是无所不包。他说:“普希金仿佛就是生活的象征,他整个处于运动中,并因这一点他的创作是如此丰富。一切活的东西都吸引他,因而他走向一切——他爱一切,表现一切。”[10]“他对每个年龄的人都悄悄地说了心里话,都说了一番同情、安慰和支持的温存话语。”[9]250这种包容性,不仅是对生活的包容,还是对全世界文化的包容。“帕尔尼,安德列·谢尼埃,夏多布里昂;同时,帕尔尼的心灵,伏尔泰的智慧;还有拜伦,最后,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他们都走过他,但都无力将他留在自己的桎梏中;而他并没有打碎它们,甚至没有刻意卸下它们。一切都自然离去,剩下一个俄罗斯人,但已经是一个因全世界文化而丰富的俄罗斯人,已经是一个品尝了向异族众神祈祷的甜美的俄罗斯人。”[8]38如果罗赞诺夫先前认为诗人本质的东西是“和谐、完整性”,那么本质中还有“融合性”和“多元整合性”。罗赞诺夫推测,如果普希金活得更长久些,那么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就不会如此激烈,因为“西方的欧洲与东方的俄罗斯的争论在普希金这里已经解决了”[8]47。因此,罗赞诺夫认为,作为俄罗斯民族主要品质的体现者,普希金具有对全世界文化的敏感、接纳和回应性。罗赞诺夫强调“普希金天才的非凡强大的力量”,能够表达各种“精神情绪”,这一点,俄罗斯的“诗人和艺术家,从茹科夫斯基到托尔斯泰,没有一个人”[7]15能够成功。 这一融合性还以全神性表现出来,即比多神论更宽泛的“一神”和“众神”的融合。罗赞诺夫称普希金为“全神人”,而他的生活是“在上帝的花园里散步”。在这个花园里,他“仿佛第二次——在智慧中、在诗的天赋中,栽种花园,重复着上帝之手的事业”[11]167。但是在他那里结出的不是“物”,而是“关于物的思想,不是花朵,而是关于花朵的歌”。诗人提供“诗歌之花”,“满足你们每一个人的需求”,同时,他还“哺育整个俄罗斯,直至她的每一个天性”。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身上的俄罗斯性自然而然地上升到最伟大、最深刻、最高尚的全人类性。在与果戈理的比较中,他认为,果戈理只在两个方向上运动:紧张的空洞的抒情——向上,和针对一切低下东西的讽刺——向下,而普希金是多样和全面的,构成了果戈理的反题。 然而,不同于维·索洛维约夫认为普希金的灵感源于上帝,罗赞诺夫不是把普希金当作先知,而是绝对的地上的诗人,普希金揭示的仅仅是大地,但这是“整个大地”。诗人注定不是以什么新事物来丰富大地,但是他爱一切已经存在的。按照罗赞诺夫的观点,普希金具有遗忘天赋,据此他可以走向新事物,并同样热烈地歌颂完全相反的事物。因此罗赞诺夫提出这样的假设:能够经常转换注意力是普希金的显性个性。不过,罗赞诺夫1899年同一年撰写的两篇文章《阿·谢·普希金》和《论普希金科学院》中却出现了普希金个性的两种解读。前者中“全能性天才”的普希金是“冷冰的”,后者中普希金是绝对“大地”诗人,亲近于每一个人。对罗赞诺夫来说,普希金的平易近人是最贴心的,而且,罗赞诺夫看到的这个“平易近人”,甚至比诗人本人所表现的还要多。这一矛盾有可能证明罗赞诺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隐藏的争论,后者的权威对他来说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决定几乎在一切方面同意他。但是偶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概念又不符合罗赞诺夫阅读普希金的感受,因此出现了两篇文章中的不一致。 三、永恒性 在罗赞诺夫那里,普希金是“奇妙的永恒”。他的作品“仿佛是现在写的。在语言和语流中,在作者对待人与物及社会关系的心理方面,没有任何过时的东西。这是奇迹。普希金一点也不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有些过时了,他们紧张的神经、一些思想和观点已经过时了,而普希金却丝毫没有过时。你们会看到,再过二十年,他会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年轻、更现代。他对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都有某种合适的东西,同样,我们预感到,他对各个时代和每一代人也会有某种合适的东西”[9]249。“普希金是最不专业化的,由此产生他的永恒性。”[10] 罗赞诺夫跟随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普希金的包罗万象性,并在此之下理解其“心灵清醒的平静”和“向往融合”。普希金没有固守任何事物,而是同时热爱一切,同时迷恋一切。但是这一属性对于罗赞诺夫来说有时成了一大缺点:“有着无限辽阔的思想,但却没有一个可以使它们聚在一起的东西;心灵没有限度,因此它不可能热爱许多,尤其是热爱矛盾的东西。”[8]42 由此可以看出,罗赞诺夫所阐释的“能够经常转换注意力”而产生的对全世界文化的敏感性,对世上一切的爱,实际上成了无对象的爱。由于缺乏恒常性,使得罗赞诺夫称普希金为“短暂事物中的永恒天才”。他对诗人的爱变得矛盾起来,失去了先前那种绝对赞赏的特点。 四、教育性 在1912年的《返回普希金》中,罗赞诺夫表达了遗憾,因为尽管普希金拥有“俄国第一诗人”的地位,但是他没有作为朋友走进每一个俄罗斯家庭中。罗赞诺夫确信,俄罗斯读者更喜欢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如果普希金拥有同样的普及性,“他会预防文学、图书、报刊、杂志中庸俗的泛滥,不可能使它们持续十几年”[11]372,而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以其“一神论”之力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心灵和兴趣的多样性可以避免被年轻人称之为“过早专业化的心灵”。普希金最重要的东西是他“在任何方面都是最不专业化的,他的永恒性和普遍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此”[11]374。 早在1899年罗赞诺夫的《关于普希金的笔记》中,罗赞诺夫就把普希金的作用归结为导师的作用,“就多面性讲,就自己的全视域讲”,他是“我们永恒的,在一切方面的导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诗人开始让罗赞诺夫觉得严厉和严肃。在这个笔记中,罗赞诺夫论述了普希金创作的哲学性内容,比起诗歌天赋,罗赞诺夫更偏爱他的智慧。导师普希金,首先具有的是教育意义。另外,罗赞诺夫把普希金归为“静态”作家,这一解读降低了普希金创作中的美感成分,也限定了他的作用在于教育青年一代。普希金“就是整个俄语语文课”。另外,在罗赞诺夫的不少文章中,普希金充当了某种“文化的保护者”,阻止一切外来的恶劣的东西。普希金的作用在于传达世界之美,它们提升和塑造读者。 五、文学的尺度、俄罗斯的尺度 正是在对普希金创作的审视中,在普希金对待现实的态度中,罗赞诺夫阐明了现实与艺术的关系,他说:“不只作为表现者的普希金给出了对待现实的正确尺度,在他的诗歌中也包含着启示:反映生活的艺术本身应该怎样反作用于生活。在这一作用中,不应当有任何加速的或使定型的东西:诗只应当照亮现实并点燃它,但并不更改、扭曲、偏离人活生生的天性中固有的倾向。诗不干涉生活……普希金教会了我们更纯净和更高尚地感受,摆脱一切精神的灰烬,但他不给我们强加任何令人窒息的形式。热爱他的诗,每个人依然是自己。”[10] 在《普希金与果戈理》中,罗赞诺夫指出,果戈理是俄国社会和文学中讽刺情绪的始作俑者,他创造了其形式和类型,自己深陷其中,忘记了自己最初的自然的倾向。而“普希金始终和自然在一起……在人的身上他只取了自然的东西——动物中最具智慧的半神半动物的特有的东西,这就是——老年,童年;少年的欢愉,姑娘的憧憬;妇人和父辈的劳动;还有我们的祖母”[9]250。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人物的个性就源于此,他们完全不能归于共同的类型。 文学中的类型——已经是缺陷,是概括;也就是现实的某种重塑,尽管非常精致。人物不是被编进各种类型,他们就生活在现实中,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携带着自己的目的和意义。正是靠这一点——不与任何其他人的面孔融合,一个人才在天性上区别于任何其他人。人的天性已经被概括为各种种类和样式,没有办法概括的只是它们的局部,这一点正是人身上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艺术最好不要加以干涉和影响。“在普希金那里就没有干涉。新人中只有托尔斯泰,在非现代层面上,能够达到这一点,为此他被认为是我们文学中自然主义的最高代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在普希金那里已经有了,只是不知为什么未被发现。”[10] 罗赞诺夫得出结论:正是普希金“是真正的自然主义流派的奠基人,永远忠实于人的天性,忠实于人的命运”[10]。普希金是自然主义流派的尺度。早在《论理解》一书中,罗赞诺夫就思考过可以将普希金归入的文学流派,认为诗人的创作属于那样一个时期,即文学还是“绝对的诗”,各种各样的流派还不存在的时期。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的《吝啬骑士》中没有任何什么自然不自然的东西,他在“真”这一概念下,理解“带有生命和天性的人的自然、真实、合理为何物”。正是根据这一指标,罗赞诺夫把普希金和果戈理对立起来。 对于涅克拉索夫所属的“揭露倾向”的文学,罗赞诺夫在总体上是否定的。在自己的一份笔记中,他不无庆幸地指出,普希金毫发无损地走过了19世纪60年代的批评,这种“凶恶”和“野蛮”的批评“一点也没有烧着他”。这一考验更加确认了普希金的价值和意义。1908年,罗赞诺夫曾非常明确地表达过普希金在俄国文化中的位置。在大家都认为普希金可以被遗忘的时候,罗赞诺夫大声疾呼:我们会诅咒那个时代,诅咒那些俄罗斯人,他们把普希金搞得完全彻底地不需要了!他认为:“普希金是俄罗斯智慧与心灵的尺度:我们不是用俄罗斯之心丈量普希金,而是俄罗斯之心被普希金丈量,而且,从自己的脚步中抖落掉普希金的俄罗斯,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俄罗斯,不是祖国,不是‘自己的国家了’。”[12]379诗人成为了“俄罗斯”的符号,这一符号不只成为俄罗斯人民主要品质最好的表达,而且成为这些品质的核心点。普希金的创作成为一种独立的价值。 六、民族性、人民性 与此相关,在罗赞诺夫那里,他还是俄罗斯民族性的表达者。罗赞诺夫的文学的民族性概念,是在别林斯基和阿·格里戈利耶夫的影响下形成的。在1888年11月25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罗赞诺夫指出,俄罗斯的民族特点在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及其独特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生活态度的表达者,成为了民族诗人。他对待现实的态度,也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作为一位诗人,他对一切高尚的事物都会赞美,正如前述指出的,“他走向一切——他爱一切,表现一切”。 普希金的民族性还有另一种含义。罗赞诺夫指出,“民族诗人”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柯尔卓夫不是民族诗人?究竟为什么我们非要格外地赋予普希金这个定义,而不是附加在柯尔卓夫的名字上?因为他不仅仅像柯尔卓夫那样在精神类型上是俄罗斯人,他还带给俄罗斯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并在文学中赋予它最高地位。成为自由的和独立的人,这是柯尔卓夫不能做到的。 斯拉夫派当中有许多“俄罗斯主义者”,但他们永远不能把自己的学说变成有价值的民族的现象。普希金不仅自己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也把整个俄罗斯文学提升到了民族的高度,因为他始于向欧洲祈祷,他祈祷的每一步都走得如此之久之诚心,仿佛竭尽全力,结果在这长长的忠心的祈祷之后,我们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俄罗斯人,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普希金的功绩在于,从他“开始了俄罗斯真正的爱国主义,使俄罗斯人尊重自己的灵魂,使俄罗斯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8]120。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俄罗斯人心灵的气质,因而把他的追随者作为特殊的一类划分出来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在罗赞诺夫的意识中出现涅克拉索夫的名字,一定是强调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人民性这一符号。在《“政府”的两种形式》中,罗赞诺夫写到,普希金“是历史的和人民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激怒了俄罗斯西欧主义者。不过在《纪念涅克拉索夫逝世25年》一文中,罗赞诺夫认为,“就‘按俄语特点创造词和语句’方面讲,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涅克拉索夫一样,无论是普希金、还是莱蒙托夫,甚至果戈理,他们就像某种程度的外国人”[8]109。涅克拉索夫比普希金更是一位人民诗人。这里出现的是对“人民性”的不同理解。在前者中,普希金的人民性就是其民族性——在于他对世界文化的回应,因为这种回应是具有俄罗斯民族特点的回应,而普希金是其最高体现者。在后者中,涅克拉索夫的人民性则在于在诗歌中使用了民间口头创作的元素。显然,人民性与民间口头创作,普希金与涅克拉索夫,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不同使命、不同历史作用的人。罗赞诺夫也承认,可以拿普希金与果戈理、莱蒙托夫比较,而如果拿涅克拉索夫与他们比较,“就如同问,铁路和冉·达克·贞德哪个更好一样奇怪”[8]118。 然而,在探讨人民性与贵族性时,针对普希金的诗《英雄》中所写“卑鄙真理的黑暗/对于我比高尚的欺骗更珍贵”,罗赞诺夫指出,“这首诗,是贵族式的,不爱劳动的诗,是在小楼的阳台上吟唱,而这小楼是饥饿的农夫建造的,为此没有付给他们一分钱”[13]137。这里强调贵族文化与人民文化的断裂。在文章《我们学生时代的涅克拉索夫》中,罗赞诺夫再一次觉得普希金的诗“做作”“不自然”“非平民化”。甚至在《苏丹王的故事》中,罗赞诺夫也看到了“某位老爷的(面孔)——却把自己包装在人民性中,表现出对人民文化的趣味与爱,尽管包装得很天才”[8]248。可见,在这一语境中,罗赞诺夫对诗人的分析开始有了社会学范畴的因素。 实际上,罗赞诺夫把两位诗人按照阶级符号孤立了起来。但在文章《神父、警察和勃洛克》中,罗赞诺夫又回到那一思想:我们受教育阶层的天才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与人民脱离,仅仅是非天才的人与之脱离。正是因此,“普希金没有脱离俄罗斯,他写了《鲍里斯·戈都诺夫》,莱蒙托夫没有脱离俄罗斯,他写了《卡拉什尼科夫商人》,果戈理更没有”[8]332。我们也看到,同样一部《苏丹王的故事》,时而被罗赞诺夫解释为“把自己包进人民性的”的老爷,时而被解释为俄罗斯精神的真正表达者。在确定普希金的人民性品质上的摇摆直接与文化语境相关。与涅克拉索夫相比,罗赞诺夫觉得普希金“冰冷”,携带着非亲人的“老爷式高傲”的文化痕迹;但与颓废派分子相比,他是“温暖的”,人民的。所有这些不同的论断,是对“人民性”概念的不同解释。前者更宽泛,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后者较为狭义,涉及具体的“人民”创作主题。 普希金究竟有没有“人民性”这一问题,后来罗赞诺夫在《隐居》中讲到,在他中学时代的教育中“甚至不提普希金”,而“涅克拉索夫则被读得如痴如狂,人们知道他的每一行诗,信手拈来他的每一首”[14]45。在《沙哈尔那》中罗赞诺夫再次指出,在思想和生活的某些方面,涅克拉索夫确实高于普希金,因为在普希金或整个他的“人民性”之后,无人再去农村,而19世纪70年代的“到民间去”正是涅克拉索夫所激发的。 七、是开端还是结束 1892年,在《俄国文学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中,罗赞诺夫指出,别林斯基、斯特拉霍夫等人认为普希金身上缺乏“新颖性、独创性,因而也就缺乏历史地位的伟大性”。但是,赞诺夫跟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讲话”,认为虽然诗人没有在已有的诗歌创作形式上有所创新,但是他善于感受西欧历史形成的一切精神情绪,每一种情绪对普希金都是“绝对的和完善的”,但是它们中没有任何一种使他彻底满足;他回归了民族的情绪——简单和善良——存在于俄罗斯民族中的心灵美的最高理想,从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来的精神美获胜了。他开始了俄国文学中这种冷静简单的对待现实的态度。早在1890年的《斯特拉霍夫的文学个性》中,罗赞诺夫就曾称普希金的创作是俄国文学走向独立的开端,创作了“一直存在于我们普通人身上的精神气质”的类型,亦即“简单和善良”,这在他的创作中开创了一种新的方向。 不过,在罗赞诺夫1898的文章《永远悲伤的决斗》中,诗人成为先前传统的终结者,按其精神结构来说,诗人属于过去,而不属于未来。普希金“在自身终结了从彼得到自己宽广思想的和精神的运动”[15]。这一说法与《俄国文学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后者中普希金是俄国文学新方向的鼻祖。这里罗赞诺夫实质上同样不承认诗人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认为其创作的意义在于,一切——“先于他的一切”——“在他这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表达的美,达到了无以企及的深度,以及意识的清澈和宁静”[15]。罗赞诺夫不同意阿·格里戈利耶夫给普希金下的定语——给“人类天性的恶魔性”念咒语的人。他称普希金的心灵是“纯朴”的,没有影响果戈理、莱蒙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由此罗赞诺夫得出与其先前观点相矛盾的结论,“我们的文学起源于‘普希金’的说法该结束了”[15]。这是在另一层面上否定了普希金的开创性。 1899年,罗赞诺夫在《关于普希金的笔记》中称普希金为“友善之人”,这一品质区别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莱蒙托夫这一类作家——“他们的本质是酒神,即与坐在三脚架上的皮蒂亚女神同源”。与他们不同,普希金的智慧多于诗歌天赋,“可以说,在他之后,世界变得更好,因为在这个世界,也就是在他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中,许多事物被给予了终极完美的花纹。但是,在普希金之后世界没有变得更富有,更丰盛。”[16]罗赞诺夫在这里再次强调了诗人没有带给这个世界任何新的东西。 在文章《伊·谢·屠格涅夫》中,罗赞诺夫提出了俄罗斯文学中的两种状态静态和动态的源头。他把普希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归为静态作家。“普希金是俄国文学这一运动的顶峰,他精彩地席卷了一切,一泻千里,涌带出我们文学的‘白银时代’——40、50、60、70年代,诞生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及整整一辈杰出人物——俄罗斯日常生活的讲述者,平静生活的幻想家和旁观者。”[8]139他说,所有这些作家最典型的是缺少“风暴和激情”,他们呈现俄罗斯过去是怎样的,现在是怎样的,借此他们“几乎打造了整个俄罗斯的文化修养,无声无息地、几乎教科书般地教育了几代俄罗斯人,对他们的思念,一如所有学生思念自己的教科书”[8]139。也许在这一观点里叠加了尼采关于创作的两个源头——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观点。这样,罗赞诺夫在评价普希金的文学史作用上出现了不同的表述:“对全世界文化作出反应”的普希金确定了俄罗斯文学的未来,而“静态”的普希金属于过去,仅仅是“给出了俄罗斯过去是怎样的,现在是怎样的”[8]139,尽管相当漂亮。在1913的《落叶》中,罗赞诺夫表述普希金对于俄罗斯文化的意义时,他重复了自己的思想,认为普希金终结了伟大的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到他自己时代的俄罗斯。 八、是痛苦的还是轻浮的 普希金是否只是和谐、轻松、快乐?在1897年的《“政府”的两种形式》一文中,罗赞诺夫反对流行的观点,即认为普希金的诗轻浮、表面。他说,普希金“散文的每一页都可以扩展为一部哲学论著,诗歌的每一行都可以延伸到页面之外”[8]21。罗赞诺夫提出了普希金与政府间关系的一个独特观点,他改变了“政府”一词的意义,认为对于作家来说,唯一的政府是读者,艺术家创作的命运直接取决于他们。“对作家来说这一真正的也是真正可怕的‘政府’的态度上,普希金没有与他们进行直接的斗争,保持了完全独立的尊严”[8]24。 在罗赞诺夫的解读中,普希金独立于社会,独立于读者的意见,独立于政府。但是这样一种独立的反面是孤独,“他上升到了观察的最高层,找到了最纯粹的对待现实的形式,这同时他早就感觉到了孤独,感觉到了身后没有一个人”[8]24,因为没有人能够在“观察的最高层”追随诗人。在《阿·谢·普希金》中,他又说,普希金始终处于上升状态,无法预测它的终点,因此“普通人”“弱小者”不能与他同呼吸一片天空,不能看见“无意识的忧郁的”天才打开的黑暗的空虚。因自己“王者的灵魂”,普希金成为了完全的孤独者。 在把普希金视为“和谐”的底色中,罗赞诺夫曾经认为普希金“不会感到作为一个人活着是痛苦的”。区别于这一观点,罗赞诺夫在《“政府”两种形式的》一文中断言,不能像通常那样把普希金看成与一切和解的诗人,“认为他一点也不会因周围的事物而痛苦,试图表现他永远与一切和解,如所说的‘显得年轻’(普希金的术语),这是无稽之谈,这不是实情,这是不公平的和可笑的”[8]24。 按照罗赞诺夫的看法,诗人对社会、人、整个喧闹的生活拥有无以表达的爱,“总是想与这些融合在一起”,但同时因自己的“怀疑的态度和‘白发的智慧’(却是黑色的胡子),他比别人如十二月党人,如恰达耶夫,走得太远太深”;诗人“看待恰达耶夫的《书信集》和十二月党人的企图,就像看待历史的‘顽皮’,看待周围社会的一切,就像看待我们历史的童年,那时如此粗鲁而错误地轻视某种东西,正如粗鲁而错误地追逐某种东西”[8]25。罗赞诺夫说,“鬼叫我带着智慧和天才生到了俄罗斯”——这诗句中包含了痛苦的对现实的批评态度,包含了那些因现实对鲜活的心、鲜活的思想、鲜活的热情的冷漠的疼痛,后来恰达耶夫、十二月党人,甚至后来的19世纪60年代,都没有这些疼痛。所有这些都是对深深假寐的国家的疼痛,那里常常有哭泣,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里的哭泣,那里有祈祷,“旷野里嚎叫的祈祷”。 普希金以其锐利和无所不包的智慧看到,这些假寐,这些品质,深埋于俄罗斯的历史源头,恰达耶夫、十二月党人的批评只是围绕着它们的儿童游戏。“诗人不再珍视人民的爱”——这著名的诗句是诗人不再假装“年轻”,带着无法形容的悲伤,说出了因疏离而带来的疼痛。因此,普希金智慧、端庄而宁静,但他痛苦于这些东西,因为在爱活生生的生活时他注定孤独。 不过在罗赞诺夫那里,普希金的个性终究是完整的、没有内在分裂的论点占着上风。罗赞诺夫称诗人的痛苦是“生平经历的”痛苦,诗人的所有感受都合流为“某种和谐”。无法解释普希金的出现这一现象:他只是历史的成功。 罗赞诺夫对普希金的界定,关于他的意义和文学地位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统一的。也有一些异于通常对普希金印象的负面评价,如诗人与对现存结构具有破坏力的文学的揭露倾向相对立;而当罗赞诺夫认为整个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衰落的原因时,普希金像其他作家一样,同样是有罪的。 在《无政府主义》这篇随笔中,罗赞诺夫把格里鲍耶陀夫、莱蒙托夫和普希金并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天的情绪》中,罗赞诺夫遗憾于普希金毕竟没有来得及到国外走走。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是“挖去眼睛的夜莺”,而他的诗歌——像是“没有眼睛的天才的幻想”,因而“他的诗是如此圆满,没有缺陷,没有瑕疵,啊!可以把现实嵌入一切理想中”[13]131。罗赞诺夫确信,普希金的作品远远逊色于伟大的教会文本的语言。在另一处罗赞诺夫讲到,与上帝的存在、阴间世界、不死的灵魂相比,俄罗斯的文学(甚至普希金)、文明、文化、中学、小学、大学,都成了愚不可及的东西。 在与果戈理的对比中,罗赞诺夫认为,在两个人的创作中,俄罗斯语言获得了“最终的成型”,正是他们确立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完全不是普希金而是果戈理向我们显示了语言的最大力量。普希金把俄罗斯民族的那些品质,如单纯、温和、忍耐和海纳百川,视为理想,他以自己的诗歌形象颂扬“贫穷和不自由的俄罗斯人民”,那时欧洲还不熟悉俄罗斯的精神层面;而果戈理以其“无法解释的心灵的不安流露出了惶恐、痛苦和对整个俄罗斯的自我批评”[8]353。普希金展示了俄罗斯人灵魂的美,但他“没有像果戈理一样创造出具有神奇力量的幻想作品”[8]121。在《形式的天才》(1909)中,罗赞诺夫指出,果戈理作品的形式比普希金更完善,果戈理的叙事“在色彩的鲜明、印象的力度、对记忆和想象力的冲击上”[8]347,都超过了普希金。此外,果戈理以可怕的负面的描写,击退了过去的对普希金的创作来说属于典型的记忆。就在同年的文章《何以果戈理纪念碑不成功?》中,罗赞诺夫重复了这一思想,确认果戈理的“形式”和“语言”甚至征服了普希金。在《果戈理及其对戏剧的意义》一文中,罗赞诺夫认为“整个后来俄国戏剧的发展继承了并且继续着果戈理,而不是普希金;继承的是‘钦差大臣’,而不是‘鲍里斯·戈都诺夫’”[11]300。这样,一方面,果戈理显示出与文学发展的自然道路的偏离,另一方面,他对社会产生了更为有力的影响,尽管普希金的创作也对社会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罗赞诺夫就什么构成了语言的最大力量无法给出唯一的见解:是精神上接近每一个人,给予人成为自己的可能性呢?还是对社会的自觉意识产生影响呢?罗赞诺夫时而偏向一方,时而偏向另一方,没有做出最终选择。不过,通过与果戈理的比较,普希金的创作显得更明亮更富有朝气,果戈理更沉闷更有力。 当罗赞诺夫开始比较普希金与莱蒙托夫时,普希金的个性与创作则完全呈现出另一幅景象。在《永远悲伤的决斗》和《关于普希金的笔记》中,罗赞诺夫就已经指出,诗人具有的是智慧,而不是天才,把他和自然力的莱蒙托夫对立起来。在《果戈理之谜》中,普希金还是不同寻常的存在,在《论莱蒙托夫》中已经是普普通通的了,尽管“在‘我们’的普通中他达到了最高最广”[8]642;而莱蒙托夫则完全是非同寻常的,永远新鲜和出人意料。 由于社会和国家危机的加剧,在罗赞诺夫生命最后几年的作品中出现了否定文学的倾向。普希金一方面与整个俄罗斯文学一起担负着终结帝国的责任,另一方面,他“预言而伟大”的创作也成为了这个帝国的荣誉。在这个帝国俄罗斯文学达到了“极致的繁荣和顶峰”。 但是最终,在罗赞诺夫那里,正是“普希金把俄罗斯人、俄罗斯思想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推进得不是一步,而是整整一代”[11]11。 ①参见田全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第二章(第64-1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②参见郑体武的《洛扎诺夫其人其文》《洛扎诺夫的文学观》,赵桂莲的《论罗赞诺夫的创作价值观》《俄罗斯白银时代普希金研究概观》。 ③参见罗赞诺夫的《自己的角落:罗赞诺夫文选》,李勤译,学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