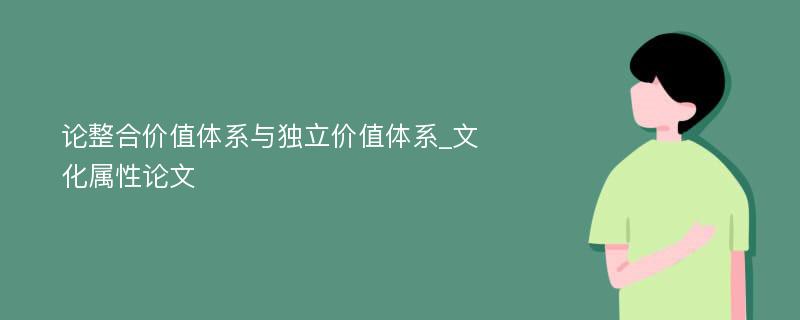
论融合型价值体系与分立型价值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1-0007-08
价值无论是在个人还是民族身上都是以体系的方式存在的。从文化价值差异看,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从而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从而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从文化价值的共同性看,由于人性的共同性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文化价值体系正在趋向于统一,尤其是在价值体系的结构上将趋于统一:人类价值体系将从融合型价值体系转化为分立型价值体系。
价值体系是由不同价值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方式组成的系统。价值体系的差异主要是由价值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和结构所决定的。“价值体系的不同有时是由于要素方面的不同,但更常见更普遍的是由于这种排列组合顺序的不同而造成的,是由于优先顺序的不同而造成的。”①由于价值体系结构的不同,便形成不同类型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中诸价值要素间的关系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外在性、分立性关系,另一种是内在性、融通性关系。据此笔者将价值体系分为融合型价值体系和分立型价值体系两种类型。融合性价值体系中诸价值要素之间缺乏严格的界限,它们是相互交融、融通的。相反,分立型价值体系中诸价值要素是有界限或边界的,各有其自性、各有其本色、各有其原则,同时各要素间又存在功能性联系。传统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一般来说是融合型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则是分立型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更新和再造,其实质就是从融合型价值体系向分立型价值体系的转化。
价值体系诸要素
价值体系是由若干价值要素组成的。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要素包含哪些内容?不同学者的看法略有差异。有学者从本体论意义上将价值要素分为四种:功利价值、规范价值、超功利价值和人的价值。②有学者将价值要素分为三种:人的价值、物质价值、精神价值。③有学者从价值范畴意义上将价值要素分为功利、真、善、美四种。有学者从认识理论意义上将价值要素分为实际的价值关系、人们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评价标准、评价活动等内容。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划分价值要素都有其合理性和意义。笔者认为将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要素分为功利价值、规范价值和超功利价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但是将人的价值与这三种价值并列则似不妥,因为人是价值本身,人和这三种价值的关系是总体和部分的关系、一和多的关系、理一和分殊的关系。
价值体系中究竟有什么价值、有哪几种价值?对此问题必须同人联系起来加以回答。价值是人本身,而人是有其本质、结构和属性的。人的本质可以从与物的区别中加以理解。物的本质是“是其所是”,就是说它是既成的、已然的、有限的。人的本质是“是其所不是”,就是说人是将是的、未然的、向前向上无限开放的生灵。正因为人“是其所不是”,是未然的、未定的、无限开放的生灵,所以人才有追求、希望、向往和选择,才有自由,从而才是价值本身。从人的“是其所不是”的本质中可以看到人的存在结构。此结构就是一体双元结构,即作为本体的人有双重存在:经验存在和超验存在,或经验的人和超验的人。因为在人的“是其所不是”的本质中,“不是”意味着人有超越既有既是的人期许理想的人的生命趋向。这就是超验的人,而“不是”总是相对于“是”而言的,此“是”就是既有的现实的人,此人就是经验的人。因而人的存在结构就是经验的人和超验的人的张力性结构,此结构可称为“一体双元”结构。之所以是“双元”是因为经验的人和超验的人不存在隶属关系,二者不能相互统属、相互派生、相互还原、相互等同。当然这是从哲学或现象学哲学意义上说的,若从科学发生学意义上说则另当别论。④经验的人和超验的人在功能意义上可以相互作用、互补互动,这是人的存在结构。人不是空洞的抽象,人有其属性。从人的属性来看,人又是“一体三维”的存在。三维指的是人的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
人的“是其所不是”本质,实质上就是自由。说人是价值本身也可以说自由是价值本身。自由是人的自因、自成。自成即自我完成。“是其所不是”中的“不是”意味着人是有欠的,而有欠的则意味着向无欠、圆满的过渡、努力。从有欠向无欠的过渡就是人从不完满(有欠)向完满(无欠)的过渡,就是人的自我完成。人的自我完成(自成),就是自由、就是价值。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什么是至善(价值)时深刻地申明:一个事物的善在于它特有性质的实现,每一种生物的目的或目标是要实现它那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殊本质或使之明显起来。⑤树苗要长成大树,是要完成自己。人使自己自我完成,这就是价值。海德格尔说:人的“行动的本质是完成。完成就是:把一种东西展开出它的本质的丰富内容来,把它的本质的丰富内容带出来,producere(完成)。”⑥这意味着价值是完成、自成、发展、完善、自由。
价值本身(人)要展现、展开、实现于人的结构和属性之中。
价值本身展现、展开于人的存在结构之中便出现两种异质性价值,即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相对价值和绝对价值。经验价值是经验的人所要实现的价值。物质价值、功利价值、富强价值、幸福价值、正义价值、技术价值、衣食住行性健寿娱价值等都是经验价值。经验价值是现实的人、生物的人、社会的人所追求的价值,其存在的领域是经验世界,是现实人生和对待性关系。超验价值是超验的人所要实现的价值。精神价值、崇高价值、宗教价值、终极关怀价值、精神境界价值、宗教性道德价值等都是超验价值。超验价值是精神的人、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区别于现实的人)、作为类存在的人(区别于种存在的人)所追求的价值,其存在的领域是超验世界、本体世界、私人精神和超对待关系领域。因而,从人的存在结构来看,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要素是两种,即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人们通常所说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功利价值和超功利价值、权利价值和境界价值、社会性道德价值和宗教性道德价值、幸福价值和崇高价值、欲价值和理价值、身价值和仁价值等对峙性价值都是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表现。在人类文化和哲学史上,这些对峙性价值一直是思想家和民众所关注和讨论的核心问题。这亦表明我们将价值要素分为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不仅有人的存在结构的根据,而且有思想史根据。
价值本身展现、展开于人的属性层面便出现三种价值要素,即幸福、正义、崇高。人的属性较之人的本质和结构是较外在的层面,因而表现于人的属性上的价值也就比较具体一些。从人的属性来看,人是“一体三维”的存在:一体的人有三种属性,即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自然的人(包括心理的人)追求的价值是幸福(此幸福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幸福,指的是人的感性物欲得到满足后的身心愉悦状态)。自然的人有生物感官,感官有欲望并本能地寻求满足,其满足状态即是幸福。同人的本质和价值联系起来理解,欲望是有欠。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即有欠是无限的。无限的有欠就是空、无。然这空、无有向实、有转化的内在冲动。空、无向实、有的转化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价值的实现,具体说就是幸福价值的实现。社会的人所追求的价值是正义。社会是诸多个人为了生存、安全和实现更大的幸福而进行的合作与交往。不同个人在相互合作和交往中会产生两大问题:一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侵犯和冲突问题,二是由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如何在参与合作的个人之间的分配问题。为了合理解决这两大社会问题就要相应的价值原则和制度,这就是正义价值和制度。按亚里士多德的分法,正义有两种: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交换正义是解决上述第一个社会问题的价值原则和方法。交换正义的基本要求是不侵犯他人。不同个人在相互交往、交换活动中都不侵犯他人,就不会发生冲突,人们就可以和谐相处。分配正义是解决上述第二个社会问题的价值原则和方法。分配正义的基本要求是给每个人以应得的。每个人所承担的由社会合作所造成的负担和享受的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是合理的,他所应得的,社会就不会产生冲突。这就是正义价值及其作用。有了社会、社会合作和交往,才有正义价值。正义价值是人作为社会的人所必须追求的价值。精神的人追求的价值是崇高。崇高的内容是美、善、信仰、信念、境界等。人的生活幸福了、社会正义了,人并不完全满足,因为人还有精神属性和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所寻求的是生活和人生的意义。当人无意义时人会感到空虚,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欠缺一样,人的精神也有无限的欠缺状态,即空无、空虚状态。不过它无法用物质财富来填充,而需要意义来填充。人的精神也有从空、无向实、有转化的问题,此转化就是人的崇高价值的生成。填充精神空虚的意义是崇高价值,是美、善、信念、信仰和精神境界价值。人类宗教、哲学、伦理、美学等精神活动所努力构建的就是这些价值。人作为超验存在、精神存在不能没有超验价值、崇高价值。显然,从人的属性出发,幸福、正义、崇高就成为人必须拥有的价值,它们构成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
据上所述,价值要素从人的存在结构看是两种,即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从人的属性看是三种,即幸福、正义和崇高。从两种和三种的联系看,幸福和正义价值可归结为经验价值,因为这两种价值都是经验的人(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所追求的价值。崇高价值可以说是超验价值。幸福价值和正义价值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权利”价值,崇高价值则相当于广义的“善”价值。因而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要素也可以分为权利和善两种。这样和现代西方伦理、政治哲学中罗尔斯、麦金太尔所讨论的权利和善(或美德)的关系问题可以勾连起来,形成共同的对话语境。
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之间存在着融合与分立的关系;幸福、正义、崇高诸价值也存在融合与分立的关系;权利和善亦有融合和分立的关系。或者说不同文化和时代的人对诸价值要素的关系存在着强调融合或分立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诉求,这样就形成了融合性价值体系和分立型价值体系两种不同类型的价值体系类型。
融合型价值体系
所谓融合性价值体系,是指将价值体系中的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价值要素融通起来、混同起来,忽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界限的价值体系。具体来说,融合性型价值体系就是将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融通、混合起来,将幸福价值、正义价值、崇高价值融通、混合起来,将权利价值和善价值融通、混和起来,不注重区分它们之间性质上、层次上、原则上的差异,使其常常相互替代、相互还原、相互等同。
1.融合型价值体系强调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融通与混合。经验价值是处于经验世界或对待性关系的经验的人所拥有和追求的价值。如富强、幸福、长寿、健康、政治自由、法律自由等价值都属经验价值。超验价值是处于本体界或超对待关系中的人所追求的价值,如终极实在、终极理想、绝对完善、天地境界等都属超验价值。柏拉图讲的理念、中世纪讲的上帝、康德向往的至善等都是超验价值的不同形态。经验价值是相对价值、有限价值,是可以在经验具体的人身上实现的价值,超验价值是绝对价值、无限价值,是不可能在经验的人和现实世界中完全实现的价值,它是人们永远所期许、向往的对象,因而它始终范导着人的活动,使人的活动能够不断升进和完善。
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本是异质的、对峙的两种价值,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领域——超验价值处于本体界,经验价值处于现象界——然而融合型价值体系则试图抹去二者的分际,将二者融通、混同起来,消除或减弱二者之间的对峙与紧张。融通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情形有以下几种:(1)将超验价值完全放入历史时间序列之中,认为超验的绝对价值在于历史时间的某一个阶段之中。在中国传统历史观中,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作为绝对价值的理想社会在经验世界中是存在的,只是不存在于历史时间的现阶段,而存在于远古的阶段,即所谓的三代时期。在他们的观念中,三代是在历史时间中曾经真实存在的时期。这样作为超验价值的理想社会就是曾经在时间中真实存在过、兑现过的价值。这是中国古代价值观结构。中国现代价值观结构略有变化,但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融通、合一的基本结构未变,思想家和政治家仍然主张作为超验价值的理想社会可以存在于历史时间之中,只不过超验价值的存在时间从远古移到了未来,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可以在未来某个时间实现。“大跃进”时期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口号背后的哲学价值思维就是超验价值和经验价值的融通与合一,就是融合型价值体系的表现。这种价值类型承认人间能够建成天堂。这种价值思维与康有为的相关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康就认为他的大同社会理想是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所以《大同书》写好后他秘不示人。
将超验价值和经验价值融通、混合起来的哲学本体论依据是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相即合的“一个世界”。凡在本体论上主张经超相融的哲学在价值思维上都强调将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融合起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最早将超验和经验融合起来,为融合型价值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庄子认为超验的道“无所不有”⑦,强调“物物者,与物无际”⑧。庄子影响到后来的禅宗,禅宗主张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经验生活、经验世界就是超验的妙道。禅宗的这种经超相即思维又作用于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认为道在日用伦常中,在事父事君的日常活动中。冯友兰先生说:“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修道的人仍须出家?何以‘事父事君’不是妙道?这又须下一转语。宋明道学的使命,就是下这一转语。”⑨从宋明理学到现在的中国,文化的表层的确发生了变化,但经超相即,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融合的价值思维类型没有发生变化,价值体系类型之特质仍然清晰可辨,这确乎令人惊叹。
2.融合型价值体系强调幸福价值、正义价值、崇高价值的融通与混合。幸福若按康德的理解,是指人世间物欲得到满足后的身心愉悦状态,具有利己性;崇高或善、德性是人对他人和社会的无私奉献,具有利他性;正义则处于中间,主张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显然这三种价值是有明显区别的。特别是幸福和崇高依康德之见是二律背反的。⑩但在有的文化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中却要将三者融合、混同起来。这种情形在中西方哲学史上都曾出现过。在晚期希腊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那里,幸福和德行就是融通的,两派都将幸福和德行的关系视为分析性关系。斯多葛派认为从德行中可以分析出幸福,德行就是幸福。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幸福是人自觉具有德行。这是将德行等同于幸福。伊壁鸠鲁则认为,可以从幸福中分析出德行,自觉到自己的准则可以获得幸福就是德行,一个有福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幸福才是“全部至善”。这样就将价值体系中的两种异质价值融合起来了,这样的价值体系就是融合型价值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幸福、正义、崇高三种价值的融合、混同情形尤为显著。儒家自觉到义利之别、德福之别,荀子曾主张义利两有,但儒家作为成德之教其思想努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想用德、善、崇高来代替福、利、乐,似乎人有了德、善、崇高就有了福、利、乐。儒家倡扬的“孔颜乐处”就是认为像孔子、颜回这样的人有了崇高的德行,就有了心理的乐。乐本来是苦乐之乐,苦乐同欲望的是否满足相关,满足为乐,不满足为苦。但儒家试图将苦乐之一乐转化为精神之乐,认为有了德行就有了精神上的乐。这实质上是想用超验的精神之乐代替经验的感性之乐。儒家多谈精神之乐,几乎不谈感性之乐。这是用德价值来替换福价值。在此替换中表现出无视德福两种价值之差异。儒家在处理崇高(德、仁)与正义价值时,表现出强调前者,有用前者代替后者之意。伦理追求美、德、仁,政治追求正义,本为不同,但儒家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用德、仁来代替正义,将德、仁等同于正义。孔子说:“政者、正也”。(11)这正指的是诚心正意之正,是道德范畴。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孔子还用孝来代替正义。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2)父为子隐是慈,子为父隐是孝,孝慈都是道德范畴,而孔子则认为直、正义就在其中,这就是用道德来代替正义,肯定了有道德就有了正义,有了仁就有了义。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义的基础、根本。劳思光说:“盖仁是自觉之境界,义是此自觉之发用。能立公心者,在实践中必求正当,此所以仁是义的基础、义是仁的显现。”(13)仁对义、道德对正义本为范导性关系,而在儒家则成了构造性关系。这就将崇高价值和正义价值融合、混同起来了。其结果是正义和崇高两种价值都难以得到实现,此为合之两伤。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纲领的内圣外王之道、三纲领八条目等体现的是崇高、正义、幸福价值的混合性、内在相通性。如果说崇高是高度价值,正义是中度价值,幸福是低度价值,那么儒家以至整个中国文化就是用高度价值代替中度和低度价值;如果说崇高是形上价值,正义是形中价值,幸福是形下价值,那么儒家以至整个中国文化就是用形上价值代替形中和形下价值。当然这是从可言说可倡扬的层面说的,从不可言说的层面看,中国传统社会则是用政治权力价值来统一其他价值层面和要素,崇高、善和幸福价值都须为政权价值服务,政权成为将价值体系中的诸价值融合、混同起来的真正力量。
3.融合型价值体系强调权利和善两种价值的融通与混合。权利和善的关系是现代西方以至世界学术界讨论的重大问题,罗尔斯和麦金太尔所围绕的中心问题即是此问题。权利和善本是异质的两种价值。权利是人的对待性关系中的价值,是个人对自己利益的主张;善则是超验价值,是无条件的绝对性的道德律令及其行动。但在有的文化体系和思想家那里却试图将二者融合统一起来,形成融合性价值体系。
权利价值和善价值的融合大体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将善等同于权利。在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是善,子要孝敬父,父要关爱子,是家庭美德。但这是善价值,不是权利或正义价值,而有思想家则将这种善价值等同于权利或正义价值了。如上面引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就是将善价值等同于权利或正义价值了。如果是在家庭范围内的私事,父子相隐是善,如父亲患不治之症,子予以隐瞒,这是善,但父亲偷了别人的羊或财物,这就是社会关系问题了,不是私人领域而是公共领域的问题了,在此范围内所涉及的是正义价值,因而在此父子互隐就是不正义。当然父子互隐的价值心理是自然的,其中的亲情恻怛是可贵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将善等同于权利、正义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将善等同于权利和正义,必定会伤害社会权利和正义。二是将权利等同于善。在现代价值观中,平等追求自己需要的满足等都是权利,这些权利从广义上来说也是善,但它同狭义的善是不同的。狭义的善是一种无私奉献、利他助人。权利、满足自己需要是低度的、起码的价值,是社会制度价值,是保障更高价值实现的价值,因此不应将其等同于狭义的善。譬如在家庭中夫妻双方为了表达爱情,愿做出更多的奉献,这属于善、美德的范畴,不能用平等权利来评判这种奉献,说这不平等,是侵犯权利。当夫妻发生矛盾难以解决时,平等、权利就会起作用。父子、母子、朋友、信徒等人群内部都存在有别于权利的更高的善价值。在社会生活中,权利、正义价值有利于社会的繁荣与秩序,但社会要文明化则离不开善价值。
将善和权利价值等同起来,都是未自觉到二者的界限和异质性的表现。将善等同于权利,会导致用善取代权利,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就存在此种情况;将权利等同于善则会导致用权利取代善,这是现代社会价值中容易发生的问题。用善代替权利,会使社会走向虚伪、无序、不正义,使社会关系变得不合理不明白,个人因而会遭受无尽的挫折;用权利代替善则会使社会走向平面化、世俗化、消费化。因此,两种情况都应避免。
总之,融合型价值体系的特征是将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融合、混同起来;将幸福价值(功利价值)、正义价值(规范价值)、崇高价值(美德价值)融合、混同起来;将权利价值和善价值融合、混同起来。从人生境界或人生哲学意义上看,这种价值融合是有其正面意义的。如要形成中国哲学所追求的“天地境界”,那就要将经验和超验两种价值融通起来。中国人讲“难得糊涂”,要达到“糊涂”境界也要将各种异质价值融通起来。“糊涂”境界有利于健康价值实现,但不利于正义、权利价值之实现,不利于“合理而明白”的社会关系之形成。不合理明白的社会关系会使个人产生挫折感,为克服此挫折感,又须追求“糊涂”境界,这是“国学热”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重大原因。显然,从个体权利、社会正义或制度哲学层面看,融合各种异质价值因素是有消极作用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价值体系须从融合型向分立型转化。
分立型价值体系
所谓分立型价值体系,是指价值体系内的各价值要素在领域、地位、层次、性质、特征、原则、目标等方面都存在严格区别和界限,他们不能相互通约、还原、归结、等同,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具本色,同时诸价值要素在功能意义上又有相互作用、协助范导和补助。
诸价值要素的分立主要表现为三组价值的分立: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分立;幸福价值、正义价值,崇高价值的分立;权利价值和善价值的分立。
1.在分立型价值体系中,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是分立的。在价值体系中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是最基本的两大要素。
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是有其严格分际的两种不同价值,二者不能跨越各自的存在范围和界限,否则价值体系及其主体人就会出现畸变。正如黄克剑先生所言:“任何一种价值追求的寡头化或某些价值追求对其当有分际的越出,都可能造成另一些价值的畸变或萎缩,而这又会涉及诸种价值体现其中的文化整合是否健全。”(14)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分立体现在二者的存在领域、性质、原则、特征等区别上。
(1)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存在领域不同。经验价值存在于经验世界或人的对待性关系领域,超验价值存在于超验世界或人的超对待性关系领域。经验世界是有限的外在世界,感性的人及其自然社会境遇都属经验世界。经验的人因其有欠性,在经验世界中寻求自身需要的满足、适意和正当,创造出幸福、富强、健康、快乐等经验价值。显然经验价值存在和依赖于经验的人及其所在的经验世界,若无经验世界便无经验价值。超出经验世界亦无经验价值。老子明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5)肉身是经验的人、经验世界,祸患得失是价值,此价值依赖于经验世界。所以,福祸、寿夭、生死、贫富等经验价值存在于经验世界。与此不同,超验价值则存在于超验世界。超验世界是人的不断拓辟和无限扩展的内在心灵世界。内在心灵或精神的特征是反观自省及其在反观自省中的无止境的创升。心灵的反观自省使得心灵世界可以不为外在境遇所支配,从而取得其自主自由性质。崇高、真、善、美、圣、信仰等超验价值就存在于此超验领域。
(2)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性质不同。经验价值是物质性、自在性价值,它同人的生物性、心理性、肉身性有直接的内在联系。幸福、健康、长寿、快乐等价值都同人的物质性存在相关。虽然它也是人的能动活动创造的,但它对人的自然性有更大的受动性。相反,超验价值是精神性、自为性价值,它是人的内在心灵的产物,没有心灵的反观自省和创造,就没有超验价值。
(3)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原则不同。经验价值的形成和获得是有待的,要遵循自然因果原则,而超验价值的获得则是无待的,其所遵循的是自由原则。幸福、富强、健康等经验价值的求取依赖于人的内外自然和社会境遇,因而要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超验价值的获取则无待于客观变化的外在境遇,即不为此境遇所支配,它通过切己心灵的反观自省就可以获得。心灵的自我督责,人格的自我提升,境界的自我超越,道德的自我完善都是自己心灵自省的结果。此自由原则依孔子的话说是“为仁由己”。(16)照孟子说,求经验价值是“求在外者”,求超验价值是“求在我者”。(17)“求在外者”有受动性,“求在我者”则由自不由他。
(4)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特征不同。前者具有相对性、有限性,后者则具有绝对性、无限性、至上性。幸福、快乐、富强、健康等价值都是相对的,有限的。贫困时期能吃饱就是幸福,现在就不一样了。远古人活四五十岁是长寿,现在就不一样了。虽说人求取经验价值的冲动是无限的,但由于经验价值有待于客观境遇和主体能力,因而它总是相对的、有限的。相反,超验价值则是绝对的、无限的、至上的。德性、至善或圆满是超验价值,康德在讨论此价值时指明它是至高的价值,而“至高的东西可以意味着至上的东西(supremum),也可以意味着完满的东西(consummatum)。前者是这样一种本身无条件的,亦即不从属于任何别的条件的条件(originarium);后者是一个整体,它绝不是某个同类型更大的整体的部分(perfectissimum)。”(18)这就是超验价值的至上性特征。
(5)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的实现情况不同。经验价值可以在现实的人和社会中得以实现,而超验价值则无法在现实的人和社会中完全得以实现。超验价值作为绝对价值只能存在于现实的人之上、之外,作为人所不断希望的终极目标而存在。倘若超验价值在某一特殊的人和社会中完全兑现了,此人便成了神,地上便成了天国,这是不可能的。孔子认为,圣价值不仅一般人达不到,他自己也达不到,连尧、舜都达不到。“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19)“若圣与仁,则吾岂敢?”(20)历代君主愿将自己称为圣君,真是“骗了无涯过客。”
2.在分立型价值体系中幸福价值、正义价值、崇高价值是分立的。经验价值和超验价值是价值体系中的最根本的两极性要素。具体来看,这两种价值可以表现为幸福、正义和崇高三种价值。经验价值集中表现为幸福,超验价值集中表现为崇高,正义则是将幸福和崇高综合起来的纽带,在分立型价值体系中三种价值也是分立性关系,各有其自性,本色和边界,不能相互代替、相互归属、相互还原、相互等同。具体来说,三种价值的分立性体现在:
(1)价值主体不同。幸福价值的主体主要是生物的人和市民,正义价值的主体主要是社会的人和公民,崇高价值的主体主要是精神的人和德民。生物的人有生物感官,生物感官和肉身有其欲望。欲望是生物自我存在的第一个环节。(21)欲望的满足就是幸福。市民是欲望主体的社会存在形式,因而市民的活动原则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充量满足,此满足即是幸福价值。显然,幸福价值的主体是生物人和市民。崇高价值的主体是精神的人和德民。精神的实质是超验性,是心灵的反观自省。超越了人的感性禀赋,经验本能和客观境遇,便会达到自由的崇高价值。德民或仁人、至人所要寻求的就是超越的价值。正义价值的主体是社会的人和公民。个人在结成社会后,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公民有一种永恒的意志——追求社会关系的公平正义。无正义,人们就会相互处于掠夺、欺骗状态,使社会退回到自然状态。
(2)心理根据不同。柏拉图将人的心灵结构中的内容分为欲望、激情(气魄或精神)、理性三大因素。欲望,如上所述其本性是寻求感性物欲满足的,因而构成幸福价值的心理根据。理性以无限的对象,即智慧,至善为目标,构成崇高的心理根据。激情是人追求周围人承认自己是人,同他人平等的永恒意志,它构成正义价值的心理根据。有人将欲望、激情、理性的要求分别理解为“爱利”、“爱胜”、“爱智”(22),此三爱亦可看作是三种价值的心理根据。
(3)性质不同。幸福价值的性质是利己,崇高价值的性质是利他,正义价值的性质是互利。这是从伦理学意义上讲的。因此在伦理学中有三种不同的伦理学体系,即功利主义伦理学、规范主义伦理学、美德主义或目的论伦理学。三者长期以来处于相互斗争和辩难之中,这亦说明幸福、正义、崇高三种价值的对立和分立情形。
(4)行为者数量不同。幸福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实行者要求是一个社会中的全体人,而崇高价值的实行主体则是少数人。幸福追求带有自发性,全体人都在追求幸福。相较而言,正义价值要高一些,虽说全体人不一定都能做到正义,但社会法律要求全体人都须践行正义。这两种价值实现了社会就繁荣有序了。崇高是比正义更高的价值,因而不是全体人都能做到的。只有一部分道德精英才能接近此价值。政治国家和社会不能强制性的要求全体人都践行崇高。
3.在分立型价值体系中权利价值和善价值是分立的。分立型价值体系中较具体的要素是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幸福价值和正义价值的结合构成权利。因为追求幸福并非在一切社会中都有合理性、正当性,而现代文化将人追求幸福视为正当,这就是幸福与正义两种价值的统一。此统一用一个概念来表示就是权利。善则与权利不同,它涉及的是个体人格的完善、境界的提升。分立型价值体系要求严格区别权利和善,避免因二者混同所带来的严重问题。
(1)对象不同。权利的对象主要是人的外在行为,善的对象是人的内在心灵。权利对人的要求是他人没有在行为上对自己构成侵犯,自己也没有在行为上对他人构成侵犯。权利关注的是人的外在行为,而非内心动机。一个动机不善的人在行为上未侵犯他人,就是一个践行权利价值的合格公民,相反一个动机善良的人在行为上侵犯了他人权利,他就成了侵权者、违法者。
(2)内容不同。权利的内容是利益、功利,善的内容是超功利、超利益的。权利是个人对自己利益的主张,其内容是利益。权利是实现和维护个人利益的社会机制。有了权利就有了维护利益合理性的制度保障。善,特别是绝对性道德中的善其内容是超功利的。无私奉献是善,其中的“无私”就是无功利、超功利。
(3)目标不同。权利的目标是形成社会秩序,是维护文明公序,善的目标是完善主体人格。权利对人的要求是三个原则,即诚实生活,不损害他人,给每个人以应得的。(23)诚实生活是个人自由,不侵犯他人是交换正义,给每个人以应得的是分配正义。权利就是要保障自由和正义,并因之以实现社会文明秩序。有了社会秩序个人还应有优良的德性品质,善就是要实现个人的优良品德,使个人有仁爱关怀之心,有良好的德性。
(4)领域不同。权利的存在领域是公共领域,善的存在领域是私人领域,权利属于公共理性,善属于私人意识。权利是个人在进入社会同利益相关人、陌生人进行合作和打交道时的一种利益调整机制,它是公共领域里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善则是一种私人观念选择和私人内心体验。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善,同一文化中也有多种善。在多样的善中个人如何选择这是他的私人意识。信仰自由就是选择善的自由,是私人意识问题,公权不可干涉,须保持中立。
(5)层次不同。权利价值是基础的、低度的,善是终极的、高度的。权利是社会生活和秩序的起码的基本要求,社会首先要维护权利以形成基本秩序。善则是很高的要求,涉及到个人人格的完善。
(6)普适度不同。权利的普适度大,善的普适度小。权利是可公度,可通约的,因而是一元性的,善则是难以公度和通约的。爱自由、爱财富、爱生命,不希望被别人损害等权利内容是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上的普适性的追求,它不为特殊文化和民族性所决定。善则是多样的,因而不同文化、不同个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个人究竟是信基督教的善,信佛教的善,还是信儒教的善,个人可以作出自己的不同选择。
(7)要求不同。权利的要求有强制性,任何人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否则就是违法犯罪。善则是劝勉性的,社会和他人只能劝说人倡导人行善,但不能强制人行善,否则善就失去了它的本性,就不是道德而是法律了。强制人行善的社会往往是不善的社会。
(8)优先顺序不同。从建立社会秩序和制度角度看,或从社会哲学角度看,权利优先于善。社会首先要维护个人的权利,保障低度的要求,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社会秩序,(24)为善的产生提供基本的社会条件。
以上我们分析了分立型价值体系中诸价值要素之间的分立、分离、异质关系,正因为是这种关系,由其所组成的价值体系才是分立型价值体系。同时亦应看到各价值要素之间存在互应互补关系。如超验价值就对经验价值有范导作用(非构造作用),而后者对前者有支撑作用。又如,正义价值可以将幸福价值和崇高价值结合、统一起来,权利对善有保障作用。鉴于本文论旨此种关联不遑详论。
注释:
①②李德顺、马俊峰:《价值论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页。
③王玉樑:《价值哲学新探》;袁贵仁:《价值学引论》;李连科:《价值哲学引论》,诸书都持相同看法。
④李泽厚先生所主张的“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或本体”观点若从科学发生学意义上讲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从哲学或现象学哲学意义上讲则大可怀疑。其说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已卯五说》,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⑤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4页。
⑥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9页。
⑦⑧《庄子·知北游》。
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4页。
⑩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11)《论语·颜渊》。
(12)《论语·子路》。
(1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14)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28-29页。
(15)《老子·十三章》。
(16)《论语·颜渊》。
(17)《孟子·尽心上》。
(1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19)(20)《论语·述而》。
(21)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0页。
(22)见陈家琪:《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23)见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24)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五章:权利的优先性与善的理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