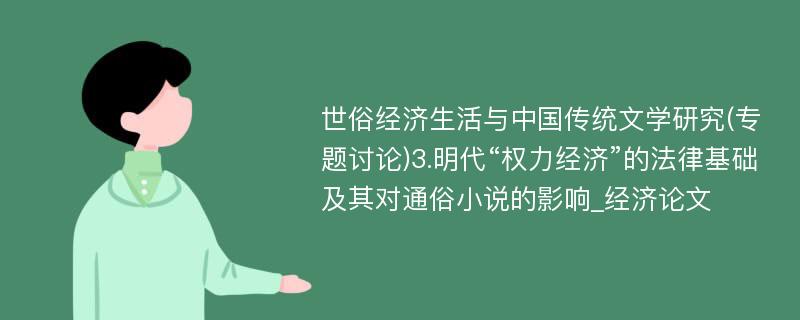
世俗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专题讨论)——3.明代“权力经济”的法权基础及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权论文,专题讨论论文,经济生活论文,明代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9-0093-13
皇权中国的经济形态所处制度环境与欧洲的不同,其要点之一就是,作为历代国家行政架构基础的“编户齐民制”规定,亿万“子民”人身和财产的存在都只能源自皇权的赐予与恩庇:“(天下百姓)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在这种法权形态中,每个子民的价值首先是,作为“编户齐民”中的一员,他必须为供奉皇权统治而尽赋役的义务(即班固所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而除了对统治者的这种依附效忠外,在国家权力与百姓地位的法权关系中,绝不可能另有“人身权利”的概念。
与“子民”上述身份相一致的是对国民财产权的法定:普天之下任何财富,在源头上都是由圣德齐天的帝王们所创造,卑微的子民能够享用这些财富则出于帝王赐福。因此,一切财富在法理上都天然和最终属于皇帝,即所谓“王者所有社稷”。土地所有权如此,商人财产更如此。所以,《汉书·食货志》对商业财富的定义是:“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上述法理同时也就决定了皇权社会一切财产的法律“权界”及其不可侵犯性,只存在于百姓彼此之间,而不可能存在于皇权与“子民”之间。所以秦以后历代“盗律”所禁止和惩罚的都是民间的财产侵害,而绝对不可能在法理和法律体系的指向上有一丝一毫禁止皇权和官府任意侵夺百姓财产的意味。
上述法权属性与古典和近现代公民社会完全不同。西方法律传统认为,人类法律来自上帝对其社会性的规定,所以国民基本权利和义务都是上帝赋予而世俗权势无权剥夺。在这种根据“自然法律和理性”确立的法权之上,就不能如中国那样还有“皇恩”、“大救星”等神圣的终极所有者和恩庇者。西方世界走出中世纪最重要制度资源之一,正是经罗马法、中世纪习惯法和城市法以来长期确立的使国民人身和私有财产得到保障的法权和法律制度。所以,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产生的首要条件是,“占有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独立经营的私人工业企业可任意处置的财产”,而这种所有权制度“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了解的一种现象”(《世界经济通史》);恩格斯则定义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在中国皇权社会城市经济中,资本主义的上述法权基础不仅不可能想象,而且通行的更是完全相反的法理。除了“禁榷”等皇权对经济的垄断之外,还包括:统治者在与商户的交易中用强买强卖、拖欠货款、贵卖贱买、名为购买实为强占等手段大量渔利;权力集团蜂拥经营商业,并利用政治特权(甚至是司法权和特务)攫取垄断利润;因为没有人身和产权保障,所以商人阶层只能“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以安身立命和博取出路;恶税制度给包括城市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灭顶之灾;权力集团公开大规模地掳掠工商阶层和百姓财产(见拙文:《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
而“权力凌驾市场”的法则在通俗小说中亦有充足的表现。《醒世恒言》中,渔民赵干捕到大鱼之后打算偷偷卖给商贩而多得几文钱,不料大鱼被公差搜出夺走,赵干还被官府暴打一顿。这个案例有几重值得留意的情节:一是衙门强迫百姓接受的“官价”要比市场价格低许多;二是物品一旦被官府看中,百姓绝对无权自己到市场上出售;三是因为一切“子民”都必须承担“编户”制度中的赋役责任,所以官府从百姓那里强买强征具有最强悍的法理根据,于是只要公差偶尔看见百姓财物,就可以立刻抄走;四是即使是被压得很低的“官价”,售物者也没有契约等可依凭的方式以保证从官府那里得到;五是如果百姓胆敢对上述法理有任何消极的表示,则将他们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也完全合法;六是小说作者丝毫不以为这些有什么值得奇怪,相反却以司空见惯的平淡口吻总结出,渔户失财受辱原因乃是他身为官府子民居然还梦想另外按照市价出售大鱼以图多得到一些利益,而这种“为利”的愿望正是使他自寻死路的祸根。
通俗小说中的类似例子很多。《拍案惊奇》总结的社会通则是:“那富的人,怕的是见官。”许多小说中的民谚也高度概括了百姓人身和财产与统治权力之间的法权关系:“自古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势争”(《梼杌闲评》);“自古道: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隋唐演义》)。又如《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写一商人在县城入厕时,“偶然官府在街上过”,吓得他“心慌起身”逃走,惊慌中把装银子的袋子遗忘在厕所——为何官员隔墙路过就将一个本分商人吓得魂飞魄散?如果了解到秦汉以后两千年间,统治者经常鼓励全民对富户监视告密并由官府抄没其财产、至明代“厂卫”特务横行之下此种制度更加横暴,就不难知道“那富的人怕的是见官”的社会通则中包含着无数商人和百姓破产灭家的惨剧。
从汉代开始,官员利用权力经商、或者与商人结盟经商以牟取暴利成为一种常规。此传统至明代更趋变本加厉,结果就是权力越大,越能以庞大规模经商牟利并攫取到垄断利润。这种情况在小说中有很多反映,如《金瓶梅》写了西门庆交结官府的各种手段,而这种政治投资反过来成为他狂热经商牟利的保障:
西门大老爷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段子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上纳香烛,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爹,朱太尉是他卫主,(蔡太师府的)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陈仓!
可见西门庆大规模的商业经营是以钻营权门的成功为前提的。
通俗小说的故事模式同样深刻反映着“权力经济”的特点。以很多人用来证实“资本主义萌芽”的《拍案惊奇》首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为例,小说用大量篇幅抒写商人如何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只是在命悬一线、飘零偶至之地才遇到冥冥中的致富福星。这种对于非制度化商业前景的幻想,表现的是在没有法权保障、没有可使商业社会进入良性组织形态前提下,商人阶层的“代偿性”心理补偿。小说序文概括全篇主旨:
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及至那痴呆懵董、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
无奈之下,商人的希望当然只能寄托于海市蜃楼般的“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如果我们知道由于统治者严厉的禁海令,明代希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只能向衙门行贿才能获得一线机会,则对此类小说的内涵会有更深了解。
类似例子又如《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写原本因木工手艺出众挣得小康的张氏父子三人,在黑暗司法制度下几乎全部丧命;《二刻拍案惊奇·韩侍郎婢作夫人》写小本店主江老儿遭一群“如狼似虎”衙役的公开劫掠,他们“险些把地皮多翻了转来,见了细软便藏匿了”,结果江老儿彻底破产,只能将女儿送给官吏为妾以求生;《照世杯·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写没有人身财产保障的商人,为了保住被贪官扣为人质的妻儿,冒死到荒蛮之地寻觅衙门派征的奇货,最后侥幸全命而归;《石点头·贪婪汉六院卖风流》写在贪官的酷税和恶法酷刑之下,商户王大郎被诬陷、全家七口惨死、家财被侵吞;等等。
许多研究者将明代通俗小说的文化意义归因于“启蒙主义”的萌生。所以,要理解通俗小说的制度内涵,还需要说明“什么是启蒙主义”、“皇权中国是否具备产生启蒙主义的可能”等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从来不乏对于皇权专制性的抨击和对自由的向往。至明代哲学和文学中这种声音更为痛切激烈。于是今人往往将这种诉求冠名为“启蒙主义浪潮”,认为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起显示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但实际上,这种诉求除了表现出人类向往自由天性永难泯灭和挑战专制威势的勇气之外,在制度构建方面的推动力却很有限。
近代西方启蒙则是由缺一不可的两方面构成,即霍布豪斯所说:“从逻辑发展以及历史意义上讲,第一个攻击点是专制统治,第一项要争取的自由是按照法律对待的权利”;这对专制的“攻击”,不仅是人类向往自由天性的喷涌和抨击专制的过人勇气,它更是“按照法律”实现,因此能够切实限制统治权力、控制专制弊害的制度化手段。所以霍布豪斯说:“(英国)人民的这第一种自由得到了《权利请愿书》以及《人身保护法》的确认”——《大宪章》(1215)、《权利请愿书》(1628)等宪政法典从来对于国民权利的“确认”绝不仅是“思想”,而首先是建立在一整套法律传统和国家制度之上,迫使统治者只能俯首遵行不能超越其外的刚性力量。因此以宪政良法限制统治权力,这在洛克、孟德斯鸠、康德等启蒙家那里一清二楚;而要建立这个基点,就必须具备古典公民政体(罗马法)、中世纪习惯法、城市法等由来久远的法治传统作为启蒙的资源。
由此可知,16世纪前后中国许多对专制积弊的抨击还不能够被称为“启蒙主义”。举个例子,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曾设计出限制皇权专制的一系列方法,可惜这些想法在专制环境中如何才能实现,却找不到任何操作性的路径。所以,他纸上谈兵式的纵横擘画、成竹在胸,也与他自己和家人羁身专制威势之下,在横遭巨大冤痛时只能引颈待戮、忍泣吞声的蝼蚁般命运形成鲜明对比——其父黄尊素与周起元、高攀龙等一大批敢于议政的朝官,被魏忠贤诬以贪赃的罪名并统统惨死于特务衙门的酷刑之下。遭此荼毒之际,黄宗羲所能做的仅是:“奉养王父及母……夜分伏枕呜呜哭,不敢令堂上知也”——思想家们连自己身家性命的法律保障都永远不知道在哪里的情况下,其制度设计当然不可能标志出整个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正确方向。
在这种困境下,无数国民只能以“政治心理幼稚化”为代价,将希望寄托于包拯式清官、“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等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寄托于“生前忠义骨犹香,魂魄为神万古扬。料得奸魂沉地狱,皇天果报自昭彰” (《喻世明言·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的政治哲学,并通过通俗小说的繁盛将这仅有的寄托方式空前强烈地彰显出来,就是必然的了。事实上,在社会制度的历史中,只有宪政真正使统治权力受到有效的法律约束;如此显明的道理,在统治者威权日益压倒一切、对权力的约束日益不可想象的皇权中国,通俗小说所呈现的斑斓社会图景、尤其是这些图景背后的“蚁民社会”法则,也就只能标示着与现代社会相逆的方向。而了解这种相逆性的产生根源,既是正确判断16世纪中国制度前景的必须,也是更深理解那时文学内容的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