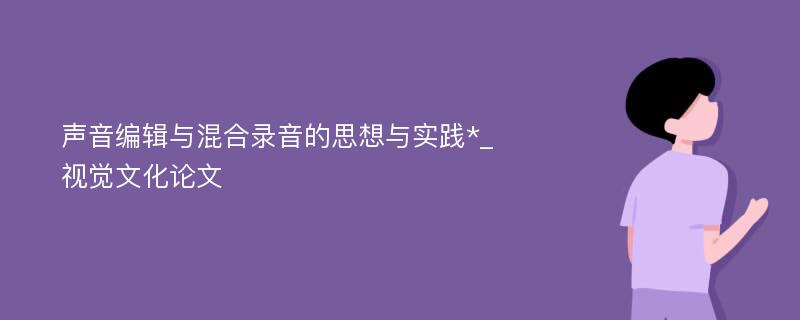
声音剪辑与混录的意识形态及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剪辑论文,声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讨论的声音剪辑与混录实践,皆发展于好莱坞制片厂体系内部。严格说来,“体系”应当被理解为具有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技术和设备)以及一种相对严格的劳动分工。然而,这些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也在这一体系之外成为“常规”——比如,它们对其他国家的电影制作工业和独立电影制作活动都有极大的影响。我的假设是,不仅声轨制作的技术,就连技术人员的语言和有关技术的话语,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目标的征兆。
强调“声轨比影像更少得到理论关注和分析”的论调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然而,这种陈词滥调并非没有真正价值,它将一种实情隔离出来,但却不给解释。这种关注的缺乏,表明一种特定意识形态运作的效用,在某种程度上,已被那种对“视觉意识形态”的强调所掩盖。确实,如其所示,一个人是去“看”电影而不是去听电影,这一表述本身就是由对电影特性(比如整体性、完整性)的肯定以及随之对其物质多样性的否定所组成。声音是加入到影像中的某物,但从属于影像——悖谬之处在于,它以一种“无声的”支持而见效。就声轨而言,对那种突出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工作的抹消是高度成功的。声音剪辑与混录实践的不可见性,似乎由声轨制作所遵从的“自然”法则所肯定。
然而,声轨在理论层面上被忽视,在实践层面上却并未得到呼应。好莱坞已经认识到,这种“增补之物”,亦即声音,一定程度上能够渗透和改变被增补之物。在这样一种工业里,其主要标准,根据产品价值,也许可以总结为“一种技巧越少被察觉,就越成功”。用于声音上的工作的不可见性,正是声轨活力的一种量度标准。对一部电影拍摄活动的宣传远远超过对包括声轨制作在内的“后台”行为的宣传。
将注意力集中于声音剪辑的意识形态决定因素,并不必然是否定让·路易·科莫里①和其他人所强调的“视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短语“看”(to see)是“理解”的文化中,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明确地被当作一种以眼睛为中心的功能。在一次关于西方文明所建构的感官层次的讨论中,米歇尔·马利②指出,某种程度上,眼睛所见是一切知识的基础。马利坚持认为,在这种感官层次中,听觉并不具有视觉具有的优势——视觉才是“理解整个外部世界的首要途径”。③
然而,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并不能被削减为纯属所见之物的一种坚如磐石的意识形态。在利用电影的历史背后,存在复杂的决定因素,其多样性保证着意识形态的微妙性和渗透性。尽管眼睛乃核心的观念把主体放到知识的特殊位置,但“知识”(to know)这一动词并没有耗尽布尔乔亚意识形态中主体的功能。或者说,知识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这种分裂得到知性与感性、智力与情感、实事与价值、理智与直觉之间意识形态对立的建构与维护所支持。罗兰·巴特认为:
布尔乔亚意识形态或是科学化的或是直觉的,它记录实事或感知的价值,但却拒绝解释;世界的秩序可被看做充足的或难以言说的,它决不会被看做是有意义的。④
声音那难以言说的、无形的性质——它缺乏实在性,这有助于一种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它被放置在情感的或直觉的那一边。如果视觉意识形态要求观众把影像理解为现实的一种真实再现,听觉意识形态则要求同时存在一种需要主体去领悟的不同的真实和不同的现实秩序。
“情绪”或“气氛”之类的词语出现在声音技师的话语里的频率,证明了另外一种真实的重要性。最明显的,是运用音乐轨和音效轨建构某种特殊的“情绪”。在《电影剪辑技巧》一书中,欧内斯特·沃尔特⑤描述了这种技术实践:
音乐被用于创建别的方法不能创造的气氛……正如声音剪辑师在某些段落中用效果声去创造一种近乎音乐的效果,作曲家创作的背景乐曲有时也会成为一种额外的音效。通常,它是一种增音的效果,与对白场景混在一起,因此观众几乎不能感知到音乐的存在,但却为场景增加很多价值。⑥
“价值”暗指未经解释之物。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必定缄默不语——正是因为这种观念诉诸语言,无法分析,或者无法理性地理解。声音是意义的承载者,它可以有效地传达而不可分析。声音领域是一个神秘的领域——但它的神秘受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制约,这种意识形态承认,视觉意识形态并未包含所有知识,而是允许有缝隙和剩余物存在,这些缝隙和剩余物被分裂知识与情感、直觉、情绪的对立面的另一极抑制和约束。然而,人们不能否认影像中存在的强大的感性和神秘力量,这跟声轨或用以保证清晰度的对白一样。影像和声轨都从属于一种多元决定的意识形态。然而,加入影片的声音不如对白的出现那么容易理解——在书写形式中,在把一个人物的言语与他/她的形象分离开来的字幕中,排除了它的缺席。用于声轨制作的技术并不具有“纯科学”的中立性。但是它们也不仅仅只是加强视觉的唯一意识形态。引入的声音在部分地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会招致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危机。隐藏在知识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中的矛盾暴露之际,这种危机就会出现。因为声音和影像被用作两种极不相同的知识模式(情感和理智)的保证,它们的联合增加了意识形态缝隙暴露的可能性——这种缝隙指向布尔乔亚意识形态两种真实的不可调和。声音剪辑和混录企图通过声画之间关系的可行规范掩盖这种矛盾。因此,在声音专家的话语中,同步性和整体感被奉为信条,声音和影像的不可分割成为目标。据一位声音剪辑师的说法,“混录的快乐”就在于观看“聚合物”的出现。⑦剪辑师海伦·凡·东恩⑧承认在他自己的工作中存在类似的目标:
某种程度上,画面与声音具有自己的组合关系,但当合在一起后它们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整体。因此,声音不仅是一个和谐的补充物,而且成为画面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画面和声音密切融合,依靠彼此发挥作用。这里没有我看画面与我听声音的分离,而是通过声画结合的整体所实现的我感觉、我体验。⑨
在技术专家的语言中,声音是被“结合”到影像上的。这并非意外。
对有声电影材料多样性的压抑,表现在抹杀音轨制作工作的实践中。声轨中的剪切就是那种工作的潜在指示器。在剪辑光学声带时会发现,胶片粘接处的重叠导致还放时产生尖锐的噪声。“接头消音”(blooping)技术的发展正是为了隐藏这种噪声,因为这种噪声只会让人想到这两段声音不是自然连接而是人为的。接头消音是一个在胶片接头处使用颜料涂或打孔或贴凌形片的过程,从而形成快速的淡入/淡出效果。在剪辑磁性声带片时,使用斜口剪辑的方法具有同样的作用。这些技术的意识形态目的与连续性剪辑的目的一样——所追求的效果就是使潜在的断裂变得平滑,保持流畅。避免音乐或声效的突然剪切,有助于淡或溶的效果均匀。很明显,循环的重复声音被认为是“烦人的”。⑩因为声音缺席会被当作连续流中断的信号,这就成为声轨制作中的大忌。当没有声效、音乐或对白之时,就必须至少有一点室内声音或环境声。从欧内斯特·沃尔特为粗剪样片放映时的声音所开的处方可以看出,某种程度上,声音的连续性和丰富性的价值支配着技巧的使用:
在粗剪样片放映时,当影片段落的声轨随着无声镜头的切换突然变得死寂无声,这对于所有看片的人都会造成极大的干扰。最好为这些镜头加上临时的音效,以便声音的正常流动不被破坏。(11)
持续的流动被视作“正常”,声音的缺乏在声音专家的语言中则是“死掉”。当一段声轨“在切换中死掉”,违规就是神学特性之一。“死”和“生”向来是关于声音的隐喻。一个房间或录音棚混响微弱时被认为“很死”,而在后期制作时为录音增加混响是使其变“活”。声音本身通常被认为给画面添加了生气。而且,声音所赋予的生命被看做是一种自然的、没有编码的流动。
这种没有编码的流动的幻觉也被不好的剪辑所支持。只有极少的情形声音和影像的剪辑点是完全一致的。相同的声音持续越过影像的剪切能够把注意力从剪切上引开。同样地,混录的过程也被描述为“一种统一化和同质化的工作,一种软化和消除声轨中所有‘粗糙性’的工作”。(12)所有这些技术都源于一个愿望,就是把电影与其来源分开,把制作工作隐藏起来,努力造成一种无需费力轻松捕捉自然的感觉。
被掩盖的是高度专业化和极其琐碎的过程,以及符合工业标准的声轨制作所需的庞大且昂贵的机器。同期声,也就是拍摄期间录制的声音,只包括对白和某些音效。大多数音效和音乐都是后来录制的。这就必须在片厂体系内建立专业的制作部门。现场没有录制的对白或是被背景噪声破坏的对白,要在后期同步录制。这种分层制作,亦即声轨制作所经历的不断细分,被严格划分声音类别的目标不断调整。因为话筒本身,无论是全指向性的还是单指向性的,都没有足够的选择性,因为它并不能保证赋予声音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它们的关系在录制时被监测到,能强化层次关系的昂贵混录设备则是标准化的。对白得到优先考虑,它的电平通常要决定音效和音乐的电平。在整个制作过程对白是唯一一种归属于影像的声音——它和影像一起剪辑,在剪辑时,声画同步被认为是一种中性的技术,在剪辑机和套片机上实现。音效和音乐服从对白,最为重要的,是受到影响的对白的清晰度,以及对白的微妙语调。用科莫里的话说,混录中声音的层次划分,强化了好莱坞故事片中“话语和命运”的认同以及“个体作为言谈主人”的观念。(13)声音的溶或淡入淡出用于对白是“不自然的”,这种出现于1931年一篇有关再录音(14)的文章中的观念,表明一种保护言语的地位如同保护个人财产权一样的欲望——仅仅从属于一种无法分辨的掌控。
这种对清晰度的要求和使用言语作为个体支撑物的做法,都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需求而建立起来的。然而,这种意识形态需求有可能在视觉意识形态中造成重大分裂。此种可能性在有规律地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技术杂志上关于声音透视的论争中可以找到。如果声音仅仅是用于巩固视觉意识形态,重申世界恰如所见的观念,它就必然侵占属于个体的言谈,定义和表达他/她的独特性,把个体从世界中区分出来。在这些关于声音透视的争论中,“现实主义”(作为视觉意识形态的一种效果)被看做与清晰度相冲突。如果遵守声音透视的要求(就是说,特写声音配特写镜头,远景声音配远景镜头),在摄影机拍摄远距离谈话对象时,对话的清晰度就会失去。对白与背景声音或音效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两个人在人群中谈话的镜头,为了对白的清晰度,人群的嘈杂拟音的力度通常要被削弱。这种为了对白的清晰度所做的妥协,表明在“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内,有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移位。好莱坞有声电影在现实主义两极之间摇摆:心理现实主义(或内心现实主义)与视觉现实主义(或外部现实主义)。(确实,内心状态通常借助场面调度和面部表情加以描述,但这种描述却不如言谈来得“直接”——它必须进行置换。言谈行为的现场规定着它的准确性)。个体的真实,个体内心情境的真实(一种最容易被说出和被听到的真实),是一种由声音确认的真实。它出现在1927年的“说话片”(talkie)而非有声电影中。
然而,在1930年代初期由声音透视的情形所引出的重要问题,还需要做更深入地解释。即使电影中的个体是由他/她的言谈所定义的,却并不能自动地为另外一类个体(观众)提供一个位置。文艺复兴透视和单眼视觉构成的影像为观众提供的位置是作为摄影机眼睛。但是,如果话筒的位置明显不同于摄影机的位置,而且不能重申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会遭到破坏和值得怀疑。在有声电影制作的最初几年,绕着场景安排多个话筒,拍摄时,它们的信号被送到一个监听室里混录,以便获得可靠的对话质量和清晰度。1930年,有人开始抱怨这个技术在对话场景中造成的后果:
一个室内的全景镜头跳到一个人的特写时,音质和音量没有任何变化。这时候观众马上就会意识到他正在看一部对话电影。这样的情形意味着电影的幻觉在这一刻部分地被破坏了。(15)
影像所传达的空间深度效果遭到破坏,透视和观众位置之间的幻觉被早期有声电影打破了。
听到演员开口说话的惊讶,体验到词语和影像同步的魔力,一度掩盖了空间位置的破碎,也掩盖了观众接受影像时的分裂感受。在1930年一篇题为“声音与影像的幻觉”的文章中,约翰·卡斯(John Cass)描述了早期有声电影对观众的身体的处置:
当使用好几只话筒时,声音混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也许不能说它代表任何一个聆听的位置,而是一种只有长了五六只长耳朵并且还得朝向不同方向的人才能听到的声音。(16)
身体上的这种混乱是不同媒介层次上另外一种混乱所造成的结果。录音领域最初是广播业、电话业以及电气工程师的领域。对于30年代早期的电影技术专家和导演们来说,声音是由一群专业人士所控制的神秘领域。在《电影工程师协会杂志》上,一位名叫乔·柯夫曼的作者对复杂的麦克风系统以及广播业入侵所造成的声音透视的缺乏进行了谴责:
从某种角度说,电影业的声音专家大多数来自广播业是一种不幸。在广播中,通常希望的是所有的声音差不多都出自同一个平面——亦即麦克风平面。因此,通过提升或减低电平来使音量大致相同,麦克风也尽量放在贴近声源的位置。但是,在有声电影的放映中,希望获得的则是空间效果,以及戏剧性的音量变化。(17)
影像决定着广播和电影之间的重大差异——影像把声音固定在给定空间中。柯夫曼的建议非常接近当今电影制作手册中的内容:用一只话筒,定好位置,设好电平,录音过程中不再作调整。1930年,西电公司的动圈话筒和RCA公司的速率型话筒在电影业开始使用,话筒杆的结构变得相当简单。(18)场景中的动作更加容易跟随,声音透视的维持得到了保证。所有声音来自同一个平面的情形不再延续。因为好莱坞银幕上演出的戏剧必须与观众身体上演出的戏剧一致——身体恢复完整,不再分裂。
位置的视觉幻觉得到了位置的听觉幻觉的配合。这种意识形态配合上的着迷渗入了声轨制作的各个环节,并要求有一种保真的技术。1930年,一篇讨论配音的文章使观众相信,配音并不是造假,因为声音无论被复制多少次,它仍然是“影片中说话人的真实的声音。”(19)真实性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对人声的要求,而不同的标准限制着无动机音乐和效果声的使用。它们的合理性由戏剧的逻辑所保证。卡内尔·赖兹(Karel Reisz)描述了《谍网亡魂》(20)中的一个场景:当抢劫磨房的人逐渐靠近他们的目标时,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响——尽管实际上比起先前的镜头他们离摄影机更远。雷兹引用这个场景作为偏离自然声音透视的一个例证:“当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达到一种戏剧性效果时,它是合理的”;磨房中具有韵律的节奏声“使得这一段落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地冗长,几乎就像是我们通过劫匪的大脑经历了那个过程一样”。(20)音乐也被用以配合这种“情绪”或这个特定场景中的动作。当模仿原则不是在再现世界里被严格地观察到(例如,在无动机的音乐或者非模拟的音效中),这个原则就会被用于匹配意义的不同物质层面。声音和影像,“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个人的戏剧,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戏剧。个体内心生活的“知识”可以更容易地被归结到他或她言谈的丰富性和自足性中,并可被音乐和音效的修辞策略强化(如同场面调度一样)。声音修辞是一种技术的结果,它的意识形态目标在于掩盖为达到一种自发性和自然性效果所必需的大量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被抑制的,是那些会暴露机器设备存在的声音。因为是声音(具有交流目的的可听见的空气振动)的对立面,即噪音(机器的随机声音——它们没有意义),决定了声音录制中如此之多的技术发展。声音剪辑和混录技术使得声音成为了意义的承载者——这种意义并不包含在视觉意识形态之内。声轨的意识形态真实适用于眼睛所遗漏的那些剩余物。因为耳朵正是一种向着个体内在真实敞开的器官——如果只凭借纯粹的视觉,这种真实不仅不可见,而且不可知。
注释:
①Jean-Louis Comolli,法国电影学者,La Femis和巴黎八大的教授。——译者注。
②Michel Marie,法国电影学者、理论家,任教于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学)。——译者注。
③(13)米歇尔·马利.声音.载:让·科勒等编.电影讲稿.巴黎信天翁出版社,1975.206.203。
④罗兰·巴特.神话学.伦敦海角出版社.纽约希尔与王出版社,1972.142。
⑤Ernest Walter,曾担任《蛮国恩仇记》、《罗望子的种子》、《渔人之靴》等影片的剪辑师。——译者注。
⑥(11)(12)欧内斯特·沃尔特.电影剪辑技巧.纽约焦点出版社,1973.212.208.208。
⑦拉里·斯图尔哈恩访问沃尔特·莫奇.声音剪辑的艺术:沃尔特·莫奇访谈.电影制作新闻组.1974,(2)。
⑧Helen Van Dongen,曾担任《四万万人民》、《土地》、《路易斯安娜州》等影片的剪辑师。——译者注。
⑨海伦·凡·东恩.转引:卡内尔·赖兹.电影剪辑技巧.伦敦和纽约焦点出版社,1964.155。
(13)让·路易·科莫里.技术与意识形态.电影手册,1972,(241)。
(14)卡尔·德莱赫.录音,再录音,声音剪辑.载:电影工程师协会杂志,1931,(16)。
(15)(16)约翰·L·卡斯.声音和画面的幻觉.载:电影工程师协会杂志,1930,(14)。
(17)乔·柯夫曼(Joe Coffman).有声电影制作的艺术与科学.载:电影工程师协会杂志,1930,(14)。
(18)詹姆斯·R·卡梅隆.有声电影.Coral Gables卡梅隆出版公司,1959.365。
(19)乔治·勒文.配音与有声电影制作的关系.载:电影工程师协会杂志,1931,(16)。
(20)英文片名《Odd Man Out》,卡罗尔·里德导演,拍摄于1947年。——译者注。
(21)卡内尔·赖兹.电影剪辑技巧.伦敦和纽约焦点出版社,1964,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