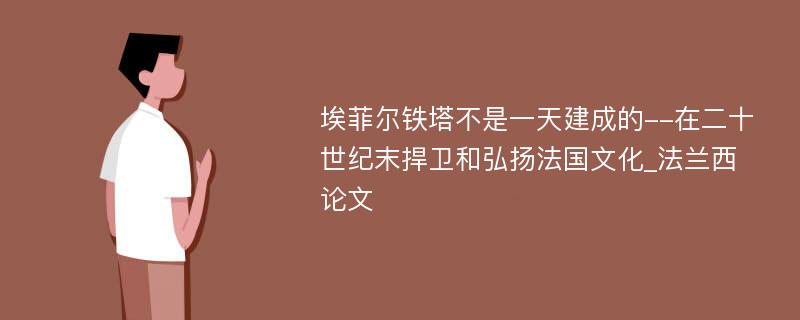
埃菲尔铁塔非一日建成——保卫和发扬法兰西文化在二十世纪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埃菲尔铁塔论文,法兰西论文,二十论文,世纪末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一五四九年,法国诗人若阿金·杜贝莱写了《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一书,这部被后人称为七星诗社宣言书的作品,应算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文艺批评著作。
为什么提出“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当时的法国,一方面由于封建割据,土语方言五花八门,各地语言差别巨大;另一方面,因教会垄断了教育和文化传播,拉丁文在文坛占据头把交椅,法语根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逐渐走着下坡路。以杜贝莱为代表的七星诗人提出“保卫和发扬”的口号,旨在改变法语的贫乏与粗陋,提高其地位,从而统一民族语言。他们提出的办法可谓不少: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假借词汇,采纳约定俗成的方言、术语,改造旧词,创造新词,等等。在七星诗社诗人们的努力下,法语终于取得了作为民族语言应有的地位。不到一个世纪,法国便出现了古典主义文化的辉煌时代,此后,法国的文化始终走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前列。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情况忽然起了变化,以法语为载体的法国文化又一次遭遇危机。对此,法国的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保卫和发扬法兰西文化”的口号。而这次,他们面临的不是内部的混乱或者无序,不是法国文化的衰退或枯竭,而是来自外界强势文化的威胁,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某种“工业文化”的咄咄逼人的进攻势态。
威胁来自美国
说来也怪也不怪,法国人素来以灿烂辉煌的法兰西历史文化为荣,往往看不起经济虽发达、历史却太短的美国,总以为他们的爷爷的爷爷传下的一件宝就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还长。他们自然也看不起日本人,认为日本人只是一类经济动物,没有自己的文化。法兰西文化确实是他们的骄傲:文学、绘画、音乐、建筑、戏剧,他们为世界留下了多少杰作,贡献了多少财富!要说文化,巴黎人的一句大话虽有些夸张,却不无道理:“一个巴黎,抵得上半个欧洲。”可不是!你到巴黎东北角的拉雪兹神甫墓地转一圈,有多少文化伟人安息在那里的苍松翠柏丛中:作家莫里哀、拉封登、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画家大卫、德拉克鲁瓦、安格尔,音乐家比才、奥伯尔……波兰人找得到他们的肖邦,意大利人找得到罗西尼,资产阶级找得到奥斯曼男爵,无产阶级找得到鲍狄埃。你随便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走一走,哪一个时代没有留下它的建筑杰作?中世纪的巴黎圣母院、半文艺复兴半哥特风格的卢浮宫、古典主义的凡尔赛宫、拿破仑时期的凯旋门、第二帝国时期的歌剧院、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埃菲尔铁塔……
但是当今,法兰西文化已遭到了严重威胁,就像它曾气势汹汹地威胁过别人那样。谁都知道,当年,法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曾向中国以及非洲、美洲的一些国家施行残酷的经济、文化掠夺,巴黎的集美博物馆乃至外省的各博物馆中陈列的中国珍宝便是见证。法国哪里想得到,自己数百年来一直实行文化侵略,到后来,别人竟然侵略到自己头上来了。而且,威胁它的不是别的,正是被法国人瞧不起的美国文化。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埃菲尔铁塔一样坚实。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已经一跃成为世界文坛的另一个中心,至少也是中心之一;同时,好莱坞电影以其高投入、精制作、程式化编导和商业化操作而迅速风靡全球,也大量地抢占了法国的电影市场;而最最要命的是,随着美国强国地位的确立,美式英语渐渐压倒一切语言,成为全球最通用的语言,法语除了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继续充当工作语言,在联合国仍留作正式语言外,在法语国家之外几乎到了行不通的地步;就连最遭法国人白眼的美国饮食也进军巴黎,麦当劳、肯德基等纷纷在塞纳河畔安家,抢夺着法兰西烹调大师的饭碗,让一个“有三百六十五种乳酪”(戴高乐语)的饮食大国尴尬不已。
且战且退,且退且战
美国文化的侵略性以其极强大的经济为雄厚基础,而在世界上只有二流经济实力的法国当然难挡这滔天浪潮,只能于节节败退中苦苦抗争,艰难地维护着昔日文化的辉煌。这种情景,从大气候来说,只能算是“且战且退”的战略方针。然而,法国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们精明的头脑中的文化意识实在是很强烈的呢。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劣势,强打起精神,付出十二分努力,扬长避短,争取法兰西文化的再度辉煌。这里又有了一些“且退且战”的悲壮气氛了。
别的先且不论,法国人的文化保护对策就有它独特的长处。简言之,他们的策略无非是两点,一是推崇精华,二是倡导普及。法国人历来喜爱标新立异,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各文化领域中的创新和实验,走在前头,领导潮流。由于法兰西文化有艺术探索的传统,故而艺术精华永不泯灭,根本无须国家去培养,政府只要保证合适的大气候,不断给予政策上的扶植,并及时推出就行。重要的倒是普及工作。法国在国际上的文化普及,实行的是一种文化渗透政策,政府每年都拨出巨额款项,向国外宣传法国文化。例如,资助出版大量的法语作品,包括翻译作品;提供奖学金,吸引外国学者和学生从事法国文化的介绍和推广工作;在世界各地开办法语学校,一方面宣传法国文化,一方面为外国培养法语人才。笔者就曾获得过法国政府奖学金,在巴黎学习法国文学;也利用过法国文化部提供的翻译家资金去法国作短期考察,为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收集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去年,法国就以政府名义向国外的图书馆赠送图书达八十万册之多,出资促成了数百人次的文化交流,专门对外的法国电视五台(注:法国电视五台为全欧频道,以文化节目为主,简称“Arte”。)的观众已经高达七千五百万之众。
本文想就法国保护和发扬传统优势文化的工作作一点探讨,提供一些例子。我们先谈一谈文化节的设置,然后对语言与文学方面的对策,作专门的论述,最后再举电影、卡通画、建筑方面的一些例子。
种种文化节
八十年代起,当时还是社会党人雅克·朗任部长的法国文化部作了许多文化普及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推出了一系列形式新颖的文化节活动,并把读书节、音乐节、电影节、开门节列为每年的新传统节日。
读书节被文化部定在三月份,即整个三月份成了“读书月”。读书节实际上是号召人们通过阅读,来摆脱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像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像文化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虽不是一回事,但在商业化、一体化(世界文化一体化)、标准化方面,却有着许多可比的成分。法国人在这方面的对策,实际上也是面对着强势的工业文化的威胁采取的措施。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是第一个音乐节,此后,每年的夏至那天都定为音乐节,从都市到乡村,这一天从早到晚人们都在演奏音乐,听音乐。一九八四年九月的一个星期日成了第一个开门节,此后,每年在九月的一个周末,法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名胜古迹都要洞门大开,免费迎接四方的游客。一九八五年以后,六月里的一个星期天便成为了电影节,人们可以花很少的几块钱去看一整天的电影。
说到开门节,其实是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家的一个优势项目,试想一下,若在美国举办开门节,能看到多少东西呢?法国则不然,光在巴黎市区和郊区就有三百多个历史建筑、纪念馆、博物馆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这样的节日,无疑为更多的法国人(自然也包括外国人)认识自己的古代文化多提供了一个机会。说来可能让人难以相信,好多巴黎人不太认识巴黎,至少不如好些外国留学生(如当年的笔者)那么熟悉,细想起来,好像也不是怪事,有多少北京人对北京风土文物的了解敢说比得上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留学生?
雅克·朗为法国文化做了一件广泛普及的大好事,至少他让法国人,也让我们知道了,在法国,每年都有专门的节日属于音乐、电影、名胜古迹。这几种文化节,虽不是与美国强势文化的直接对抗,但无疑是在为保卫法兰西文化的较量增加砝码。
听写决赛进军纽约
法国人在劣势的文化领域中是坚韧不拔的。随着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波一阵阵地袭入欧洲,美式英语也冲入了法国的社会,其俚语、词汇大量涌入法语,造成法语在使用上的混杂及其国际地位的动摇;同时由于广播、电视、卡通读物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不爱读书;加之学校语言教育质量的下降,许多人虽会讲法语,但却写不好法文,一动笔则错字连篇。
面对着法兰西语言中美式英语词汇的泛滥,法国人在广告语汇、语言教学中做了大量工作,竭力维护法语的纯洁。这包括在世界各地开办法语教学的专门学校,为其他国家培养法语人才。(注:目前北京已经有了“法语联盟学校”。1979年,法语联盟学校总部派两名老师在北京开办了在中国的第一个“法语联盟学校速成班”,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大学生中招收了四十名学生,笔者就是其中的一名。法国政府为向海外推广法语与文化是不惜重金的,文化部每年为此目的的预算经费高达五十亿法郎。目前,新加入欧盟的芬兰、瑞典、奥地利等国都开始鼓励青年学习法语。)其中,法国《读书》杂志和电视台组织的、已有十多年历史的、一年一度的法语听写比赛(注:听写比赛是由《读书》杂志、三大辞书出版社、两家广播电视台与一些工商企业联合组织的。)尤其值得一提。它从一九八四年起,连续十几年举办得轰轰烈烈。听写比赛旨在唤起公众的注意,清除语言混杂,减少学生“错别字”,共同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以及使用的标准化。
法语作为拉丁语系的一种拼音语言,拼写与读音有不少共同规律,一般情况下能读就能写,故而学校教育在指导学生规范拼写时作的努力不大。久而久之,一些词的拼写在许多人心目中便模棱两可。所谓听写,本是学生语言训练的基本作业,老师读一段文章,让学生逐字逐句默写下来,看谁的错最少。
听写比赛越办越红火,不仅参赛者逐年增多,已达数十万,以致组织者不得不把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而且决赛地点均选在法国文化的“圣地”:国立图书馆阅读大厅、巴黎大学索尔邦梯形剧场、卢森堡宫议会厅、国民议会大厅,其中一九九二年的决赛一直进军到了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法国人宏扬法兰西灿烂语言的战役竟然打到“敌手”的老家,气得美国人拒绝参加共有一百七十五个国家参加的决赛,因为“法国佬”的举动实在令他们太难堪。
除了听写比赛,除了世界各地的“法语联盟学校”,法国人还特别注意报刊、电视中的用语规范,例如,九十年代初期,电视台的几个体育解说员在转播法国罗兰-加罗斯网球公开赛时,连着用英语说了好几个体育术语,结果引来几十封听众的批评信,他们不允许电视台在能说法语的时候说英语,有的信还不厌其烦地写出网球术语的法语表达,“为什么说deuce(指网球赛中每一局中的平分),而不说égalité;为什么说tie break(指每一盘赛到六比六平后的抢七决胜局), 而不说le jeu décisif?”逼得评论员在电视中公开认错。
还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叫西尔维斯特的美国人因写电影剧本《兰波和罗基》而被法国文化部长授予文化勋章,引起法国作家贝尔纳·皮沃(注:这位皮沃先生正是听写比赛决赛的主持人。他曾在法国电视二台主持过长达十五年(1975—1990)的读书节目“阿波斯托夫”,后又开办了“文化培养”的节目。他还主持介绍了《理想藏书》一书。)不满,他撰文抗议,称影片庸俗、粗糙,并责问文化部长,要发勋章还不如发给在条件艰苦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从事法语教学的人。有这样保护民族语言的意识和勇气,还愁大事不成吗?
不是法国文学,而是法语文学
在与美国文化的较量中,法国文学似乎已经成了法语文化中最后的堡垒,当然这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堡垒,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城堡。
但是,一味坚守堡垒终非长久之策。法国人也不愿老老实实地等人家来攻,他们还想打出去呢。在防守反击中,法国人施展了各种各样的战略战术,首先,他们把法国文学的概念扩大为了法语文学;其次,他们竭力鼓励人们翻译法国文学;再有,他们吸引外国人用法语创作。
我们知道,除了法国人,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的人说法语,其中有比利时人、部分瑞士人、加拿大魁北克省人、非洲和美洲原法国殖民地的人,等等。谈到法国文学和法语文学,法国人用的是一个词:littérature francaise,它既可表示法国文学,也可表示法语文学。而在法国人看来,它更多地表示语言范畴,而不是地理范畴,它实际上是一种littérature d'expression
francaise。 所以,
litt ératurefrancaise不是法国一国的文学,而是世界上所有用法语创作的文学。当然,这种文学无疑要以法国的文学为核心或曰中心,以巴黎文坛为大本营,以巴黎的几大出版社为基地。
当法国人模糊了国别的概念,把加拿大、比利时、瑞士的许多作家、作品都归属于定义模糊的“法语文学/法国文学”时,不爱较真的比利时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们把出生并成长于比利时,但成名于巴黎的一些作家拉到法国文坛中。结果,我们看到,亨利·米修、费利西安·马尔索、弗朗索瓦丝·玛莱-若里斯这些一直在法国出版作品的作家被大多数人当成了法国作家,而不像始终坚持自己是比利时人的乔治·西默农那样,为世人熟知其国籍。我们真不知道,有多少非法国的法语作家,为法语文学作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
世界文学与法语文学的交融
还是那位出生于比利时的女作家弗朗索瓦丝·玛莱-若里斯,她在答法国《读书》杂志的调查提问“什么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事件”时,曾这样说,“有一个现象在我看来很重要:在最近几十年中,尽管法语在许多友好国家中失去了影响,却有许多作家,且数目不小,放弃了母语而选用法语创作作品……这一现象应该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并且刺激我们的创作。”(注:法国《读书》杂志,1997年夏季号。)她列举了许多名字,其中有以《等待戈多》而开创了荒诞派戏剧的爱尔兰人萨缪尔·贝克特、写了剧本《乒乓》的亚美尼亚人亚瑟·阿达莫夫、把《犀牛》搬上舞台的罗马尼亚人尤金·尤奈斯库、与肉欲搏斗了一生的天主教徒美国人朱利安·格林,名单中还有至今仍活跃在巴黎文坛的赫克托·比昂乔第、埃杜阿尔多·马奈、安德烈·马金等人。
其实何止这些人呢,出生于俄罗斯的新小说女将娜塔丽·萨罗特,文笔犀利的评论大师罗马尼亚人埃·米·齐奥朗,都选择了法语为创作语言,从东欧走向了法兰西;捷克人米兰·昆德拉早就定居法国,他的《被叛卖的遗嘱》、《缓慢》、《本体》等都改用法文来写。就连我们中国人,也有四十年代去留学的程抱一用法语写小说、诗论、随笔,他的小说《天乙之说》在去年获得了费米娜文学奖。八十年代去法国的作家亚丁,也以一篇小说《高粱红了》,竟使许多法国人以为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就是从这篇小说改编的呢。
那么多外国人都在用法语写作,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走向了法兰西,毕竟是法国的魅力吸引了那些外国作家,实在值得法国人自豪。
笔者认为,这里的吸引和趋向有不少原因。首先,法国文化所处的十分自由、宽松的大气候,有利于国内外作家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华。作为文化大国的法国,已基本排除了文化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相反,基于某种文化渗透主义,政府倒是特别提倡向全世界传播法兰西文化。外国人用法文来写作,对他们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其次,如上所述,被法国人称为世上最美丽、最纯洁的语言的法语,已渐渐地被美国人的英语打败。语言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工业”方面的落后,迫使法国人下力气在传统的优势——文学、艺术——上作出更大的努力。至今居然仍有那么一些外国人在用法文写作,怎能不让法国人感动呢?
还有,法国文学历来具有标新立异、推陈出新、反传统的“传统”,谁都不要求今天的作家写得跟福楼拜和梅里美一样漂亮,而写作者也都在追求能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来。这就使那些外国人在用法文写作时跟法国人一样,有了同一个起跑线,觉得自己并不比法国人缺多少法兰西文化底蕴,他们在用法文写作时无疑多了几分豪壮,至少不那么胆怯。
其实,反过来说,那些用法文写作的外国人也可以为此而自豪,因为他们掌握了法文,至少不比法国同行差多少,他们使用法兰西的语言为法国文学添彩,并让法国文坛刮目相看。
凡事均有两面,“走进”中就有“走出”。外国作家在“走向法兰西”的同时,也使法国文学呈现出一种相反的趋向,即“走出法兰西”:外国作家在选择用法文写作,在法国出版,赢得法国读者的同时,也把读者和出版市场引向了法兰西之外,引向了他们作为外国作家所熟悉的外国题材。作家写的必是自己心中有的,心中有的必是自己熟悉的。这些作家尽管选择了法文,却无法选择自己的亲历和感受。于是,他们熟知的外国题材形成为法国的文字,印在书中,刻在读者心中。以一九九八年获奖的两部由外国人写的法文小说为例,获费米娜奖的程抱一的《天乙之说》描写的是一个留学法国的华裔文人的心路历程,故事的环境氛围当为中国文化;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俄裔作家安娜·维亚津斯基的《一小撮人》展现的是俄罗斯土地上一个当年贵族庄园的没落。
法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多年来一直在国外从事法语教育(看!这又是法语在世界范围中的抵抗的一个例子),与此同时,他写出的小说也越来越多地以外国人的生活为题材,非洲大陆、美洲大陆、安的列斯群岛的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他已经写了十来部了。这一位被许多人看成当代最伟大的法语作家,小说中竟充满异国情调的故事,不是很有些反讽意义吗?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外国作家在“走进法兰西”,也不能笼统地说,法国文坛在“走出法兰西”。法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一直在交融中,法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直在交流中,而且是在宽松、自由、推陈出新的良好氛围中交融。法国人对具有各国特色的文学和文化宽容地认可,而带有各自特色、属外国文化范畴的作品,尽管用法文写成,也在吸引、改变着法国人的趣味。世界走向法兰西的同时,法兰西也就走向了世界。
金棕榈、阿斯泰里克斯、蓬皮杜中心及其他
确实,法国人在优势的文化领域中永远充满信心,不仅继承和发扬着探索、实验、标新立异的精神,而且还与美国文化叫上了板。
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且不论,光是建筑,就能看出法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既保护又发展的政策。早在十九世纪前期,法国就开始制定法律,对文物加以分类、保护,小说《卡门》的作者梅里美就曾是最早的历史文物督查之一。二次大战后,戴高乐政府一方面强调发展市政建设,一方面又重视保护文物,马尔罗任文化部长时,主持实施了保护、维修法国古建筑和珍贵艺术品的大规模计划,使一大批古迹从摇摇欲坠、面临瓦解的状态,又恢复了昔日壮美的面貌。一九五九年由马尔罗下令,文化部设立了建筑和遗产司,其使命为保护历史古迹。到下世纪初,将在巴黎的夏约宫建立“遗产和建筑博物馆”,它既是一个博物馆,又是一个网络中心和研究中心。(注:见《今日法国》1999年4月号。根据该期杂志介绍,从1964年以来,全国文物普查委员会在马尔罗的倡议下,一个区一个区地开展了文物“总普查”,“小到汤匙,大到教堂”,无一遗漏。登记在册的古迹有二万五千处。)在修复文物方面,不仅有文化遗产学校(九十年代开设)培养专业人员,而且还把细砂喷洗、激光处理、生物矿化等所谓的软性技术用于实践,以去除风化、污染等对古文物、古建筑造成的伤害。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改造工程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当年左拉笔下乱糟糟、闹哄哄的集市,如今已成了一个花园式的商业中心,但近在咫尺的圣欧斯塔什教堂(注:教堂的整体设计与构架为哥特式,内部装饰为文艺复兴风格,从1532年起兴建,到1637年才落成开光。)保留了下来,无辜者喷泉池(注:无辜者喷泉池由著名建筑师皮埃尔·莱斯科设计,由让·古戎雕塑,建成于1550年,为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保留了下来。巴黎的艺术建筑在近数十年中有不少传世之作,几乎每届总统任期内都有堪称大手笔的杰作诞生:蓬皮杜时期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德斯坦时期有中央菜市场的改造工程,密特朗时期有拉德芳斯新区和巴士底国家歌剧院,到现在,希拉克执政时期,规模宏大的国立新图书馆矗立在了塞纳河的左岸……这些建筑无论从设计上、工艺上、装饰上都是一个时代的艺术的代表。
从电影来看,法国人与美国人的较量颇具悲壮气氛。好莱坞电影固然夺走了一大批观众,但以“新浪潮”为代表的艺术电影仍走在世界电影探索之路的前头。法国人设立的政府奖凯撒奖,还有半官方的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始终在艰难地与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抗衡着。作为许多法国人心目中艺术电影的圣殿,戛纳电影节的主角是欧洲电影,不过近年来,亚洲、中东的电影也渐成气候,而美国电影在逐渐减少。众所周知,金棕榈奖的独特标准几乎是在与奥斯卡奖唱反调,最近三年分别颁给了伊朗影片《樱桃的滋味》和日本影片《鳗鱼》(并列)、希腊电影《一日永恒》、比利时与法国合拍的影片《罗西塔》。这是奥斯卡奖所不可想象的。另外,与冗长拖沓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不同,戛纳电影节的仪式,无论是开幕还是闭幕,都简洁明了。这恐怕是对好莱坞电影文化一种有意识的反动。
在卡通画方面,美国的迪斯尼系列形象(如米老鼠、唐老鸭)在世界各个角落可谓无孔不入。不过在法国,却依然有一个充满高卢特色的卡通形象家喻户晓,它就是阿斯泰里克斯:阿尔贝·乌德佐(绘画)与勒内·哥欣尼(撰文)通力合作创造的形象。(注:1959年,在刚创刊的卡通漫画杂志《领航员》的组织下,乌德佐创造了第一个阿斯泰里克斯的形象,以期与美国迪斯尼的米老鼠、唐老鸭为代表的喜剧漫画人物相对抗。此后,他与哥欣尼连手推出“阿斯泰里克斯”系列。1977年,哥欣尼逝世后,乌德佐继续单干。参见拙文《高卢精神的象征》,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2月5日。)阿斯泰里克斯是一个充满智慧、幽默和勇敢精神的高卢战士,小个子,黄色的八字胡,头盔上饰有白翎毛,只要喝下老魔法师配置的药汤,一段时间内他就具有神奇的功能和本领。他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布列塔尼沿海的一个小村,和乡亲们一起不畏强暴,奋勇抵抗着大举侵犯的罗马军队。他是法兰西(古高卢精神的继承者)大众文化的象征,他最显著的性格就是幽默,他和同伴们还具有高卢人常有的诸多优缺点:贪吃、爱喝、好吹牛、夸夸其谈、耍小聪明、雄辩、有计谋、标新立异、慷慨大方、不屈不挠,正如一个法国女读者所说的,“他们跟我们一样,阿斯泰里克斯就是我们的自我”。人们喜爱阿斯泰里克斯,恰恰是因为他身上除了有诸多优良品行之外,还有那么多的小毛病。
现在,阿斯泰里克斯已成为法兰西文化整体的一个象征,到一九九六年底,整套系列漫画已有三十本,被译成七十八种外文,销售量突破了两亿八千万册。据最新报道,法国人已把阿斯泰里克斯这一高卢人形象搬上银幕。(注:据《环球时报》1999年3月5日报道,这部影片名为《阿斯泰里克斯和奥贝里克斯大战凯撒》,制片人是克洛德·贝里,由克洛德·齐迪执导,影星钱拉·德帕迪厄和克里斯蒂安·克拉维耶主演。)在巴黎北郊的普拉依,建有一个名为“阿斯泰里克斯公园”的游乐园,内中有高卢村、罗马城、古代城市街道等复古景观,有古代市民生活的表演专场演出,当然,也有过山车、激流船等现代游乐场“必备”的设施。“阿斯泰里克斯公园”每年有上百万游客光顾,其数目尽管远不如同在巴黎郊区的迪斯尼乐园,但它毕竟在以传统文明与强大的迪斯尼文化作着抗衡。
约二十年前,笔者的第一个法国老师讲了一个流传在法国的笑话,说是有日本游客游览巴黎,见到巴黎圣母院时,法国导游解释说,它前后经一百余年方才建成,日本人说,若是他们来建,用一年时间即可。接着,见到凯旋门,导游说,造它时,一共花了三十一年时间,日本人大言不惭,称他们三个月就能完工……最后见到埃菲尔铁塔,日本人先问,这又花了几年才造成的?早已憋着满肚子气的法国人不无幽默地反唇相讥:“什么,什么?今天一早我路过这里时,还没看见有它呢!”
法国人有谚语:“巴黎不是一日建成。”埃菲尔铁塔能在一天内建成吗?我们可以把这则笑话改编一下,使它富有中国特色,我们应该问两个问题,其一:万里长城能在一天之内造成吗?其二:它会毁于一旦吗?
标签:法兰西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法国埃菲尔铁塔论文; 巴黎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加拿大法语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法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作家论文; 法语联盟论文; 法国留学论文; 法国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