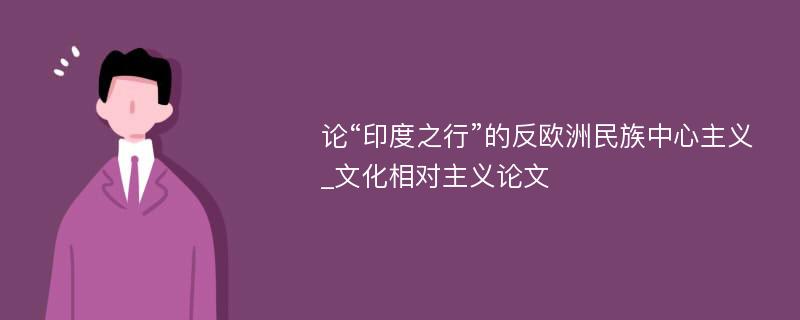
论《印度之行》的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欧洲论文,之行论文,主义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的英国作家E.M.福斯特在他的评论集《小说面面观》中对文学批评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如果我们有能力或被允许把视野更加扩大。……我们得出的结论便大不一样。”(注: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11页。)1924年问世的《印度之行》是他最负盛名的小说之一,讲述两位英国女士的一次印度之旅。在对《印》的评价中,有人认为这是福斯特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作,因为它承袭了许多写实主义的技巧和风格,如小说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按时间顺序安排起首、发展、高潮至结尾,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结构。另有人认为该小说的“不凡之处在于运用了象征手法”,(注:Babara Rosecrance,Forster's Narrativ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186.)显示出福斯特作为现代派作家的创新意识。不论定调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这两种意见强调的都是这部作品的艺术特点。如果挖掘其思想价值,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部作品的跨文化性。考察福斯特全部的作品,我们看到,他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在多部小说中逐渐展开,从早期《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直至最后的杰作《印》,他的笔触渐自深探异国文化,这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在他对大不列颠文化和外族文化的比较中,福斯特表现出超越他时代的民族平等、文化等值的民主思想,这在他的时代更是难能可贵。该小说虽然在写作手法上较多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但更大的力度则来自于其超前的民主文化意识。我们认为,这才是《印》被称为现代主义作品的思想价值所在。
福斯特在比较英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时,能够跳出其时代和民族的主导思想的桎梏。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是当时大英帝国乃至全欧洲的垄断价值观和意识,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福斯特以深刻的社会良知和清醒的理智在《印》一书中对跨英国和印度文化现象进行了描述与分析,率先发起对欧洲民族中心主义的自我批判,从而使这部作品透出超越他时代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民主思想锋芒。正是开文化相对主义这一现代民主思想潮流之先风,《印》具有了文学作品的深刻主题意义,因而有了最大的价值存在,成为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中一部优秀的作品。
民族中心主义认为本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衡量其他民族意识和行为的标准。其极端化的表现是‘文化沙文主义’,即认为“自己的风俗和信仰无可质疑地优越于其他民族”,(注:Michael C.Howard,Contemporary Cultural Anthropology,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e.,1986,p.13.)“自己的文化模式是‘自然的’,‘合理的’,而其他民族的则是‘不好的’,‘奇怪的’或‘难以理喻的’。”(注:Oriol Pi-Sunyer,Zdenek Salzmann,Humanity and Culture:An Introductionto Anthropolog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8,p.483.)
古希腊旅行家Herodots也许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民族中心主义”观点的人。他认为“每个社会的人都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佳的。”(注:郑金德:《人类学理论发展史》,台湾1978年版,2页。)以后,欧洲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兴起、高涨到衰落的三个阶段。从16至18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主要进行领土和经济掠夺。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和思想上受启蒙主义的影响,他们力图在殖民地推行欧式教育和生活模式,诱导或强行土著改变原宗教信仰,按欧洲模式界定土著的道德标准和其他社会行为准则。19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生物竞争原则(the Jungle Law)泛化,从而助长了人类社会恃强凌弱,竞争生存的强权政治。人类为生存而相争是合乎道德的;拥有先进武器的白人战胜和奴役殖民地土著也是合理的;强大的殖民主义者淘汰或改造弱小民族就是推动社会进步。因此,这一世纪成为种族主义(Rac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时代,欧洲民族中心主义浪潮空前高涨。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科学技术尤其交通运输的发展、世界人口的剧增等等因素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逐渐形成了民族平等、公平竞争、世界大同的新观念。在多元民族文化的现实中,人们动摇了过去笃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衡量价值观念的全球统一标准。在逐渐开放的现代社会中,具有宽容精神、人道主义和民主倾向的文化相对主义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成为当代社会民主意识的一部分。随着本世纪60年代美国民主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的大发展,美国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概念从此风靡西方思想界。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种价值都是相对的,没有普遍的标准。”(注:郑金德:《人类学理论发展史》,台湾1978年版,85页。)“任何习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都是同特定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应该在其相关的社会环境中设身处地地来理解和评价这些观念。”(注:Richard A.Barett,Culture and Conduct-An Excursion in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New Mexico,1984,p.13)不同的社会土壤产生不同的文化,各民族文化没有高低贵贱。文化相对主义无疑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的大背叛和大批判。
然而早在“英国维多利亚余风犹存,西方殖民主义悍悍然,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仍占主导地位”(注:朱望:《以文学人类学方法析〈印度之行〉中的文化体系》,见《思想战线》,1996年第2期,38页。)的本世纪初,福斯特就单枪匹马地发起了这种背叛。在《我的信仰》一文中,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国家和朋友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希望我有胆量来背叛国家。”(注:候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157-158页。)《印》充分表现了福斯特的这种胆量与社会良知。作为一个英国人,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尖锐地指出他的同胞普遍有颗“发育不良的心”,(注:E.M.福斯特:《关于英国人性格的说明》,见《福斯特散文选》,李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5页。)批判了英国贵族阶级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冷漠与伪善;他甚至敢于对当时普遍崇尚的民族中心主义这一殖民主义的文化实质进行揭露和鞭挞,指出由于这种文化观念对英帝国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影响,英国民族劣根性从而无限膨胀。因此在与印度人民的交往中,他们撕下伪善的面纱,露出赤裸裸的轻蔑。冷漠甚至冷酷、排斥和歧视民族已成为英国殖民者的一种普遍态度。
在作品中,印度人与英国人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这种殖民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矛盾斗争的社会氛围无疑有碍甚至有害于极少数怀有良好愿望的个人。刚从英国来到印度的穆尔夫人和奎斯蒂德小姐,以及在印度任中学校长的菲尔丁都渴望与印度人平等交往,真诚沟通。他们分别与印度人阿齐兹构成三对个人交往的关系。怀有友好愿望的个人之间可能建立良好关系吗?英国殖民主义者与印度殖民地人民之间为何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笔者将以阿齐兹为中心,分析他与这些英国人放射状的关系,从而揭示出福斯特在思考这两个问题时对欧洲民族中心主义的反思,在描写各个人物特别是塑造印度人为主角时所体现的文化相对主义意识。
福斯特对印度民族深入细致的观察、对印度文化的赞赏和对印度人民的同情都集中地体现在阿齐兹这个人物身上。因此,“阿齐兹是福斯特塑造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注:约翰·塞耶·马丁:《论〈印度之行〉》,见杨自俭译的《印度之行》的附录,385页。)阿齐兹是其民族性格的典型代表。他真诚善良,热情好客,助人为乐。与他的同胞一样,他怀有虔诚而热烈的爱国情绪和宗教情感。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激起了他对英国人的仇恨,使他的爱国情绪高涨。在全书中,福斯特淋漓尽致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歧视和压迫。阿齐兹的英国上司为了显示权势,常常无缘无故将他呼来唤去。他租下的马车,上司的夫人和她的朋友“竟一声不问就坐上悠然而去”。在英国人居住区,“那些笔直的街道都以战胜印度的将军的名字命名,这是大不列颠撒向印度的一只大网的象征。他感到自己已经落入了他们的大网之中。”(13页。本文除特别指明,译文均出自杨自俭、邵翠英翻译的《印度之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页码随文标注)阿齐兹感到屈辱无比,“必须从英国撒下的网中逃脱出来”的爱国激情勃然而生。因此在与朋友们讨论和英国人建立友谊的可能性时,阿齐兹就断然否定之:“何必讨论与那些家伙交不交朋友?统统没有必要,我看还是把他们赶出去,好让我们自己快活快活。”(9页)
另一方面,因为阿齐兹是一名西医,受过西式教育,他自然比其同胞更多地遭遇与西方人的碰撞,产生更复杂的内心矛盾。作为殖民地被压迫人民,英国殖民者的大英民族中心主义也对他产生无形的影响,使他下意识地承认西方人高人一等,从而产生自卑心理。印度同胞之间的宗教、民族隔阂使阿齐兹对其团结统一失去信心,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民族自卑感。因此,在与英国人的交往中,阿齐兹表现出极大的矛盾心理。他时而象孩子一般纯善友好,时而又是一个激愤的爱国者;遇到少有的善良英国人时,他欢喜之际不免流露出受宠若惊的自卑;他与英国人的友谊是执着的更是脆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卑、本性的善良友好和本能的防范排斥在阿齐兹身上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他在跨文化交往中常常表现为爱走极端。这是殖民地人民深受殖民主义和欧洲民族中心主义之害而产生的典型心态。福斯特对这种扭曲心理的观察与分析准确无误,入骨三分。他对阿齐兹即印度人民的理解与同情是真诚而又深沉的。
有别于带有浓厚大英中心主义思想意识的绝大多数英国人,穆尔夫人基于宗教的人道主义使她成为了阿齐兹和其他印度人心目中英国人的最高典范。她坚信“印度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上帝让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让我们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并要我们把这爱变成实际的行动。上帝无所不在,当然印度也不会例外。”(54页)正是这种尊重印度民族,包容和接纳印度文化的基督博爱精神使穆尔夫人在这一点上不自觉地与欧洲民族中心主义相悖,而与文化相对主义达成一致。她刚刚踏上印度这片土地就了解到当地的风俗习惯。进寺脱鞋一个举动和“有人看见没人看见都一样,上帝在此。”(18页)一句话就打动了阿齐兹的心。这次与友善英国人的际遇使阿齐兹把满腔热情都投入到他与穆尔夫人新建立的友谊之中。宗教相通和民族平等构筑了他们之间友好情谊的基础。穆尔夫人深受印度人崇敬,更在于她的公正和对本族自我批判的勇气。在初识阿齐兹并听他诉说了上司夫人的所做所为之后,穆尔夫人批评了自己的同胞,对他表示了同情。就此事与儿子朗尼谈论到殖民者对印度人的歧视时,她察觉到朗尼已经完全放弃了“他少年时代信仰的人道主义”,(54页)变成了冷酷的殖民者。穆尔夫人痛惜地感到:“只要有真正的悔恨之情,朗尼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人,大英帝国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国家。”(54页)能够从道义上审视自己的国家而对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表示反对并希望改革之,这个人物无疑带上了福斯特理想主义的色彩。英国著名的福斯特评论家约翰·塞耶·马丁将穆尔夫人评价为一个“基督教人道主义者”,(注:约翰·塞耶·马丁:《论〈印度之行〉》,见杨自俭译的《印度之行》的附录,374页。)许多评论者同意这一观点并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这是穆尔夫人思想的核心或福斯特塑造这个人物的指导思想。但笔者认为,穆尔夫人这种仁爱与宽厚、公正与义愤来源于福斯特超越了单纯宗教博爱的人道主义,体现了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的进步倾向和民主精神。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同情和怜悯,那么后者便能激发反叛和革命精神。福斯特安排的高潮情节正是趋向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与暴动。在阿齐兹与英国人打官司时,支持他的印度人在法庭内外“呼唤穆尔夫人的声音接连不断,人们象念咒文一样地重复着她的名字,……穆尔夫人这几个音节已经印度化,喊出来就变成了‘埃思米斯-埃思莫尔’……”(255页)印度人将她与印度女神的名字等同了起来。福斯特塑造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认同的形
象,无疑是企图表达他的一种新思想,树立他的一个理想——废除欧洲民族中心主义,建立民族独立与民族文化平等的民主秩序。这便是现当代文化相对主义的主旨。然而,穆尔夫人黯然去世的结局暗示了在当时欧洲民族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中,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理想。
与阿齐兹发生密切关系的奎小姐本意是来看望她的未婚夫朗尼,顺便“看看真正的印度”。(23页)朗尼是英国殖民者的典型代表,他们本着英国文化价值取向和英国利益对印度人实行所谓的“公平裁决,为他们维持社会安定”。(53页)“我是为事业才到这儿来的,是为了用强权控制这个不幸的国家才到这儿来的。”(53页)“只要宗教不违背国歌的意旨,朗尼就赞成,但如果这种宗教试图影响他的人生哲学,他就要反对。”(55页)福斯特显然用一种厌恶的笔调来描述朗尼所谓优等民族的傲慢心理和施恩态度,进而揭露了朗尼之流以大英民族中心主义为心理基础的人生哲学。与朗尼不同,奎小姐是个心地纯善,好奇好学,无根深蒂固的大英帝国价值观念的英国小姐。这个人物是福斯特用来向欧洲民族中心主义挑战的又一个筹码。当她发现英国夫人们对本地人的冷落和歧视后,奎小姐善的本能使她焦虑:“我听说,一年之后我们都会变得粗暴起来。”(166页)她拒绝其同胞对她进行殖民意识同化:“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绝不应该变成这样一种人。”“我要与我的环境对抗,去避免成为她们一类的人。”(165页)然而,奎小姐毕竟没有了解和完全接受异族文化的心理准备;她生活在英国殖民者之中,无意识地多少接受了本国人灌输给她的对印度人的偏见与不信任,这成为了她产生错觉的心理诱因。因而在与印度人一起游览山洞时,误解了阿齐兹,将他告上法庭,造成了后果严重的“马拉巴山洞事件”。面临来自英印双方的压力时,在真理正义与谎言欺诈威胁之间,奎小姐的良知终于被唤醒。她鼓足勇气,冒着被当作判国者的危险撤回起诉,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解除了加与阿齐兹的不实之词。这场戏写得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法庭上一个拉布风扇的卑微的印度人“触动了这个出身英国中产阶级的姑娘的心,遣责了她那所谓苦难的偏狭之见。她凭什么把这么多人聚集在这儿?是靠了她那贴着特别标记的主张,还是靠了那个持了偏见的把她的主张神圣化的耶和华?——他们凭什么声称其权力在世界上如此重要?他们凭什么戴上了文明这顶桂冠?”(248)这个好似不经意设计的贫苦印度人在情节中预示着一个转机,因为这唤醒了奎小姐被成见所遮蔽了的良知;同时这又是一个表达福斯特怜悯贫苦人,更同情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民主思想的动情点。福斯特通过奎小姐这个人物形象对“神圣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发出质问,对那“贴着特别标记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提出了最早的批判。这个人物的经历和心理转变是*
杂曲折的,因而是真实可信的。奎小姐在“马拉巴山事件”中由误解到迷茫再到认清形势后反悔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当时跨文化交往的困难何其之大,大国民族认可弱小民族自尊与平等是何等艰难,因而更反衬了福斯特对本国民族中心主义进行自我批判精神的可贵。福斯特以其文学的方式喊出了现代思潮——文化相对主义的先声,他超前于时代的质问与批判在当时一定震动了读者的心灵。
菲尔丁可以说是一个颇有文化相对主义意识的英国人,是又一个福斯特反大英殖民文化,建立民族平等意识的代言人。在他管辖的地区学校中,“他从不反对学校接受印度学生”;在他对印度孩子的教育中,他不用传教士的方式,而是用“平等交换思想的方式进行了个人交谈”。(67页)对于他在印度的英国同胞来说,他是异己分子,他的民主平等思想是“毁灭等级制度的力量”。(67页)菲尔丁是唯一深入和欣赏印度生活的英国人。福斯特借他之口表达自己对印度文化体察入微的观察和高度的赞赏:“(印度)文明是从高贵的印度人一坐、一卧、一举、一动的姿态之中表现出来。……这里显示的文明是西方人可以把它搅乱但却永远学不到的。”(284页)福斯特就此对印度人如动作、声息、服饰、生活用品到宗教仪式等的细节描写铺陈了一幅印度生活的人文景观,传达了作者文化相对主义的民族学观。福斯特通过菲尔丁之口表达了“避免从本国文化角度去评价他国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多样性采取宽容,理解和尊重的态度。”(注:Fernando Poyatos,Literary Anthropology-A New 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 to People,Signs and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Brunswick,1988,p.xv.)菲尔丁的民族文化平等观使菲尔丁有可能与阿齐兹建立兄弟般的情谊,甚至与印度人并肩战斗,而不畏成为一名“反英分子”、“煽动叛变的家伙”。(199页)然而,在英国和印度民族矛盾无法解决的大前提下,怀有“友好愿望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建立长久的友谊的。福斯特直接向读者指出殖民主义和欧洲民族中心主义在跨文化交往中的破坏作用,他赋予全书一个政治立场鲜明的结尾,清醒而又遗憾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福斯特将印度的寺庙、大湖、神殿、苍天都拟人化,让天地发出“不,你们现在在这儿不能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呼喊,宣告了阿齐兹与菲尔丁及全书中所有“怀有良好愿望的”英国人之间友好关系的破裂。阿齐兹向菲尔丁的告别:“无论如何要打倒英国佬,这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我们要摆脱你们,还需要五百年。那好,我们会把所有该死的英国人都统统赶到大海里去,到那时候我们一定会再成为朋友。”(371页)这无疑寄托了作者的期待,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和友谊必须建立于民族独立和民族文化平等之上。
《印》选取了世纪初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现象作为素材,福斯特以文学的方式对当时西方的垄断价值观——欧洲民族中心主义率先进行了批判,造成的客观效果无疑是开创了现代文化相对主义之先风。作为生活在20世纪初的英国人,福斯特能够“不带民族偏见和歧视,对民族特别是殖民地民族的文化进行公正评价,并籍此表达对受压迫民族的同情,对自己民族的殖民统治意识予以批判,……确实难能可贵。”(注:朱望:《以文学人类学方法析〈印度之行〉中的文化体系》,见《思想战线》,1996年第2期,38页。)正是其超前的民主文化意识赋予了这部以传统手法写成的作品一个鲜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特质。从而也给“《印》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现代主义作品?”的争论提出一个明证。《印》正因为蕴涵着前卫的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观点,显示了文化相对主义这样超前于时代的民主思想而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因而震撼了一代代读者,成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