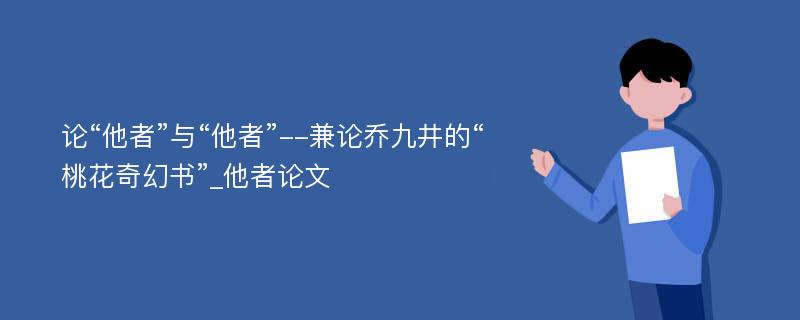
讲述“他者”,讲给“他者”——辻井乔《桃幻记》①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讲给论文,辻井乔论文,桃幻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当代作家辻井乔的《桃幻记》,在日本文学中属于极为特殊的“异例”。众所周知,日本文学史上有过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古代自不必说,近代以后,比较知名的作家如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中岛敦、横光利一、武田泰淳、井上靖、山崎丰子乃至村上春树等,都留下了熠熠生辉的“中国文本”。这些作品要么取材于中国古典,成为日语中所谓的“翻案文本”,要么取材于作家本人在中国实际生活经历,成为“记忆文本”,要么取材于中国历史,成为“历史文本”,及至一九九五年,才终于出现了以当代中国为题材的作品。②所以,《桃幻记》这部收录了八篇以当代中国为舞台、且故事是完全虚构、登场人物完全都是中国人的短篇小说集,当是独此一家,绝无仅有。
只是,出版方集英社却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桃幻记》文本的特殊性,甚至书腰上也只是“点到为止”的宣传语:“抒写当今中国的短篇集。细致描写了生活在动荡历史中的中国人的日常细节和精神世界。”由于收入其中的小说都是以“文革”前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当代中国为主轴的,日本读者对它的读解,自然而然地就集中在了对“文革”期间中国人生存痛楚的同情和对“文革”的批判,③对中国人敢于直面伤痕、勇于跨越逆境的生活态度和人性成长的赞赏,④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后如何保持传统等问题的忧虑⑤上。
辻井乔的文学深沉凝重,多表现现代人的孤独和抵抗,关注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关联,饱含对战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忧思,被认为是日本最后一个战后派作家。这样一个日本作家,他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中国题材的作品?如果按照《桃幻记》后记所提示的方向理解,小说是要“描写我所感受到的中国”(第146页),那么他是为了什么表现中国?这样一部“另类”的表现中国的作品,对日本、对中国,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这应该是进入《桃幻记》文本之前或之后,每个读者都会思考的问题。
“他者”是西方哲学和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拉康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中,借用“镜子”的概念,形象地揭示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他认为,一如婴儿最早是通过镜子中出现的自身的影像——亦即他者——才唤起自我意识一样,从“他者”出现在“镜子”之时起,人的自我意识才得以真正确立。也就是说,没有“他者”,便无所谓“自我”。这种认识,恰恰是开启《桃幻记》大门的钥匙。
《桃幻记》中很多篇章的主人公都富于自省的性格,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陵之墓》的徐怀宾、《发现者》的李志远、《柳絮飘飞时节》的李士友、《神树》的杨国伦等,他们身上充满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质疑、对自我的反思、对历史与现实的再认识以及对自我的再认识,而这一切,都是凭借“他者”的出现才得以实现的。这个“他者”,在李志远,是初恋情人在“文革”中平步青云、在“文革”后悄然自尽的际遇;在杨国伦,是离开香港、“落叶归根”后整理乡土史过程中接触到的人和事。由于“他者”的介入,使李志远看清了初恋情人作为“文革陶俑”、自己作为“签名陶俑”的存在本质,也使杨国伦找到了“把自己的痛苦放到历史中去定位,使之成为客观的东西”(第58页)的契机。
《柳絮飘飞时节》的主人公李士友是武汉一家大医院的医生,业务过硬又不善张扬,在院方处理副院长兼外科主任手术事故的过程中,被指定为“替罪羊”。李士友念及副院长一直待自己不薄,加之院方保证风头过后就让他回来并予以重奖,便慨然应允。被指派到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山区的李士友,从护士赵翠的来信中得知人们已经看透了这场骗局,要为他申冤,但为了不连累赵翠,硬是拒绝了赵翠的好意。断绝了同赵翠的书信往来后,李士友完全与世隔绝了,然而,回想起大医院里的尔虞我诈,李士友反倒觉得眼下的日子过得心安理得。特别是在接到院方的开除通知和赵翠的死讯后,他更加坚定了在乡间行医的决心,好像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
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中,“他者”总是凌驾于“自我”之上,规定着“自我”的存在,“自我”也总是在与“他者”的协同、调和的过程中求得赖以存在的基础,使“自我”的尊严获得保证。李士友发现自己可能会就这样不清不白地终其一生时,也没有萌生一丝一毫的抗争的念头,而是选择了进一步地放逐自己——到更内陆的无医村去。这种看似懦弱的对荒诞命运的坦然接受,却恰恰体现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自我意识。李士友的“自我”在副院长打着为全院着想的旗号力劝他以进修的名义代己受过之前,一直是处于蛰伏状态的,不曾有任何事情让他对“自我”有更多的意识。李士友之所以能接受副院长的无耻要求,原因除去副院长待他像待家里人之外,还有自认为这是搭救恩师、挽救医院声誉的仗义之举的想法夹杂其中。能为他人所不能为,这令李士友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成为他自我意识萌生的根基。而赵翠的死,让李士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第92页),他开始审视自己的自私,为自己的傲慢生硬而懊悔,心里感到“一阵刺痛”(第92页)。尽管李士友也曾对是否继续行医产生过迷惘,但他终于若无其事地收拾好出诊用的药箱,冒着无照行医的风险,去为苦于病痛的村民看病了。李士友的存在不乏“他者”的恶意捉弄,但也正是在“他者”的狞笑中,他悟出了“医”的真谛,确立了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自我存在价值,开始了自己掌握命运的尝试。
《李陵之墓》的主人公徐怀宾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青年“海归”。在美国留学时,美国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个“他者”让徐怀宾确立了新的“自我”——一个已经可以“将中国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眺望”(第8页)的学者。一直为此自鸣得意的徐怀宾,回国后亲身体会了温馨的日常生活,遂对汉代名将李陵的遭遇产生了新的理解。然而,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六十年代后期逃往海外的前辈历史学家以自身的经历和理解告诉徐怀宾:“在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时候,周围环境如何并不能成为条件……学者生存下去的根本,是要坚守自我,并非是考虑结果再去行动”(第8页)。在这个强有力的“他者”面前,徐怀宾产生了极大的动摇,直至面对庞大的李陵墓遗址才警醒过来:“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什么事都得不出结论的人……就连关于李陵到底是以何种心情滞留匈奴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有人认为是作为古代武将自我惩罚的意志使然,他会点头同意;而教授说李陵是逃亡者,他也首肯称是。这是因为自己心里作为一个人的判断中心尚未形成的缘故”(第16页)。显而易见,是“他者”的出现,才让徐怀宾对自己产生了自省,看清了自身的弱点,并认识到了“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自我”意识的紧要。
从现象学的理论上讲,“他者”的所指非常明了,即相对“我”或“自我”而言的所有“他人”、“他我”。虽然由于对“自我”的认识不同,使得“他者”的定义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但“他者”归根结底还是意味着那种“将自我存在的危机和非对称性予以揭露的东西”。⑥进一步讲,没有对“他者”的认识,就不会有对“自我”的意识,“他者”既起着颠覆“自我”的作用,又起着建构“自我”的作用。尽管事实上“他者”多是扮演着隐喻的角色,但无论怎样以隐喻的方法引入“他者”,最终都有必要回归到“自我”上去,“自我”才始终是言说的主体。《桃幻记》几乎每篇都设置了回归“自我”的装置,这使得整部小说集通过“他者”这面“镜子”映照“自我”这条红线清晰可见。《桃幻记》的主人公们都是在层出不穷的“他者”的步步紧逼之下,或主动或被动、或清醒或懵懂、或艰难或顺畅、或遍体鳞伤或水到渠成地感受着“自我”,确立着“自我”,完成着“自我”。他们的生存样态,是中国人“文革”后普遍的生存样态,却被日本作家辻井乔呈现在了日本读者面前,这意味着什么?
在文本的叙事上,《桃幻记》的每个故事都是由一个全知全能的讲述者叙述的,讲述者站在时间和空间的高处,鸟瞰历史和世界,进行冷静而客观的描述,加之倒叙、插叙的方法,更增添了叙述历史和世界时的回顾意味和沧桑意味。以这种叙事方式描述重大历史事件时,笔调和语气往往是平和的、节制的,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大变动,就会被平和而节制地以“个人史”的面貌再现出来。
《世事无常》就是这种叙事方式的典型文本。作品历史跨度相当之大,涵盖了女主人公八十六年的个人人生经历和此间中国的社会历史变故。出生在北京琉璃厂一家老字号店铺“贵宝堂”的马瑞钧,经历了初恋、抗战、结婚、北京解放、政府接收店铺、丈夫被枪决、再婚、“文革”、逃难、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等人生及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化。如此宏大的历史变故,在万余字的短篇中得以精彩呈现,又不给人以一种“流水账”的感觉,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叙事。
步入老境的马瑞钧回到北京,租住在老旧的民房里,习惯了把藤椅放在路边,坐在那儿看着过往的行人想想心事、打打盹儿的生活。
瑞钧坐在那儿,后背微微有些弯……女儿戴了一副亮闪闪的耳环,穿的衣服看上去做工很好,恰到好处地显露出她腰部的曲线。这好像完全没有经过革命嘛,想法和我少女时代一模一样的。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眼下状态的不满,她大吃了一惊。现在,她很是怀念革命开始后街头巷尾的那种紧张气氛……望着往来的行人,马瑞钧时常想,为什么自己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呢……马瑞钧反省自己,却寻不出答案……马瑞钧活动活动身子,现出一副苦涩的表情,注意地看着往来的行人。她对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尤其留意,想来,比她小六岁的楚风之也该八十了。当然,我们无法搞清楚马瑞钧的意识里是不是在寻找自己的丈夫,我们能搞清的只是,在无常的世道中,自己不知道去了何方。(第31-32页)
作品在通过“个人史”来探究社会历史重大变故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社会历史重大变故的认识时,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更有利于内容的展现。在上面引用的这段叙述中,前半部分的讲述者自己处于故事之外,用可以随意变换的上帝般的眼光,对马瑞钧及其女儿的衣着外貌、行为举止、心理活动了如指掌,悉数讲述给读者。作品采用的几乎都是这种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事(亦称作“零聚焦叙事”),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潜入主人公马瑞钧的内心,将其对世道变迁的不适应和对自己人生的疑惑和盘托出。只是,在这种整体的全知叙事的大环境下,作品中还存在着视点转换的情况。上面这段文字中描写瑞钧女儿的穿戴后的“这好像完全没有经过革命嘛,想法和我少女时代一模一样的”一句,就换成了瑞钧的视点。作品中其他段落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描写瑞钧和接管了“贵宝堂”的党代表楚风之结婚、生女后的幸福感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瑞钧感到很幸福。过世的父亲、被枪决的长兄和前夫常常把革命的恐怖挂在嘴边,可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治安好得非过去所能比,街路上干净得没有蚊蝇、不见纸屑,街道的品位也大有提高,只是听琉璃厂以前认识的几个店家说,买卖不好做了,那些干部不懂生意,活儿干得没劲什么的,可这已经与瑞钧没什么干系了。(第27页)
尽管一头一尾的两句依然是全知全能叙事,但中间部分很明显是从马瑞钧的视点来看待当时的社会境况的。在接下来描写“文革”时造反派冲击“贵宝堂”进行打砸抢的部分中,采用的也是马瑞钧的视点:
有一天,街道入口处突然打出了“造反有理”的大旗,还出现了一群举着“打倒走资派”的标语牌的年轻人。那天早晨……她……忽然听到砸东西的声音,朝窗外一看,只见一伙年轻人正抡着棍棒往琉璃厂一家店铺里闯,另一伙人则正朝贵宝堂这边跑来。(第27页)
在这些地方,作者暂时放下高高在上的全知叙事,转而用主人公的眼光进行叙述,为的是让读者站在主人公的一方,同她一起感受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达到感同身受的效果。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时以全知讲述者的视点、有时以主人公马瑞钧的视点进行叙事,但作者辻井乔,才是统领这些视点的主宰者。
通常情况下,作者支配下的讲述者只是站在高处娓娓道来,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而在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的最后,一直鸟瞰下界的讲述者却降至和读者同样的高度,并站在和读者同样的角度看着瑞钧:“我们无法搞清楚……我们能搞清的只是……”根据热奈特的理论,叙述者的功能除了讲故事、叙述文本(即指明内在结构)、叙述情境之外,还具有交际职能和情感职能,叙述者可以插入解释和辩解性的话语,以表达作家的思想和情感。⑦可见,辻井乔正是借助了叙述者的这些功能,并充分利用了视点转换的优势,是要通过讲述者的口,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具体而言,便是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感慨。想来,一个激情状态下的写作者,是很难生发出如此凝重、深沉的情绪的。这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的批判和挽歌的相互交织,使得这篇作品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审美倾向。
同样的感慨和情绪,在《桃幻记》其他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体现,如《发现者》、《神树》等。《发现者》中李志远的初恋情人许瑞华“文革”期间步步紧跟,不断高升,甚至被调进了中央,却在“四人帮”垮台后自杀身亡。学生时代曾经温柔细腻的少女却落得个“殉教者”般的下场,成了一个可悲的“文革陶俑”。作品在描写作为李志远的“他者”出现的悲剧人物时,同样使用了全知叙事方式,使这个追逐时代大潮却最终被时代大潮所抛弃的典型得以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讲述者在这篇作品中并没有露面,也几乎没有使用其他视点,令人感到作者辻井乔对许瑞华这一人物并未移入太多的同情,只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一点点地揭示了“文革”众生相的其中一种,并同李志远一道,对之予以无情的哂笑而已。辻井乔在这篇小说中唯一一次使用李志远的视点,是在临近结尾的地方感慨了一句“学生时代她是一个多么温柔细腻的少女啊”(第48页),流露出一丝无奈和惋惜之情。
辻井乔写作惯于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特别是那些取材于自己特殊家世、特殊人生经历⑧的作品(如《父亲的肖像》等),更是因其第一人称叙事而时常引起孰真孰假的猜测和是否为“私小说”的争议。然而,在通过《桃幻记》为日本读者讲述一个个当代中国的故事时,辻井乔却没有选择自己惯用的叙事方式,想必是考虑到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局限。毕竟,第一人称叙事很容易情绪化,视点又太过单一,难以冷静客观地驾驭如此宏大、沉重的话题。《桃幻记》在描写中国人如何面对“文革”这场大劫难时,选择了全知叙事,使故事本身更具真实感、历史感,更具可信性、客观性,这才应该是辻井乔所想要达到的效果,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前面曾经提到,关于《桃幻记》的创作初衷,辻井乔自言是想“描写我所感受到的中国”。这也正是被出版社印在书腰上的一句话。但在这篇后记中,辻井乔还有一段话,却并没有引起出版社及更多读者的注意。
每当我接触到这样的场面和光景(指多次访华时所见——笔者注)时,令我无法释怀的就是,我国的一般民众在战争期间的遭遇和当时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对先人们历经苦难的忘却。既然如此,尽管已是三十年过去,现代的中国人们又是如何记忆始自一九六六年的十余年岁月和席卷中国全境的文化大革命的呢?《桃幻记》就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中几经修改而成的。(第147页)
辻井乔在多次访华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的多重性和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样态,于是想到母国日本,这是正常的、下意识的反应,这时,“中国”、“中国人”,虽然是作为辻井乔的“他者”出现的,但还没有形成将这个“他者”具象化的自觉。但是,当他把“他者”中国当作反思自己的历史、文化、现实的参照系时,“中国”、“中国人”便成了作为“日本”、“日本人”的“他者”这个认识装置被使用的参照物。日本虽然自古就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但却并不了解当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阿Q的阶段,所以,辻井乔才会将这篇后记定名为《阿Q到哪儿去了?》。
《桃幻记》在描写当代中国时,显得很凝重、克制。看得出,温和宁静、平实质朴的表层叙述下,涌动着无尽的感慨和飞翔的思绪。在《桃幻记》即将出版单行本之前,辻井乔特意通过出版社请几位日本的中国文学专家和活跃在日本的中国人分头校订书稿中不符合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地方,对一些人名、机构名、职务名等也一一进行了确认(第146、147页),力求细节上的完美,这都显示出作家对中国的理解和尊重。尽管如此,辻井乔毕竟是长年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当他把自己想象成中国人,来构筑笔下的中国社会、描绘印象中的中国人时,文本中不可避免地会留下日本人的视角、日本人的感觉、日本人的描述,让中国读者感觉有些差异,甚或饶有趣味。⑨然而,当这些包括误读、改写、吸收抑或重建在内的“异文化”作为“他者”被呈现出来的时候,准确与否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我们最初始的疑问也似乎就有了答案——辻井乔之所以用《桃幻记》向自己的母语读者展现一个完全非母语的世界,其终极目的,是要通过冷静而客观地表现中国、中国人对社会历史重大变故的记忆和态度,反观日本、日本人,并为之提供一个“他者”。
托多罗夫曾就“我们”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过一个“荷马法则”,指“他者”距离“我们”越遥远就越容易被美化。⑩说辻井乔对中国的抒写体现了“荷马法则”或许有些偏颇,但《桃幻记》这个短篇的标题,作者自己也在《桃幻记》中文版作者序《致中国读者》中明言是来自《桃花源记》的启发,而整部短篇小说集也选择了这个标题为总题,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极有意味的关联。中国对辻井乔来说的确是一个遥远的“他者”,辻井乔用深沉的思绪和想象,依照自己对个人、国家、命运、人性等诸多问题的理解和追求,为这个“他者”创造了存在的价值,并赋予了这个“他者”以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为其注入了一定的乌托邦憧憬。
“乌托邦式的想象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它具有‘社会颠覆功能’。”(11)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当人们感到自身文化或者所处现实暴露出诸多矛盾而无法令自身处境感到满足时,往往会在“异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出口,将其构建成乌托邦。《异邦人》是辻井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一部诗集,同题的诗中,辻井乔充满隐喻地这样认识他的母国日本:“在心灵的地图上/仿佛有一个遥远的国度/那是一块汇集起记忆断片的/沉重的国度/走近它时/它总是无奈地扭曲”。(12)中国,是辻井乔“缺席”的“异邦”,是一个“他者”,这一点早已不言而喻,但是日本,又何尝不是辻井乔“在场”的“异邦”和“他者”呢!它之于辻井乔,是遥远的、沉重的、无奈的,甚至是扭曲的。正如大汉和匈奴最后都成了李陵的“异邦”一样,中国和日本也都是作为辻井乔的“异邦”、“他者”而存在的,都是辻井乔言说自我、实现其自我主体建构的观照。就其他文本而言,在对日本的观照中,辻井乔毫不留情地在精神的层面予以过否定;而就《桃幻记》而言,在对中国的观照中,辻井乔却竭尽全力地予以了肯定,使“他者”中国具有了一定的形而上的意义,并迫切地将这些“他者”的故事讲述给同样作为“他者”存在的日本人听。
辻井乔是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中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这种意识一直贯穿在他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哲学中。辻井乔曾在谈及日本文学现状时说:“看似百花齐放的我国文学之中,潜伏着多么脆弱的部分。我们应当视之为我国文学的问题,我痛切地感到有必要通过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文学家进行对话,找出我们的问题所在。”(13)《桃幻记》,或许就是辻井乔试图通过对话重新审视自身文化和所出现实、实现文化自觉的努力吧。
日本学者竹内信夫曾指出,日本文化面对另一种文化时,多是将自己拟为对方,并凭借将自己置于同等地位的办法,将“他者”的冲击力吸收殆尽。它不是通过与“他者”的对立来发掘新的“自我”,而是将威胁到“自我”的“他者”脱胎换骨,直至彻底地将其驯化。(14)而在另一极的中国人,则似乎历来是不大在意别人的眼光的。于是,在当今世界文化大交流大交融大交锋的背景之下,《桃幻记》中一个个讲述“他者”且讲给“他者”的故事,就显得意义非凡了——《桃幻记》的“他者”意义和乌托邦意义,不仅承载了辻井乔观照日本历史、批判日本现实的意愿,而且也能让我们通过“他者”的理性刺激对我们的生存现状和本位文化做一点理性的怀疑和思考。这正是《桃幻记》的价值所在,也是它应该获得日本读者和中国读者共同喝彩的缘由。
注释:
①辻井乔:《桃幻记》,王新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本文中作品及后记等引文皆据此版本,下文只标出页码。其中所收作品先是在文艺杂志《昴》上隔月发表,2003年由集英社结集出版单行本。
②获《昴》文学奖的《韩素音的月亮》,描写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女性通过在中国的游历超越了认同危机的故事。
③川西政明:《辻井乔〈桃幻记〉》,《昴》2003年4月号。
④饭冢容:《日本作家笔下的现代中国——关于辻井乔的〈桃幻记〉》,《尤里伊卡》2003年4月号。
⑤book.akahoshitakuya.com/b/4087746402.
⑥柄谷行人:《探究1》,第2页,东京,讲谈社,1992。
⑦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第182页,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⑧辻井乔为曾两任日本众议院议长的父亲堤康次郎和非婚妻子所生,大学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后在担任其父秘书的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并接手经营西武、四季财团。
⑨如批评家李敬泽就在《桃幻记》中文版序中指出:“看这部书时,我不断地对他(指辻井乔——笔者注)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中国人不是这样感受的,中国人也不会这么想。毕竟是‘异邦人’,他看不清中国经验的细微之处。”作家铁凝也在一次日中文化论坛的基调讲演中提到:“主人公们虽被设定为中国人,但他们身上有些东西却不是中国人的,比如《发现者》中的李致远,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但他身上却带有外国人的味道,《世事无常》的主人公马瑞钧亦然。于是,读这样的小说时,说实话,我时而会感到别扭或不够劲儿。”
⑩托多罗夫:《我们与他者》,第452页,小野湖、江口修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1。“荷马法则”源于公元1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本(Strabon)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对于荷马来说,最遥远的国度是最美好的。
(11)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第12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2)辻井乔:《异邦人》,第41页,田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辻井乔:《日本文学的现状》,李锦琦译,《作家》2003年第1期。
(14)竹内信夫:《日本文学中他者的谱系》,鹤田欣也编:《日本文学中的他者》,第96页,东京,新曜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