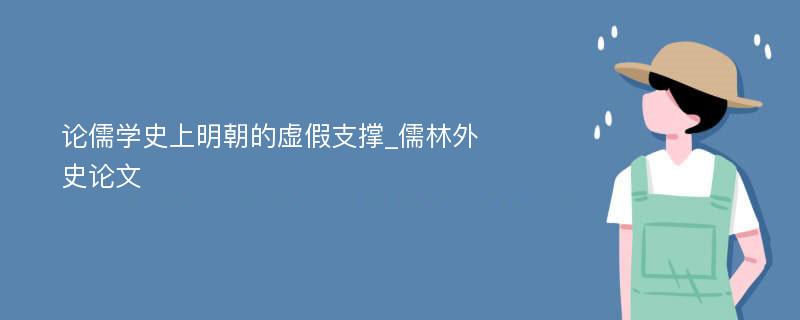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林外史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420(2000)01—0100—05
《儒林外史》以明代社会为背景,实际描写和反映的主要是清代的社会生活。这种情况向来被视为“假托”,并被认为作者所以如此,一是要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开文字狱的迫害和其他可能的干扰;二是其时尚有明季遗风,托明事以写当代也最为方便。总之,这是个表现手法问题,作品对所托的明代并无认真的反思和深入的表现。因此,很少有人把《儒林外史》与明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研究者对此书内容和思想倾向的认识,除一般地说到“对明、清科举制度的批判”云云之外,绝少涉及作品写及明代历史的意义,以为那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这是《儒林外史》研究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从理论上说,《儒林外史》的假托明代不可能只是一种形式,而必然包含相应的内容,即它托明写清的地方就是明、清共有或可能共有的。读者若单认它写了清朝,而以作品之描写与明朝并无关系,就未免深求而失诸伪了;而且《儒林外史》的假托明代不仅是借一个年号,而是在给全书一个几乎是明代全史的框架的同时,还有关于明代人物事件的具体描写和议论,是决不可以忽略的。因此,即使不从它写清即是写明的辩证效应去看,而单论其有关明史的实际描写,也是全面考量和正确判断该书思想价值的应有之义,为之试论如下。
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祸连绵,小说家下笔多忌讳,反映世情往往托古,但托古的方式每有不同。一类假借其朝代岁月、人物姓名,而故事并无根据,如《绿野仙踪》的“点缀以历史”(注:转引自侯忠义.绿野仙踪(校点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红楼梦》甚至“并无朝代年纪可考”(注:红楼梦.第一回.)等,对所托之“古”并无认真具体的描写,从而没能形成真正思想的意义;二是假借其朝代岁月,同时穿插描写了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显示了作者褒贬爱憎的倾向,表现了作者对所托时代历史过程的某些认识。这部分内容虽然最终配合作品表现当代的中心,但自身有一定独立的意义,构成作品内容的一个方面,如《女仙外史》写唐赛儿起义和燕王“靖难之役”,《歧路灯》中有关明嘉靖间朝政的描写议论等都是如此(注:参见拙作《女仙外史》的显与晦[J].文学遗产,1995,(2).关于《岐路灯》的几个问题[C].文学论丛(4).)。《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而且典型地代表了考据之风方兴之际的清中叶知识分子对明史特有的关怀和认识,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一定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
作家是创作的主体。作者的身世经历素养兴趣从根本上决定作品的面貌。吴敬梓出身科举世家,自幼笃好经史。吴檠的诗说他“何物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注:转引自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4.)。金榘赠他的诗中也说:“见尔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秘函。”(注:转引自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4.)据平步青《霞外捃屑》记载,吴敬梓曾撰有“《史汉纪疑》未成书”,可见他早年对《史记》、《汉书》是下过功夫的。这影响到《儒林外史》的创作,卧闲草堂本第一回评说:“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宫”;第二回评说:“非深于《史记》笔法者,未易办此”;第三十三回评说:“想作者学太史公读书,遍历天下名山大川,然后具此种胸襟,能写出此种境况也”;第三十五回又评说:“作者以龙门妙笔,旁见侧出以写之”;第五十六回回末总评又照应说:“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也说,《儒林外史》“源出太史公诸传”(注:也不乏说《儒林外史》“篇法仿《水浒传》”(黄小田:《儒林外史评》),或说“《外史》用笔实不离《水浒传》、《金瓶梅》”(张文虎:《儒林外史》评)者,但关于《水浒传》、《金瓶梅》的评点也往往要说到仿《史》、《汉》笔法,与上引诸说并无矛盾.)。虽然动辄以《史》、 《汉》相标榜为明清小说评点家之习,但是,联系吴氏生平学问素养,上引诸说应是反映了他写作《儒林外史》的实际。
《儒林外史》本文正有着取法《史》、《汉》羽翼正史的特点。首先,此书名标“儒林”,取自《史》、《汉》的《儒林传》;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明显有“儒林传序”的性质;而全书主体叙事系统也是“纪传性结构”(注:张锦池.《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J].文学遗产,1998,(5).)。其次,自金和《儒林外史跋》,至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及其后来多家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现,也不断加强证明本书非同一般的纪实性风格,正如鲁迅所说: “《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这显然不是作者缺乏想象力所致,而是其有意把“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第五十六回),借小说以传人。故卧本闲斋老人《序》说:“夫曰《外史》,原不自居于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于元(玄)虚荒渺之谈也。”这种“纪传体”和“纪实性”,表现了作者平生耽于经史而养成的小说创作的史家态度和思路,它必然贯串体现于《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的总体构思和具体描写之中,从而读者有理由认为它的“假托”可能是有深意的。
另外,吴敬梓治史留意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而各种因素使他尤为关注明代史事。这既是他写《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的部分原因,也是他的“假托”所要表现的部分真实内容。吴敬梓的时代,由顾炎武重开端绪的汉学方兴。但是,由于环境的压迫,当时的学人大都效顾氏考据之法,而遗其经世致用的精神。吴敬梓则似乎不然。他没有史著留存下来,但仅存的一些有关史事的诗文,都不徒为考据,而是借历史事实发为关怀社会人生的浩叹。《金陵景物图诗》中《冶城》有句云:“庾亮清谈日,苏峻称兵时。”慨叹西晋的清谈误国;《青溪》有句云:“筑城断淮流,怅然思李升。”缅怀南唐李升改筑金陵的业绩;《天印山》诗序据《南史》考证“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等等,都确考时地,究论兴废。顾炎武曰:“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证古今。”(注:《日知录》卷三.)吴敬梓咏史的态度正体现了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金陵景物图诗》虽写于《儒林外史》之后,但其中治史以究兴废的学风文心却非一朝一夕之渐,不可能不早就体现于《儒林外史》的创作。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金陵景物图诗》涉及史事最多的是六朝和明代。这当然因为金陵是六朝古都,又是明朝开基立国的所在,更因为作者长期生活在这里。但是,涉及史事中明代的又多于六朝,却应当是作者对明代史事有更多关心所致,而作者并不掩饰他对金陵作为明初都城的特殊感情。且看他写“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第二十四回)一段文字,竟是充满自豪,无疑是恋怀故明感情的流露。而作者对明史的思考也可以从他最为人称道的《老伶行》一诗中窥见消息。这首诗中写康熙南巡说“驻跸金陵佳丽地,旧京凭吊思明季”,固然主要是纪事,但是,康熙“思明季”干作者何事?因吴敬梓对康熙“旧京凭吊思明季”的注意,而推想其本人之并未忘却甚至常常思考明亡之教训,应当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在清朝的文字狱箝制之下,到了乾隆初,明史早就是汉族知识分子论议的禁区(注:参见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15~17.);其时又入清已久,吴敬梓一代人生为清朝的臣民,对前明没有旧国旧君之义,自然不会有明遗民那样激烈的反清情绪。但是,他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又遭受困厄,也绝不会忘记清朝是所谓异族的统治。并且清初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的时代”(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生当其后的吴敬梓从前明遗老接受某些关于明史的认识,表现于他“假托明代”叙事跨越二百余年历史过程的小说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而使作品带有了对明史的反思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情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姚雪垠、吴组湘先生先后提出《儒林外史》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苦于没有具体的说明,迄今未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可。窃以为从此一路做深入的探讨,有可能找到较有说服力的根据。
明朝灭亡之后,学者们痛定思痛,除了恨“闯贼”和那班阉党降臣之外,很自然地就想到朝廷三百年养士,何以颠危之际没出几个力挽狂澜的干城之才?前明的遗老们几乎都归咎于科举制度的实行。顾炎武说:时文之出,每科一变。……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注: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朱舜水也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注:舜水余集·答林春信问,转引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清初这样的议论甚多,综合起来即是说八股文和理学相表里,诱困读书人于功名利禄之途,使学非所用,人才匮乏,“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注:李塨.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以至于有“断送江山八股文”之说。这些议论虽不无偏颇,却也不失为对明代弊政的一个深刻的批评。二百多年后,梁启超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说导致明朝亡国的是“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和与他们相反对的“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吴敬梓生当明遗民著作逐渐流布的时期,受到它们的影响乃是很自然的。《儒林外史》所写的正是这两种八股先生。在某种意义上,吴敬梓是把读书人的命运、八股取士制度和明王朝的兴亡联系起来作文学的思考,用《外史》的巨幅画卷形象地总结了明朝以八股亡国的历史教训。
首先,这可以从《儒林外史》的总体布局得到一定的说明。笔者以全书原本五十六回,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回“楔子”“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第二回至第五十五回是全书正文;第五十六回“幽榜”为全书结尾。这三大部分叙事流年几乎跨越整个明朝:“楔子”从元末至明洪武初,其时八股取士制度确立,作者借王冕之口论定“这个法却定得不好”、“一代文人有厄”;正文从第二回开始于成化末至第五十五回结于万历二十三年,其时八股盛行已久,人才日至于败坏,初还有虞育德、庄绍光那样的“真儒”,杜少卿那样的“豪杰”,而终于在万历二十年左右“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结尾第五十六回终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这年满洲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称帝为后金天命元年,成了明王朝后来的克星。这一年份的相值应当不是无谓的巧合。而第五十六回开篇说:话说万历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天子整年不与群臣接见。各省水旱遍灾,流民载道,督抚虽然题了进去,不知那龙目可曾观看。这番话的情调如《三国演义》的开篇,预示了大乱将作。然后是结局“幽榜”的故事,最后缀以“词曰”一首。论者有以为《儒林外史》的叙事编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很有见地(注: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J].学术月刊,1982,(7).)。若进一步指出作者精心的用意,则好像正应该从这三大部分的时间跨度上作些考虑。
明代科举取士可上溯到吴元年(1367),至洪武三年(1370)正式定科举制度、“制义”格式,十七年颁科举取士式(即八股),后乃逐步完备和近于僵化。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论及八股取士制度的变迁,以为“定于明初,完备于成化,泛滥于有清”。其实科举弊端泛滥之势早在明末已经形成。而明朝政治的变迁,洪武至宣德间为开国和鼎盛之期;正统至嘉靖间为中叶转衰的时期,一切敝政大端始于此期成化一朝(注: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第二编第三章第六节.);万历至崇祯末为后期,但论者谓“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 这个说法无论是否一定正确,却是吴敬梓时代一个很时髦的见解。把这两件事的时序相对照,洪武——成化——万历三朝,既是八股取士制度确定——完备——泛滥的三个关键时期,又是明王朝兴盛——衰落——灭亡的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儒林外史》以这三个时期分别为全书起——中——结三部分叙事的中心,特别是结束于后金立国努尔哈赤称帝的万历四十四年,其叙事编年的用心大约就有“断送江山八股文”之意。这应该就是它书名为“史”又叙事作如此大跨度安排的用意。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儒林外史》以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反映仅仅是文化的批判,而应看到它进而深入到了政治的历史的批判,即对明史一代兴亡历史教训的反思和总结。
其次,更进一步,《儒林外史》在它叙事编年的范围内穿插描写评论了明史若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在对明史作总体考量的前提下,也表现了对明史的具体看法和一般历史的观念。一是关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描写,第一回“楔子”从他“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叙起,写他入浙后戎马倥偬之中,亲临茅舍,问治道于王冕;后来得了天下,诏请王冕入朝为官,颇具明王圣君的气象。第九回还借邹吉甫的口称赞“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怎得天可怜见,让我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这反映了明清一般民众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位文人、思想家,吴敬梓更借王冕之口,着重指出明太祖八股取士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从此“一代文人有厄”;又借迟衡山之口评议“我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一部大书的主旨和叙事就是从批判朱元璋制八股、薄礼乐推衍而来。虽然这一批判不免也可以看作指向作者的当世,但是明朝的事实显然不能只是被看做清朝社会的影子,作者首要表明的是对一代明史严肃的看法,仍然是“断送江山八股文”。
二是有关高启文祸的描写,实际也包含了对朱元璋迫害文人的针砭。第三十五回卢信侯私藏《高青邱集》一案,金和跋说:“《高青邱集》即当时戴名世诗案中事。”胡适则认为是指清雍正间刘著私藏顾祖禹《方舆纪要》事,也许是对的,但是,书中第八回写枕箱的案件,早就有了蘧公孙冒名刊刻箱中《高青邱诗话》骤享大名的描写。这两件事应当联系起来看。不排除影射当世文祸的成分,但是,认为这仅仅是影射当世而与明初诗人高启之祸没有任何实际的联系,是说不通的。高启毕竟是历史人物,他被明太祖枉杀,著作在后世不禁而禁,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高启才华横溢,作为明一代诗人之冠,他的死为千古痛惜,说到明诗便不能不说到高启,而且因此不难想到明朝自朱元璋发难,文祸也曾是空前的严重。所以,写高启直接正面的意义首先还应当是这一冤狱的本身,是对高启之死的同情和对“洪武爷”大搞文字狱的针砭。正是他制八股轻诗文,摧残了明初的文坛,造成“一代文人有厄”,满清统治者只是袭其衣钵变本加厉而已。因此,有关高启文祸的描写首先不是托明以写清,而是写明以讽清,不可误会。
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作者有关高启文祸的描写,用心似不仅在于揭露和影射,还有教人防范自保的用心。蘧太守说:“须是收藏好了,不可轻易被人看见。”庄绍光说:“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李汉秋先生说这是宣扬无伤而隐的主题(注: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纵览[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169.),自全书大处观之,是完全正确的。但大祸临头,要想“无伤”,作者亦深知不能不有所作为。所以他写上述两案中当事和有关联的人各都能团结起来,与告讦者斗争,与官府周旋,或者化解无事,或者“反把那出首的人问了罪”。作品称赞为蘧公孙解释困厄的马二先生为“斯文骨肉的朋友,有意气!有肝胆”;写庄绍光面对缇骑为卢信侯担保,“遍托朝中大老……把卢信侯放了”;卢信侯则临危不惧,自称“硬汉”,不肯带累他人。作者的意思似要写出各类与文祸作斗争的榜样,这在朝廷日以杀人焚书为事的清中叶是有现实政治意义的,而对于明代文祸就是总结历史的教训,二者不可分割。
三是关于“宁王之乱”和朱棣“靖难之役”的评论,主要有以下文字:
(娄)四公子道:“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王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每常只说:“自从永乐篡位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第八回)
邹吉甫道:“小老还是听我死鬼父亲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的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又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第九回)
杜慎卿道:“列位先生,这‘夷十族’的话是没有的。……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萧金铉道:“先生,据你说,方先生何如?”杜慎卿道:“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第二十九回)
“宁王之乱”和“靖难之役”是明史大事。作者借人物之口发为评论,虽小说家言,但此等大事,出自一位严肃作家之手,却不可能是纯然的游戏笔墨,而是包含对明史一代政治的认真思考。这些出自各种人物之口的话看似矛盾,其实互文见义。大致说来,作者以为皇帝无所谓正统僭闰,不过胜者王侯败者贼,论定其功过,一在于他是否使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二在于他是否使政治一统,国力强盛。永乐没能做到前一点,所以不如“洪武爷”;但是他做到了后一点,所以比起“建文软弱”来总还是好的。在永乐还是建文谁做皇帝这类问题上,做臣子的可以完全不去管它,只论天下“大事”。方孝孺“讲那皋门、雉门”,“迂而无当”,正就是梁启超所说“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一类人,明朝的天下就断送在他们手里。这既是对明史的直接评判,也有抨击道学八股的意义。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假托明代并不只是一种手法问题。鲁迅说:“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林盖尚有明季遗风……”(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固然带来假托的方便。但是,吴敬梓却不仅在创作的形式而且在内容上恰当地利用了这一方便,上下求索,探讨了八股取士制度与明朝一代兴亡的关系,以小说对明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入的反思。这虽然不是作品的中心,显示的史识也无多卓越之处,但作品内容是一个客观存在,研究者不应忽略。如前所述,假小说以作这类反思探讨的还有与《儒林外史》先后成书的《女仙外史》、《歧路灯》,说明清中叶屈辱于满清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不忘前明历史教训,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收稿日期 1999-01-10
